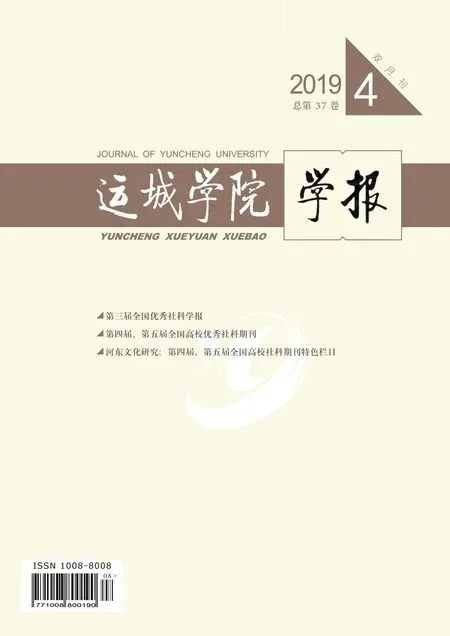柳宗元《永州八记》对山水游记的开创
于 成 君
(山东中医药大学 宣传部,济南 250355)
中国古代的山水意识产生较早,但山水游记产生较晚。早在先秦,孔子就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明山水已经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走下神坛,成为审美对象。东汉的马第伯在《封禅仪记》中第一次用散文的语言,真实、具体、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东岳泰山的风貌。[1]37但在此之前山水描写只是作为背景出现,并未独立成章。山水诗最早在魏晋成熟,在唐朝形成了山水诗派,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诗歌成为山水描写的独特载体。直至中唐时期,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出现才使以散文为载体的山水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此之前,晋宋地记对山水的描写以及六朝行纪对游踪的记写,都为山水游记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柳宗元之《永州八记》是山水游记的开创,是山水游记史上重要的一笔。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对柳宗元山水游记赞赏有加。
《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钴鉧潭记》《小石潭记》《小石城山记》八篇,作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前四篇作于法华寺,后四篇作于作者居住愚溪期间。这八篇作品,描写的大多是眼前的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或写奇山怪石,或写深潭游鱼都是形象鲜明,深入人心。八篇游记以游西山始,引出以下几处美景,一景接一景,让人目不暇接;虽非作于一时一地,但经作者的巧妙组合后,毫无衔接之弊,一气呵成。八篇游记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在此,笔者将从形式体例的开创、佛道玄理的结合、山水景物的特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总结柳宗元对山水游记的开创之功。
一、形式体例的开创
任何一种文体的成熟都要伴随着与之相应的形式体例的完善。唐律诗的成熟离不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对格律、音韵等形式的探索,宋诗摆脱“诗庄词媚”的藩篱独成一派也离不开苏轼、李清照等人对词境、词格的开创之功。同样,山水游记形成也必然有其形式体例。
首先,应该对山水游记做一界定,山水游记具有散体性、真实性、独立性三个特点。王立群指出“游记作品界定在散文领域是从众多无争议的游记作品中归纳出来的,它毫无疑问地排出了赋体、骈体”[1]18。这就点明山水游记是散文的一种,虽然历朝历代的文体形式中也有对山水和游踪的详略描写,如屈原的《离骚》《哀郢》《涉江》以及王勃的《滕王阁序》,但并不能将它们归为山水游记。另外,山水游记必须是作者亲历所见所记录的一种真实之景。“游记文献是以真实的旅游、游览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技术内容的真实性”[1]21。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亦是记录游踪的优秀散文,但由于所及之景之事出于作者的主观创造,因此也不能将其归为山水游记。最后,“我们所言的游记是指独立成篇的作品,因此那些仅包含部分描写山水片段的文字自然不能视为游记。”因此,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都不能归为山水游记。《永州八记》都具有山水游记的以上三个特点,以《使得西山宴游记》为例。整篇文章以散文的语言和笔法,描绘了“自余为僇人”后发现西山、游览西山、流连忘返的整个过程,简略并完整,其中西山之景是作者笔下独特的不依附于人事的一景,有其独特的欣赏价值。
其次,应该明确山水游记的要素。王立群指出“游踪、景观、情感是山水游记内在基本要素”[1]18。游览名山大川,记叙行踪、描写景物、抒发情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成文的一条重要路径。继承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诗文都将山水景物描写作为抒发情感的背景,柳宗元却对此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增加了山水所占的篇幅,全文围绕宴游之乐展开,大多在结尾中抒发情感,以至于“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因此,柳宗元笔下的景观大多明丽清新,使人读后犹如身临其境一般。观山之景如“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观鱼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当然,柳宗元在文中也有抒发其苦闷心情的只字片语,如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并自比“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就连部分景物也沾染了其苦闷的情绪,“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但柳宗元的创新在于他将情感作为山水游记的要素之一并引入了游踪、景观两要素重点叙述,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在这一点上,柳氏继承了陶渊明的思想,在山水田园中寻找一得之乐,并取得了突破“从而在散文领域中开创了山水游记的新途径”[2]154。
二、佛道玄理的结合
(一)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其对知识分子本身、文学形式、艺术欣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在意识形态上实行儒佛道三教合一,使得佛教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佛教对于知识分子的创作和心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哲学玄理表现在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已变成恬淡宁静、物我两忘的山水诗。王维是盛唐山水诗的代表,也是佞佛的代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空灵意向的背后是参透玄理的机智,亦是将矛盾心态隐藏至不易察觉的表现。佛教对于散文创作的影响即表现在柳宗元山水诗的创作上。
禅宗在唐代分为两个派别即北宗禅和南宗禅,其代表人物分别为神秀和六祖惠能。据说五祖弘忍在挑选接班人时,要求弟子们写实表达对佛教禅理的理解。神秀诗作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诗作为:“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尘世本无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便体现了后来成立的两派的基本观点。北宗强调“渐修”,南宗强调“顿悟”。[3]北宗一派在初唐和盛唐兴盛,中唐以后社会的动乱和民间的疾苦使人们更加依赖于佛教,但痛苦的修行已经不符合人们想要“立地成佛”的心态,于是南宗崛起。柳宗元生活的时代正是南宗兴起的时代。南宗的核心观念是“顿悟”,就是内心本来就是空,外在世界本来也是一个空幻的假象,所以在心里面做到“无念、无住、无相”。[3]21
《永州八记》中在景物描写的同时会掺杂部分佛教玄理,体现了南宗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由陈述发现西山为始,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为终。作者在游览西山美景时,产生“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之感,这便是一种“顿悟”,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同时,排除杂念、忘却痛楚,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从而那种“为僇人”的自卑感和“恒惴栗”恐惧感消失殆尽。在禅宗的这种“无念、无住、无相”思想的影响下,他笔下的景物也仿佛无所依托、自由自在。“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小石潭记》)“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颺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
柳宗元佛教的态度与韩愈不同。韩愈全面批评宗教狂热,冒着被贬的危险写下《谏迎佛骨表》,柳宗元不把佛教看作洪水猛兽,鼓励它与中国同化的道路。[2]222他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初来永州,无家可归,是法华寺的僧人们收留了他,他在法华寺居住的几年中与僧人们相处融洽,写诗作对,再加上年迈的母亲也信佛,使他专心研究在长安期间不曾关注的佛学,从而获得心灵上的安慰。柳宗元佛学思想在山水游记中的体现可谓独具匠心、别开生面,与王维在山水诗的创作上贡献等同。由此使佛学渗透进散文的创作领域。
(二)道教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于《永州八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八篇文章中很多语句带有《老子》《庄子》的痕迹。“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之句与《庄子·天道》中“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有密切联系。“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之句与《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有密切联系。
1.“天人合一”思想
柳宗元在游览山水诗,将对山水的审美与道家哲学体验相融合,形成“天人合一”的完整境界。在《使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登上西山,所见“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其中“特立”二字体现了西山的与众不同,而在此之前无人认识到它的价值。柳宗元将西山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审美个体,立于与人平等的地位,这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而后,“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正体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同样,《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亦体现此观点,不作赘述。
2.“小大之辩”
在道家思想中,个人为小,宇宙万物为大。相比偌大的虚无宇宙,个人的情感都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减轻痛苦无我两忘。
《庄子·秋水》指出“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以此来关照人生,不难看出,从柳宗元个人角度来看,青云折翼,贬为僇人,这件事当然大得不得了;可是与悠悠的历史长河相比,或者从无垠的天地宇宙角度来看,个人的仕途得失便不算什么。不过是沧海一粟,渺小得不值一提。[4]运用此种思想来看待自己的得失,才会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之感。
三、山水景物的特写
(一)情景交融的思想境界
柳宗元在描写山水景物时并非像谢灵运一样绞尽脑汁模范山水,力求还原景物的原貌。而是移情入景,追求一种情景交融的思想境界。在《小石潭记》中作者写道:“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并非是小石潭处的景物真的令人不寒而栗,而是因为景物的欣赏因人而异,柳宗元被贬后带着一份孤独悲愤的心情欣赏,自然使山水染上灰色。正如元好问所说:“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带着一颗“寂寞心”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中失意的臣子之一,在这之前他家道中落,饱尝人间冷暖但始终怀着一份进取之心,他学识广博,力图在政治上谋得出路,重振家门。“永贞革新”可以说是柳宗元人生的转折点,仅仅几个月,他感受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落差。德宗在王叔文的支持下企图以一己之力颠覆宦官专权的政局,启用初出牛犊大胆改革,柳宗元与好友韩愈、刘禹锡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当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洛中冯韩七中丞吴兴口号》)正体现了意气风发得意之时的场面。事与愿违,改革失败,“二王八司马”都受到迫害。柳宗元收到了难以忍受的屈辱和压力,反对派散布谣言,众口铄金,在一些人心目中他甚至变成了“怪人”。而柳宗元并不像刘禹锡那样心胸豁达,流落江南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钻研民歌,他的愤懑在心中郁结,倾诉而出便是对反对派的痛击,在他的文章《三戒》《蝜蝂传》中清晰可见。山水游记成了柳宗元排遣苦闷的唯一窗口。“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所谓兼济与独善的相互补充,然而这互补的充分展开,使这种矛盾具有一种时代、阶级的特定深刻意义,却是在中唐以来的后期封建社会。”[5]
《使得西山宴游记》可谓八记之总纲。作者开篇点出“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表明在游西山之前,游而不能乐在其中,心中苦闷,而在在此之后则“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似乎心中的愤懑以减轻不少,游西山是作者心情转好的开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几天后所作的《钴鉧潭记》中,作者便指出黑暗的统治导致民不聊生。民“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而“既芟山而更居”。《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则采用象征的手法,借“唐氏之弃地”来表现自己才华卓越却被世俗摒弃的悲剧命运。并在结尾处大发感触“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在《小石城山记》作者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永州之地虽然景物美不胜收,但难敌寂寞之情,作为一位儒者,作者更希望以一己之才“兼济天下”而非将才华淹没在远离京城的蛮荒之地。
按照王立群的说法“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的感情抒发主要采用融情于景与由景入情两种方式。”[1]126
融情于景者如《小石潭记》,全文写了石、树、鱼、溪四种景物形象,都透着一种“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之感。并非是景物自带的情感而是作者融情于景。小石潭地处偏僻荒凉之地,无人问津,因此这里的景物只是一种奇美,并非常人能够领会。这里的石头奇形怪状,潭水清澈,游鱼如“空游无所依”,树木参差不齐,溪水“斗折蛇行”,都奇特无比。写石潭之幽凄也是写心境之忧愤,文中虽无一字一笔写心情,读来却能感受到作者忧愤之情在心中。
由景入情如《小石城山记》。全文分为两段,第一段写了石山的奇特之景,是独特的景物描写;第二段借小石城造化天工否定造物者的存在,表达了鲜明的无神论思想。此段论述由景入情,带有鲜明的哲理性过渡自然,体现了山水游新的特色,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景物描写的特色
柳宗元山水游记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描写的自然之美。山水游记要求在游踪中描写景物,如果说记叙情感是全文的骨架,那么自然之景的形象描绘就是全文的血肉,而柳宗元在这一点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描写自然之美时“动与静的自然结合,虚与实的巧妙幻化,形与色的无间构形,都通过他精湛的笔墨展现得淋漓尽致”。[6]
1. 动静结合
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景物动静结合得十分巧妙。动则奔腾而下“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静则千奇百怪“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动静相宜是自然之态,而能描绘得如此吸引人唯柳宗元能做到。
不仅不同的景物动静相异,同一景物也有动静不同的描写。叙述袁家渴之草木,静则“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动则“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颺葳蕤,与时推移。”形象地写出了草木在风中的形态之变。
2. 虚实幻化
《永州八记》多是描绘的实景,但亦有虚实结合巧妙的描写。作者登上西山所见之景为:“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此为实景,但虚写西山之高峻险拔。正如是所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此山中”。
描写小石潭潭中鱼时刻画为:“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实写游鱼姿态,虚写潭水之清澈见底。虚实幻化巧妙得当,游人只观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的自由之态,实际上是因为潭水清澈,“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的缘故。
3. 形色构形
柳宗元描绘山水时强调形与色的组合关系。形,即山水景色的空间构造;色,即柳宗元山水游记体现出来的绘画美,由色彩和线条组合成妙不可言的山水图。[7]在景物的描写中柳宗元强调“以色聚形”。“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白砾”之白,草木之青,花之艳美,各色草木齐聚,使画面明媚秀丽。
柳宗元善于写景物,或是将不同景物依次排列描写,或是虚写同一景物的不同形态,都能物尽其态,自然天成,达到形与色的完美统一。
四、结语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山水游记散文的开创。《永州八记》不仅对永州地区的八出景物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而且结合超然物外的佛道玄理对自身怀才不遇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艺术手法的运用出神入化,不着痕迹,语言亦有一种动人的感发力量。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世遭遇融入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赋予山水景物以灵性和悲情色彩,同时融合佛道玄理,赋予了山水游以理性的色彩,提高了山水游记的审美价值,不愧为山水游记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