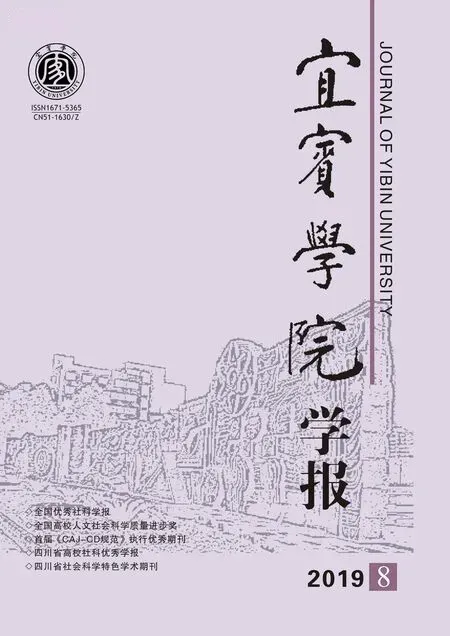唐君毅对罗近溪思想的诠释
李慧琪
(台湾“中央大学” 中文系,台湾 桃园 32001)
唐君毅先生对于中西哲学都有深入研究,其中在中国思想的宋明理学部分,往往能循着思想承继的线索,呈现出整体的思考,并道出各家特色。而针对明儒罗近溪的学问,唐先生于《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等著作都有论及,但比较完整讨论的文章主要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文中对近溪学的特点,以及其在本体与工夫的主张,都有精要的说明,特别是将近溪置于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王学的系统中,突显其特殊性,对于后学研究近溪思想极具启发性。
牟宗三先生曾言,顺王学的发展,只剩下光景的问题,即“如何破除光景而使知体天明亦即天常能具体而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1]290-291,因此牟先生便以“破光景”为近溪学问最大特色所在,重在体现道体之顺适浑沦、当下即是,而显示出一种无工夫的工夫。是故,虽然牟先生也以为近溪学之所以“清新俊逸,通透圆熟”的原因在于“本泰州派之传统风格”“特重光景之拆穿”与“归宗于仁,知体与仁体全然是一,以言生化与万物一体”三点,但能表现近溪学最特殊风格就在第二点,所以牟先生说:“人或以归宗于仁,以言一体与生化,为其学之特点,此则颟顸,未得其要也。”[1]288,291但唐先生正是倡言近溪之求仁、生生义,以此为近溪宗旨。有关唐、牟两先生对近溪学的不同看法,前人已有讨论,如杨儒宾与吴震先生皆指出唐、牟两人从不同方向立论,但比较支持唐先生的意见,以为破光景仍须以求仁为基础;[2]194-195[3]12谢居宪先生认为两人对近溪的意见并非截然不同,然各有不足,如唐先生未能掌握孝弟慈的内涵,牟先生减少了近溪学的丰富性;[4]李瑞全先生则从近溪是否算是圆教的面向,来比较唐、牟两人的不同评价。[5]而本文用心主要在更细致地梳理唐先生对近溪思想的理解与判断,除了呈现唐先生诠释近溪思想的内容与特色外,也藉此提出一些掌握近溪之学值得注意的环节。
一、 近溪论本体:即生即身言仁
对于近溪学问的特色,唐先生主要是顺着阳明学的发展来理解,其认为同为阳明学派,近溪学之特殊精神在于“直接标出求仁为宗,本‘仁者人也’之言,而语语不离良知为仁体之觉悟”[6]419。而自孔子重仁以来,后学对仁可有不同的体会,唐先生指出近溪言仁之方向便在于“即生即身言仁”,这也是其思想的第一义。[6]420如此,便可给出掌握近溪对本体的理解的一条线索。
首先,就“即生言仁”来说,近溪曾言“善言心者不如以生字代之”[7]121-122“夫心,生德也,活泼灵莹,融液孚通”[7]34,故近溪是从“生”来体会心之所以为心的意义,此以“生”言“心”的想法,反映出近溪认为“生生”才是对本体最适切的掌握,因最能显出本体作为造化之机的那种活泼的创生性。从天地万物到吾人视听言动,从往古到来今,无不是表现本体生生不已的作用,若能复此人心原有之生生义,自然天地物我全打合通贯成一块儿,纯是一片生机。所以说“生”是“心”最具体而生动的指点,能复其生机便是心的意义。而“仁”的内涵也是从“生”来理解,所谓“生之谓仁”[7]34“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7]31所以无论言心言仁,近溪皆重在生生义,人心即仁心即生生之心,皆显示本体无间断地运行遍润义。
但诚如前言提到牟宗三先生以为从归宗于仁、一体与生化等来言近溪学,并不能显现其特点,唐先生自己也说“以生生说仁,以灵明说知,固是宋明诸师一贯之教义”[6]419,因此唐先生进一步点出近溪特殊处之一,在于“其于天道之生生,天道之仁,则恒连乾知坤能之义以言;并以人之良知良能,即乾知坤能,而善论天心”[6]419,也就是说,近溪透过乾知坤能,把天道之生生、天道之仁,与人之良知良能贯串起来:
易传之言乾知,盖初自天地万物之交感上见……凡物有所生,必先有所感。凡有所感,必有所通。凡有感通,以今语言之,即皆有作用之相投映相表现。此相投映相表现,即相明。则天地万物交感不已,即见一大明之终始不息。有明即可言有知(如常言感觉之知,即言物之作用表现投映于吾人之感觉),则统体以言交感之天地万物,即可说为一统体之乾知所运之地矣。吾人于此,如复能更进而深体吾之良知灵明,涵盖弥纶于自所感通之天地万物,而未尝忍与相离之义;则匪特人伦相与,不在良知之所感通之外,且盈天地间,鸟啼花笑,草长莺飞,山峙川流,云蒸霞蔚,凡吾人之闻见之知之所及,皆吾之良知之感通所及……吾人于此,如复能不自躯壳起念,以私据此良知之流行为我有,再由之以识我与天地万物共同之本根,则可会良知即乾知之义矣。而万物之生而又生,即有所成,故乾知即统坤能。乾知为良知,坤能即良能。又万物之生,依交感生。即其生意,原不容间隔,周流贯彻,浑然一体。生意之周流贯彻之谓仁。则充塞天地,上下千古,唯是一统体之乾知不息之大明,终始于其间,亦即一坤能之终始于其间,仁体之周流贯彻于其间矣。[6]420-421
在此段中,唐先生对于天道生生不已之义有很细腻的分疏,其言天地万物之生化并非各自独立之事,而是统体间的感通作用。所以说有所生必先有所感通,即“皆有作用之相投映相表现”,换句话说即“相明”,而从“明”便可言“知”。好比吾人一般之知,是对于对象物之作用的感觉,“乾知”便是从天地万物相感、相明不已中见一本体的感通。而“坤能”从万物生化必有所成上说,“仁”则从天地万物交感之周流贯彻不息上说。故统言之,天地古今只是一乾知、坤能、仁体之流行活动,其内涵是一。而人亦是天地父母之所生,如唐先生言:“天地之生生之仁之流行于我,而命我生,故我即以此生生之仁为性;当我之既成,即将有以继天地生生之仁,以有所生,而有所仁。”[6]422故吾人所拥有之良知灵明的作用非一般之知,盈天地间无不是良知感通所及之处,天地感通生化不已,吾人良知之感通亦随之不已。因此若能秉除私欲限制,发挥良知的作用,则可识得良知通乾知、良能即坤能,而与天地生生之仁浑沦为一,如此“通天地人,唯是浑沦之一生,唯是浑沦之一仁,亦唯是浑沦之一心。”[6]424由唐先生的诠释可看出,近溪藉由乾知坤能、生生之仁将人心即天心,人心之知即天心之乾知之义表露无遗,不但清楚呈显心体的超越义、创生义,而且不仅“以生生说仁,以灵明说知”,更将其通贯,展现出良知为仁体之体悟。
其次,唐先生还点出近溪另外一条“即身言仁”的路向,强调回归吾身来体会仁的意义:
其(近溪)释仁,直引孟子仁者人也之言;言性则特引孟子“形色天性也”之言。盖人之一身,视听言动,浑是知能充塞,亦即仁体充塞。故人即是仁,形色即天性,而圣人亦不过能真作一个人者。[6]438
近溪以为人之一身,不仅是血肉形躯,更是知能仁体之所充塞。如前所述,吾人秉天地生生之仁而生,良知良能通于乾知坤能、人心通于天心,关键在于是否能使人身形色全幅实现人的价值,散发生生之仁的光辉,所以说“欲知此一人之身,则当知此生;欲知此生,则当知此仁。人之所以为人,即仁也”[6]389。而圣人与常人之不同,也就在“能真作一个人者”,若真能呈显身为人之意义所在,便如近溪所言“盈天地之生,而莫非吾身之生;盈天地之化,而莫非吾身之化。冒乾坤而独露,亘宇宙而长存。此身所以为极贵,而人所以为至大也”[7]12。因此,仁不远人,吾身便是仁的体现。
而这种大人之身的想法,并非止于吾人一身,唐先生更征引近溪“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以为肝肠;通天下万世之休戚,以为发肤。疾痛疴痒,更无人我,而浑然为一,斯之谓大人而已矣”[7]7之言,指出近溪是“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说,大人者更能“合家国天下,以万物万世为一身”[6]388,即大人者不止于己身,能超越时空限制,于此身展现无穷的意义。唐先生并解释大人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在于“此身之生,与其外之天下人之生、天地万物之生,原互相感应孚通,而不可二。此即昔贤所谓仁体之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6]388-389由此可知,即身体仁虽说是从吾身体证,亦能通贯家国天下、天地万物来体证,甚至愈能感通于外,愈能完成此身的意义。
是故,由“即身体仁”这条了解本体的进路可知,近溪不是把仁体当成高悬的存有、认知的对象,而是在每人身上就可探求着落,展现仁体无穷的意义,所以说“许多道妙,许大快乐,即是相对立谈之身,即在相对立谈之顷,现成完备,而无欠无余”[7]129。而这也就是为何如唐先生所说,近溪喜从孩提赤子之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良知良能、家家户户同赖以过日子之孝弟慈,或不待思虑安排之一言一动上,来随机指点仁体之真实,[6]419此正是即身来体验仁体之平常、自然,从最切身之生活处来体会。如此言本体,特显本体的内在义、当下义,即表示本体并非超绝挂空的,就平铺遍在于眼前所见的天地万物、日用伦常中,不断呈现其生机作用。
二、 近溪论工夫:复以自知
既然近溪强调在吾身所处的当下情境中体证天知天能、生生之仁义,就必须要下工夫,而工夫就在“复以自知”。所谓“复以自知”,即是“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7]64,唐君毅先生对于近溪“复以自知”的工夫,亦有详尽地展开:
然心之所以为心,虽必待复以自知而后知;此自知,亦非另有一心以知此心。盖所谓复以自知者,即此滞形迹之心,一念自形迹超拔,而逆知“心之自然之外用,而有之滞于形迹之知”所本之天知而已。盖心由自然之外用,而滞于形迹,原是由于天聪天明,不能不明通于物。即人原来之天知,不能不顺而外出。顺而外出,乃滞于形迹,不免滋生物欲。故又不可不逆此自然之外用,而滞迹之势,以复其本来。然则逆知之为逆,乃对滞迹之势而为逆,非逆其聪明之用也。此所谓逆其滞迹之势者,不外使此顺而外出之天知,自迹折回而自照,不复陷溺于物欲,乃得更显其天聪天明之大用耳。故人之逆知,虽逆乎“自然顺出之天知”之“滞迹”;正所以迎迓天知之大用,而顺承之。夫然,故此逆知,虽人为,亦即天之所为。盖逆知既所以迎迓天知之大用,而顺承之;是即天知之大用,自求继复,而方逆知。故逆知者,即“滞于形迹之天知”,自超化此“形迹之滞之知”;亦即是“本无形迹之滞之天知”之自显。[6]427-428
唐先生首先提醒“复以自知”非另有一心知一心,而是心知其自己。而心何以需“复”?这是因为心原有之天知不是高高在上,必然要求通于物,便自然顺而外用,如此就有滞于形迹、滋生物欲的可能,因此需做工夫以回复心之本然。而复的工夫可从两方向说,就逆其滞迹之势,从中一念超拔而折回心原有之天知而言“逆”;由其复返亦是天知之自显,是迎迓天知之大用而顺承之而言“顺”,于是不论从逆说、从顺说,皆是表现天知之自觉。若能实践此“复以自知”的工夫,自能复见吾人本有之天知天心,重归生生不已的作用,人便能成其为天人。
唐先生曾言龙溪谓工夫有两途,“由工夫以复本体之渐入,及即本体为工夫之顿入”[6]388,而近溪也有类似之说,以为学问有以用功为先,有以性地为先。①而上段所言“复以自知”的工夫和此处所言“以性地为先”,自然是属于“即本体为工夫”这种先悟本体、先识大本的工夫路线。但唐先生进一步指出“此所谓性地为先,即从现在言动平淡、意念安闲处,下工夫,更不别求工夫效验之谓。而此所指者,则唯是于日用常行处下工夫。”[6]388因此就如同上一小节提到近溪喜在日用中指示仁体,工夫亦是常于日用中指点。如以孩提赤子为例,唐先生言近溪从赤子对母怀之依恋中,道出不容已之仁,这种自然而然的表现,正是常人欲作工夫者可深思的,其实天道生生不已的运作,正也如同赤子的反应一般,随机感应,无所造作。虽然赤子与圣人终究有别,如唐先生所说“赤子唯未尝经化为常人一段事,故其不识不知之天知,为先于思虑分别之人知;其任天而动之天能,为先于依意欲而造作之人能。圣人之天知,则化滞迹之思虑分别之知,以成后于人知之天知;化不免于逐物之意欲、与造作之人能,以成后于人能之天能”[6]436,赤子并无自觉而复其天知天能的过程。然人可藉由赤子之心的表现,帮助体悟天心,所谓“赤子之心沕穆,可止常人之滞迹之思虑;赤子之心浑沦,可以止常人逐物之意欲”[6]436,从赤子深微无分别之心,正可提醒人从一般思虑意欲中超拔,复归生生之心。
不过实际从事道德实践时,往往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刘蕺山曾点出王学的流弊:“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8]278从中便可看出若未对良知有真正体悟、下真切工夫所产生的毛病。因此唐先生在指点近溪工夫特色时,除前所言“复以自知”义之外,还说道:“其言工夫,则破光景之妄,以言灵明之不可离仁而炯炯,并言悟得仁体,当敬畏奉持之。”[6]419其中“破光景”之说,正可面对“荡之以玄虚”的问题;“敬畏奉持”之说,则可解决“参之以情识”的情况。
关于“破光景”的工夫,其实也是出自近溪个人真实的悟道体会,《明儒学案》曾记载其因执持“一念耿光”而造成心病一事。②按理说“复以自知”的工夫应即于日用平常,依所通感之物不断的作用,但如果这种工夫变成“一往之逆复”,便会中断原本自然的感应,而之所以会有此情形的原因,唐先生解释:
如修道者,专用停止其心,使之不动之工夫者,惟恐其明之陷于物,而不肯用其明以通物;或自惜其明,而欲积聚此明,握持此明,则为绝自然之感通之事。此中,由自惜其明,而积聚之明,握持之明,则成为纯粹之逆明。此逆明亦是一种自明。然此自明,唯是以灵光反照灵光,于此即构成一片光景。在此光景中,人之灵明自玩其灵明,自享用其灵明。[6]431-432
由此可知,由于修道者把捉住良知灵光,不再外用以通物,只是以此自明反照自身,如近溪所言“回头只去想念前段心体”[7]94,执泥那“心中炯炯”[7]98“心中光光晶晶”[7]99,使得良知不复为良知,灵明不复为灵明,而成为一片光景。然诚如唐先生所说“盖此种纯粹之逆明之所以可能,仍本于自然明通之用之不息”,只是一旦有所执持,反显一己之私,使得良知灵明不再感通于物,强制压抑久了,则“构成一种灵明之胶结与凝固”,如此一来,原本生机变为死机,灵光反成鬼窟。[6]432因此学者工夫必须破光景,也就是不自惜自持其灵明,让良知感应之机时时作用流行。
另外,若能复以自知,则本体呈现,但唐先生也指出近溪于此还特别提醒“恭敬奉持,毫忽不昧”之义:
近溪言悟得仁体以后,当恭敬奉持,恒存戒惧……重敬之义,宋明儒大皆有之;唯言之罕能如近溪之警策动人。知悟得仁体以后之须恭敬奉持,故仁体非可把握占有。悟得仁体以后,不自瞒昧,乃能真正致良知;而坦坦平平,勿忘勿助,不着矜持之意……近溪言悟道,即在现在日用平常之言动中,悟后之工夫,则在于此道之恭敬奉持,不自瞒昧,平淡安闲,以顺此道。此则在近溪之答人问语处多可见。故曰“前此大儒先生,其论主敬工夫,极其严密;而性体平常处,未见提掇,学者往往至于拘迫。近时同志先达,其论良知学脉,固为的确;而敬畏小心处,未加紧切。故学者往往无所持循”。前语乃评宋儒,后段语则评明儒。近溪之论工夫,则可谓善于自性体平常处,提掇良知良能,而又能知敬畏小心义者。此其所以别于龙溪,而在泰州学派中最为迥出者也。[6]440-441
虽然近溪工夫以性地为先,强调先悟得仁体的本质工夫,然而对此先一着工夫有所把握之后,近溪还强调“恭敬奉持”。一般来说,虽然宋明儒者皆不否定持敬工夫,但此通常是伊川朱子学较关注的部分,故唐先生以为近溪之重敬,不但其言“警策动人”,也是近溪有别龙溪、泰州学派之特殊处。而近溪主敬之说之所以“警策动人”的原因,应在于有着真切的实践感受。虽然近溪总在日用平常之视听言动提点本体,能显出本体之自然作用,然平淡安闲中实有绝大的工夫在里头,如同近溪所言“岂独人难测其浅深,即己亦无从验其长益”[7]189,所以很容易有所把捉偏失而不自觉,因此近溪以为言良知就其敬畏小心处不可不紧切。此外,由于近溪言敬是从悟得仁体后说,也不至于流为空头的持敬。
三、 诠释近溪思想的特色与反省
综上所述,透过唐先生对近溪所言本体与工夫内容的诠释,可知近溪对本体的体会着重生生不已的创生义与平铺遍在之当下义;对工夫则特别喜欢从平常中指点,强调在日用中“复以自知”,并从“破光景”与“敬畏奉持”两方面来避免工夫之弊。这些说法,都有助我们对于近溪学的重要主张有基本掌握。因此,虽然牟宗三先生认为近溪学须从“破光景”来理解方得其要,但唐先生从“求仁为宗”而来的诠释,看似未能直接突显近溪顺王学发展而来的问题意识,却亦能从本体与工夫两方面,呈现其学问关怀,显示近溪透过逆复吾心本有生生之仁体,以破虚幻光景,真正即于日用应物中,显仁体不已的作用,成就大人之身。故不论从“破光景”还是从“求仁”说,其实是一体两面之事,“破光景”来自真实的体现仁体,“求仁”终须破除本体的光景才能达至。因此唐、牟两先生之说,皆可表示近溪重视道体于日用平常体现之用心,若说以归宗于仁言近溪学是“未得其要也”[1]291,实未必如此。
此外,牟先生曾把光景分成两义:
良知自须在日用间流行,但若无真切工夫以支持之,则此流行只是一种光景,此是光景之广义;而若不能使良知真实地具体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而只悬空地去描画它如何如何,则良知本身亦成了光景,此是光景之狭义。[1]287
而从近溪“破光景”用词中,多指破除狭义的光景,即拆穿良知本身的光景,关于近溪破除广义的光景,即拆穿流行的光景之意,要从近溪言悟本体之后的恭敬戒惧工夫处较可看出。于是唐先生点出近溪重敬之义,反倒能帮忙补充近溪破除广义的光景的用心处。而且针对后人对王学流弊的反省,或是欲融合朱陆的想法,在唐先生所展示的近溪之学中,都有一些脉络可循,可再作进一步连结。
而从“求仁为宗”的线索来理解近溪学还可有一个意义便是,更清楚显示近溪思想上的传承,事实上,近溪的“求仁”不是重复前人旨趣,而是融合诸说展现自身特色。由于唐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往往会具备一个思想史的思考向度,让我们能了解各学者于学术发展间的位置,于近溪处亦然,因此当把近溪关于本体与工夫的想法放回思想史的脉络,更能显其地位。龙溪曾说:“罗近溪,今之程伯子也,接人浑是一团和气。”[7]286基本上近溪求仁之说就是继承明道,故唐先生说:“总观近溪之学,远承明道,以求仁为宗。”[6]442而其重敬之说,不仅是“未违宋儒主敬之教”[6]442,更具体的说,“即明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之旨。”[6]440除了承袭明道之外,近溪求仁的特色在于“喜于赤子之良知良能,家家户户之孝弟慈,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视听言动上,指点仁体”[6]442,这点则是承泰州学派而来,故唐先生也特别点出近溪与王学各派的关连,尤其是不同处、发展处。
因近溪属于泰州学派,自然受到心斋相关主张影响,唐先生就提到心斋所言“安身”“乐”之说,“为近溪即身言仁,以生生言心之说所本”[6]418,然唐先生也指出近溪进于心斋处。首先,虽说近溪于日用常行用功之说,与心斋父子重在日常生活中求安身格物无异,但“心斋言安身,初即只以一人之身为本;唯由其末之贯于家国天下,以言此本末一贯之学。而近溪则依此本末一贯之学,更‘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6]388也就是说,近溪更强调言身不能拘限于吾身,必须关联家国天下、天地万物才能完整。其次,关于“乐”的方面,唐先生认为近溪能点出“生之乐本于人之生,原即依于造物之生机,亦依于仁”,并言人能“透悟其心体性地之仁”而成就大人之身,[1]389这些都过于心斋父子说法。由此可知,近溪对于心斋“安身”“乐”之说,都有进一步的发挥。另外,还如前所论,近溪之重敬在泰州派也是其特色所在。
除了和泰州学派的比较,近溪与龙溪并称“二溪”,唐先生也常将两人对照,以为两人有许多共同处。如近溪强调透悟心体性地之仁,重视此心性之知能之复以自知这些主张,与龙溪重良知与一念灵明以悟本体之旨相通。[6]389且两人皆能发展阳明良知之义,近溪言人之良知良能即乾坤知能,“颇同龙溪一念灵明从混沌里立根基之语。皆阳明学之向上一着之推扩”。[6]442还有像彻底扫荡凡心习态、重当下用工夫、信得及圣人即在自己、悟良知之效等想法,皆与龙溪无异。[6]418-419而唐先生指出两人最大不同,在于“龙溪只言于此灵明上参究,而近溪则谓此灵明之心,乃浑融于吾日用生活之生生之中,唯于此见心体性地,方得免于光景心疾也。”[6]389-391唐先生认为二溪虽皆强调先悟本体,然悟本体之道还是有所不同,其关键就在于龙溪只参究良知灵明,然而由近溪个人悟道经验,以及教导弟子破光景之言,都可看出近溪对于从事道德实践可能有的问题感受更深,因此近溪将此灵明之心浑融日用生活之中,当机指点仁体,藉此避免本体流于玄虚,不能具体落实之弊。此外,唐先生更说到其实近溪重生生之仁之义,亦可顺龙溪心知空寂义引出。这是因为良知之灵明不只是可用空寂表示,既是灵明,必有所感而有所生,否则不足以称灵明,如此一来,良知当然也可从生生来表示,而生生不息之谓仁,所以亦可说良知即仁矣。[6]420凡此皆可显示近溪有进于龙溪处。
既说“良知即仁”,这也就是唐先生认为近溪发挥阳明良知学的地方。唐先生以为:“阳明言良知,固即仁者之好恶;然阳明既以致良知标宗,即不免下启龙溪重知而忽仁之失。近溪直下以仁智合一,语意乃复归圆足。”[6]442所以近溪从仁来说良知,可以展开良知原有的意义,避免“重知忽仁”的问题。而且唐先生也提到,近溪重在从日用中指点一不学不虑之仁体,这也是有别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义,并非重在善恶念上省察以存善去恶,而“重在直契一超思虑计较安排之本体为工夫”。[6]483-484只是这中间还有可再进一步思考之处,即之所以工夫要直契一超越思虑计较之本体,是因为工夫的最高境界还是要超越对治相臻至自然而然,那么近溪那种从赤子之心不学不虑、自然之知爱知敬来了解良知,从孝弟慈来指点工夫下手处的方式,其实正可表现对本体及工夫更圆融的理解。所谓“夫良知者,不虑不学,而能爱其亲,能敬其长也”[7]13,从知爱知敬来了解良知,可对良知有亲切的体会;又“知为己子,则自以慈相亲;知为己父,则自以孝相亲;知为己兄,则自以敬相亲”[7]82,从孝弟慈来做工夫,更显工夫之自然平常。然唐先生较着重从赤子不学不虑之知言良知的部分,对于从知爱知敬言良知之义便没有深论。而杨祖汉先生即是从知爱知敬这方向出发,并点出近溪此说不但能避免良知之荡越,更能透过孝弟慈让悟本体成为人人可做的工夫,甚至纵向来看,可让人更容易契入天道之生生;横向来看,配合《大学》的纲领,可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功,[9]如此便可对近溪学有更多开展。
最后关于近溪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其思想中的佛学色彩。黄梨洲在《明儒学案》曾提到近溪近禅的批评,亦言其“然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所谓鬼窟活计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阴界之呵。不落义理,不落想象,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10]3-4对于近溪学所受到的佛学影响,唐先生谈得不多,但也注意到此,曾针对近溪“一念迷觉”之说有过讨论,以为其说“近起信、华严、天台之迷觉一心之旨,归于翻迷即觉之教”[6]392,这也提供一条研究近溪思想可发展的向度,如古清美就曾从这个角度探究近溪学,认为“近溪学的特色其实是其求仁之旨中融入了佛学”[11]153。当然近溪学最终还是为了复知生生之仁,成就大人之身,还是儒学,但其思想与佛学之交涉,仍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结语
虽然唐先生对于近溪学的诠释,由于篇幅有限,内容不算全面,比如对于近溪在儒学经典上的解释特色等就无法论及,但已足以精要点出其学问宗旨与精神。透过“即生即身言仁”这条线索,可呈现近溪对于本体的理解,包含如何阐释生生之仁的意义,并透过乾知坤能,将人心与天心贯串起来,并提出良知即仁之义,以及即于吾身及生活中以显仁,并联结到家国天下、天地万物,以成就大人之身的无限意义。从中可知,近溪对于本体的体会可说是既超越又内在的生生之体、流行之体。而藉由“复以自知”这条线索,则可显示近溪对于工夫的主张。强调吾人需即于形迹,逆复吾心本有、不学不虑之天知,让心的作用能如孩提赤子般自然的感应表现。而针对做工夫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从“破光景”与“敬畏奉持”两方面加以解决。从中可看出近溪工夫属于先悟本体的本质工夫,又能避免王学的流弊。此外,顺着“求仁”的宗旨,唐先生还从学术发展脉络上,道出近溪对于前人的承继与发扬,和在王学中的特色。如其继承了明道言仁、言敬,阳明言良知,心斋言安身、言乐等说,又能进一步通贯推扩,特别是提出良知即仁之义,使知仁并重;其与龙溪虽有许多共同处,却又能让本体更具体落实。只是唐先生对近溪从知爱知敬言良知和近溪思想中的佛学影响的部分,讨论较少,但已可提供许多重要方向,供后人继续研究。因此,虽然唐先生对于近溪宗旨的诠释方向与牟先生不同,但只是切入角度的问题,仍能各自展现近溪学的特色。
注释:
① 师曰:“学问原有两路,以用功为先者,意念有个存主,言动有个执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众共见闻;若性地为先,则言动即是现在,且须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闲,尤忌有所做作,岂独人难测其浅深,即己亦无从验其长益。纵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趋彼矣,然明眼见之,则真假易辨也”(《盱坛直诠》, 189页)。
②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又尝过临清,剧病,恍惚见老人语之曰:‘君自有生以来,触而气每不动,倦而目辄不瞑,扰攘而意自不分,梦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则予之心得,岂病乎﹖’老人曰:‘人之心体出自天常,随物感通,原无定执。君以夙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结习,不悟天体渐失,岂惟心病,而身亦随之矣。’先生惊起叩首,流汗如雨。从此执念渐消,血脉循轨”(《黄宗羲全集》(八), 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