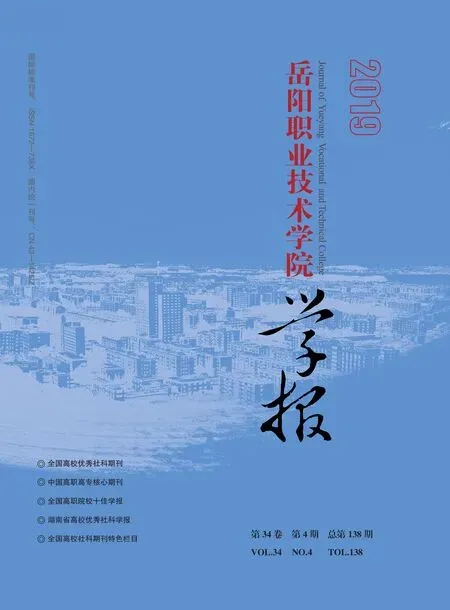社会角色理论视阈下李瓶儿的悲剧形象
肖婉莹 马克文
(1.国家开放大学 人文教学部,北京 100039;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李瓶儿时,认为她作为《金瓶梅》的主角,其性格缺乏真实。李瓶儿从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的凶悍、狠毒,变为对西门庆的善良、懦弱,性格具有矛盾性,缺乏合理性解释。但是从角色理论的角度来看,李瓶儿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不是叙事的断裂、角色的矛盾,相反,李瓶儿人物形象的塑造符合逻辑的层层演进,一切都围绕李瓶儿的“痴”展开。
李瓶儿的性格内核是“痴”,其性格的首要特质是懦弱谦和,温顺忍让,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奥尔波特的人格特质理论认为,特质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构成元素。首要特质,即一个人最典型、最有概括性的特质,影响个体各方面的行为。李瓶儿的“痴”,既指痴心,即对西门庆痴情入迷,执着坚持;又指无明,即为人处世愚昧无知,不明事理。佛教认为,贪、嗔、痴是“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为毒害众生出世善念中之最严重者,能令生命个体长劫受苦而不得出离苦海。[1]正如佛家所言,李瓶儿的“痴”使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均深陷苦海之中。李瓶儿识人不明,执著盲目。在面对不同的角色对象时,她对同一角色的角色认同程度并不相同,导致其看似矛盾的行为经常发生。
1 李瓶儿的角色认同和角色扮演
角色(role)一词来源于戏剧,指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现出的行为。角色理论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的“象征互动理论”[2]。他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动机,个体根据其社会位置而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而角色是个体对社会期望的反应。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进一步强化了个体角色的自我认定,并指出,行动者表现自己的方式是通过强化自我概念,将其展现为某种特定的客体。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依照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按一定的社会期望,履行相应社会职责的行为即个体的社会角色。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经常需要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即角色丛,亦称角色集或角色组。社会按照各类社会角色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符合角色期望的个体行为,将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许。因为所面对的角色对象不同,李瓶儿对同一角色的认同有所差异,因此角色扮演亦有所不同。李瓶儿自幼父母双亡,由遗传、血缘关系等先天因素所决定的先赋角色所起的作用较小。在几次角色转换中,只有西门庆之妻是她真正意义上的自致角色,即通过活动或努力而获得的角色。
角色认同,是指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其当时的社会位置和角色一致。一个人接受角色规范的要求、愿意履行角色规范的状况为角色认同。个人按照他人的期望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为角色扮演,以此来获得并感知他人的态度,完成作为自我的“客我”方面的构建。李瓶儿前期面对的是不负责任、只知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花子虚;又误信蒋竹山的挑拨之言,对西门庆死心,转而招赘了扶不上墙的蒋竹山,而他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有性吸引力,均无法与西门庆相提并论。李瓶儿对于前两次婚姻中的妻子角色并未认同,社会角色期待和她自身的内在需求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从而引发了巨大的角色冲突。嫁入西门家以后,李瓶儿严格按照贤妻良母的角色规范进行自我约束,结果反而爆发了更为激烈的角色冲突,最终导致角色失败。
李瓶儿在面临不同的角色对象时,角色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她前后行为的极大反差也反映了其对花子虚、蒋竹山以及西门庆的感情有所不同。
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1986 年提出的爱情三元理论指出,爱情应该包括三个主要成分:亲密、激情和承诺[3]。亲密包括热情、理解、支持、交流、分享等内容;激情通常是以身体的欲望激起为特征,主要指对于伴侣的性的欲望,并且对方可以满足其强烈的情感需要;承诺则是指决定将自己投身于一份感情并为了维持这份感情所做出努力。这三个成分之间深浅程度的不同组合可形成8 种不同的感情类型。而这三种成分则构成了一个三角形,随着每种成分强弱的不同,三角形亦随之发生变化。只有同时具备三种基本成分,才能称为爱情。根据三大成分在爱中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分为无爱、喜爱、痴迷的爱、空洞的爱、浪漫的爱、伴侣的爱、愚昧的爱以及完美的爱等不同状态。
花子虚对李瓶儿而言,是“无爱”的状态。他只是李瓶儿名义上的丈夫,不管是物质还是感情上,他都无法满足李瓶儿的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包括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等。作为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受尽了花太监的折磨染上了血崩之疾。虽则衣食无忧,人身安全得以保障,但花子虚终日流连在外,夫妻关系畸形变态,连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均无法满足。李瓶儿和花子虚并不亲密,是一种畸形的婚姻关系,激情和承诺更是无从谈起,这段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蒋竹山对李瓶儿来说,是先从“愚昧的爱”转为“空洞的爱”,最终到达“无爱”。李瓶儿对蒋竹山最初是抱有极高的期望,在她病重之时蒋竹山趁虚而入,其在不了解蒋竹山的情况下,仅仅在势不可挡的激情驱动之下便迅速缔结婚约。这种依靠激情来维系的感情很不稳定,斯滕伯格称之为“愚昧的爱”,具有较高的风险。之后,李瓶儿彻底看清了蒋竹山的真实面目,也认识到不管从经济条件还是个人能力方面,他都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帮蒋竹山还债之时,她便已经厌弃了蒋竹山,对他仅仅剩下保有承诺的“空洞的爱”。最终她对蒋竹山彻底失望,在“无爱”的状态之下将其赶走。不管是花子虚或蒋竹山,她连最起码的生理和安全需求都未曾被满足,更不用说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西门庆对李瓶儿而言,是先从“痴迷的爱”转为“浪漫的爱”最终达到“完美的爱”。李瓶儿对西门庆的感情,最初只有激情。刘晓林等指出,李瓶儿作为一个贵妇人,金钱、地位,她什么都不缺,所缺者,性也。找到西门庆,真如干柴烈火,欢娱之至,什么封建礼义廉耻,她全都不放在心上[4]。西门庆的外表和能力激起了李瓶儿心中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是“痴迷的爱”。在隔墙密约之后,随着了解的深入,逐渐发展为亲密,转为“浪漫的爱”。李瓶儿自认为找到了“三十三天之上的好丈夫”,多次主动催促西门庆早日娶她进门。嫁入西门家之后,李瓶儿终于在激情、亲密的基础上获得了承诺。西门庆家境殷实,既有责任心又有能力,事业成功,经商做官均游刃有余,充分满足了她的生理、安全需求,也满足了其对于归属和爱的需要。尤其是有了官哥以后,李瓶儿对西门庆真挚的感情和毫无保留的奉献也打动了西门庆。他对李瓶儿百依百顺、细心体贴,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支持、相互理解,这种感情在激情、亲密和承诺三个成分上均达到了至高峰——“完美的爱”。
由此,李瓶儿的个体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也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认同。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扮演中,她以贤妻良母的规范来要求自己,认同并且自觉内化社会对传统女性的角色要求,将社会的期望转化为自身的心理需要。
2 李瓶儿的角色冲突
一个人在与他人发生交互作用时,会出现个人的角色表演和他人对其角色期待的矛盾;一个人同时扮演一个或多个不同角色时,也会发生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即角色冲突,由罗伯特·默顿于1957 年提出。[5]默顿将角色冲突分为角色间冲突、角色内冲突和角色外冲突。李瓶儿从花子虚之妻到蒋竹山之妻,再从西门庆的情妇、西门庆的小妾,到西门庆之子的母亲,她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痴”人性格使其在角色认同和角色扮演过程中非但没有获得理想的家庭生活,反而爆发了激烈的角色冲突。
2.1 角色间冲突:“自杀”以明志
角色间冲突是指一个人所担任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的冲突。李瓶儿在花子虚之妻、西门庆之情妇、蒋竹山之妻等不同角色之间存在相互矛盾。
对于花子虚和蒋竹山,李瓶儿因为有大笔财富,经济上相对独立,再加之没有感情的投入,她对于“妻子”角色并不认同。在认清蒋竹山的真面目之后,她对这个狡诈且无能的男人彻底死心,但她并不愿听天由命,同时也明白自己所忍受的一切并不值得。她求助无门,但也不愿屈从命运,借机找玳安说动西门庆。而西门庆恼其另嫁,接连三日不入其房,这种羞辱亦是她始料未及的,她的自杀以歇斯底里的形式表达她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抵抗。她抗议西门庆、命运以及自身的生存处境,但因为对西门庆尚存留恋之心,注定不能成功地摆脱这一切。由此,在经历了西门庆的羞辱和折磨之后,她便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西门庆的权势、财富,可以保证她的安全,她也注定无法像以前一样逃离西门家,寻求新的角色。于是,李瓶儿便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将爱情奉献给了西门庆。
2.2 角色内冲突:母凭子贵
角色内冲突,是指同一个人在同一个角色内部发生的冲突。在西门家中贤妻和妒妇的角色,李瓶儿选择了前者。
假若妻子角色满足了李瓶儿对于爱情的需要,母亲角色则充分满足了李瓶儿的个人实现需要。在父权制文化中,保守的传统女性价值观认为,女性只有通过婚姻、母性和家庭生活才能获得自身价值,而母性是女性的最终成就。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中,李寅生等指出,几个女子唯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家里唯一的男主争风吃醋,每天挖空心思讨西门庆的欢心。有了孩子的女人,中心由丈夫转到儿子,没有孩子的女人则想方设法要怀上儿子来巩固其在家中的地位[6]。李瓶儿最先生育,因此西门庆对此极为看重。有了孩子以后,李瓶儿“母性”的欲望得以满足,其独立地位亦得到保障。她作为妻子要与潘金莲等众多妻妾分享西门庆,但作为母亲,她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保障。
2.3 角色外冲突:委曲求全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色扮演者之间发生的矛盾,称为角色外冲突。李瓶儿的角色和西门庆家其他妻妾的角色本身处于对立面,其他妻妾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纷纷处心积虑争夺西门庆的财富和宠爱。尤其是潘金莲,她嫉妒李瓶儿的美貌、财富、子嗣,于是对李瓶儿百般排挤,不仅言语诅咒,并且造谣生事。而李瓶儿因有了官哥,一心只想安心度日,便按照封建礼教与儒家思想的社会期待进行角色扮演,希望恪守三从四德,以此换来相夫教子的安乐生活。但她一味的忍让和压抑非但没有保全自己,反而导致官哥的死亡和自身的悲剧。
人物角色冲突的三种类型并非各自发展,与之相反,不同类型的角色冲突关系十分紧密、相互关联。如何解决激烈的角色冲突,成为李瓶儿生存的最大困境。格罗斯(Gross,1958)主张,在解决角色冲突时,应该采取在期望之间进行选择、回避或者妥协的策略[7]。弗拉特(Van de Vliert,1976)认为,解决强烈的角色冲突必须采取三个步骤:选择、妥协或从情景中退出[8]。李瓶儿采取的是“妥协”的方式。嫁入西门家之后,便见识了西门庆作为“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的凶狠和暴戾,她自知再无法像对花子虚、蒋竹山一样轻易脱身。既然无法再次选择,亦不能通过回避摆脱西门庆的控制,她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选择妥协,以消极的态度,恪守“容忍和节制”的原则,在“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扮演中消磨了自己的生命力,最终毁灭了自己。
角色冲突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在中国文学史中,与李瓶儿这一形象相似的还有乐府民歌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刘兰芝这一人物形象。面对与焦母的激烈的角色间冲突,她先是妥协,逆来顺受,“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而冲突一再激化之后,她只能“从情景中退出”“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另外,如《水浒传》中的林冲、《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甚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均展现出人物性格在面对角色冲突时的不同表现,这种角色本身的纠结外化表现为人物的动作、行为及话语。虽然以上小说的艺术成就各有千秋,语言风格亦不尽相同,但主人公面对矛盾后的应对方式,往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角色间的矛盾,甚至引发了更多的矛盾。这种激烈的戏剧冲突,成为故事矛盾的主轴。读者亦在角色间矛盾中,潜移默化地体会出人物内心的纠结,形成悲剧的艺术效果。
3 李瓶儿悲剧的成因:角色冲突引发的道德性焦虑
3.1 客观性焦虑、神经性焦虑与道德性焦虑
在人格的发展中,对基本安全感的需要以及对现实的或者假想出来的、威胁的反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个体对现实或假想威胁的反应,即焦虑,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动机力量。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焦虑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客观性焦虑、神经性焦虑、道德性焦虑三种类型[9]。他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了完整的人格结构,本我受本能和欲望的驱使,自我是现实世界的联结,超我指道德化了的自我,受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影响。而客观性焦虑和外部世界紧密相关,由对个体具有威胁性的、真实的危险情境所引发。神经性焦虑对人的影响比客观性焦虑更为严重,它源于本我和自我的冲突,当自我认识到本我的需要引发危险的时候,产生的对本能的、冲动的恐惧,这种恐惧已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很难摆脱。而道德性焦虑是自我和超我的冲突,是后天产生的,受社会习俗、道德教化的约束,当自我认识到个体的需求和道德良心产生冲突的时候,将体验到羞耻和罪恶感,并且和神经性焦虑一样,无法通过回避来获得解脱。罗洛·梅进一步指出,通过检视焦虑是如何在事后被运用的,可以区分正常与神经性焦虑。正常焦虑会被建设性地用来解决造成焦虑的问题,而神经性焦虑会导致对问题的防卫和逃避[10]。
3.2 角色冲突引发的道德性焦虑
李瓶儿最初可能出现的是危险的客观性焦虑,她迫切寻求归属,以求生活有所依仗。李瓶儿的性格具有过强的依赖性,她的习惯性压抑造成了人格的内在矛盾,使其心理处在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对于真实的危险无法分辨。而在潘金莲的一再迫害下,其只有通过压抑自己以求自保。她希望与西门家的人建立和维持好归属关系,以求获得稳定的生活。但李瓶儿的“慷慨”和“好性”,一再顺服和被动的态度,使其更易被人欺凌,故更需要压抑自己的攻击性与敌意。自小父母双亡,六亲无靠,失子之痛更是对李瓶儿的致命打击,这种归属关系的丧失加重了她的焦虑,进一步升级为神经性焦虑,李瓶儿的“痴”人性格使其对西门庆有着极强的依附性,对失宠抱有极端恐惧心理。对潘金莲的恐惧以及对西门庆的失望使其个人力量进一步内缩与框限,冲动行为给她带来的是麻烦、羞辱和无穷无尽的被折磨,她便通过压抑本我的需求来获得平衡。
如果说客观性焦虑和神经性焦虑让李瓶儿的恐惧逐步加深,那么道德性焦虑的发展所带来的疚责感则最终引发了李瓶儿的角色崩溃。李瓶儿在角色冲突中的妥协,使其极度压抑和被动。为了早日与西门庆在一起,她不惜坐视花子虚病死,将钱财拱手送入西门庆府上。未遇到西门庆之前,她甘于接受自己传统女性的命运,在可怕的孤独中守着所谓的丈夫和家庭。西门庆的出现,让她发现这个在各方面都是佼佼者且合她心意的人,可以将她从失望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但是作为花子虚之妻,她要唯夫命是从。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害死花子虚以嫁予西门庆。但她尚未泯灭良知,始终难辞其咎,寝食难安。而她内心深处角色认同的爱情对象只有西门庆。由此李瓶儿所接受的道德规范和她的主观情感,以及其自身的角色期待和社会期待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李瓶儿的超我和本我无法协调一致,超我的道德良知让她无法摆脱愧疚感和焦虑,时刻谴责自己的冲动行为,一旦精神脆弱的时候,这种焦虑将使其身心备受折磨。李瓶儿害怕道德惩罚以及失去西门庆的关爱和认可。这些恐惧和疚责感被一再压抑,进而导致其对问题的逃避和个人的独立性的损害。李瓶儿希望通过妥协或服从获得安全感,以对抗“原始焦虑”,即面对自然力量、病痛以及终极死亡的脆弱。但道德性焦虑无法通过回避来摆脱,内在的道德判断和坚信佛教的“因果报应”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加重了她的焦虑,最终导致角色崩溃,含恨而亡。代清认为,李瓶儿,生得漂亮,有钱作为保障,却少了杜十娘的清醒,她多了对西门庆的一份痴,却少了些许聪明[11]。从某种角度而言,李瓶儿的悲剧暗合了佛家对于“痴”毒的解释。
3.3 外部因素加剧角色冲突
就外部因素而言,晚明的社会环境和封建纲常伦理的压抑对李瓶儿的悲剧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明末社会经济的变化,农业、手工业生产有所发展,商业日益繁荣,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从李瓶儿这一人物角色形成过程来看,充分体现了在社会资本蓬勃发展阶段,金钱对人的异化。李瓶儿虽然拥有财产,但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她依旧为财产待价而沽,希望能通过出卖自身获取理想的生活和爱情。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李瓶儿屈服于男性,而在明末的社会新思潮中同时做了金钱的奴隶。李瓶儿在嫁给西门庆之前的遭遇,更多的是金钱的悲剧,而嫁予西门庆之后,在西门庆的宅邸中逐步屈服于传统家庭的封建礼教,成为以男性为核心的封建家庭的奴隶。这“两个奴隶”的枷锁,使李瓶儿的角色冲突成为必然。即使不嫁西门庆,她也不会获得独立自由的生活;即使她一开始嫁予西门庆,同样亦不会获得美满的家庭。
4 结束语
《金瓶梅》成功塑造了李瓶儿作为一个“痴”人的人物形象,从角色理论的角度分析,她看似矛盾的行为是由于面对不同的对象时,对角色认同的差异。对花子虚和蒋竹山的所谓“反抗”,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再屈服于其所中意的西门庆,反抗与屈服互为因果。这样的“痴”,不仅使其在花子虚和蒋竹山事件上表现得极为狠毒,同时使其在西门家的“自致角色”中不断沉迷,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人物特质。嫁入西门家之后,其贤妻良母角色扮演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角色冲突,“妻子角色”暗气上身,“母亲角色”的失败导致角色崩溃。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李瓶儿的悲剧从侧面展现了晚明时期市民阶层小人物的命途多舛,进一步揭示了封建社会夫权制度的荒诞。付善明指出,“悲剧是兰陵笑笑生用来暴露的有力武器,通过他的神工鬼斧,使我们看到了作为封建社会悲剧根源的封建家庭制度、妻妾制度、官吏制度等的罪恶。”[12]可以说,西门家中李瓶儿的刻画是对嫁入西门家之前李瓶儿的升华,这样的设计强化了对残酷现实的揭示。同时李瓶儿母子双亡的结局亦使其具备了动人的悲剧内核,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些并非十全十美,亦非十恶不赦之辈,他们应当是好人,但又有一些缺陷和过失,由此而给自己招致了灾祸,这样悲剧才能激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才能使我们的情感得以净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