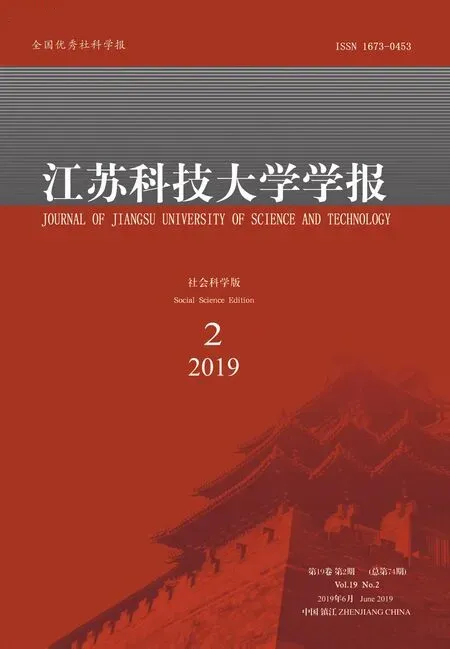春秋“卿”“大夫”辨正两则
惠翔宇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春秋史(前770~前453)是一部列国卿大夫的生成演变史。作为春秋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体,卿大夫不但传承、践行着西周以降延续发展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而且对其予以损益、诠释与创新,并在社会演进中重塑、整合、建构着春秋社会的伦理体系与价值认同,最终宣告贵族社会的终结——开启战国“布衣将相”新时代。因此,对春秋卿大夫的研究显然是了解春秋伦理、信仰与政治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但长久以来,学者在“卿”“大夫”“卿大夫”的概念及其使用上则显得较为混乱。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曾就春秋卿、大夫、卿大夫的内涵生成与时代变迁[1],春秋卿大夫与“国人”的历史关系[2]等作过系统研究,并以之为基础,分析了春秋称谓演变所揭示的政治社会结构变动及伦理变迁。然因题旨和篇幅所限,还有如下问题尚待厘清,即春秋“卿”与“上大夫”的身份关系,“卿大夫”是“官”名还是“爵”称,以及春秋“官”“爵”合一征象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等。鉴于此,本文拟以《春秋左传》记载为基础,辅以《国语》《仪礼》等传世文献,并通过相关史料分析对比,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春秋“卿”非“上大夫”辨正
对于春秋“卿”与“上大夫”的身份关系,清代学者江永在《乡党图考·上大夫下大夫考》中说:“按卿与大夫,《春秋》皆谓之大夫。分言之,卿为上大夫,其大夫皆为下大夫也。诸侯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就三卿分言之:司徒,执政一人,为上卿,亦曰冢卿;其余为下卿,亦曰亚卿、介卿也。总之,皆为上大夫。”[注][清]江永《乡党图考》卷十《上大夫下大夫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二〇四·四书类,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9页;[清]阮元编《清经解》卷270(影印本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4页(B栏)。又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之二·周职官附考》中则指出:
按:《春秋》于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后,卿日益尊,故但称为卿以别于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后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郤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
子》此文[注]按:这里崔述所说的“《孟子》此文”指《孟子·万章下》“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参(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十《万章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第677页。为近是。[3]
近人杨伯峻先生也说“上大夫位即卿”[4]221。但征诸文献,江、崔、杨三氏之说可商。通过相关资料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春秋时期“卿”非“上大夫”。其一,春秋“卿”“大夫”称谓的内涵、外延不同;其二,从春秋时期的整体状况来说,“卿”是总称,它有明确、清晰的内部秩次,而“上大夫”为特指,是“大夫”内部秩序的最高一级;其三,江永指出“大夫”可指卿与大夫,崔述更敏锐地发现《春秋经》用“大夫”指“卿”的事实,却忽视了“大夫”的内涵生成与时代变迁,即“大夫”一词有一个从狭义指“卿”到内涵、外延渐次扩大(将一些中层贵族纳入其中),再到“卿”“大夫”称谓逐渐分化而适用不同等级人群的演进过程[1]。除此之外,传世文献《左传》《国语》还可提供以下五条铁证:
(一)《左传》桓公三年载:“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4]99在这段记载中,“诸卿”“上卿”“下卿”与“上大夫”并言,则“卿”非“上大夫”。此证一。
(二)《左传》昭公二年记:“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4]1228-1229《左传》又载:“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4]1230-1231根据以上记载,前者说陈无宇非“卿”,后者谓陈无宇为“上大夫”,是“卿”非“上大夫”,清晰可辨。此证二。
(三)《左传》昭公元年说:“郑为游楚乱故,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熏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杜注曰:“自欲同于六卿,故曰七子。”[4]1215若杜预所言不误,可知郑公孙黑(子晳)不属于“六卿”之列,故而郑国史官才将与盟者写作“七子”。换言之,如果公孙黑不与盟,郑大史或将书作“六卿”。此外,同年《传》载郑子产说:“子皙,上大夫。”[4]1213将这两则史料对比分析,那么至少在春秋时期的郑国,“卿”非“上大夫”。此证三。
(四)《左传》昭公五年载“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4]1266,楚灵王称两人“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4]1267。根据同年《传》薳启强之论[4]1268-1269,此时晋国六卿的排列次序是韩起、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晋国“九大夫”排序是叔向(羊舌肸)、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可见在当时的晋国,“上大夫”(如叔向)位列晋“九大夫”之首,“上卿”(如韩起)则位列晋“六卿“之首;“卿”与“大夫”判然有别,更无须论“卿”非“上大夫”这一问题了。此证四。
(五)《国语·鲁语上》谓季文子使子服它(即孟献子之子仲孙它)为“上大夫”而不言“卿”[5]173;又《国语·晋语八》载韩宣子问叔向如何处置秦后子、楚公子干的禄邑问题,叔向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5]435-436叔向所言十分清楚,“卿”与“上大夫”判然有别。此证五。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卿”非“上大夫”[注]对于“卿”非“上大夫”的身份关系,段志洪先生亦持此论,她说:“或认为卿、大夫的等级相互交错,即卿为上大夫,然后有中大夫和下大夫。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上大夫不在卿之列。”(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唯其所述颇为简略,且有史料阙漏。,至此可下断言。前贤所谓“卿为上大夫”之说,不符合春秋史实。
二、春秋“卿”“大夫”是“爵”抑“官”辨正
关于春秋“卿”“大夫”“卿大夫”的内涵、外延及内部等级秩序,有人已对其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1]。但在“卿”“大夫”的性质上,目前学界尚存在“爵”位与“官”名之争。因此,还需要对这一问题予以分析和辨正。
按:爵者,酒器也,《说文》将其归入鬯部可证[6]229。具体而言,殷周时代的青铜爵乃“合煮郁金之类香草以为香酒的煮酒器”[7]。用“爵”制作的这类香酒不但弥足珍贵,而且有通神、降神之用,是周人祭祀、飨宴、朝会时的必备之物[注]按:《说文解字·第五篇下·鬯部》:“鬯,以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段玉裁注云:“攸服,当作条畅。周汉笺皆云‘芬芳条畅’可证也。《郊特生》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云‘郁合鬯’,与下文‘萧合黍稷’,皆谓二物相合也。《周礼·郁人职》:‘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注》云:‘筑郁金,煮之以合鬯酒。’按:此正所谓郁合鬯也。郑注《序官》‘郁人’云:‘郁,郁金香草,恒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酿秬为酒,芬香条畅于上下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9月版第228页)据上可知,鬯酒(即香酒)不仅弥足珍贵,而且具有通神、降神的作用,是周人祭祀、飨宴、朝会时的必备之物。。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饮酒器的“爵”渐渐向礼器转化,从而成为社交、邦交的礼序之器,其伦理意味已远超器物本身。对此,(宋)王黼在《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四)·总说》中写道:
凡彝器,有取于物者小,而在礼实大;其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设施也至广。若爵之为器是也。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至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8]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周社会,“爵”的上述社会功能遂使其具有其他酒器如觚、觯、卣等不可比附的特殊地位。或许,这就是后世用它代指功勋、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爵”何时用来指称社会等级,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证据。根据晁福林先生的研究,爵制应与分封制、宗法制的实施同步,“可以说它滥觞于周代的册命制度”[9]。衡诸史实,其说可从。
学者周知,在春秋时期,凡称“卿”抑或“大夫”者,都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如采邑)、政治基础,这一社会群体是位于春秋社会秩序中国君之下、士之上的一大社会阶层,是春秋贵族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导。这一历史状况与前述“爵”的社会功能若合符契,故而《白虎通·爵篇》说“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10],当是对春秋社会状况的正确概述。换言之,春秋时期的“卿大夫”称谓是“爵”称而非“官”名。
或云:从《左传》所载春秋话语体系看,时人多称卿、大夫以“位”而不以“爵”。实则不然,这恰恰是春秋时人将“卿大夫”视为“爵位”的坚实证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
晋士鲂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4]913-914
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4]1191
上述文献,前者说臧武仲论“无失班爵”,后者言公孙挥善辨“班位”,则爵、位同义。除这两则史料之外,其他文献亦不乏实证。如《国语·鲁语上》载孟文子[注]孟文子,鲁大夫公孙敖之子文伯榖。曰:“夫位,政之建也。”韦昭注云:“建,立也。此位,谓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5]162爵、位同义,不言自明。再《说文》人部:“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清人段玉裁曰:“引申之,凡人所处,皆曰位。”[6]394卿大夫的社会等级,即其在春秋伦理秩序中所处的位次。这与“爵”之本义及引申义类同,故爵、位同义可知。如果细究左氏之文,则在春秋时人话语体系中,爵、位、班三者皆同义,均指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左传》桓公十年: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4]128
按:引文“周班”即“王爵”,即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周五等爵”[注]这里仅以“周爵”论说班、爵同义,并不细究周代“五等爵”这一复杂、深奥的学问。笔者视野所及,迄今为止,学者对周代“五等爵”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否定“五等爵”的存在,代表作如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129页),杨树达《古爵名无定称考》(《积微居小学树林全编》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郭沫若《金文丛考》第二章《金文所无考·五等爵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0—53页),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34页)等;(2)肯定“五等爵”的存在,代表作如金景芳《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5页),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3—17页),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59—72页),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62—78页);(3)肯定周代贵族等级制的存在,但对于“五等爵”制持审慎态度,代表作如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589页),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9页)。此外,刘芮方《周代爵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魏芃《西周春秋时期的“五等爵称”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对周代爵制问题的系统梳理也有助于“五等爵制”的深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庄公二十三年《传》曰“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4]226,文公六年《传》载“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4]552而使赵孟(赵盾)为中军帅[注]《左传》文公六年载:“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4-545页。,皆为班、爵同义之证。总之,班爵、位班、爵位等,皆指春秋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贵贱等级和位次高下。
因此,从语源、语义及时人话语体系三个角度来看,春秋卿大夫是爵位而非官职甚明。又《仪礼·士冠礼》载:“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汉)郑玄注:“杀,犹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唐)贾公彦疏:
云“以官爵人”者,以,用也,谓用官爵命于人也。云“德之杀也”者,杀衰也。以德大小为衰杀,故郑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官者,管领为名。爵者,位次高下之称也。[11]959
郑玄、贾公彦对官、爵分别加以诠释,则官、爵不同十分明确。另外,从《左传》所载春秋前中期的相关史事来看,亦无称“卿大夫”为“官”的具体语境。换言之,在春秋前中期时人的话语体系中,“官”与“爵”有着明确区分。笔者视野所及,《左传》所载当时史事,凡言“官”者无一例外[注]《左传》庄公十四年载:“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茍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7~198页]虽有“官爵”连称一语,但似乎非官爵同义复指之谓。细究郑厉公“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上大夫”重指爵位,“之事”重指职事,原繁之答语亦针对郑厉公而言。这里官与爵还是区分得比较清晰。,皆指具体职事,似无以“官”指代社会等级秩序者。其证据如次:
(1)隐公八年《传》众仲云:“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杨伯峻注:“谓以先世有功之官名为族姓,如司马氏、司空氏、司徒氏,宋之司城氏,晋之士氏、中行氏之类。”[4]62可见,众仲所谓之“官”乃针对具体职事而言,并非社会等级伦理秩序。另外,桓公六年《传》鲁申繻论取名时说“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4]116,更特地突出“官”的职事性特征。
(2)《春秋》文公八年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左传》记其事云: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锺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亦书以官,皆贵之也。[4]567-568
又《左传》文公十六年追述史事,说:
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4]621
通过分析对比,可知上述史料中的“官”均指司马、司城二职,甚明。
(3)昭公七年《传》载郑罕朔出奔晋国,韩宣子问朔之位于子产,子产对曰:“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寘之。”[4]1293根据郑子产所言,罕朔在郑国,其“位”是“亚大夫”,其“官”乃马师一职。由此可见,至少在郑国“官”与“爵”是判然有别的,否则子产不会说出“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这样的话。
(4)《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出使鲁国,宴会之上,叔孙昭子(叔孙婼)问“少皞氏鸟名官”的根据,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4]1386-1389
当孔子听说郯子关于古官名沿革的讲述之后,便立即向郯子问学。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通过对《左传》文本的比较分析,可知叔孙昭子(叔孙婼)、郯子、孔子所言之“官”指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五工正、九农正等具体职事,郯子“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可证。
(5)文公十年,楚、陈、郑、蔡等国陈军于厥貉,将讨伐宋国。宋华御事自度力不足御敌,所以“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对此,《左传》载:
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纵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4]577-578
对于子舟(文之无畏)“敢爱死以乱官乎”一语,杨伯峻先生注:“爱,惜也。不行其职责为乱官。言不敢惜死以弃职守。”[4]578若杨氏所论不误,则子舟所言之“官”当指左司马。结合子舟所说“当官而行,何强之有”,可知他强调的是左司马一职的分内之责,而非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前述同类史料,见载《左传》者极多,不一而足。若欲详察,只消查阅《左传》有关“官”“位”“班”“爵”的相关记载,便会了然于心。
总而言之,在春秋时期(至少前中期)时人的话语体系中,凡言“官”者,都针对具体职事而言。这同《说文》中“官,吏事君也”[6]773强调官吏的职事性特征颇相符契。无怪乎童书业先生曾斩钉截铁地说:“卿为爵位,非官职。”[12]这是正确的结论。
三、春秋时期“官”“爵”合一征象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
春秋时期,“卿”“大夫”是“爵”称而非“官”名,前文已明。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尚不能就此止息,因为学者还有卿大夫“亦官亦爵”[注]赵伯雄《周代大夫阶层的历史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1至26页),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第十四章《晋国的各种制度·职官和军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5页)。的折中之论。因此,我们在前文所述基础之上,需要对春秋时期“官”“爵”合一征象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予以赘述。
学人周知,春秋时期虽有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变的历史趋势,但毋庸讳言,血缘组织及其宗法伦理依旧是当时政治社会的主流文化。于是,贵族爵位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其权力、官职大小,而且决其采邑的多寡、规模及其社会待遇,所谓“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注]按:语出《国语·晋语八》所载晋大夫叔向之口,参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436页。者也。对此,齐思和先生曾在《周代锡命礼考》一文中说:“盖古者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有禄者必有田,任命与封建,其实一也。”[13]这在《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是有迹可循的。譬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郑伯赏入陈之功,赐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不受,并陈述了如下理由:“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4]1114当时,郑国六卿的排序是: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子产位居第四。按照郑卿之间“降杀以两”的规定,则子产是不得越级受赐的。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公与免余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4]1128-1129《国语·晋语八》载叔向之言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5]435-436如果这些记载是春秋时期晋、郑、卫等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那么其他诸侯国当不例外。总之,春秋时期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这应是时人“官爵”“禄爵”连称的社会根源[注]相关史事见《左传》庄公十年、襄公二十六年,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第198页、第1123页。。
但从《左传》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又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在春秋时期,官职大小又是卿大夫巩固、延续其家族势力的有力保障。如《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孙寿说他“弃官,则族无所庇”[4]621;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说“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4]1192-1193;又北宫文子对卫侯说“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4]1194。这些历史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结构中,“爵”“官”“禄”之间又呈现出交叉、合一的征象。其中,“爵”是获取官职、禄邑的前提和基础,是春秋卿大夫及其家族在其诸侯国内社会地位、权力等级的重要标志。《仪礼·丧服》郑注云可证:“爵,谓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无爵,谓庶人也。”[11]1097如前所述,春秋前中期“官”“爵”之间有明确区分;但到春秋晚期,“爵”“官”之间的界线似有渐渐缩小的态势。这可从齐灵公时《叔尸锺铭》(1.272·2b-6)所言“余命汝职,佐正卿命于外内之事”[14]得到印证。铭文将“职”“正卿”与“外内之事”联系到一起,说明在春秋晚期的齐国,作为等级秩次的“爵”称也有了职事性的社会特征。此外,《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时说“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庇其家事,而后即安”[5]196,同样将“卿大夫”与职事相关联。春秋晚期齐、鲁言语上的这一征象,应是当时政治伦理变迁的一个反映。究其实质,实乃地缘政治不发达、官僚体系不完善时期的历史现象,同时又蕴含向官僚社会转型、发展的潜流及趋势。比如:秦国的“右大夫”[注]《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楚子嚢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第990页。,晋国的公族大夫(任“公族大夫”者,似与后世“流官”性质接近)[注]根据李毅忠先生的研究,晋国在公元前607年“作公族”之后,公族之职便具有“流官”的性质;“其选材范围限定在卿族内部,可谓是一种有条件的‘流官’,具有进步性。”这在晋国公族大夫的选任上表现尤为突出。参李毅忠《两周政体变迁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27-230页。,尤其是春秋晚期魏献子所命十个县大夫,实际已与战国秦汉时期的“流官”性质相近,然而又带有封建制的历史遗痕[15]。或许,正是上述历史因素才使读者产生“官”“爵”合一的感知错觉,亦是学人称春秋卿大夫“亦官亦爵”的原因所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