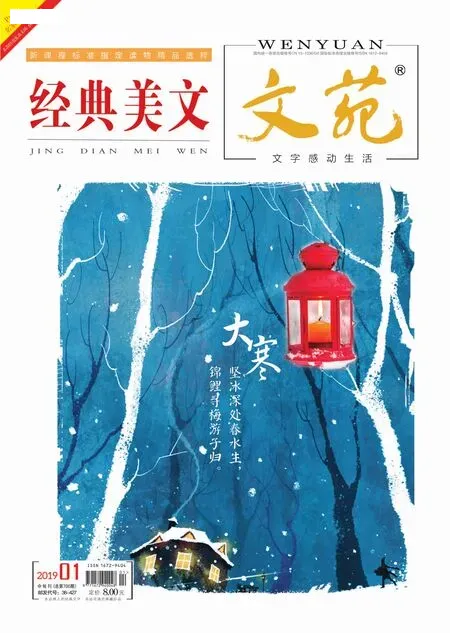野有蔓草
文/李 涛

1962年4月末,张充和在打理自家花园。她与弟弟宗和信中记此事:“后园中有许多花,也叫不出名字来,只有芍药还认得。这几日在拔草,拔草除了得好空气外,还可以消恨,拔一棵又顽固又坚硬的草根,好像是除了一个坏人。不怪旧书上常提到蔓草之忧恨。”
她所说的旧书应为《左传》,其中有一段“郑伯克段于鄢”:“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在这里,蔓延不绝的杂草,成为敌手的意象。
在人类文明史上,杂草的命运,一向如是。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古原草”,即杂草也。也可以说,在现代园艺出现之前,所有的草都是杂草。所不同的是,从前地广人稀,草与人类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下相安无事,并可入画入诗。
每年四五月,是杂草的登场季。吾园虽小,却不缺它们,对杂草我有自己的态度。
蒲公英我会留下来,看它开花,摘它的叶子煮水。一年蓬也是我喜欢的,如果它不是太放肆,我会等它过了夏天。水花生一定要除掉,一旦放任,便不可收拾。至于荠菜,估计不够包一次馄饨的,算了,还是请它离开吧。我多么希望什么地方能生出一株鸭跖草,这种蓝色花,从前外祖母的屋檐下年年都有,多年未见了。
“禾大壮”除草剂的广告是不少人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之一,普通人却完全不会料到其对生态的干扰。至此,杂草的定义,在地点、文化之外,又增添了技术的维度。对杂草而言,无处藏身的难度在增加,每当我看到园林工人喷洒除草剂,总不免杞人忧天,人类对非我族类之戕害,是否正走向自身的末日?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精彩的书《杂草的故事》,可称为杂草辩护词:“杂草不仅指那些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包括那些误入错误文化的植物。”
这番话我甚为认同。谚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杂草啊,你生错了地方,你的转运,要看遇到了什么人。
我一位同学的祖父,从前是位秀才,晚年居家,每日仍是作诗写字。他的房间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字面上实在是老妪能解,个中深意却非我等毛孩子所能领会,老先生曾为我解说,可惜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他家的院子里还真的有一口大缸,小鱼数尾嬉戏于睡莲中,庭中尚有凤仙、天竺葵、月季之属,杂草嘛,虽不丛生,似乎也的确未除,历经浩劫,尚能有这样的日子过,也算天赐。
我去过不同海拔的草原,草色连云,野蜂飞舞,没有人会在那里提起杂草的话题,因为它们是优质的、有经济价值的。而在都市的大街上,你找不到杂草的踪迹,间或会在一条僻巷,看见它生在水泥地砖的缝隙,享受着少数派的自得其乐。
回头说说张充和姐弟的书《一曲微茫》。私人通信一旦流布,便成了公共空间的话题。坊间多有“合肥四姐妹”、“最后的闺秀”一类读物。当人们恢复了对理想化生活之路的憧憬时,她们的故事,成了某种合适不过的榜样。
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天街小雨,故园路遥,如此况味,亦只能付诸诗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