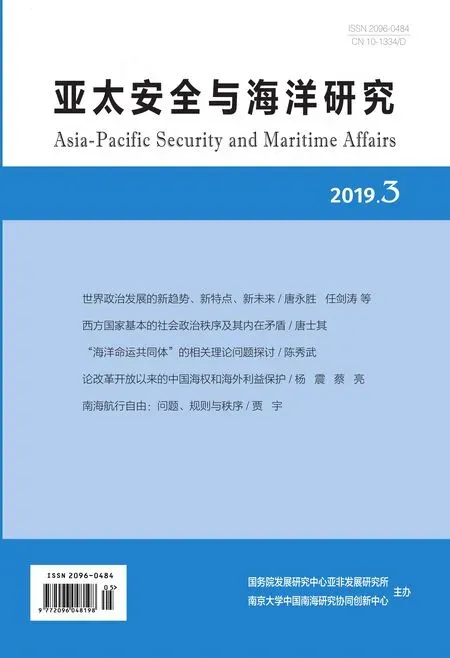西方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及其内在矛盾
唐士其
[内容提要]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之初,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政治平等与社会差异的相互隔离。但在历史的演进中,政治领域的平等不断向社会领域扩展,这表现在经济、文化层面,也表现为移民和难民问题,而社会领域的差异也开始向政治领域内渗,表现为认同政治的产生。政治与社会之间边界的失守,而非暂时的政策失误,是导致当前西方国家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当前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并非简单地对某些外部因素的回应,而是西方国家内在矛盾使然。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比如,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西方国家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特别是各种极端主义政治思潮的出现等等,以致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应该说,变化的出现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这些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
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西方国家目前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加以考察,并且尝试对其原因加以理论上的解释和分析。
一、自由主义与平等
当前西方国家发生的变化,比如认同政治、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某种新形式的极右翼思想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了问题,或者说这种政治秩序本来就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历史的演进一点点表露出来,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本文把西方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虽然西方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但自由主义始终是这种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色。这意味着它的根本使命,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权利和自由,或者被称为“自然权利”,或者被称为“基本人权”,是西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为了使“国家”这样一种强制性的机构和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最大限度地相互协调,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而这种秩序的本质特征,就是力图同时保障公民政治层面的平等与社会层面的差异,并且使两者尽可能相互隔离。
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为何需要保证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平等?从理论上看,主张个人的自由并不必然要求人们相互平等,而且直觉告诉我们,自由与平等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着某种冲突。“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才是自由;限定鱼游的深度和鸟飞的高度,这样的平等就剥夺了鱼和鸟的自由。但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又的的确确是一种平等的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应该说,自由与平等的嫁接,这是西方近代特殊历史进程的结果。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平等的自由主义。
(一)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虽然这种宗教并不要求改变世俗的政治经济秩序,即并不要求建立一种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实际平等的社会制度,但人格的平等,即人在出生时作为上帝的受造物相互之间的平等,则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思想。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一切的不平等,都是附加的而非本源性的,因此并不影响上帝在临终审判时对每一个人的判断。随着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主体性的宗教,人格平等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对于近代自由主义来说,基督教是重要的思想背景和思想资源。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就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对人的平等权利的宣示,意味着人的平等来自上帝的赋予。可见,人与人在出生时的相互平等这一基督教的基本信念,作为自由主义一个默认的思想前提被人们接受下来,并且成为自由主义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
(二)近代自由主义诞生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认识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政治运动,不仅需要了解它们主张什么,同时还需要了解它们反对什么即它们的对立面。近代自由主义是在与欧洲的封建等级秩序和刚刚出现的专制主义、当然还有教会特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换言之,现代自由主义的对立物就是各种专制、等级和特权制度,因而平等不仅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政治主张,也是自由主义者们能够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思想工具。为反对各种专制、等级和特权制度,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提出了所谓的“自然状态”理论。自然状态指国家出现之前的状态,但并不仅仅是一种没有国家的状态,它同时也是一种把所有的社会差异全部抹去的状态。“自然状态”剔除了包括文化、历史、民族、地域等等一切能够使人相互差异的因素,从而把所有人置于上述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造人的最初状态,以此保证了所有人“起点的平等”。可见,“自然状态”理论的根本目标,就是“还原”在没有任何社会政治差异的情形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状态。
(三)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社会契约论的内在要求
社会契约论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这一理论表面上是要说明国家的起源,但实质上是要通过解释国家的起源说明国家的性质和目的。严格地讲,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规范性理论。也就是说,虽然社会契约论者们承认至少有不少国家是通过战争与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他们仍然坚持,只有通过社会契约,即经由自然状态之下每个人的同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具有正当性。在契约过程中,每个人的同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自然状态则保证了所有人天然的平等,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同意都具有相同的权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意志,任何一个人的同意都不能大于、也不能替代另一个人的同意。从理论上看,这实际上就要求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国家,只能以每一位成员即公民的政治权利相互平等为前提。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在自然状态之下人格的平等经过社会契约过程的传递,成为政治权利方面的平等。这种平等,最终将导向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制。
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虽然从逻辑上看,自由主义并不必然与平等主义挂钩,但由于历史性的原因,现代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主张政治平等、并且以民主制作为制度载体的自由主义。
但是,自由主义者真正核心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每一个人的平等的自由(即作为权利的自由)。当然,在现实中,这种平等的自由最终可能会具体化为能够享有自由的人的自由。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不清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充满了不平等,即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严格地说,他们需要扫除的,其实是那些来自旧的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差异,即各种社会和政治等级与特权。至于基于自然的差异,或者因自然差异而导致的其他方面的差异,只要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结果,他们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要求予以认可。
因此,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不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消除这些基于自然的不平等和差异,而且甚至担心新建立的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已经得到确认的公民的政治平等会影响到这些差异。其实就是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在确认公民政治权利平等,即平等的政治表达(投票权)和政治参与的机会的同时,也并不要求公民们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相互平等。正是为了防止政治上的平等从权利变为现实(权力),也为了防止政治平等抹平社会差异,西方国家当时普遍采取的一种制度措施,就是对公民的选举权进行财产资格的限制,即不允许没有缴纳财产税的人获得选举和被选举权。当然,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女性选举资格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认为,自由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提供的平等实际上又被经济上的不平等给取消了。[注]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1—485页。西方国家全面废除财产资格限制,要等到20世纪上半叶。
二、平等的政治与差异的社会
可以认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既把公民的政治平等作为其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差异或者说不平等,也就是说,使它们相互隔绝。为此,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平等的东西归政治,差异的东西归社会”
这里套用了西方传统上区分国家与教会权限时所谓的“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的原则。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安排将严守政治与社会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保证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上的差异并行不悖;既不能让政治的平等干扰社会的差异,也不能让社会的差异,比如人们在财产上的差别、在知识上的差别等损害政治上的平等。因为,前一种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而后一种可能会导致等级社会的重现,也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政治压迫和政治迫害。不管哪一种可能性的出现,都会对自由主义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造成威胁。
(二)严格限定政府权力的边界
这其实是对第一方面的补充或者说保证。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政府并不能当然地拥有政治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产生权力或者为自己授权,政府权力只能来自公民的授予或者委托。只有公民通过同意把某些权力赋予政府,政府才能合法地享有并使用这些权力。用美国宪法的概念来说,政府的权力是列举性质的,社会和人民的权力是保留性质的。[注]参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九、十条。在制度层面,这体现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明确区分。行使权力的机构是政府,但它自身不能创造权力;创造权力的机构即立法机关由经选举产生的选民代表构成,但不能行使权力,而且立法机关的成员要定期选举,而且会期有限,完成立法任务之后他们理论上应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自己所在的选区。从制度上禁止政府即行使权力者为自己授权,这是限定政府权力边界的根本性举措。
(三)严格限制政府的职能,奉行有限政府的原则
自由主义不仅要求政府严守自身权力的边界,而且要求政府只能行使非常有限的职能。这种政府因此也被称为“守夜人的政府”。有两句话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有限政府的原则,即“越小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什么事情都不管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注]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 ed. Owen Thoma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6, p. 224.之所以要求政府只能拥有非常有限的职能,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对政府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或者说警戒,认为政府天然具有滥用其权力的倾向。孟德斯鸠就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英国思想家潘恩则干脆把政府称为“必不可少的恶”[注]潘恩:《常识》,载《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中文译为“免不了的祸害”。。另一位英国思想家密尔虽然是一位社会改良运动的支持者,鼓励政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但他依然反对为政府授予太多的职能。他指出三种情况,认为并不适于由政府出面:“第一种是,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种是,“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一般看来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练的知识”。“第三种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注]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8—120页。
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关系,其中哪一方面出了问题,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三方面的制度安排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主义更倾向于防范政治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而非社会不平等向政治领域的浸透。这样一种倾向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毕竟平等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不容颠覆的根本原则,而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对自由主义来说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
三、平等的扩展与差异的内渗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设想,即如果自由主义真的维持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严防死守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今天的西方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西方国家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这条边界并没有能够守住,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根本守不住。可以说,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那一天起,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就在被穿越,政治的平等就不断地被扩展到社会当中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既然人们已经得到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特别是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机会,而政治又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干预手段,那么那些在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自然就会利用这种手段,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抱有此种政治追求的群体,往往还构成了社会中的大多数,那么在一个奉行民主制的国家,政治上的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显然就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实际的结果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自建立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而言,到现在为止经历了几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法律权利的平等,即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个阶段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即实现了全民普选权,既废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私产资格限制,也消除了对女性的政治排斥(至少从法理上讲);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即人们获得了平等的社会经济保障,如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西方社会的确正变得越来越平等,但与此同时,平等向社会领域的蔓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经济上由于国家干预主义和广泛的福利制度的建立,虽然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有明显的提升,贫困阶层的经济状态有了明显改善,但经济的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文化上虽然人们的教育水平有了全面的提高,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却变得越来越均等化和同质化,精英文化不断受到大众文化的挤压,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失去了文化意义上的立体和深度;在价值和伦理的维度,一方面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开放,人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失去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规范和核心的价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价值方面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这样一种社会各个方面平等化或者说均等化的趋势,甚至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的标准,它们使任何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讨论都成为政治上的“禁忌”。
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对此类现象西方社会也一直有人在加以批评。19世纪末有尼采。他甚至把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立视为“奴隶道德”占上风的结果,把西方社会称为“末人”的社会。[注]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1页。“末人”们没有理想信念,没有不可动摇的追求,只会在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中浑浑噩毕其一生。在“末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不再会有任何的新奇与挑战,也不再会有任何的欢喜与忧伤。只有“超人”的出现,才能把人类从这种末世的沉沦中解救出来。21世纪之初有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质疑一个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民族构成已经高度多元化的社会,是否还有可能长期维持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特质。[注]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最近,十位欧洲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发表了《巴黎宣言:一个我们能够信赖的欧洲》,他们呼吁基督教、欧洲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等传统价值的复兴,以对抗虚无主义、世俗主义、多元主义乃至过度的平等主义的影响。[注]https://thetrueeurope.eu/[2019-03-15].
只不过,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评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罢了。但是,一旦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遇到了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质疑和批评就会从涌动的暗流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比如,特朗普总统的很多说法和做法,显然就是对各种“政治正确”的反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他的个性使然,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反叛那些“政治正确”标准的倾向,而这样一位人士能够当选总统,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对过度平等的警觉或者说厌倦。
平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出现,乃是平等从国内政治领域向国际社会领域延展的结果。移民和难民问题,比上述经济、文化和价值问题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都要大得多。这个问题之所以十分难解,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中,移民和难民正在获得与接收国公民一样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
按照自由主义基本的政治理念,移民和难民作为人都具有与接收国的居民同等的人权,因而应该得到起码的生活保障。从移民和难民的角度来看,他们首先会要求获得生存的权利,下一步他们自然会要求与接收国居民同等的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们会感觉到在他们所移入的社会中往往会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而要改变这种状态,他们就会进一步要求政治上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但是,由于实际上移民和难民的文化传统或者宗教背景往往与接收国有很大差异,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会给接收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暂且不论移民与难民在社会经济方面给接收国带来的影响,比如与本地居民竞争就业机会、分享社会福利等等),就成为这些国家不可能不严肃对待的问题。
欧洲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了政教分离的传统或者说根本原则,而伊斯兰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甚至一座清真寺就可能兼具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在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如何处理一个政教合一的群体,这显然是个两难问题,因为无论宽容还是不宽容这个群体,都意味着违背了这个国家自身基本的政治价值。看起来,移民和难民问题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秩序提出了某种根本性的挑战,它将在实践中测试和考验这种秩序能够容许平等向社会领域扩展到多远。在上述《巴黎宣言》中,保守派知识分子们在反对过度平等、反对世俗化、反对文化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同时,他们同样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在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各方面对欧洲政治社会秩序带来的重大影响。
在西方国家政治平等不断地向社会领域扩展的同时,社会差异也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认同政治的出现。认同政治的实质,是一些特定的少数群体通过其作为少数的身份为自己争取与多数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具有的一个制度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在多数决定的体制下,一个大共同体内部某些特定的少数,总是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满足他们的要求,实现他们的权利。正是这一制度困境的存在,促使那些在不同领域不可能通过多数决定的程序解决自身利益诉求的个人或者群体,转而诉诸他们自己与多数的差异,并以这种差异为由为自己争取权利。就此而言,认同政治也可以被称为“差异的政治”。
认同政治这样一种针对某些特定少数制定特殊的法律或者政策、对其予以特殊对待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维持更大的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特别是针对少数族裔(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英国的北爱尔兰人、法国的科西嘉人等)所提出的要求时更是如此,因为当他们彻底认识到他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时候,他们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脱离这个大共同体而形成自己的政治单元,从而威胁到大共同体的统一。但从根本上说,认同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并不超越自由主义的价值范畴。少数群体要求的同样是自由、平等、公正,只不过他们认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这些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认同政治实际上是利用自由主义的原则,来反对一个更大的共同内部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
但是,认同政治却有可能伤害这个大共同体的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秩序。虽然从结果上看,认同政治提供的各类妥协方案的确保护了那些特定的少数,也避免了共同体的分裂,或者防止了共同体内部可能会趋向激化的社会政治矛盾,但同时又会鼓励人们依靠抱团的办法争取自己的权利,从而有可能会瓦解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一个人拥有某种社会权益,不是因为他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也不是因为他的某种社会身份(status),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自然状态”之下摆脱了一切社会联系的个人、上帝的受造物),或者某个国家的公民。如上文所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对“身份政治”的反抗。
就此而言,“身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则性的冲突。美国最高法院20多年前就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一系列判决中反复强调不能因为过分强调认同政治而让美国社会分裂为无数的小集团。比如,1993年,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裁定为确保黑人当选国会议员而重划选区的做法无效。奥康纳法官就此表示:“任何按种族对人分类的做法都有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持久损害的危险,会让人重新产生那种在我国历史上已被太多的人坚持得太久的错误见解,即人应按肤色予以评价。”过分强调种族因素,会“使我们巴尔干化,分裂成彼此对立的族群”。[注]“Shaw v. Reno,” 509 U.S. 630 (1993), http://supreme.justia.com/us/509/630/index.html/[2019-03-15].
当然,关于如何评价认同政治,人们的立场目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支持者认为,认同政治是有效保护某些特殊群体特别是少数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必然选择。反对者则认为,这样一种对群体赋权的做法,最终将会把社会分裂为大大小小的特殊利益团体,结果是“只有认同而没有政治”[注]Susan Hekman, “Beyond identity: Feminism, ident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Feminist Theory, No. 1, 2000, p. 302.,从而可能既产生新的不公正,又会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对圈外人的排斥和对圈内人的强制”[注]Elizabeth Kiss,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I. Shapiro and C. Hacker-Cordon (eds.), Democracy’s Ed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4.,甚至腐蚀公共精神,导致政治共同体的破裂。因此,有反对者甚至认为,解决认同政治带来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对认同的要求从政治中完全移出”,也就是让这些要求重新回归社会,最终实现一种“超越认同的政治”。[注]Susan Hekman, op. cit., p. 303.
四、如何认识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即以政治平等和社会差异之间的区隔为基础的秩序,由于没有能够严守两者之间的边界,即没有能够阻止政治平等扩展到社会领域,也没有能够阻止社会差异内渗到政治领域,因而正面临某些前所未有的问题。
一方面,平等向经济社会领域的过度延展可能会导致“福利病”和经济效率的降低,向文化精神领域的过度延展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向国际领域的过度延展则导致了西方国家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两难。总之,政治平等向其他领域的延展,不可避免地与各相关领域实际存在、甚至需要保护的差异相矛盾、相冲突。如果借助“政治正确”的标准、辅之以民主政治的手段,试图进一步人为地消除这些差异,则必然会导致自由主义的危机,即严重地损害社会领域的自由。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看认同政治的出现就是在政治平等绝对化的大环境中保持社会的差异的一种尝试,然而通过社会差异向政治领域的内渗,认同政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小群体或者弱势群体面临的权利受损问题,但这种政治的逻辑却又与自由主义基本的政治原则相矛盾,因为它保护的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如果政策得当的话,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平等的政治与差异的社会之间划定的界限可以得到坚守。很可能的是,试图在政治与社会之间划定这样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所以这条界限注定会被突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的就不是一些暂时的困难,而是某种根本性的挑战。
因此,我们不能把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极端保守主义的出现,仅仅视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负面后果。这些新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以及西方国家目前出现的一些政策调整,包括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先是对这些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的应对,是对政治平等与社会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某种再平衡的尝试。就此而言,比如特朗普总统追求的“公平的自由贸易”也许就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而他所主张的“美国优先”也许就具有比我们通常的理解更深的含义,即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仅仅解读为一种内外政策的策略性转变,甚至是对中国崛起的应对或者遏制,可能就会有失偏颇。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创造的政治规范、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部分要素,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我们因为看到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境而全盘否定这些规范、价值和制度的积极意义,甚至企图重拾中国传统中一些已经被近代革命进程所抛弃的糟粕,那么于人于己,都绝非明智的选择。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说现在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中国与西方都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双方能够相向而行,即能够以一种批判自省的态度对待自己,理性认识自身的问题,积极地、建设性地从对方借鉴合理的因素,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合作。如果双方相背而行,以对方的问题为由拒绝自我完善,那么这个世界的风险就会大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