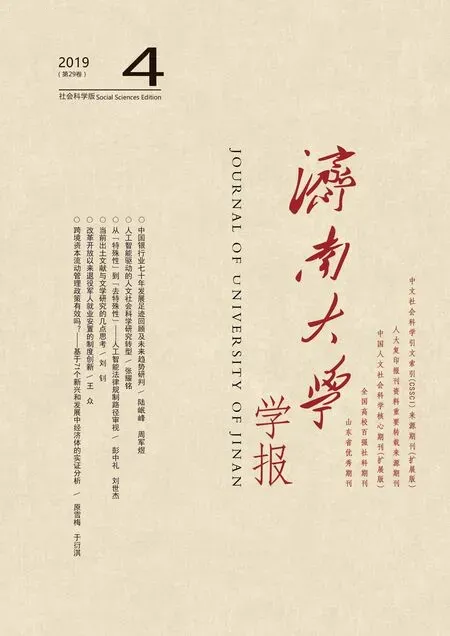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刘 钊
(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本文只想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期向方家请教。
第一点,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出土文献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尤其近二三十年,战国秦汉简牍相继出土,更是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生在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能够看到太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看不到的好东西。作为研究者,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也是非常幸福的。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地下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内容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很高的关联度,尤其是习总书记在2014年访问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时候的讲话和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为出土文献研究带来了强劲的东风。目前,研究出土文献的相关机构纷纷建立。在各级各类项目中,有关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选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最近两年,各级各类项目中还纷纷出现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冷门“绝学”专项和相关选题。目前,有关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专业刊物已经达到了17种。可以确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出土文献研究都将是学术界的热点,成为吸纳研究经费、吸引研究人员的一块热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出土文献研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我们要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必须预流,否则就是未入流。所以,我们选择从事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就是提前的预流。以蔡先金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济南大学和聊城大学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推动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尽快成立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会非常必要。
第二点,出土文献研究圈子外的学术界,一直有很多人对目前已经经过科学鉴定的几大宗出土简牍还抱着真伪的疑虑。但事实情况是凡经过真正出土文献的专家集体鉴定过的简牍,还没有一宗材料是真伪难辨,或是原来被认定为真,后来又证明是伪的。浙江大学藏简的情况很特殊,当时的鉴定团队也是认定是伪的,后来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出版了,其结果就是学术界一片沉寂,这已经表明了态度。真正的核心学术圈子外,常常有人在讨论真伪的问题,其实讲真伪问题的人都是外行。不同于造伪技术已经很高的铜器和陶器,简牍的造伪技术现在还很低,不光从字体、内容来看很容易辨伪,就是用最简单的检测技术,比如说就一条,其饱水率现在就做不出来。像战国楚简的饱水率有的可以达到百分之四百,现在你就是每天往上浇水也做不到,它是经过上千年的慢慢渗透进去达到的。所以已经鉴定过的简牍都没有问题。
第三点,以往的出土文献中,有不少按后世的标准可以定义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现在的出土文献中还在不断出土这类作品。譬如前几年在殷墟就出土了一件甲骨,目前已经发表。这件甲骨字数很多,上面有很清楚的界栏,很显然是模仿简牍的形式,因为简牍是一条一条的,所以它也画上了一条条的界栏。它上面记载了一场战争,写的很细致,这是典型的记事刻辞,可惜上下残得很厉害。这件甲骨的出土打破了我们以往头脑中的成见,甚至可以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以前没有见过这么规整的界栏和这么多字数的记事刻辞,这个是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和研究的。接下来北京大学藏的秦简和汉简会相继推出一些跟文学有关的内容,比如有一篇叫《善女子之方》,就是讲好女人标准是什么样的,句式很工整,而且是押韵的,类似后世的《女诫》或者是《女史箴》一类。还有一篇叫《公子从军》,是一篇俗赋,另外还有《隐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谜语,还有用诗的形式写的《酒令》,都也很有特色。更大宗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安徽大学藏简,其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六十篇《诗经》,它有《侯风》,是以前不知道的,而且里面有大量跟传世本不同的异文,意义非常重大。除此之外,有两篇谈楚国历史的,字数很长。现在我们看《史记·楚世家》字数不多,但是安大简的一篇居然有一万多字谈楚国历史的内容,谈到楚国的祖先,比如说穴熊起名的缘由,就说穴熊长在洞里边,所以叫穴熊。原来研究文化的萧兵先生曾经有过推测,在《山海经》里边有一座山叫熊山,经常有神人出没,他就跟楚的祖先穴熊相比较。以前大家不相信,现在看来,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安大简记录楚国历史的这两篇,我提议命名为《梼杌》。因为《孟子》里边说楚国的历史就叫《梼杌》,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楚辞类的作品,还有很多儒家作品,关于孔子的、子贡的都有,还有《占梦书》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
第四点,对待出土文献要坚持几个原则。一个是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轻易信古,也不随便疑古,而应该采取释古的态度。这个释古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出土文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知,颠覆了很多以往的传统认识,可以正史、补史。出土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中的共时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未经过后人的增删篡改,更为真实可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出土文献还有大量的保存在地下,对此我们要充分估价。在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比照的时候,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就轻易地怀疑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这一点就正如王国维所说“然则经典上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这也就是学术界的熟语“说有易,说无难”。不能轻易说什么没有,如果说没有,可能明天就挖出来了相关文献。但也不能因为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真实,未经过后世的增删改动就轻易的全盘接受,当成信史,必须要加以抉择和判断。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战国时代的出土文献不少就是当时人写的,是当时人眼光和观念观照下的历史和书写,战国时人看更早的历史并不见得比我们看更早的历史更准确、更深入、更清晰,当时就有很多伪托和编造,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注意。
第五点,从商代到秦汉最常用的文字记录载体还是简牍。《尚书》已经明确说殷人“有典有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和西周铜器铭文都不是主要记录文字的载体,都是当时一种有特殊用途的文体,其所记录的内容有相当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充分反映当时的文字语言状况和文学面貌。南方,尤其像湖北、湖南这个地方,其特殊的气候、土壤、地理环境,以及埋藏手段,非常便于简牍的保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出土的大量的楚简,有的保存很好。这是属于湿的一类;还有一类是干的,甘肃新疆这些地方出土的汉简,保存得也非常好,有些像新写的一样,甚至上边的编绳还都在。其他地方很少出简,像山东银雀山汉简是很稀有的。不是当时没有简,是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地方没有出简就根据仅有的这些简牍发现,对当时的语言文字和文学面貌做出狭隘的分析和评价。虽然我们目前只能就已发现的材料说话,但是在观念上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全局认识。
第六点,出土文献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古代很多的思想观念都有一个非常久远的来源。我们根据传世文献对很多事物概念、思想观念起源所得出的认识常常会滞后或偏晚。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各种文体的起源,其中,小说的概念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按后世某个时期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定义,其实甲骨文中有些记载,如甲骨文里边,一些体现出最早记异传统的——就是专门记录特殊的奇怪的事,这是中国史书的传统,一般的事它是不记的,有些有时间、地点、人物及各种祥瑞、灾异记录的例子,就完全可以算作早期的小说。对文体文本性质认定的问题,是完全依傍后世的定义还是根据当时的分类,或是根据实际文本做出自然分类?很显然,如果当时有分类,比如秦汉时期我们就按照着《汉书·艺文志》来,可是更早的怎么办?因为没有依傍,有些话题都无法展开。可是完全依傍后世的概念,按后世的标准去套前面的实际,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可以操作的标准和认定的方法。
第七点,目前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体涉及到的范围还需不断的扩充。比如甲骨文里边的作品,甲骨文分为卜辞和记事刻辞。在笔者看来,所有的记事刻辞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但现在的很多研究都是以卜辞为主,这是没有抓住重点。研究金文,很少有人提到《豳公盨》,但《豳公盨》是跟文学作品最接近的作品。它跟其他的金文体式内容都完全不一样,很像是一篇古书,里边很多内容跟《尚书·洪范》可以相合,其中又谈到大禹治水这个神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艺作品。研究志怪小说,大家举的例子一般都是放马滩秦简的《丹死而复生》和北大秦简的《泰原有死者》这两篇,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睡虎地秦简《诘咎》篇,它的形式跟早期的志怪小说更像,就是谈有一个什么鬼,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表现,我们用什么办法驱除它。这跟后世的《白泽精怪图》相似,敦煌文书里边也有这个材料,这个就更接近典型的志怪小说。谈到汉代的赋,一般都是讲《神乌赋》,很少有人提到马王堆帛书里边的《相马经》,《相马经》是用赋体写的,所以有人就认为应该称为《相马赋》,这是典型的赋,里边的文学色彩非常浓厚,但是几乎没有人研究。当然,一个原因是里边有关相马的专业术语太多,很多搞不清楚,指马的哪一个部位不清楚。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先生藏有一尊青铜马,马上有嵌银的铭文,就指明了马的很多部位,跟《相马经》里边很多名称是可以相对应的。还比如历代的铜镜的铭文,现在的关注度也不够。汉代的铜镜铭文,一般都是用诗体写的,它不光是文学作品,而且是当时最典型的广告,语言和修辞都很特殊,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
第八点,研究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是利用后世的概念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纯文学作品,还是打破传统的概念,把所有的出土文献都当成文学研究对象,从而进行大文学、广义文学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有时笔者也很迷惑,完全打破学科界限,没有学科畛域,造成迷茫一片,这个思路不行;可如果以纯文学为对象,又很容易陷入资料短缺、话题单调、论述干瘪的境地。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双管齐下,既要有纯文学的学科分界清晰的研究,又要有打破藩篱、沟通整合、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勇于开拓的精神和融会贯通的格局和气象。
第九点,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方向,同时也是一个边缘的学科方向,需要研究者具有语言学、文学的专业知识,同时最好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当然,如果既能做到对第一手资料有精深的文本校释的功夫,同时又能在正确无误的文本上进行文学阐发,才是最理想的。可是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这两个学科的充分背景和积累,所以,一方面,只具备一个学科储备的学者要及时补充学习另一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同时,这两个学科的学者最好要进行充分的协同与协作。当前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种出土文献出土后,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本校释,期间对字词的考释和理解会反反复复,逐渐逼近真相并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期间研究文学的学者最好不要急于利用这一材料,尤其当很多疑难字词还未解决的时候,很容易用了有错误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一些错误的认识和阐释,应该要等到出土文献和古文字学界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文本之后再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