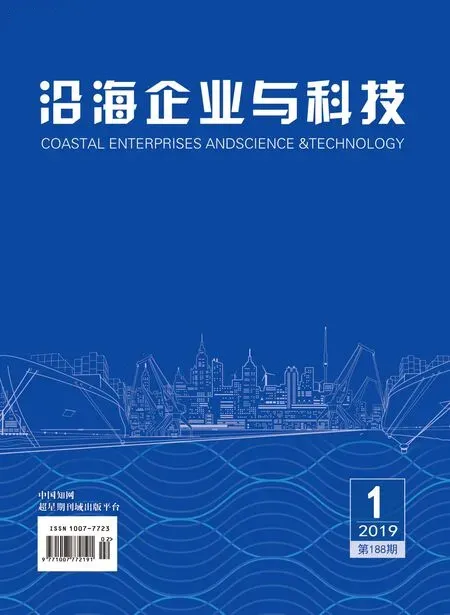东汉末时期西南地区治理研究
张 弓
东汉末期的西南地区大概相当于今天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和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基本涵盖了当前我国除西藏之外的西南地区。从当时行政区划来说,则为益州和交州、荆州部分地区①东汉三国时期并未形成类似于后世省市县的三级模式,所谓的州、郡、县最初只是郡国并行制,州本是为便于监察与巡行而划分出来的,并不是郡的上一级行政机构。东汉末年州一级行政区划才渐渐形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西南地区对于汉代有着特殊意义,益州甚至被称为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益州一直也被看作天下富庶之地。同时,这一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交通不便,政局不稳的不利因素也同时存在。考察当时经略西南民族地区的措施,发现其优越点对于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地区稳定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东汉末年,随着黄巾军的冲击,中央政府已基本丧失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因此,许多研究者将东汉末年历史当作三国史来考察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汉王朝终结于曹丕建立魏国,在此之前的历史只能算作汉。另一方面,虽然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必须得到中央政府承认才能更好控制相关区域,即使这个“承认”中央政府有时是被迫作出的,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个“承认”的重要性。在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汉王朝权力的延伸。
一、东汉末刘焉西南地区治理的特点
东汉王朝末年的西南地区大体上为两个割据势力控制,一个是益州刘焉刘璋集团,另一个是交州的士燮家族。在后来的《三国史》或者是小说戏曲里,这两个集团都是腐败无能的代言人,生来就是被贤明君主和政治强人吞并的,但是考察史料却发现其中蕴含着被人忽视的地方。
先看刘氏父子控制的益州。前面说过益州是经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的地区。经济优越是由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接近关中经济带,有利于得到关中先进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这在农耕时代是十分有利的。此外,益州与外界沟通的道路并不发达,往北、往西都是十分险要的山路,往东只有水路较为通畅。这些险要的自然条件构成的天然屏障使得这一地区十分容易形成割据集团。刘焉恰好是一个具有敏锐前瞻性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在天下尚未爆发动乱之时就预判出即将到来的战乱,他认为割据一方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乞求赴益州为官。②刘焉最初欲往交趾,但恰好此时益州刺史在任上遇到了麻烦,他被派往益州作监军使者,并领益州牧。另外要说的是州牧的设置也是刘焉提出的。见《后汉书·刘焉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431页。又《三国志》记载说“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足见其政治野心。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865页。尽管益州地区是所谓的天府之国,但其时黄巾乱起,蜀中大乱。比起首都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可能这也是朝廷爽快答应的原因。刘焉入蜀后很快利用当地势力平定黄巾军,之后刘焉刘璋父子控制蜀地达二十余年,③刘焉约自公元188年入蜀,刘璋公元214年降于刘备,父子在蜀前后达26年。虽然其父子能力有限,但是能够在乱世控制一地如此之久也说明其治理之术确有可观之处,现略作梳理如下。
(一)招降纳叛、施以恩惠
《后汉书》载“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④见《后汉书·刘焉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432页。对于贾龙这样的西南实力派,刘焉予以笼络。对于其他参与叛乱者,刘焉施以宽宥,用小恩小惠笼络大众。《华阳国志》也说刘焉“抚纳离叛,务行小惠”。特别是刘焉对东州集团和张鲁集团的笼络,为其统治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华阳国志》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拟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刘焉曾为南阳太守。南阳因是光武帝刘秀故乡,在东汉一朝地位十分特殊,是十分富庶的大郡,人口众多。三国战乱频仍,后期吴、蜀等国之人口尚不及南阳一郡巅峰时期的人口。因此,对于这一地区的士人,刘焉极为看重,甚至容忍东州人凌驾在蜀地本土居民之上,而刘焉纵容东州人士的结果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刘璋时期赵韪叛乱,蜀地基本上都起来响应赵韪,刘璋全靠东州人“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①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869页。才将叛乱平定下去。
而对于张鲁集团的利用则体现出刘焉对民间组织的重视。张鲁是五斗米教的教主,刘焉通过张鲁之母笼络鲁,并派张鲁击杀汉中太守苏固,占据汉中,断绝斜谷与中原的联系,成为了益州北部的屏障。虽然养大了张鲁集团,但刘焉留张鲁之母在身边为质,张鲁集团终刘焉之世只能处处表现恭顺。直到后来刘璋杀张鲁之母才造成两家互相攻斗,互为唇齿的格局不复存在。
(二)打击豪强,外扶异族
刘焉以外人身份入蜀,自然要时刻找机会树立威信。前面说过,蜀地四固,其地方势力十分强大。马相黄巾起义本是刘焉树威信的大好时机,结果等刘焉入蜀后,马相起义已被贾龙平定。而贾龙通过平定黄巾军又坐大,使得刘焉在蜀地的地位十分不稳。为此,刘焉不得不笼络东州人和张鲁集团来打击当地势力。除此之外,刘焉的做法就是“立威刑以自尊大”,屡次找借口诛杀州中豪强,结果引起益州士民极大的怨气,最终导致了任岐、贾龙的反叛,当然叛乱很快被平定了。不过关于这次叛乱的结果《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的一则史料暴露了一些细节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②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867页。这则史料反映了两个方面的细节:首先,刘焉能击破叛军靠的是青羌人;第二,再次强调被杀的是蜀地本土人士。刘焉能用青羌人说明其平时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还是施以恩惠予以笼络的。《三国志》还载刘璋的姻亲庞羲善于笼络賨人,这些都可以说明刘焉集团身处西南民族地区,比较重视民族群体,从而在危机时刻,这些少数民族群体能为其所用。这一点是与其平日“务行宽惠”的政策分不开的。
然而,其打压本土人士,导致蜀人离心离德,后来张松、法正诸人引刘备入川即是事态发展至最终的后果。因此,从治理的角度看,刘氏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采取利用民间团体治理一方的策略,又比较注意处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在各方势力集团中间取得平衡,终于导致失败,这也应该引起重视。
二、东汉末期士氏集团的交州治理措施
再看汉末士氏交州集团。士燮出生于今广西梧州。他学识渊博,曾为《左氏春秋》作过注。③《释文·序录》:士燮注《春秋经》十一卷。《隋书·经籍志》:《春秋经》十三卷,吴卫将军士燮注。《唐经籍志》:《春秋经》十一卷,士燮撰。《唐艺文志》:士燮注《春秋经》十一卷。侯康《补三国艺文志》疑为注《公》、《谷》。姚振宗《隋志考证》认为其治《左氏传》。《隋志》:梁有士燮《集》五卷,亡。这些都可证明士燮的学者身份。大约在公元187年左右成为交阯太守,郡治龙编,在今广西凭祥州南附近。弟壹,合浦太守,次弟黄有领九真太守,黄有弟武领南海太守。兄弟几人控制了交州大半领土,大约204年左右曹操为防止刘表势力侵入交州,委任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领交阯太守如故,后又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成为交州最高长官。到公元210年,孙权遣步骘入交州,士氏才降于孙氏,其控制交州也达二十余年。史籍都记载士燮为人宽厚,谦虚下士,又勤而好学,似有君子之风。然观其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上表朝廷乞求交州建牧,④周寿昌《三国志证遗》卷四,清光绪长沙周氏对竹轩刊本,另《艺文类聚》卷六引苗恭《交广记》亦载此事。亦有割据一方的野心。考现存史料可发现士氏治交州有如下特点:
(一)文质彬彬,威仪赫赫
上文说过,士燮专治《春秋左传》学,并有作品传世。至于其学问水平怎么样,史书上也有过记载。“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①见《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1191-1192页。能够得到专人向朝廷推介其学术成果,并有作品流传后世这无疑是对其学术功力的一个肯定。而且士燮在公务结束后即与人讲习经书,因此,其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文士,如袁徽、许靖、刘巴、程秉、薛综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三国名臣。在天下大乱,斯文尽丧的时期,士燮高举文治的旗帜,对于中原文士无疑有着极大地吸引力。而文治的称号也为其治下的环境营造了一个安定的氛围。
汉末交州相当于今天两广、海南一带,本属于中南地区,或者华南,也有人把广西归为西南(方位属华南,经济属西南),也是一个民族聚居地区。这也使士氏集团面临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问题。士氏的做法是大树威仪。《三国志》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锺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②见《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1192页。士燮大树威仪的做法是以此占据文化上的至高点,以文化的力量增强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团结在士氏周围。甚至远在益州的雍闿也受到其影响,向其投诚。
(二)与人为善,招徕远人
士氏集团控制的交州与刘表、孙权、刘璋集团接壤。除刘璋集团因交通不便无力染指交州之外,刘表、孙权无不对交州虎视端端,刘表甚至曾委任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太守。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至岭南。确幸赖吴不和,赖恭为吴巨排挤回到荆州。只有一个苍梧太守吴巨在交州,才没有让刘表势力在交州坐大。而当孙氏遣步骘来岭南时,步骘即执杀吴巨,给岭南士人极大地震慑。士氏集团立马又向孙氏效忠。无论是对嵌入交州的刘表集团,还是对占据交州的孙氏集团,士燮都表现得相当的包容和大度。史书上没有记载其与吴巨、赖恭或者孙氏有什么大的冲突。恰好是这种谦和包容的胸襟使得其能在交州扎根四十余年,并控制交州政局达二十余年之久。
当时中原战乱,交州处于南方远离主要战场,故相对安定。《牟子·序传》说“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可见为躲避战乱许多北方士人都纷纷南迁。加上士燮宽容的性格和文治政策,使得“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士燮又通过大树威仪、以中原礼治为凝聚力吸纳远人来附。这种治理理念是古代儒家修齐治平的最高原则。所谓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修文德以徕之,就是士燮的这种做法。如果说士燮的做法只能对文化落后的西南夷起作用,对各州人士的吸引力十分微弱,也不尽然。《三国志》载士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雍闿是益州大姓豪族,亦传说为刘邦时期的开国功臣雍齿之后。士燮甚至能吸纳雍闿的归附,可见其文治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以学术、礼典威仪为表,以儒家思想为里,增强意识形态的向心力,促使周边各族团结在其周围,也使得士氏家族即便没有强大的武力,也能在刘表、孙权、刘璋集团包围下安然存在二十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三、东汉末期西南地区的治理启示
治理本是一个当代政治学名词,古代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治理。但是从其政治措施,挖掘其有意义的部分,还是可以看出其蕴涵治理思想的地方。这些闪光点加以吸收并运用到今天治国理政上来还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前面分析了刘焉集团和士燮集团的治术。他们控制的地域绝大部分属于今天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地区,也就是说除广东外大部分属于西南民族地区。对于这一地区的治理,因为涉及边疆、民族聚集区,其治理情况十分复杂。当权者要面临的问题要比非民族区多。考察两个集团的治理策略,可谓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刘氏善借外力压制地方势力。观其利用东州士人组建东州兵、征召西南羌人、賨人组建的青羌兵、賨兵都是战斗力十分强悍的武装力量。这说明从刘焉的时代统治集团即认识到要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并将其运用到相关事务中,发挥他们的长处。这对我们今天尊重少数民族,更进一步从思想上尊重民族自治政策是有很大的启示的。但是,刘氏不知道平衡各个集团的关系,导致本土集团离心离德,最终叛迎刘备。而刘备集团也有这个问题。虽然刘备在位时,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史载“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③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882-883页。在战胜刘璋后,刘备集团吸纳了西凉集团、益州集团、荆州集团的力量,并都将他们处于显赫地位,使其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特别是对于益州本土集团,给予了极大的权利。如作为刘备谋主的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可谓权势熏天。不仅如此,《三国志》载法正一旦得势“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①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960页。乃至于有人向诸葛亮抱怨法正太跋扈时,诸葛亮也无可奈何。再加上许靖、董和、黄权、李严、吴壹、费观等人都是益州集团的骨干人士,而刘备都委以重任,李严在刘备弥留之际甚至与诸葛亮一道被委以托孤之重。可见益州士人地位的提升程度是十分显著的。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下,刘备集团力量大增,所以才能自刘备起兵以来首次独自一举击溃曹操,占领汉中。但诸葛亮秉政后这个平衡逐渐被打破了,蜀汉四相,三人都是外来群体,蜀土人士又被打压,刘焉时期面临的问题再次出现。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所谓治理而不是统治,前者强调的是协同为治,追求各方的和谐。而统治是以威权为治,追求的是重压和服从。这些都是当前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地方。
士氏治理岭南,文治为重,不仅注重儒学的作用,还比较注意新兴的意识,如佛教。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重要著作《牟子理惑论》的作者牟子就是在士燮治下宽松的政局中写下了这部佛学经典。另外,前文所引史料中“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烧香的胡人应该就是当时来华传教的南亚佛教徒。②此据任继愈先生观点。见氏著《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这些史料反映出的细节既体现出士氏对于各种意识形态能够等而视之,又能现实他为政以宽的基本理念。同时,以文为治取得的良好效果实际上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这些对于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可以将其置于推进治国理政现代化的视阈,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向心力、凝聚力,从而团结各族人民一道为新时代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奋斗,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意识形态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