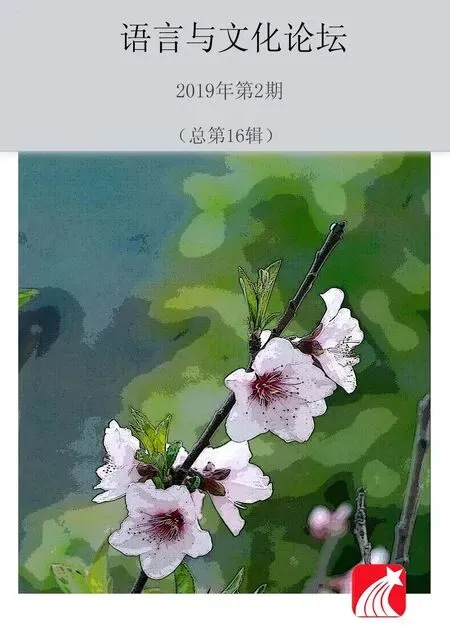山谷往海洋的心灵挣扎
——评刘剑诗集《短歌行》中的海洋意象
◎韩庆成
刘剑先生的《短歌行》共分6辑,前5辑是短诗,第6辑是一首300多行的长诗《献给喜马拉雅的长卷》。这首长诗具有史诗的性质。作者通过对喜马拉雅雪域高原历史与现实宗教的、神性的叙述与思考,试图寻找人类灵魂的最后皈依。虽然这种神性的、宏大叙述的史诗在海子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但作者这种探行的努力仍然显得可贵。
本文想重点谈一谈前5辑的短诗。
通读前5辑的短诗,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些诗中通过海洋意象的密集运用,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作者的心灵从“山谷”向“海洋”“挣扎”前行的这么一种轨迹(引号内文字未注明的均摘自刘剑诗句,下同)。
海洋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多有应用,自《诗经》中的《沔水》《崧高》开始,到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到了唐宋,随着古典诗歌的空前繁荣,海洋意象也进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阶段。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玺吾在《古典诗词审美建构》一文中说:“浩如烟海的唐宋诗词中的咏海之篇也如瀚海明珠,光耀夺目,在洋洋文学大观中构架起了天地、世人、幻境沉浮的碧海长天。作为一种意象,海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视野,乃至被留连、咏叹,总有特定的心理发展轨迹。唐宋诗词的辉煌不再,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涉海作品也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境,但唐宋诗词中海的意象之丰富、寓意之深厚、境界之空阔、格调之浪漫,绝非其他文学样式可以比拟的。”
那么,如何认识这个“绝非其他文学样式可以比拟”?我以为看两个唐代的诗人就足以说明。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表现的是一种入世、济世的情怀;“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则表现了诗人心目中人生、社会的最终走向,诗人要把济世情怀付诸实践,并且看清楚了天下的归宿,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我觉得,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更进了一步。这首诗顾名思义本来是一首怀思之诗,但诗人起笔横空出世的两句,写出了远远超越怀乡思亲情调的博大胸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的核心,就是天下大同,就是普世情怀,这也是海洋意象最精髓的部分。即使是今天,这个境界也还无人超越。而刘剑诗歌中的海洋意象,我认为也表现出了一种同向的价值追求。
谈刘剑诗歌中的海洋意象,需要先梳理一下中国当代新诗中海洋意象的演变。当代新诗的海洋意象,是从“文化大革命”诗歌极端意识形态化、样板化的海洋意象中挣脱出来的,海洋意象在新诗潮中最早被赋予质疑和反抗的象征意义。如北岛1976年创作的《回答》:“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这是质疑;“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是一种反抗。到了1981年,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中的海洋意象已经从质疑和反抗变为既有反抗也有正视:“大海,我应诅咒你的暴虐。/但去掉了暴虐的大海不是/大海。失去了大海的船夫/也不是/船夫。”进入第三代以后,海洋意象更多体现出一种对所有传统意义和语境——包括“文化大革命”正统,也包括新诗潮反正——的消解,这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是沈天鸿写于2002年的《海的解释》。它把20世纪的后50年,特别是7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中所有的海洋意象的象征意义都消解了,把海的附加全部剥离,把海还原为海,一个异于我们的习以为常但却是本真的海,一个贴近存在本相的海,让读者感受到无穷弥漫的理趣和意味,也让读者在这个无意义的海上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赋予意义。
我在主持中国诗歌流派网“重读经典”栏目时,对这首诗做了征评和推介,诗很短,引用如下,做一个参照:
许多人看见风景,而我
看见海
它与我想象的
不完全一样,它不适合做梦
也不适合弹奏
它呼啸着退去又复来
没有人饮用海水——
它里面有盐,气味像血
但滋味是苦的
它自说自话
就像它哪儿也不去
它只说给自己听,仿佛
自身就是目的
没有谁能把自己加入进去
成为海的必需元素
那些正在游泳的人
也仅仅是泡在海里
相对于海
一个人什么也不保存
这就是我们
饥馑与渴望的原因
很少人懂得这一点
我幸运地是其中之一
海没有赝品
这种消解当然是痛快的,它相当于让海洋意象所象征的意义重新归零,但归零之后,时间还在继续向前,在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里(耿占春语),象征还得产生。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意象重新复活,并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状况,这实际上是对事物本身的多样性、包容性的一种回归。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背景下,刘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种声音首先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冷静的活着/在这个悲摧的时代孤独地思考。”刘剑在《思考者》中这样写道。冷静、孤独,我认为是诗人写出好作品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这样的心态下,刘剑十几年来不断打磨他的海洋意象,不断接近前面说到的海洋意象的“精髓”。2015年,海洋意象从刘剑的诗中喷薄而出。
这一年,仅《短歌行》这本诗集中,刘剑就写了近20首直接涉及海洋意象的作品,诗集中的第一首《倒影》,是这样起步的:
众人的屋顶覆盖着青青的草原
牛在月光下反刍
而我的帆船
已升入虚幻的云间
这四句里面形成了一种比对关系,众人和我,牛和帆船,草原和云间,前者是作者的来处,后者是作者的去处,我们看到作者仍然是孤独的,众人活在草原,只有我驾船远行。作者同时也是坚决的,这种坚决正如本文的标题,带着从山谷向海洋挣扎的心灵轨迹:
我在稀薄的空气中挣扎
留恋于一只失去双翅的海鸥
我难道要与她一起沉浮
水带着它涩涩的苦漫越头顶
《倒影》的结尾,作者暗示了去往海洋的过程的严酷性,陪伴他的是稀薄的空气、失去翅膀的海鸥,这样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众人”只能选择留下。但留下并不代表一种认同,作者在第二首《红日》中接着写道:
所有的山峰皆时光倒悬
所有的植物皆向海的方向生长
“时光倒悬”喻示一种颠倒的生活,“向海的方向生长”是这种颠倒生活中人心的守望和寄托。最终,这种守望会迎来它的黎明:
星辰与船儿一起隐去
人们盘踞屋顶
在等待着一轮红日
红日啊红日
我已嗅到了你淡淡的暗香
即使在这红日将出的时刻,作者同样是孤独与冷静的,冷静到一种近于“麻木”的状态,一种麻木并清醒着的状态:
还有一只承载光明的舟子在等候
啊 茫茫的海上
我麻木的头颅仿佛隐约的听到
大海深处的呼唤
在撞破黎明
撞破两个字用得非常精到,它暗示这种黎明并非仅是自然界的黎明,在它不能按照时序的指引正常来临的时候,可以借助“海洋”的力量来撞击它、催生它。这种撞击并非基于一种破坏性,而是基于艾青式的“爱得深沉”。作者是这样写的:
幸好我的双眼还在满含着泪水
还有一些火焰的灰烬
正是灰烬的“复燃”,在作者看来,“萌芽”了“撞破”的愿望和力量。因此,即使有“漫越头顶”的苦难,作者仍然要“挣脱于蒙昧岁月的枷锁”,从“麻木 冷漠 死亡”中“复活”——
我的复活得益于舟子和阳光
得益于蔚蓝色的大海
……
激情重新燃起
那跌破山崖的波浪
总会重新聚集
在《平静》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黎明被撞破后的情景:
黎明到来 一切的喧嚣归于平静
舟子无论漂泊在何方
都会承载着花朵
这样的情景眼前只能是作者的一种梦想,这应当也是整个人类的梦想,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中国梦”。只不过他们入梦的方向不对,不应该往回走,往山谷走,而应该向未来走,向海洋走。这就是刘剑海洋意象所昭示的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发自个人经验,止于普遍价值。
这本诗集中还收入了一首《青海湖》。在这个内海面前,作者同样表现了心灵的孤独与冷静,这说明作者的海洋意象有着它的承续性。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与沈天鸿的《海的解释》同样创作于2002年,在沈天鸿刻意消解的时候,刘剑带着“安徽的蝴蝶”“陕西的油菜花”“甘肃的百合”已然开始重新建构:
倒淌河翻山越岭 自下而上
万水皆东流 唯独我向西
世上从未有过的水系
只是为了寻找你哟 青海湖
在海洋意象的重构中,刘剑既刻画了美好的梦想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世界中那些无以栖居的“流浪”心灵。在失去了精神家园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心灵的流浪图景被作者在诗中反复描述:
我又一次出离现实
进入一个未知的冥域
幻像与火鸟已成为历史
一月里 被冻僵的树随风流浪
天使在流浪 河流在流浪
大海在流浪
(《大海的畅想》)
它们的飞翔是孤独的
这世上漂泊不定的生灵
(《大雁》)
这世界长满了伤口
……
我的呼喊穿透长夜
我的歌声使大海飘零
(《梦幻》)
我们常常丢失自己
或流连于空无一人的孤岛
或踯躅于浩瀚无垠的荒漠
(《前行》)
人像小船四处逃散
汪洋中的惊魂 在寻找彼岸
(《咆哮》)
有多少人在饥渴中
他们在四处寻找水源
(《水的世界过于庞大》)
在这样的漂泊和流浪中,在看似漫无目的的苦难表象的背后,实际上也有“寻找”的不舍和冲动。在《自画像》中,作者更为这种“寻找”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我向神许下诺言/我远在天涯的方舟/何时才能出现//我向佛许下诺言/要有多么深沉的海/才能容纳我内心汹涌的潮汐。”这些句子出现在《自画像》中,无疑是诗人的生命告白,诗中“深沉的海”是刘剑海洋意象所象征的最深沉也是最终极的意义指向。诗句中的“水源”“彼岸”“方舟”作为海洋意象的衍生体,与海洋有着同一的象征意义,它们与诗集中的类似衍生体共同构成了刘剑海洋意象丰满而又一致的成色。
最后,也提一点建议,主要是语言方面,通读诗集中的作品,相对于海洋意象的精髓而言,感觉语言还不够精致。可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简约,要有惜字如金的“吝啬”;二是陌生化,多用新鲜的有个性的词语,以使语言与思想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