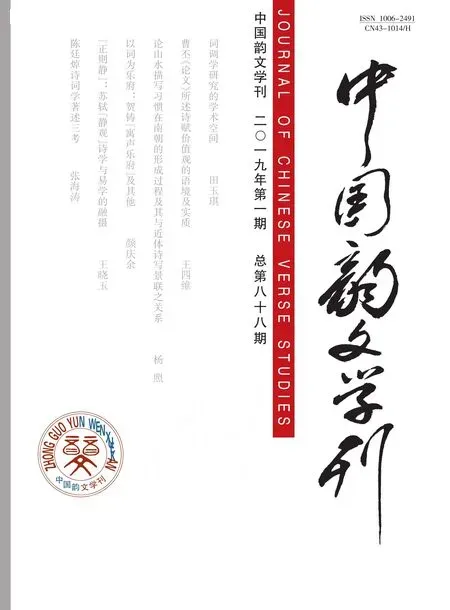苏轼诗歌用典“错误”新探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对苏诗用典错误的批评建立在其用典精切的基础上,否则这类批评本身便失去意义。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苏轼用典既然如此精切,则前人对其用典错误的批评是否存在失误?存在哪些具体失误?这些失误有没有原因可寻,从而避免再犯?经过对前人胪列的苏诗用典错误的逐条分析和对洪迈《容斋四笔》、王文诰《苏轼诗集》等学者成果的吸收,发现其中确实存在失误。其致误原因可分为三类:一是诗歌文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二是批评者没有联系苏诗创作背景而致误;三是批评者没有联系苏诗文本而致误。下面以类为别,对具体的诗例展开探讨和论证。同一类别中,以诗歌创作时间先后为顺序。
一 诗歌文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前人所指苏轼诗歌中的用典错误,有些是诗歌创作完成以后,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字词讹误所致。如熙宁六年(1073)《次韵代留别》:“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旧住西”,一本作“旧姓西”。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二“东坡用西施事”云:“赵次公注:‘按《太平寰宇记》:东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旧姓西,坡不契勘耳。’仆谓坡公不应如此之疏卤。恐言‘旧住西’,传写之误,遂以‘住’字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问新旧?此说甚不通。‘应记侬家旧住西’,正此一字,语意益精明矣。”《苏轼全集校注》(后称校注)云:“所言是……后二句意谓,日后你若退隐,别忘侬家,当携我同去。”
在苏轼诗歌典故中,某些典故的运用,是在文本流传出现歧义时做出选择,代表其学术见解,而非用错。如元祐二年(1087)《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宋张淏《云谷杂记》卷三:“东坡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以上皆东坡语。”李冶不赞同苏轼之说,其《敬斋古今黈》卷八云:“冶曰:四注所援东坡之说,吾恐非苏子之言也。信如苏子之言,则苏子之见厥亦偏矣。所谓先辈不敢改书,是固有理。若断‘凝神’以为‘疑神’,则吾不知其说也。《庄子》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系辞》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今东坡以为与‘阴疑于阳’‘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翁方纲则批驳李冶而赞同苏轼,其《苏诗补注》卷五云:“乃疑于神者,谓直与神一般耳,非谓见疑之疑也。坡公所引《易》《礼》二语,其释疑字最精。”无论是否赞同苏轼的观点,都说明苏轼此诗并非错用典故,而是在诗歌创作中对典故的字词使用有所选择,尽管与众人不太一致,但也不能简单地归入错误。
二 批评者没有联系苏诗创作背景而致误
苏轼所到皆有诗歌,其诗歌用途广泛,如果对其创作背景不甚熟悉,很容易致误,如有学者就由于对苏诗唱和背景不熟而致误。嘉祐六年至八年《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田翁里妇那肯顾,时有野鼠衔其髭。”校注云:“上二句主要写寺庙之冷落,塑像之毁损,随手点出‘髭’字,乃暗用谢灵运之典。”谢灵运之典,出自《刘宾客嘉话录》:“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校注引赵尧卿曰:“苏公诗妙处,含蓄甚多,引用事实,亦复称是。只此一‘髭’字,不无所本。”实则苏轼此诗是对苏辙《杨惠之塑维摩像》的和诗,苏辙原诗中明确说到谢灵运:“长嗟灵运不知道,强剪美须插两颧。彼人视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况塑画已身外,岂必夺尔庸自全。”苏轼才在和诗中回应,并非“暗用”典故。又元祐六年(1091)《谢关景仁送红梅栽二首》其一:“珍重多情关令尹,直和根拔送春来。”张道《苏亭诗话》卷一:“‘珍重多情关令尹’,以尹喜为关姓。东坡岂不读书,缪舛如此?特一时应酬迅疾,不暇点检耳。此率之病也。”尽管苏轼多以典故切姓,但在这首唱和诗中是调笑关景仁,没说尹喜姓关。《次韵刘景文西湖席上》:“将辞邺下刘公干,却见云间陆士龙。”刘公干指刘景文,陆士龙指苏辙,不能同理推出他不知道陆士龙不姓“苏”。
又有由于不清楚唱和诗人之间的关系而致误。元丰七年(1084)八月《次韵滕元发、许仲途、秦少游》:“坐看青丘吞泽芥,自惭黄潦荐溪苹。”司马相如《子虚赋》:“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蔕芥。”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指暇》:“按,相如《子虚赋》‘芥蔕’,刺鲠也,非草木之芥。坡诗云尔,岂非误欤?”元祐七年(1072)《送路都曹》:“恨无乖崖老,一洗芥蒂胸。”可见苏轼并非不知。据《宋史·许遵传》记载,滕元发与许遵(即许仲途)曾在妇人阿云杀人未遂案中意见相左:“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按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于朝……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顗皆言遵所争戾法意。”御史中丞滕甫,即诗中的滕元发,初名甫,字符发,后改字为名,字达道。此“芥”字,实隐含“刺鲠”之意,而诗句“坐看青丘吞泽芥”则意谓滕、许二人已弃前嫌。但此类事体不好明言,故苏轼既用司马相如之典,又不拘泥于典,滕、许二公见之,作为当事人自然为之莞尔。正因“云梦芥”的含义丰富,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复次放鱼韵,答赵承议、陈教授》中又用一遍:“青丘已吞云梦芥,黄河复绕天门带。”表面当然是说环绕泰山的黄河如带而青丘山之广大可以吞云梦泽如芥,不正是叶大庆所指责的把“芥”字弄混吗?然而联系诗中“正似此鱼逃网中,未与造物游数外”句,则“芥蒂”之义得以暗示:苏轼元祐时期勇于报主,不顾身危,因而难安于朝,不得不外出守郡,来此颍州,却心中坦荡,毫无芥蒂。绍圣二年(1095)《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又用此典:“胸中几云梦,余地多恢宏。”连“芥”字一并刊落,独留磊落宽广之意。考虑到苏轼与程之才的关系,两家因为苏洵之女出嫁早亡而结成嫌隙,至此一并宽容,则二人之心胸,确乎无愧此典。同年《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云:“念兄独立与世疏,绝境难到惟我共。永辞角上两蛮触,一洗胸中九云梦。”意更显豁。
在题画诗中,也有由于离开题画背景单独论诗而致误。元祐六年(1091)《书浑令公宴鱼朝恩图》:“不须缠头万匹锦,知君未办作吕强。”沈钦韩《苏诗査注补正》卷三:“按,《唐书·浑瑊传》,大历十二年以前鱼朝恩贵盛时,瑊尚为偏裨,未能与朝恩作宾主也。坡公信手落笔,未究史传本末,故刘辰翁评此诗不可晓,査强为护短……”此图非苏轼所画,乃题画诗,不能将其画之是否符合史实归咎于苏轼。且画乃艺术,本非史传,即便虚构,有何不可?诗中明云:“不须缠头万匹锦,知君未办作吕强。”冯应榴云:“诗意似云不必有缠头万匹之奢,方知朝恩之不能如吕强清忠也。”由诗按画,则画上似并无浪费场景,乃苏轼议论生发之词,意谓君子见机,尽管画面上没有画到鱼朝恩日后的铺张排场,但已经由图可知,他日后肯定不会像东汉宦官吕强那样忠君报国。诗用对比手法,突出浑、鱼忠逆之别,赞美画面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深入。
苏轼诗歌创作背景跟其所处社会和时代也关系密切,因而也有由于未联系创作时代的社会风气而致误。元祐三年(1088)《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二首》,其一:“谁知默鼓无弦曲,时向珠宫舞幻仙。”《上清黄庭内景经·上清章第一》有“琴心三叠舞胎仙”,故王十朋集注引赵次公曰:“变‘胎’为‘幻’未详。”王文诰云:“琴心犹言和心,以琴字作和字用也。三叠乃和心之节度,非谓琴声分三叠也。道家以坐去为骑鹤化,而鹤为胎禽。舞胎仙亦借喻之词,舞幻仙即此意也……此诗因清献好道,而发意谓景仁必有所传,盖偕琴鹤为言也。”其二云:“乘轩故自非明眼,终日僛僛舞爨薪。”“爨薪”指琴,“舞幻仙”指鹤。王文诰所言极是。但还是没有解释赵次公的疑惑。因为就诗意而言,“舞胎仙”既符合诗意,又与典故一致,鹤又为胎禽,如此巧妙,苏轼为何弃之不用?从诗的格律来看,此诗为七律,“幻”字处当为仄声才合律,而“胎”为平声,故不用“胎”字。从诗意表达来看,鹤为胎禽之说不实。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九云:“渊材迂阔好怪,尝畜两鹤。客至,指以夸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语未卒,园丁报曰:‘此鹤夜产一卵,大如梨。’渊材面发赤,诃曰:‘敢谤鹤耶?’卒去。鹤辄两展其胵伏地。渊材讶之,以杖惊使起,忽诞一卵。渊材咨嗟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佳话所误。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语,余皆勘验。’余曰:‘渊材自信之力,然读《相鹤经》未熟耳。”刘渊材比苏轼年长,苏轼在写诗的时候自然要去掉此类不实之说,否则也会成为取笑对象。“胎”字符合典故、诗意,但不符合格律、时代风气;“幻”字符合诗意、时代风气和格律,但不完全符合典故。二者相权,苏轼选择“幻”字,并灵活运用典故,又在其二中以“乘轩”之典加强暗示,因此并非他误用。
就苏轼诗文内部来看,也往往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因此也有由于对苏轼本人的诗文背景忽略而致误。如绍圣二年(1095)《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着意寻弥明,长颈高结喉。”韩愈《石鼎联句》序:“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韩愈文中的“结”字,意为“髻”,曾季貍《艇斋诗话》云:“韩文《石鼎联句》云:‘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结’字断句。‘结’音髻。西汉‘髻’字皆作‘结’字写,退之正用此也。今人读作‘结喉’,非也。东坡云‘长颈高结喉’,盖承误也。”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上、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也持此看法。以苏轼对韩愈的了解(绍圣二年《答周循州》:“后学过呼韩退之。”)此类错误太过低级。袁文则认为东坡是在“以文为戏”,《永乐大典》卷八二引《瓮牖闲评》云:“然东坡高材,岂不知此?而故云耳者,以文为戏也耶?”此说似有意为苏轼开脱。实际上苏轼诗词中有此句法。元祐五年(1090)《点绛唇》(闲倚胡床)云:“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与赵陈同过欧阳叔弼新治小斋,戏作》云:“梦回闻剥啄,谁乎赵陈予。”王注云:“先生《诗话》云:‘元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祷雨张龙公,会景贶、履常、二欧阳子,作诗云:梦回闻剥啄,谁乎赵陈予。景贶拊掌曰:句法甚新,前人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语也。”所谓“清风明月我”“主簿少府我”,与“长颈高结喉”同一句法,“长颈”“高结”“喉”同作停顿,乃“着意寻弥明”之后,对弥明特征的三个概括,而非“结喉”连读。且从字面上来看,“着意寻弥明,长颈高结喉”似乎又形成对称之美,符合苏轼晚年诗歌“渐造平淡”而实则“山高水深”“绚烂之极”的总体风格。
三 批评者没有联系苏诗文本而致误
典故的运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诗意的表达。二者一旦脱离,不仅会影响对诗歌的理解,甚至导致误解。如熙宁六年(1073)八月《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其二:“孔明不自爱,临老起三顾。”冯应榴引何焯:“孔明始从昭烈,年二十七耳,何谓‘临老’?”纪昀:“孔明出时未老。”张道:“孔明释耒从先主,年仅二十七,未及颓老也……东坡岂不读书,缪舛如此?特一时应酬迅疾,不暇点检耳。”王文诰云:“诰谓孔明讨贼,正以受昭烈三顾之重,故临老不能自已也。此‘起’字从‘不自爱’贯下,谓临老犹起此念,与起卧龙之‘起’字不同,且此诗非着意用孔明事,乃以孔明作龙使耳。意谓龙知念故居,而卧龙不知念故居,公盖以龙自比,故其下紧接吾归也。”王文诰虽然常有庇护苏轼之处,然此诗的分析却深中肯綮。何、纪、张三人只看孔明事实,而不联系苏轼诗歌本身,所以会认为是苏轼用错。但从苏轼对孔明的史论以及其他诗歌作品来看,苏轼对孔明是极其了解的,不会犯此低级错误。而王文诰从“龙亦恋故居”入手,认为孔明这条卧龙是苏轼故意拿来跟径山之龙形成对比,苏轼更倾向于径山之龙的行为,诗中说“便欲此山前,筑室安迟暮”,意思非常清楚。径山之龙,蔡襄《游径山记》云:“其间小井,或云故龙湫也。龙亡湫在,岁卒一来,雷雨暝曀。”则此龙常回故居,苏轼拿卧龙与其对比,自然是指他不回故居。如果是三顾茅庐后刚刚出山,何谈回与不回?只有等到临老还没返回故居,才有可比性。此处苏轼活用典故,而何、纪、张三人死扣典故,不懂苏轼匠心所在。
联系苏轼诗歌文本的同时,也要对典故文本有深切理解,否则依然会错。熙宁十年(1077)六月《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四:“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百尺楼者刘备,非元龙。亦误也。”《三国志·魏书·陈登传》:“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百尺楼”不是陈登,也非刘备,而是刘备假设的“小人”,故此处不能拘泥原典。陈登做过徐州典农校尉,为徐州恢复农业生产立过功劳,而其职责所管,略同于太守。苏轼此年四月为徐州太守,故以陈登自比。此联前句意谓“四川老家没有扬雄那样的陋室可以归隐”,后句意谓“在徐州做太守也懒卧百尺高楼之上落井下石,更愿意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元祐二年(1087)《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好卧元龙百尺楼,笑看江水拍天流。”此处也非取义“小人”之喻,而是以“百尺楼”映照此画之大。
诗意的提炼,需要建立在对全诗的整体了解上,如果仅仅顾及典故所在的诗句而不通盘考虑也会致误。元丰元年(1078)九月《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其一:“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古泉清。淡游何以娱庠老,坐听郊原琢磬声。”陈师道《后山诗话》:“眉山长公守徐,尝与客登项氏戏马台,赋诗云:‘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古泉清。’广陵亦有戏马台,其下有路,号‘玉钩斜’。唐高宗东封,有鹤下焉,乃诏诸州为老氏筑宫,名以白鹤。公盖误用。而后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王文诰云:“玉沟斜,人尽知为扬州事,可谓公独不知乎?且所谓玉沟斜道者,像其形也,非真有玉钩之一物,不可移掇他处者。此诗因戏马台借用,犹言台下之路,悉为芳草所合,不见如钩之形而已。”校注云:“则以为乃借用,非误用,似较旧说为胜。”王文诰的借用之说,方向是对的,但没有结合全诗。诗中云“淡游”,则徐州戏马台本无风景,惟诗中所写戏马台与西轩而已。苏轼因此拿徐州戏马台与扬州戏马台对比:“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古泉清。”徐州戏马台的路只有芳草掩径,根本没有扬州戏马台那样的玉沟斜道;徐州戏马台的林中只有古泉清澈,没有扬州戏马台的白鹤观。因此诗中特意点明“失”“亡”,以为戏谑。诗末云“淡游”,正是紧承前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章法井然。后人不明苏轼诗意,率尔以为苏轼混淆徐州与扬州的戏马台,殊不知,苏轼正以“戏马台”产生联想比较,从而无中生有,使诗歌显得幽默有趣。
对诗意的体味,有时应该“以意逆志”,否则执着于字词而忽略诗意也会致误。元丰八年(1085)十月《登州海市》:“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校注引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认为是作于“永贞元年秋由山阳令移江陵掾”,而“苏轼误记为元和十五年由潮州召还事”。苏轼并非“误记”。韩愈南迁有两次,一为贬山阳令,二为贬潮州太守。诗中所写“南迁归”,乃第一次,故后面所接诗句皆转化自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之所以引为“潮阳太守”,乃是苏轼自比,此时苏轼正知登州,若用“山阳令”,则与自己身份不合,故改用“潮阳太守”指代,并非是指韩愈第二次南迁。且苏轼绍圣元年(1094)《临城道中作》一诗,其引云:“始余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澈。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书以付迈,使志之。”其诗云:“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可见第一,苏轼对此极为熟悉。第二,柳宗元所贬居之地乃愚溪,见《愚溪诗序》,袁文《瓮牖闲评》卷五云:“柳子厚所居乃愚溪。苏东坡《过太行》诗云‘未应愚谷能留柳’。‘溪’字遽改为‘谷’字矣。”轼考虑到诗歌韵律的和谐,改“愚溪”为“愚谷”,因为愚溪得名本就仿造“古有愚公谷”。《登州海市》也是灵活运用。
另外,苏轼对典故的使用是为更好地突出诗意,这就需要对典故所含的丰富意义有所取舍,从而更好地适合表达诗意。如果不考虑典故含义的取舍,也容易致误。元祐六年(1091)《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其一:“得我新诗喜折屐。”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八:“按《晋书》,折者屐齿,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诗齿折屐’,则其为喜不言可知。”张秉道之喜乃形露于色,是一种褒义的喜悦,谢安之喜则是“矫情镇物”,若非点出“喜”字,则意不仅不明,且与诗不符。
四 辨析前人致误有利于苏诗研究的展开
对前人所指苏轼诗歌用典错误的辨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苏诗。元符二年(1099),苏轼在《子由生日》诗中说:“季氏生而仁,观过见其实。”典出《论语·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而对前人致误原因的分析和归类,可以让我们避免一些误区,从而更确切地探寻苏轼的诗人之心,展开诗学研究。除去对苏轼诗歌文本的版本、目录、校勘的梳理和甄别外,还能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加强对苏轼诗歌中典故的重视。前人对苏轼诗歌的某些指责,恰恰是没看出其用典。元丰七年(1084)五月《庐山二胜·开先漱玉亭》,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上:“敬斋于苏诗用典错误处亦颇有指谪,然亦无伤坡之全体,且可为学苏诗者作针砭。其一条云:‘徐凝《庐山瀑布》诗云:千古长如白练垂,一条界破青山色。坡笑之,谓之恶诗。及坡自题云:擘开苍玉峡,飞出两白龙。予谓东坡之擘开与徐凝之界破,其恶一也。此宇文叔通《济阳杂记》云尔。(李)冶近读坡集,其《游灊山》诗云:擘开翠峡出风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则坡之诗,峡凡两度擘开矣。’殊不知‘擘开’用巨灵事,岂得与徐凝同讥乎?”
第二,苏轼诗歌用典复杂,没掌握充分资料的情况下慎作判断。元丰八年(1085)九月《次韵徐积》:“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先须问子来。”据《庄子·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赵次公按:“子桑,非子来也。岂先生误记人名耶?”对此用典错误,赵次公倾向于是苏轼“误记人名”。这就使问题简单化。据査慎行注:“《艺苑雌黄》云:……裹饭者子桑,非子来也。先生诗讹。然观退之《赠崔斯立》诗云:‘昔者十日雨,子来寒且饥。’其失自退之始矣。”冯应榴案:“今本韩退之诗云:‘子桑苦寒饥。’并不作子来,岂旧本有作子来者耶?”孔凡礼校:“《永乐大典》卷八二一(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七册)引《瓮牖闲评》:‘唐韩文公、苏东坡皆误用《庄子》中子桑裹饭事,作子来……余原此字之失,盖‘来’字与‘桑’字颇相类。文公已为误用,东坡又承其误尔。’”苏轼出于诗句韵脚的考虑,承袭韩愈诗歌用典错误,而非“误记人名”。
第三,在明白苏轼诗歌创作背景和用典的基础上结合诗意,慎重地探究其典故的灵活运用。元祐三年(1088)《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其一:“不见何戡唱《渭城》,旧人空数米嘉荣。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此诗明显脱胎于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这里容易引起误会之处,在于刘禹锡所写的是歌手,所以用“唱得……声”,而苏轼所写为画手,却用“画出……声”,于字面上看存在语病。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予谓可言‘声外意’,不可言‘意外声’也。”査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也说:“刘宾客诗本是‘唱得凉州意外声’,而先生乃改作阳关。虽偶尔借用,然未免牵率之病。”《阳关图》,据元代胡祗遹《跋阳关图》云:“画至龙眠别立新意,不袭朱碧故智,水墨溶化,而物物意态自足。《阳关》一图,去者有离乡辞家之悲,来者有观光归国拜父兄见妻子之喜。挽辂援车,驱马引驼,祖饯迎迓,一貌一容,纷纷扰扰,恍然在京师门外尘坌群动中。一渔父水边垂钓,悠然闲适,前人以为得动中之静。”图中的一动,正是《阳关图》本意所在,而一静正是“意外声”,即画家主体的思想载体。这“意外声”,就是其二所写:“两本新图宝墨香,樽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这跟米嘉荣不阿时好的“唱得凉州意外声”正同。苏轼不仅用典无误,反而更好地表达出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