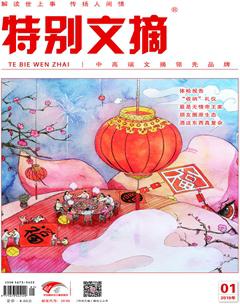肥皂营销故事
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对今天大部分人来说,需要肥皂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一百年前并非如此。
人一直有清洁身体的习惯,但以前并不用肥皂。19世纪的化学工业,使欧美人可以买到便宜肥皂;而新出现的细菌致病理论,对肥皂使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没有抗生素(还要几十年后才会问世)的情况下,仔细擦洗身体似乎是最佳保健之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套,于是,宣传上场了,而这些宣传主要从社会学而非生物学角度切入。
1887年,某英国杂志上的Pear公司肥皂广告,就是很好的例子。广告中,一箱肥皂被冲上海滩,箱子裂开;一名几近全裸的非洲女黑人握着一块肥皂(和一根矛)。广告标题是“文明的诞生”,广告页最底下写着:“肥皂消耗量是衡量财富、文明、健康、人的纯洁的标准。”Pear公司的广告,很多以奇异古怪的“非洲”为场景,但在那些广告问世的很久以后,该公司卖到非洲的产品仍是寥寥可数。他们锁定的对象是中下阶层的英国消费者,广告中告诉他们如何向更优秀者(和他们功绩辉煌的帝国)看齐,与“野蛮人”划清界限。在美国某些广告里,非洲人的角色换成那些被认为不爱干净的移民,但所要传达的信息相同:文明人应该使用肥皂,清洁肌肤、头发、碗盘、衣服等。
我们如果跳出自己所处的时空环境,就能清楚地看到,肥皂的需求是商人创造出来的。殖民地时代的非洲,就是个理想的例子。20世纪肥皂厂商进入非洲,很多营销人员相信,是他们率先提供了解决非洲“肮脏”的办法,但他们的前輩其实比他们更了解事实。1870年之前,来到非洲南部的欧洲人,不认为土著肮脏,并指出土著有多种相当有效的祖传除污办法,包括使用当地的油、兽脂、黏土。只有在殖民活动增加(且许多土著被迫放弃迁徙生活)后,“肮脏的非洲”才需要使用新商品。广告特别针对土著女人开导,说她们是自己男人事业有成的贤内助,如果男人的衣着、身体、头发、牙齿、口气不符合欧洲人的标准,甚至妻子不符合欧洲人的标准,就别想得到好工作或升迁。在旧的身份地位标准正在消失,而新身份地位标准仍让人困惑的社会里,这样的广告很能打动消费者。渐渐地,这些办法奏效了,到20世纪70年代,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不仅大量购买有品牌的肥皂,还把这视作理所当然。
问题不仅出现在跨文化营销领域里。历史上就曾发生过一个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造商担心美国境内肥皂产量过剩。一战后,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所抢占的海外市场,随时可能失去。国内市场也面临同样威胁,制造商担心,柏油路取代泥土路,汽车取代马,瓦斯炉取代煤炭,电灯取代油灯之后,肥皂的需求会降低。于是,他们没有努力推广个人品牌,反倒联合发起行动,“以说服美国人相信自己仍很脏”。
行动的结果之一,就是由产业界支持成立了干净协会(Cleanliness Institute)。该协会除了发起一些稀奇古怪的运动(例如不握手运动),还成功地促进了肥皂使用量的增加,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该协会把女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宣传对象。协会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道,“从哪个地方最早知道春天已经来到?不是旅鸫出现于枝头,也不是番红花长出嫩叶,而是女人开始有了要将房子从阁楼到地下室全部打扫干净的冲动。”新病被人为炮制出来,传统疗法被遗忘,于是口臭有了极专业的称呼——“halitosis”,原来用于清洗伤口的李斯德林漱口水,取代了吃荷兰芹等清新口气的传统办法。1920年,几乎没有人知道漱口水是啥东西,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已无所不在;牙膏、除臭剂等产品的使用,也传播开来。止头皮屑洗发液、漱口水、除臭剂广告还灌输给美国人一种观念,即清洁用品用得不对,会失去工作、约会、配偶等等,而且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所以,最妥当的做法就是购买、使用大家都在用的清洁用品。
现在,每个人都养成了使用肥皂的习惯。这是件小事,而且大概是件好事。但在习惯养成过程中,广告所连带灌输给人的更大原则(即开始懂得依赖广告里的陌生人,而非依赖现实生活中的伙伴,了解什么是合适的行为),已对社会、经济、心理产生巨大影响。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看待、评价他人,如何与他人交谈、相互竞争的信息,不是出自殖民强权之口时,表达方式或许有点儿拐弯抹角,但很管用,卖出的肥皂反倒更多。
(摘自《贸易打造的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