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匍匐在大地上的人
周百义

《2011.壹壹.06.04-07.09.036》徐勇民纸本20.9×28.5cm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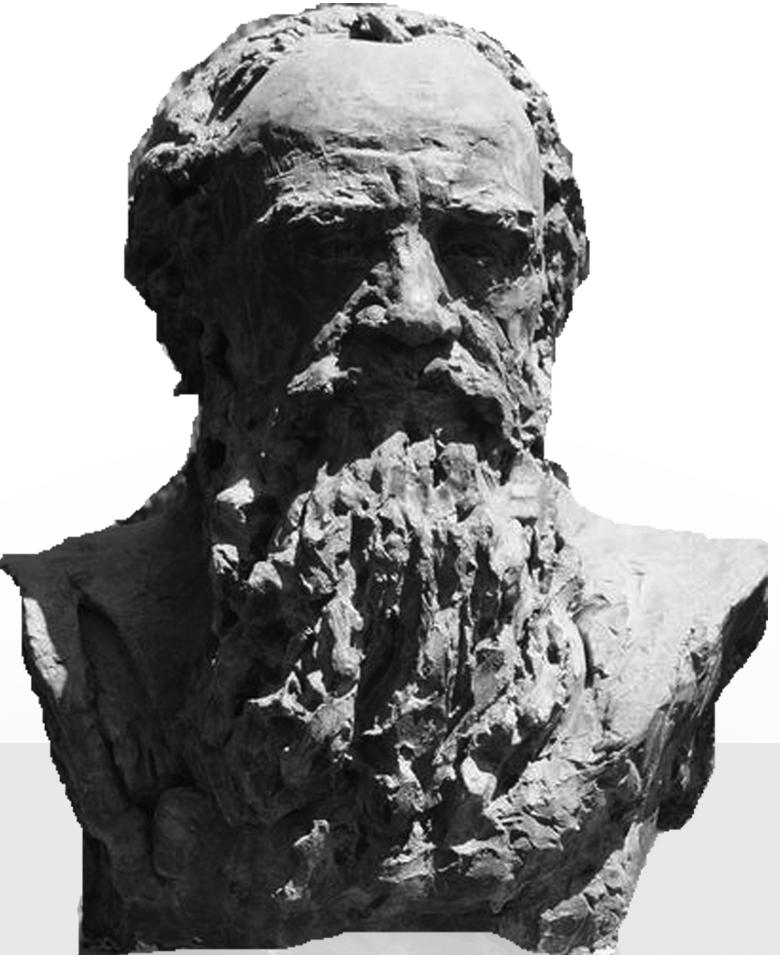
一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在枞树、橡树、桉树和松树的呵护下,在九月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树林深处。
已值正午,斑驳的阳光从树隙间透过,闪闪烁烁地洒落到这个长满青草的长方形土堆上。土堆前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也没有雕塑或者墓碑之类的标志。如果不是在托尔斯泰庄园,没有人会相信土堆下面埋葬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
刚才还一路喧哗的游人瞬间静寂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森林和青草的气息,人们围绕着这个土堆行注目礼。有人蹑手蹑脚地走到土堆前,献上临时采折的一片树叶或者一朵野花。那神情中,满是崇敬和怀念。
我们一行六人,飞越高山江河湖泊和大漠,飞越森林草原和城镇,来到俄罗斯。我们的目的之一,到这个距莫斯科二百公里的雅斯纳雅·波良纳,瞻仰长眠了一百零五年的世界大师。
现在,我站在俄罗斯最高贵、最伟大的巨人最简陋的坟墓——一个土堆前,凝视着那个和泥土融为一体的列夫·托尔斯泰。
二
列夫·托尔斯泰和所有的人一样,没有逃脱死亡的魔咒。1910年,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一心要离开贵族家庭,到人民中去的托尔斯泰因风寒导致肺炎而告别了人世。这年,他82岁。至今,岁月已流逝了108年。但108年前的托尔斯泰,如天上的星辰,仍照耀着这个日夜旋转的星球。
托氏家族,无论他的父系还是母系,在俄罗斯历史上都是显赫至极的:枢密院首脑、将军、省长、伯爵、贵族……他们拥有权力和财富,拥有那个时代的尊严和骄傲,但只有一个两岁失恃,九岁失怙,自认为长相丑陋的小托尔斯泰,后来成了世界文豪。他与他的作品一起,永远生活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也因为他的卓越成就,托氏家族才得以让世人熟知。
是什么赋予了托尔斯泰超人的艺术才华?是家中那个盲人讲的民间故事,还是亚斯纳亚·波良纳美丽而迷人的风光?有研究者说,是普希金发表于1821年的长诗《拿破仑》唤起了托尔斯泰对文学的兴趣。除此之外,卢梭对少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影响也非同凡响。托尔斯泰自己说,他十五岁前读完了卢梭的二十卷作品并且将一枚刻有卢梭画像的纪念章挂在胸前,而不是十字架。当然,托尔斯泰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经典作品,如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和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民,是托尔斯泰生活了70年的雅斯纳雅·波良纳,这儿,寄托了他对祖国俄罗斯所有的爱与眷恋。“如果没有雅斯纳雅·波良纳,我将难以理解俄罗斯以及我对它的态度。”他在一篇散文中如许倾诉。
1852年,时年24岁的托尔斯泰,和哥哥尼古拉一起,来到了高加索的战场上。两年前,他从喀山大学休学回家了。他在战事之余,修改完成了在家乡图拉就开始创作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童年》,并将此寄给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
从此,俄罗斯文学的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托尔斯泰的作品,受到了评论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德鲁日宁等人好评。《现代人》杂志是托尔斯泰崇拜的诗人普希金所创办,现在由诗人、评论家涅克拉索夫担任主编。涅克拉索夫是最先看到托尔斯泰作品的人。他在看完《童年》后写信给托尔斯泰,称赞“作者的思想倾向,故事的质朴和真实性都是这部作品的不可剥夺的优点”。屠格涅夫看完托尔斯泰《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后写给友人巴纳耶夫的信中,称文章“精美绝伦”。车尔尼雪夫斯基撰文评论托尔斯泰的《童年》,称赞其写出了“触及灵魂的辩证法”。
《童年》的成功坚定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信心,他一发而不可收,断断续续写了27个中短篇小说。在他开始创作的前七年中,他的创作都与那个进步的《现代人》杂志密切相关。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童年》《少年》《青年》,通过对主人公尼古连卡性格的形成过程,写出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不良影响,提出了摆脫不良影响的方式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让托尔斯泰引人注目的还是他那些战争小说。他在高加索相继写出了《袭击》《伐木》《暴风雪》《两个骠骑兵》,还有以他熟悉的赌博生活写出的《弹子球记分员手记》。他写出了高加索人的勇敢、真诚与自信,以及高加索的道德风俗,托尔斯泰因此受到了高加索人的尊敬。当一百年后俄罗斯与车臣发生冲突,前苏联和俄罗斯建立的博物馆和塑像都被车臣人破坏,而托尔斯泰的纪念馆与塑像则毫发无损。
塞瓦斯托波尔的系列战争纪事,是托尔斯泰用生命抵近战场的一次文学体验。他写出了《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这些作品在《现代人》杂志发表后,据说俄皇后读后为之而流泪,尼古拉沙皇二世下令将其翻译成法文发表在官方的《北方》杂志上,并要求将托尔斯泰调离战斗区域,担心这样一个天才死在战场上。这篇作品托尔斯泰用熟人闲聊的口吻表达个人对战争的观感,对战争的残酷的描述,对战士的英雄气概和苦难遭遇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描写:
是的,棱堡和整条壕堑上竖起了一面面白旗,开满鲜花的山谷满是臭味四溢的尸体,明晃晃的太阳正朝着深海的海面缓缓下沉,大海的蓝色波浪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熠熠闪亮。成千的人聚到一起互相打量、交谈、微笑。我们不妨认为这些人——这些承认共同的爱之法则的基督徒——一旦看到他们所做的事,会立即跪下来在上帝面前忏悔。
这些经历,为他以后创作《战争与和平》中写作战争场面积累了丰富的生活。
三
祖国和人民,从托尔斯泰这些早期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后来,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则成为了主要的基调。
34岁那年,他娶了宫庭御医、八品文官别尔斯十八岁的二女儿索菲娅,这让一直不安分的托尔斯泰感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创造的灵感被激发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流溢而出,终于,一部传世的史诗诞生了。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这个时期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史诗性作品。小说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鲍尔康斯、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家族的经历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描写中对贵族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等社会重大问题进行探索。
这部小说的手稿现在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共有五千二百多页,其中作品的开头就有十五种之多。开始托尔斯泰只计划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作品,后来,他在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笔触延伸到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他力求让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历史的真相。他广泛搜集当时的文件、书信和当事者的回忆录。他的岳父别尔斯为了支持女婿的事业,也积极为他收集资料,提供书籍和当事人的信件。托尔斯泰还专程到战役发生地鲍罗金诺去实地考察。为了写好这部让他激动不已的小说,他动用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储存,包括他庞大家族的光荣与梦想,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所感受到的俄罗斯的国魂和它的伟大生命,还有他的疯狂的赌博生涯,最后连他可爱的妻子、活泼的小姨子塔妮娅都作为素材写进了这部小说。
这部本来只计划写几个贵族家庭生活的小说最后变成了一部具有宏大历史规模的史诗性作品,而促使托尔斯泰拓展表现领域的是一位十二月党人费·格林卡的信件。这位俄国军官的信件发表后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信件中,这位亲历了卫国战争的军官呼吁沙皇政府让人民的愤怒合法化:“所有的人,每一个能够拿起枪来的人,都拿起枪来!” 托尔斯泰因此修改了主要人物的发展线索,展现了宏伟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场景,写出了千万生灵的悲壮,并插入了许多哲学和历史性的议论。
这个时期,年轻的妻子给予托尔斯泰意想不到的快乐。他沉浸在这种极度欢愉中,促使他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创作能量。《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863年10月他在写给亚历山德琳的信中说:
我以前从未觉得自己的心智,甚至所有的道德力量,会像现在这般不受拘束,能够完全胜任工作。我在心里已经对工作有了整体构思。这项工作就是完成一部时间跨度大概从1810到1820年的小说……我现在是一个充满灵魂力量的作家,写作和思考时所处的状态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是一个快乐而安宁的丈夫和父亲,无须对任何人隐瞒什么,心里别无他念,唯愿一切将永远这样持续下去……
四
65岁开始,托尔斯泰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那时,他的七岁的小儿子万涅奇卡死于猩红热。托尔斯泰夫妇俩伤心之极。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下他希望如何处理他的身后事,他的理想的葬身地是简陋的公墓,没有鲜花,没有神父,更不要有讣告。
追求生活的质朴与简单,是托尔斯泰成年后一直思索的问题。年轻时的风花雪月、纸醉金迷让他惭愧。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借列文之口表达了他的忏悔。这一次,他通过《忏悔录》这本书,系统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索,在思想上完成了他从贵族向平民的转变。
1881年,他发表了《忏悔录》,坚定地表示要转到劳动人民方面来,“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我愈了解他们的生活,我愈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愈安闲舒适”。
当时,《忏悔录》的原名是《一部未出版的作品的序言》。这部未出版的作品是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的《东正教教条神学》。因为涉及教会,托尔斯泰的作品被送到宗教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没有通过——托尔斯泰对东正教态度不敬。审查委员会要求杂志社将刊有《忏悔录》作品剪掉销毁。但是,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却在地下广泛发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发行人却是俄国警察总长的亲戚。
托尔斯泰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俄国农奴制度改革后二十年的现状。“农民忍饥挨饿,大批死亡,遭到前所未有的破产,他们抛弃了土地,跑到城市里去。”
1882年,托尔斯泰参加了莫斯科的平民调查,并且请求在最穷的地段任职。目睹因饥荒而流入城市的贫民的悲惨现状,他写成了《论莫斯科人口普查》一文,“这次调查,在我們这些富裕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面前,展现出那隐藏在莫斯科各个角落里的贫困和压迫的全貌”。他亲自到国会杜马去朗读自己的文章,并将文章印发给参加人口的普查员——一群贫困的大学生。
现实让托尔斯泰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正如他在《人生论》中引用帕斯卡尔的那句话,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他的内心,一直放在基层民众的身上,“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他觉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过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缠绕着我,他们毒害了我的生命。
他要成为新人了。为此,他身体力行,要改变自己的贵族习气。他在1884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一直在改变自己的习惯,起得早,多做体力劳动。……酒已经完全不喝,喝茶时也不把糖放在茶里,而只是吮着糖块喝,肉也已经不吃,烟还在抽,但抽得已经比较少。
他放弃打猎,改吃素食。他亲自参加耕地、做木活、当皮匠,给寡妇犁地,穿农民一样的简便衣服,扎草绳。每当家里开舞会,他关在房子里,很痛苦、矛盾。1884年底参加“媒介”出版社工作,以平民读者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出版各种书籍。为了近一步地与贵族身份划清“界限”,他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著作权在内,都划给妻子索菲娅。他把自己在萨马拉的马匹和牲口都卖掉,将土地分成四块租给农民。
他这种“灵魂的救赎”,完整地体现在他的最后一部文学巨著《复活》中。
《复活》以法律活动家A.P.科尼给托尔斯泰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涅赫留朵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了从城市到农村俄国社会的真实面貌:监狱的黑暗,法庭审判的虚伪,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官办教会的虚伪,神父们的市侩嘴脸,宗教仪式的荒诞无情,十九世纪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后的破败景象和农民的悲惨处境,托尔斯泰以他最清明的目光,深入了每一个人的灵魂。
《复活》与其说是在描述玛丝洛娃与涅赫留朵夫的恩怨,不如说是托尔斯泰想借涅赫留朵夫之行为,表达一位七十岁老翁的忏悔与救赎。
有评论家认为,这是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一次升华。
五
托尔斯泰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教育家、慈善家。
1859年10月,时年31岁的列夫·托尔斯泰在家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办了农民学校。教室就在他家的苹果园里,浓郁的苹果香味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但农民对他的学校并不信任——因为不收费,实际上,是托尔斯泰自掏腰包。到了次年四月,经过托尔斯泰的宣传,学校终于招收了五十名学生,包括男生、女生,还有一些成年人。托尔斯泰在学校里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后来,他利用自己当政府与农奴之间调解员的身份,在当地开办了21所学校,并且招募了部分失业的大学生来当教师。1862年,他又创办了教育期刊《雅斯纳雅·波良纳》。他是主编,同时又是撰稿最多的作者。他还编印了《识字课本》《算术》和四本《阅读课本》以及《新识字课本》。
托尔斯泰认为,初级学校的学生知识面要广。他规定学生要学十二门课,包括阅读、文法、书信、历史、数学、自然科学、绘图、唱歌等。他还划出一块土地,让学生们自己耕作、收割。
为什么开设学校,英国传记作家罗莎蒙德·巴特利特认为,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他的“天职”,“只有当他采取措施以赎回俄国对它无知的农民欠下的巨额债务时,他躁动不安的心灵才能归于平静”。
作为伯爵和退役军官的托尔斯泰居然让农奴的子女接受教育,这激起了附近贵族的反感,他们控告他,恐吓并辱骂他,逼他决斗。1862年1月,警察局建立了一份有关托尔斯泰的秘密档案,详细记载了托尔斯泰的一言一行。如他在国外与赫尔岑、勒莱韦尔等危险人物接触,他雇佣政治上激进的学生担任教师,他担任调解员期间过激的言论等等。这些人还诬陷托尔斯泰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地下印刷厂,印刷煽动反对政府的文件。警察趁他外出之机,派人搜查了他的庄园,监禁了他聘请的十二个老师。搜查整整进行了两天,他家的地窖和厕所都不例外。托尔斯泰回家后勃然大怒,给他最亲密的女友,在沙皇身边担任要职的堂姑妈亚历山德琳写信倾诉他为什么要办学校:
这是我全部的人生,我的修道院,我的教堂,我在其中得到了救赎,它将我从所有的烦恼、疑虑和生活的诱惑中解救出来。
后来,他又给正在莫斯科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写信控诉,沙皇让警察头目写了一封委婉的辩解信给图拉省长,让省长将信转交给他。
1891年,饥荒在托尔斯泰所在的梁赞省四处蔓延,而沙皇政府和知识阶层有些人对此漠不关心,托尔斯泰获悉后,和他的两个女儿塔尼亚和玛莎一起率先投入赈灾。他放弃了到莫斯科过冬的打算,骑着马到农村四处察看灾情。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迅速行动,便率先在农民的庄园里开办救济食堂。他撰写《论饥荒》《一个可怕的问题》等文章,顶着沙皇政府审查官的压力,寻找媒体发表,呼吁社会各个阶层不要漠视农民的困境。他通过朋友将文章译成法文和英文到国外发表,希望其他国家也了解俄罗斯农民的困境,既伸出援手,也藉此向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他的妻子索菲娅在他的感召下,也投入了赈灾工作。索菲娅发动募捐,撰写报道,处理世界各地寄来的邮件,也直接到农村去帮助救灾。托尔斯泰的两个女儿不仅帮助父亲开办救济食堂,设立专门的儿童食堂,还负责为马匹采购饲料,向农民分发燃料、种子、亚麻和树皮带,给他们找活干。托尔斯泰的其他一些朋友对他们一家人充满钦佩,捐款捐物,还有一些外国志愿者加盟,截止到1892年秋天,他共筹集到几百万元的卢布捐款和一些物资,在四个地区设立了212个救济食堂。托尔斯泰后来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沙皇政府感到托尔斯泰又一次赢得了民心,自觉颜面扫地。而托尔斯泰从此也站上了俄罗斯道德的高地,被称为“人民的代言人”。
六
这是一个并不宽敞和高大的两层白色楼房,在5500公顷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里,它只占了很小一个角落。
卧室、书房、餐厅、会客室,一切都是那么简陋,甚至有些逼仄。那狭窄的楼梯,那窄而又长的木床,那张简单的书桌、椅子,与农民一起干活使用的镰刀、绳索,还有他常穿在身上的肥大宽松的农民式罩衫,让你难以相信拥有二千多亩土地和几百个农奴的贵族、大文学家托尔斯泰会是如此的简朴。
1886年6月,美国记者、旅行家乔治·凯南在造访托尔斯泰的书房后,也曾有过与我们一样的感受。他在130年前的这篇文章中曾写道:
地板光秃秃的,家具的样式都已过时,一张宽沙发或者说高背长靠椅,蒙着破旧绿色的山羊皮面子,一张没铺桌布的廉价小桌子。……很难想象还会有哪间屋子陈设比这里更朴素、更简单。东西伯利亚许多农民的小屋里都可以找到更值钱、更华丽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书房,是由一间储藏室改造而成的。家里孩子多,客人多,为了安心写作,他将书房移到这里。书桌不大,四周安有小小的围栏。紧挨着书桌,有一张沙发——那应当还是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的仆人制作的沙发(美国记者看到的也是这张沙发)。托尔斯泰母亲尼古拉的五个孩子都出生在这张沙发上,托尔斯泰自己的十一個孩子也全都是出生在这张沙发上,就连他的两个孙儿也是如此。托尔斯泰的书房曾经换过四个房间,房间里唯一不换的家具是这张沙发。在托尔斯泰的几部小说中,也都曾出现这张沙发。《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安德烈公爵为了迎接儿子的诞生从书房里搬出了一张名称相似的沙发。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不止一次地被提及。不知是托尔斯泰恋旧还是冥冥中觉得这张沙发延续着家族的使命,上百年来,他一直视若生命般看护着这张沙发。
沙发旁边,有一张铺在地上的黑色熊皮。茸茸的熊毛,透露出一种恒久的温暖。这张熊皮,是托尔斯泰外出狩猎时的战利品。那年冬天,他与哥哥尼古拉邀朋友一起去猎熊,托尔斯泰带有两把步枪和一把短剑,第一天打死了一只熊,但是在第二天,一只因枪声受惊发狂的熊在他的前额留下一个永久的疤痕。他冒着生命危险守了几个星期,终于杀死了那只袭击他的熊。这只熊的皮做成了室内的地毯。他写作《战争与和平》时,新婚不久的妻子索菲娅就睡在这张熊皮上,紧紧地挨着他的脚。当他在书桌上奋笔疾书,拿破仑冒着严寒进攻他心爱的祖国,库图佐夫元帅率领着军队展开殊死的抵抗,而他的脚下,却是十八岁的小妻子舒缓如音乐般的鼾声。这时,托尔斯泰的笔下仿佛灌注了灵感的魔力。
那是一段多么甜蜜的夫妻生活。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幸福一百万对夫妻中只有一对才能享有。在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六年间,索菲娅为他生了四个孩子,还有过一次流产。凡是不需要照看孩子的时候,索菲娅都乐意为丈夫誊写手稿。其中《战争与和平》前后抄写了七遍。
但是,这对恩爱的夫妻晚年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托尔斯泰要把他的所有财产分给农民,要把他的版权全部交给社会,要放弃自己舒适而奢华的生活,而索菲娅作为一个母亲,她不希望自己及其子女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何况,那时他们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可是晚年的托尔斯泰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仅与俄国专制社会和东正教会势不两立,也因为观念的冲突与妻子的裂痕越来越大。他无法忍受妻子对自己的监视,几次计划离家出走。最后一次,当妻子索菲娅得悉托尔斯泰背着她与人签了一份遗嘱后,便趁托尔斯泰熟睡后前去他的书房寻找——她要看看这份遗嘱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惊醒了的托尔斯泰被激怒了,他星夜叫醒家庭医生和小女儿,凌晨趁着妻子尚在梦中便离开了庄园。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出走会使你难过。对此我很抱歉。但请你理解并且相信,我别无选择。我在家里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除了其它种种原因,现在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这一走,托尔斯泰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座建筑里了。
七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伟人,但他不是一个圣人,特别是在他荷尔蒙十分旺盛的青年时期。
十四岁那年,他的两个哥哥尼古拉和谢尔盖带他去了妓院,在那个他称为“命中注定”的日子里失去了童贞,事毕之后他站在那个女人的床前悄声啜泣。之后的二十年,他在日记中称是“粗鄙放纵,生活中时时受到野心、虚荣,尤其是食欲的驱使”的日子。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在日记中不停地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如发誓要鄙视奢侈的享受,要早睡早起,但也计划“每月只去妓院”两次。
1844年秋天,十六岁的托尔斯泰去了喀山大学,先学东方语言系,后转学到法律系。他最初很多的精力放在喀山的社交活动中,舞会、音乐会,业余剧团演出,在法律系读书的后期,他广泛阅读文学和哲学书籍,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狄更斯、席勒等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特别迷恋卢梭的启蒙思想,开始对农奴制和学校教育产生不满。
大学三年级时,托尔斯泰休学回到了庄园。哲学的研究唤起了他独立自学的兴趣。再加上一同上学的两个哥哥即将毕业,他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喀山。他回到家乡,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学习计划,但年轻的他始终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他酗酒、赌博、跟吉普赛姑娘混在一起。他在牌桌上损失惨重,单是一次便输了四千卢布。庄园里的几个漂亮的农奴的姑娘,他行使主人的权利,将她们一个个勾引到手。
三十岁这年,他爱上了离波良纳六公里外一个村子里的一位少妇。这位少妇的丈夫经常不在家,列夫·托尔斯泰便经常到树林里与她约会。这位妇人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波良纳的人都认为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私生子——从长相上看。列夫·托尔斯泰把这一切记在自己的日记里。晚年以此为素材写出了小说《魔鬼》——他为青年时的放荡而懊悔。在《复活》里,他借涅赫留朵夫的口,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个自负而且极为偏激的人。他与屠格涅夫的交恶可见一斑。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在即将离开从军的塞瓦斯托波尔之际,收到了屠格涅夫的第一封信。托尔斯泰对这位比他年长的同时代人心怀敬意。托尔斯泰在文坛初露头角时,屠格涅夫已经活跃在圣彼得堡十年之久。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后,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一个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并且为托尔斯泰将他的作品《伐木》题献给他而深感荣幸。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都情不自禁地亲吻对方。
屠格涅夫带他去见圣彼得堡所有的文学家、批评家、出版商,带他到《现代人》杂志去见素未谋面的编辑。他们一起彻夜喝酒,游玩。当托尔斯泰出现困难时,这位只年长十岁的朋友便像父亲一样呵护他。
圣彼得堡的作家们也都很喜欢托尔斯泰,欣赏他的才华,但是他们都意识到很难与这位怪脾气的作家相处。他时常表明自己挑衅性的观点,硬要与别人过不去。如《现代人》杂志有联系的作家中,有人在写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有人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是托尔斯泰却对莎士比亚不屑一顾,他因此对这些喜欢莎士比亚的人十分痛恨。就连性情温和的屠格涅夫因为没有与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也与之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他去拜访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向他朗诵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托尔斯泰觉得它枯燥无味,竟然睡着了,这让屠格涅夫感到十分恼火。1861年6月,两人一起访问诗人费特,屠格涅夫非常得意地谈起,他的非婚生女儿正在學习行善布施,亲手为奶妈补衣裳。不料托尔斯泰反驳说:“我认为,一个姑娘穿戴得漂漂亮亮,坐在那里修补又脏又臭的破衣裳,不过是装模作样地演戏罢了。”
两人由此引起争吵,言词都十分粗暴尖刻。托尔斯泰觉得受到了侮辱,他要与屠格涅夫决斗。他气得通宵未眠,派人去庄园里取来了武器。后来决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断绝了关系,直到十六年后,两人才真正复交。
八
在托尔斯泰书桌上方靠墙的部分,摆放着一排他经常使用的工具书。这上面有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书籍。在这并不多的书籍中,我们一眼就看见,这里也有一本中文图书《道德经》。
托尔斯泰是如何接受了中国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影响呢?
据法国学者罗曼·罗兰研究,托尔斯泰早在1877年就开始关注老子的著作。1881年,他根据巴黎出版的法译本翻译了《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1884年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圣贤孔子和老子,“后者犹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爱戴”。1984年3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在3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说的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1893年10月,他与波波夫合作根据德文译本翻译了《道德经》。为了表述准确,托尔斯泰本人仔细核对译文,并且为之作序。他称赞《道德经》里的基本教义与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教义相符。1895年,他参与校订了在俄国研究神学的日本人小西氏翻译的《道德经》,在他去世的1910年,他还撰写出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编选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
1884年,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孔子。他在写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在日记中都提到了孔子。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具有“非常的道德高度……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即智慧,即力量,即生命”。这一年,他还写了《孔子的著作》和《大学》。托尔斯泰在研究孔子的同时,也对孟子和墨子等圣贤开始研究。他十分热爱墨子的兼爱思想。1910年他还编辑了布朗热的《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一书。
对老子等中国圣贤的研究一直伴随着托尔斯泰一生。他在1909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表示,要出版中国古代圣贤的书籍。其中包括道教。他还计划写一部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问题的讨论。尽管他的这一打算未能实现,但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结束。
1906年始,托尔斯泰对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使命产生了怀疑,他想起“伟大而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的修养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罗曼·罗兰在他的《托尔斯泰传》中如是描述。
怀着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托尔斯泰一直希望与中国人接触。在他的晚年,才有机会与北京同文馆派往俄国留学的张庆桐以及中国国内大名鼎鼎的辜鸿铭通信。他在写给张庆桐的信中说:
……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虽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常有的情形);更不用说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著作的注疏(被孟子驳斥了的墨翟学说,更特别使我为之惊佩。我对于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
九
晚年的托尔斯泰成了一位斗士,他以自己坚定的信仰,向一切巨大的偶像进行攻击: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运动,还有社会主义。
教会和沙皇对他恨之入骨,宫廷里的官员们谈论该把托尔斯泰关进苏茨达尔修道院的监狱,还是把他流放到国外,或者送进精神病院。甚至有人传说托尔斯泰已经被关进了索洛茨韦基的修道院监狱。不过,托尔斯泰的堂姑妈亚历山德琳发挥了作用——她向沙皇游说,为这位任性的亲戚开脱。
当局只好迫害他的追随者。他的秘书、阅读他的图书的读者、参加他举办活动的信徒,都被抓起来了。他再三地向检察官、法官、部长写信:
实在没有什么像把我关进监狱——关进一个真正的、好的、又臭又冷又挨饿的监狱,更使我满意,或更能使我高兴的事了。
托爾斯泰希望以身殉道,但沙皇政府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托尔斯泰为此感到愤慨。但是最后,俄国东正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1888年2月20日的《教会新闻》周报的头版发布了这一命令。
公布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这天,莫斯科发生了向托尔斯泰致敬的游行,来访者将他在莫斯科的庄园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莫斯科市政当局只好出动骑警维持秩序。远离莫斯科的马特舍夫玻璃厂的员工送给托尔斯泰一块镌有金字献辞的绿色玻璃:
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俄国民众将永远视您为伟大人物和亲爱的人,并为您感到自豪!
教会没有估计到,开除托尔斯泰的教籍使他的影响迅速扩大到俄罗斯的各个社会阶层,托尔斯泰迅速成为俄罗斯的灵魂和良知的代表。
如果说托尔斯泰有什么教义,那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宽恕和博爱。
即使托尔斯泰公开宣称“不以暴力抗恶”,沙皇政府对他仍然心存戒备。
1910年11月5日,重病的托尔斯泰弥留在阿斯塔波尔车站站长的床上之际,早已驻扎在此的秘密警察队伍里又增派了六十名警官以防不测事态。获悉托尔斯泰去世后,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这个车站,但是政府禁止加开任何一辆临时客车去阿斯塔波尔车站。大学生们深夜冒着严寒守在装载托尔斯泰灵柩的车将要经过的扎斯卡车站等候,他们希望藉此向托尔斯泰表示最后的敬意。
托尔斯泰的死,在俄罗斯土地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俄国社会各界人士赶来参加了他的葬礼,送殡的队伍足足有几英里长。托尔斯泰的儿子和亚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们抬着单薄的棺木,队伍前面,有人拉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因失去了您成为孤儿的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永远铭记您的恩典。”
人群里,响起了哀婉动人的《永垂不朽》的歌声。那低沉的歌声在俄罗斯初冬凛冽的清晨寂寥的旷野上缭绕。
托尔斯泰回到了他深深热爱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与这里的土地融为一体。
十
列宁生前十分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小本残缺不全的《安娜·卡列尼娜》他曾经读了上百遍。列宁曾经对高尔基说:“怎样的一个大师啊!哦,怎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啊!”他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同样,对于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而言,托尔斯泰也是一面镜子。鲁迅在《祝中俄文学之交》一文中指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于将来才有意义” 。
托尔斯泰,一个终身匍匐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的作家,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文学顶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在《那么我们怎么办?》一文中指出:“作家,就自己的使命本身来说,——应该为人民服务。……艺术,就自己性质来说,必须让人们接近。……艺术界人士为什么不可以服务于人民呢?” 生前与生后,托尔斯泰都兑现了自己的这份诺言。
责任编辑 何子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