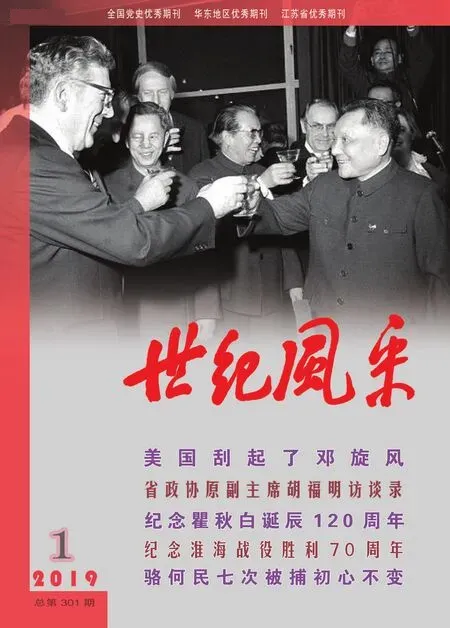骆何民七次被捕初心不变
骆何民,著名的《文萃》三烈士之一。1914年出生于扬州,1948年12月被害于雨花台。这个15岁就投身革命的战士,为了人民,为了心中的信仰战斗了20年。在2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七次被捕,多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最后一次被捕入狱,他的党员身份仍然没有恢复,但他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彰显了一个革命者钢铁般的坚定意志和不可动摇的革命信念。

骆何民、费枚华和幼子(两岁时夭折)合影
第一次被捕
骆何民,1914年生于扬州,家中四个孩子排行老三。父亲骆国章是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国文教员,为人谦逊和善。母亲生于扬州大户人家,相夫教子,勤俭持家。
1919年6月,父亲骆国章病逝,骆何民5岁半,弟弟骆根清只有3岁。原本温馨的家庭顿时陷入了困境,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母亲身上。骆何民母亲的兄长叶惟善曾任两淮师范学堂堂长,辛亥革命后任江都县督学、县署第三科科长、劝学所所长等职。母亲若靠着自己的勤劳和兄长的帮助,生活下去是不成问题的,可那样的话,人家会以为自己靠娘家生活,自己的人格受到伤害虽不算什么,关键是对4个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于是倔强好强的母亲带着四个儿女进了广陵路上的“全节堂”,在这个收容孤儿、寡妇的慈善机构里,靠洗衣缝补艰辛度日,抚养孩子。
骆何民自幼勤奋好学。除了正常的上学之外,他每天放学之后去戴子秋家学习国文,寒来暑往,从不间断。戴家与骆家是世交,戴子秋是骆何民姐夫的父亲,他的国学造诣名闻扬州。扎实的国文功底为骆何民走上革命道路后以笔为枪进行战斗,打下了基础。
1925年,骆何民考入省立第八中学。省立八中是扬州传播进步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扬州革命形势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骆何民。同时,他的哥哥骆孟开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组织,经常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这对小小的骆何民影响很大,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一些进步青年和进步书籍。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扬州后,社会状况的变化使骆何民渐渐地对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大革命处在低潮。但随着扬州党组织的逐步完善和工作渐次展开,年仅13岁的骆何民勇敢地加入革命队伍。10月,他和张一萍等5人被党组织指派建立扬州共青团特别支部,负责儿童团各项工作。1928年冬,中共扬州特委执行委员、东乡特派员曹起溍在扬州东乡一带开展工作。东乡孙家墩支部党员景子英被捕叛变,供出特支书记曹起溍及特支联络地址。随后不久,反动派们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作为党活动的重点区域“全节堂”也成为搜捕的重点。1929年农历新年初三的晚上,骆何民在家里被捕。这次大搜捕致使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除了青年团特支负责人骆何民外,还有耀扬火柴厂党支部书记李前康、香业支部书记张学义、江上青等人,扬州党团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破坏,有四五个月完全停止了活动。这是骆何民第一次被捕,当时他还是个不满16岁的中学生。然而,他毫无畏惧,把亲自审问他的国民党政府县长驳得哑口无言。虽未成年,骆何民还是被关押了3个月。刑满出狱后,即被校方开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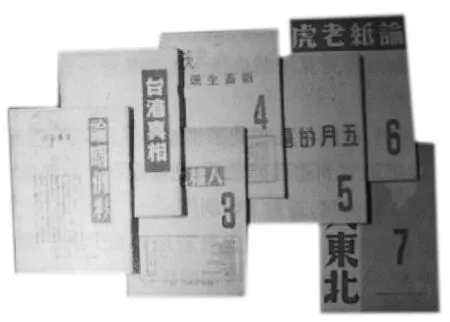
《文萃》丛刊
第二、三次被捕
1929年冬,骆何民经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进入私立浦江中学读书,边从事地下斗争,边继续求学。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上海的运动呈现严重“左”倾态势。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党内的“左”倾一度有所遏制,但革命力量稍有壮大,“左”的急性病便继续发展。党领导上海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可最终都被国民党镇压下去,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骆何民经常参加罢课、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平时看上去文质彬彬,完全一副书生模样,但与巡捕发生冲突时,他便成了一个拼命三郎,勇敢向前,毫不畏惧。他还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逮捕无辜留日学生的活动。由于他经常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不久又被学校开除了。
1930年7月,在骆何民强烈要求下,党组织安排他回到苏北,参加红十四军。9月初,骆何民因在黄桥总暴动中不幸中弹受伤,回到扬州家中休养。回到扬州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的形势使骆何民再也坐不住了,他又回到上海投入革命工作。回到上海不久,骆何民又多次被捕,但因年轻被当作一般学生释放或伺机跑掉。他的革命经验和阅历也随着一次次被捕不断地增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带领进步青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有一天,他正在演讲,被一个国民党警察抓住,说要治他扰乱抗战之罪。由于战事发展太快,整个闸北就是个大战场,远近炮声隆隆,到处火光,警察一看大事不妙,顾不上骆何民,自己先仓皇出逃了。
3月初,骆何民因在上海火车站演讲反对国民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被捕,被送到龙华看守所关押。面对敌人的淫威,他决不屈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在党组织和亲友的全力营救下,方获保外就医。伤势还未痊愈,骆何民又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第四次被捕
1932年,骆何民先后担任共青团沪西地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1月,骆何民参加沪西区团委会议,因叛徒告密,连同骆何民在内5名同志再次被捕,押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判刑5年,送到漕河泾监狱服刑。1936年春,骆何民被转押到江苏省反省院,11月才重新恢复自由。
4年对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而言是一段多么珍贵的黄金时光,骆何民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的。漫长的铁窗生涯非但丝毫未能削弱、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念,相反把他炼就成更加理智、干练、百折不挠的钢铁战士。牢房的条件极其恶劣,终日阴暗潮湿,骆何民凭着惊人的毅力,抓紧时间,刻苦学习。亲友们为他捎去食品及生活日用品时,他总是请他们多带些书报杂志。4年中,他阅读了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和进步书刊,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充实自我,还自学了英语、日语。他常说:坐牢不仅能磨炼人的意志,也是丰富自己的学识,掌握更多革命斗争本领的好机会。他乐观地把坐牢当作革命征程中的暂时休整,因此,每次出狱归来,便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战斗。
第五次被捕
1936年11月,骆何民出狱,返回扬州老家休养。他在扬州家中住了大半年,身体也渐渐康复。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即赶回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心中早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要为革命贡献一切。
回到上海后,骆何民参加了史良领导的救亡协会,此外,他还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上海沦陷后,骆何民到了武汉,按照党的指示向鄂西撤退,参加了“汤池训练班”。
1939年3月底,中共鄂北特委委派骆何民以湖北建设厅“农村合作指导小组”指导员的身份,去保康合作办事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鄂北保康县发放农业贷款,同时在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是年秋,在一次摆脱敌人追捕中,骆何民与同志们失散。他孤身一人翻山越岭,经武汉、抵长沙,涉足新闻战线,先后在《国民日报》《阵中日报》《开明日报》等几家报社担任编辑、记者,并参加了范长江等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公开发表了多篇坚持抗日民主、反对妥协投降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湖南当局的注意。1940年底,骆何民遭军警逮捕,囚禁于耒阳狱中。这是他第五次被捕。
敌人对骆何民先是威逼,见无用,便开始利诱。敌人声称:“只要承认是共产党员,就放你出去,你们这些文人也只是一时糊涂,党国不会治你们的罪。”骆何民坦然一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员,我就是靠写新闻吃饭的,你们不能硬逼我说假话承认吧。我倒希望是共产党员,可是共产党的组织认可我吗?”敌人的利诱对骆何民而言毫无效果。
由于远离亲友,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保人。保释看来是行不通了,只有寻求别的途径争取早日出狱。可是,耒阳监狱内外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狱警日夜防守。积累了丰富狱中斗争经验的骆何民开始琢磨该从哪儿打开缺口。一天,骆何民的监房押进一个因斗殴受罚的狱卒,他就主动与之攀谈,渐渐取得狱卒的信任。闲聊中,了解了监狱四周的地形和警戒情况。同时,他又利用仅有的放风时间摸清周围环境。越狱,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周密地酝酿着并很快付诸行动。骆何民乘上厕所的间隙,在狱卒的帮助下,躲过监狱看守和岗哨的视线,从粪坑通道逃离了魔窟。他一路风尘,辗转跋涉于桂林、香港等地,靠着笔杆子,过着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活。
第六次被捕
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省港大营救出来的在桂林的共产党员陆续离开桂林,奔赴苏区或敌人后方。1942年秋天,骆何民经友人介绍经韶关入福建永安、转南平,准备去上海再转苏北解放区找新四军。到福建后,他们才知道,没有熟悉道路的人做向导,很难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样,骆何民只好留在永安、福安一带一边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一边秘密重建福安党的组织。1945年7月因受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案件的牵连,骆何民第六次被捕入狱,并因此而失去了党组织关系。
1946年9月,由社会上层人士出面保释,骆何民被无罪释放。之后,他四处奔波、急于接上党的关系。有些同志和朋友不明真相,对他产生了误解,投以不信任的目光。骆何民一度深感苦闷、委屈,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

骆何民(1914-1948)
第七次被捕
1946年11月,骆何民带着妻儿重返上海。长期的牢狱之苦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骆何民的身体受到损害。到了上海,骆何民不顾休养身体就开始积极寻找组织。他想去解放区,想为革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但要通过重重关卡,顺利到解放区去,谈何容易,于是他只好先在上海安顿下来。
时值国共和谈濒于破裂,国民党政府大肆扼杀进步舆论,上海出版的许多报刊《民主》《周报》《群众》等相继被查封,《文萃》也已屡遭查禁,被迫转入地下。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全市各印刷厂一律不准承印《文萃》。骆何民不顾自己刚出狱不久,自告奋勇担负起筹建印刷厂的任务。在亲友的帮助下,从筹集资金、购置机器设备到落实厂址,很快就建起了友益印刷厂,使《文萃》得以继续出版,保住了共产党仅存的几个宣传阵地之一。1947年春,国民党中统上海办事处派特务到处收缴《文萃》丛刊,可《文萃》丛刊仍以不同的封面形式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人民中广泛传阅,当出至第十期时,中统特务终于找到了印刷《文萃》的工厂所在地。7月下旬,连续逮捕了《文萃》发行经理吴承德、主编陈子涛和印刷厂经理骆何民及部分工作人员。
对骆何民来说,这已是他投身革命20年来的第七次被捕了,距前次获释相隔还不到1年。年仅3岁的女儿眼看爸爸被一群陌生人带走,用稚嫩的嗓音边喊爸爸,边向爸爸扑了过去,被妈妈紧紧地抱在怀里。听到女儿的呼唤,骆何民放慢了脚步。回首凝望着一直伴随他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妻儿,浓眉下一双刚毅而充满智慧的眼睛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眷恋与歉意。
骆何民和妻子费枚华1942年结婚。费枚华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追随两个姐姐加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随新四军疏散到浙江丽水,后辗转到了桂林,在新知书店工作。他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深情。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见证了他们爱情的坚贞。骆何民曾对战友说过,生命只有一次,我这一生,一是选择了党,一是娶了费枚华这样的好姑娘,我对自己的选择,虽九死犹不悔。
特务们对骆何民施尽酷刑,一无所获,找到他的妻子,她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敌人又企图用亲情来感化他们,对他妻子说:“你先生不说话是不行的,你要是不想他死,就快劝他自首吧!”还故意安排受了重刑,双腿几乎难以支撑行走的骆何民与妻子见面。妻子一眼望见他脚后跟血迹斑斑,又红又肿,忍不住难过地哭了。骆何民强忍伤痛亲切地安慰她:“没什么,里面蚊子很多,抓破了皮,涂了些红药水。”他们默默相视,一切尽在不言中。临别时,骆何民说:“不要悲伤,死并不可怕,只是对不起你,今后也只好靠你的努力了。望你好好抚育孩子,告诉她,爸爸希望她做个好人。”短暂的相聚竟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诀别。
虽然身陷囹圄,骆何民还是像前几次在监狱里那样读中外文书报,和难友们憧憬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恢复组织关系。他让获释出狱的同志带出一封信,请求党组织审查他的党籍。1948年12月27日深夜,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骆何民与另外两位难友陈子涛、卢志英牺牲在雨花台。
1949年7月1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作出《关于追认骆何民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恢复了骆何民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