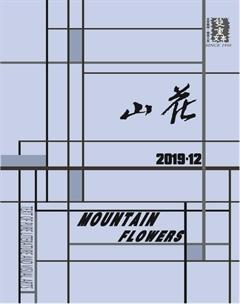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黄德海
一
这几天,因为翻读一本新书,思想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就一边读一边在网上搜求里面提到的十几种相关书籍。有几本因为早已不是新书,网上的价格竟已涨到五六倍,而十几年前这些书打折出售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些书有什么重要,即便有师友郑重提起,也并不特别在意。这不禁让我意识到,及时阅读并敏感地识别出某些书中蕴含的重要信息,本身就是读书有得的特殊标志,甚而言之,我们几乎可以从某个人选择购置或仔细阅读的书中,看出其自身的读书水准。这个情形大概并不限于新书,即便是旧书中提示的相关线索,仍然需要敏锐地识别出其中的含义,沿着某个方向追溯下去,如此温故知新,大约才可能学有所进。
仿佛是为了给我提供一个练习上面认识的机会,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再一次遇到了金克木的话,说的是朱熹《四书集注》中《孟子》注的最后一段:“他引程颐给程颢作的墓碑记作为全书的总结。孟子暗示自己继承尧、舜、汤、文王、孔子(没有周公)而结束。朱熹接着在注中引来此文,明示程氏兄弟继承周公、孟子。‘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云云,不过两百多字,若抄出来大家一看便知其中奥妙和文体特色。”线索已经出现,那就赶紧翻出朱熹的这段话来看——
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程颐所撰的墓志好像没什么难懂的,核心是说其兄程颢虽生于孟子之后一千四百年,却“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那么,金克木说的“奥秘”是什么?或许可以从金克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来猜测:“代言的应对,应对的代言,可以说是传统古代文体的极致。句句是自己说,又句句是替别人说;仿佛是自己说,实在是对别人说,特别是对在上者说;这就是奥妙。”那么,朱熹及由他提倡出来的《四书》,让程颐的序代言应对的是什么呢?“(朱熹编定的)《四书》若作为一篇对策,很像是朱熹为忽必烈、永乐、乾隆预备的。说不定他在南宋时已隐约见到并盼望天下大势必归一统,不过没想到统一者会不是汉族,正如《四书》(各自产生的时候)没有想到统一天下的是秦始皇一样。”
在我看来,金克木的话里还含着另外一个奥秘,即上文括号中的“没有周公”。这个取消周公的行为,说不定暗含着“孟子升格运动”的奥秘——“《孟子》升为经部的的运动,实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宋淳熙间,朱熹以《论语》与《孟子》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并列,《四书》之名始立。元延祐年间,复行科舉,《四书》一名更见于功令。于是《孟子》遂与《论语》并称,而由子部儒家上跻于经部。”伴随这一升格运动的,恰恰是被或明或暗抽掉的周公,也就是圣人序列由周孔(中间经过孔颜)而转为孔孟:“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这个转变或许也就是“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学”一歧为二的过程,以周公为标志的治、道合一的人物被取消(如在孟子那里),或归入“圣人之道”的“治统”(如在程颐所撰的墓志中),而“圣人之学”则独立而为“道统”,并在读书人中有了超越“治统”的独立位置(“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
“治统”和“道统”的分割,很确实地切断了哲人-王之间的短横,哲人(或深思有得的读书人)放弃或终止了成为王的可能,一方面表明自己对世间权力的放弃,从而变成了一个旁观(监督)者,另一方面也就大大减损了精神上某个极为重大的维度。从我开头提到的那本新书梳理的思路来看,权力和智慧本来“像恋人一样纠结于恩怨情仇、相爱相杀的有趣关系”,但抽掉了周公的爱智者等于斩断了二者神秘的亲缘关系。与此同时,权力却并未放松对智慧的注意,弄不好,就是罪犯和哲学家成了同盟:“罪犯——尤其是重罪犯——和哲学家都是逡巡在政治秩序边界的特殊物种,只有他们深识政治体的漏洞,也只有他们能够对政治体构成致命的挑战和根本的保护。”也就是说,即便哲人主动放弃了可能如周公一样为王的嫌疑,仍然难以避免被权力和与权力相关的城邦神警惕,显现出天然犯有过错的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古代读书人采用“代言的应对,应对的代言”方式来委婉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许不是出于天性的胆小,而是对自己“历史境况做出的政治调适”。不过,即便表述得再委婉,哲人也未必能避免历史境况的吞噬力,即如朱熹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曾被当时南宋朝廷宣布为邪说”,要到南宋末期才平反。朱熹真正受到重视,并最终配享孔庙,是历史境况发生更大转变之后的事情了:“从蒙族统治的元朝起,历经汉族统治的明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他都被尊为继承孔孟的大儒。他的《集注》和《四书》本文一样受到极端尊重。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这三朝都是一统天下而且眼光甚至势力远达境外,非南宋可比。”如此,是不是不妨说,同一个朱熹思想,某一时期“对政治体构成致命的挑战”,另一个时期则变成了对政治体“根本的保护”——弄不好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话说到这里,差不多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再写下去难免要左支右绌。好在这篇文章的本意不是要谈朱熹的思想和他面对的历史境况,只是要挑出几则他关于读书的说法来学习,用来比照自己在此一问题上因不够诚恳而来的虚荣和不够踏实而来的浮躁,也就顺势打住,来看看作为卓越读书人的朱熹是如何谈论读书的。需要提到的是,朱熹集中谈论读书的话,一是收在《朱子语类》卷第八“总论为学之方”,以及卷第十、第十一“读书法上、下”里,一是收在后人编定的《朱子读书法》中。
二
数年前,跟师友们共读列奥·施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觉得终于为自己因为懒惰而偏好读书找到了理由:“我们被迫与书一起生活。”可是,等有时间仔细推敲,不免又疑惑起来,在没有书之前,不是照样有人做出了卓越的事功吗,为什么我们要“被迫与书一起生活”?再翻开这篇文章,原来施特劳斯已经提前给出了理由:“一个未开化的社会,在其最好状态中是由沿着原初立法者,亦即诸神、诸神之子或诸神的学生传下的古老习惯统治的社会;既然还不存在书写,后来的继承者就不能直接地与原初的立法者联系;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否偏离了原初立法者的意图,是否用仅仅人为的附加或减少去毁损那些神圣的消息;因此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不能前后一贯地按其‘最好即最古老的原则去行为。只有立法者留下的書写才使他们向后代直接说话成为可能。因此,企图回到未开化状态是自相矛盾的。”
这次因为重新读《朱子读书法》,在其中一个编定者张洪的序里,竟然看到了相似的话,不禁惭愧自己因读书少而来的多所怪:“皋、夔(舜帝时贤臣)所读何书?世率以斯言藉口。岂知帝王盛时化行俗美,凡涂歌里咏(路途邑里的人歌唱吟咏)之所接,声音、采色、乐舞之所形,洒扫应对、冠昏丧祭之所施,莫非修道之教,固不专在书也。三代而下,古人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恃以植立人极者,惟有书耳。此书之不可不读也。”作为“古人养德之具”的歌咏、乐舞、礼仪,都可以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诸神、诸神之子或诸神的学生传下的古老习惯”,不必非得读书然后有获。或者照朱熹的说法,“上古未有文字之时,学者固无书可读,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读书而自得者。但自圣贤有作,则道之载于经者详矣,虽孔子之圣,不能离是以为学也”。参照施特劳斯的意思,我们不妨说,“圣贤有作”差不多是开始书写的立法者一种特殊的断代,表征着历史自此进入了可供检视的记载时代。由此,或许可以解开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即便传统有所谓“最好即最古老”的原则,那也说不定正是圣贤(立法者)有意书写下来的,以便为这洪荒的人世确立某些可以凭靠的路标。
可惜的是,像我这种资质愚笨的人,尽管明白不得不跟书一起生活,仍然难免在读书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书一时提不起兴趣该如何?明白读书的重要已经太晚怎么办?读的时候悟性太差又该怎样对治?每个想读书却不得其法的人,是不是都有如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问题,也是“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朱熹恐怕就没少遇到(对他这样层次和声名的人来说,只会更多)人来问,或许因此他才会跟学生说:“读书……只认下着头去做,莫要思前算后,自有至处。而今说已前不曾做得,又怕迟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个难,又怕性格迟钝,又怕记不起,都是闲说。只认下着头去做,莫问迟速,少间自有至处。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补填。莫要瞻前顾后,思量东西,少间耽搁一生,不知年岁之老。”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一次讲座之后,有人问讲课的老师,我想努力读书,您觉得应该怎么做才对呢?老师回答说,努力没用的。问的人一愣,继而问,那您的意思是不必努力了?不努力更没用,老师接着回答。问话的人一时没了方向,讪讪地坐了下来。我在旁边听了这问答,自此便多了件心事——在问答的缝隙里,什么才是对的呢?现在有了朱熹这段话,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把这话作为对的方式呢?进一步推求下去,是不是可以说,那个提问的人,或许问题本来就提错了。如果已经努力读书,本身就已经在做应该做的,哪里还有另外的心思呢;如果还没有努力,当然就谈不上对错了。再进一步,提问者如果就自己努力读书之后的心得向老师请教,那会不会更为直接而有效呢?沿此再进一步,或许提问者的问题本身才是读书应该解决的,把心力收束在这个地方,“莫要瞻前顾后,思量东西”,问题或许就会消失吧——就像老师后来讲的,“有问题没答案,没问题有答案。”
我很想确认,上面朱熹的话和老师的那番回应,可以作为最好的读书法,此外不需要寻找另外的路径了。可我也很担心,这样的想法恰恰是我自作聪明寻找出来的捷径,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可能偾事。何况,人的资质和境遇各不相同,大部分人——尤其是资质相对普通的人(真的足够聪明的人,哪里需要向人请教怎么读书呢),会希望自己有个具体的把手,可以借此往高处宽处走去。也果然就有人这样问过朱熹:“问性钝,读书多记不得。(答:)但须少看。熟,复子细推求义理,自有得处。”这话看起来无甚奇特处,平实得让人心生疑虑没错吧?世上真有性钝的人能读书有得吗?
时举(朱熹弟子)云:“某缘资质鲁钝,全记不起。”先生曰:“只是贪多,故记不得。福州陈晋之极鲁钝,读书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积累读去,后来却应贤良(古代选拨人才的科目)。要之,人只是不会耐苦耳。凡学者须要是做得人难做底方好。若见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缘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大约有十年时间,我始终困扰于一个问题不能自拔,即我是不是适合走读书这条路。如果不是天生的读书种子,每天在书的外围打转,无法深入以求,却扮演着喜欢读书的样子,岂不是玩物丧志?这情形要到我遇到一个特殊的机缘才得以缓解,现在看,也不妨用朱熹举的这个例子作为榜样。我还记得我读到这个例子时的激动,仿佛陈晋之是一类特殊的先知,以其鲜烈的鲁笨者形象,在因资质而遇到的精神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提示出性钝者读书有得的可能性。《论语·雍也》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的这种举例方式,大约就是“能近取譬”的绝好诠释吧。
上面的情形大概还可以稍作推广,即不用先确认自己是性钝还是性利,只根据自身的情况与世界或书相处,遇到问题,则“因其势而利导之”,“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遇聪明就在聪明上做工夫,遇鲁钝就在鲁钝上做工夫,不用拿出多余的精力去思量分别,提前用性钝之类为自己的不成功找好理由,而是沿着自己性情的方向专心读下去。如此,书或许会在某些瞬间敞开自己紧闭的大门?
三
前些日子跟一个朋友见面,他很郑重地跟我说,他忽然不知道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还需要写作,如果写,要写些什么才好。我愕然,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应。后来,我偶然翻开阿兰·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在临近结尾的地方看到一段话,觉得可以回应朋友的问题,便抄下来送了给他:“一位认真的学生在读完柏拉图《会饮》后,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他说,难以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氛围还会再现。那时人们友好和睦,富有教养,朝气蓬勃,珍视相互间的平等关系,既文明开化又富于自然情感,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意义。然而,这种体验总是可以得到的。实际上,这场戏剧性的对话恰恰发生在一场可怕的战争期间,雅典已经注定陷落,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够预见到,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但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他们并没有陷入文化绝望,而是尽情享受着自然的欢乐。这恰恰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生存能力,证明了人独立于命运的趋势,不屈从于环境的胁迫。”
人们很容易对自己置身的时代不满,即便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们,也“总是四处抱怨一切事物看起来多么的黄”。可细想一下就差不多可以明白,精神性的对话,阅读和书写等精神活动,可能永远无法自如地挑选时空。无论我们准备得如何充分,最后,恐怕都不得不迎头遇上那些必然的艰难时刻。不用说阿兰·布鲁姆提到的险恶环境,即便是一本稍微艰难些的书,都需要一点克服的力量,因为“人是靠辛苦的陶冶而成其为人的”,精神生活上轻易获得的贫薄快乐往往“令人生厌——它败坏了那开头艰涩、终而美妙的精神事物的滋味”。何况,即便通过努力弄清楚了某些书中深含的意蕴,写出那些伟大的书的伟大心灵,“在最重要的主题上并不都告诉我们相同的事情;他们的共存状况被彼此的分歧、甚至是极大量的分歧所占据”。大概不妨说,几乎在读书过程每一个可能的点上,都有艰难伴随。
或许,在准备进入一本可能艰难的书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像澳大利亚的矿工们一样生活?我的丁字镐和铲子是不是完好无损?我自己的身体行不行?我的袖口卷上去了没有?我的呼吸正常吗?我的脾气好不好?”在这种询问之中,读某本书之前,人其实已经进入自我调整状态,也即已经达到了跟读书相似的自我校正状态——这大概才是读书的意义所在。读书,并非捧着一本书摇头晃脑才算,阅读前对艰难所作的精心准备,阅读后对所读之义的反复思量,都可算是读书的状态。这种状态聚集起的能量,便如朱熹说的那样,“如天地之气刚,故不论什么物事皆透过”。因此,人“凡做事,须着精神。这个物事自是刚,有锋刃。如阳气发生,虽金石也透过”,“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转去,如何做得事!”这阳气发生般的能量,不妨看成克服艰难时“刚决向前”的意气和锋芒,会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朱熹说上面其中一番话的时候,居然罕见地举起了酒杯,说“未尝见衰底圣贤”。读到这里,我几乎能看到朱熹宽和外表下锐利而饱满的一笑。
卡夫卡曾在自己的一个八开本笔记里写过:“人类的主罪有二,其他罪恶均由此而来: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把这个意思挪到读书上来,上文所说的勇猛精进,恐怕只是克服阅读艰难的一种方式。因为艰难总是与读书长时间相伴,故此在勇猛之外需要济以耐心:“读书别无法,只要耐烦子细,是第一义也。”“读书需要耐烦,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药,初煎时须着猛火,待滚了,却退着以慢火养之。”“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且不可粗心。若曰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认底深坑也。未见得道理时,似数重物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
我很担心上面的说法过于强调读书的艰苦了,因而会坏掉一些人读书的好心情——如果读书只是不停地克服艰难,没有实质性的身心安顿,人怎么会又怎么愿意去读书呢?我想起老师在讲《诗经·风雨》的时候曾说过:“风雨是天地,环境为乱世,鸡鸣知时而报晓。‘鸡鸣喈喈就是信心,然而单凭信心还不够,还要看到确实的人,这就是‘既见君子。鸡不停地鸣叫,一定要叫破黑暗,引出曙光,把晴朗的天召唤出来。鸡鸣是上达之象,从没有希望中真正找到希望,必须把握到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处于阴阳变化中的君子。阴阳相配,性命相合,得到物质上的支持,生理上的反应变了。”读书恐怕也是如此,要把握到实质性的东西,读书才不是消耗多余精力的消遣,而是变成一种精神上的负熵,在某个特殊的点上为人补充真正的能量——
凡看文字,端坐熟读,久之,于大字旁边自有细字迸出来,方是自家见得。
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鹘突,都只见成一片黑淬淬地。须是只管看来看去,認来认去。久之,自见得开,一个字都有一个大缝罅。今常说见得,又岂是悬空见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见得。文字只是旧时文字,只是见得开,如织锦上用青丝,用红丝,用白丝,若见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长期读书有所会心的人,看到朱熹的这些话,肯定会觉得亲切吧?读一本有品质的书,往往先是不得其门而入(都只见成一片黑淬淬地),每个字都认识,却无法读懂其最核心的内容。认真地读下去,某个瞬间,字与字之间(大字旁边)现出缝隙(缝罅),另外的字跳出(有细字迸出来),这句话豁然开朗,读的人切切实实从句子中获得能量,身心有所振刷。继续认真读下去,细字开始在每句之间迸出,那本看起来一片混沌的书(一片皂布,浑沦物事),开始显现出自己的内在结构,一点一点(用青丝,用红丝,用白丝;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清晰起来,夺人的光芒从整体灰扑扑的文字中跃动而出(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读的人感受到来自精神深处的透彻之光,由此照亮心中原本昏暗的一隅,内心深处的某处获得无比绝对的休息,从而脉解心开(脉络自开),身心为之舒展。
这个状态是不是足够吸引人?读书到这一步,是不是会感觉到心中充满力量?可是,我非常担心描摹出的这种情形,最终会变成一个原本出色的读书人的化城。因深入阅读而来的身心舒展之感,应该是随着读书深入而自然出现的,描摹出来,很容易把人的专注力误导到追寻这个状态上去,反而丢了朱熹一直强调的沉潜踏实功夫,因而成为进一步读书的巨大障碍。“月明帘下转身难”,为了避免卓越的读书人耽溺在这美好的境界里,再次强调读书必须先切己与踏实,或许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四
在柏拉图的《阿尔喀比亚德》中,苏格拉底以一贯的方式提问:“认识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呢,还是像德尔斐神庙的铭文那样轻而易举,抑或艰难而非所有人的事。”继而接着说:“无论那是否容易,于我们而言都意味着:认识了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关心我们自己,不认识就永远不知道。”有人从这个说法推断,“关心自己本来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方式,但为了能够关心自己,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己,然后才知道如何加以关心”。这一“认识你自己”问题,因其来源的神圣性及苏格拉底对其意义的丰厚赋予,一直盘旋在西方思想的关键位置,在很多精神世界的关键时刻成为纠正性的力量,不至于让某些头脑游戏把人带走得太远,是世界的幸运。
在中国,则可以举出《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安国注:“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朱熹《集注》引程子云:“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并加按语:“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在谈到读书时,更是于此义反复提撕:“今之学者不知古人为己之意,不以读书治己为先,而急于闻道,是以文胜其质,言浮于行,而终不知所底止。”“学者之病,在于为人而不为己。若实有为己之心,但于此显然处严立规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将,不令退转,则便是孟子所谓深造以道者。”只是,在体味“认识你自己”和“学以为己”的时候,不知是否有人跟我有相似的疑惑,什么才是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为己的方式?有没有提示性的把手可供参考?舍近求远查了很多书,仍然没能释疑,倒是这次在朱子读书法里,看到不少例子,或许可以作为有益的借鉴——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到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
入道之门,是将自己个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元不曾相干涉。
圣人说话,岂可以言语解过一遍便休了?须是实体于身,灼然(清楚)行得,方是读书。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人,看到圣人、道理这样的词,心里会生出些厌倦来吧?那不妨试着把“圣人”换成“伟大的心灵”,把“道理”换成“哲思”,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是不是感觉就好了一些?其实每个不同时空中都会有名相的多种变化,即如先秦论道,宋明言理,西方说哲学,儒家称圣,释教称佛,西方称哲人,不妨都看成对某些高端思维或达至某些思维级别的人的尊敬,不用先在心里存个成见。慢慢消除了名相造成的滞碍,古人或异域人的很多话,其实一直跟我们现在相通。朱熹上面的话,差不多就是“古之学者为己”(“认识你自己”)的反复解说——要全身心投入那些卓越的书中去,与书中所言相亲,把读书所得在自己身上推究,并见之于行事,这样才算得上是读书。舍此而往,只在纸上辗转,恐怕算不得真正的读书。
不过,上面所说的名相转换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即非常容易把现代(变得单向化的)语言置放进古人的言语中,因此怎么想都不过是在自己固有的思维里翻筋斗,无法真正“身入”古人的世界。更有甚者,贸然以己意为古人之意,或者立异以为高,就更加失去了读书的可能意义。朱熹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反复向学人申说:“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惟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今来学者(读书)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读朱子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几乎句句中己之病,不免汗涔涔而下。
仔细思想起来,不管读书还是学习,是因为曾有一些伟大的心灵走到了险峻的思想山峰或开阔的精神平原,我们平日无缘得见,只好借书中的话尝试跟随他们到那些地方去,以此来校正自己的庸常与狭隘,“所以读书,政恐吾之所见未必是,而求正于彼耳”。如果读来读去只不过读出来一个自己,那读书的益处恐怕也就有限了。朱熹举苏洵读书为例:“老苏自述其学为文处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这个过程,就是读书祛除私意的过程:“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之自然有得。”有了这个得,人才能通过读(经典)稍微调整自己思维的运行轨迹,以期脱离思想的窠臼,走进可能的精深思想领域,用朱熹经常引的张载的话来说,就是“读书有疑,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如此不断校正自己,去旧见而来新意,则书中的“道理与自家心相肯”,见得那些伟大的心灵“如当面说话相似”,恐怕才是读书有所深入的标志。经过这样的校正和梳理,书才不是逝去者的遗迹,而是可以觌面相见,数百数千年的时间,差不多只是一瞬。“一旦我们对生命所知更多,莎士比亚就会进一步评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那些伟大的书,只要以特有的小心去反复阅读体味,就会不经意间参与我们日常的讨论,“如见父兄说门内事,无片言半词之可疑者,什八九也”,从而让我们得以跟随伟大的心灵一起解决面临的无数问题。是的,我想说的是,人有时候正是因为置身于这样一条长河,才能看到生生不息的力量,才不会时时感觉空虚寂寞。
五
文章写到这里,原本应该结束了,但后来想起一个问题,还是觉得应该再说几句。自汉代佛教传入,加之中国原生的道教不断吸取各家的内容,出世间法在唐宋之后越来越有兴盛之势,儒家为保持自家位置,难免对此有所防范。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朱熹谈论读书法的文字里,或许是出于后人的有意,或许朱熹本人就有此意,主要谈论的是四书五经,基本上排斥了佛、道的内容,偶有提及,也殊无表彰之意。翻看朱子其他各种文字,关于佛、道的内容也算不上多,排斥的部分也远远大过肯可。当然,很少有人或学说在跟对手的交锋过程中完全不被对方影响,唐宋(甚至更早)的儒家当然也如此,面对佛道造成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以力辟的方式拒斥,一方面也不断吸收着对方的优点,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分不清其究竟来处。
即如朱熹,从儒家经典里特为突出“四书”,就应该带有回应并吸收二者思想的意味——如果不是有自己置身時代的迫切需要,朱熹这样对圣贤之言无比推重的人,哪里需要抛开更权威的“五经”而倡导“四书”呢?可就是这样的朱熹,早年曾学道学禅,“出入于释老十余年”,晚年还化名空同道士邹而作《周易参同契考异》,不但考证精审,且“于内丹之理能味乎其身”。也就是说,在讲授过程中总体上排斥佛道的朱熹,自己读书却并不局限于儒家,说不定早岁的十数年间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判教。这差不多等于给后来的我们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我们该不该跟随朱熹推荐的书而且按他的方法来读呢?忘掉了朱熹自身的知识来源,读书的航道会不会越来越窄?
列奥·施特劳斯曾在某处说:“我们应当倾听的最伟大的心灵并不只是西方的。妨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心灵的仅仅是一种不幸的被迫: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我们不可能学习所有的语言。”生逢如今这时代的我们,遇到的差不多是跟施特劳斯反向的相似难题,或者,这里说的几乎是每个爱好读书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境况——根据变化的世界情境选择读书的种类和方式,几乎是读书人的天然命运。我们现在应该倾听的伟大心灵,早已不只是古代的儒释道,也包括西方及起源于其他地域的各种各样作品。即便通过翻译和其他有效的学习途径,有机会听到这些伟大心灵的声音,我们又该相信哪些,不相信哪些呢?朱熹和其他先贤提供的读书方法,是否必然要经过一次艰难的现代损益?损益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没领会错,除了某些极为特殊的机缘,解决读书遇到的问题的唯一途径,应该是继续读书。比如我对自己上面提出的问题一筹莫展,就寻出朱熹反复提示先读的《大学》来看,翻到朱熹写定本的第二章,忽然觉得此前的郁塞有松动的迹象,隐隐感受到了点儿振奋的能量。那就不妨抄写下来,以此作为包括读书在内的每个一筹莫展时刻的提醒——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