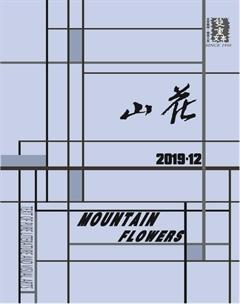动物(四首)
龚学敏
蛤 蟆
隐身在中药秘方的软泥中,咕嘟出
阴冷的险招。汉字的手推车,
把活路与末途的分界线,牵引到
放大的中药里。
坐在尽头的夕阳,一跳,
混凝土像春天的铠甲,
池塘与此生已是无缘。
丑陋作为防腐剂,涂在童话中,
天鹅丧失性别,
把美丽平摊给每一个生锈的童年。
人工林圈养的潮湿,
已经不足以产生真正的丑陋。
那些高贵的丑陋,如同失传的秘方,
在软泥的眼神中,
一动不动,像是吹过的风,被少年
拾进来路不明的童谣中。
天鹅的绳子在空中不断地升高,
所有的人整齐地抬头,
向绳子的童年,
行注目礼。
蟋 蟀
《聊斋》线装的瓷盆被促织搬到保鲜膜
提供的露珠上。
不同的外号,像是画在同一张纸上的
不同代码。程序们如同彼此谅解的麦穗,
把田野,挤成拖拉机拓展出的广阔。
激素将刀在纯净水中磨得透亮。
塑料品質的水,
在秋天的底牌上,瓦解季节的外套,
和拉长的夜色。虚假的繁殖把器官,
卸给一片片残疾的汉字。
翻新的庙宇,油漆味警告性别相同的草丛,
土穴,和被传说遗弃的砖头,
移植过的野外,与众多的翅羽交配。
钟声被噬碎,洒成一地的月光,
凸出的黑,像是被游戏攥皱的纸巾。
依次朝上亮着灯光的楼房,演练着
暮色的仪式感。
田野日渐收拢,
精致的事物,包括工厂中的过程,
被一页书冻僵的翅,
鄙视在想象贫乏的玻璃中聊《聊斋》。
狈
已经灭绝,
只是在汉字堆砌的成语的遗址上活着,
让学生作文时,形容人。
河 马
硕大的皮朝着干裂奔跑,地球的卵
日渐升高体温,
河流的水的鸟一只只飞离树枝,皮肤
干裂出的树枝。
非洲用土著的方言一边怀念,
一边被水越洗越浓,像是一块被博物馆
点燃的炭。
气温高过水草,水先死了。
气温高过树枝,树枝上的方言先死了。
气温高过河流,河流到的地方先死了。
给地球生火的人,用钻井的火柴,
偷听密码。
知道得越多,水越少,
河流的树枝越细,抽在博物馆标本上的
目光,越痛。
硕大的嘴和远处夕阳的烧饼之间,
是用衣服站立的人类。
从地上生长的棉,
到地下流出的腈纶的口号,烫手的口号,
地球像是童年的山芋。
我是水浸泡的药,
整个江河是我流向大海的酒,我的药力
越来越小,直到成为扔在河床上的
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