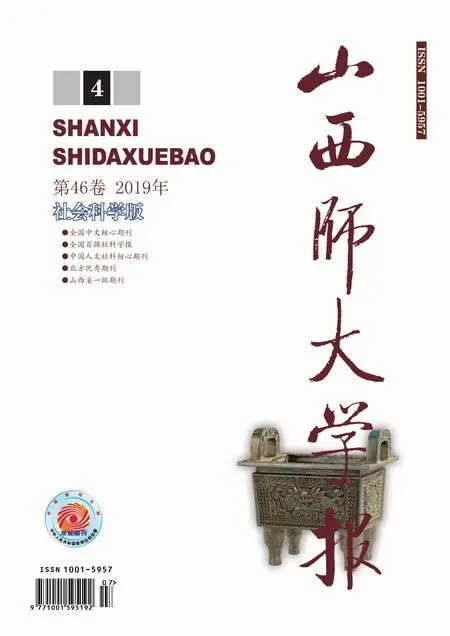论古代女扮男装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及其性别启蒙意义
孙 萍 萍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女扮男装”含意丰富,既指文学作品中女扮男装的故事题材,也指女性作家发表作品时用以隐藏自己性别身份的男性化的署名,还有研究者指当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女尊文”“女强文”所着力的“女强男弱”“女尊男卑”的叙事策略。[1]168本文所指属于第一种情况。
在中外文学史上,女扮男装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西方如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终成眷属》《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中国如南北朝民歌《木兰辞》,徐渭的杂剧《雌木兰代父从军》(简称《雌木兰》)、《女状元辞凰得凤》(简称《女状元》),冯梦龙的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刘小官雌雄兄弟》,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及清代弹词《再生缘》《玉钏缘》《玉连环》等作品。中国古代女扮男装题材作品似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人们的审美愿望,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性别文化规范及女性的社会处境。作品塑造了一群易装突破性别陈规,才华横溢、有胆有识进入广阔社会空间的女性群像。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无疑在当时社会有着积极的性别启蒙意义。
一、女扮男装文本叙写的多元化
中国古代女扮男装题材文学创作出现了几次高潮。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逐渐崩溃,名教的道德体系也受到挑战,礼教对人的束缚尤其是对妇女生活的禁锢不断被打破,女性走出闺阁,或参与社会生活,或执掌家务大权。女扮男装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随之涌现,并展现讴歌了女性的才华和魅力,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北朝乐府诗《木兰辞》;其次是唐代,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出现了女诗人、女政治家,相应地,在唐传奇中出现了女扮男装题材的作品。再次是明代。宋元时期,封建礼教的各种礼教秩序把对妇女的约束推到了极致,关于女扮男装的传说及文学创作十分罕见。明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及市民阶层的出现,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反封建、反宗法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妇女问题也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扮男装题材的作品。如徐渭的杂剧《雌木兰》《女状元》,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刘小官雌雄兄弟》等。最后是明末清初时期,循着明代中叶反理学的解放思潮,随着知识分子李贽、钱谦益等对女子才华的肯定推崇,文坛出现了女扮男装题材创作的高潮,主要有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春柳莺》《凤凰池》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弹词女作家如陈端生、邱心如、程蕙英等,创作了大量女扮男装的题材的作品。
由此观之,作为文学创作的传统题材,该类型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文化氛围有着紧密的关系。以魏晋为例,玄学涌现,道盛儒衰;官办教育衰微,家族教育昌盛;门阀士族制度使得高官贵族们非常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贵族女子也是这一时期私学兴盛的受益者。宗白华先生评价这一时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史书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多位优秀女性:有“林下之风的咏絮才”的谢道韫;有被赐号为“宣文君”“隔绛纱受业”《周官经》的“十六国时期”前秦女经学家韦氏;有因《中兴赋》被赏入宫,后担任博士,教六宫书学的南朝女作家韩兰英;有南朝刘宋时期著名的女诗人鲍令晖等。钟嵘在《诗品》中写道:“令晖诗歌,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2]22对两位才女的诗歌成就、艺术特质做了精准的评价,也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状况的重要参考。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写的小说《世说新语》中描绘人物约五六百人,其中女性占到1/4强,另单列《贤媛篇》专写女性共计23位。正如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所言:“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3]66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关注更多偏向于女性的智慧和才华。魏晋女性在接受教育方面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在家庭事务、子女教育及文学文化艺术等方面较前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关于女扮男装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还有一种现象,即同一故事内容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呈现出来,使得这些故事在反复的被书写、被叙述、被阐释中成为经典,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以木兰故事为例,如:“作为道德楷模的木兰形象,由于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赞扬和崇拜,被广泛传播,是接受度较高的人物形象。”[4]15木兰故事大量存在于各种诗词、文章、小说及戏曲中。木兰故事的源头是北朝民歌《木兰诗》。唐宋时期是木兰故事的生成期,“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韦元甫《木兰诗》强调木兰的孝顺及其高尚的道德,确立了木兰孝道偶像的形象。宋代的木兰故事多以典故的形式出现在诗词中。元明时期与木兰故事相关的文献数量大增,有了第一部以木兰为主角的杂剧《雌木兰》,作者进一步丰富了细节,增加了人物和情节,木兰故事也走向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更为世俗化。清代是木兰故事叙写的集大成时期,出现了诗词、笔记小说、章回小说、戏曲、鼓词、子弟书、宝卷等多种文体,长篇小说和传奇作品中木兰故事规模变大,内容增多,情节也越来越曲折丰富。而历代学者在叙写这个故事时,其不同的政治环境、两性文化、文人心态等因素影响了对故事各个文化主题的叙述,使得木兰故事在不同时期的叙述中呈现不同的形态。
二、女扮男装突破性别陈规
中国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强化了两性的自然差异,弱化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性别制度,出现了一系列规训女性行为的性别文化读本如《女训》《女德》《女诫》《女则》《列女传》《孝女经》《女论语》等,这些都是从男性中心出发要求女性,将女性边缘化、弱势化,女性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被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环境中,被限制了社会活动的范围及才能的发挥。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逐步形成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性别秩序。封建社会女性的主要活动范围框定在家门之内,主要事务为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她们的人生价值及意义更多地附着在丈夫及儿子的功名利禄上。日常生活中男女“不同巾栉”“男女不通衣裳”,易装被视为是有悖礼法的行为。除了戏曲表演等特殊情况外,通常男扮女装被视为投机取巧,是一种耻辱;而女扮男装被看作是女性对男性权利的僭越。《南史·崔慧景传》中记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还为老妪,岂不惜哉!’”[5]143真实记载了南齐女子娄逞女扮男装做官升迁后事发被免的事。
古语“女子无才便是德”常被视为“反女才”的名句。根据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的考证,该句起源于明末。[6]190其确切出处应该是明晚期文人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文中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解释道:“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陈继儒的本意不是“反才”,而是强调儒家传统的“德本位”“德重于才”的观念,主张男性应以“德”为本;对女性,更重视她们的德行,不主张更不要求才学。而晚明时期“才女文化”的兴起,恐“才可妨德”,故有此语。因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真正意涵不在‘反才’,而在‘正德’;其‘反才’口吻是在儒家‘轻才’传统的惯性推助下产生。”[7]55类似还有如“世之女妇,德胜于才,家之福也;才胜于德,家之祸也。如有聪明才智达古今者,可吊不可贺也”等反女才的言论。由此观之,儒家传统将“德”放在首位,尤其对于女性要求更严格。封建社会基于性别的双重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使得男性建功立业求取功名,施展才华有广阔的社会空间,而女性稍有不慎,便可能违背妇德。
而易装以男性的身份进入社会公共空间,使女性摆脱道德枷锁的束缚,一方面享受男性的性别身份特权,体验男性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获得了在处理社会事务中施展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和平台,获得一种主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古代文学中出现许多“女扮男装”特立独行的女性,她们以“女扮男装”形式打破性别壁垒,突破性别陈规,参与社会事务,展现女性的才学和胆识,作家们运用虚构的故事情节讲述现实社会中女性被淹没的才华。
(一)征战沙场,保家卫国
自古保家卫国、征战沙场、建立功勋都是男儿的志向与梦想,按制度,女性是不允许从军的。但在极端特殊情况下,也有女性带兵驰骋沙场的记载,例如西汉末年反抗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领袖吕母、迟昭平,帮助父亲李渊起兵反隋、带领军队驻守娘子关的平阳公主,协助丈夫韩世忠抗击金兵的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明末代领夫职的著名女将秦良玉,等等。历史中存在的女性征战沙场的史实为作家构思情节塑造人物提供了基础。在我国通俗小说史上著名的“三大家将小说”《薛家将》《杨家将》《呼家将》中,也塑造了如佘太君、穆桂英、樊梨花等武艺超群、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女将形象。不同之处在于,家将小说中的女将能够顺理成章地带兵打仗缘于她们身份的特殊性,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出身于英雄家族,担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她们作为家族男人们的辅助出现在战场上。而作为平民的花木兰只有易装才能进入军队,而且努力要伪装自己的第二性征,掩饰女性的性格特征,因此女性娇柔的一面就不能在作品中肆意表现。
木兰女扮男装征战沙场之后回归闺房的行为才得以被世人接受和原谅。借着尽孝缘由奔赴战场,也间接实现了她的远大志向。“趁着青年,靠着苍天,不惮艰难,不爱金钱,倒有个阁上凌烟。不强似谋差夺掌把声名唤,抵多少富贵由天。”[8]48争“阁上凌烟”倒成了木兰上战场的最好理由,而“乌纱亲递来克汗”也表现了女子有同男子一般保家卫国、成就功名的可能。
(二)入学竞考,为官为相
在古代,女子是不允许进入官办教育机构学习的,更不可能参加各种选拔考试进入政府系统任职。皇宫里主要由女性掌管后宫事务,但不得参与干涉朝廷事务。例如唐代内廷有宫官制度,系仿照朝廷六部尚书制而置,分设六尚,下统二十四司,分掌宫廷事务。女性易装考取功名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徐渭的《女状元》是以五代才女黄崇嘏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杂剧,剧中人物春桃自诩“生来错习女儿工,论才学,好攀龙。管取挂名金榜领诸公”[8]62,又说“不是我春桃卖嘴,春桃若肯改妆一战,管取唾手魁名!那时节食食禄千钟,不强似甘心穷饿?”[8]62明代经济的繁荣发展虽然带来了教育的普及,但封建科举取士制度仍将女性排除在外。于是春桃乔装成男儿参加科举,就像她自夸自信的一样,果然一举中第成了状元郎。徐渭的《四声猿》之后,明代的短篇小说还有《喻世明言》第28卷里“李秀卿义结黄贞女”的故事,在《二刻拍案惊奇》里也有“女秀才”的故事,这些都是黄崇嘏女扮男装故事的改编。明末清初出现“才女崇拜”思潮,鲁迅曾评价明清时期的文学是“显扬女子,颂其异能”[9]119。在这样社会风气的推动下,女扮男装题材的作品在清代弹词和小说中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其中,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颜氏》中聪慧善读的颜氏因丈夫无能平庸、屡考不中,便负气易装考试,不想丈夫落榜而她却通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后中进士授官桐城令,然“深恐播扬,致天子召问,贻笑海内耳”“于是使生承其衔,仍闭门而雌伏矣”[10]581。还有清代弹词女作家陈端生《再生缘》中因被逼婚而女扮男装出逃,后考中状元官至宰相为夫婿洗刷冤屈的孟丽君。剧情发展到孟丽君即将被识破女性身份时便搁笔没了下文,后是由弹词女作家梁德绳根据前面的故事发展脉络续写完成。孟丽君反抗男权社会种种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也恰恰是陈端生对当时女性命运的思考,女作家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中与男权势力做最后的抗争。
(三)自立自强,德才兼备
从男性功名标准去审视,女扮男装题材中的大多女性角色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当然女主人公易装本身就是僭越规矩、不守妇道,所以德才兼备是从男性的标准去衡量的。故事中的花木兰因为“尽孝”易装替父从军,除了对长辈的孝和对国家及国君的忠诚,凯旋后作为兄长身份的她对弟弟妹妹表现的关心爱护,也展现出她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在《雌木兰》中亦有:“万般想来都是幻……我杀贼把王擒,是女将男换,这功劳得将来不费星儿汗。”[8]51木兰不仅具备了战场上格斗的基本技能,而且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志向,作为长女,替年迈父亲奔赴沙场毫无推脱。也是因为心怀对家国的大爱,才能战无不胜,载誉归来。
《女状元》中的主人公黄崇嘏,本是位千金大小姐,怎奈家道突然中落,只有奶娘可相依为命,为了生存而女扮男装参加科举,做官后也没有因为奶娘卑贱的地位而抛弃她,并且答应与奶娘平分俸禄,没有半分犹豫。虽名义上有身份贵贱之分,但奶娘多年的不离不弃、养育之恩,她已视奶娘为亲人、为长辈。至于当官,黄崇嘏也真是为百姓办了实事。徐渭说过:“嗟夫,世独忧无善言者,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昌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事之所以日敝也。”[11]529在这样鱼龙混杂背景的官场之上,黄崇嘏深知百姓疾苦,为百姓申冤平反,守护着百姓的安宁。而陈端生笔下的孟丽君女扮男装是有着“愿教螺髻换乌纱”的愿望,当她真正成就功名,却自问“为什么,弃将紫蟒和玉带?为什么,换就霞帔和红裙?”“何喜洞房花烛夜,蟒玉威风过一生”,不想说破自己的真实身份。冒着“搅乱阴阳、欺君罔上”的罪名,继续扮演着自己的男性身份。孟丽君“篇篇珠玉高兄长”阐明的是她自身对女子无须有才只需要顺从丈夫的社会心理的反抗;当皇帝赞叹她“千秋世界全凭你,一国山河尽仗卿”时,是对她能力出众的肯定;“何必嫁夫方妥适,就做个一朝贤相也传名”道出了她的愿望,也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为了这个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毅然舍弃自己的终身大事,将女性谋求独立自主的意识展现得更为突出。
三、女扮男装催生性别意识觉醒
女扮男装题材在魏晋时期出现,经历唐宋时期的发展,在明末清初出现高潮,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真实生存境遇的关注与思考,对被淹没的女性才华的肯定与赞扬,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与惋惜。作为伫立时代潮头、关切国家民生百姓生死疾苦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遏制人性发展的性别秩序进行着艺术的反思和批判。此类题材的创作体现了作家性别意识的初步觉醒,觉醒意味着对原本自以为是、习以为常、看起来合理而正确的性别规范进行质疑和反思,其中也包括对性别秩序中男性的种种期待和规定,同时也不排除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借助人物寄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期望。
(一)男性作为启蒙者的启蒙与被启蒙
女扮男装故事的构思书写者多为男性,他们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被淹没的才华,也意识到了封建性别文化对男性和女性人性的束缚,女性没有自主权被困在家庭中,男性被捆绑在考无止境的求取功名的战车上。因此作家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借助作品中人物的种种际遇来影射自己的现实生活。不论是徐渭、蒲松龄还是沈复,封建社会男性求取功名的道路都异常艰难。徐渭才华横溢,郁结于报国无门,写花木兰征战沙场,部分地将内心愿望托付于笔下的人物,塑造了易装的木兰可以骁勇善战、保家卫国,与现实中自己身为男儿却是无法征战四方形成强烈的反差。徐渭学识渊博,怎奈屡试不中,于是借笔下的黄崇嘏官至宰相,弥补自身在现实仕途上的遗憾。蒲松龄借女性易装考取功名的故事来讽刺社会的黑暗,男子未必达成的事情让区区小女子做到了。李贽也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12]144肯定了女性的才华,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及初步的性别公正的意识。
清代沈复在记述自己生活的散文集《浮生六记》中写道:“余常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13]30其妻陈芸聪颖贤惠,能吟咏诗句,与丈夫沈复“常寓雅谑于谈文论诗间”,但因女性身份的限制,不能随同丈夫参加活动或出游。于是沈复说:“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13]37于是“易髻位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13]37,他们还真去水仙庙携手同游了一番,其间陈芸还有几番迟疑,沈复强行挽着她去。丈夫在这里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是夫权的自我放逐,也是对这种不合理的性别规定的挑战。
(二)女性作为被启蒙者的被启蒙与启蒙
男性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女性才华的肯定和赞扬,借助于文学的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人阅读和思考,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人的意识的进步。明清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明清时期中国女性,既体现传统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又昭示着现代女性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一种从传统到现代嬗变的态势。”[14]113其时江南闺阁文学的繁荣兴盛就是例证。清代弹词女作家陈端生结婚时,丈夫还未中举。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发生在顺天乡试的科场作弊案中,丈夫牵连其中,被发配到新疆服刑十年,陈端生孤苦伶仃抚养子女。其笔下孟丽君为救夫君女扮男装参加科考进朝做官,而大功告成时却不想还原女性的身份,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孟丽君不是按照礼教的规训退回家庭,而是继续在官场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一种成就感和存在感。同时作品对封建社会男子求取功名的艰难历程进行反思。作者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挫折,十二年后再续写《再生缘》时,面对朝廷对孟丽君性别及身份的怀疑及整个男权社会的声讨,使她不知该如何下笔。作为女性作家的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在其中凸显出来,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所做的预见性的思考。
另一方面,从这些女扮男装的作品内容看,也体现了男性作家自身的阶级和性别的狭隘性。文中几乎所有的女性易装都是为了求取功名,始终没有摆脱封建社会主流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同时,女性女扮男装的缘由或是为父、或是为夫、或是为家族,都没有摆脱男性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这种觉醒只仅限于男性主体或者男性立场之上,女性处于“他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