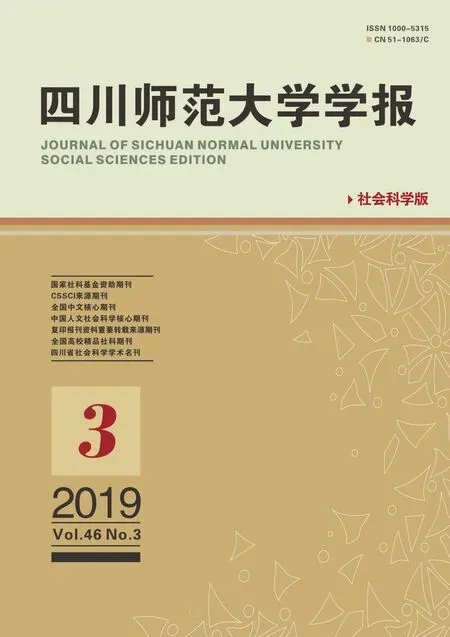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处境恶化
——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社会根源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明治后期,日本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从外部考察,是由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从内部考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治时期,由于新政府“殖产兴业”国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各行业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二律背反”现象——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处境日益恶化的这一现实矛盾却并未能避免,劳动者的待遇和处境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提高和改善,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各地劳动者处境恶化的信息不断流传于世,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社会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因此与日俱增。随着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这种人文关怀思想逐渐演变,导致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因此,要研究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生长,不能不深入考察明治时期生产力发展前提下劳动者的处境恶化状况。本文拟依据当时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作深入考察,以探索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萌发的内在社会根源。
一 明治时期日本经济迅猛发展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依靠国家的力量,在日本全国推行“殖产兴业”的国策。政府施行各项政策,推动资本主义产业在日本各地兴起和发展。在这种政策的扶持下,各行各业迅速崛起,加上欧美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到明治20年代后,日本经济呈现出百业兴旺发达的局面。
日本明治时期经济迅猛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铁路大量开通。“经济发展,交通先行”的规律,在日本得到充分展现。铁路建设投资较大,一般是先由国家筹资兴建。所以,率先兴建的大多是国营铁路,主要有1872年东京-横滨铁路、1874年大阪-神户铁路。以后,随着私人资本的积累,私营铁路也很快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华族出资的私营铁路公司“日本铁道”,1884年兴建了上野-前桥铁路。所谓的“铁路热”开始兴起。1886年就有伊予铁道、山阳铁道、甲武铁道被计划组建,到1890年又有干线大铁路、地方性铁路的规划接近50条。[注]中西健一:《日本私有鐵道史研究》,東京:日本評論新社,1963年,第34-35頁。到1885年有100条私营铁道线路运营,到1889年达到了516条,实际数量超过了官营铁路。1889年官营东海铁路线的新桥-神户线,1891年日本铁道的上野-青森线,1894年山阳铁道的神户-广岛线等主要干线全部贯通。1892年的《铁路敷设法》确定了日本全国铁路网络的基本构想。1886-1893年,在矿工业运输部门社会资本金12382万中,铁路资本占了41%。[注]④⑥⑦山本義彦:《近代日本経済史》,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1992年,第32頁;第33頁;第34頁;第35頁。铁路运输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它不仅直接创造了产值,而且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带动了其他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
在各行各业中,棉纺织业的发展较为突出。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纺织设备的更新,日本国内棉纱生产和出口呈上升趋势,相反国内进口棉纱则呈下降趋势。国内棉纱生产若以1880年指数为3,到1890年上升到100,而到1902年则迅速上升到735,比22年前扩大了244倍;出口棉纱到1890年才开始起步,指数只有0.2,到1902年出口指数上升到了188,12年扩大了940倍;相反,进口棉纱数量则大幅度下降,1880年的指数为88,1902年下降为9,经过22年几乎下降了90%。[注]高村直助:《日本紡績業史序說》上,東京:塙書房,1971年,第146頁。这说明棉纺织业的水平在短时间内已大幅度提高,逐渐向欧美各国靠近。同时,日本棉纺织业的规模也逐年扩大。1883年,机械纺纱开业的只有大阪纺织的1万锭规模的公司,到1887~1889年则有10家左右同类公司开业。由于不少原本与棉纺织业无关的大城市商人、地方商人、地主等加入投资,棉纺织业规模迅速扩大,1887年达到7.6万多锭,1889年猛涨到21.5万锭,1893年再度上涨到38万多锭④,是1887年的5倍多。到了1912年(明治45年),纺锤数(包括捻线纺锤)达到了210万锭[注]⑧⑨⑩帝国通信社:《明治大正產業史》上卷ノ二,東京:クレス出版社,1999年,第1332頁;第147頁;第35、36頁;第13頁。,相当于1893年的6.3倍。大量的纺织工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治日本经济发展另一个突出的经济部门,就是采矿业和与之相关的冶炼业的迅速发展。例如铜矿生产发展较快,铜的生产量1881年为4772吨,1892年达到2万吨,为1881年的4.2倍,11年间增长了300%,其中80%以上的铜用于出口。当时有三大著名铜矿:别子、小坂、足尾。其中,足尾的铜矿还建成了日本最早的水力发电所,1890年竖坑排水已电力化;由于电缆索道搬运的近代化,1893年又采用了转炉,将以前需要32天的冶金工程缩短为2天。⑥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足尾铜矿完成了采矿、搬运、制铜的近代化。
这一时期日本煤炭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9世纪80年代日本煤炭业迅速扩张。1883年,日本煤生产量为100万吨,1894年便增加到427万吨,翻了4倍,其中出口量占40%-48%。筑丰地区用扬水泵解决了排水问题,导入一部卷扬机,使煤炭出井机械化,再由铁路运往各外贸港口输出。这些煤矿最大的特征,就是大多由国家开发后卖给私人企业,如三池、高岛、别子、足尾、小坂等煤矿分别出售给了三井、三菱、住友、古河、藤田等与政府有关系的政商财阀,使他们私人的资本在煤矿业中占据很大比重。另外,与设备近代化的趋势相反,三池铜矿利用犯人劳动,煤矿和矿山建立在库房和工地宿舍制度基础上的过分残酷的持续劳动也使人难以忘却,并引起社会关注。⑦
明治2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比起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来说则显得相对缓慢。本来,由于受到较重剥削的农民不断骚动,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已经将农民的地租税率从3%下调到2.5%,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税负,加上银价和纸币价格下跌、粮价上涨,农民获得的实际利益大为增加。⑧但是,整个农业比起工业来说,其发展显然缓慢得多。例如,粮食省产粮1878~1887年的指数如果为100,1888~1897年只上升到120。粮食虽然百分之百能够自给,但国家对农业税征收仍显较重。据统计,当时国税中有50%~60%来自于地租⑨。对于本来就不太发达的农业征收重税,势必造成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总之,到明治晚期,日本完成了第二期的产业革命⑩。由于生产水平在亚洲首屈一指,并迅速缩小与欧美各发达国家的差距,产品质量在亚洲领先,使日本的出口额逐年快速增加。1882年,全国出口额为0.3亿日元,到了1897年上升到1.24多亿日元,比15年前上涨3.1倍;到了1908年,出口额达到4.24亿多日元[注]帝国通信社:《明治大正產業史》上卷ノ二,第312頁。,比26年前上涨了13倍!这使日本积累了大量财富。据不完全统计,到1910年,日本的固定资产已达到294亿多日元[注]日本銀行統計局:《明治以降本邦主要経済統計》,東京:並木書房,1999年,第20頁。,国家经济实力大增。
二 劳动者的处境恶化
按常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相应的物质文明的提高,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处境也会得到同步提高和改善。但是,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后发的赶超模式,无论是生产部门的安全设施还是资本家管理的文明程度都远远没有同步跟进,以致在极短的时间内资本原始积累尤为迅猛,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处境却愈加恶化,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现象——即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待遇成反比。这一状况比较典型地表现为煤矿矿工处境悲惨、其他行业劳动者处境恶化、农民及城市贫民生存异常困苦。
(一)煤矿矿工处境悲惨
最为典型的是当时私人经营的高岛煤矿工人的悲惨处境。高岛煤矿作为三菱资本的一个据点,位于长崎港。它“系30年前荷兰人某某所发现,其后经10余年,由后藤象次郎创办采煤事业。后将之让渡给三菱公司”[注]④⑥⑦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東京:日本評論社,1993年,第3頁;第3頁;第4頁;第4頁。。这座煤矿从外观看“壮丽罕见”,似乎工人们所处环境很好,但实际上在里面的矿工工作状况却异常艰辛。高岛煤矿工人的悲惨处境,被亲自到煤矿考察的政教社社员松冈好一、吉本襄以及作家今外三郎等人所揭露。
松冈好一撰写的《高岛煤矿之惨状》一文,于1888年6月18日登载于政教社办的《日本人》杂志上。据该文报道:“三菱公司一取代后藤氏执掌炭矿事业,便设立千古未曾有之压制法,将作为人类的三千矿工使役驱逐,连牛马也不如。惨淡状况如佛教所谓阎罗殿,矿工宛然如饿鬼。事务员、海岸管理员、小工头、宿舍监、计数员等,如青鬼赤鬼,矿井宿舍长如阎魔大王。”④矿工的工作时间乃为12小时,大致分为白日方和夜晚方,白日方早晨4点下坑、下午4点回宿舍,夜晚方下午4点下坑,次日早晨4点回宿舍。矿工不仅劳作时间超长,而且劳动强度异常高。据该文描述:“其矿工所干12小时劳业苦役,首先在坑内一里到二里的场所,从脊背也无法伸直的煤层间屈步曲立,用鹤嘴锄、地雷、火棒等,一块一块采煤,然后装入竹畚。重量15贯至20贯,边忍边爬,一町二町地担着,运到蒸汽轨道。还要担任其它如碎岩、搭框等危险工作,看门、通风等烦恼的任务,实在是惨不忍睹的场景!”除此而外,劳动环境也十分恶劣。据描述:“由此渐渐进步,若下到被称为‘蒸汽卸’之大道,恰如东京的瓦斯灯,照着千百盏洋灯,明晃晃的情景,感觉在地底看见了不夜城。煤箱升降其间,轰轰贯耳,行步之危险亦不可言。气温随着下到地底而逐渐炎热。到最极端温度计达华氏百二三十度[注]华氏120度相当于摄氏48度。。矿工在炎热瘴烟之间不间断劳作,汗流如洗澡。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煤臭穿鼻,几乎不可忍受。”⑥可以看出,尽管采煤、照明硬件设施已经大为进步,但有关人身保障的通风设备、运输设备等却没有同步改善,导致工人劳作条件异常艰辛困苦。在管理方面,资方也完全无视工人的基本权利。据该文描述:“尽管在如此令人惊讶的环境从事劳作,但作为煤矿宿舍的规则,也不给予分秒休息。担任小工头者,在采煤场所巡视监督,若有稍微懈怠者,便以携带之棍棒殴打苛责。是余目击小工头等,岂有不称为青鬼赤鬼之理?又矿工中有人不堪过度劳累申请休息,或有违逆宿舍监之意者时,为警告众人,将其矿工反手捆绑,吊在梁上,双脚离地数尺,加以殴打。让其他矿工观看之。”⑦如果矿工不堪矿业待遇,企图脱离该岛,但若逃跑失败,便会被海岸管理员等逮捕和处罚,“或踢或打,或倒立或悬吊,其苛责之残酷,苟具备人情者不能为也”。管理人员完全将工人当作牲畜对待,没有丝毫人权可言。即便工人有病也不给认真治疗,而是为了保住煤矿,采用消灭病人的残忍手段。据该文报道:“明治十七年夏,该岛被霍乱病侵入,三千矿工之大半即超过1500人因该病而死亡。然而,煤矿宿舍不问其死者或未死者,从发病一天起,就将之送至海边焚烧场。放在大铁板上,5人或10人一组焚烧。”[注]②③④⑤⑥⑦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第4頁;第7頁;第7頁;第9頁;第14頁;第22-23頁;第24頁。尚未病死者也被焚烧,矿工处境真是惨不忍睹!
另一政教社社员吉本襄到高岛煤矿呆了一年,亲眼目睹了矿工的悲惨遭遇。1888年7月,他将亲眼所见写成《向天下人士诉说》一文,揭露了高岛煤矿的矿工惨状。文章认为,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所有的资本经营都“不可不图欲使社会幸福进步之事”,决不能公开施行违法之事,但他在高岛煤矿之所见却十分怪异,“三千余名同胞无罪而在孤岛中成楚囚之身,无故而在无限之坑底尝努力之苦。其悲痛惨酷之状况,以涂炭倒悬而不足形容。而法律放任之不干涉,社会旁观之不动手相助”。②文章指出,从事采矿业本来就是百业中最艰辛的行业,“其劳多,其乐少。素来作为其业,根据劳苦的报酬,工资较其他力役者,常常不得不贵几成”,即工资应当更高一些,而且矿工可以根据身体耐劳状况,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在煤矿中工作,“矿工自身任意出入外,不能从旁干涉”,但高岛煤矿的实际情况却是矿工“日益勤勉却日益困苦,愈益劳作却愈益贫穷。欲去而不能去,欲诉而无处诉”③,矿工处境犹如囚徒。不久以后,吉本襄又发出《陈述高岛煤矿矿工之惨状,禀告社会志士仁人》檄文,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高岛煤矿矿工的悲惨处境。他指出,这些矿工与社会普通人一样,都是日本的善良百姓,都应当受到政府法律保护,成为拥有相当自由权利的人,但他们“一旦被诱拐入彼岛,下到黑暗得白天如同黑夜之数十仞之井下,呼吸冬季仍达百余度以上之炎炎空气,过度劳动伤害肢体,深埋于尘芥,一身比昆仑奴还黑。双眼炯炯,与手足一起恰如石榴之裂口。鬓发蓬松乱垂,身着一寸布帛,疲惫困顿,昼夜搬运煤块。其状态,曾闻鬼界之流人也盖不至如此”;接着,他又进一步从人的正常需求分析了矿工们的绝望境遇:“生于人间,终身没有夫妇团乐、父子兄弟相见之期。旭日东升时,遥望东方,空慕家乡。夕阳西下时,面向西方,祈愿早至死期。悲愁哀鸣无处诉说,或从千仞绝壁投身成海底之藻屑,或向百丈岩角撞头洒鲜血于绿苔。怜火阴阴,冤鬼夜哭,悲风飒飒,游魂彷徨于何处?满岛荒草,共显悲哀之色,环海激浪,互呈忿怨之状。呜呼伤哉彼等之境遇!呜呼悲哉彼等之心情!世虽太平,而彼等常倒悬受苦,时虽丰饶,而彼等常不免冻饿之忧。”④吉本襄饱含对劳动者的同情之心,将矿工们遭受的极度悲惨境遇揭露得淋漓尽致,力图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想法拯救矿工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有识之士的揭露文章流传于社会之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针对高岛煤矿的矿工悲惨遭遇,社会媒体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1888年7月6日的《福陵新报》就发表社论《谁说高岛煤矿无惨状?》,生动描述了高岛煤矿矿工遭受的非人待遇:“至五六年前,有违背该矿规则者,被倒悬于‘警众台’,用生松叶熏之。担心其嚎叫之声外泄,用线缝塞其口,或恣行惨毒,用木棍插入其肛门等”,矿工们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一旦陷于该岛者,终身无脱离之期。不免空成孤岛望乡之鬼,与以前无异。故虽其后,平安无事返回乡里,与父母妻子再聚,得到一家团乐之欢者,始终未有一人”。⑤社论深刻揭露了高岛煤矿矿工的悲惨现状,矿工不仅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而且受到类似前资本主义社会奴隶般的超经济强制。另一位作家今外三郎于1888年在《日本人》发表评论文章《高岛煤矿》,揭露了高岛煤矿矿工因过于劳累而不能持久工作的状况。他从生理学角度考察认为,人的劳动最大限度不可超过12小时,但是高岛煤矿的矿工不仅仅是劳作时间超长,而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无法适宜保持生理循环,则不能维持生命”;他进而指出,“此所谓12小时者,乃云寻常一般之劳动。并非云在如彼之高岛煤矿极热之场所,呼吸最脏之空气,从事牛马也不如之劳动也。想来高岛煤矿之矿工,服人类无上之苦役,却不能永久保住生命也”。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辛苦劳作的工人们生活待遇如何呢?他一针见血地分析道:“何况如彼之食物,终究并非按劳力构成正常比例者呀!彼之矿工乃人类也。若然,没有被排除此生理原则之外者。如今日,或可堪一时,但至后来,消耗复补不得其当,营养组织不能完成其功能,以至运动器官不能发挥作用,只能摆头卧死病床。……余辈于此断言,如使役高岛煤矿矿工之今日,就生理上而论,决不可永久持续!”⑦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沉重剥削和人身压迫,最终将会导致正常的煤炭生产难以长久持续。
1906年4月,另一进步杂志《光》发表《高岛煤矿之内幕(三菱公司的暴行)》,也披露了煤矿工人遭受迫害的情况。文章指出:“高岛煤矿与其他地方不同,作为从海底挖掘的矿井,在水面下,浅有五六百尺,深则达千尺到二千尺。这样,由于通风的不充分,在最底下时,呼吸不畅会感到非常痛苦。若非相当熟练者,简直难以忍耐。尤其是在夏天,温度异常高,达到华氏100度至120度。在这样的坑道内作业的矿工,其艰难随处可见。本来高岛煤矿煤层厚重,瓦斯颇浓。虽然公司也加强注意,但正如前述,若不能使通风充分的深井,动辄有爆炸的恐惧,但禁止谈论危险。而且,坑道内十分倾斜,坡度至少有二十五六度至四十度,这样,即便用蒸汽力搬运的采煤箱,也会一天数次翻倒或脱线,杀伤人或撞坏坑道内支柱,导致天棚塌下等,危险状况不胜枚举。”[注]②④⑦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会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第31頁;第32頁;第35頁;第15-16頁。在这种状态下,平时即便瓦斯不爆炸,每天也会看到工人伤亡。根据矿工所说,每天只死2名是公司所预期。文章哀叹:“呜呼!可怕的资本家!他们认为伤害工人的生命,比抛弃一块煤炭还要轻。”②文章还揭露了煤矿管理人员对工人的身心迫害情况。当时的监工等管理人员,如果对工人有所不满,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工人,最轻的是罚款,即克扣工人应得的工资,重则采用人身伤害,“惩罚最重的,是在他们中被称为‘鲔’的刑罚。其法是将双手捆绑在背后,以脚趾头刚刚接触地面为尺度吊起来,暴晒于坑道口人流最多处。其状态很像吊鲔鱼[注]鲔鱼即大金枪鱼。,故得名”④。这种压迫实际上也已类似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超经济强制。
(二)其他行业劳动者处境恶化
除了煤矿工人处境十分悲惨之外,其他企业的劳动者境遇也日趋恶化。1890年10月26日,《读卖新闻》发表了山口县人北公辅写的纪实文章。他在旅行途中遇到3人,听闻东京北边37里远的野州足尾铜矿的矿工处境悲惨。他将三人所谈记载如下:“若世界上真有地狱,那铜矿正是现世之地狱。我们3人不曾知道铜矿实况,最初的目的是决心在这个地方打工几个月,然后买些衣服,携带旅费就回家。岂料在铜矿不仅每天1钱也存不起,而且还增加了借债,离开无期。偶尔患病希望休息1天,但那些残酷的饭场长不会轻易批准之。疾病日益加重,借债逐月累积,进退维谷,遂产生逃走之念头。然而如果暴露,会蒙受残暴的斥责,有时几乎置于死地。因此,不能企图轻易逃脱,何况老幼耶?只有日夜仰天叹息不幸。我们3人仅仅能够脱离虎口,出到狱外的世界,但身无分文,昨天起便没有吃饭。然而,若追忆在彼之铜矿之当时,空腹岂难忍受耶?”其中有一人甚至将监狱和铜矿的条件和待遇对比后说:“我曾于乡里醉酒后与人打架斗殴,因伤人而被关进监狱。但狱吏待遇比饭场长更优厚,何况狱中重视卫生,故如其伙食远远优于铜矿。若矿工为不顾廉耻者,皆更喜欢去进入监狱。”[注]⑥北公辅:《足尾铜山坑夫の惨状》,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3卷社會篇下,東京:日本評論社,1993年,第219頁;第228、224頁。听了这些诉说,将信将疑的北公辅亲自以矿工身份进入足尾铜矿开展调查,他发现矿工在里面除了劳动艰苦、收入很低之外,根本没有人身安全保障,工人们的生命完全被视同草芥。例如出入矿井必须攀登很高的直立梯子上下,经常很多人同时攀登;如果其中1人不慎从上面跌落下来,下面的人也将会被砸中,一起跌落井底丧命;如果有人设法逃走,被抓回来后,将会被活活打死,而矿主不负任何法律责任。⑥这与高岛煤矿矿工受到的超经济强制大同小异。同时,由于规模扩大过于迅速,安全设施无法同步完善,导致铜矿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而远近闻名。
纺织行业的工人状况也大同小异。1904年2月7日,《平民新闻》第13号刊登文章《纺织女工之实状》,揭露了纺织女工的悲惨境遇。文章指出,女工通常13岁以上要签3年的合同。按合同规定,每天劳动时间12小时,分昼夜两组轮流,每月休息4天。工作这么长时间的女工,每天收入仅有18钱,月收入仅有4元68钱;伙食1天有1次添加煮蔬菜,其余2顿仅有咸菜,“见到她们在宿舍中起居的模样,大抵脸色苍白,瘦弱,全都有气无力,如睡着了一般,呆然张口,熟睡得连躺到枕头外都不知道……患病主要是砂眼和肺病也。可能是处在如烟般的棉尘中之结果。平常大约有30至70名住院,但去年末大概患病者也要出工,所以仅有16名住院者。特殊重症者迅速送还乡里”,而且该文在比较其他公司后指出:“此公司女工待遇被称甚为良好,而其实状如此。其它各公司之残忍可想而知。”⑦可见,日本近代纺织行业的迅猛发展,无不浸透着纺织女工们心酸的血泪。
1898年2月初,工人们手中流传的《促进改善待遇大同盟》的秘密出版物,也强调了日本铁路司机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该出版物指出:“公司方面对我们的待遇,是越来越残酷,不!简直是在愚弄我们……司机们不得不俯首帖耳,像奴隶般劳作。一旦表示不平,便会被放逐到人人厌恶的五线区去,像惩罚仇人一样暗地里白做苦工。如此这般,若不堪忍受不平等待遇,为了一身清净而欲辞职,也不易获得许可。若硬要辞职,则不是被免职,就是在采取各种妨碍其就业的手段之后,才获得允许。妨碍自由权利也甚为厉害。大公司剥削人的手段真可谓无所不尽其极!”[注]②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第202-203頁;第214頁。火车司机应当是技术性很强的工种,他们都受到如此待遇,其他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种的工人待遇可想而知。两年以后,东京马车铁路公司的工人们对进步报纸《万朝报》记者诉说自己的处境恶化,报纸作了详细报道。据工人诉说:“我们清晨五点就得上班,晚上过了十二点才能归家。偶然有事,又得增加一、二小时的劳作。但次日上班若迟到,便会受到很重的罚薪处分。一旦被马车铁路公司雇用之后,都必须宣誓: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皆不得辞职。然而,公司方面虽然明确表示,连续服务二年以上者,可领取一百余元的赏金。但迄今为止,几百名司机、售票员连续服务二年以上者,不,就连服务五、六年以上者,也几乎没有得到那种赏金者。真是奇怪至极!”工人们还对公司强加给自己的超长工作时间表示了极大愤懑:“我们每天要从事19小时的劳动,而且还动辄要延长到20小时以上。在这期间又无分时休息,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几乎没有!而一个月所得,仅仅十一、二元。世上劳动困难者素来不少,但还有比我们的劳动更困难者吗?我们被马车铁路公司雇佣之后,必须预先缴纳保证金若干,接着每月要缴会费若干。它虽名为会费,但其实不外乎仍为用来束缚我们不得离开公司的保证金。故工作不满2年而离职者,会费就被全部没收。”②铁路工人们不仅受到残酷的经济剥削,实际上在人身上也被资本家束缚而失去了自由。
不仅私营企业的工人处境艰难,而且连官营企业的工人处境也同样日趋恶化。例如1907年7月《社会新闻》第6号发表文章《佐世保工厂之现状》,揭露了位于长崎的大城市佐世保的官营工厂里劳作的童工惨状:“佐世保很有名的是死伤者多,童工多,待遇惨绝悲绝。特别是童工的实情,就是在夏天都要打冷颤。还天真无邪的十一、二岁的儿童600多名,全都赤裸裸地劳动。而他们全身都有烧伤。只有一只眼睛闪闪发光,站立着劳动。看到他们从早到晚,被赶进大人无法出入的很小的锅炉升降口洞内,目光呈现出悲哀,实在是此等少年也。”[注]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会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44頁。这些尚未成年的儿童都受到如此虐待,无法受到法律保护,说明作为出资办厂老板的政府,与残酷剥削工人的其他资本家一样,并无本质区别。
(三)农民及城市贫民生存异常困苦
当时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自由主义思想家大井宪太郎(1843—1922)历来对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十分关注。他针对社会上有人说农民困苦是源于懒惰的论调,分析了农民的困苦状况及其原因:“山间僻村之民当然是一般农民之状态,大体相同。周岁无一天之快乐,披星而出,戴月而归。若问衣食,仅不足承受饥寒。至极贫者,特尝辛酸,粟饭芋饼,敝衣跣足。以至发出感叹,将人几乎等同于牛马!”大井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农民普遍的生存状态:“夫如是农民一般之情态,尽管勤劳简朴,但家无储粮者比比皆然。若见勤劳节俭如彼,却几乎不免冻馁,则可推断得知,皆由我国税法苛刻,故只能使农民无法富裕。”[注]大井憲太郎:《時事要論》,平野義太郎:《馬城大井憲太郎傳 主要著作》,東京:大井馬城傳編纂部,1938年,第371頁。他认为,政府对农业征税过重,是导致农民虽然辛劳却不得温饱的根本原因。
对此,大井反思了日本农业发展的历史与农民处境的关系,认为:“这样,在我国农民中,因无多余收入,一旦家庭遭受不幸灾厄,数代不能偿还之。耕种三代或四五代之前就已典质之田地,虽然名为自己所有地,但实际上变成了佃农。又有数代之前便租借他人土地耕种而谋生者。若直言,我农民概数代之前便已成为穷人也。在农民中,能独立生存于安心之地者,寥寥无几。夫如是,我农民中,大农即有相应资产者,不足十分之一。十之二三为中农,其他应为穷民。则仅怠惰便致贫之评论失当也。今之贫民,大抵乃世袭贫乏者也。故纵然没有怠惰,但素来无多余收入之贫民,数代之间,必然由于疾病或其它灾厄,流离颠沛,虽不想陷于贫困却不可得也。”[注]大井憲太郎:《時事要論》,平野義太郎:《馬城大井憲太郎傳 主要著作》,第371-372頁。而且大井认为,这种农民贫困状况,不但没有因明治维新后政府法令规定地租减轻而有所改善,反而有逐年加剧的趋势,“至近世,世事愈益极其纷扰,世间加倍疲弊人类生计之困难,一日甚于一日。盖由此陷入多重困难。今既观平民社会之现状,食就粗恶,衣极褴褛,鹄形菜色,简直难以避免饥饿。实堪怜悯!若徐徐推论其惨状,还不如宁愿成为受人喂养之牛马。人若无爱惜生命之天性,皆只有不堪劳苦而上吊了事。”[注]③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13頁;第342頁。也就是说,如果继续维持现状,而不实行社会改革,贫困农民只有死路一条。
社会主义者铃木生也在《社会新闻》1910年第66号发表文章《横暴的地主》,揭露地主通过提高地租加强对农民剥削的社会情状。文章指出:“租米1石不通用1石,必然每石分派额外增加5升米,称之为‘込米’缴纳给地主。此已成地方持续之习惯。于是,此次因重新订立加租契约,佃农方面当然认为这种不合理习惯应当废止。去年冬天基于加租规则欲缴纳年贡米的时候,地主方面称不能改变习惯而要求込米。佃农不答应之,遂提起此次诉讼,直至被强制执行。”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强制执行加租是十分蛮横,不顾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野蛮行为:“而且此强制执行极为酷烈,闻所未闻。若举其一例,佃农感到最痛苦的是,连日用品都被没收。佃农交租要做各种准备,特别挑选品质而包装库存,所谓年贡米不能到手,就没收充作食粮的粗杂米。佃农在租米上有一定规矩,不能将年贡米充作食粮,即事实上构成夺走食粮之残酷。可云真是极为横暴!”③通常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言下之意,还留下了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力价值。但是,由于农村文明程度更低,所以甚至连农民维持生计的必要劳动力价值也要被掠夺,农民的极端困苦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近代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1859-1933),1903年曾在政论著作《我社会主义》中细致分析了当时日本贫民大众的悲惨境遇:“若夫妻俩平安无事劳作,一日收入50钱,一月所得14元,经营6人的家庭生活,彼等乃贫民窟之居民也。房租1月3元,6人之家庭每月用12、13元维持生计。常食南京米,丈夫有时因感冒休业,收入减少时,妻子只能暗地里以剩饭度日。一日饭米至少也得1升5合,每月4斗5升,虽下等南京米也要支付6元。剩下3、4元,从蔬菜到豆酱、酱油、燃料、油,以及其他衣服、鞋袜等,也必须支付。偶尔有孩子生病,也不能请医生治疗,要买药充分服用也很困难。”而且他还指出,这是在经济比较繁荣的顺利时光里劳动者的状况,但若遇到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大大增加的困难时期,劳动者又如何生存呢?他指出:“若一朝因产业不景气而失去工作,处于失业状态,又因歉收而物价腾贵,此家庭之困难,远非通常人之智能所能想象的。南京米变成剩饭,放弃豆酱、酱油而用盐。在如此场合,孩子由于饥饿而悲鸣、痛叹,会妨碍母亲工作。老母亲由于贫血病而身体无法动弹,丈夫因感冒而终成肺病。母亲操心的结果,引起神经疼,一家内的惨状呈现无法描述之悲惨。此决非吾人仅仅记载特殊家庭之状况,如今城里150万人口中,沉沦于如此悲惨境遇者,实为多数也。”[注]片山潜:《我社會主義》,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5卷,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第46頁。由此可见,城市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已成普遍状态。
三 对社会不公正的谴责、反思及其应对
经济迅速发展与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矛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不公正状况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批判,同时也表达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并开始反思如何改变这种不公正状况。
例如高岛煤矿工人们的恶劣境遇,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心。当时的思想家将这种残酷对待工人的制度斥责为“奴隶制”。著名思想家、社会评论家三宅雪岭(又名三宅雄二郎,1860-1945)就认为矿工受到的是奴隶般待遇。1888年,他在《日本人》杂志发表文章《应当如何对待三千奴隶》,将高岛煤矿压迫矿工与古代奴隶制下对奴隶的虐待相比较后指出:“一听就厌恶的奴隶陋习,近来存在于肥前之高岛也。虐待奴隶,将人与牛马同样对待,被认为是前代异域之恶弊,今存在于号称我国第一煤矿的肥前之高岛也。无罪而受皮开肉绽之鞭笞,成为奴隶之地位。日夜孜孜劳动,而苦死于路旁,乃奴隶之命数也。世上虽有种种值得怜悯之事,但就中没有比奴隶更可怜,没有比奴隶更可叹,没有比奴隶更应需要迅速救助。呜呼!彼高岛实际大约三千人在劳苦、痛疾、呼号、困倒,继续降于饿鬼之道,将堕落于阿毗地狱。”[注]②③④⑤⑥⑦⑧明治文化研究會:《明治文化全集》第22卷社會篇上,第14頁;第17頁;第7頁;第7頁;第9頁;第8頁;第10頁;第24頁。三宅雪岭在文中,将挣扎于煤矿井底的工人们与地狱中受煎熬的奴隶们相提并论,对煤矿工人们奴隶般境遇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其深切同情也溢于言表。不仅如此,三宅雪岭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极不公正状况是阻碍日本文明进步的不可忽视因素。他说:“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将妨碍正当之工业者也。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毁伤具有慈仁之名的帝国人民之体面者也。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欲消灭锐意推进文化之东洋全般之荣光者也。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欲阻碍经千载万载进化发展而来之人类社会之大道者也。”既然如此,他强调,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想方设法解救这些类似奴隶的工人,“居住煤矿之三千奴隶,当然必须急速救助。今闻非常之惨状,意迫语尽而不知所言。待情绪之稳定,更欲陈辩救助之企图”。②
吉本襄在揭露了煤矿内工人们的种种惨状之后,强烈抨击这种剥削制度超过了远古时期的奴隶制,“至如疲惫困顿,只能等待朝暮死去的高岛煤井矿工,吾人即便欲坐视之,却不忍坐视也。高岛煤井矿工不能没有工资,然而,实际上却有种种诡计夺取也,一钱也不许到手。高岛煤井矿工虽非失去进退自由之人,然而,实际上遭受严厉管束,一步也不能走出岛外。驱役比牛马更甚,束缚比奴隶更甚”③。他在此分析了矿工们的实际处境,名义上是有工资的雇佣工人,在法律上也是自由人,但这些法定权利皆被资本家剥夺。他们一方面工资不能按时按量领取,另一方面连人身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比起奴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谴责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和国家法律制定者对矿工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其悲痛惨酷之状况,以涂炭倒悬而不足形容。而法律放任之不干涉,社会旁观之不动手。几乎如为秦越之思。故抑果如何”④?他主张应当千方百计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因为“彼等与余辈同为日本良民,与余辈同受日本政府之保护,成为拥有相当自由和权利之人”⑤,所以政府和社会对此决不能袖手旁观。他向社会有识之士发出号召:“志士仁人岂可有一日安然,将此视为对岸之火灾耶?应共同愤然崛起,将此等人民拯救于涂炭之中。不可不使此等凶汉绝迹于社会。”⑥他希望能有人想出万全之策,拯救这些处境艰难的劳动者,而且表示自己愿意为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工人兄弟倾尽全力。他说:“作为吾国人士,苟有相亲相爱之情者,见同胞沉于如此惨境,岂可袖手旁观、不为之谋划一策、拯救其危难哉?余辈不顾微力,今与同志密切相联结,倾注心血,将之诉于舆论,乞于官衙,尽力所及,从事其救援,欲死而后已。余辈最敬爱之志士仁人诸君哟,希望添加一臂之力,以不堪至恳望上为国家谋划扩张人权,下为欲赐予解倒悬之苦难也。”⑦即无论是向社会媒体披露,还是向政府请愿,自己都愿意尽一份力量。
今外三郎在揭露了高岛煤矿的工人悲惨处境后,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上升到社会现代化的高度。他指出,这种残酷剥削工人的不公正状况,如果不立即纠正,“不仅为彼三千矿工之不幸,而且我国后来应当勃兴之事业,其萌芽也将受阻止也”。⑧即像现在这样只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地压榨剥削矿工,最终将会阻碍日本正在勃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
针对纺织女工的悲惨处境,1907年9月《大阪平民新闻》第8号也刊登专题文章《纺织女工》进行强烈谴责:“柔弱而无抵抗力之妇女工人们,无论如何哭泣悲惨之境遇,但由于如此周密之工厂的充分防范,而无法被社会了解。仅仅有泄露而听闻之事实,不禁使人想起一个世纪前英国的棉纺织工厂中流行的‘奴隶之下的奴隶’。请牢记吧!资本家的财富和荣华,都是这样从我们姐妹那里榨取的血液。”[注]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23頁。媒体这段生动的描述,不仅揭示出当时日本纺织工业繁荣背后工人们血淋淋的遭遇,而且试图唤醒当时的人们透过经济“繁荣”的外表,认识到劳动者所遭受的极不公正待遇。
另一方面,思想家们还从社会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的视角来谴责这种社会不公正状况。如社会主义者片山潜从对资本家阶级奢侈生活的描述,揭示出日本社会贫富悬殊的惊人状况:“听闻大隈重信以其庭园壮观美丽而夸耀。而彼即便在寒冷中,其温室里也种有蔬菜,在与贵客共赏雪景时,可以吃到瓜、茄子等任何蔬菜。回顾一下,他一点不劳动,而每天有五、六十名园丁劳动,支持他一身。而为此,不知有几千万劳动者付出劳动。又听闻资本家岩崎(弥太郎)在城里深川有别墅,其园丁乃不通日语之外国人。是其意在于担心普通人民知道别墅内部。而其连古代帝王都自叹不如之极端奢华,若不能保守秘密,因过分奢华之故,以至于害怕社会攻击。真令人叹为观止。”[注]②片山潜:《我社會主義》,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5卷,第47頁;第469-470頁。这里说的岩崎弥太郎,就是三菱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前述高岛煤矿的老板。可见,他们通过残酷压榨劳动者的血汗,使自己过上了奢侈的生活。而对于劳动者水深火热的处境,身处优裕环境中的资本家们是不可能关心,也不打算改善现状的。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社会制度,仅仅希冀资本家“发善心”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是不现实的。
社会主义者森近运平于1907年7月至9月在《大阪平民新闻》发表连载文章《劳力的掠夺》,也从这一视角谴责了贫富悬殊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每日每夜汗流浃背劳动之人,应该贮存非常多的财产,衣食住都十分优裕。然而事实完全相反。带着最痛苦的神情劳动的人们,没有丝毫贮蓄,买米的钱也不够,一年连一次有趣的游玩都不可能。”反过来对比那些靠剥削工人过活的资本家,“随心所欲地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专门雇进人研究无用的游戏,并且还有用不完的收入。假定有钱人完成一份生产也同样是人,那么普通工人断无完成千倍万倍生产之道理。彼等收入之大部分,不,其全部不外乎掠夺多数工人之劳力而取得之物”②,揭示出工人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掠夺,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
那么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呢?社会各阶层都在反思。显然,这种状况是与政府的监管责任缺位密切相关的。于是,当时有人提出由政府兴办企业,在善待工人方面,为私营企业做出榜样。但是,严酷的现实却粉粹了这种美好构想。20世纪初的日本,正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明治政府更加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于是大力兴办兵工厂生产战争武器。在这些工厂里的劳动者,受到的苛酷待遇比起私营企业的劳动者有过之而无不及。1908年1月,《日本平民新闻》发表连载文章《大阪炮兵工厂之内幕》。文章作者非常感叹地认为,作为应当保护国民权益的政府,居然比资本家还恶劣:“资本家的权力强大,强大到可以虐待工人,我们常常有所目击。这样可以明白,比起其他的资本家的工厂来,在政府的工厂中,工人的状态更加悲惨。有种说法,将其在铁路国有之前和之后比较便可明白。考察印刷局、造币局和邮政局等部门的实况时,便不得不产生‘政府乃最暴戾的资本家’之感觉。尤其是在绞尽我们血汗的陆海军的工厂中,会看到工人之状况可以称为最恶中之极恶。”[注]④資料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編纂委員會:《資料 日本社會運動思想史》明治期第4卷,第50-51頁;第51頁。文章针对有人提出政府兴办的企业为私营企业做表率的主张,指出:“社会上也有人认为,政府的工厂应当向其他资本家工厂展示出楷模。但那终究不是在当今的社会组织下可以商谈执行的事。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必要的设置过大的陆海军,使我们工人陷于涂炭之苦。驱使本来可以生产自己衣食的工人,去制造令人恐惧的杀人武器。在今天政府的工厂——其杀人武器制造所大阪炮兵工厂,是如何虐待酷遇工人的呢?打算恭贺新年的人们,在以喝一杯新年酒的心情,热衷于资本家报纸的恭喜发财中的今日此时,将会破灭之,从资本家社会的恶酒之醉中醒来吧!”④文章笔锋犀利,抨击尖锐,不仅揭露出殖产兴业方针指导下的官营企业对工人剥削压迫同样沉重,而且力图唤醒人们放弃希冀政府“能够保护工人”的幻想。
既然政府不可依赖,于是有人提出用宗教信仰来拯救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主张,但这种作用能否奏效也受到怀疑。伦理学家大西祝(1864—1900)曾发表文章《社会主义之必要》,谴责了宗教家们对劳动者所受苦难无动于衷的不作为。他指出,今天我们大家都应当高声“倡导平等之福音”,因为弱肉强食、富胜贫败成为社会一大事实。但是,宗教家们都不愿意与穷人做朋友,更没有谴责为富不仁的勇气。现实社会中,“自我主义、争斗主义”成为推动社会的动力,人们动辄为了私利而争斗,宗教家难道没有责任“矫正其弊害之义务耶”?大西祝强调,人们很容易趋之若鹜的这种相互争斗,不可能带来社会全面进步。而对此种现象,“宗教若不宣传博爱,宣传大慈悲心,主张一视同仁之平等主义,何者能为之”?对于因社会不公正而受苦受难的不幸之人们,想法给予他们平等待遇,“难道不是宗教之义务耶”?然而在现实中,宗教家们为了宣传虚张声势的教义,“动辄欲献媚于种种阶级的、血统的、财产的、权势的、国家的、社会的差别,这算什么事”[注]大西祝:《社會主義の必要》,松本三之介:《明治思想集》II,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第160頁。。他实际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不能指望宗教界能在改善劳动者处境方面发挥什么有效的作用。既然如此,就只能如同这篇文章的标题所示,寻求一种能改善劳动者境遇的新制度已成为必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萌发。
四 结语
从上述考察可以深切地了解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使日本在亚洲率先迈入到近代化行列,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发家史”,无不是以劳动者被残酷剥削甚至超经济强制作为沉重代价的。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7頁。尽管维新后官方提出了“四民平等”的人际关系原则,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但在社会实践中,劳动者的权利仍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殖产兴业”国策大力推行和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广大工农劳动者的经济待遇并未相应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工作环境日趋恶劣,生存状况愈益悲惨。这种状况在当时日本出现,除了世界各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共同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因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了尽快赶超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使日本在极短的30余年时间内,经济迅猛发展,但许多前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者实行超经济强制的习惯做法仍然继续保留下来,难以在文明程度尚未提高的极短时间内消除。脱离封建时代不久的资本家们,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榨取最大利润,除了增加工时以榨取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外,还往往尽量降低生产成本,甚至包括必要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和完善也被忽视,因而导致劳动者的处境不但没有伴随经济发展而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呈现日趋恶化的态势。这一切构成了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的舆论环境,并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萌发出日本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这种人文关怀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萌发,笔者将另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