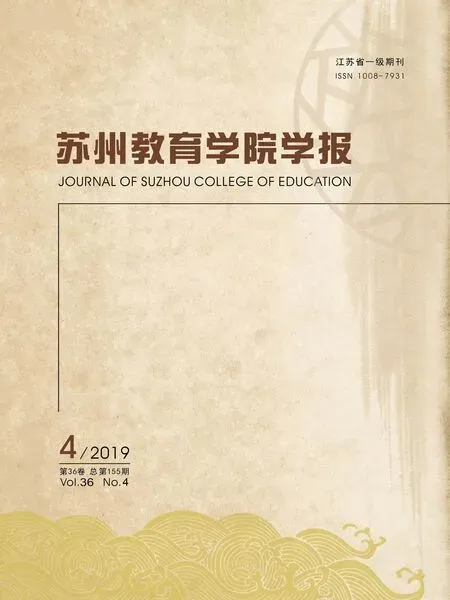叶圣陶1946年演讲钩沉
金传胜,李宁宁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1946年,叶圣陶先生离开四川回到上海,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还出任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直至1949年。根据叶先生自述,“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离开上海,这三年中,他接触的人最多,参加的会议最多,发表的演说最多”[1]。其中又以1946年发表演讲最为频繁。根据本年的叶圣陶日记,仅2月至12月的10个月间,叶圣陶就曾先后到私立储能中学(3月18日)、山海关路育才小学(3月24日)、沪江大学(3月27日)、银钱业联谊会(4月11日)、育才学校(4月14日)、中国建设服务社(4月21日)、南屏女中(4月22日)、市立拉格勒小学(5月11日)、新闻专科学校(5月29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7月11日)、幼稚师范(10月7日)、工商专科学校(10月21日)、罗溪中学(10月31日)、复旦大学(11月3日)、中华第四职校(11月24日)等处作公开演说。可惜日记中关于这些演讲的内容记录甚少,演讲底稿大多数均已散佚。《叶圣陶集》《叶圣陶教育演讲》等虽辑录了叶圣陶的大量演讲,但1946年的讲稿则寥寥无几。
一
1946年3月1日,叶圣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八时,大学新闻社以汽车来邀,至震旦大学,参加其社主办之文艺晚会。同被邀者为熊佛西。熊与余皆说话半小时,此外为朗诵歌唱等节目。十时散,仍以汽车归。”[2]45这表明震旦大学的大学新闻社曾于1946年3月1日晚举办文艺晚会,叶圣陶和熊佛西应邀到场,并分别发表演说。可叶圣陶当晚讲了哪些内容呢?日记语焉不详,并无交代。令人欣慰的是,笔者在民国报刊上找到了这次演讲的两个不同版本的记录稿,未见《叶圣陶研究资料》《叶圣陶年谱长编》等著录。
第一个记录版本以《阅读与写作》为题,刊载于上海《真话》1946年4月1日新7期,署“叶绍钧”,副标题“三月一日在大学新闻社主办文艺晚会讲”。因文末注明“材新记”,可知记录人即材新,具体生平待考。《真话》系月刊,1943年10月创刊于浙江云和,1944年12月出版至第2卷第3期,由张凡公、陈一然编辑,真话杂志社出版,发行人翁华康。1946年2月迁到上海出版,改为周刊,期数另起,出版至1946年4月新7期,主编翁北溟,编辑祝育元、陆祖武、董蘅、郑昭。1948年1月5日、25日刊印第5年第1、2期。主编仍署翁北溟,编辑王健行、方影村,发行人署真话杂志社。《真话》宣称以“人民利益第一,绝无党派成见;据真理,依真情,照真事,说真话”为宗旨,属于综合性刊物。
现转录原文如下:
文艺晚会在内地是常常举行的,在上海却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今天主席叫我讲些关于内地文艺界的情形,但我为自己工作关系,跟文艺界接触不多,实在不能说出些什么来。看见今天礼堂上挂着“大学新闻社主办文艺晚会”几个大字,我想来参加的大多数一定是爱好文艺的朋友们,那我还是随便来谈谈“文艺”吧,这是算不得什么演讲的。
文艺是什么呢?文艺是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的表现。表现的方法是有两种,第一种是作者把自己所见的东西,源源本本,有条有理说出来,并且或者加进自己的见解。这是论文的作法。第二种是作者把自己所见的东西,并非像论文式的写出来,而把论文的意思寄托在形象之中,使读者知道作者所要说的是什么。这就是文艺的作法。论文是使人“知”,读者看了,“哦,知道了”。它的效果仅不过是这一点。而文艺是使人“感”,不但使人知道,而且感动,深切。甚至于对读者的行为与思想有所影响或发生作用。
文艺既然是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的表现,那么我们读文艺的时候,便应该注意作者所要表现的—即作者所见的东西—是什么,否则仅留意故事情节是不够的,这只是最最起码的读法。我们要研究文艺是万不能只是如此读法的。至于写文艺呢?也就是把自己对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用文字艺术地形象地表现出来。
接着的问题,便是怎样读文艺与怎样写文艺。实则这也可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怎样读文艺就是自己去读,这是最重要的,不能只研究怎样去读而并不去直接实践地读文艺,这是毫无用处的,至于写文艺一点,也如此。手捧住什么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是决不能写成小说的。老实说,怎样读与怎样写的问题,是不能回答的。这只有自己去读自己去写,从自己实践中得到经验,自己会知道怎样写与怎样读的秘诀。这种秘诀□①无法辨识的文字以□标示。靠别人传授而自己不去实践,是绝对没有用处的!
其实,无论怎样读文艺或者写文艺的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人生问题。有人说研究文艺要确立人生观与世界观呀,先要多方面观察呀,先要多方面去体验呀,等等。这些话都对,非常对。就是大家见到了根本问题而说的。不过有一点意思似乎应当补充,这种努力本是为人之当然,我们为人,就该留意这些项目,即使不弄文艺,也不能荒疏。(按: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作者《西川集》二一页《关于谈文艺修养》)我们觉得因要弄文艺而去确立什么人生观等,实在是本末倒置。我的意见是研究文艺或创作文艺的先决条件是做“人”要及格,否则一定“搞”不好。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爱好文艺的青年是不大注意到的,因此我再不厌烦地向诸位说一声。(材新记)
注:“搞”即“搅”,“搞文艺”即是“从事文艺”之意。“搞”为此次抗战期间后方作家惯用的词。
第二个记录版本《关于文艺的阅读与写作》载于上海《青年文艺》1946年6月15日创刊号,署“叶绍钧讲S.T.记录”。S.T.显系笔名,其真实身份同样尚待考证。《青年文艺》系双月刊,主编韩逸影、魏力行。现亦抄录原文如下: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大学新闻社主办文艺晚会,叶绍钧先生演讲……
文艺晚会在内地是常常举行的,在上海却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今天主席叫我讲些关于内地文艺界的情形,但我实在很惭愧,不能说什么;因为我在内地的几年之中,几乎全为着忙自己的私事,跟文艺界很少接触。看见今天礼堂上挂着“大学新闻社主办文艺晚会”几个大字,便想到来参加的大都是爱好文艺的朋友们,因此我还是随便来谈谈文艺吧;这是算不得什么演讲的。
首先我们来研究“文艺是什么”的问题。这问题好好地讨论起来,可以写成厚厚的一大本书,决不是在这里几十分钟的时间内,所可讲得完的。现在我只能够极简单地来说明一下。文艺是什么,可以说是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的表现㈠。不过所谓表现有两种方法,这里是单指艺术式的表现,而不是论文式的表现。论文式的表现是把自己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源源本本,有条有理地说出来,或者并加以阐述与批判,这是纯粹理智的表现。而艺术的表现却不然,把自己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并不像论文式的诉诸理智,而寄托于形象之中。不但能使读者像读了论文以后一样地懂得作者所要说的东西(即指思想或真理),并且使人感动,深思,甚至于还能影响读者的思想与行动。所以说起效果来,艺术的表现是比论文的表现大得多。论文是使人“知”,而艺术是使人“感”。
文艺既是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的表现,那么我们读文艺,便得注意作者所要表现的,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所见是什么。切不可仅仅注意故事情节,这是最起码最原始的读法,除非是把读文艺当作消遣的。我们要研究文艺决不可有这样的态度。至于写文艺,也是如此,决不可只有故事情节而没有自己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的表现。这一点不注意,无论读文艺,写文艺,一定都失败。接着的问题便是怎样写与怎样读,实则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怎样写,就去写;怎样读,就去读。只研究“怎样”而不去写读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切不要只讲理论,不讲实践。我们应当从实践中得到经验,自己自然而然地会知道怎样写与怎样读的秘诀。但这种秘诀是不能传授给别人的,别人即使得到了也是没有用处,因为这至多是理论呀。
其实,无论读文艺或写文艺的根本问题却不是读写的本身,而是人生问题。所以有人说研究文艺先要确立人生观与世界观呀,先要多方面观察呀,先要多方面去体验呀……这些都说得非常对。不过,有一点意思似乎应当补充一下,这种种努力本是为人之当然,我们为人,就该留意这些项目,即使不弄文学,也不能荒疏㈡。所以人生修养是文艺修养的先决条件。做人“及格”了,才有资格去“搞文艺”㈢。否则,一定失败。但现在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似乎不大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今天乘机会再向诸位讲一遍。……
S.T.注㈠可以参阅以群著《文艺底基础知识》中的第一章《文学的本质》,和第三章《文学和现实》。㈡参阅叶氏新著《西川集》二一页《关于谈文艺修养》。㈢“搞文艺”即“搅文艺”,意思是弄文艺,或从事于文艺之谓。据叶氏谓此“搞”字为此次抗战时后方作家所发明,且甚流行云。
将上述两个版本的记录稿进行对照,可知它们内容上基本接近,据此可以还原叶圣陶本次演讲的原貌。现代文化名人发表公开演讲,有时并未预先明确讲题。演说结束后,笔录者时常根据自己的理解“越俎代庖”式地拟定标题,嗣后又未经讲演者审校,便将演讲记录投寄报刊发表,是故,不同听众记录的讲题常有出入。上述两文的讲题略有不同,即应属这种情形。
叶圣陶的演讲围绕文艺的阅读与写作展开,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文艺是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所见的东西的表现”,不但使人知道,而且使人感动、深思。二是只有自己去读、去写,从实践中得到经验,才会领悟怎样写与怎样读的秘诀;只讲阅读与写作的理论,而不去实践,是无济于事的。三是“人生修养是文艺修养的先决条件”,无论一个人是否创作文艺或研究文艺,都应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做“人”及格了,才有资格去从事文艺。如1943年的《关于谈文艺修养》(后收入《西川集》)一文,叶圣陶在申说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即强调“生活在先,文学在后”,如果为了文学而求生活充实,则不免有些本末倒置。这体现了叶圣陶对于创作主体的思想立场和综合素养的重视。
二
1946年12月,上海《夕芒月刊》第15期刊发了一篇署名“桢”的《叶圣陶先生讲的“怎样学习写作”》,实系叶圣陶一次演讲的笔录。记录者“桢”原名不详,仅知他/她是《夕芒月刊》的撰稿人之一。本刊1945年7月15日创办于上海,属于学生文学刊物,实行“编辑轮流制”,以“供校友阅读和互道信息”为创刊宗旨。主要登载戏剧、小说、幽默小品、漫画、读书心得、译文等,如若微《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铁帆《陶行知先生追悼会归来》等文。该刊“读书心得”栏目相继发表了青年们阅读老舍、巴金、朱自清等现代文坛名家名作的读后感,如邦维《阅巴金的〈火〉后》(1946年第9期)、彭年《〈火〉的观后感》(1946年第9期)、邦维《介绍老舍先生的〈火葬〉》(1946年第10期)、萃芳《读〈骆驼祥子〉后感》(1946年第11期)、水彭年《〈我这一辈子〉读后感》(1946年第13期)等文,对于研究新文学作品在民国时期普通读者圈的传播与接受,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资料。因“一周纪念特大号”由上海慕时英文补习学校的校长徐慕时题字,创刊号载有一篇讲述几位学友拜访生病住院的徐慕时先生的散文《访候慕时先生》,因而该刊编撰人很可能以慕时英文补习学校的校友为主。
兹将叶圣陶的演讲词转录如下:
“怎样学习写作”这个题目的范围很大,一时说不完也说不明白,现在姑且大略的讲一讲。
讲到写作,这“写作”二个字,现在可说是时髦极了,在二十年以前,还没有这个名字,写是写,作是作,现在我们谈到写作,总是关于文艺一方面的,写一本账,写一封信,就不能算是写作。
然而要问什么叫文艺呢?我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大人往往谈故事给我们小孩子听,什么猫会说话,狗会跳舞啰,在大人这不过是说假话哄孩子罢了;但听得津津有味的孩子们,则以为真有这种事。还有,孩子们总喜欢唱一些山歌,什么:月光光,贼来偷酱缸;排排坐吃果果之类,这可说就是倾向文艺的初步表示,年纪大一些,便会想到用文字把它发表出来。
可以说做文章,其实就是把你所想到的,听到的用文字表示出来而已,表示的方法,用文字是一种,用嘴说当然也是一种方法。有时候我们心中往往有一种感觉,或是忧,或是喜,不过放在心里似乎很不舒服,非得一吐为快,假使把它发表出来,使别人听到或是看到之后,也发生忧喜的情绪,那你好像会感到胸中松了一松一样的舒畅。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你所发表的东西最起码要具有二个条件,一个是“知”,使别人了解你的意思;还有是“感”,非但要知,并且要使人发生同样的感觉。为了要使人“知”并且“感”,在你的文章中,就不可多用抽象的字。譬如你解释“道德”,说了一篇何谓“道德”的话,旁的人听了只知道你对于道德的见解,而并没有感到道德,因为道德根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不比一块黑板,看得见,摸得着。反之,假使你讲述一个故事,大致是说“一个爱国志士遭敌人逮捕,以严刑拷打,想逼他说出同志的姓名,什么地方堆贮粮草,什么地方埋藏军火;结果这个爱国者誓死不肯说出来,因而被敌人杀死了。”那听的人一定会感到这个人是那样的为国家而宁愿牺牲个人,真是了不起—发生了景仰的感觉,你也就达到了你讲述的目的,写作也是相同。
简单如中国的古诗,也能使人发生深切的感觉,这完全是不用抽象的字的缘故,《唐诗三百首》,诸位一定都读过的啰,试举一首来说:
故国三千里,
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
双泪落君前!
第一句里,故国三千里是形容遥远的意思,故国、三千都是实词;深宫二十年是说时间的长;《何满子》是曲名,双泪落君前描写悲戚的样子,通篇二十个字中,没有一个抽象的字,而含义至深,很能使人感动。我们写文章也要这样才好。
还有,写作切不可像聊天一般的尽是说一些废话,譬如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上台演讲,往往会说:“咳……今天兄弟来参加这个集会,真觉得非常荣幸,但兄弟才疏学浅,加之兄弟今天又未预备,讲得有不对的地方,还得请各位指教和原谅……今天……”诸是云云的一大套,倒化费了三五分钟的时间,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废话,没有预备来说话,何必来参加什么会,对不对?
诸位学习写作,我奉劝还是多写现实的文章比较好,尤其是初学的人。因为描写的文章不易写,涉于空想的更甚。又要者,有许多人往往欢喜摹仿或是抄袭一些名作家的文章,我以为这样也不大好,因为摹仿或抄袭的文章,连别人的意思也被放进你的文章里面,未必能处处紧凑,天衣无缝的成为一篇“佳作”,你还是写你自己的意思,自己要说的话,时常琢磨,自然会进步的。虽然名著作是不可不读的。假使你一篇作品写成以后,有许多地方的确是和某某作家的笔法相同,那时只要不是摹仿或抄袭来的,你不妨引以为“英雄之见略同”,你的进步已够惊人,你的程度,也可以做一个作家了。
不过写记实的文章,你得小心,别让你写得太夸张了,而溢出事实之外。我记得在抗战时期,我曾在内地某大学执教。有一次我出了二个题目叫那些大学生们任意选择一个做,那二个作文题目是《对于汪精卫艳电的意见》,因为那时汪逆刚发表这篇通电,另一个《记本校的图书馆》。结果我把卷子收下来一整理,出乎意外的,写汪精卫的多而记图书馆的反少,而且没有一篇是够称满意的,内地学生的程度之差可知。有一位大学生他把图书馆记得很有趣,原来校中的图书馆,是设在孔子庙大成殿内的,他描写这大成殿的庄严肃穆,更有那俨然的孔子塑像立在神龛中;怪了,大成殿神龛中压根儿就没有孔子的神像,左右不过一块“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木牌而已,这个学生就是犯了太夸张的毛病;反而不及那些做论文的,反正是把汪精卫臭骂了一顿吧①“吧”应作“罢”。了,倒也词严义正。
写作,我还可以把它比之于雕刻,一个雕刻者面对着一团石膏或是一块大理石,要雕刻出一个人的面目来,正如我们提起笔来预备写一篇文章一样,他必须想妥:鼻子是应该高的还是低的,眼睛、嘴应该怎样,面部是什么表情……方才动手;做一篇文章也正相同,预备说些什么,用什么方法把它分别表达出来。不是这样,雕刻者的面前仍是一团石膏或是一块大理石,而写作者的脑中还不仍是漆黑的一片吗?有种聪明的人,往往会打所谓腹稿的,提起笔来,从□到底的一直写下去,淋漓尽致,这是很难的。不过一篇文章,内中的意思是有层次的,决不会是一团糟,所以你在写作之前,先想好层次,然后一层一层的说去就得了,否则像普通学校中学生上作文课一样的想一想,写一句,那就费力了。
一篇作品,有时对于各地的方言拣其有价值的,有力量足以加强语气的,不妨把它放进去。因在我们现在所写的,等于都是像□□官话的腔调。我是苏州人,有一句苏州方言,现在在白话文中很是时髦,就是“像煞有介事”这句话,假使译成文言就是“若有其事”,把它放在文章中,就没有前者来得有力而亲切感了。
今天因为身体不好,就此想打住了,对不起。
十一月廿四日
由于文末所注时间“十一月廿四日”,表明此文脱稿于1946年11月24日。倘若记录者在讲演当日即整理成文,则叶圣陶的演讲时间亦应在同一天。查叶圣陶当天日记,其中恰有“七时,至浦东大楼,为中华第四职校同学演讲,谈写作。九时归,疲惫之甚”[2]140的记载。因上文正是一篇“谈写作”的讲演,当即叶圣陶在中华第四职校的演说记录。当日他身体不适,故有“疲惫之甚”之感。“中华第四职校”指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或称“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址设在爱多亚路浦东大厦(亦称“浦东大楼”或“浦东同乡会大楼”)三楼。该校是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江问渔等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的七所补习学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为上海拥有数十万职业青年学生的教育机关”[3]。叶圣陶与黄、江等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相识,他对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学、办刊等工作,都曾给予过大力支持[4]。
据有关资料显示,上海大多数的补习学校都聚集于浦东大楼。1939年《上海生活》杂志所刊的一篇文章《四个学校区的素描》曾对浦东大楼作过如下描述:“自三楼到五楼,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中华职业第四补习学校、慕时英文补习学校、大陆汽车学校、炳勋速记补习学校、哑青学校、上海建设工程专修馆等。”[5]记录者“桢”或许正系慕时英文补习学校的学生。虽然叶圣陶的讲座为中华第四职校的同学而开设,但其他补习学校学生以及社会听众慕名前来听讲的可能性甚大。
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叶圣陶曾指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6]这是针对将国文教学等同于文学教学的错误观念而发的,强调国文教学中的写作训练不能局限于文学。然而在上述演讲中,叶圣陶所谈的写作却主要是“关于文艺一方面的”。讲演中首先以浅显的语言阐释“什么是文艺”,述明文艺“使人‘知’并且‘感’”的功用。随后则开始分析写作中的诸多问题,涉及写作的方法、取材、步骤和用语等方面,可谓面面俱到,层层深入。此文虽是演讲,但与《以画为喻》等文章相似,以和青年谈心聊天的语气,将自己多年从事创作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听众。本篇演讲既显示了作为文学家的叶圣陶对于文艺写作的独特理解,又体现了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
三
如将1946年的这两场演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些相似之处:演说内容均涉及如何写作,属于叶圣陶驾轻就熟的话题;一些观点在两处皆有出现,如认为文艺不仅使人“知”,而且使人“感”。不过两次演讲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前者所面对的听众主要是爱好文艺的青年大学生,后者则以职业学校的学生为主,因此第二次演讲的内容较之第一次更为通俗易懂,对写作方法的指导更为具体细致。另外,两场演讲还有可以相互发明的地方。在震旦大学的演说中,叶圣陶使用了“搞文艺”的说法,这对沪上听众而言显然是十分新鲜而陌生的表达,所以记录者特意添加了按语或注释,点明这是抗战时期后方作家喜用的词。叶圣陶这样表述当是有意为之,其背后的原因则恰好可在第二次演讲中找到答案:“一篇作品,有时对于各地的方言拣其有价值的,有力量足以加强语气的,不妨把它放进去。”[7]
虽然这些集外演讲存在个别文句不够晓畅等瑕疵,且尚无证据显示经过叶圣陶本人的审订与校阅,但作为记录其文艺活动的第一手文献,还是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叶氏上海时期的生平行迹、文艺思想的了解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