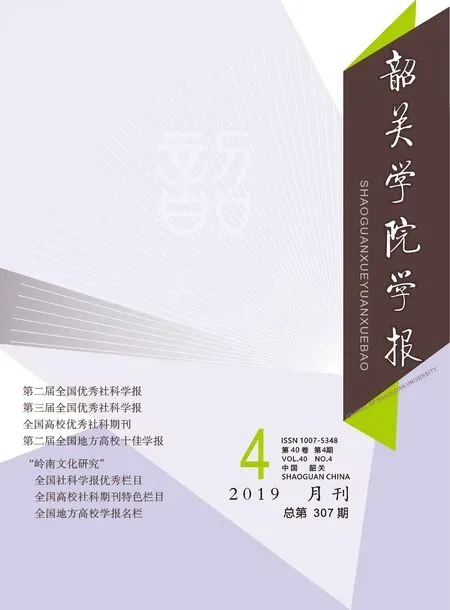论宋代诗歌创作选材的禅学化
徐 璐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两宋时期,禅宗迅猛发展,五家之中,以临济宗的文字禅发展得最为兴盛。所谓“文字禅”,即指以文字为禅,它主张通过文字来习禅、教禅及衡量参悟的深浅。文字禅的表达方式大致有 “颂古”、“拈古”、“代语”、“评唱”等等。最常用的“颂古”一般都是有韵诗体,韵律分明,琅琅上口。如此,便加强了禅与诗的融合,禅家以诗明禅的现象逐渐频繁。
与此同时,文人以禅入诗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从而出现了诗歌创作选材禅学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禅典入诗,二是禅理入诗,三是禅趣入诗。所谓禅典入诗,即在诗中引用禅学故事。所谓禅理入诗,即在诗中阐发某种禅学道理。所谓禅趣入诗,即指诗歌并没有试图道明禅理,却呈现出了与禅学思想类似的趣味和意境。
一、禅典入诗
以禅学故事入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诗作是刘克庄的《达摩渡芦图》和《卢能》。《达摩渡芦图》言:“长啸生风白浪起,高桅千尺如折棰。佛狸百万不敢渡,师跣双髐踏一苇。视鲁叟桴差简捷,比博望槎尤俶诡。岂小儿女狡狯然,亦大神通游戏尔。老胡西来纷文字,遍东西旦撒种子。塔藏共礼熊耳骨,壁观谁得少林髓。吾闻至人未尝死,岁晚翩翩携只履。学人其如初祖何,应身已渡葱岭矣。”[1]547这首诗描述的是达摩东渡的故事。其中涉及了三个典故:一苇渡江、少林面壁、只履西归。据《五灯会元》记载,当达摩准备出发时,天竺国国王“即具大舟,实以众宝,躬率臣寮,送至海壖”[2]43,达摩经历了三周寒暑,方到达中国南海,于广州登岸。至金陵见梁武帝,话不投机,再行洛阳。由此可见,“一苇渡江”可能只是传说,与禅学典籍中的记载不同。又据《五灯会元》载:“当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2]43此为“少林面壁”之典。接着,《五灯会元》载:“即魏文帝大统二年丙辰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后三岁,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祖曰:‘西天去!’云归,具说其事,及门人启圹,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2]46此为“只履西归”之典。整首诗中,除引用禅典之外,并无禅理,更无禅趣,它仅仅描述了达摩祖师东渡普法的经过,并表达了作者对达摩祖师的敬赞之意。
《卢能》言:“明镜偷神秀,菩提犯卧轮。更将旧衣钵,石断不传人。”[1]417“明镜偷神秀”指慧能借神秀的偈子来作偈。据《五灯会元》、《坛经》等记载,神秀书偈于壁,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3]348,慧能则将其改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3]349此为一典。“菩提犯卧轮”指慧能应卧轮禅师之偈来作偈。卧轮禅师言:“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3]358慧能则言:“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3]358此又为一典。“更将旧衣钵,石断不传人。”此处藏有二典:一是慧能得法后南行,遭百人追逐,欲夺其衣钵,他将衣钵掷于石上,且与惠明说法;二指慧能圆寂之时,并没有把衣钵传给弟子。这首诗中,除引用禅典之外,也无禅理和禅趣,它仅仅描述了与慧能相关的几个事件,且诗中的“偷”、“犯”二字似有批判之意。
通过以上举例可知,这类诗歌大多都是单纯的用典之作。或仅对禅典本身进行描述,或借助典故自抒胸臆。在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方面,即没有蕴含深刻的禅理,也没有蕴藏奇妙的禅趣。不过,禅典的使用,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语言,亦算有所贡献。
二、禅理入诗
禅理入诗,常见有三种类型:一为以诗歌阐明自性佛性的本质,二为以诗歌阐明修持觉悟的途径,三为以诗歌阐明觉悟与自性之间的关系。
(一)自性佛性的本质
王安石诗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之一言:“人人有这个,这个没量大。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过。锯也解不断,锤也打不破。作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若问无眼人,这个是甚么?便遭伊缠绕,鬼窟里忍饿。”[4]89“这个”指自性佛性,“人人有这个”即人人都有佛性。“这个没量大”指佛性无量大,可以包摄一切。因此,它有“坐不定”、“跳不过”、“锯不断”、“锤不过”的特点,或牛或马,自由任运。而且,自性不可言说、不可开示,“若执言执理,以求了撤,则鬼窟里做活计”[5]306。此处,王安石借诗歌表现了万法唯心、自心归依、见性通达的禅理。
晁补之诗作《次韵练定祥符听法》言:“弥天一滴水,何处是曹溪?若作声来解,还成瞪发迷。白云遮刹远,翠竹向檐低。是物元非物,庄周未可齐。”[6]该诗提及了“曹溪”。曹溪之法即慧能之禅法,它好比弥天一滴水,落入凡尘,无处不在,天下皆同,万物无差无别,都归于自性。“刹外白云,檐间翠竹,虽皆色界之物象,而真如自性即在其中”[5]308,故“物元非物”。这种禅法比庄子的《齐物论》,更为高超。此处,晁补之旨在说明佛性无处不在、自性无所不在的禅理。
苏轼有诗偈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7]“广长舌”是禅语,指佛的舌头。《大智度论》卷八言:“是时佛出广长舌,覆面上至发际,语婆罗门言:汝见经书,颇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语不?”[8]《法华经》言:“现大神力,出广长舌,上至梵世。”[9]《阿弥陀经》言:“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10]佛学中的“广长舌”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为语必真实,二为辩说无穷。此处,溪声便是这种超能无量的声音。“净洁身”也可视作禅语。佛教有“净洁五欲”的说法,即去掉色、声、香、味、触五欲。这里,青山就是五欲皆净的超凡所在。苏轼旨在说明:佛禅的智慧在自然万物中显现,人生于天地万物之间,一直都在聆听佛禅的诉说,接受自心佛性的指引。
(二)修持觉悟的途径
范成大诗作《病中三偈》其一言:“莫把无言绝病根,病根深处是无言。丈夫解却维摩缚,八字轰开不二门。”[11]此诗探讨了禅悟与语言的关系。禅是亲证的智慧,不是知解的智慧,依靠语言来悟道是病根,但如果完全脱离语言来悟道也是病根。“八字”指“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意思是:只有跳出生死轮回,不生不灭,才能获得真正的永恒的解脱和安稳的快乐。佛陀当年在雪山中修行,为了获得这八个字,不惜舍弃爱身。也就是这八个字,使其获得了不二法门。范成大想借此说明,悟道还是可以依靠语言的,但其前提是悟道者必须要有体道、求道的决心。
张孝祥诗作《赠鹿苑信公诗禅》其一言:“句中有眼悟方知,悟处还同病着锥。一个机关无两用,鸟窠拈起布毛吹。”[12]“句中有眼悟方知”指句中有令人发疑之处,这便需要禅者去妙悟,悟得其言外之意,则通达无碍。“悟处还同病着锥”指开悟之后便需放下“悟”之念头。“金沙虽贵,翳眼成病”[5]309,开悟极其难得,但若执着于“悟”这一行为中,则会阻碍体道的进行。“一个机关无两用,鸟窠拈起布毛吹”的意思是:悟或不悟就在于一个机关。触着机关,则开悟;未触机关,则迷误。鸟巢和尚拈起布毛吹,侍者便开悟,正是因为侍者触到了机关。此处,张孝祥旨在说明“悟”是禅修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觉悟与自性之间的关系
杨万里诗作《送乡僧德璘二首》其一言:“湖上诸峰紫翠间,三年欲到几曾闲。侬今去处侬知么?不是南山即北山。”[13]杨万里以“湖上诸峰”来比喻僧德璘所想达到的开悟之境。为了达到这个境界,德璘三年都未曾闲过。所谓“南山”与“北山”,其实是比喻“空”和“有”的境界。禅人常以“这边”、“那边”来比喻“空”、“有”,故杨万里也效仿之。此诗旨在说明觉悟之后便能彻见真空妙有的自性。
叶适诗作《题扫心图》言:“大心觉也无亏成,小心沤也随灭生。道人常与帚柄行,遇其欻起须扫清。世间亦有无根树,又言朗月当空住。劫尘颠倒不自繇,只笑本来无扫处。”[14]51“大心”指自性妙体,“觉”即觉悟,禅者觉悟之后便发现自性是无亏无成的。“小心”指欲望之心,“沤”意在虚空无常,欲望之心随物境变化、随生随灭。修行之人常常清扫自己的心灵世界,就是要去除内心的妄想和欲念。这些烦恼都是无名而生的,就像无根之树无根而生一样。其实,自性本是真空妙有的,它就像明月一样常挂于天空,禅者若能彻见自性,则水静沤止,根本无需清扫所谓的“小心”。此诗与慧能之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类似之禅理。其旨在说明:心灵的觉悟就是自性(佛性)的显现。
通过以上举例可知,宋代诗人极力借用诗歌形式来阐明各种禅理,这样的方式十分有利于禅学思想的传播,同时也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和题材。但是,禅理入诗只利于言理,并未能构建出诗歌艺术本该具有的审美意境。
三、禅趣入诗
禅趣入诗,常见有两种类型:一为表达自在随缘之禅趣,二为表达观物明心之禅趣。
(一)自在随缘之禅趣
宋诗中最常见的就是自在随缘之禅趣。王安石诗作《钟山即事》言:“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4]1155此诗的主要基调是“静”,原本活泼跳跃的涧水是幽静的,原本婀娜摇曳的花草也是幽静的,屋檐下的“我”是宁静的,山中的鸟儿也是一声不鸣的。万事万物,无声无息,气静神闲。“一鸟不鸣山更幽”改自王籍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15]。王籍用的是反衬法,王安石用的是直抒法。正面渲染山中之宁静,实则暗指自己退居后再也听不见朝野谗佞之言,落得一片清净,颇有自在悠闲之禅趣。
叶适诗作《无相寺道中》言:“傍水人家柳十余,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鸡露啄堪幽伴,芦菔风干待岁除。与仆抱樵趋绝涧,随僧寻磬礼精庐。不知身外谁为王,更觉求名计转疎。”[14]113此诗关键点在于“自然”。人家傍水而居,亭子以山而建,水旁有绿柳,山下有秋菊。这里描写的是人生活在天地自然中,与自然万物相伴的场景。“竹鸡”又称竹鹧鸪,是一种观赏性的鸟类。夏季,竹鸡多在山腰和山顶活动。秋冬季时,竹鸡移至山脚、溪边和丛林中觅食。故“竹鸡露啄堪幽伴”是自然而然的行为。“芦菔”即萝卜,萝卜一般在夏秋季节收获,将萝卜风干,准备在冬季岁末时食用。故“芦菔风干待岁除”也是顺应自然四时的行为。“我”与仆人抱着柴在溪边行走,随着僧侣的步伐到禅舍祈福,不知道当朝君王是谁,求得功名又有何用呢?诗人自身也渴望超脱于仕途之外、寄情于自然之间。整首诗表达了恬淡随心、任运随缘之禅趣。
(二)观物明心之禅趣
宋诗中亦多见观物明心之禅趣。王安石诗作《暮春》言:“无限残红着地飞,溪头烟树翠相围。杨花独得东风意,相逐晴空去不归。”[16]花落红飞,是诗人所观,观万物之衰败;溪流树翠,也是诗人所观,观万物之欣荣。世界万物,欣荣衰败,皆为自性的作用。诗人观东风、观杨花,以东风喻有执之物,“惟空灵之杨花,得知‘东风’之作用,能了‘空’证‘空’,归于‘真空’中,不再落于‘有’界之中。”[5]357诗人以心观物,得真空妙之境,尽显禅趣。
戴昺诗作《幽栖》言:“幽栖颇喜隔嚣喧,无客柴门尽日关。汲水灌花私雨露,临池叠石幻溪山。四时有景常能好,一世无人放得闲。清坐小亭观众妙,数声黄鸟绿阴间。”[17]诗人幽栖于尘世喧嚣之外,观“汲水灌花私雨露”,观“临池叠石幻溪山”。一方面,天地总有慈悲,对他物施以雨露;另一方面,临池叠石无非是人造的假象幻影。诗人坐在小亭中,观万物之妙,观“数声黄鸟绿阴间”,悟“有声”于“无声”之中,得无限禅趣。
胡寅诗作《题岳麓西轩三绝》言:“月户风窗悄不扃,静中真乐故难名。山泉未识幽人意,自作穿林泻壑声。”[18]诗人观月,月在户;诗人观风,风入窗。此时此刻,悄然寂静,诗人已达禅定之境,这其中的乐趣不可用言语表明。然而,山泉未解个中乐趣,仍穿林而过,发出冲击深谷的巨响。诗人以心观物,心定则山泉亦无法扰心,此为“观”与“定”的禅趣。
通过以上举例可知,此类诗歌多为借景言趣,呈现出了一种颇具智慧的禅学意境,充满了韵味和妙趣。以禅趣入诗,或空灵、或闲适、或深奥、或飘逸……大大提升了诗歌的审美意境,这是禅学与诗歌相融的最佳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诗学的发展。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