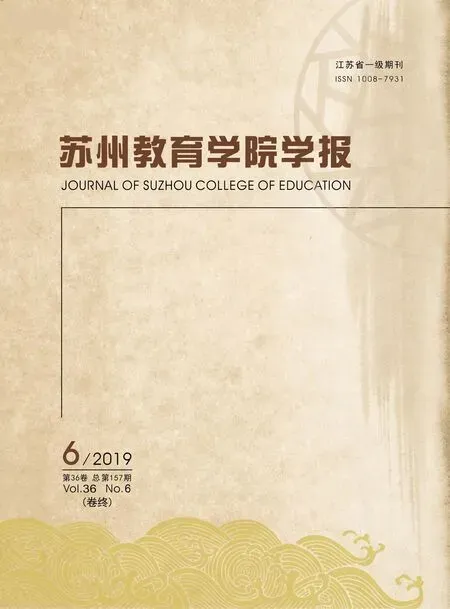东北沦陷区侦探小说的空间构置与文学想象
詹 丽
(1.沈阳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辽宁 沈阳 110034;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问题的源起
1941年,伪满洲国《艺文指导纲要》①1941年3月23日,伪满洲国弘报处制定并发布《艺文指导纲要》,是伪满强化文艺统治的重要措施。的出台,限制了新文学的发展,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以《麒麟》和《新满洲》等期刊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满系”侦探小说家,主要有李冉、李北川、忠祥、金原等年轻作家。他们在官方意志和消费文化的双重规约下,在借鉴中外侦探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如李冉的《夜之汽车》《夜半枪声》,李北川的《覆面的杀人犯》和忠祥的《烟斗》等,都名噪一时,大受欢迎。当“满系”侦探小说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以自己的方式在殖民语境的论述框架内为东北沦陷区的区域特殊性找到坐标时,“在满”的日本侦探小说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将“满洲想象”纳入这个时代的文学体系之中,竭力捕捉“满洲”的种种形象。[1]这批“在满”的“日系”侦探小说家主要是指20世纪活跃在旅顺、大连——东北最早的殖民地——的“南满”地区作家群体②还有一部分“日系”侦探小说家集中在新京(即长春),主要发表园地为《同轨》。《同轨》作为殖民者官方意志下的国策刊物,所刊载的侦探小说多是从日本翻译过来发表的,是脱离东北“满系”的小说创作,不列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这里主要以大连区域的侦探小说家为考察对象。,他们以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为中心,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人大多也是“满铁”的职员。如大庭武年、山口海旋风、岛田一男、木坚原一郎、鲇川哲也、南泽十七、西村望、椿八郎、石泽英太郎、中岛敦、清冈卓行、谷让次、加纳一郎等,主要作品有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ペトロフ事件》)[2],大庭武年的《十三号室杀人》[3]《赛马会前夜》《白杨山庄事件》等。作为东北殖民地的最早体验者,这批“日系”侦探小说家的创作不仅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东北“日系”“满系”的侦探小说创作,同时也影响了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不可忽视。
细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日系”和“满系”侦探小说家笔下的侦探小说多以“满洲”世界为书写背景,在创作中融入了关于“满洲”的空间想象。这种空间的设置既是东北被殖民时期时代意志的显现,同时也是他们对现实空间的“文学关注”,是真实体验的隐性表达。那么,“满洲”对在地的“日系”和“满系”作家而言代表着什么?以消费为主导的侦探小说与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空间“满洲”相遇会产生怎样的文学想象?身份迥异的“满系”和“日系”侦探小说家在现实取舍中如何赋予虚拟的文学空间以深层意义?“日系”“满系”侦探小说的互文比较研究,对于确立东北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意义何在?
本文力图在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框架中,从东亚双边互动到全球殖民化的宏观视野出发,通过观察“日系”“满系”侦探小说家共时而迥异的空间构置和文学想象,分析“日系”侦探小说家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满系”侦探小说家的被殖民者和解殖民者的双重身份。对“日系”和“满系”侦探小说家的对照比较研究有三点意义:首先,以侦探小说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应引起足够重视;其次,东北沦陷区因为具有政治性、国际性、现代性、本土性等多重复杂形态的“殖民乱象”,是中国区域史或中国现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隅;最后,东北沦陷区文学无论作为反抗的文学抑或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都应该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体系相对接。
二、“日系”侦探小说家:从“摩登都市”到“贫民窟像”
分析“日系”侦探小说可以发现,大庭武年、鲇川哲也的作品都是通过捕捉殖民地的各种元素,并充分利用侦探小说的神秘、紧张等特点,铺设出具有异域情调的交织着富有与贫穷、高贵与粗野、法制与犯罪等鲜明对比的摩登都市和贫民窟像等空间构置。这个空间既是作者生存的现实空间,也是文学想象的审美空间,具体到作品,往往由一系列意象来完成,如“都市”“大广场”“霓虹灯”和“鸦片”“窑子”“支那澡堂”等。这些意象的构建不仅是文学的美学追求,也是解读文学深层价值的实现形式,它体现了殖民者的优越心态和对“满系”人的鄙视,如果将殖民地放在全球视域下进行考察,会发现更深层的意义。
(一)西方的镜像摹本:“大广场”“月光海岸”“摩天大楼”
首先从几部作品切入。鲇川哲也创作于1943年的《佩德洛夫事件》,讲述了西洋人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分割而引发的杀人事件。小说开篇就定下了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
“大广场”是这个都市的中心。在其周围圆弧之上耸立着领事馆、宾馆、银行、警察署等建筑。沿着这一线路有轨电车穿行而过。内圆是个小公园,建造了花坛,还设置了长椅。而且在其中心,初代军政官某将军的铜像,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姿态,睥睨着四周。据说是曾经从欧洲归来,单骑横断西伯利亚的勇敢无比的帝国陆军军人。在那里的长椅上坐着带着幼儿的年轻俄罗斯母亲,正在给鸽子扔吃的……中国老头儿舒舒服服地打着瞌睡。到了午饭时间,附近公司的女职员们三三五五地来到这里,说着同僚谁谁的闲话,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2]11
大庭武年的《十三号室杀人》讲述了在殖民地大连由日本人经营的“皇后宾馆”中发生的西洋人之间的凶杀事件。开篇就设计了一幅都市美景:
那是日本唯一的殖民地都市D市郊外的号称“月光海岸”的海滨避暑地发生的事情。我想大概也有知道这里的先生。如果对“月光海岸”略加赘言的话,“月光海岸”就是将美国风格的人工设施和大陆自然风情巧妙融合的、东洋少有的异国情调的海岸避暑地。每到旺季,那里是唯一能够吸引满洲支那一代内外的有闲阶级,让人感到仿如来到美国一样、呈现着豪华和繁盛场景的地方。[3]2
这两部作品都是以“南满”殖民地作为小说的空间背景,充满了浓郁的摩登都市色彩。不可否认,在小说的空间设置上,作者表现出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和强势地位。但是细读作品,其中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他者”——西方景观——的介入。如《佩德洛夫事件》中欧味十足的大广场——欧式建筑群、有轨电车、花坛、欧式长椅、飞来飞去的白鸽、三三两两的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幅国际化摩登都市的景象跃然纸上。由此可见,西方都市成为日本侦探小说家描写殖民地都市的参照物,摩登的都市风景、散发着异国情调的咖啡馆和舞厅、频频登场的外国人、有闲阶级的时尚生活等描述,满足了日本人对欧洲的向往之情,成为他们确立自身优越感的标志,这种浸润着西方文化的符码,成为富足、优越、现代的隐喻。为此,“日系”文人将“南满”作为西方文明的载体,使之成为让人怀想不已的对象物。
“18、19世纪欧洲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西方帝国梦的催生,使得地球一下子变得小且可把握,当两个文明在西方视野里会合时,已经几千年生活在大陆农耕文明、皇权专制下的东方‘病夫’暴露出其文明的颟顸和落后,全球帝国的‘霸权梦’和‘改造梦’、‘殖民梦’成为西方大小国家向外扩张的唯一意识形态。”[4]东方各国无一幸免地被殖民化,“日本历史上同中国一样是封建制国家,近代开眼向洋、维新图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其物质的现代化在亚洲是最快最有成效的,但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的现代化思想却并未同步,缺乏‘个’的思想和以此为鹄的的制度是日本现代化严重缺失的,并导致最终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5]。所以,来到殖民地的文人享受着殖民城市的优待,臆想着西方文明,从侧面反映出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脱亚入欧”的殖民口号相符。
更有意味的是,身处异地的日本人,通过殖民地都市这个中介想象西方的生活。这种虚拟的西方景观也成为日本人所讲述的虚构故事,成为一种叙事策略。小说形成了一种跨文化视野,通过直接切入异民族的生活领域和异化人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多种文化诉求。《佩德洛夫事件》以俄国人的异族视角勾勒出独特的存在。《小盗儿市场杀人》[6]通过本民族的边缘化,或者说是异化的人在异域的独特感受,完成了他者形象的塑造。《赛马会前夜》以“星之浦”旁边的赛马场和牧场为舞台,讲述了“彗星”被骑手射杀,紧接着骑手也被杀害的故事。《白杨山庄》讲述了大连市郊别墅风景区中的西洋人杀人事件。“日系”侦探小说家描摹都市现代化时释放快感的炫耀性行为,其实是对隐性欲望操纵下的虚假幻象的迷恋,在简单的表象后面有强大的神话体系,“能指背后有更大的符号系统和意识形态的钳制,西方神话成为了永远的缺席的在场者”[7]。这种对西方的臆想其实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巴赫金就指出:“什么是杂交呢?这是两种社会性语言在一个表述范围内的结合,是为时代或社会差别(或某些其他因素)所分割的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在这一表达舞台上的会合。这种东西方交织的景观是东西方之间的‘时空滞差’所造成的。”[8]“时空滞差”导致殖民地文化的缺席和西方文化的在场,恰恰是无意识的西方优胜论的象征色彩,完成了侦探小说从“追寻东方审美之根”到“追寻西方审美之根”的转变过程,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从殖民者身份到被殖民者身份的隐性转换。
(二)消费“满洲”的表征:“鸦片窑”“妓院”“支那澡堂”
“日系”侦探小说设置了大量的贫民窟意象,如“鸦片窑”“妓院”“支那澡堂”等。这些空间想象充满了贫瘠、野气、混乱、落后、粗俗的乱世众像,表现出暧昧、肉色、糜乱的色彩。《小盗儿市场杀人》是体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满洲异闻》中对大连的“露天市场”是这样记载的:“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露天市场’不仅是满洲人生活日用品的大超市,还是他们,特别是底层人难得的民众娱乐场,自不必说有梨园(剧场)、书馆(妓楼)、料理店,还有说书场、杂耍场、魔术师,甚至还有西洋景,不仅能够大饱口福,还能达到无比的慰安。即此处为欢乐之境也。这种‘露天市场’全满各地都有,但大连最脍炙人口。”[9]相信这是大连“小盗儿市场”的真实写照。然而,在很多日本人的眼里,“小盗儿市场”却是个神秘的罪恶聚集之地。因此,大庭武年称此地为“猎奇之地”,只要“稍稍猎取”就能挖掘出很多侦探小说创作的素材,《小盗儿市场杀人》里呈现的“小盗儿市场”就是这样的地方。大庭武年通过对“小盗儿市场”“鸦片窑”“支那澡堂”等现实存在的地方和那里生活的人们细致入微地描述,实现对伪满“满系”的颟顸书写,既体现出作为殖民者的“日系”小说家的殖民意识,也或隐或显地体现出西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他们思维的支配,空间设置成为消费文化的表征,后殖民主义则是思想的核心。
《小盗儿市场杀人》从异化、边缘的落魄日本画家“我”和小偷龙崎的互动视角展开了一系列的空间转换:“我”在发现妻子不忠之后,企图制造“厌世舞女自杀”的假象来杀害妻子,不料这一行为却被小偷龙崎发现,这成为威胁“我”的砝码,“我”趁夜乘船奔向“满洲”,来到了日本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过上了挥霍无度、享受安逸的乐土生活,但是好景不长,不节制的挥霍很快使“我”捉襟见肘,只好典当妻子遗留下的胸针,却被追到“满洲”的龙崎发现,龙崎开始讹诈“我”从典当行得来的钱。于是“我”带着龙崎,不停地穿梭在“鸦片窑”“妓院”“支那澡堂”等地,如此一番异地消费享受。“我”无法填补龙崎无底洞般的欲望,决定铲除他。计划实施的场地就是“小盗儿市场”,“我”将龙崎打扮成支那人来到这个“超级魔窟”参观感受,趁其不备将其杀死在暗娼胡同路口,制造了露天市场“支那苦力被刺死”的假象。“我”以为计划天衣无缝,但最终仍被绳之以法。
《小盗儿市场杀人》将故事的舞台放在了日本的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将杀人现场设置在大连的著名之地“小盗儿市场”,并通过对此地耸人听闻的奇闻异事的描写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设置了边缘化的主角,他在走投无路之时,意去中国东北,他认为那里是寻求欲望、追求刺激、摆脱困境的海外化、神秘化、财富化的地域。大批日本流浪汉和白丁都将目光投向东方,其中犹以东北的大连、哈尔滨为甚。大多日本作家到了满洲殖民地后,都是以一种审视、享受和具有主动权的主体者视角,将满洲人作为“他者”进行审视。对满洲空间的建构建立在殖民者优越的身份特征之上,形成了主客体的不平等[10]。在东北的繁华都市这种空间里展开的文学想象中,作者有意无意间强化了或隐或显的身份认同,一方面表现了侵略战争带来的文学异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西方主导权的强势所在。“我”经历的故事几乎完全遵从西方消费文化和叙述模式:冒险——探窥秘境——尝鲜(原始情欲)——种族优越。他们利用殖民者的身份自由穿梭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将自己建立在西方化的殖民者之上,从而完成自我身份西方化的转化,这表现了一种东方地域的民族自卑和作为弱势民族的表征,以及其殖民侵略的深层心理机制。
这里的空间意识和文学想象是建立在西方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万国公司的世界观深刻影响着日本小说家的创作。“19世纪以来,东方总是处在被观看的位置,西方人总是看客,他们总是保持着距离,从不介入其中,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东方,从而得到‘怪异的快乐’。”[4]殖民者身份的确认为“日系”侦探小说家实现西方主义提供了条件,他们站在西方立场,把玩作为弱势存在的中国,深谙全球化消费主义之道,懂得将殖民地的神秘之道推销给外界,供殖民者“观看”和“猎奇”。用消费主义叙事构置的文学空间,成为他们消费伪满洲国的表征,这种表征无意识地瓦解了日本殖民统治者既定的殖民者身份,并落入跨国欲望、消费主义等全球化陷阱中,最终成为西化的被殖民者。
(三)现代主义创作与话语所指的逆转:身份的隐性转换意义
日本同中国一样曾是封建制国家,近代开始,“西学东渐,潮落潮涨……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11]。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其物质的现代化在亚洲是最有成效的,但思想的现代化却明显滞后。“人本位”思想及相应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其文学思想也多以西方“他者”的“现代文明”为价值标准。“日系”侦探小说家也不例外,他们在文学中建立的空间意识及构置的文学话语和叙事中,处处隐含着西方的价值标准,这主要表现为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和国策文学下的话语逆转。
20世纪3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①《新青年》是森下雨村、横构正史等创办的日本侦探杂志。及其发表的侦探小说,影响了“在满”的一批文学家,并与其在感性上达到共鸣。于是,部分小说家开始转向侦探小说创作(如大庭武年),并在小说中设置具有浓重的都市色彩的空间,将“神秘的气氛和机智幽默的雅趣调和在一起……营造现代主义的旨趣”[12],形成了兼具现代性、颓废性和实验性的文学特点。但是这种与现代主义存在精神联系的文学意识②这种文学意识,冈田英树称之为“大连意识”。,却与作为军国政治思想代表的日本所要求的“新京”意识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不配合”,甚至与国策构成了一定的冲突。[13]从而形成了迥异于“新京”等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参与意识,这些意识的转换促成文学中形成鲜明的“他者”形象,这既表明殖民地话语环境与意识的裂痕,也表现殖民文学场域内部出现真空与漏洞,导致日本殖民文艺政策从制定到落实出现错位。
日本提出的“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意在美化对东北乃至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因此,与英美发生的战争,都被殖民意识形态描述为抗击英美帝国主义、实现大东亚共荣、创造世界历史新模式和新格局的“善举”,即把英美描述和制造为他者、恶魔和复仇对象,把自我和其他亚洲国家描述为具有共同历史命运、共同任务和共同道路的“想象的共同体”,进而消弭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仇恨,并将其转移和转嫁到“共同敌人”——英美等国——身上,这是日本在其殖民的亚洲国家的文化文学政策中极力推行和实施的“意识形态”举措。但是,日本侦探小说家却潜在成为西方先进文明的追随者,形成了迥异于“新京意识”的“大连意识”。殖民者力图宣扬的殖民话语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文学语境中发生了话语逻辑和所指的逆转,意图和结果之间出现了背离。换言之,殖民国策和文艺政策力图达到的“大一统”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实现,殖民意识和意志并非铁板一块、万能无隙的,这是我们研究殖民环境和话语时需要注意的。殖民国策和政策支配下的文学活动,其自身也存在矛盾,或者说是意图与结果之间的不平衡,这样的不平衡事实上给殖民意图和意识造成颠覆性的消解。
三、“满系”侦探小说家:“原乡记忆”与“反现代性书写”
不同于“日系”侦探小说家,“满系”侦探小说家设置的空间架构一致地脱离了都市生活,小说中大量隐喻意象的展示、情境的处理和故事的展开,都表现出了“满系”侦探小说家作为通俗文学创作者和被殖民者的文化心态。作为都市文学的“衍生品”,侦探小说是伴随着都市的繁荣和现代化的发展而被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但是,“满系”侦探小说家却在都市小说的内核里,表现出回归自然的强烈渴望。
(一)阴郁、压抑的空间设置:“黄昏”“草原”“大地”
《一〇八指纹》中开篇设置的空间场景是这样的:
在初秋的风里,田野尚茂腾腾地长着大半熟的高粱、大豆,牧牛的孩子在叱乎着牛群,不时传来一两声的啼鸣,打破四野的寂静。[14]
《古庙月夜》中:
事情发生在一个暮秋孟冬的晚上,狂风摇撼着枯树,黄叶飞舞在空中,昆虫息鸣,路体阴暗,除去偶尔听到间歇的汽车喇叭声外,整个都市几乎全被风声吞没。
黄昏,无声无息地充满了宇宙,远处连绵的山,大平原上的村落、树木,都被暮色淹没了,只有一撮山巅,朦胧地浮在黄昏的表面上。[15]
黄昏、田野、平原、村落等意象代表了“满系”侦探小说家精神结构深层中乡土、家园、自然与传统的潜在意识。这些意象景观的交叠出现,带来的是表象背后的阴郁和压抑。不仅如此,在“满系”侦探小说中,“乡土”意象既指现实具体的农村家园,也在深层和隐喻中表现为对乡土的追随,对都市的逃避或者说难以进入,体现出一种疏离的潜在意识。他们“看”故土乡村时的目光和方位,以及乡土意象呈现出的深邃、灰暗、阴郁的视景与色调,实际上表现了他们的一种态度。这种书写不同于现代性叙述者那种居高临下的悲悯和审视,更多是一种自我压抑。这种意象的选择不仅表达了在地小说家的心态,也暗示了伪满洲国的黑暗现实。
以“乡土审美”为坐标的“满系”侦探小说,把城市作为潜在的对立面,对现代化都市的描写也多是批判性的,如“火车似一匹发了狂的野兽,仿佛要撕毁了这黄昏的宇宙,飞似的在铁轨上驰行着”[16],作为都市现代化标志的火车,在作家看来却犹如野兽。《十三点的钟》中的老侦探衫浦认为都市是“罪恶的原始林”,都市是人们互营生活的地方,而那绝对不是理想的。[17]虽然都市的文化程度比乡村高,但是那种文化是表面的、轻薄的、不堪的,这种轻浮的文化引发的犯罪也比乡村多。都市并无森林,可是却撒满了犯罪的种子,结果,都市就变成和原始森林一样阴暗的存在了。小说表达了都市文化的浅薄以及易引发集中犯罪的性质。都市同样带给人以压抑感——晨露中的楼巅,车马喧哗,人行如蚁,进而生发出对都市文化的批判,如对都市中不伦关系的批判、对摩登女郞的批判。
(二)对传统文化的推崇
通过对乡土的追随和对都市的批判,“满系”侦探小说隐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仁、义、忠、孝、节等思想——价值的肯定,遵循着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如金原的《一〇八指纹》用一个西式的标题讲述了一个仆人杀主的传统故事。仆人李日成在刘老爷出差奉天之际,预谋偷盗刘家财产,霸占其姨太太,姨太太誓死不从,终被仆人杀害并弃尸荒宅。故事梗概简单,破案过程顺利,恶仆李日成被绳之以法。小说情节可以说并无新意,但其中成功塑造了三个仆人形象:吴妈、小红和李日成,并用大量笔墨描写吴妈的沉稳忠心和小红的年轻机敏,并通过他者之口痛骂李日成的贪财好色、狡诈不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都能发现,小说其实是以侦探为噱头,讲述一个关于忠贞的故事。同样以此为文化内核的还有李冉的《荒草里的男尸》[18],男主人公张世明因工作调到外地,留妻子新虹在家中,并托付好友王世新关照妻子。不料,朋友和妻子日久生情,张世明怒火中烧,顿起杀机。通过精心谋划,张世明在一个雨夜杀死妻子和好友。故事结局是张世明归案,但同时描写道:他的眼中透着坚定的神态,寓意其对行为无悔,表明了作者的道德准则。小说意在表达凡是不守妇道、不遵伦理、不讲信义者将被生活的逻辑和传统的道德予以教训和惩戒。
现代文学中,继承传统、弘扬儒家文化精神的作品多是武侠、言情小说[19],侦探小说很难嫁接其中,但伪满洲国的侦探小说却是一个例外。为什么“满系”侦探小说家会利用儒家传统文化构成其故事和意义元素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地区侦探小说创作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伪满洲国在特定时期文人的潜在选择和一种文学创作姿态,其情节中包含着与现实政治的隐喻和寓言关系。作为直接受日本侦探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满系”侦探小说家,具有与日本侦探小说家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审美意识,其深层意义是通过曲折书写实现话语逆转,即面对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彼此混合、难以辨析的复杂局面,“满系”侦探小说家或将殖民性与现代性完全等同,通过传统书写,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殖民性,以瓦解殖民主义的逻辑,或不加选择地反殖民现代性,拒绝殖民主义的逻辑。[20]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伪满洲国文学法规禁止颠覆性的、悲观的甚至是消极的著作发表,至20世纪40年代,相关法规愈加复杂繁琐,明令作品不得有消极情绪,并对所谓堕落和消极文化进行查禁①1941年2月21日的《满洲日日新闻》中,当局刊登了“八不主义”: 1.对时局有逆行性倾向的;2.对国策的批判缺乏诚实且非建设性意见的;3.刺激民族意识对立的;4.专以描写建国前后黑暗面为目的的;5.以颓废思想为主题的;6.写恋爱及风流韵事时,描写逢场作戏、三角关系、轻视贞操等恋爱游戏及情欲、变态性欲或情死、乱伦、通奸的;7.描写犯罪时的残虐行为或过于露骨刺激的;8.以媒婆、女招待为主题,专事夸张描写红灯区特有世态人情的。参见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这是所谓的“国策”的一部分。而在地的侦探小说乃至通俗小说、女性文学、儿童文学等都是被统治者默许的存在,他们在完成殖民书写的过程中融入了反殖民的思想,在创作中具有一定的、曲折的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国策的对抗与颠覆。“满系”侦探小说家大部分作品中存在的所谓阴郁描写,其实是作家无法反抗政权和“国策”,但艺术家的良知又使其深感此政策的反人性反人类,是曲折对抗法西斯意识的心曲。为此,他们共同完成了“反抗的伪满洲国文学”[21]。其二,通俗文学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传统文化基因和传统文学创作规则,“言说了作家的某种人生存在、某些心灵隐秘,又书写了现代社会的某些人文景观,并同现代社会之间构成了某种张力态势,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反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也体现出一定的现代人文品质”[19]。从刘晓丽教授的“解殖”观点[22]这个思路进行延伸,可以说他们衔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民族国家叙事。但另一方面,“满系”侦探小说家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殖民统治者的文化策略。伪满洲国建立后,殖民统治者为了安抚民众,为殖民统治正名,提出“五族协和”“王道乐土”,文化上主张尊儒重道,提倡儒家传统文化。以女性观为例,殖民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利用儒家思想提出“贤妻良母”观念,即顺从的、温和的,凡是不符合这些要求,即被贬低为淫荡的、自私的,这种女性观在“满系”小说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以上分析表现出伪满洲国通俗文学在殖民性、现代性、本土性、传统性多重纠葛中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变化,以及在文学类型中的自我建构。从更深层面来说,也拓展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思路和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路径。
四、结语
“满系”侦探小说家的创作“既有大历史视野下的殖民主义乱象,同时又有个体角度生发的解殖民叙事或复杂原乡”[23],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对殖民地满洲的理解和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伪满洲国文学加以审视,不失为一个新鲜的视角。从“日系”和“满系”侦探小说家的创作可以看出二者的对立关系——现代性/乡土性,西方/东方,自由/拘压,改造/被改造,观看/被看,先进/落后,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符号赋予的隐喻式能指体现出殖民性、现代性、本土性的复杂纠结与矛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力图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文学现代性的立场上来考察,在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以世界为参照系,为现代文学寻求历史坐标。[24]而在这种主导型的历史叙述中,伪满洲国文学被排除在主流研究之外。21世纪以来,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它仍然没有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叙述中。关于日本侦探小说家的东北都市空间构置并非异数,在地的“满系”知识分子,如爵青、小松等作家的都市书写,实现了东北都市的现代性叙事与世界体系的对接。进而推敲可知,中国通俗文学不应该被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的脉络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支,他们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和样式。
“满系”侦探小说家在残酷的殖民统治下利用文化产品的政治矛盾性,以娱乐和消遣,让沦陷区的民众在这个文化空间内参与构建一种娱乐文化话语,[5]以逃避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和操纵的大东亚侵略文化。也就是说,沦陷区的通俗文学一方面和日本统治者妥协,另一方面又抵抗了他们的文化政治。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参与写作的“日系”小说家都像现实中的政治和军事殖民统治者那样,想利用这些想象的软性的侦探故事麻醉殖民地人民。也就是说,并非所有殖民宗主国的人都是殖民者或殖民帝国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和执行者。当然,其作品不可能不为本国的殖民政策服务,但他们也在无意中流露出对殖民的反思。如鲇川哲也在小说中就借主人公之口流露出反战情绪,这一点是颇有意味的,这既说明伪满洲国的日本殖民者尽管制定和颁布了“国策”性的纲要,但并未严丝合缝地得到忠实、全面和统一的贯彻,也说明大连甚至整个东北的日本殖民者,对殖民话语构成和内涵的认识与理解是存在层面差异的,也是不全面的,对殖民话语与殖民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把握不准[25],进而形成了文学创作中的复杂性和多重解读的内涵,拓宽了多类型文学研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