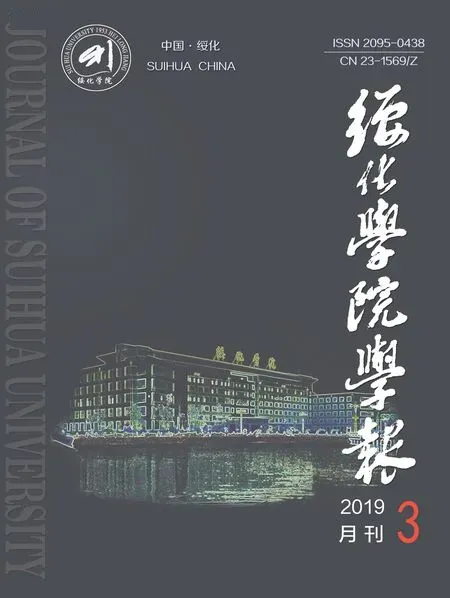东北鼠疫与民众反应(1920-1921)
梁坤莲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鼠疫(Plague Pestilence)是一种由鼠疫杆菌所致之烈性传染病,分为腺鼠疫、肺鼠疫、肠鼠疫、皮肤鼠疫等,[1]能经人和人直接传染,病死率甚高”,对近代东北(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及奉天省)影响深远。1920年冬季,东北爆发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尽管有十年前的经验,这次鼠疫仍旧造成了东北境内近万人的死亡,成为民众不可抹灭的记忆。重构历史现场,勾勒重灾之下的众生百态,无论是对近代东北民众的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还是对近代灾害史与环境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一、听闻有疫
(一)惊与防。1920年11月间,海拉尔地方传来鼠疫的消息,“以患者甚少,尚未惹人注意。迨至年杪,猝薨十数人,始各相顾失色。”[2]因为,“鼠疫一症,医者认为有防法无治法,故于染有鼠疫之人,认为必死。且此疫由于呼吸传染,故防止传染亦极困难。于是不有鼠疫则已经,如有鼠疫发现则邻人相惊以伯有,恐慌极矣。”[3]在惊惧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着手防范。各界“筹议预防亦极急激”[4],“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日来城关来往之行人,带防疫囊者,亦较前骤增。”[5]惊恐与防范,是大疫之下东北民众的自觉反应。
(二)利与善。东北疫讯传来之后,有人研究、发布各种预防、辨别及治疗方法。治疫奇方、鼠疫读核消毒散、专治鼠疫神效汤等消息频频出现在各大报刊之上。[6]这些消息的背后,或包藏着商人的逐利之心,或蕴含着民众的良善之意。肺鼠疫流行之下,有的肺药号称治疗肺病的“唯一之良剂。”[7]肺鼠疫死亡率几为100%,即使早期大量服用磺胺类药物,治愈之希望亦不大。[8](P6)广告中的溢美之词,不过是商人逐利的遮羞布。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鼠疫发生之后,许多人将自己的经历、对鼠疫的认识、听闻的药方“送登各报,普告大众,以免疫害”[9]。还有的人“对于防疫之事,均极热心”[10],或施医施药,或帮忙检查行旅。灾害之下,人们作出了逐利以利己与行善以利他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
(三)评与讽。有人关心鼠疫的生物及社会意义,有人则关注其文化意义。鼠疫发生之后,有人撰文讽刺政府只知关注“未必真有其事”之事和“防不胜防”之事,而忽视对社会民生关系重大的“不可不防”的鼠疫。[11]还有的人以鼠疫作类比,抒发自己对某个领域或某个事件的看法。如有作者指出鼠疫流行是因为人们“贪饮食起居之不慎”,因此“防疫以去贪为第一义”。以此为引子,转向其要论述的正题:“商界流行的一些毛病也是由于贪心引起的,要改革商界,也当“以去贪为第一义”。[12]对比两种行为可知:对鼠疫进行评论者,关心鼠疫流行之下的社会民生;借鼠疫进行讥讽者,并不十分关注鼠疫流行的后果。两者的区别,在于一颗颗有温度的心和一张张冷漠的脸孔。
二、眼见疫者
(一)予以关爱。鼠疫之可怖,甚于猛虎,“令人闻之心胆战”[13],何况接触。但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心怀大爱,热心检疫,对防疫事务十分尽心,甚至为防疫献出了生命。1921年3月18日,哈尔滨地方公益会助理防疫的俄国医官斯尼次不幸感染鼠疫,两日后身亡。哈尔滨地方长官和防疫总处医官亲自前往吊唁并上报内务部。[14]这并不是个例。当时,许多年轻的医官如苑德懋、阮德毛、俞树棻等都在照顾疫者时被传染,以致因公殉职。除心怀大爱的医护人员之外,有些亲朋好友也愿意侍奉床前。长春同街德发祥皮靴店的李伍患鼠疫后,好友陈镒湘“因笃友谊,不顾一切,前往看护”[15]。由此可知,无论是防疫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愿意燃烧自己,给鼠疫患者以温暖。
(二)趋利避害。鼠疫流行之时,因畏惧而隐瞒、躲避者及因利益而抗拒者,不胜枚举。居民因为害怕医官检验,“初病时匿不报告,既死后,亦不敢收验,或埋雪中,或弃之田野”[16]。哈尔滨医学研究会主任的妻子就因为害怕隔离留验,而把丈夫的尸体弃于街道;[17]头道沟寓东兴源车店店内有客人死亡后,由于店家匿不报告,导致鼠疫蔓延。[18]从中也可得知,患者和隔离所,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所在。有人“因病被逐”[18],有人已“届隔离期满,应送回家时而不将原有住址报告,盖恐又将其接触者送赴火车隔离”[17],有人“恐受牵连,拟将物品运往他处”[19],许多人即使看到“有尸体两具,弃之露天”,也“无人过问”[20]。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人们对鼠疫患者和隔离所的躲避心态。此外,有部分人士,“因不明防范之本旨,妄敢抗拒报告之天职”[17],而有部分人士,则想从中渔利,故而反对规定。哈尔滨防鼠疫委员会规定,一旦发现鼠疫病人和可疑病例,须马上向防疫总处报告,违反规定的中医辩解说“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上门的病人都由防疫总处处理,他们的收入怎么办?”[21](P192)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但是为了逐利而罔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就太可悲可叹了。更可悲可叹的是,这样的事情,在鼠疫流行期间,屡见不鲜。
(三)背德加害。鼠疫流行期间,道德沦丧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有人怕被检验隔离,竟然“将罹疫者打死,乘夜静时,投弃于街外”[17],以求蒙混过关。有人更是借着鼠疫的契机,行报复之事。哈尔滨铁路的工人李才,因为平时与人有嫌隙,就被人诬陷为鼠疫患者,并由此引发了1921年4月12日的铁路华工罢工事件。[20]当时有谣言称“防疫机构收容病人‘有进无出’”[22](P151),因此,“没有人愿意进隔离区,进去以后也拼命想逃出来”[21](P192)。诬陷健康人为鼠疫患者的人,其居心之险恶令人不寒而栗。
综上可知,在面对鼠疫患者的时候,有人愿予以关爱:防疫工作者用职业道德和爱人之心予以患者以关爱,普通百姓用一腔情谊给予亲朋好友以温暖;但是,也有但求自保的人,他们隐瞒消息,躲避患者,甚至抗拒防疫规定;更有一种人,背德加害于人:或将患者活活打死,或将健康人诬陷为鼠疫患者。
三、被检验者
(一)遵守防令。经过1910年那次惨绝人寰的鼠疫大流行之后,东北人民对于防疫有了一定的认识,为了让“误听谣言”[23]或“品性顽固”[24]的人民也遵守防令,防疫人员采取了系列行动,“除了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之外,防疫总处人员从伍连德开始,主动走出去,到社会上讲演、作报告,回答民众的问题。哈尔滨的街头,经常见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疗人员在回答民众的问题,使民众感到防疫人员的存在,稳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些公开疫情、取信于民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效果,从一开始的“抵触和拒绝”,到后来的“合作和配合”,“自觉地在防疫总处的领导下,一起和鼠疫搏斗”。[21](P191)由此可知,部分民众愿意遵守防令。
(二)规避查验。害怕查验的人们想出了各种逃避的办法。最常见的一种是特意错开检验严格的车站。“长春中日防疫官吏防范异常严密,凡北来旅客一律消毒或即隔离,但多数旅客为规避查验起见,往往在距离哈埠较远之车站买票至米沙子(在长春北二十英里)下车以避隔离。”[25]特意绕道是其一,潜伏而行则是其二。伍连德在信中说:“哈埠防疫异常困难,客运虽已停止而公事车每星期开行三次,带疫旅客往往搭乘此项列车及其他运货之车潜来此处,故疫症不特未灭,且益加盛。”[26]
(三)无理闹事。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因检查而闹事”[25],甚至对隔离所和医护人员发起攻击。俄国医士哥鲁哥夫和助手被乡民无理“罚困于疫室,扣留36小时(室内有染疫小孩二名),幸被困者卒无恙”[27]。当时,“人民反对将病人送回医院,与众隔离,及反对限制铁路交通,致发生种种谣言。医士于服务之际,多为人举枪拔刀相向。亚希洛地方有暴民六七人,攻击隔离所,释出二病人,并进击管所之医士。”[28]尽职尽责、心系百姓的人,却遭到百姓的攻击,殊堪悲痛。
综合以上可知,防疫工作可谓一波三折。一些思想先进或受到启发的人会遵守防令;部分民众会千方百计规避检查;而那些冲动、蛮横、无知又听信谣言的人,则把言语和身体上的痛苦,施加给了保护他们的人。可悲乎?可叹乎?
四、身染鼠疫
(一)仍想苟活。染上鼠疫之后,人们因“恐医官检验,初病时匿不报告”[23],“时而看西医,时而看中医,时而看草医,时而求算命先生甚至巫医神汉,各种药物乱吃一气”[30](P46),只盼能够痊愈。即使明知治愈无望,也希望趁活着时达成最后的心愿。长春顺和街阜丰永杂货铺的柜伙陈镒湘发觉自己感染鼠疫之后,想趁一息尚存,到奉天见兄长最后一面,因病势已重,被医官验明,带至隔离所。[15]
(二)但求速死。人们深知鼠疫造成的可怕后果,知道鼠疫的治愈率之低。因此,有的人在患疫之后,甚至了无生意,只求速死。有人“亲目所睹,忽有一人染此症,以为无救,莫若速死。遂取水烟袋水和旱烟袋油,调和服之,意欲加毒,谋求速死。”[31]
(三)处之泰然。还有的人,在生死面前十分冷静。负责哈尔滨防疫事务的陈医师描述说,中国的鼠疫患者完全知道自己的命运,因此“处之泰然”[22](P153-154)。这种情况在医护人员的身上尤其常见。伍连德医士前去看望染上鼠疫的阮德毛医生时,后者显得十分平静,他轻轻地说:“伍博士,您事务繁忙,就不用来看我了,而且这里也不安全。”[21](P192)
其实,在生死面前,人性都是相类似的。1920-1921年东北的每一个人,在经历了历史上和身边的人的死亡之后,都会明白,身染鼠疫即意味着步入阎罗殿。然而,尽管如此,还会有人挣扎着求生,当然,也会有人绝望地死去,还会有人听天由命。
总而言之,1920年爆发的鼠疫,在东北人民心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场灾难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诠释了他们对灾害、生命乃至道德的理解。
一次大鼠疫,十万众生相。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并不是历史记忆中不起眼的尘埃。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灾害降临之时传统道德的存续,折射了社会变迁之际思想文化的多元化。1920-1921年东北鼠疫和清末民初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两次鼠疫并称为近代东北三次鼠疫大流行。它们一同构成了近代东北“鼠疫流行”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32](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