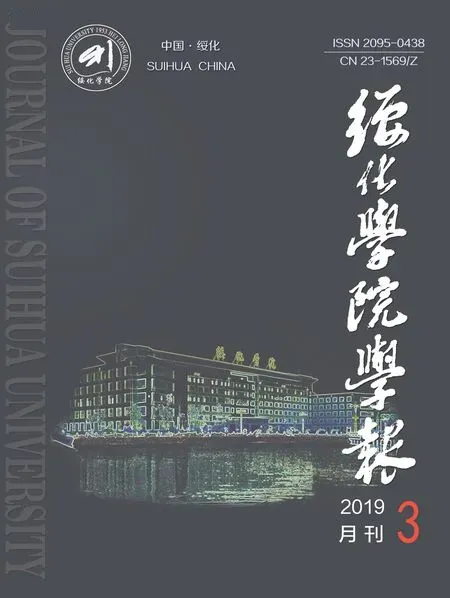何处可以安身:《小夜曲》的疏离主题
丁 平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石黑一雄于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将其创作母题归纳为“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并称他的小说“以巨大的情感力量,揭露了我们与世界联系的虚幻之下的深渊”。石黑一雄在2009年发表了他迄今为止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情感虽一度在人们之间变得虚弱,但作者最终仍寄希望于情感,认为只有爱才能让人走出孤立的困境。作者以其作为现代人的精神漂泊感,以及作为移民在文化上的无所归属感,在其作品《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中书写了疏离主题。
一、石黑一雄疏离感的形成
石黑一雄高中毕业后曾去加拿大以及美国游历一年,在北美期间担任过乐队Queen Mother的鼓手,时年19岁的石黑一雄将成为一名歌星作为自己的梦想,从他的嬉皮士流浪经历透露出,石黑在年轻时便拒绝绝对的管控,追求精神的自由,而当他正式成为作家后,每一部作品中都可见爵士乐的身影,或许这种嬉皮精神在石黑的血液中从未离去,精神的流浪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与主流世界,抑或是价值观的疏离与距离感。
如果说石黑一雄年轻时的嬉皮式流浪经历折射出作家与一切保持距离的内在精神,那么石黑一雄所处现代的文化情绪则使他的人物蒙上了一层若即若离的疏离面具。石黑一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山淡影》1982年一出版便获得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并受到广泛关注,可以说石黑一雄的创作生涯开始于20世纪后半期,整个20世纪的现代及后现代时代的文化情绪也不可说没有影响到作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有自己的病状,如果说现代主义时代的病状是彻底的隔离、孤独,是苦恼、疯狂和自我毁灭,这些情绪如此强烈地充满了人们的心胸,以至于会爆发出来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1](P156)在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变得极为接近的时代,人们心灵的距离却越来越疏远,有时宁愿向陌不相识的人倾诉内心,也不愿意与亲密的人互诉衷肠,石黑一雄在《小夜曲》中描绘了这一现象,作品中的人游走在家庭、自我和他人之间,无法安身。
20世纪整体的文化氛围使得一些关注人性本身的作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精神上的疏离与漂泊,如奥康纳、雷德蒙·卡佛以及艾丽丝·门罗等。但石黑一雄特殊的移民身份给作家带来的文化上的无所归属,令他作品中的“疏离”蒙上了别样的色彩。石黑一雄五岁随父母由日本移居英国,接受典型的英式教育,家中父母对其进行日本文化教育,因而作家的成长伴随着双重文化的滋养。高中毕业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游历使其接触到了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他曾在1989年与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谈到:“我没有明确的社会角色,因为我既不是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我没有明确的角色,没有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供我书写,没有人的历史看起来是我的历史。我认为这使我有必要采取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写作。”[2](P58)石黑一雄虽然与“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中的另外两位——奈保尔与拉什迪,同样有着移民经历,但石黑一雄却并未在作品中过多的书写移民作家身份杂糅的尴尬、痛苦境遇,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体自身如何面对过往的伤痛与过往的自我。可见,石黑一雄的创作并非只为某一种文化代言,而是以一种开放多元的方式与各种过度亲密的关系保持一定距离,以清醒的头脑去书写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二、疏离的表现形态及成因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的五篇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涉及到家庭,并且总是表现为一种残缺的夫妻关系。这些夫妻都自认为彼此相爱,却无法维持和谐的婚姻,他们或为名利相爱却不能相守,或因生活庸碌而渐生不满,或疏于精神交流而冷战不断。人与家庭的疏离伴随而来的是家庭观念的破裂,家庭不复成为个人的归属。当人主动或被动地从病态的家庭关系中疏离,指向的并非自由,而转变成了人与自我的疏离。置身金钱社会,物欲对本真之人的压抑则成为了个体难以逃脱的圈套。
(一)人与家庭的疏离。第一篇故事《伤心情歌手》中的托尼与琳迪因金钱与美貌结合,最后又因名利而分开。金钱成为衡量家庭关系的唯一指标。基于物质条件前提下缔结的婚姻为夫妻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当二人的婚姻走过27个年头,托尼的事业却走向衰落。虽然两人都深爱彼此,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解除了婚姻关系。深爱之下,托尼为重返歌坛而另寻年轻妻子,琳迪趁年华还未老去及时抽身。爱情敌不过金钱,成为了“金钱至上”这一信念的牺牲品。现代社会名利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破坏、对夫妻亲密关系的瓦解,迫使着人们走向疏离。看似是爱而不能相守,其实是在名利场和现代社会的“便利”中,“爱”具有了可消费性和随意性,因而家庭中的婚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都遭到破坏。在《小夜曲》中,孩子也处于缺席状态。石黑一雄并未详述小说中的夫妻为何没有生育子女,也未将重心放在家庭伦理的探讨上,而是将人物放入家庭关系中,意在表明或许正是对于家庭责任的淡漠,他们甚至未曾考虑养育后代,人与曾经最为亲密的家人之间的联系也渐渐微弱。现代社会中,金钱取代了情感,成为了维持家庭关系的条件,这种条件的不稳定极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破裂;而当人们不再以真挚的爱作为缔结家庭的纽带,家也就不再成为可以慰藉的归属地,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使得人们成为孤独城市中彼此陌生的无根游魂,疏离成为现代人难以克服的力量。
(二)人与自我的疏离。现代社会中对人的异化,不仅表现为现代人与家庭的隔膜,还表现在金钱观念侵轧人的精神世界,个体的艺术追求为名利所困,人与自我本身发生疏离。
《不论下雨或晴天》中,雷德蒙在老友查理与埃米莉家中上演了一场人扮狗的闹剧,他将自己当成一只正在搞破坏的狗,撕烂看起来像艺术展览的查理家的客厅。在扮狗过程中,雷德蒙发现以人的视角无法做出狗能做出的事,“突然,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完全没有从亨德里克斯的角度来想问题。现在我明白了事情的关键是把自己当作亨德里克斯。”[3](P80)于是,雷德蒙“四脚着地,低下头,把牙齿伸进一本杂志……轻轻地咀嚼、下巴不停地轻盈摆动,效果最好:这样书页就会变得乱糟糟、皱巴巴”[3](P81),模仿狗的行为将埃米莉的客厅弄乱。
雷蒙德在这场闹剧中既是人,也是狗,可以说他对自我的认同发生了分裂,回到了如拉康所说的处于“镜像阶段”的幼儿,对自己身体的同一性和整体性还未完成确认,雷蒙德如此怪异的举动正是与自我产生疏离的隐形投射。埃米莉的婚姻之所以摇摇欲坠,是因为众多欲望的推手在摇晃这脆弱的基石——爱情,唯有丈夫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的婚姻才会更稳固。因此雷蒙德作为失败的象征,他的落魄生活就成为了巩固好友婚姻的工具。当雷德蒙成为一条狗时,他便转变为这个虚荣世界的破坏者,决意与被当作弱者的自我割裂,成为一个不甘臣服于虚假物质世界的人。巧合地是,小说中雷德蒙扮演的这只狗名叫“亨德里克斯”,与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同名,雷德蒙在音乐的身上获得了暂时性的破坏力量,自我得以彰显。但这股力量并未能持续,面对埃米莉,雷蒙德再次恢复成为失败者,向她假装承认自己忘记了共同热爱的爵士乐。在现实世界中,他与真实的自我无法得到统一,在金钱准则的衡量下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内部世界疏远。正如他对埃米莉所说的:“人很难知道哪里可以安身,何以安身。”[5](P90)
如果说雷蒙德将自己当成一条狗是其与自我疏离的隐性表征,那么《小夜曲》中的史蒂夫,则是在现实社会中逐渐被金钱和名利所蚕食的音乐梦想家。史蒂夫是一个打零工的萨克斯手,他梦想自己能成为爵士乐家。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才华,却一直无法成名。周围的人告诉他,正是他失败者的丑阻碍了他的成功。史蒂夫本人对此不以为意,直至妻子出轨,他才开始接受现实。如果整容能够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音乐,也未尝不可。于是他接受了妻子的出轨补偿——免费整容。
修养阶段史蒂夫与女明星迪琳·加德纳偶然相识,琳迪·加德纳以自身的经历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意识到想要在这个市场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顺应市场的规则。他的音乐梦想已在悄无声息中置换成了获得名利场认可的通行证。尤其是当他得知曾经技不如人的杰克·马弗尔成了年度最佳爵士乐手时,内心的愤懑更是喷涌而出。琳迪却给出了一套现代社会的奋斗法则,缺乏才能的人们为获取成功而作出的“努力”应该受到认可。这套准则为史蒂夫所接受,他不再满足于自己内心的音乐追求,而在名流堆中兜售自己的才华。此时同样是带着绷带面具的琳迪,仿佛就是下一个史蒂夫,他在现实的镜子中找到了如同琳迪一般的自我。
石黑一雄在《小夜曲》中谱写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个体不再将家庭作为自己归属的港湾,细细品味可以发现,个中人物都处于焦灼、疏离、无所归依的状态,这也昭示了人们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曾经支撑人们的爱与梦想,如今在物欲的压抑下所剩无几。但石黑一雄笔下的世界并非是毫无希望的荒原,而是通过人与他人之间的松散关系透露出消弭疏离的微光。
三、克服疏离的可能
石黑一雄在每一篇故事中,都使陌生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但又迅速结束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这种“自发而短暂的友谊是爱德华·霍尔描绘的‘低语境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拥有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倾向于保持一种广泛、松散而短暂的联系”[4]。这或许解释了人与人在冷漠世界中的生疏与隔阂,但笔者认为在与他者建立短暂、易逝的关系之余,石黑一雄还传达了人们在这一关系中所投射的爱与真诚,看似冷漠无望,实则预示着归属的可能性,而人们在与亲人或是伴侣的亲密关系中,将周围的其他人都视作与自我相对立的客体,这正如马丁·布伯所认为的:“与我产生关联的一切在者都沦为了我经验、利用的对象,是我满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5](P5)也即“我—它”关联,而在石黑一雄的笔下,人们借助与陌生人的短暂对话,回忆梳理他们过往的纯粹情感,思考如今既无法融合又渴望理解的隔阂,最终暗指了小说中人物“我—你”关系的走向。
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演讲,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写作,试图和另一个人建立联结,而那个人也在另一个安静的——也许不那么安静的房间里阅读。小说可以娱乐,有时也可以传授观点或是主张观点。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小说可以传递感受;在于它们诉诸的是我们作为人类所共享的东西——超越国界与阻隔的东西。”[6]从石黑一雄对小说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十分看重小说中感受的传递,它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性别,跨越种族,跨越历史,这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脉络。石黑一雄看重具有共同性的感受,另一个重要影响便在于,人与人将会因为感觉的相通相连而走到一起,发生对话沟通,或许在短暂的联系之中,人们也能重新唤起对过往的人与事的热爱,无论是多么冰冷的隔膜与疏离,也会出现些许打破的可能。
在《小夜曲》中,每一篇都以人与人之间缔结一段友谊而开始,以因某一方的离开而结束,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认为:“当代社会的独特特点不仅是它的大小和数目,也是它不断增长的互相影响——既是身体上的(通过旅行、更大的工作单位和更高的居住密度),也是心理上的(通过大众媒体)——这种互相影响将我们跟那么多其他人直接地、象征地联系起来。”[7](P95)《小夜曲》中人物即是生活在这样的当代社会,他们通过一段旅行结识,对陌生人诉说自己曾未向亲密的家人或伴侣的内心。虽然互相陌生的人们彼此影响着对方,但这种关系带来的影响却是短暂而脆弱的,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如同《大提琴手》中的无名者“我”所说:“今日的知己明日就变成失去联络的陌路人,分散在欧洲各地,在你永远不会去的广场和咖啡厅里演奏着《教父》或者《秋叶》。”[3](P204)石黑一雄在《小夜曲》中描写这种充满流动和异质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人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无法与他人形成稳固的亲密关系,这也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但仔细考察五篇故事,正是因为人际关系的流动与不定,使得“人类共享的感受”得以流露,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可以察觉个体内心的爱和梦想从未缺失,总是在疏离、隔膜的间隙中若隐若现。
《伤心情歌手》中托尼在与“我”的倾诉中,表现出对妻子琳迪深深的爱意,而琳迪在听到丈夫给他唱的具有特殊意味的歌曲后,失声痛哭,虽然他们甘愿屈服于对名利的追逐,但仍然爱着对方。借由与陌生人“我”的对话,托尼仍然在回味与琳迪的美好过往,“离开餐桌时轻轻碰一下我的肩膀。在房间那一头莫名其妙地微微一笑,没什么好笑的事,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在乐什么。”[3](P33)时隔20年,托尼对这一场景仍历历在目,即便他们都在金钱的异化之下不再忠诚于唯一的爱,但这一细小真实却即将走向终结的爱在石黑的笔下依旧动人。《小夜曲》中即便史蒂夫在琳迪的建议之下,已经决意向前看,但令人无法释怀的是,当初史蒂夫是怀揣着对海伦可能回心转意的幻想而答应整容,可以想见,如今令他无法正视的容貌是他怀念妻子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通话中海伦快要挂机时,史蒂夫对她说了“我爱你”,显然史蒂夫还未反应过来海伦已是他人妻的事实,如若史蒂夫对海伦恨之入骨,便不会再对她说出哪怕是例行公事般的“我爱你”。无论是夫妻之间曾经的爱意,还是《莫尔文山》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作者都给予了温情的笔触,姐姐玛吉对“我”事业的了解甚少,甚至不如那对陌生的瑞士夫妻,“我”宁愿去山上写歌,也不愿意与姐姐姐夫待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在“我”的内心依然有所期待,“我在她家待了这么久,她从来没有像蒂洛和索尼娅那样要我唱首歌给她听。这个要求对自己的姐姐来说不过分,而且我突然想到,她十几岁的时候也热衷于音乐。”[3](P125)看似疏离的关系中,实则涌动着还未枯涸的爱,人们还是保有着对稳定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渴求。石黑一雄在描画人物的情感时,即便现实已很残酷,人与人之间淡漠疏离,但他仍不愿忽视人们曾经在记忆中储藏的爱,当他们与他人诉说起来,人们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它”之经验世界,无论是自己还是亲密之人,均被异化成可利用的对象,然而正是通过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未枯竭,“爱以其作用弥漫于整个世界。在伫立于爱且从爱向外观照的人之眼目中,他人不再被奔波操劳所缠绕”。[5](P18)因而这关于爱的回忆和感受或许可以成为克服疏离的一股细流,帮助人们走向亲密平等,开放信赖的关系。
《小夜曲》中纵然有着人与家庭、人与自我以及人与他人的种种隔膜与疏离,但在他们交互的关系中,可以体味到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以及身处其中孤立、隔阂的精神状态,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对爱与梦想保有期待的个体,在集体走向分散孤立的时代,即便是与他人建立松散不稳的关系,依旧也可看作是消解疏离,建立“我—你”关联的微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