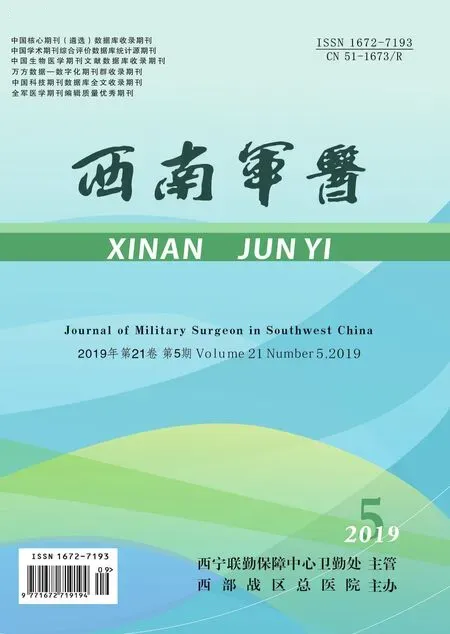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在诊断原发性肝癌中的研究进展
张 雷,祁 峰,龚建平
在世界范围内,肝癌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2016年约有82.9万人死于肝癌,是第7大常见癌症,且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大多数(70%~90%)原发性肝癌是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2]。肝癌的生存率低,5年的年龄标准化相对生存率仅为10.1%[3]。我国HCC患者数量及死亡人数均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2]。我国是乙肝大国,肝细胞癌患者往往有病毒性肝硬化背景,肝功能和肝储备均不理想。而肝细胞癌起病隐匿,早期无明显症状,在我国肝细胞癌患者中有根治机会的仅占发病人口的30%~40%[4]。因此,寻找敏感性及特异性较高的肝细胞癌诊断指标对于提高现有的肝细胞癌治疗手段的疗效和治疗策略的合理性,以及肝细胞癌患者整体预后及生活质量,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本文阐述了目前国内外筛查诊断肝癌的一般方法的局限性和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应用在诊断肝癌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1 目前诊断肝癌的方法的局限性
目前,超声成像(US)、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以及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的测量是诊断和筛查肝细胞肝癌的主要方法[5]。但传统的影像学方法对于小于1cm的肿瘤诊断价值有限,改进的影像学技术虽使超声检查小肝病变成为可能,但往往又高度依赖检查者的经验,在区分肝细胞肝癌和肝脏良性结节方面能力有限,故很难广泛应用于肝癌的早期筛查[6]。将影像学手段结合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多可明确诊断肝癌并提高其早期检出率,自从20世纪80年代FDA批准以来,测定血清AFP浓度一直是协助诊断HCC的常规方法之一。尽管AFP对早期的HCC诊断较为敏感,但对于诊断结果来说,它的敏感度只有66%[7]。80%的小肝癌病例显示血清AFP浓度没有增加,且当肿瘤直径小于3cm时,AFP的敏感性由52%降至25%[8]。此外,约有10%~43%的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15%~51%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以及肝硬化或者其他肝病患者的AFP也有所升高,2010年版美国肝病研究学会指南已不再将AFP作为筛查指标[9-10]。
2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Glypican)在诊断肝脏及胰腺肿瘤中的作用
2.1GPC的结构及生理功能Glypicans(GPC)是一种细胞表面蛋白聚糖核心蛋白,大小约60-70kDa的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它通过其N-末端分泌信号肽,C-末端的糖基磷脂酰肌醇(GPI)锚与细胞膜相连接,由十四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来维持整体的三维结构。有研究表明,GPC在一些生物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已经被认为是几种细胞信号传导通路中的调节因子,它已被证实作为一种调节剂参与Wnt信号传导通路、Hedgehog信号传导通路(Hhs)、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FGFs)信号传导通路以及骨形成蛋白(BMPs)信号传导通路。此外,GPC-3还通过刺激Wnt信号传导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
2.2GPC的分类GPC家族由六个不同的基因(GPC-1~GPC-6)组成,人类编码GPC-1的基因位于2q36染色体,编码GPC-2的基因位于7q22染色体,编码GPC-3和GPC-4的基因彼此相邻位于Xq26染色体,编码GPC-5和GPC-6的基因彼此相邻位于13q32染色体。总的来说,GPC-3和GPC-5具有非常相似的一级结构,具有43%的序列相似性;另一方面,GPC-1、GPC-2、GPC-4和GPC-6具有35%至63%的序列相似性。因此,GPC-3和GPC-5通常被称为一个glypicans亚家族,GPC-1、GPC-2、GPC-4和GPC-6构成另一个亚家族[11]。而在亚家族之间,GPC大约有25%的序列相似性[12]。
2.3GPC在肝脏与胰腺肿瘤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2.3.1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 在2001年,OkabeH等[13]通过由23040个基因组成的cDNA微阵列分析了20个原发性肝癌及其对应的非癌组织表达谱,发现GPC-3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但在正常肝脏中不表达。后续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Yan等[14]对1088例组织进行了GPC-3组化分析,结果显示65%的肝细胞癌组织为GPC-3阳性,而肝内胆管癌、腺癌及肝良性结节均无GPC-3表达。2008年美国肝病研究协会[15]指出“GPC-3阳性表达在小肝细胞癌中的诊断敏感度为77%,特异度为96%。因此,GPC-3可用于肝细胞癌的诊断”。
Jia等[16]对283例肝细胞肝癌患者、445例肝硬化患者、162例正常对照的血清GPC-3表达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肝细胞肝癌及肝硬化患者的血清GPC-3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均显著升高,但两者水平无明显差异。当以0.002ng/ml为界值时,血清GPC-3对肝细胞肝癌诊断敏感度为39.9%、特异度为60.6%。而将血清GPC-3与甲胎蛋白结合诊断时,肝细胞肝癌的诊断敏感性可达72.8%。美国肝病学会[17-19]指出GPC-3、热休克蛋白70及谷氨酰胺合成酶中的两个表达阳性时,肝细胞癌的可能性较大。大量研究也证实了与单一的检测血清学GPC-3水平来诊断肝细胞肝癌相比,联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mRNA结合蛋白3(IMP3)、异常凝血酶原(DCP)、高尔基体蛋白73(GP73)、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热休克蛋白-70(Hsp-70)、谷氨酰胺合成酶(GS)等可以一定程度提高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
2.3.2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1(Glypican-1) 除了GPC-3外,GPC-1也与肿瘤进展密切相关,特别是胰腺癌、胶质瘤和乳腺癌中[20-21]。SoniaA.Melo等人[22]从外泌体方向(外泌体是一种直径50~150nm的细胞外囊泡,它的生物学过程尚不清楚,区分癌症外泌体和正常外泌体的特异性标记物也还未知)入手,对其生物学机制进行研究,发现GPC-1是唯一一个在癌性外泌体上发现的生物学标记物。他们通过对32例乳腺癌、190例胰腺导管腺癌和100例健康捐赠者的组织进行分析,在75%的乳腺癌组织、100%的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发现了GPC-1阳性的外泌体。研究者进一步对6例慢性胰腺炎、56例胰腺导管腺癌和20例健康捐赠者的组织进行分析,发现胰腺导管腺癌中GPC-1阳性外泌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余两组,慢性胰腺炎组织中GPC-1阳性外泌体水平与健康组织相近,将GPC-1阳性外泌体作为评价指标,可以将慢性胰腺炎、正常组织与胰腺导管腺癌区分,并且敏感性、特异性、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然而,这个结论是存在争议的,在最近的关于胰腺癌潜在标志物的综述中,均未提及GPC-1[23-24]。
外泌体与正常肝脏生理功能密切相关,肝脏中多种细胞均可分泌外泌体,或作为外泌体的靶细胞,如肝细胞、胆管上皮细胞、肝星形细胞等。不同的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又有着不同的功能,如来自肝细胞的外泌体能调节肝细胞的增殖,来自肝星形细胞的外泌体可以参与肝纤维化的形成[25]。此外,外泌体与多种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也密切相关。Conigliaro、Huang、He及Qu等学者[26-29]研究发现外泌体含有丰富的RNA和蛋白,可以通过外泌体循环影响周边细胞和组织的生理功能,影响、改变肿瘤微环境,促进或抑制癌细胞增殖、转移和浸润能力。
综上,GPC-1是癌症外泌体的特征性标志物之一,而外泌体又和肝脏正常生理功能、异常病变密切相关。GPC-1是否能用于肝脏疾病,尤其是肝脏恶性肿瘤的筛查、诊断,仍未见相关文献研究和报导。
3 总结与展望
肝细胞肝癌作为一种具有高致死率的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患者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肝细胞肝癌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机制复杂多变,至今临床工作中所应用的筛查、诊断方法均有一定的短板。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家族与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已有大量研究,GPC-3因其在肝细胞肝癌中的高表达的特点,可以作为肝细胞肝癌筛查、诊断的生物学标记物之一。而GPC-1通过外泌体这一新兴的研究热点,与肝脏病变,尤其是肝细胞肝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无疑为肝细胞肝癌的筛查、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