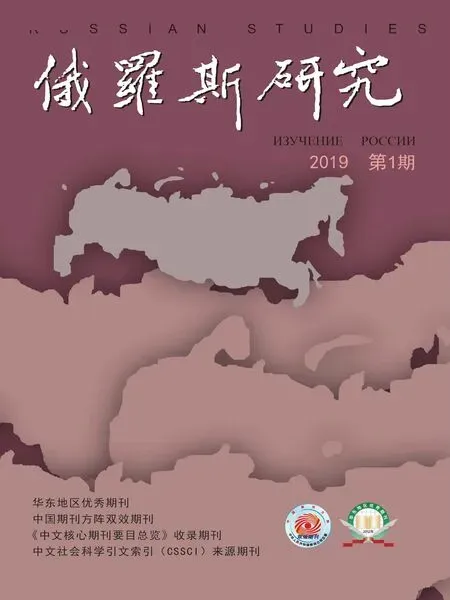金砖国家的扩容:基础、路径与风险*
孙艳晓
金砖国家的扩容:基础、路径与风险*
孙艳晓**
作为金砖国家合作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金砖国家扩容的基础、路径和风险具有特殊性,须予以特别关注。在跨越制度非中性与机制内部矛盾性之间的悖论、偏好上的同质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间的悖论,以及深化合作内涵与扩大合作外延之间的悖论的基础上,以软性扩容的方式推进“金砖+新成员”模式与“金砖+区域”模式,是金砖国家扩容的合理路径。而扩容的风险如影随形,金砖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兼容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弥合性,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包容性将经受考验。
金砖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金砖扩容 金砖机制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创立至今,发展与困境并存,悲观、乐观、怀疑之声不断,其中不乏对其开放性的质疑。一是质疑其没有明确的成员国标准。2010年南非的加入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扩容,基于对成员国标准的不同解读出现了两种相悖的判断。质疑者基于其较小的经济体量、缺乏有助于增加其他成员国战略影响力的前景①,称南非不符合金砖国家成员国标准。而支持者认为,经济体量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南非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作用②,拥有独特的海洋位置优势③,是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气候谈判的“搭桥者”④,能够在南北关系中发挥协调作用⑤,是合理的扩容对象。二是质疑其在扩容问题上的开放性。继南非之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埃及、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亦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加入的意愿,但至今金砖国家尚未再次接纳新成员,其内部未就扩容问题达成一致,也未出台关于扩容的细则。2018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土耳其作为受邀国参会时再次提出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并获得与会国商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扩容问题成为显性议题的趋势。
金砖国家有其独特性,五国综合实力强但凝聚力缺失,发展阶段相近但异质性突出,成员国地域跨度大但缺乏集体认同感,国际上同类组织不多,可供借鉴的扩容经验有限。当前学界对金砖国家扩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视角,探讨土耳其⑥、哈萨克斯坦⑦、印度尼西亚⑧、韩国⑨、墨西哥⑩等单个国家是否应该被纳入金砖国家。而把金砖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关注其自身的融合能力,基于其集体身份这一整体视角去探讨其是否应当扩容、如何扩容、扩容前景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⑪一方面,这与当前学界国际组织研究的工具理性倾向有关。⑫然而,国际组织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将国家行为的动力和效果,机械地移植到国际组织理论框架的做法,已遭到质疑,国际组织有相对独立的行为逻辑与伦理体系。⑬另一方面,金砖国家迟迟未能就扩容问题达成共识也源于扩容本身的政治性,扩容与否以及对象国的选择取决于成员国尤其是核心成员国之间的博弈。事实上,扩容应是组织发展轨迹的自然延伸,扩容的选择应立足于组织自身的发展需要,因而本文立足于将金砖国家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而非仅仅看作是国家间交往的“媒介、工具与平台”,拟从这一整体视角去考察金砖国家扩容的基础、路径与风险。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软性扩容⑭是金砖国家扩容的合理路径。
一、扩容的基础:跨越三个悖论
金砖国家的扩容是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促进国际机制合理化,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兼容性制度重构的有效路径。但扩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成员国间异质性突出、认知差异大和向心力不足等现实瓶颈,又需克服规模困境、利益困境、强者可信与小国搭便车困境等技术难题,更应充分考量扩容可能增加深化难度、而深化可能抑制扩容进度等结构性矛盾。
(一)制度非中性与机制内部矛盾性之间的悖论
国际制度通常形成于国家之间集体行动的高级阶段。然而,国际制度与生俱来的非中性特征又往往成为合作延续的障碍。即便在公正的制度安排下,受限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条件与能力的现实差异,成员国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也难以均等。“制度非中性”⑮的概念阐释了这一现象。受建制成本、资源分配、合作策略等因素影响,制度非中性往往与国际制度相伴而生,并随着累积效应不断加深,导致既有制度内成员分化为坚守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力主改革的期待利益集团,两个集团的博弈与平衡推动国际制度的变迁。当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拥有的制度性权力,相较于其实力与贡献严重失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便是成员国为改革制度非中性导致的权力失衡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新兴国家发起的制度变迁有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和建立于己有利的新制度两个路径。⑯作为一种新兴力量,金砖国家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更多的空间,⑰但是其难以与拥有话语优势的发达国家(集团)相抗衡,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而通过相互之间的深入合作,一方面在既有国际制度中谋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一方面建立新的制度以平衡现有的全球非中性制度架构。这种努力或许是最为现实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合作是五国回应制度非中性挑战的集体行动方案之一,改变制度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处境还需要联合足够多的发展中经济体。然而,金砖机制内部矛盾性的存在制约了集体行动,与制度非中性下集体行动的动力形成悖论。
一是成员间异质性强,互信度低。尽管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加强,但它们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这些差异给寻找合作基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并经常限制金砖国家在许多问题上的合作。比如,在大宗商品的供需方面,金砖国家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但在定价问题上却存在尖锐的矛盾。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俄罗斯、南非和巴西造成不利影响,对印度却是有益的,因为印度是一个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国。⑱尽管加强对大宗商品的市场监管以及促进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对话是金砖国家的共识,但是金砖国家目前仅愿意就粮食安全问题开展紧密合作,而对于石油、铁矿石等利益冲突较多的大宗商品,并未形成正式的政策。⑲同时,五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共识相对较少,尤其体现为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对金砖合作信任不足。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战略定位意味着其不愿甘当“配角”,其对中国在金砖机制中的作用,表现出既依靠又担忧的矛盾心态;⑳印度国内存在联美制华的论调以及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质疑,它认为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主导性地位是对其战略自主的外交空间的威胁;巴西传统上与美国关系更为密切且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往往追随美国;而南非在每次参加金砖会议之后都会主动在南非召开针对西方外交人士的通气会。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金砖国家深度合作的障碍。
二是议题领域向心力不足。金砖国家在改革议程中要求拥有更多话语共识,但在具体议程中的离心力又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在G20内部,金砖五国缺乏凝聚力,并不总是在具体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只能在大的范围内达成一致,进而阻碍了金砖国家积极制定议程。[21]相较于发展议题,五国在其他议题上分歧较大。例如,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6月9日对伊朗核项目实施制裁的1929号决议,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12个理事国投了赞成票,巴西与土耳其投了反对票。[22]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分属“伞形国家”和“基础四国”阵营。新疆域治理如网络空间问题上,尽管金砖国家成员都同意建立全球治理架构,但在建构方式上存在分歧,中俄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多边谈判,而其他国家支持构建一个政府、企业与社会共治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Fluid Multilateralism),即各国为了某些共同利益团结在一起,而不要求意见完全一致。[23]此外,尽管历次金砖国家峰会宣言都会提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所有成员国也都认为联合国需要全面改革,但由于中俄两国在是否支持印度、巴西、南非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安理会改革并未成为金砖峰会的真正议题,[24]金砖各国如何协调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目前尚不明朗。[25]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与推进,是否必然促进成员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一致立场,尚有待观察。从数据统计来看,金砖国家2006-2014年间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性,并未受到2006年开启合作、2011年后强化互动的显著影响。[26]事实上,金砖国家在诸多议题中仍表现出作为个体的存在,而并没有展现出作为一个集团的统一立场。[27]
三是主体认知差异大。首先,各国对国际秩序的改革设想不同。尽管成员国在现存国际秩序需要改革或完善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看待金砖合作与当前国际秩序的关系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28]这种差异形成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另起炉灶”催生新的国际秩序两个基本进路。[29]俄罗斯作为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文化上自认是西方的,政治上不被西方接纳而与西方陷入对抗;印度从现存国际秩序中受益较多,同时又是改革现存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从积极融入开始,以改革的推动者而非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自我定位;巴西与西方在政治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它却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谋求在全球事务上积极作为;南非在对待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上与印度和巴西有许多类似的地方。[30]
其次,各国对金砖合作的定位不同。[31]最大的分歧在于,俄罗斯将金砖国家视为与西方博弈的地缘政治工具,而其他四国则尽力避免金砖合作政治化。[32]印度与巴西高层多次表示,如果金砖变成与西方冲突的工具,两国宁愿退出。尽管俄罗斯在意识到其他成员国无意与西方闹翻时,放弃了借助金砖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安全联盟的想法,但将金砖打造为对抗西方的“政治筹码”这一出发点不曾改变。[33]

表1 金砖成员国的认知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三,各国对“南南合作”的认知不同。[34]中国、印度、南非认同“南南合作”,但在金砖机制内,印度更多的是从问题领域而不是从南南合作视角看待问题的。俄罗斯认为“南南合作”的定位会限制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独立政策的能力,南北之间的桥梁或中介的地位是很难接受的。[35]巴西由于其西方文化的属性,认为“南南合作”的定位并无实际意义,对以南南合作为主要方向的金砖机制不抱太大的希望。
(二)偏好上的同质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间的悖论
任何有效的集体行动都基于成员达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往往体现在一个强有力的愿景宣言。[36]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金砖国家处于传统制度非中性的弱势,在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上有着共同的需求,偏好上的同质性促使金砖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带来在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同时,扩容也考验着合作机制自身的融合能力。除去对整体偏好同质性的冲击,单从技术层面考察合作机制的设计,扩容增加了合作从理想兑现为现实的不确定性。
一是规模困境,即成员国数目及成员国构成对集体行动效果的影响。从成员国数目来看,组织规模的扩大深刻影响着每个成员国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金砖五国合作的形成,反映了相似国际地位的五个国家避免较多成员的集体行动困境,而其本身就建立在需克服五国之间异质性远大于共同性这一基础之上。更多的参与者意味着无法避免的集体行动难题,对提供公共产品责任的相互推诿,利益分享与成本分担之间的不公平将增加。从成员国构成来看,集团越大,寻找共同议题与组织共同行动就越难,建立一个集团协议或组织的难度就越大,由此带来行为体数目与合作机制的代表性之间的弥合困境。南非的经济体量被质疑不符合金砖国家的身份,巴西一个远离亚洲的国家被质疑是否能促进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俄罗斯处在东西之间的特殊身份被质疑金砖国家并非“南南合作”,印度的左右摇摆被认为是金砖机制中的“最薄弱环节”;而新进一些成员之后是否会冲淡机制的代表性,还需要观察。据此,成员规模在机制建设初级阶段要尽可能小,而后逐步吸纳相关国家加入。
二是利益困境。按照曼瑟尔·奥尔森(Mansor Olson)的理论,金砖国家属于相容性利益集团,但并不意味着成员间不存在排他利益。例如,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并非所有的金砖国家均能从中获得显著的收益,部分国家投票权份额上升,但另一部分国家投票权份额却在下降。又如,在海洋合作领域,五国同为沿海国家,都希望提升新兴国家在海洋治理中的话语权,也拥有潜在优势和合作空间,但现实的利益分歧尤其是中俄印三国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现实矛盾,[37]以及三国对于亚太地区海洋权力秩序的认知及立场差异[38],迟滞了金砖国家在海洋治理这一重要议题上的合作步伐。事实上,尽管金砖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但经济上的竞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际地位的差异,都促使成员国在合作中倾向于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只有在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实现平衡,才能促进集体行动的成效。那么,扩容对弥合成员之间相容利益与排他利益的影响如何?有观点认为,扩容可以弥合成员国现有的分歧,增加共同利益。事实上,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源很多时候不在于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解决,而在于国际制度安排不够合理和科学。通过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对利益进行重塑,即通过改变各国在集体行动中所面临的成本—收益结构,使其选择供给的收益高于不供给时的收益,可以促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实现。
三是“强者可信”与“小国搭便车”的弥合困境。一方面,“强者可信困境”,即强国如何让自己的行为承诺在较弱的国家看来是可信的,或者说较弱一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对强国形成制约,使其承诺可信。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拥有最强经济实力,其他成员担心金砖机制由中国主导,变成“中国+BRIS”合作,成为中国的国际政策工具,因而追求绝对平等化的金砖内部治理规则。[39]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为例,在银行的选址和行长人选问题上,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博弈,最终金砖五国享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和运营权,五国均摊500亿美元的初始认缴资金,总部坐落在上海,首任行长是印度人,首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非洲区域中心设在南非。显然,坚持合作平等是金砖合作的显著特点。[40]然而,追求权力与地位的绝对平等不排除合作会陷入非自由性困境,导致合作的排他性与冲突性,使众多中小国家被排斥在合作门槛之外;而“势力均衡”的过分考量也给金砖银行埋下因缺乏主导权威而效率低下的隐患。另一方面,一个小成员一旦免费地从最大的成员那里获取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就已经比它自己能购买的要多了,由此催生“搭便车”现象。即便在抱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中,也存在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41]小国更关注对其自身有利的合作议程,对金砖机制建设所投注的精力也将取决于金砖合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其国内发展受益这一核心条件。2017年,受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影响,巴西参与金砖机制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为金砖机制提供新鲜想法的能力减弱。南非更加关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进度及“非洲议程”是否能够成为金砖机制的常设议程,对机制的发展蓝图,无力也无心有更多投入。由于没有新成员加入,中国在金砖国家中体量远超其他几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他金砖国家在经济合作中对中国的依赖,无疑会加重中国的负担。
(三)深化合作内涵与扩大合作外延的悖论
促进金砖机制集体结构的优化是使合作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是对内推进机制化建设,二是对外进行扩容。两者的抉择根植于各成员国对金砖国家合作的不同定位与期许。受制于现实利益与未来话语权考量,基础性的问题聚焦于三点:第一,金砖机制将从松散的议事组织转向紧密的实体组织,还是长时期作为一个成员间松散议事的便利渠道?第二,金砖合作将把重心放在扩大与深化成员国之间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还是有意转向成为经济与政治安全议题并行并重的综合合作平台?第三,扩大与深化的取舍是任何国际组织都要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有待达成共识的是应当打造一个更深入合作的金砖还是更大规模的金砖?
一是关于合作性质的界定。金砖国家正由非正式机制发展成为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正式约束机制”的嵌套机制[42]。非正式对话机制占主体地位,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为围绕其内核的外围机制。非正式对话机制灵活,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务实,并随着提高合作效率的需求而深化,这也正是符合金砖国家发展趋势的理想化的机制化路径。然而现实中各国对合作性质的定位仍存在分歧。俄罗斯立足于将金砖国家建成为一个紧密合作的正式团体,通过金融合作实体化、具体领域合作机制化,使金砖国家朝一个国际实体组织方向转化。[43]而其他四国并不主张将金砖国家建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认为应加强常规性机制建设,重点是推进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为代表的金融合作。
二是关于发展方向的图景。尽管金砖五国有意合力促进国际秩序变革,但对如何实现这一过程却没有更多共识。[44]金砖合作从建立之初的经济领域拓展为经济、政治“双轨并进”,厦门峰会上又提出向经济、政治、人文“三轮驱动”拓展。[45]但五国对机制的发展前景仍缺乏共识,各成员国在价值观、经济与政治结构、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显著分歧阻碍了金砖达成一个广泛共享的积极议程。俄罗斯重政治协调,中国、印度、巴西重经济合作,南非更重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努力淡化政治集团的形象,印度强调金砖合作的非战略色彩。定位无共识则扩容无标准,各成员国在选择扩容对象时自定标准、各有倾向,影响扩容共识达成。虽然安全议题在历次宣言中占据越来越大的篇幅,但事实上,金砖国家在发展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仍远大于政治、安全议题,经济协调往往先于政治协调,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见证经济集团形成的初步迹象”。[46]
三是关于深化与扩大的分歧。扩大与深化的取舍是任何国际组织都要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无论是通过接纳新的成员国形成规模优势,还是通过增设议题拓展合作领域,通过机制化加深合作程度,都是金砖机制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当前阶段有待于达成共识的是,应当打造一个更深入合作的金砖还是更大规模的金砖。无疑,扩大可以强化规模优势,扩大经济合作空间,增强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扩大政治影响,使新兴经济体作为群体的价值理念得到推广。但探求金砖国家的扩容之道,不能仅关注扩大可能带来的诸多益处,更要充分考量扩大可能增加深化难度、深化可能抑制扩大进度,从金砖国家发展的大局统筹二者关系。
“深化”可能抑制“扩大”进度,而“扩大”可能增加“深化”难度。深化以促进成员国在更多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为使命,深化程度越深,就意味着扩大门槛越高。金砖国家处于机制化进程中,以对话为主的“非正式+正式”机制本身不利于共识的达成。深化无定向则扩容无标准。深化方向的不确定性,使成员国标准更加模糊,而扩大使成员国构成更加多元,机制的“纯粹性”遭到削弱,协调的难度增加,一味地扩大可能损害金砖国家发展的大局。举例来说,如果接纳土耳其为新成员,土耳其外交政策偏好与金砖国家相近,联合国投票行为灵活,金砖国家可能利用土耳其的穿梭外交能力建构外交政策协调网络,联通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47]。然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其现代化历史轨迹与任何一个金砖国家都不一样,[48]在非殖民化和种族歧视问题上与金砖国家立场一致,但是在人权、自决、解除武装、使用雇佣军等问题上与西方一致,[49]西方身份和投票取向的双重性增加了其与金砖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土耳其究竟是会成为金砖国家与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梁,还是成为东西矛盾的掣肘,尚未可知。
欧盟经验值得重视。在欧共体/欧盟发展过程中,内部一直存在着“扩大”与“深化”的争论与抉择,曾经经历了同步走、深化为主、协调为主的不同阶段,每一轮扩大都给欧盟的一体化带来新的课题。2004-2014年间的十年是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2004年欧盟的爆炸式扩大,2005年法国、荷兰公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2008年爱尔兰公投拒绝批准《里斯本条约》,事件频发,争论愈烈,扩大和深化由可以融合的路径变成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选择。直到2008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才似乎有了结论,深化成为欧盟主要的政策选择,欧盟发展呈现深化为先、延缓扩大的趋势。[50]至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至今未再次扩容。欧盟的经验表明,“保持列车运行正常、安全和舒适比快速更重要”[51],深化与扩大的选择须结合自身状况和发展阶段。基于以上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金砖机制应以深化为主、扩大为辅,从严渐进扩大。
二、扩容的进程:推进两个模式
鉴于金砖国家合作仍处于初始阶段,扩容需面临三重悖论,同时成员国立场各异,因此,金砖扩容将是一个缓慢的、也须十分谨慎的过程。推进金砖国家的软性扩容,既是扩大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应对扩容难题的折中方案和曲线应对办法。一方面,渐进式推进“金砖+新成员”模式,但这不应是“金砖+”的全部和唯一方式,而是最高级形态;另一方面,深层次推进“金砖+区域”模式,这是以扩容之外的方式扩大合作辐射圈的第二层面,也是在制度非中性前提下,应对治理非中性、提高金砖国家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一)成员国的立场分析
扩容问题不仅仅是学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益分歧和定位差异导致成员国在扩容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对候选国的不同偏好。
俄罗斯针对扩容问题有两种声音。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金砖国家目前没有计划扩容。[52]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С.В. Лавров)也曾指出,就金砖国家可能的扩容而言,这个问题需要在这个组织中达成共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计划进一步扩大的想法。[53]俄罗斯总统府金砖委员会主任托洛拉亚(Г.Д. Толорая)也曾指出,“当前立即直接扩大成员国的可能性不大,要在五个国家间达成一致意见本就是很难的事情,更何况六个?”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扩容呼声,俄罗斯的态度有所松动,不排除可以接收一些地区大国,在机制内设立“对话国”与“伙伴国”的位置,除增加金砖的国际影响力外,还可以积累这些国家参与金砖事务的经验,待时机成熟可发展为正式成员国。托洛拉亚认为,印度尼西亚或者土耳其有可能在下一个五年内成为金砖准成员国。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尼日利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不成熟,对金砖成员这一名称而言“太年轻”,可设为观察员国。由此可见,俄罗斯并非完全排斥扩容,而是把机制化作为优先事项,扩容与否关键取决于对象国是否符合俄罗斯战略诉求。在扩容对象的选择上,俄罗斯更多出于地缘政治和对美划线的角度考虑,俄罗斯致力于塑造一个战略性的“非西方世界”集团。托洛拉亚认为,“未来将伊斯兰文明的代表纳入金砖机制完全合理的,如印尼或土耳其”,“整个伊斯兰国家都不满美国的霸权和单极世界”,金砖国家可与伊斯兰世界合作。而墨西哥因其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身份,韩国由于其经合组织成员国身份,均难以获得俄罗斯支持,土耳其虽同为经合组织成员但符合俄罗斯对美划线的外交逻辑。同时,部分俄罗斯专家提出,金砖暂不扩容,不意味着金砖框架下的其他机制不扩容。例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实体,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吸收新成员,实现变相扩容,如吸收阿根廷等。俄副财长也提议希腊加入金砖开发银行,认为这种做法既可以扩大经济合作范围,又可提升金砖的政治分量。[54]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扩容持开放态度。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金砖国家奉行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针对阿根廷有意加入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关于金砖国家扩员问题,需要各成员国协商一致决定。金砖国家合作是开放包容的,中方支持金砖国家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55]。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扩容问题上持开放立场,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员国间的分歧阻碍了扩容的进程。[56]对中国而言,五国抱团合作可以实现经济互补,为共同管理国际事务扮演积极角色,同时可以为解决中俄、中印之间的不和谐声音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国内学界也普遍支持扩容,[57]庞中英认为,扩容是必要的和不能拖延的。[58]王磊则提出了成员国需满足的五项标准:发展中国家、大国、可持续性、底线思维、代表性。[59]在扩容对象的选择上,基于“南南合作”的定位,墨西哥、韩国难以跻身优先考虑之列。鉴于金砖扩容将是一个缓慢的、审慎的过程,2017年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了“金砖+”[60]的拓展模式,扩大金砖国家的“朋友圈”[61],以此实现曲线扩容。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江时学指出,“金砖+”可能成为金砖国家未来多年的核心发展方向之一。[62]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认为,与简单的扩容相比,“金砖+”模式将是一种更好的思路。[63]中国的这一创新得到了其他四国的认可。尤其是俄罗斯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金砖国家+”不失为“重启”经济全球化的不错路径,认为“金砖+”是理想的“扩容”模式。2017年7月19日,瓦尔代国际论坛俱乐部专门召开了“金砖+”讨论会,瓦尔代国际论坛俱乐部基金项目主任利索沃里克(Я.Д. Лисоволик)连续撰文,高度评价该倡议,认为其拓展了金砖与第三方合作空间,未来可进一步发展成为“金砖++”。他认为,扩容会淡化金砖的色彩,而“金砖+”则在保留核心的同时,拓展了金砖的合作空间,“金砖+”可轻松实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重超过15%的目标,提升了其影响力。[64]
印度将金砖国家合作定位为“跨地区经济金融合作组织”而非反西方的战略集团,对金融合作领域有较高期许,希望在金砖国家银行和应急储备问题上加强合作。对印度而言,“印巴南”合作更能强化其“民主气质”,还能在金砖机制内打造一个“并非由中国主导的集团”的身份认同,而“四国集团”也更能助力其入常诉求,[65]金砖国家在其整体外交中位阶不高。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教授辛格(Swaran Singh)对金砖四国的扩容持谨慎态度,称这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阻碍达成共识。在扩容对象的选择上,出于对中国在金砖机制内操控能力的担忧,对于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抱谨慎态度。印度对扩容问题的主导有限。
巴西外交部长曾表示,巴西不希望看到金砖国家的新兴国家在目前扩大,但希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66]巴西的态度经历了变化,曾经在南非加入的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杨首国认为,巴西对“金砖”的态度有些微妙变化,对“金砖”扩容不太积极。原因在于:第一,巴西认为,设立秘书处,机制会僵化,财政负担会增加。第二,早期南非加入的时候巴西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时候巴西各方面实力处于上升态势。近年来巴西经济衰退,外交收缩,所以对金砖扩容不是很积极。第三,在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大国情结很深,巴西肯定不希望墨西哥加入,也不希望阿根廷加入,所以说在扩容问题上是不太积极的。[67]在扩容对象上,因为巴西在地区主导权上受挫,因此对于墨西哥与阿根廷,持保守立场。
金砖国家合作在南非的整体外交中位阶较高,南非希望充当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桥梁,在金砖发展方向上优先考虑深化合作,尤其希望“非洲议题”成为金砖讨论的重点。鉴于目前非洲在金砖国家中仅有一个成员,作为非洲大国,尼日利亚GDP已经连续六年超越南非,将其扩进来可以增加非洲的分量,但同时又会稀释南非的区域代表性,因此南非的态度是模糊的。在南北问题上,自视为南北关系的协调者,在选择扩容对象上没有西方与非西方、南与北的芥蒂,但南非整体影响较小,对扩容问题的主导有限。
扩容的实现有赖于主导国的推进。相较而言,印度尚不足以成为金砖的主导力量,巴西并不愿意坐第一把交椅,南非主观意愿和影响力皆有限度。俄罗斯希望做金砖机制的主导国,而中国由于经济体量和影响力,是事实上的主导国,若中俄能够达成共识,金砖扩容进程将有机会尽快推进。但两国最大的分歧在于,在是否扩容的问题上,俄罗斯专注机制化而中国希望扩大朋友圈;在扩容对象上,俄罗斯希望政治合作而中国更希望经济合作;中国希望增加南南代表性而俄罗斯对美划线,因此一方面扩容迟迟未实现,另一方面对扩容对象的倾向性不同,背后反映出中国希望抱团提升在国际组织中发言权和投票权的发展思路与俄罗斯打造政治团体以防范美欧打压的外交定位的差异。但共识在于:第一,俄罗斯并不反对“合适”的地区大国加入,因此扩容并非不可实现;第二,由中国提出的“金砖+”模式得到俄罗斯的肯定。
(二)渐进式推进“金砖+新成员”模式
由于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成员国标准,缺乏分析工具来识别和比较潜在的成员国,因此更适宜通过一种比较方法来分析:潜在成员国是否与金砖国家具有相同的主要特征?金砖国家的共性,即评判潜在的未来成员国身份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1)改革国际秩序的共识,即促使目前的国际秩序转变成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秩序。主要考察相关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协调能力、话语权及在重要议题上的态度,不能只关注经济上够格的国家,要吸纳认同金砖国际秩序理念的国家。[68](2)物质性指标,即政治稳定、在地理、经济等方面有较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面积、GDP、经济增速、地区代表性等。(3)考虑金砖国家的融合能力,即增进群体优势与弥合分歧的能力。前者关注扩容能否增进更多共同利益,后者关注金砖机制弥合内部分歧并回应外部分歧的能力,即是否有能力消解扩容带来的副作用。三个指标中,物质性指标[69]相对较易衡量,改革国际秩序的共识需考察潜在成员国在议题领域的参与度及投票倾向[70],而融合能力既需考察候选国的外交战略,又需在互动实践中检验。因此,可设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待时机成熟再发展为正式成员国。
据此,扩容对象可考虑G20成员国中的新兴国家及G20之外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国家。金砖五国代表的区域涵盖东亚、欧亚、南亚、南部非洲以及南美,目前在中北美地区、中亚、东南亚、阿拉伯世界等地区还没有代表,未来可考虑在金砖五国所在区域增加1-2个代表,重点吸纳其他区域有代表性的国家加入。呼声较高且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加入意愿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埃及、尼日利亚等。以物质指标结合现有成员国立场来看,阿根廷、沙特、哈萨克斯坦、埃及、尼日利亚发展为正式成员国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韩国的经合组织成员国身份、人口规模限制了其可能性;墨西哥的经合组织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身份,以及专注于北美大陆及美国因素限制了它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土耳其的北约、经合组织成员国身份,以及在东西方外交中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并非是最佳候选国。

表2 金砖国家备选成员国物质性指标
数据来源:1、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除特殊注明外,均为2016年数据;2、世界GDP年增速率2014-2016年分别是2.47%、2.47%、2.44%。
相较而言,印度尼西亚是最合适的候选国。首先,印度尼西亚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作为G20中唯一的东南亚成员,印度尼西亚把G20看作是发挥全球性作用的一个主要平台,在寻求国际秩序的改革方面与金砖国家有共同诉求,在提升在全球金融、贸易、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上与金砖国家有一致立场。[71]其次,硬实力方面,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是东盟的核心国家和对外“代言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扼守连接沟通东西方咽喉的战略通道马六甲海峡,这是印尼最重要的战略资产。金砖国家目前尚没有这一地区的代表。第三,2013年“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的成立表明,中等强国开始寻求合力维护自身利益,已发展成重要的第三极力量。作为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成员,如果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可以起到桥梁作用,连接金砖国家与中等强国合作体在G20以及其他领域中的话语权合作。有西方智库曾提议在G7中纳入两个中等强国,组成“G7+韩国+澳大利亚+欧盟”的合作模式,以冲抵金砖国家在G20中的话语权,[72]面对话语权竞争,金砖国家可能寻求与中等强国的联合。除G7和金砖五国外,其他G20成员多为中等强国。此外,印尼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通过全方位外交发展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推行独立友好的外交路线,信奉“零敌人”政策,还利用自身的独特身份,试图担当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桥梁。金砖概念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认为,印尼是N11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够得上金砖成员国资格的国家。[73]
(三)深层次推进“金砖+区域”模式
曼瑟尔·奥尔森指出,“代表的利益愈广泛,该组织或集团会更倾向于增加社会总收益。”[74]金砖国家区域色彩浓重,成员均为所在区域或次区域的主要经济体。在这些区域的一体化安排中,金砖国家的合作伙伴都可能形成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模式,使“金砖+区域”合作成为可能。之所以要深层次推进“金砖+区域”合作模式,一方面基于扩大合作规模,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的集体行动形成一个方式上更灵活、效果上更有力的组合;另一方面在于突破成员间经济合作缺乏活力的瓶颈,促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寻找互补合作领域,突出规模优势。
“金砖+区域”的实践始于2013年南非德班峰会,自此每年度金砖国家主席国都邀请本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开创了南非德班峰会的“金砖+非洲”、巴西福塔莱萨峰会的“金砖+拉美”、俄罗斯乌法峰会的“金砖+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印度果阿峰会的“金砖+环孟加拉湾经济技术合作组织”的合作模式。2017年中国以“金砖+5”的方式首次从全球范围内邀请墨西哥、埃及、几内亚、塔吉克斯坦、泰国等5个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席对话会,凸显了金砖的开放性和受邀国家的代表性。2018年南非邀请了9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地区的政府首脑参加会议。目前,区域合作形成三个主要区块:“金砖+欧亚”、“金砖+南美”、“金砖+非洲”,合作仅限于领导人会谈,缺乏明确的合作议程。纵向上,合作机制亟待建立,横向上,对话伙伴有待拓展。
事实上,“金砖+区域”属于区域间主义的一种叠加形态——集团对区域,区域间主义为“金砖+区域”交往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75]金砖国家可立足于自身协调能力选择适合的区域间合作模式。具体而言:
第一,关于制度建设。“欧盟模式”、“东盟模式”、“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76]是目前最典型的区域间合作模式,相比较而言,欧盟模式是契约式的强制度安排,东盟模式是协商式的软制度对话,美国模式是以硬实力为根基的霸权合作模式,中国模式则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平等合作。[77]金砖国家在主体上是类似于东盟的政府间组织,缺乏超国家机构的参与和自主性能力,在议题上兼有欧盟的发展议题与东盟的“软政治”议题,在合作性质上更类似于中国的平等合作。“金砖+区域”交往应是博采众长,兼而有之,但复杂的成员构成决定了“金砖+区域”模式的自主决策能力较弱,以金砖自身特点为基础,灵活采纳中国模式、欧盟模式与东盟模式,或将有助于“金砖+区域”合作取得较好的成效。例如,通过论坛等初级形式搭建金砖国家与不同区域的常规沟通渠道,筛选合作区域,探索合作领域,寻求合作共识;以双边合作为基础,并由此带动多边合作,形成较低标准的多边合作框架;借助成员与区域的合作基础,从建立试点开始,启动制度建设进程。
第二,关于议题设定。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区域间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加,诸如“薄荷四国”(MINT)、“展望五国”(VISTA)、“灵猫六国”(CIVETS)、“新钻11国”(NEXT-11)等存在竞争关系的新兴经济体的合作组织越来越多,[78]要保持金砖合作的自主性和引领性,防止“金砖+”变成“+金砖”,金砖国家需要展示出在关键议题上的决策和领导能力,打造金砖国家的标签。议题设置是至关重要的发挥场所,议程设计应由易而难分期规划,同步实现共同利益的增进与合作空间的拓展的目标,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减贫问题等,可以作为弥合分歧、增强凝聚力的优先议题深度推进,而后过渡到其他议题。[79]敏感议题须谨慎对待,例如安全问题,尽管金砖内部合作已较多涉及安全领域,但“金砖+区域”合作中应谨慎推进,安全领域并非应置于优先合作领域。
第三,关于认同建构。新兴国家群体化的集体身份并不是自然获得的,“金砖+区域”提供了一个将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纳入金砖合作范畴、避免发展中世界内部分裂的可能路径。但该群体的组成复杂,将差异很大的价值体系、文化系统、社会制度、对国际体系的期待与观念一并囊括,实现在国际事务中集体发声,应积极创造内生性共识而非基于外在刺激,关键就在于构建共同的话语背景,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政治等复合的、相互依赖的议题领域,为新兴大国可能的集体身份之再造或强化提供“时势”场域。[80]认同的建构是双向互构的过程,在诸多议题上的集体身份有助于增进金砖内部的集体认同,区域间合作作为外部力量也可能推动区域形成集体认同,“金砖+区域”合作即是如此。

表3 区域间主义合作的四种运行模式
资料来源: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三、扩容的风险:兼顾三个视角
扩容进程的推进将不可避免改变金砖国家合作的地理空间、议题设置和合作前景。就收益而言,金砖国家的话语权将提升,经济合作将深入和泛化,机制开放性将增强。但风险与收益相伴而生,计算风险时的审慎视角和评估收益时的乐观假设,对于实现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基于金砖国家扩容的复杂性,金砖国家将面临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兼容性论战、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弥合性难题和成员之间的包容性困境三重风险。
(一)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兼容性论战
金砖国家在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同时,与发达国家产生价值理念的冲突与权力关系的冲突,伴随着金砖国家的扩大,冲突将呈现加剧态势。
第一,价值理念的冲突。“区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不仅是领土的,也是思想的和概念的”。[81]随着不断扩容的金砖国家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坚力量,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治理理念上的显著差异将成为南北关系中新的冲突热点,不排除发达国家将理念层面的冲突转化为金砖国家发展的现实障碍。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而形成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倾向,是二者理念冲突的焦点。新兴国家影响的扩大,使其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理念更加可信,“华盛顿共识”遭遇挑战,而“北京共识”受到关注,国际机制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中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主义色彩,全球治理方式正面临变革,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担忧的。[82]伴随着论战上升到理念价值层面,具体议题上的争论也更加复杂,例如,在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人权问题、气候谈判等议题上的立场对立愈发显著。论战的复杂性还在于金砖国家成员复杂,内部远非铁板一块,部分成员虽然经济上是新兴国家阵营,但政治上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例如,俄罗斯在文化上自认为是西方国家,政治上因不被西方接纳转而与西方对抗;南非、巴西西化痕迹明显,定位上的模棱两可与外交上的两面下注,使金砖国家内部面临二元性挑战。
第二,权力关系的冲突。国际秩序的构建就如建造一座建筑,理念价值描绘设计效果,实力对比提供砖瓦水泥,而权力关系才是施工图纸,理念和实力的竞争最终要落实到权力关系层面。金砖国家的力量越壮大,西方国家的受威胁感越强,[83]西方国家将金砖国家视为对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金砖国家对国际秩序变革参与程度的加深,更强化了来自西方的敌意。以非洲为例,近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受经济发展驱动,对非洲大陆的投入增长较快。欧洲发达国家将其在非洲影响削弱的事实归罪于中印等国,进而采取对抗性措施。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上,使金砖国家遭遇对抗性误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金砖国家成为全球再平衡的力量,要依靠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内部协调,然而,部分成员国应对与西方国家直接或潜在的紧张关系的策略,背离了促进政策协调的组织期待。例如,印度加强与中俄合作的同时,强化其“东向战略”与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对接,潜在成员国中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墨西哥等国家也在与金砖国家和与西方关系上两面下注。可见,即便金砖国家依靠自身扩容与深化成为国际体系中平等成员的潜力很大,[84]也不能忽视与主要西方国家关系的影响。
(二)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弥合性难题
合作边界的拓宽可能引发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体现为与发展中国家在议题上的分歧以及外交选择的不确定性。
第一,现今某些发达国家试图使用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贫穷发展中国家三分法来取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将相对发达的新兴国家剥离出发展中国家阵营,意图削弱其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身份的合法性,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例如,2008年的多哈回合谈判时,美国就农产品补贴问题区别对待,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做出妥协,对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决不让步,最终导致谈判无果。其企图让那些认为可从美国的让步中获益的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谈判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印度和中国。这种离间无疑会增加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弥合难题。又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是全球气候政治互动的主要平台。在谈判进程与博弈各方交锋当中,最为显著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南北对立。不过,南北国家群体内也存在严重的分化,使原有的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二元对立有裂变为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足鼎立”的趋势。俄罗斯与基础四国的分歧便是例证。然而,尽管有分歧,但新兴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远非对立的群体。“金砖+区域”的合作,意在增进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共同追求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贫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难以以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获益,因而倾向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传统路径;新兴国家基于所积聚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而获得增量收益。尽管各有侧重,但并非对立。如果新兴国家不愿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将陷入孤立;如果贫穷发展中国家不支持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出的“平等与无差别待遇”的主张,其发展诉求便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束缚。事实上,大部分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相同的发展要求和发展共识,这是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前提和基础。[85]两者可以结成牢固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从不同战线回应发达国家发起的攻势,合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86]同时不能忽视,金砖国家与贫穷发展中国家因发展阶段的不同,在议题领域、追求目标上是存在差异的。如何弥合差异?其一,继续追求两者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公平”;其二,新兴发展中国家要给予贫穷发展中国家以一定的帮助。
第二,外交选择的不确定性,既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外交方向的摇摆性,又体现为金砖国家成员外交的实用主义倾向。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与金砖国家的走近就意味着与西方关系的疏远,两面下注、左右逢源才是理性选择。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排除这些国家出于经济利益、战略利益的考量而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联盟,成为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在金砖国家内部,巴西对墨西哥、阿根廷及南非对尼日利亚加入金砖国家持保留态度,理由是其加入会带来合作困难。事实上,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自身的区域代表性被削弱的担忧。另外,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2016年印度果阿峰会上,印度作为轮值主席国邀请“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领导人参与金砖国家对话,巴基斯坦并非该组织的成员国,而巴基斯坦所参加的南亚地区合作组织(SAARC)却并未被邀请。而且,此次峰会更是把反恐作为重要议题,对巴基斯坦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反映了印度意在挤压巴基斯坦在南亚的生存空间。尽管最终印度提出的企图将巴基斯坦与恐怖主义相联系的条文没有写进峰会宣言,但对外交空间的竞争,增加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复杂性。[87]
(三)金砖国家成员之间的包容性阻力
经济方面,金砖国家成员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在生产、贸易结构及全球价值链中基本位于同一层次,经济关系存在竞争性,若扩容不能弥合现有分歧,不仅竞争将会加剧,也会使本身内生性合作动力不足的金砖更难以达成协定。潜在的扩容成员国,例如印度尼西亚,对外资进入的制度限制、歧视性的国际货物认证要求以及严苛的用工制度等大量的服务障碍、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88]构成经济合作的现实瓶颈。鉴于经济体量的差距,若加入新成员后未能及时采取适当的制度设计来平衡成员国间的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经济合作将放缓,进而扩大金砖国家的离心力。
政治方面,成员国基于不同的偏好和资源分配,形成了不同的策略,对合作的优先方向设想不同,如:南非及其所代表的非洲大陆偏重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印度更关注反恐与安全议题的协商与合作,扩容将不可避免增加利益整合的难度,具体议题上分歧的弥合难度将加大,合作成效也会打折扣,进而在某些分歧较大的领域难有共识,无所作为。潜在成员国基于不同诉求希望加入金砖国家,或为提升合作空间,或为寻求外交平衡,或为缓解地缘政治压力,这无疑将导致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加集体行动的阻力。
安全方面,扩容将会增加成员国间关系协调的难度,目前成员国之间已经存在一些矛盾,扩容将使矛盾关系更加复杂化,进而可能会出现在机制内外对外交资源的争夺。如果出现成员选边站,或者外部力量的渗透,将增加组织的离心力。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之间的三边纠葛、印度借重美国与中国进行角力便是明证。矛盾激化时,组织框架可能成为相关方的角力场,例如,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可能提出对对方不利的议程,此举虽然符合轮值主席国权限,但无疑将扩大成员分歧,甚至使金砖国家某些领域的合作陷入僵局。在扩容对象的选择上,若一个区域同时接纳两个成员国,尽管会为两国的竞合关系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但也可能使原本限于区域内部的安全困境扩大至金砖国家合作。
身份认同方面,身份认同不是伴随着加入组织而应然获得的,而是一个需要主动建构的过程。对于金砖国家来说,显著的内部异质性和模糊的成员国标准使金砖国家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难度较大,而扩容带来更多元的政治、文化和利益因素,更可能稀释集体认同感。如果内生型的新认同感迟迟未能建立,成员国应对利益冲突的策略就更具有利己主义色彩,维系组织运行的根本将不存在。另外,民众对于金砖机制的了解和参与赤字也是一个挑战。[89]缺乏群众基础是欧洲一体化遭遇今天民粹主义挑战的重要原因,前车之鉴值得金砖合作机制加以警惕。而民众过度参与又可能导致效率低下,有可能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如何平衡也是值得思考的事情。[90]
四、结论
金砖国家是联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立足于弥补和提升原有机制的民主性与合法性,而原有机制也需适应新机制并与之共存,只有建立兼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满足双方期许。当前发达国家作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推动改革的意愿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尽管有改革的意愿和偏好,但受制于实力,其对于支柱性的国际机制影响力依然不足。因而,金砖国家的扩容,是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促进国际机制合理化,实现兼容性制度重构的有效路径。但扩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成员国间异质性突出、认知差异大和向心力不足等现实瓶颈,又需克服规模困境、利益困境、强者可信与小国搭便车困境等技术难题,同时更应充分考量扩容可能增加深化难度、而深化可能抑制扩容进度等结构性矛盾。
成员国各持立场。俄罗斯更专注于金砖机制的深化以服务其“政治集团”的外交偏好,在对象选择上有较强的地缘政治倾向和对美划线思维;中国将金砖合作定位为“南南合作”,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寻求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的提升;印度将金砖国家定位为跨区域经济投资合作平台而非反西方的战略集团,同时试图在金砖机制内打造一个“并非由中国主导的集团”的身份认同,这也直接影响到印度对扩容候选国的选择偏好;巴西扩容立场相对保守,担心本地区竞争者的加入会稀释其地区影响力;南非更关注“非洲议题”,因而更倾向于深化而非扩大,既希望提升非洲话语权,又担心本地区国家加入会稀释其代表性。
主导国存异求同。印度目前尚不足以成为金砖的主导力量,巴西不愿坐第一把交椅,南非主观意愿和影响力皆有限,俄罗斯希望做金砖机制的主导国,而中国由于经济体量和影响力是事实上的主导国。中国更倾向扩大,俄罗斯更倾向深化,映射出两国对金砖定位的差异。中国希望抱团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而俄罗斯希望打造政治团体以防范美欧打压。然而,中国提出的“金砖+”模式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四国认同,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也延续并拓展了“金砖+”模式,以软性扩容的方式推进“金砖+新成员”模式与“金砖+区域”模式,成为金砖国家扩容的现实路径。
外部环境可资利用。虽然金砖国家越强大面对的外部压力也会越大,不仅要应对来自于西方国家的阻力,也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质疑,然而金砖国家的扩容依然有可借之力。金砖国家大多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拒绝把金砖机制发展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对抗性集团,通过“金砖+新成员”模式扩大合作核心圈,通过“金砖+区域”模式扩大合作辐射圈,并开拓“金砖++”模式将西方国家拉入金砖合作圈,多层推进,将更有利于金砖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① Brooks Spector, Jim O’Neill, “South Africa’s Inclusion in BRICS Smacks of Politics”, October 4, 2011, 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11-10-04-oneil-south-africas-inclusion- in-brics-smacks-of-politics/
②[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著:《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钱亚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③“南非是金砖国家中唯一真正具有双海岸性质的成员国,它在非洲大陆的作用取决于它向西南印度洋和南大西洋提供的海上通道。”参见Vreÿ François, “A Blue BRICS,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South Atlantic”,, 2017, Vol.39, No.2, p.358.
④赵斌:“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7页。
⑤ Biswajit Dhar, “The BRICS in the Emerging Global Economic Architectur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ember17, 2012, No.125, http://saiia.org.za/research/the-brics-in-the-emerging-global-economic-architecture/; Machiel Renier van Niekerk, “South Africa’s Role in the BRICS Vision”, EIR, February6, 2015, https://larouchepub.com/eiw/public/2015/eirv42n06-20150206/09-11_4206.pdf
⑥ Kurşun, Ali Murat, and Parlar Dal, Emel, “An Analysis of Turkey's and BRICS’ Voting Cohesion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during 2002-2014”,, 2017, Vol.8, No.2, pp.191-201; Gokhan Bacik, “Turkey and the BRICS: Can Turkey Join the BRICS?”,, 2013, Vol.14, No.4, pp.758-773.
⑦ Monowar Mahmood and Golam Mostafa, “Kazakhstan–BRICS Economic Cooperation: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January 2017, pp. 148-164.
⑧Karen Brooks, “Is Indonesia Bound for the BRICS?”,(Singapore), November 11, 2011.
⑨ Lee Young Hwan, “Vision and Strategy to Make BRICS as Blue Ocean for Korean Economy”,, 2006, Vol.9, No.2, pp.1-17.
⑩张兵、李翠莲:“墨西哥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研究”,《亚太经济》,2011年第5期,第67-71页;王超:“墨西哥:下一块‘金砖’”,《中国海关》,2012年第8期,第60-61页。
⑪张庆从合理性、潜在对象、意义三个方面论述金砖国家扩容的可行性,但其更多是从功能意义,而非伦理视角去探讨的。参见张庆:“金砖国家扩容的可行性研究”,载肖肃等主编:《当前金砖国家研究的若干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年,第23-39页。
⑫蒲俜:“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组织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第48页。
⑬刘莲莲:“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4-26页。
⑭本文所指的“软性扩容”,意指两个层面的叠加:第一层面即狭义理解上的扩容,仅指加入机制或组织,成为正式成员国;第二层面即广义理解的扩容,泛指扩大规模、范围、数量等,包括正式成员国的接收、观察员国与对话国的加入及组织规模的扩大。为方便表述,文中统一使用“扩容”一词指代两个层面的含义。
⑮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⑯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1982, Vol.36, No.2, pp.379-415.
⑰[英]R·萨科瓦(Richard Sakwa):“金砖国家和泛欧洲的终结”,《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2页。
⑱ Manuchehr Shahrokhia, Huifang Cheng, Krishnan Dandapani, Antonio Figueiredo, Ali M. Parhizgari, Yochanan Shachmurov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BRICS: Unbundling Politics from Economics”,,February 2017, Vol.32, pp.1-15.
⑲王永中、姚枝仲:“金砖国家峰会的经济议题、各方立场与中国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77-78页。
⑳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页。
[21]Suresh P Singh, Memory Dube, “BRICS and the World Order: A Beginer’s Guide”,,2013, pp.42-43. www.saiia.org.za
[22] Sijbren de Jong, Rem Korteweg, Joshua Polchar and Artur Usanov,,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4.
[23] W.P.S. Sidhu, “BRICS: Shaping a New World Order”, May13, 2018. www.brookings.edu/ opinions/brics-shaping-a-new-world-order-finally
[24] Jorg Husar,
[25] Gokhan Bacik, “Turkey and the BRICS: Can Turkey Join the BRICS?”,, 2013, Vol.14, No.4, pp.758-773.
[26] Bas Hooijmaaijers, Stephan Keukeleire, “Voting Cohesion of the BRICS Countri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2006-2014: A BRICS Too Far?”,, 2016, Vol.22, No.3, pp.389-404.
[27]Niu Haibin, “BRICS in Global Governance: A Progressive and Cooperative Force?”,, September 2013, p.4.
[28] 庞中英:“要有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治理方案——金砖合作与世界秩序的转型”,《学术前沿》,2014年9月(下),第26-35页。
[29] Andrew Cooper, Asif Farooq, “The Role of China and India in the G20 and BRICS: Commonalities or Competitive Behaviour?”,, 2017, Vol.43, No.3, pp.73-106.
[30] 庞中英:“要有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治理方案——金砖合作与世界秩序的转型”,第26-35页。
[31] 参见表1。
[32] Bobo Lo, “The Illusion of Convergence-Russia, China, and the BRICS”,, 2016 March, No.92. 转引自肖辉忠:“金砖国家的起源、内部结构及向心力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7页。
[33]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金砖发展战略报告(2015)》(金砖国家经济智库),2015年12月,第7页。
[34] 参见表1。
[35] 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第28页;Vadim Lukov, “A Global Forum for the New Generation: The Role of the BRICS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BRICS Information Centre, January 24, 2012. www.brics.utoronto.ca/ analysis/Lukov-Global-Forum.html
[36] Lee Young Hwan, “Vision and Strategy to Make BRICS as Blue Ocean for Korean Economy”,,2006, Vol.9, No.2.
[37] Juan L. Suárez de Vivero, Juan C. Rodríguez Mateos, “Ocean Governance in a Competitive World: The BRIC Countries as Emerging Maritime Powers-Building New Geopolitical Scenarios”,, 2010, Vol.34, pp.967-978.
[38] Vijay Sakhuja, “BRICS: The Oceanic Connection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ugust 4, 2014, www.ipcs.org/article/india/brics-the-oceanic-connections-4594.html
[39] 庞中英:“金砖合作面对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挑战”,《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35页。
[40] Alissa Wang, Chair. Summit Studies BRICS Research Group, “From Xiamen to Johannesburg: The Role of the BRICS in Global Governance”, May 20, 2018. www.brics.utor onto.ca/analysis/xiamen-johannesburg-event.html
[41]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42] 成志杰:“复合机制模式:金砖机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向”,《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9-129页。
[43] William Pomeranz, “Why Russia Needs the BRICS”, September 3, 2013, http://global publicsquare.blogs.cnn.com/2013/09/03/why-russia-needs-the-brics/
[44] Sijbren de Jong, Rem Korteweg, Joshua Polchar and Artur Usanov,, pp.54-56.
[45] 外交部:“杨洁篪就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接受媒体采访(全文)”,2017年9月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hdqzz_681964/jzgj_682158/zyjh_682168/t1490622.shtml
[46] Sijbren de Jong, Rem Korteweg, Joshua Polchar and Artur Usanov,, p.53.
[47] “Erdogan Scheduled to Attend South Africa BRICS Summit, Meet with Putin”, www.rferl.org/a/russia-turkey-erdogan-putin-brics-summit-johannesburg/29384090.html
[48] Gokhan Bacik, “Turkey and the BRICS: Can Turkey Join the BRICS?”,, 2013, Vol.14, No.4, pp.758-773.
[49] Kurşun Ali Murat, and Parlar Dal Emel, “An Analysis of Turkey’s and BRICS’ Voting Cohesion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during 2002-2014”, pp.191-201.该文运用了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土耳其与金砖国家之间在联合国投票中的一致性问题。
[50]刘作奎:“‘深化’还是‘扩大’——东扩十年欧洲一体化走向分析(2004-2014)”,《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第49-62页。
[51] 同上,第60页。
[5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普京表示:金砖国家目前没有计划扩员”,俄罗斯卫星网,2018-07-27,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07271025984081/
[53] “Lavrov: No Plans for BRICS Expansion”, The Brics Post, November 5, 2018, http://the bricspost. com/lavrov-no-plans-for-brics-expansion/#.WvQQ43--nIU
[54] 徐庭芳:“俄罗斯总统府金砖委员会主任托罗拉亚:中国提出的‘金砖+’计划很及时”,《南方周末》,2017年9月7日。
[55] “2014年5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4年5月14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4/content_2679640.htm
[56] 庞中英:“金砖合作面对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挑战”,《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36-37页。
[57]当然也存在部分反对的声音,例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认为,在起步阶段扩容需谨慎,也不急于设立秘书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加力提醒,警惕因扩容而引发的成员间共同性下降、“公约数”缩小、决策力萎缩的风险,当前主要应加强凝聚力。中国社科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黄薇认为,金砖短期内扩容可能性不大,初期规模比较大意味着较高的谈判成本,做出具体扩容举措要谨慎。(杨洁勉观点参见杨洁勉:“金砖国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机制建设”,《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3页。马加力观点参见李明波等:“谁将是下一块,‘金砖’智库不赞成短期扩容”,《广州日报》,2011年4月15日。黄薇观点参见李静:“德班‘金砖’峰会带来什么?”,《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4月2日。)
[58] 庞中英:“金砖合作面对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挑战”,《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36-37页。
[59] 王磊:“‘金砖+’要为金砖加什么?”,《光明日报》,2017年9月2日。
[60] 目前关于“金砖+”应当如何解释,官方和学界尚未形成定论,学界仍处于学术探索期。
[61] 王毅:“要探索‘金砖+’模式 扩大金砖国家‘朋友圈’”,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3-08/8168988.shtml
[6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金砖+’:应对贸易战的新合作模式”,俄罗斯卫星网,2018年7月25日,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807251025964915/
[63] 缪培源:“推动全球治理是金砖合作不竭动力——访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新华社,2017年8月2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824/c1002- 294918 92.html
[64]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金砖发展战略报告(2017)》(金砖国家经济智库),2017年12月,第51-52页。
[65]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金砖发展战略报告(2015)》(金砖国家经济智库),2015年12月,第26页。
[66] Ben Blanchard, Olivia Rondonuwu, “No BRICS Expansion”, IOL, November16, 2011, www.iol.co.za/news/world/no-brics-expansion-1179994
[67] 林蕴:“‘金砖+’到底加什么,金砖可能启动新一轮扩大和扩容?”,新浪网新闻中心,2017年9月3日,http://news.sina.com.cn/o/2017-09-04/doc-ifykpzey4102832.shtml
[68] 庞中英:“金砖合作面对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挑战”,《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36-37页。
[69] 参见表2。
[70] 金砖五国在政治、安全议题上抱团合作的趋势远低于发展议题,因而对投票倾向的考量仅作参考。
[71] Sijbren de Jong, Rem Korteweg, Joshua Polchar and Artur Usanov,,pp.1-86. 该研究采取量化的方法分析了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韩国与金砖国家之间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程度。在经济治理问题上,印尼与金砖五国一样,似乎更容易表现出对西方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反对,但是他们的提议往往模糊且范围有限;尽管相互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都表现出在经济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的雄心。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外交方面印尼与南非一样,在海外的外交影响力并不大,它们主要关注亲密的邻居;安理会投票方面,当安理会内部存在分歧时,金砖国家往往是单独行动而不是协同行动;核不扩散问题上,巴西、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不同立场;在武器贸易方面分界线明显存在,巴西、土耳其和南非依赖西方的武器供应,中国和印度则从俄罗斯进口大部分武器,印度尼西亚位于这两个群体之间。
[72] 米军:“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90页。
[73] Jim O’Neill and Anna Stupnytska, “The Long-Term Outlook for the BRICS and N-11 Post Crisis”,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Commodities and Strategy Research,, December 4, 2009.
[74]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75] 根据目前国内外比较公认的划分方法,按照参与行为体将区域间主义划分为三种形态:双区域间主义、跨区域间主义和准区域间主义。我国学者郑先武指出,区域间主义强调的是来自不同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的多个行为体之间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所以,至少一方必须是区域组织、集团或某一个或多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这是定义区域间主义的“底线”。(参见郑先武:“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63页。)金砖国家合作是来自不同区域的五国组成的对话与合作,属于典型的跨区域间主义,而“金砖+区域”构成区域间主义的叠加状态——“集团+区域”,此处的“集团”,与传统区域间主义概念界定的“集团”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概念中的“集团”指同属一个地区的区域集团,而金砖国家的“集团”是跨地区五国组成的“集团”,在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其构成“集团+区域”的区域间主义形态的性质。
[76] 参见表3。
[77]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9年第1期,第85-98页。
[78]《金融时报》曾迫不及待地报道金砖国家的终结命运,甚至做了个红字标题——“超越金砖”,称其他的新兴市场将会取代金砖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参见[英]R·萨科瓦(Richard Sakwa):“金砖国家和泛欧洲的终结”,第109页。
[79] Samuel A. Igbatayo, Bosede Olanike Awoyemi, “Exploring Inclusive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BRICS Economies: A Multi-Country Study of Brazil, China and South Africa”,, 2014, Vol.5, No.6, pp.54-68.
[80] 赵斌:“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第127页。
[81] Bahgat Korany, “End of History, or Its Continuation and Accentuation?”,, 1994, Vol.15, No.1, pp.7-15.
[82] 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107-121页。
[83] Manuchehr Shahrokhia, Huifang Cheng,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BRICS: Unbundling Politics from Economics”,, 2017, Vol.32, Feburary, pp.1-15.
[84] Gokhan Bacik, “Turkey and the BRICS: Can Turkey Join the BRICS?”,, 2013, Vol.14, No.4, pp.758-773.
[85]潘兴明:“三种纬度下的金砖国家关系考察”,《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第125页。
[86]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86-204页。
[87]王蕾:“金砖国家间安全利益的关联与安全合作前景”,第125-128页。
[88] Sijbren de Jong, Rem Korteweg, Joshua Polchar and Artur Usanov,, p.41.
[89] Suresh P Singh, Memory Dube, “BRICS and the World Order: A Beginer’s Guide”, p.44.
[90]王义桅:“‘金砖’行稳致远面临的挑战”,《环球时报》,2018年5月31日。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cooperation, the foundation, the path and risks of the BRICS expansion are unique and thu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Based on transcending paradoxes between system non-neutrality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mechanism, between homogeneity in preference and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between deepen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operation and expanding the extension of cooperation, it is a reasonable path for the BRICS to expand through modes of “the BRICS + new members” and “the BRICS + the region” in a much softer way. Meanwhile, risks are paralleled by its expansion. The BRIC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West,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inclusiveness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will stand the test.
the BRICS,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BRICS Expansion, the BRICS Mechanism
【Аннотация】В качестве важного аспекта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основа, пути и риск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БРИКС являются особыми и требуют к себ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основе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парадоксов между ненейтральностью системы и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ми механизма, однородностью предпочтений и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 парадокса между углублением содержа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расширени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модели «БРИКС + новые члены» и «БРИКС + регион» путём мягк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разумным путём по расширению БРИКС. Однако последуют риск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и будет проверена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между БРИКС и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близость между развивающимися странами и инклюзив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 член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траны БРИКС, страны с формирующимся рынком, расширение БРИКС, механизм БРИКС
D751.2
A
1009-721X(2019)01-0055(30)
*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给予的评审意见。
**孙艳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