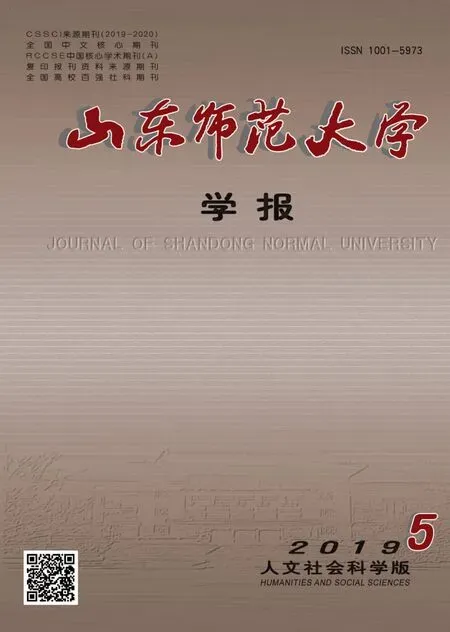走向神坛:《兰亭序》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造就*①
吕文明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014 )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其原因主要是兰亭雅集和《兰亭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南朝梁武帝首先大力推崇王羲之,唐初李世民定王羲之为书界一尊,特别是《兰亭序》的面世,更使整个社会形成崇王的风气。系统考察兰亭雅集的文化价值和《兰亭序》的艺术创造力,对于深刻剖析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咏彼舞雩:兰亭雅集作为文人集会典范的意义
永和九年(353年),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遍邀诸友,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兰亭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向往和追寻的文化圣地。郦道元《水经注》载:
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1)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4页。
可见,在王羲之身后不久,兰亭地理即已发生变化。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绍兴知府沈启见到“亭所在已非故处,坏且不存,而所谓清流激湍,亦已湮塞”(2)文征明:《甫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9页。。清人吴骞亦云:“今之游兰亭者求右军故迹,不特茂林修竹风景已非,即流觞曲水之地已无可据。”(3)吴骞:《尖阳丛笔》,《丛书集成续编》(第9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895-896页。所以,世人才重建兰亭,所选地址亦为大概位置。日本学者铃木春彦认为现在的兰亭是为迎接乾隆皇帝而造,朱关田则认为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营建。另有唐代杜佑、南宋吕谦、明代文征明、清代全祖望、于敏中等,也对兰亭位置有所推断。可见,在王羲之身后,围绕兰亭所在已经形成学术争鸣。这也是王羲之名士风范的一种表现,即他不选择城里的官舍、酒肆作为宴集地,却选择这样一个处在天地造化之中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所在,这就为兰亭雅集成为文人集会的典范埋下了伏笔。
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所载《天章寺碑》记述参加兰亭雅集的人员是:
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郗昙、王丰之、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平、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各赋诗,合二十六人。谢瑰、卞迪、丘髦、王献之、羊模、孔炽、刘密、虞谷、劳夷、后绵、华耆、谢藤、任儗、吕系、吕本、曹礼,诗不成,罚三觥,合十六人。(8)施宿:《嘉泰会稽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5-196页。
与会人员虽然算不上整个东晋王朝的文化精英,但对于浙东来说,已经是难得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羲之无疑群贤之首,他既是当地行政长官,又是名士之望,受人推崇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也恰恰成就了王羲之的风范,他在酒会上开怀畅饮、直抒胸臆,把自由自在的心态全部表现出来。待到雅集名士公推他作序时,整个活动达到高潮,王羲之在这样的高潮中完成了精神世界的彻底升华。《晋书》载:“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9)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9页。王羲之的这种风度正是其自由精神的表现,完全符合魏晋士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的人格特征。
兰亭雅集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此前,东晋虽有雅集的传统,如庾亮在武昌的“南楼理咏”,但当时还只限于清谈,没有上升到文艺精神的层面。在兰亭雅集中,诸名士仰观俯察,饮酒作诗,已不仅仅是休闲和娱乐,而是具有一定主动性的文学创作活动。与会人员作出35首诗,多为四言或五言,主要描写周围风景,寄托个人情感,与此前之玄言诗大不相同,开山水诗之新境界。所以,兰亭雅集是纯粹的文人活动,文学创作的趣味非常浓厚,诗歌的水平和境界也普遍较高,兰亭雅集由此而成为后世文人集会的典范。唐初,王勃在云门寺主持了模仿兰亭雅集的修禊活动;大历年间,鲍防在越州组织了著名的“浙东联唱”;元代刘仁本在余姚组织了“续兰亭雅集”;清人杜甲组织的兰亭雅集,赋诗采用唱和的形式。总之,兰亭雅集之后,仿照其进行的后续活动源源不断,兰亭雅集成为文人世界的第一等奇事。
由此,兰亭雅集成为中国文人雅集的代名词。这是王羲之走向书法神坛的基本条件,即他受人推崇的圣人风范在这一事件中得到持续酝酿和发酵。
二、尽得风流:《兰亭序》文本的文化包容性和艺术创造力
要明确《兰亭序》对于王羲之的重要意义,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个文本创作和流传的基本情况。《兰亭序》文本最早出现在《世说新语》中,原文仅25字:“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后有刘孝标注:
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暮——引者注)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3页。
“海航从2018年开始,资产出售步骤加快。悉尼写字楼、淄博石油、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写字楼等被悉数出售。海航首府、海航棚改地块、海航科技广场、海航广州白云项目等先后出售给融创、富力及万科等。”丁晓晓表示,这样的资产出售远未停止,海航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世说新语》正文和注对《兰亭序》的称谓已然不同,后人对此更是众说纷纭。桑世昌《兰亭考》云:“晋人谓之《临河叙》,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题曰《禊帖》。”(11)桑世昌:《兰亭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自晋至宋,这些称谓让人莫衷一是,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世说新语》透露出的信息。刘义庆以《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作比较,而刘孝标作注却说是《临河叙》,作注本就有解释和纠正之意。鲁迅言:“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12)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可见,《临河叙》与《兰亭集序》应为两篇文章。王羲之在雅集现场仿照《金谷诗序》作了《临河叙》,以记述雅集盛况,二者风格相似;后来为诗集作序,才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兰亭集序》。刘义庆所说《兰亭集序》实际是《临河叙》,所以刘孝标在注中作了纠正。
有了上面的推断,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如为什么《世说新语》和《晋书》都提到时人称赞王羲之的文章和风度,却唯独不提及其书法?王羲之又如何能在酒醉状态和山野集会的混乱现场写出如此精美的书法?笔者认为,王羲之现场所书《临河叙》是为雅集而作,主要用于诵读,急就而成,书法平平,所以没有引起注意。雅集结束后,王羲之在为《兰亭诗集》作序时,酝酿许久,情深意满,因此写成优美的《兰亭集序》,经过几次修正、誊写,最后形成精美绝伦的书法作品,并作为传家宝留给第五子王徽之,后来经过王桢之、王翼之、王法朗、王彦祖、王昱,传至第七代孙智永。这件作品因为不是在公众场合书写,所以无人知晓;因为是传家之宝,所以严格保密,在整个南朝无人提及。南宋姜夔曾云:“然考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13)桑世昌:《兰亭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智永出家为僧,把《兰亭序》传给弟子,所以,《兰亭序》不再作为王氏家传秘密。后来被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由此而大显于天下。何延之《兰亭记》和刘餗《隋唐嘉话》在100年后记述此事,难免添油加醋、揣度臆测,遂形成“萧翼智赚兰亭”故事。宋人王铚就认为《兰亭记》所述不实:“此事鄙妄,仅同儿戏。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尪残老僧,敢靳一纸耶?诚欲得之,必不狭陋若此。况在秦邸,岂能诡遣台臣?亦猥信之,何耶?”(14)桑世昌:《兰亭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以上问题莫衷一是,但却共同传达出一个信息:《兰亭序》在唐代受到广泛推崇,所以才有那么多摹本和刻本传世。同时,民间也出现了研习《兰亭序》的高潮,20世纪初在敦煌文献中就发现多件《兰亭序》写本,其中最精彩的是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伯二五四四号”写本。这份初唐写本与现本《兰亭序》基本吻合,当是《兰亭序》在唐初广泛传播的力证。
接下来分析《兰亭序》的笔法问题。对《兰亭序》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兰亭序》笔法与唐人相似,完全没有了隶意,东晋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笔法的。清代李文田最早提出质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15)水赉佑:《〈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826页。郭沫若在看到南京新出土东晋墓志后也指出:“这可证明,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辟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16)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李、郭二人的怀疑主要集中在:王羲之笔下到底能否出现这种成熟的“唐楷笔法”?围绕这一问题,学界进行了论辩,持否定意见的人占到大多数。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王羲之是文人书家的代表,并以创新精神著称,他的书法与墓志、砖文等民间书法绝不可同日而语。清代阮元“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云:
此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17)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2页。
东晋已经是行书和楷书大量使用的时代,即清代阮元所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18)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91页。,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指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1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44页。可见当时已通用楷书,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和王献之《洛神赋》即是代表作品。当时,隶书主要用于书写墓志、匾额等,已不是生活常用体。另外,像二爨这样的书体也主要出现在偏远地区,所以字体古拙,虽充满生机,但从字体发展的角度来说却是远远落后了。而王羲之书法创作的主体是清新雅致的行草,如《丧乱帖》《得示帖》《二谢帖》等,已鲜有隶书笔意,属于比较成熟的行草书。像《快雪时晴帖》,则是标准的行书,其风格之先已不亚于《兰亭序》,不过因为是尺牍,仍能见到快速行笔和牵引连带。而《兰亭序》是王羲之精心创作的长文,字体工整,楷书的意味较浓,接近“唐楷笔法”。实际上,这种“唐楷笔法”本就是从王羲之楷书、行书发展而来,它们就是这种所谓“唐楷笔法”的鼻祖。
再进一步分析,这种“唐楷笔法”也未必就是《兰亭序》的真实展现,毕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唐代及后世书家的临摹本和刻本。欧阳修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兰亭修禊序》,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模,失真弥远,然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20)桑世昌:《兰亭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米芾亦云:“褚模兰亭宴集序,虽临王帖,全是褚法。”(21)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4页。清代阮元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他对这种在临摹中加进个人笔意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22)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99-600页。
当然,阮元是站在融冶北碑南帖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却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兰亭序》笔法提供了思路。在《兰亭序》面世的十年里,见过真迹的诸人未留下任何评价,后世描述都是对临摹本和刻本的评价,那么,这些评价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后世对《兰亭序》的置疑实际是对临摹本和刻本的怀疑,而不是对真迹的怀疑。尤其是初唐诸位大家,他们本就是书法名家,早已形成个人风格,在临摹时难免会将个人笔意带入其中。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兰亭序》版本,笔意相差较大,即使是最好的冯承素摹本也是妍美过度。作为御用搨书人,冯承素在摹写时故意加进一些细微笔法,使摹本更加生动,以取悦太宗,也在情理之中。
除唐代临摹本和刻本以外,后世书家又对这些文本进行临写、摹刻,如赵孟兆页、俞和、董其昌等,遂形成新的《兰亭序》文本,而这些文本在今天又被书法爱好者临摹,由此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兰亭序》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历代书法名家不断把个人书风融入《兰亭序》中,遂形成《兰亭序》的一系列文本。这些文本虽然不是真正的《兰亭序》,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人知道真本的风格,这些文本也就成为具有不同审美倾向的《兰亭序》。其实,即使是传世的第一代临摹本,也没有明确标识是何人临摹,多是后人臆测。如虞世南临本就是董其昌鉴定,而董其昌常将一些不知名的作品归于大家名下;褚遂良摹本则是米芾所定,但也有人认为是米芾临写;冯承素摹本是元代郭天锡所鉴:“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23)郭畀:《快雪斋集·附云山日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第14页。郭天锡说的是“冯承素等”,只是在后来的传述中逐渐简化省略,尤其是明代项子京强加以“冯承素奉敇摹”之名,就变成了冯承素摹本。《兰亭序》究竟是谁临摹的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这些文本能带给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即各种《兰亭序》文本的文化包容力和艺术创造力。1000多年来,《兰亭序》不断汲取历代书家的笔法精华,形成一个以王羲之为核心的《兰亭序》书法体系。这个体系的文化包容性和艺术创造力是历史上任何书家的任何作品都无法比肩的,所以,后世书家对王羲之和《兰亭序》顶礼膜拜。
三、帝王推崇:《兰亭序》在传承中至圣地位的进一步彰显
艺术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受环境影响很大。丹纳认为:“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24)[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9页。而影响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统治者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书法是与统治者关系最密切的艺术形式,所以受其思想影响最大。《兰亭序》受到几乎所有爱好书法的帝王的一致推崇,并因此而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王羲之身后的南朝,其书名一度被少子王献之所掩。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开始收集二王书法,到宋明帝刘彧时,内府收藏已超过200卷。梁武帝萧衍进一步搜求,共得二王书迹78帙,计767卷,15000纸。此时,因为梁武帝的推崇,王羲之已经摆脱不如其子的尴尬,但是还没有上升到“书圣”的地位,而且《兰亭序》一直没有出现,这大概是王羲之书法在南朝非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即人们对于王羲之的推崇还缺乏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
唐初,因为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天下出现搜求王书高潮,《兰亭序》终于出现。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几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搨书人汤普彻等搨《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25)张彦远:《法书要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1页。《兰亭序》完全符合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成为“书圣”的条件,如字数多、书风新、文辞美等。所以,太宗倾满朝书家之力,大力推崇《兰亭序》。《兰亭序》自进入内府至贞观二十三年陪葬昭陵,面世只有短短十年,遂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在书法界的地位愈加神圣。李世民对《兰亭序》爱不释手,心慕手追,烂熟于心,其作品《温泉铭》雍容华贵,润朗丰满,字势奇崛,起伏跌宕,应该是受到《兰亭序》的影响。当时的书法大家虞世南、欧阳询等早已成名,书风很难再有变化,他们临摹《兰亭序》多是为完成皇帝敕命,不是艺术的自觉追求,而李世民对《兰亭序》的追慕却是一种艺术自觉。可见,李世民才是王羲之书法的真正传人。
经过李世民推崇,王羲之和《兰亭序》在唐代书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以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奔走天下。世谓唐初犹有晋宋余风,学晋宜从唐入者,盖谓此也。”(26)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7页。李嗣真《书后品》进一步指出:
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犹雾谷卷舒,烟云炤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忽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27)张彦远:《法书要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147页。
王羲之此时被誉为诸体皆工无所不能的书法圣人,这是对李世民推崇王羲之的进一步强化,即推崇不再局限于《兰亭序》,而是扩大到王羲之的书法体系。这一过程的变化正是王羲之受帝王推崇后艺术境界不断升华的结果,是一种艺术典范的确立。
然而,李世民对《兰亭序》的推崇最终随着五代温韬盗唐陵的发生而烟消云散。欧阳修云:“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乱,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28)桑世昌:《兰亭考》,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据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郑文宝《江南余载》等文献记载,确有温韬盗昭陵得钟王墨迹之事,但只有《江南余载》提到郑元素曾见过《兰亭序》。到了元代,刘有定为《衍极》作注时则有了另一种说法:“或云《兰亭》真迹,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温韬发掘,取金玉,弃其纸。宋初耕民入陵,纸已腐,唯石刻尚存,遂持归为捣帛石。长安一士人见之,购以百金,所谓古雍本也。”(29)郑杓撰,刘有定注:《衍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0页。刘注以“纸已腐”来解释前面几种文献提到的《兰亭序》不知所踪,应是受到欧阳修“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说法的影响,并不可信。总之,《兰亭序》经过这样一段故事便更加神秘,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也因之而更加稳固。
宋代皇帝多为书画爱好者,对于《兰亭序》的推崇也更加突出。宋仁宗曾临写《兰亭序》,作品工整有余而活力不足,与唐初临摹本的面貌相差甚远,但这毕竟是在宋初《淳化阁帖》不收录《兰亭序》的情况下对其所作的正面弘扬。后来的宋徽宗、宋高宗父子,更是不断抬高《兰亭序》的地位。宋徽宗诏令蔡京等在《大观帖》中摹刻《兰亭序》,以弥补《淳化阁帖》不收《兰亭序》之憾。文献记载宋徽宗有《兰亭序》临本传世:“真书《禊序》于青缯中,虽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蓝而已。”(30)楼钥:《恭题宇文绍节所藏徽宗御书修禊序》,《楼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89页。宋徽宗的《兰亭序》以楷书写就,非是全力临摹,已有意临和创作之意。宋代真正受到王羲之书法影响的是宋高宗赵构,他一生浸淫汉魏六朝书法,尤其钟情于《兰亭序》。他到处搜求《兰亭序》,曾命人索求褚摹本:“闻知会稽县向子固有褚遂良所临《兰亭叙》,后有米芾题识,卿可取进来,欲一阅之。十四日。付孟庾。”(31)胡世安:《禊帖综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97页。他在《翰墨志》中自述个人学书体会:“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32)赵构:《思陵翰墨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8页。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太子临写《兰亭序》:“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有披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笃学如此。”(33)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页。在几代帝王的推崇下,宋朝士林掀起研习《兰亭序》的热潮。且当时刻帖技术先进,社会上收藏《兰亭》帖蔚然成风,从帝王贵胄到公卿士子,甚至一般市民,都热衷此道,这成为南宋收藏界的一大奇观。《兰亭序》从唐代的宫廷书法变成了社会书法,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通过刻帖感受《兰亭序》的魅力,这对于《兰亭序》的普及和推广大有益处。但是,这也造成了传播的泛滥,《兰亭序》原有的神秘和高妙完全化为乌有,对于《兰亭序》的认识便开始走向形式化。这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巩固非常不利,《兰亭序》逐渐走下神坛。
清代的康熙和乾隆是最后托起《兰亭序》神圣地位的帝王,他们不仅认真临摹,更御书题碑,并亲自造访兰亭旧迹。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圣祖御书《兰亭序》,刻于石上,三十七年(1698年)又书“兰亭”二字悬于御碑亭。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亲自前往兰亭遗址,并作诗一首,命人刻于康熙御碑之后。至此,历代皇帝对于《兰亭序》的推崇已达极限,当时学习王书和《兰亭序》者比比皆是,形成宏大规模。此后,因为刻帖传播的泛滥和碑学的兴起,《兰亭序》在书法界的地位开始动摇,但仍是书法家心追手摹的对象。
在这种状态下,学界出现了对于《兰亭序》真伪的讨论,从清代李文田、阮元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都是在《兰亭序》走下神坛之后而出现的学术争鸣。这种争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对于《兰亭序》艺术生命力的挖掘和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历代帝王对《兰亭序》的推崇只是研习探索现象的一部分,还不是《兰亭序》受到推崇的全部。但是,帝王的推崇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使《兰亭序》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期受到文化精英的关注,不断被注入新的活力,最终形成艺术膜拜与推崇的强大推动力。在这种推动力的作用下,《兰亭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王羲之也在这种推崇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唯一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