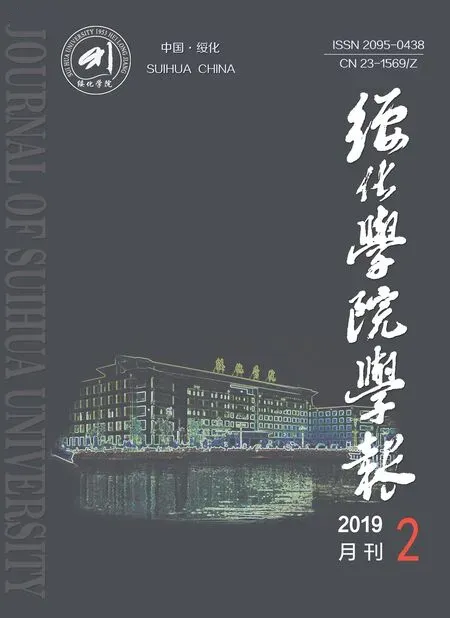浅析量词“枚”的形成及其认知语义特点
袁 静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量词丰富是现代汉语的一大特点,而汉语中量词与名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量词“枚”为例,重点探讨量词“枚”的认知语义特点,并考察其与所称量的名词之间的规律。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量词都是从其他词类演变过来的,即由一些有实在意义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的成分的实词虚化的过程。现代汉语量词“枚”就是这样,是由有实在含义的名词逐步虚化为量词的,这种语法化过程就是语义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分析量词“枚”的认知语义特点,首先应当对其语法化化过程进行全面考察。
一、量词“枚”的语法化过程
(一)量词“枚”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对“枚”这样释义:“枚,干也,可为杖。”[1]段玉裁注:“攴,小击也。……杖,可以击人者也。故取木、攴会意。”“枚”的本义即树干,特点是小而细长。《诗·周南·汝坟》中有“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毛传:“枝曰条,干曰枚。”这里“条”和“枚”都是动词“伐”的宾语,表示“树干”。从先秦时期的文献来看,“枚”的意义后来多引申为占卜或计数的工具,如:
(1)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春秋左传》)
(2)南蒯枚筮之。(《春秋左传》)
(3)书其枚数。(《春秋·墨子》)
(4)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於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於此乎?(《春秋左传》)
从以上例句我们推知,“枚”由本义“树干”引申为“占卜或计数的工具”,如“枚卜”“枚数”等,我们推测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树干”的“枚”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可以随时获得,所以用来作为计数工具是极为方便的。后来随着先民对数的概念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枚”也就从“树干”的意义发展出了数量的功能。
从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我们发现“枚”作为称量“树”的量词的例子是很少的,张万起先生只举出《汉书》和《后汉书》中的四例[2],而汉初“枚”作为泛指量词已经十分广泛,即称量“树”以外的名词的例子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我们不能证明量词“枚”来源于其本义“树干”。刘世儒先生认为,本义为“树干”的“枚”首先引申为计数的工具,再引申为“算筹”的意思,最后由“算筹”义引申为量词。[3]由于“算筹”义并不区分具体的某类事物,所以量词“枚”就具备了泛指量词的语义基础。
对于量词“枚”的产生时间,张万起先生认为“量词‘枚’产生于汉代初期或更早些时候[2],据先生考察,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墨子》中有量词“枚”的用例,如“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其他十几部文献中均未发现,因此,我们推测,“枚”起初作为量词出现可能只在极个别地区使用,且在汉代前,“枚”作为量词的用法已经有了萌芽的性质,到了汉代才有了相当的发展。
(二)量词“枚”的发展。
1.两汉时期。上文提到,《汉书》和《后汉书》中只有四例表示量词“枚”用于称量“树木”,其他大部分语料都用于称量“树木”之外的动物、植物、衣物、器物等多种事物,如:
(5)七回光雄肪发泽一盎,紫金被褥香炉三枚。(《赵飞燕外传》)
(6)而无功德者,不能得谷一斗,钱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史论·太平经》)
(7)是岁犍为得石磬十六枚。(《史论·前汉纪·荀悦》)
(8)隻,鸟一枚也。(许慎《说文·隹部》)
例(5)中量词“枚”称量“香炉”,例(6)中量词“枚”称量“钱币”,例(7)中量词“枚”称量“石磐”,例(8)中量词“枚”称量“鸟”。
2.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枚”进一步发展,可以称量的名词几乎到了不受限制的地步,不仅可以用于各种事物和动物,还有少部分用于指人。如:
(9)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西京杂记》)
(10)三棺遂有竹杖一枚。(《抱朴子·论仙》)
(11)宫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上杂物疏》)
(12)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宋书·明帝纪》)
(13)於嵩庙所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全刘宋文》)
(14)於万山中采药,忽闻异响,从石上得铜钟一枚。(《全梁文》)
(15)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齐民要术》)
(16)选取好桃数十枚,擘取核。(《齐民要术》)
(17)有一大树,高数十丈,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上。(《搜神记》)
(18)唯玉蟾蜍一枚。(《西京杂记》)
(19)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长五六寸许。(《述异记》)
例(9)至例(14)中的量词“枚”分别称量器物或日常用品,如:“铜剑”“竹杖”“象牙尺”“金钗”“玉璧”和“铜钟”,例(15)和例(16)中的量词“枚”分别称量瓜果子实“赤小豆”和“桃”,例(17)和例(18)中的量词“枚”分别称量动物“黄鸟”和“玉蟾蜍”,例(19)中的量词“枚”称量人物“小儿”。
3.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这个时期量词“枚”的应用范围逐渐缩小,张万起先生考察了唐代30 位诗人的诗集作品,只在王梵志的诗中有发现有2 例。[2]南宋的《朱子语类》,共230余万字,但量词“枚”只出现了4例,而且只能用来称量小物品。[4]而明清时期量词“枚”的使用范围就更小了。我们推测,这极有可能是因为进入唐代后量词“枚”逐渐被量词“个”所代替,而且随着语言系统精细化的的发展,出现了分工较为明确的不同量词,因此量词“枚”的使用范围逐渐萎缩。
4.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枚”。量词“枚”在现代汉语中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中对量词“枚”的用法总结了三点:①计量形体小的东西。如:三枚奖章、一枚金牌、一枚钉子等。②计量弹药。如:一枚炸弹、一枚火箭、一枚导弹等。③计量硬币。如:一枚铜钱、三枚银元、五枚硬币等。[5]个体量词“枚”已经被其他专用量词或通用量词“个”替换。如“三枚金牌”,我们一般说“三块金牌”;“十枚子弹”,我们一般说“十发子弹”;“三枚邮票”,我们一般说“三张邮票”等。在现代汉语中,量词“枚”更多地运用到书面语中,一般在口语中不经常出现。不过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网络平台的推动,量词“枚”又重新活跃在大众视野中,例如“帅哥一枚”“香吻一枚”“吃货一枚”等。
从以上对于量词“枚”的语法化考察中,量词“枚”是表示“树干”义的名词“枚”语法化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再到唐以后,量词“枚”的使用范围呈现出先扩大后萎缩的过程,到现代汉语时期又有了复活的迹象。
二、量词“枚”的认知语义特点
(一)量词“枚”范畴化分析。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事物,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也在不断出现。语言同样是这样,它会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但另一方面人们大脑的认知能力却是有限的,所以当新的语言现象出现时,我们就会依据已有的经验对其进行分类和命名,人们对客观对象进行分类的这种认知过程就叫做范畴化。[6]57同样,我们在使用量词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外在形状,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根据事物的形状来给量词划分不同的类别,从而进行范畴化。同时,从历时角度来看,由于量词的来源基本上是名词,因此,量词对名词的选择也就是量词对名词所表示的客观事物进行范畴化的集中表现。其次,认知范畴理论认为,在同一个范畴内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同一个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它们可能在某个方面是相似的,但却不是完全一样的,这种语言现象就叫做“家族相似性”。[6]59因此,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事物就会被划分到同一个范畴中。
“枚”的本义是“树干”,所以量词“枚”范畴的原型成员即范畴中心应当是具有名词“枚”特点的词,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名词“枚”来说,它的语义中包含有三个义项,即[+小]、[+细]、[+长],那么当它虚化为量词后,它所称量的名词范畴的共同特点就是“小而细长”,那么这就把量词“枚”所称量的名词放在了同一个范畴里,它们的家族相似性就是“小而细长”,当一个新的名词出现时,我们就可以根据“小而细长”这一家族相似性对其进行考察,确定其是否可以与量词“枚”相搭配。但从以上各个历史时期的例句来看,我们发现,量词“枚”所称量的部分名词并不具备家族相似性,有的只具备其中一种或两种,这类名词就不属于量词“枚”范畴的原型成员,它们处于量词“枚”范畴的边缘上,是通过认知方式中的隐喻来归入量词“枚”的范畴的。
(二)量词“枚”的隐喻分析。上文我们主要运用范畴化理论对量词“枚”进行考察,我们知道,量词“枚”对于其后面名词性成分的选择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也不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认为,这其中隐喻等内在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将从隐喻的角度对量词“枚”进行分析,寻找量词“枚”对于名词性成分选择上的理据性。
隐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就是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说从一个认知域(来源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6](P321),即用一种概念来表达另一种概念。通俗地说,就是指人们用自己已经熟知的、具体的的经验或概念来理解并不熟知的但有关联性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概念的一种认知活动。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隐喻并不是修辞格,它和比喻是截然不同的,隐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认知方式,它产生的基础是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指的是人们通过认知领域里的联想发现的两种概念之间的共同特征,并不是指两个同类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因此,这种认知方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量词“枚”的本义是指“树干”,这种“树干”并不是指粗壮的树干,而是指细小的树枝,其主要特点是小而细长。[7]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量词“枚”在汉代可以修饰钱币,如“钱一枚”;在魏晋南北朝可以修饰“铜剑”“竹杖”“尺”“金钗”等。那么,量词“枚”是如何由“小而细长的树干”这一本义虚化成为量词来称量以上的事物呢?这正是隐喻这种认知方式在发挥着作用。“小而细的树干”具有“小”“长”“细”的特点,而“钱币”“铜剑”“竹杖”“尺”“金钗”等这一类事物在人们的认知里也大多具有细长而短小的特点,人们通过隐喻这一认知方式找到了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似处,因此可以用本来指“树干”的“枚”通过隐喻来称量同样具有“小”“长”“细”这三种特点的事物。
后来随着量词“枚”的进一步虚化,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的量词“枚”所称量的事物范围逐渐扩大,某些不具有小而细长特点的事物也可以被量词“枚”来修饰,如上文例句(15)和例(16)中的“赤小豆”和“桃”,它们都具有“小”的特点,但是不具备“细长”的特点,但是仍然可以受量词“枚”的修饰,这其实就是认知领域里的隐喻在发挥作用,即认知域与目标域之间有了相似性,虽然“赤小豆”和“桃”并不属于量词“枚”所属的范畴中心,但它们处于量词“枚”扩展的范围上,所以也可以被称量,这就使得量词“枚”称量的范围越来越大。
上文提到,量词“枚”可称量的名词范围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扩大、唐以后的萎缩后,发展到现代汉语,由于网络平台上的传播,又出现了重新活跃的迹象,经常用来修饰与人有关的名词,如“美女一枚”“吃货一枚”“帅哥一枚”等等。
(20)不化妆也是美女一枚,清新透气。(快资讯2018年5月4日)
(21)作为一枚吃货,如果你连南瓜腊肠饭都没有吃过,那就太不合格。(今日头条2018年6月11日)
(22)前方发现大帅哥一枚:肖战为古装而生,因北堂墨染圈粉无数!(今日头条2018年6月14日)
从例句中我们发现,由量词“枚”修饰的“美女”“帅哥”以及“吃货”并不具有“小而细长”的特点,那么为什么可以用“枚”来称量呢?其实这是认知经验在发挥作用,由于“枚”具有“小而细长”的语义特征,因此给人一种可爱、亲切的感觉,而在以上例句中,“美女”“帅哥”以及“吃货”这三个词的表达效果也是一种亲切、温馨的活泼感,这时两种概念就有了相似性,根据隐喻这种内在因素就顺理成章地用量词“枚”来称量这些词,这是心理上的认知经验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总之,从认知规律上看,人类最初认识世界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具体有形的事物,随着认知的发展,就有了参照已有经验来表达新的概念的能力。所以随着人们认知的提高,量词“枚”所称量的名词范围逐渐扩大,依据隐喻这种认知方式,就有了从称量具体事物转化为称量抽象事物的能力。
三、结语
本文首先从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五代及宋元明清时期、现代汉语时期五个阶段对量词“枚”的语法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之后从范畴化以及隐喻的认知方式分析了量词“枚”的认知语义特点,我们发现,人类认知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到量词“枚”和其所称量的名词之间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搭配也不是任意的,具有一定的理据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通过注重从认知的角度寻找量词和其所称量的名词之间搭配的重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