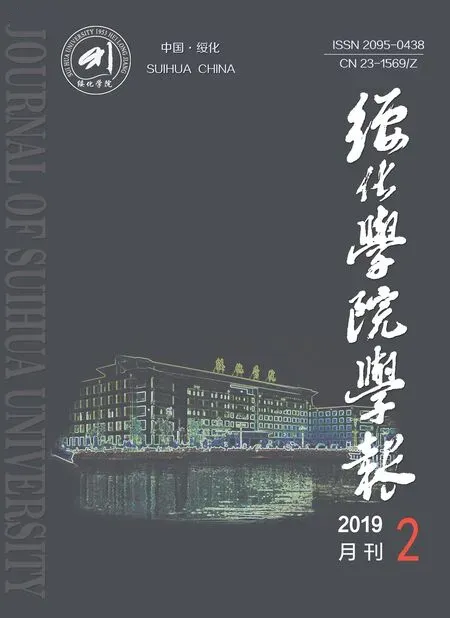太宰治《惜别》中的青年鲁迅形象
李玉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北京海淀 100089)
二战时期,日本出版了三部关于鲁迅的著作,分别是1941年小田岳夫的《鲁迅传》、1944年竹内好的《鲁迅》和1945年太宰治的《惜别》。其中,只有《惜别》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叙述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在仙台留学时不为人所熟知的一面。为了创作《惜别》,太宰治阅读了大量鲁迅本人创作以及关于鲁迅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经历了细致的考察和请教,甚至亲自赴仙台取材。同时,《惜别》释放着细腻丰富的情感,太宰治以他擅长的心理描写刻画鲁迅,写出鲁迅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波动,在传记的真实性和小说虚构性之间,创造了独特的“太宰鲁迅”。《惜别》描写青年鲁迅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台的留学生活,通过鲁迅的朋友“我”(医师田中卓)的回忆,讲述了青年鲁迅到仙台学医,后弃医从文的经历。太宰治“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打算仅仅描写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1](P135)。《惜别》让人了解到鲁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鲁迅不仅有中晚年的尖锐、严厉,还有青年时的孤独、彷徨和激情。《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是潜藏自我意识的孤独者,忧国忧民的批判者,陷入医学、文艺、革命旋涡的彷徨者,力挽狂澜的革命者。
一、潜藏自我意识的孤独者
奥野健男认为:“太宰治对拥有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并潜藏着自我意识的鲁迅有特别的亲近感。”[2]在《惜别》中,青年鲁迅以腼腆羞涩的孤独者的形象出现,“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很沉默”。[1](P5)跟“我”初次见面时,他“白净的脸变得通红,很害羞地笑了”,[1](P18)跟“我”谈天时,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1](P19),“脸微微有些发红”[1](P22)。他“似乎很喜欢孤独这个词”,他一边自言自语着“Einsam(德语,孤独),一边看着远方思考着什么,突然说:“但我是Wandervogel(候鸟),我没有故乡。”[1](P21)鲁迅幼年时父亲去世,从此全家各奔东西,自幼无依无靠,“虽说故乡仍在,但宛如没有。在相当不错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家,就必须要看到‘人世’的根本面目。我寄居在亲戚家,被说成是要饭的。可是,我没有服输,不,说不定已经服输了。”[1](P23)在“我”看来,当时周先生一定实在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那种孤独寂寥,于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与家乡附近的西湖风景相似的松岛,但还是不能解除忧愁,又无意间遇到了日本医专的学生(“我”),就真诚地想结交朋友。[1](P22)新的学年,鲁迅从东京回到仙台后对“我”说:“我最近是Kranke(病人),所以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成了Einsam(孤独)的鸟。”[1](P101)
青年鲁迅的孤独感与他的自我意识是分不开的:“同样羽色的鸟,如果汇集数百的话,反而看起来猥杂,因此有种同类相互嫌弃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总也是清国留学生,还曾经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拔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1](P41)“我渐渐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们在一起了。”[1](P43)“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暂时脱离留学生群体,单独生活。也许是自我厌倦吧,一见到自己同胞们漫不经心的面孔,就感到羞愧、可恨、无法忍受。啊,我真想到一个支那留学生都没有的地方去呀。”[1](P47)“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1](P108)正如川村凑所说:“周先生置身于革命的旋涡中,对于实践革命运动的人们,‘私’的不和谐感不可避免地强烈起来。”[3]
二、忧国忧民的批判者
鲁迅在松岛第一次与“我”见面时,二人一同欣赏松岛的风景,此时鲁迅的言辞中就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文学的不满:“我不相信我国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而且很堕落。”[1](P26)鲁迅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1](P28)但是,鲁迅的批评源于他对国家的热爱,正如“我”和鲁迅所说:“您也正是因为过于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评价的标准才会这样严格吧!”[1](P26)“真正的爱国者,反而会经常说国家的坏话。”[1](P26)“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1](P29)随着与“我”交往的深入,鲁迅对中国的批判也愈发深刻,他不满清国的现状:“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强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帝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现在的清国,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1](P29)鲁迅还看清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1](P36)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糟粕也提出批评:“在支那,‘孝’原本就是包含着政策意味的,被统治的人从早到晚都战战兢兢,很夸张地孝顺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那样愚蠢的传说流传在民间。”[1](P86)鲁迅认为老莱娱亲“是Wahnwitz(德语,“精神错乱”),不是正常的精神行为”。[1](P86)在谈到郭巨埋儿时,鲁迅说:“我突然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者先生们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1](P87)因此,“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1](P33)鲁迅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连平日敬佩的藤野先生也不例外,“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1](P106)
鲁迅虽然怀抱救国的志向学习西方文化,却能够批判地看待西方文化,他不满基督教“装腔作势”的姿态:“周先生和我一样,敬重基督教的邻人友爱,对于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宿命也深表同情。周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看不惯教会职业牧师那伪善家一样的悲怆表情,以及往来于教会的青年男女的装腔作势的态度,因此对于大量散布在仙台市内的教堂采取了敬而远之的策略,尤其是周先生他们断定耶稣的使者不是真正的耶稣,如同支那的儒者先生们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样,外国的传教士也使基督教堕落了。”[1](P101)“我现在的确是Kranke(病人),于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过,对于西方夸张的礼仪,还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1](P102)“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1](P106)
三、陷入医学、文艺、革命旋涡的彷徨者
为了挽救中国的危机,青年鲁迅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他“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所以“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1](P37)于是他决定留学日本,想到自己即将在日本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1](P40)可是不久,当他到达弘文学院学习、遇到不务正业的清国留学生时,渐渐从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还常常会被往昔的疑虑和忧郁所笼罩。[1](P41)他“打算暂时离开东京,忘却往事,独自研究医学,已经不容再迟疑了。”[1](P47)
青年鲁迅是带着远大的理想来仙台的--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挽救那些不幸的病人。[1](P66)“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1](P29)“告诉我新学问必要性的,是少年时代遇到的那个骗子医生。那时的愤怒,使我离开了故乡。学习新学问的志向,从开始就与医术紧密相连。我首先在日本学习医学,回国后,治愈那些同我父亲一样受庸医蒙骗、只能等死的病人,让他们了解科学的威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早日从愚蠢的迷信中清醒过来。如果支那同外国交战,我将以军医的身份参战,为建设新支那不惜粉身碎骨,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1](P46)
鲁迅在二年级的夏天去东京时接触到了日本青年掀起的文学热潮,便开始畅游于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回仙台时他带回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文艺热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里的是本国青年们的革命呐喊。医学、文艺、革命,换句话说,科学、艺术、政治,他被卷入三者的混沌旋涡中。”[1](P114)从东京回到仙台后,鲁迅不无迷茫地对“我”说:“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1](P108)“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1](P109)鲁迅最终选择了文艺。太宰治在《惜别》中借“我”之口,细腻地描写了鲁迅内心的彷徨,“周先生后来大量的著作,我几乎都没有读过。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大鲁迅文艺的功绩。可是有一点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台时代的周先生,苦于近代文明之病,为寻求其病床,甚至叩响了教会之门,可是,那里也没有救济之法。像往常一样,他又退了下来。懊恼的结果,这个品质高尚、正直的青年,脸上甚至浮现出了奴隶的微笑。混沌的产物是自我厌恶。他对于文明的感情,的确可以称之为支那可怜的先驱者之一。这样,这种痛苦内省的地狱,越来越接近所谓人间百感图的文艺了。文艺原本就是他喜欢的路,疲惫的他爬上了这个病床,稍感舒适。”[1](P115)
四、力挽狂澜的革命者
《惜别》虚构出的“大雪夜事件”体现了鲁迅作为革命者的一面。在一个大雪之夜,鲁迅在美以教堂听到《出埃及记》的说教内容——摩西为了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去往迦南,四十年间历尽艰辛,却受到同胞们的曲解和责怪。鲁迅联想到祖国愚昧无知的民众,打算弃医从文。“文艺好像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便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表面看文艺不过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兴亡没什么关系,可其的确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无用之用,不可小视。……想找到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支那语,让我的同胞们读。”[1](P116)
在经历了幻灯事件后,鲁迅告诉“我”:“亏了那张幻灯片,我终于下定决心了……精神革新!国民性改造!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支那将永远无法确立真正的独立国家的尊严。灭清兴汉也好,立宪也好,只是改变了政治口号而已,东西的质地不变,不是没有用吗?因为我这段时间离开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众,心里就定不下来明确的目标,迷茫、不知所措。今天我的目标确定了。看了那个片子,挺好。我马上弃医回国。”[1](P124)鲁迅打算回国之后发起文艺运动,来改变那些民众的精神,为此奉献一生。他将和作人一起办文艺杂志,而杂志定名《新生》。“他微笑着回答。那笑中一点儿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称之为‘奴隶的微笑’那种卑屈的影子。”[1](P125)
在《惜别》中,太宰治借“我”解读1907年鲁迅写于东京的论文《摩罗诗力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1](P118)《惜别》的这段话,与竹内好那种极大地误读了《摩罗诗力说》的“无力的文学因为无力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批判”[4]的“革命文学迟到论”相比,真正理解了鲁迅的文学观和革命观。
结语
在《惜别》中,太宰治借藤野先生之口说:“我想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历史的开花结果。应当称作‘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潜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延续着。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们东洋人都连接在一起,可以说背负着共同的命运。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家庭,尽管人各有志,却还是一朵大的花儿。”[1](P68)《惜别》曾一度被贴上“国策小说”的标签: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太宰治参加完文学报国会召开的作品协议会后,便写下了近6页的《惜别》创作意图说明书并上交给文学报国会,表示愿为实现中日两国全面和平共处效力。一向不理会日本政治的太宰治的“政治意图发言”的行为显得不寻常,太宰治却说:“这本《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进行创作的小说。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总有一天我也会试着写一写,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进行了。”[1](P128)发表于二战结束前夕的《惜别》,看似不违背军国政府的意图,实际上太宰治并非迎合时局,也不支持战争。《惜别》中的送行会赋予了鲁迅的仙台生活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宰治在小说中抚平了生活给青年鲁迅造成的心灵创伤,太宰治于鲁迅的友善同时表现为对中国的友好,正如《〈惜别〉之意图》所说:“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1](P136)这种创作意图体现了藤野先生所说的包容了互相尊敬、爱与正义等内容的“东洋本来之道义”。通过《惜别》中的青年鲁迅形象,太宰治表达了对鲁迅的尊敬和对中国的友好,这种写作姿态唤起读者的钦佩。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