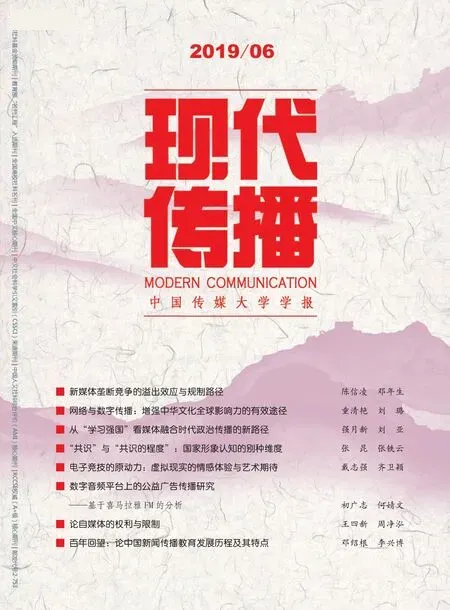“看”与“见”的辩证:认知视阈下纪录片创作方法论刍议*
■ 谷 李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认知科学的深入发展以及被越来越多的学科吸收借鉴,从认知的视角探究人类创造性活动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的前沿。如萨迦德所说,解释“人体验到的对于创造性的自我意识”是认知科学的“终极挑战”①。许多人文学科对认知科学的引入和吸收产生了广阔而丰富的成果,例如认知诗学②、认知叙事学③、神经电影学④等。近年来,我国传播学者也试图从不同角度和切入点将认知科学与传播学进行结合并产生了一定成果。与此同时,对纪录片创作实践和教学进行科学、系统的总结这一任务也要求我们在以往个体的、经验的模式基础上进行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把握。我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孙增田曾说:“(纪录片)记录的应该是思想的过程,展现的应该是思考的脉络。这样,我们从纪录片中,才可以观照自己,认识世界……不能见什么拍什么,不假思索。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也不能离开了思考和选择,只是这种思考藏得比较深。拍摄过程,随时都在检验我们的认识和判断。”⑤这段话既生动地揭示了纪录片创作实践中包含复杂多样的认知活动(“观照”“认识”“思考”“判断”乃至“思想的过程”“思考的脉络”等),又提出了对这些认知活动予以深入把握的要求。
综上,对纪录片创作这样的创造性活动进行认知研究,从而逐步揭示其中涉及的认知运作,既是认知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纪录片创作和纪录片研究发展的必然方向。关于“怎样才能看见”以及“怎样才能看见他人所不见”的问题事实上涉及了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既创新又真实的纪录片创作何以可能?——而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入认知的层面:如果真实是确实存在的,那么为何有的人会“看见”,有的人会“看不见”?创作者要怎样才能“看见”?诸如此类的问题,亟待回答。
二、纪录片创新之源:“看”与“见”的辩证
从创作者的角度看,成功的纪录片能够带给观众一种认知意义上的通透:一方面,创作者通过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承载着痕迹的证据来提出关于真实的命题,另一方面,经由创作者建构的形象,观众发现某种意义上的真实被揭示出来(“我也看见了!”)。因此,组织影音证据和提出可辨识的真实命题是纪录片创作者的中心任务。而创作者能够“看见”(痕迹/真实)则是这一中心任务的前提和基础。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淆,我们需要明确指出,这里的“看见”“盲目”“观看”不等于生理的、光学感知意义上的视觉行为,而是作为一般认知行为的隐喻。“看”不(仅仅)是视觉动作,而是携带着视觉中心主义的历史性偏颇而与知识生产密切相连,成为一般认知的代名词。以“看见”一词自身的意涵为例:作为探求、摸索的隐喻,“看”强调过程的开启,“见”则强调活动的效果——探索并非徒劳无功,而是颇有收获;在“看”与“见”之间展开的缝隙是富有创造性的张力:“看”未必“见”,但没有“看”就不会“见”;“看”是“见”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见”之或然性正对应于纪录片“真实”的或然性。那么,怎样看,才能有所见?何为看见?
2016年9月27日,来自西太平洋的热带台风梅姬正面登录台湾地区,以最高220公里的时速肆虐了10小时,造成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以及估计价值数亿元的经济损失。那天傍晚,一位名叫欧家瑞的业余摄影师在海边的台风中待了大约一个小时,用500毫米镜头拍下了一组照片。第二天,当欧家瑞把他的照片发到他的脸书账户,其中的一张引发了大众和媒体的持续关注。在这幅照片的左侧,是伫立在茫茫大海中的一片礁石,礁石的右边海面之上,一片海浪翻卷腾空,犹如一个女性头部的侧面轮廓:“她”背对着礁岸,面朝海洋的方向张着嘴,仿佛正在大声喝止肆虐的风暴。人们在报纸、电台、电视节目中热烈讨论:照片里的头像正是妈祖;在台风中,妈祖显灵了!如果我们可以同意说,图片中翻卷的海浪像是女性的侧面头像,我们有什么依据说那个女性就是妈祖,并将台风中的这一影像称为妈祖显灵?——此处的要点不在于民众是否“迷信”而在于认知:毕竟,没有人见过妈祖这位传说中庇护渔民和海上安全的人神,那么当人们聚集在这幅图片周围,情真意切地辩称“那就是妈祖”“妈祖显灵了”时,其中的指认和判断所暗含的“看见”包含了怎样的认知结构和过程?“看见”是怎样发生的?
美国传播学学者Briankle Chang在近作中提到以上这一则故事⑥。Chang在文中指出,这个故事为我们揭示出“看见”涉及的一个关键转换:那就是从“看见”(see)到“看作”(see as)的转换;由于这个机制,在上述案例中,海浪被看作女性头像,头像被认作妈祖,整个影像及其发生背景被定名为妈祖显灵。重要的是,Chang强调,这是在一切观看行为活动中的转换机制,其中包含着阐释、替换、投射,因而绝不仅仅是一条制造误解的链条:“看作”蕴含在一切“看见了”的确认中。Chang认为,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在观看行动以及被看见的事物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把将被看见之物由内向外投射,从而使之变得可见(visible);换言之,在我/眼睛(I/eye)实现“看见”之前,关于“可见之物”,投射机制已经打过了“草稿”。由于这一机制以及“被混淆的因果”认知,不仅我们所见的是我们要见(look for)乃至想见(want to see)的,我们更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客观的,它先在于我们的“观看”并且独立于“观看”而持续。
从海浪的影像到妈祖形象,在Chang看来,这其中的转换涉及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幻想”(productive fantasy),它使得人们看见自己相信的,而这一貌似荒谬的案例也揭示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看—认知机制,即“相信即看见;因为相信(believe in),因为想见(wish to see),于是看见”。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相信”和“想见”并非采取“唯心”的立场,因为同样需要强调的是“相信”和“想见”绝非纯粹主观的活动——恰好相反,如同在本案例中那样,它们是媒介技术和文化影响下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例如,长期以来人们对摄影这一影像技术所持有的信任,再例如,在妈祖文化传统中一脉相承的图像要素的世代积累(女性、海浪、二者间的对立等)。从认知发生的角度看去,正是这些技术的、文化的元素一方面累积成为人们的习性(habitus)或知识型(episteme)构成,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界定出“可能的”“不可能的”“可信的”“不可信的”“适宜的联想”“不当的替换”等基本想象范畴,一方面构建我们的图像库(iconological repertoire),而二者的互动形成的识认图式(scheme of recognition)使我们可以生产出“X像Y”,或“Y就是X”这样的命题和判断(“看见”)⑦。
迪迪-于贝尔曼在《看见与被看》中重构了一个弗洛伊德初次描述的实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作”这一机制在人类早期经验中的浮现。⑧这一实例由两个场景组成,主角是一个此时无人照看的幼儿,配角是不在场的母亲,道具包括几样小物件,都是能帮这个幼儿排遣孤独的,比如一个玩偶、一个木纱轴、一块积木或幼儿的床单。在第一个场景中,幼儿看着眼前的物件,仿佛在等待什么,但我们无法知晓他看见了什么或是他以怎样的方式在看;在第二个场景中,幼儿——或许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玩耍木纱轴(或别的物件):他“看见它,抓在手里,摸它,然后不想再看见它。把它扔到远处:它消失在帐幔后。他像在海中钓鱼一样用一根线又把它拉回来,回来的它看着他。”当木纱轴消失时,幼儿面露焦急或许还拖长声音发出一个不变的“噢—噢—噢”的声音,当木纱轴再次出现时,他则“高兴地发出一声‘达’!(在了!来了!)”。假设我们观察到这一切,我们看见了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情景被弗洛伊德和后来的一些学者大书特书。弗洛伊德认为在这一情境中发生的是“象征的诞生”——无论木纱轴在形态上与母亲如何迥异,当幼儿把它扔开又拉回的时候,木纱轴实际上成为了不在场的母亲的替代品:不是说它在功能上帮助幼儿驱散了孤独,而是说它和母亲一样地消失和回归,而且,它带来了母亲所没有给予的惊喜,由于那一条纱线,幼儿得以控制木纱轴消失和回归的节奏,这个节奏给他带来愉悦,所以他对这个游戏兴致盎然、乐此不疲。显然,这样的发现与弗洛伊德潜心探究人的无意识世界这一问题意识取向密切相连:人具有的象征能力是怎样获得的?作为他的理论大厦的基础性问题,是这个疑惑引导着他的观察和阐释(“想见”),帮助他在上述情景中“看见”象征行为在个体早期经验中的诞生。同样是面对这个场景,别的理论家发现了不同的真实:试图厘清言说与精神的理论关系的拉康看见的是语言的迸发,乃至个体最初语言能力的出现;而强调媒介物质性的迪迪-于贝尔曼聚焦于幼儿对差异的生产和感受,并将这一场景归纳为个体生产力的最初感受。
以上两个案例,一个属于大众文化,一个属于科学研究,将其中的“看见”并列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相同之处。首先,在其各自的“看”与“见”中,前文提到的“看作”(see as)结构都被激活,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在“看”的行为中进行特定的转化并生产出特定形象(海浪—女人—妈祖;木纱轴—母亲—象征力;幼儿玩木纱轴—象征力的诞生);其次,这一转化的发生有赖于特定的认知基础,即前文所说的“草稿”或识认图示——任何“看见”都会动员识认图示,识认图示在“看见”中曲折延伸;最后,“看见”的发生有赖于证据,即外来信息或数据的刺激乃至压力:如果没有外来信息或数据的刺激,或者外来信息或数据不产生刺激或压力,也就是如果它们完全符合已有的识认图示,那么在显著认知意义上的“看见”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本文讨论的“看见”,其实质就是对现有识认图示的显著修订和创新。在“妈祖显灵”案例中的“看见”将形似女人头像的海浪看作妈祖,以及将这一表象在台风天的出现看作妈祖显灵,这些都完全符合妈祖文化的传统,因此,这个案例只是对现有识认图示的引用(citation)而不是修订(modification),在此意义上在只是为这一传统增加了又一条记录。与之对照,“象征的诞生”案例中,弗洛伊德的提炼堪称洞见,因为,在那个伴随人类历史的寻常情境中,在那个此前所有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的幼儿的形象中,他读出了超越人类已有的识认图示的讯息,从而提出了对我们的识认传统的重大修改。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出人意表的深刻洞见的背后并不是什么天才,而是接收和转化信息的能力。正如在“妈祖显灵”案例中,海浪的形态、台风天气、摄影技术、妈祖传统都被当作了可以作为证据的信息,“象征的诞生”中,不在场的母亲、围绕幼儿的物件、幼儿的神情、行为和发声也都成为了弗洛伊德理论建构的素材,而如果没有对这些素材的可能价值的识认和把握,如果没有向这些证据敞开的能力,弗洛伊德也将会是“盲目”的。
事实上,所谓的象征力正是“see as”的能力,也就是将X看作Y(或者Z),从而揭示世界隐藏的秘密的能力。第二个案例中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就是,在那个场景所代表的特定时刻,幼儿从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成为了具有象征能力的人。迪迪-于贝尔曼的重构为我们还原了敏锐的幼儿-观察者在这一场景中的历史性认知历程:母亲的不在场、形象消失、背景中的物件、新形象的出现与宝贝失落和失而复得的感受交织在一起。在任何特定时候,作为我们的习性的一部分的具身识认图示参与界定我们的“舒适区”,当外来刺激或压力超出舒适区时,都会产生陌生、迷惑的感受,就像母亲不在场的幼儿那样。向痕迹、证据敞开的能力便包括接纳外来信息,克服不适感,修正和发展识认图示的意愿和能力。而这一过程往往是纪录片创作和创新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幼儿园》的拍摄中,张以庆早早地按照当时已有的识认图示构想了幼儿园:“在拍摄前,我一直以为童年是美好的,幼儿园是美好的,想领着所有成年人重新上一次‘幼儿园’,去净化一次,美好一次,纯粹一次。但观察了三四个月后,我就傻了眼,没有办法,原先的想法全部被推翻了。”当这些想法在实地观察中受到了挑战,他持续而努力地调整惯习的认知图式。他回忆道:“当时有很多人问我:‘你拍什么?’‘你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非常茫然,非常痛苦。后来我们慢慢观察到其实孩子们面临着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不是说童年不美好,最起码它是多元的。说童年是美好的,其实只是一个概念,是人们认为的,是成年人认为童年就是美好的。所以说,在我拍摄前倒是主观的,后来才慢慢地变得非常客观了。我必须真实地面对我看到的一切,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表达的是经过一点点观察、感受到的,这就是人的本质的东西。”⑨
当“美好”“纯粹”的幼儿园被“痛苦”的痕迹不断证明为虚幻的、无效的想象,张以庆必须提出新的、有效的假设和命题,但要走出固有识认图示的舒适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他感到“非常茫然”“非常痛苦”,即便是确认了孩子们面临的“问题”和“痛苦”,他还需要面对进一步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童年不美好”?应该如何概括眼前的童年?最终,张以庆将童年、问题和痛苦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涵括在“美好而多元的童年”这一理念下,并获得将其确认为“本质性的东西”的信心。可以说,在《幼儿园》的拍摄过程中,张以庆最终“看见”的正是这一理念——作为《幼儿园》这部纪录片的核心讯息,它的创新意义就在于,在大量真实的童年影音痕迹的支持下,它修正了当代大众关于童年的识认图示。
三、纪录片真实之翼:“认”与“真”的缠绕,以具身通透为例
《幼儿园》最终成功的曲折创作历程生动地演示了识认图示怎样在具体的情境中蜿蜒演进。正如“蜿蜒”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识认图示演进的轨迹自有其限度,而这一限度就是真实——我们还记得“看作”是对所“见”之物(痕迹)的创造性转换,而“认真”则是对痕迹的忠实,二者同为“看见”的构成性组成部分。“看见”不能被化约或缩减为其中任何一项:正如阐释离不开痕迹,而痕迹只能经由阐释得到呈现;“看作”和“认真”这两种机制无法分拆地缠绕在“看见”中。相对于“看见”的转换性作用,我们可以将真实的规定性作用称为真实的锚定:通过对“看作”的创造性边界的限定,它确保了识认图示即便经历突变,也仍具有可辨的连续性。
对痕迹的忠实意味着,向外部世界的敞开和接纳不等于简单的不加判别的接受。如同证据是相对于特定命题和论点而言的,就特定的话语标的而言,并非一切信息都应该被接纳为证据。一部作品要成为纪录片,它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主观真实(特定的真实理念),也不是简单的客观真实(痕迹/证据),而是二者间的共振:即,意向性的真实理念需要能够在特定的痕迹/证据中得到支撑,而痕迹/证据的真实性需要被真实理念摄取和确认。
在个体的层面看,成熟的创作者可能表现出某种堪称“真实观”的识认图示,同时这一“真实观”也可能发生蜕变和演进。例如,贾樟柯至今为止的创作或许可以概括为分属两种彼此参照的“真实观”,一种是“被轻视的平常人”,一种是“内心的真实”,而这两种“真实观”贯穿了他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创作这一事实表明“真实的锚定”在认知中具有的基础性。
在宏观的层面上,在艺术史、视觉文化史和认知诗学等领域的研究中,我们不仅看到,主动积累对真实的把握能力是人类的普遍需求,我们还发现,文化艺术的广阔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认知经验可以供纪录片创作活动汲取。美国学者Zunshine关于欧洲绘画中的迷醉题材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佳例⑩。迷醉绘画(absorption painting)是18世纪法国一些绘画名家们曾集中创作的一种题材,它描绘的形象是各色人等迷醉在游戏、祈祷等活动中的情景。迷醉绘画的创作意图包括“无视”观者——即通过将主体置于心无旁骛的情景,从而表明主体的状态全然发自自在,而并非为观者表演、做作而来。当然,主体越是以这样的方式“否定”观者,越是凸显此时的绘画对观者和观看的高度关注。正如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注意到的,这种反戏剧化的陈设恰恰表明了全社会都已被某种戏剧化意识笼罩,即没有什么可以免于“作秀”的揣测。尽管这样,人们似乎孜孜不倦地追求这样的袒露“灵魂”的瞬间——Zunshine指出,与“沉醉”绘画相似,一种被称为“具身通透”的文学传统之核心在于将主体置于不得不流露本真意识的情态,而且,由于具有说服力的“具身通透”往往是短暂、自发、新颖的,人们不得不不断更新关于“具身通透”的人物塑造技巧和技术,于是,对他人的内在真实的追求与人们的自我掩饰之间的永恒张力构成“洞察”与“矫饰”的永无止境的辩证运动。构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个体之间不可消弭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或Chang(2003)所说的“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tivity)。由于主体间的不可完全超越的距离,人类需要践行“心论”(mind-reading),也就是使人们得以将他人的表情、行为等外部表现归诸于其内在意识活动这样一种认知能力,因为它或许是主体间认知、沟通的机制,是构成“主体间性”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通透是一种特定认知状态,人们在这一见证经验中获得极大的、关于他人的,也是关于普遍的人的洞见;因其短暂、自发、新颖,它是极富认知吸引力的状态——成为“具身通透”的见证者的冲动是巨大的社会性动机和愉悦的来源。
对纪录片创作者和细心的观众而言,这一切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在追求具体的、或然的人的主体性真实这一意义上,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纪录片)和“迷醉”绘画和“具身通透”(embodied transparency)文学具有同样的诉求。当纪录片创作涉及人类主体时,人的复杂性对创作者提出较高的要求:创作者必须能够判定,就眼前的具体情境而言,主体的言语行为中,哪一些较为真实可信,哪一些是模棱两可的,虚饰的,哪一些适合作为作品中的“证据”,哪一些无足轻重?怎样理解具体场景中的各种表现所传递的信息,怎样穿透和剥离种种矫饰,能否捕捉乃至激发恰当的信息,这不仅涉及创作者关于真实的一般理念,而且涉及个人在具体的和具身的社会场景中把握真实甚至创造真实的能力和经验。而在纪录片观看过程中,观众也会通过实践“心论”评价作品形象的真实性和作品本身的质量。而这些不是抽象获得的,而是在这样的经验中逐渐累积和丰富起来的。
换言之,纪录片也可以看作“具身通透”传统在影视媒介中的发展,而纪录片创作也参与到“具身通透”的生产中。作为对人的精神状态的直接裸露,具身通透对纪录片具有广泛而重要的意义。在观察、采访、互动中,如何让拍摄对象进入具身通透的状态,也就是如何在人的主体性中生产可以成为证据的痕迹,这几乎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必修课,而有经验的创作者在这方面有各种方法和策略。例如,罗伯特·德鲁认为危急关头能够帮助人们解开内心的深层感受,拍摄一个人物在压力之下作出何等反应,是展示人物真实内心世界的最好时机:当危机时刻来临时,拍摄对象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在手头的问题上,进而忽视身边摄影机的存在,拍摄对象卸下心防之后,就会展现出最真实的自我性格,让观众看到最真实的人物。与此相比较,有的创作者强调用时间,用漫长的等待,换得对主体的充分了解和信任,进而捕捉其真实流露。有经验的编导发现,不同的拍摄设备、场景、主体的选择也会影响创作者捕捉和呈现真实的能力。天马行空的赫尔佐格对“会计师的真实”感到不屑,但他对工具及其可能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认可能会让人们在感到惊讶之余深受启发:“你可以真切感到我们在操作摄影机时用了很温柔的手法。我希望角色们都尽可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出现,于是让施密特-莱特维恩不要用三脚架,否则的话会显得呆板无情。我想感受摄影机的呼吸,从而去触摸施密特-莱特维恩所拍摄的对象。他必须让摄像机像他自己的心脏那样搏动。”
段锦川回顾《拎起大舌头》时提到:前期调研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选择“正确的人物”,也就是“有表现能力,能够适应摄影机,能够和摄影机有一种互动关系的人”。例如,他选中的那个村的村长是女的,但是村长“不是那种拍纪录片很理想的人物,比较在乎自己的形象。而同时我发现这个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性格特别好,有表现的欲望,有和人交流的能力,属于比较有趣的那种,再加上他自己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就拍了这么一个故事”。这里所说的村长,之所以“不是那种拍纪录片很理想的人物”,大概就是因为她“比较在乎自己的形象”,会自觉地做作、修饰,从而阻碍具身通透的状态呈现。而管计划生育的干部则相反,“有表现的欲望”,“有和人交流的能力”,因而利于观者进入他的内在世界。可以想象,计划生育干部也并非没有矫饰的可能性,事实上,矫饰永远无法避免,关键是创作者的整体判断和把握。
想要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的纪录片往往面对更复杂的情况。例如,《浩劫》的导演试图让二战中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回顾集中营的经历,然而,一方面,幸存者所剩无几,另一方面,被找到的幸存者的意识早已被创伤后的心理机制重重包裹起来,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创造机会,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帮助幸存者打破记忆的高墙,让回忆再次流淌。有时候,纪录片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已经体察到创作者的内在意识活动,从而对创作者的意图有了特定推测和理解,这一难以避免的情况对形象的真实和影片的整体真实产生的影响该如何把握?例如《归途列车》中的女主人公在镜头前和父亲发生冲突并扭打起来,忽然她转过脸正对摄影机镜头喊道:“你要的就是这个吧?!”
显然,按照本文的观点,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统一的正确答案,也没有惯例可循。即便是有经验的纪录片创作者也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境。事实上,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创作的契机——对纪录片创作而言,真实不是预先封存的完成品,创造一个能够向问题敞开,发现问题,创造性地面对问题的自己正是纪录片创作的根本。
注释:
① 参见[加]保罗·萨迦德: 《心智:认知科学导论》,朱菁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Peter Stockwell: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Routledge. 2002.
③ Frederick Luis Aldama:TowardaCognitiveTheoryofNarrativeActs.University of Texas. 2010.
④ Uri Hasson et al:Neurocinematics:NeuralScienceofFilm.Projections 2(1),1-26.
⑤ 刘洁:《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⑥ Briankle Chang:SeeingGoddessinTyphoons,Differences: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2018,29(3),1-32.
⑦ Norman Bryson:VisionandPainting:TheLogicoftheGaz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⑧ 参见[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看见与被看》,吴泓缈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⑨ 刘洁:《出画的情境——中国新派纪录片人访谈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3页。
⑩ Lisa Zunshine:TheoryofMindandMichaelFried’sAbsorptionandTheatricality:Notestowardcognitivehistoricism,in Federick L. Aldama (Ed.):TowardaCognitiveTheoryofNarrativeActs,179-204. Austin,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