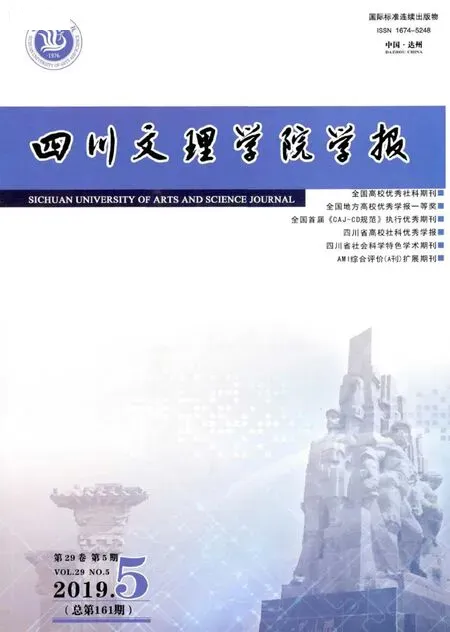理论·书写·实践:十三年来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纵观
汪 玥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0 引言
2004年,小说《狼图腾》走红并引发争议,当民族文化性格的争论淡去后,浮出水面的是关于以“狼”为纽带表达生态的文化体验.这里所强调的文学生态层面,让人联系到21世纪初引入国内的“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等学术概念,以此为关照,我国“生态文学”图景蔚然大观,并为文学、美学带来了一场颠覆传统观念的冲击.自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国知网可查询关键词为“生态文学”的论文共1,021篇,“生态美学”1,573篇,“生态批评”2,520篇,其成果是过往研究总数的十多倍.可以说,十三年来,“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三者互相激发、互相促进.
1 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学的哲学依据
对“生态”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于中西“环境”与“生态”概念的异同上,西方的环境与中国的生态有着相同的立足点——生态环境,但不同的是环境限于中心主义思维,而生态更为自然化、风情化.环境伴随着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才出现,因此它强调主客体关系.生态美学是以“审美方式”为论,探讨如何在人类的审美体验中发挥生态意识的作用,它以生态或是生态性为研究对象.人类中心主义的衰败预示着生态美学兴起的必然,从其本质上看,生态美学将“现世”“栖息”的美学特性与生命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存在论美学.[1]随着欧美生态思潮的兴起,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生态危机根源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追求,于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的发展观和生态的科技观是生态文化的思想基础”的生态美学逐渐成为定于一尊的解救之道 .[2]
曾繁仁沿着存在论的视角对生态美学加以界定,他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视为一种当代存在,在和谐中意味着人与社会、自然的动态平衡;同时,绿色也就预示着积极、健康的审美.同时他还将生态美学同当时的热点“人文精神”联系起来,即以人类积极寻求的精神家园对抗非美的物质异化世界,这其用意是为了惊醒人们生存中的危机意识,以求实现健康、持续、绿色的发展模式.[3]作为以人类为研究对象,并意在反观自身的思维方式,生态美学确立了其学科意义上的科学性,从存在论、整体论的视角否定了以往实践论的某些弊端,特别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反思.这使得生态美学将生态美从一般意义上美的领域中凸显出来,加强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延伸了美学的藤蔓.从现代美学的感性学转向来看,“生态美”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歧义,有学者认为生态美学不能脱离“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的三元模式,因此将生态审美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4]迈向存在论.在存在论的基础上,生态美学还立足于整体主义,基于此生态文学能具备独特的审美与艺术标准.王诺曾指出生态美学的三大基本原则:自然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及交融性原则.一方面,生态美学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内部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交融性流露出对整体中部分的重视,它要求我们立足语境,思考不同文化对现代性的纠偏,在此应特别强调东方传统生态文化对人类整体的重大意义.
对汉字含义的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生态文化现象,鲁枢元借助“语义场”解读了“风”字当中自然和谐的文化意蕴,其积极意义在于对人性、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5]袁鼎生则以中国古代的“生态中和”论述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古代的依生性和谐,经由近代的竞生性非和,走向现代的共生性和谐,抵达当代的整生性和谐,形成了生态和谐的历史发展规律.生态中和是整生性和谐的质态和机制......生态系统在各部分的中和中,形成了统领全局的整生质、全面协同的整生关系、匹配适度的整生结构,成为和谐生态、和谐生境、审美生境、艺术生境”.[6]可见,“生态”代表了一种境界,曾繁仁对生态美学的界定融合了这一思维,它意味着古今文学、神学及东方古代生态智慧的交汇.而西方思想家也在不断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思维,例如海德格尔因深受《道德经》影响而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生态美学的当务之急在于中国话语的探索,在中国古代批评范畴中,例如“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一”,蕴含着丰厚的古典生态智慧,这些都是当代生态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7]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视野中的自然之美》中,曾繁仁表示“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和”“中和论”“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美学观所蕴含的不仅仅是自然的实体美,更多是萦绕在其中的关系美,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相融的美.而辩证地看,中国古代的中和论生态与生命美学也存在需要扬弃的迷信成分,这需要积极的与西方生态文化交融沟通,走向更广阔的平台.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生态体现了人与其最为贴切的自然环境的相互关联,自人类产生审美意识起,自然被赋予人化意识,形成尚不系统的生态审美.生态与美学在“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上的结合可以说势在必行,要求我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认识到“生态整体主义”的重要性,为人类提供现代发展的新模式.
2 近年来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现状
中国生态文学自90年代始迈向自觉写作的阶段,其理论发展却相对滞后,王诺借《欧美生态文学》阐释了生态文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8]随着“生态美学”“生态批评”概念的引入,更多秉持着“新人文精神”的作家加入了守护“人类共同生活圈”和“诗意栖息地”的队伍.在这些作家群中,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创作由于其生长环境的“自然性”而显出别具一格的生态意识.正如任强曾表示,生态文学对人类精神与社会发展的探究体现出文学在人类意识和文化意识等问题上的最终目的,意义深远.
除去地方性、乡土性之外,生态性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品格,它并没有藏在文本深处,而受生存环境影响,这些题材表达较为直观深刻,同时选择多样,其中生存、死亡、仪式、自然信仰等都可纳入其中.学者们对民族文学的他者化想象,致使“生态性”成为分析民族文学的,部分研究者对这种“生态恋歌”的情调表示厌恶.但少数民族作家们则捍卫他们所特有的叙述模式并不是源于“固步自封”,而是“有意为之”,他们对生态观重塑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郭雪波称对生态文学的书写应该是光荣的,值得称颂的.文学在现代化都市高楼的包裹下太久,是时候回归到它曾经的家园去追寻的新的生命力.[9]
自2005年来,少数民族生态写作的自觉性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叶广芩(满族)的《黑鱼千岁》即体现出作者对建立新生态观的急迫心理.此时少数民族作家依独特的生态视野进行着必要的反思,亚森江·萨迪克(维吾尔族)的《干涸的河流》中,水站管理员的私心和贪婪造成阔坦东村的桃园般生态荡然无存.《沙漠》中因官场斗争而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危及当地人民生活.此外韦启文(壮族)《寻找敕勒川》、徐岩(满族)《野马滩》、突尼亚孜·麦迪尼亚孜(维吾尔族)《多浪河》、刘耀儒(苗族)《酷夏》、额鲁特·珊丹(蒙古族)《遥远的额济纳》、郭雪波(蒙古族)《银狐》等也是该年的代表作.
2007年、2008年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丰收年,此时对生态性的已经引入民族性书写的常态中,以阿来(藏族)《空山》为代表,其中《荒芜》写在自然灾难面前,机村人的精神与土地都走向无可奈何的荒芜,揭示出发展和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达隆东智(裕固族)的《苍鬓母狼》中人类对狼崽的肆意捕捉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最终给自己带来厄运.其他作品还有萨娜(达斡尔族)《达勒玛的神树》《山顶上的蓝月亮》、白雪林(蒙古族)《霍林河歌谣》、了一容(东乡族)《林草情》、阿来(藏族)《大地的阶梯》等.
在2009年到2012年之间少数民族生态写作更注重人的意识,代表作是瓦·萨仁高娃(蒙古族)的《草原蒙古女人》,歌颂了蒙古族人坚韧精神,展现对自然的破坏,过度的采矿而获得的利益是短暂的,失去的财富是永久而悲痛的.阿尤尔扎纳(蒙古族)的《一个人的戈壁》展现了原生态的“诗意栖息地”生活画面,老人、自然、万兽和谐交融.艾则孜·沙吾提(维吾尔族)《狼崽“蓝眼”》描绘人与狼共处共生,互相救助的场景,体现出众生平等的意识.此外还有阮殿文(回族)《一个漫游者在迪庆高原》、郎确(哈尼族)《阿妈的土地》、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狼谷炊烟》、李梦薇(拉祜族)《扎拉木》等篇目.
2013年及2014年生态文学的创作成绩在诗歌领域比较突出,代表诗集有郑秀文(黎族)《水鸟的天空》、谢来龙(黎族)诗集《乡野抒怀》、金戈(黎族)诗集《木棉花开的声音》.小说及散文代表作有胡玛尔别克·壮汗(哈萨克族)《无眠的长夜·翡翠》、合尔巴克·努尔阿肯(哈萨克族)《灵羊》、吉狄马加(彝族)《我,雪豹......》等.
2015年阿来(藏族)的《蘑菇圈》具有较大影响力,小说描写原始森林被过度砍伐和消耗导致来年干旱,全村陷入饥荒,斯炯挑水细心灌溉蘑菇圈,给全村和山里野兽们提供了果腹的食物,然而贪心的商人却用着破坏“可再生”生态规律的行为来高声倡导“可持续发展”,将最后的蘑菇圈破坏.其他代表作有龙道炽(侗族)《清水江歌行》、非夏曼·蓝波安(达悟族)《敬畏海的神灵》等.2016年的代表作有肖龙(蒙古族)《榆树》,满都麦(蒙古族)《绿松石》,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草原》,丹增(藏族)《猴王与野人》.2017年,光盘(瑶族)的《重返梅山》描写了一名不为利益,不进行开采,反而植树造林,力求恢复梅山生态的资本家形象,表现在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后,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该年还有代表作丹增(藏族)《大理风花雪月》、鲍尔吉·原野(蒙古族)《土离我们还有多远》、龙章辉(侗族)《进山遇到神》等.
由此看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始终对生态现象报以密切关注,描写多集中于人类行为导致的生态报复,如何激起人类共同生态危机意识的觉醒是生态文学的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很多作品在生态内涵、生态批判及生态自觉等方面表现不足,少数民族作家仍是生态文学发展中的一支有力的主力军,他们丰富了人们的生态视野,成为一种文学景观.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一文中,汪东树批判了国内生态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作家们缺乏整体性的生态观,他们对危机缺乏深入的认识,甚至广泛存在对知识常识的盲区,这致使生态文学中艺术魅力的缺乏即现实关怀度不够,因此当下的生态叙事易于流入模式化、概念化,更难言深刻的人性探索.具体在书写中就是刘青汉在《中国当代江河生态文学论》论及的中国内现代江河生态文学多描写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状况,对生态的整体观念概念欠缺,并没有考虑到江河整体生态系统的利益.以及王静在《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中对当前少数民族生态创作进行剖析,认为当前少数民族作家未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未达到维持生态平衡,升华人文精神的高度.因此,正如批评家所言当前生态文学创作的问题客观存在,当前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希求文学批评的不断指引.
3 生态美学作为批评的实践
理论引入文学后常伴随着强烈的自我解释冲动,这是文学学科除知识性属性外更为深远的学科意义,生态美学、文学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必然延伸出其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阐释.但是,现有的许多生态文学作品仍然对“生态整体观”的把握不足,始终无法跨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面对超世俗伦理和新型文学领域时,缺乏探索精神,当下,生态文学急需少数民族文学以开阔其眼界.[10]从外部看,丰富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内涵对现代生态文明、生态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从内部看,它意味着对传统文学发展的内部反思,当作家们盲求各类形式、手法时,生态文学指明“复得返自然”的精神价值重构.龙其林将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分为三个创作类型:批判型、忏悔型与审美型.[11]生态文学是随着生态美学的出现而成为一个整体概念并被纳入批评视野,当文学参与到社会建构的过程中,生态文学以生命整体为表达对象,进行美化、批判、反思,因此,生态文学在类型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同时,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生态文学仍然延续“人学”的表达思路,当下的中国文学能立足于民族,又超越民族,这意味着中国文学视线的审美超越.而随着作品的与日俱增,生态文学不免显露出一些不足和许多发展的可能性,它使研究者们明确了何为生态文学,也推动了理论与批评朝着具体个案的深入.
在作为批评的具体方法上,普遍采用四种路径.第一是以跨学科的方法引入生态学的视角.譬如余晓明在《论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提出的生态学隐喻,即是用生态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与环境的交融,这其中生态学与文学互为整体.生态批评的学科转向,特别是生态维度,使之脱离了知识与价值“二者必居其一”的学科范式,并体现出以本体回归的视角再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
第二是以文明观来响应社会新的发展,“人类纪”是人类文明引来的新的机遇,同时我们急需有新的文明立场来支撑生态主义时代下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而其中第一点就是观念上的转变[12].生态批评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中重差异、去中心、多元共存的一种,它与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密不可分.
第三是将生态批评视为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刘文良在《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生态批评》中认为生态批评是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一种考察方式,建立科学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增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跨文明、跨文化性,还可以此达到文化性与审美性的交融.同样,张华在《生态批评的现代性背景及其当代发展逻辑》中也论述了生态批评在文化批评实践的功用.生态批评发挥着自身跨学科性的优势,不断丰富完善着自己.
第四是袁鼎生提出的“三位一体论”,“审美规则、生态规则、自然规则三位一体运行,是生态批评的规律,是生态批评从艺术领域走向其他领域的机理和依据”,在这里我们看到“生态批评”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文本内部,伴随着“外转向”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深刻地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反思中 .[13]
理论的蓬勃也推动了广泛化的生态批评实践,其包含文本的内部研究以及外部研究,涉及作家、文体、地域等诸多方面,可以视之为对现状的反思以及生态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作家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或具有民族风情的作品受到了较大关注,譬如曾繁仁分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表现了“回望家园”的主题,揭示出隐藏在当代人们心中对“诗意的栖居”的追溯.于国华认为阿来的山珍三部“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与相互关联,展现了藏地人对自然敬畏的新特征,批判了破坏生态系统和谐,将自然引向深渊的欲望动力,同时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希望所在,从而成为生态文学的典范之作”.[14]对“秦岭系列”的解读中,李玫认为叶广芩的秦岭系列展现出了作者生态思维的拓宽,成为生态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吴秀明与陈力君在《论生态文学视野中的狼文化现象》和《从<狼图腾>看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中提出了“与狼共舞”的生态想象.韦清琦《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张文刚《“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张晓光《徐志摩文学创作和生态美学思想》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当代作家的生态意识进行了阐述.
从文体来看,吴景明认为当代生态诗歌和生态散文缺乏总体性哲学思考的深度,一些作品仅停留在危机揭露的初步,在一腔热血地激情叙事之后应何去何从?这些作品显得力不从心.[15]在《生态危机与戏剧危机的双重探寻—中国当代生态戏剧简论》中他简述了现代派戏剧的内部转型,表示凸显人与自然矛盾的戏剧逐渐显现.刘秀珍《“看云在绿叶间缠绵”—试论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徐治平与胡明慧也分别在《生态危机时代的生态散文—中西生态散文管窥》、《论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意识》中梳理了我国当前生态报告文学、生态散文和儿童文学生态观.
在地域上,学者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学创作,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宗教、环境是使作家生态观和作品呈现的生态意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首要原因,在提供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的同时也局限了他们的生态表述.魏永贵,赵富荣在《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中认为郭雪波等少数民族作家所接触的宗教教义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使得他们的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名列前茅.《论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中谢廷秋表示神话,自然风景与家园都是少数民族的集体“经验”.沈茜在《生态文学视野中的苗族古歌艺术》中表示苗族诗歌中透出的生态意识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影响,显示出人类先民的“泛灵论”思想.此外还有宋坚《论广西生态文学及其审美批评》、刘汉青《当代甘肃生态文学论》、唐长华《生态批评视域中的京派乡土文学》等具体生态批评的实践.
虽然在实践上生态批评蔚为大观,但依然有人表达出不满与焦虑,首先是在文学内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人在书写自己民族的文学史时,疏漏了“自然”......文学应该是人学,但不能仅仅是人学,对自然书写的缺失会造成文学史书写上的空白,文学对自然的关注度还有待提升.[16]其次,生态批评应在社会效益与审美价值上更进一步,而不是止步于浅层的生态破坏上.
文学始终指向人学,生态批评需要重审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价值,用和谐、整体、平等的生态意识挖掘文本的意义,更要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整体视野下进行深刻反思.[17]无论是在现象还是文本,生态批评实践都应担负起促进人们生态观念重塑,推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4 反思与前景
随着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的研究不断深化,不少学者进行了再思考,指出以下问题:首先是本土性缺乏,不仅要避免西方学者对生态问题做出的“东方主义”思维误导,无论是作为西方当代文论的观念,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延伸,生态批评都应积极立足于中国当代本土生态文化资源,以求交流、对话并加深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的理论转换.[18]其次是研究视角狭窄.反思是自我超越的第一步,国内生态文艺学研究囊括了三个基本走向:生态整体观照下的文学研究;重审人类生态意识;挖掘东方古代传统生态观,丰富的学科内涵也激起了学界对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发展与前景的探索热情.
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概念自古已有,在当代才得以关注是源于严峻的现实需要,它们是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重要一环,极具现实性,这就使得它们与其他文学思潮有着不同的意义.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文学被处于边缘位置,不具有改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影响力,因此它要接受理论的审视,挖掘我们历来所忽视的盲点,让人们认识到“路”是的的确确走错了.但显然国内生态理论在学界也缺乏关注,更不必说产生颠覆性的社会效应,尚未获得“生态革命”所期盼得到的反馈.
目前,生态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给人文学科带来了生机,但在人文学科整体没落的背景下,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实践还是理论思辨,亦或是深层反思,目前都无力为人类整体性生态危机提供一剂良方,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未来还需要加强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