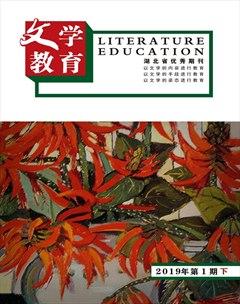创造社躁动性青春型文学社团的文化策略选择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五四新文学初期创造社作为“五四之子”一代在文化选择上的极端激进姿态,进而发掘这种姿态后面所呈现的创造社青年群相近的個性气质和人生道路,最后尝试由此管窥中国新文化现代性之旅上较为普遍的反哺与反噬之间的悖论。
关键词:反哺 反噬 创造社 青春型 文化策略
“五四”新文化运动端启何时,向来说法颇多,恰似“风起青萍之末”般踏浪无痕,自然也就莫衷一是,纵是如此,却有一百年不易的观察点可为共识,即这场文化运动崛起于政治反抗的失败,因为无力靠“武器的批判”阻止袁世凯复辟称帝,只能感应于袁世凯为称帝而施行的尊孔教为国教以为复辟张目的道统一途,转而以“批判的武器”来曲线挽救民国国运。新文化运动台前之巨擘陈独秀和幕后之策划蔡元培,都经历过为创建并捍卫民国从政治而文化的转换之路,他们的人生轨迹,用鲁迅的话来表述,则是“从旧营垒中来”,并且给这旧的“反戈一击”是也,换言之,这是一批人到中年者的叛逆之旅,这也是一批事业有成者的求新之旅。惟其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以“新文化”来缔造“新青年”,谋求“民国”新的基础,但是开其端、肇其始、奠其基者是一批介于新旧之间并极力完成蜕旧变新的中间人,从年龄和心态上他们大多为中年人。
观察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一九一七年初自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任职北京大学,实现所谓的“一校一刊的遇合”以后,两者间便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在长时间不温不火的积储阶段以后呈现出勃然迸发的新态势,夺目的光彩之后留给后人的印象似乎这是一场由中年人蓄谋已久而后动的攻坚战,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老而渐衰的社会势力,从文学、文化的战阵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搏杀,刀剑起落处杀伐有声,摧枯拉朽中在在显示出中年性社会力量的沈勇猛健来。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初始阶段就表现出中年人对阵老年人的情势,故尔战事未毕,胜负已判。虽然其时的主力将领如胡适才25岁(均以1916年计算),李大钊27岁,钱玄同29岁,鲁迅35岁,周作人31岁,其主帅陈独秀也不过36岁,但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横空出世,自然沉雄劲健,应对裕如,极具一种气度或风范。
随着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旧道德的战役一路报捷,新青年一帮人名声鹊起,热闹到极处便不免于潜生出岑寂落寞来,一个个都有些“荷戟独彷徨”的况味。有意思的是,其时这批领导人物距前期的冲锋陷阵的矫健劲儿才不过四、五年时间,历史似乎刚刚掀开一角便要落下沉重暗灰的大幕,疲沓之势已是不可避免了,因为他们普遍有种“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困顿难以排解。
在这新文化运动行将消歇、蕴育新变的当口,一批新的文化生力军的出现既是现实的急需,也属历史的必然,他们往往被冠以“五四之子”的代际标识。文化文学新军的出现是前几年新思潮结出的最早的果实,于首倡义旗的一代而言应该是求仁得仁,后继有人,幸甚幸甚。对于感应而出者而言,理应再接再厉,勠力创新,襄赞大业,完成每一代人应该有的属于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可是,想象的历史中的和衷共济却往往被真实的历史中的歧见歧途所惊破。其中,创造社是文学新军中姿态最为决绝、态度最为极端的一支,他们与后之“狂飙社”之高长虹、向培良等类似,只是其人更众,其势更强,其对于文坛生态的冲击亦更具影响力。
创造社是与文学研究会作为最早的单纯的新文学社团联袂出场的,它的出现可谓是那地里忽地杀出的一彪人马,给二十年代初期的文化界带动许多躁动不安的因素。先行半步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北京,自成统系的创造社却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于东京民宿里几个留日文学青年简单的餐聚中从动议走向诞生,应该说创造社之前几个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如叶绍钧、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孙伏园、许地山甚至周作人与创造社一帮人年龄不相上下,但创造社甫一登场便显示出与先驱者,也与同场竞技者迥乎不同的异数,并且以他们带群体性的独有的青春期的躁动搅扰文坛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给后世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留下几多不结的悬案和难解的谜。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头十年的情形打一比方的话,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对垒的便是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和克字辈,而他们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同人便是觉字辈的一帮伙计,而在觉字辈中创造社便毫无疑问的是那愣头青式的高觉慧,是伙计中之小伙计。他们本来应该持有的文化的反哺者的角色却被文化的反噬者。
那么,是什么机缘使创造社成员普遍的打上大家族中最小的反叛者的印记呢?下面我将试就创造社的搴旗大将郭沫若与不二殿军的郁达夫为个案来略作探讨。因为一个社团的特性往往就是其成员的特性,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
首先,我们观察下不受羁拘的个性和不太正统的出身而来的叛逆者姿态。
少年郭沫若的调皮不服管教与他的聪颖明敏是同样的有名,频繁的闹学和三次被学校开除或许表明郭沫若反抗反叛的性格中不无些顽主的痞气,而在每个学校郭沫若都能以年少负高才引得朋辈的折服,更使得郭沫若自信中不无自负,自强中亦时有自纵。在他的中学堂学习期间,多次与酒友纵酒以资排遣,便是少年人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证明。高傲的心性和对多有抑压的生活环境的强烈反感,是郭沫若不断出走,不断寻找新的团队的内在动机,这也是郭沫若终生不安分的宿因,对革命或类似革命性质的事物或状态的向往在郭沫若是至老不稍减。
当然,郭沫若袍哥之家的出身,让他打小就较多的脱离传统绅宦之家正统的家教,偏离大多数诗书耕读的人生道路,与三教九流等社会边缘人群的接近甚至于亲近,也同样让他养成任性使气的游侠豪放的性格,这种人生起点让他不仅仅只是由新的向旧的发起挑战,而且还夹杂着由边缘向中心的挑战。所以成都求学时,郭沫若感应于时局的动荡和革命的风气,“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同样性质的对未来的崇仰和向往伴随着郭沫若后来放歌《新华颂》,醉心《科学的春天》,至老不懈,之死无悔。
其实,同样的变易不居的心性也表现在郭沫若的家庭观念上。郭沫若一生多粉脂情缘,除了客观的际遇,主观上的崇新厌旧心态恐怕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即就一九三七年“别妇抛雏”“投笔请缨”,准备偷偷回国时,面对妻子安娜“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的劝诫,郭沫若确曾在心里立下大诫:“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但是,谁曾成想七月二十五日回国的郭沫若,十一月十九日得到安娜的来信,当即作七律一首,诗中有云:“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孰知翌年元月就与于立群在精神上紧紧“拍拖”着了,还赠于立群小诗一首:“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及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在保卫大武汉的热潮中,郭沫若栖居珞珈山教授宿舍时,于立群已然成了一个贤内助。
不受牵拘的个性,“性格不定”差不多也是创造社同人共同的性情特征,这种普泛性的成员间相近的性格,是他们相互吸引、相互共事的关键,同时也给创造社带来社团色彩的青春型印记。
也正是受这种个性的牵引,创造社同人在谋学、谋职、谋事等人生选择上同样游移不定,特别是留日学生群,如果同留美学生群相比较,这种“流民”、“游民”色彩显得更其明显。
郭沫若初赴日本留学,先补习日语,家书中表示“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后考入东京一高学医时,坚信“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打算将来“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故尔“立志学医,无复他顾”。后与冈山六高学工的成仿吾结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但同时“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种对文学的业余性质,使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陶晶孙等人相与往来、唱和,并成为后来组织社团的基础。而在组织社团、编辑出版文艺刊物的过程中,创造社同人几乎都有过中断学业、抛弃职业的经历,学医的不行医,学经济的学工的也不搞自己的专业。这种种不免少年人的冲动之举,让他们不同于文研会诸人,更不同于以大学教席为谋生方式甚至事业基点的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人,常常陷入生计无着、举步维艰的窘境。这反过来也更加激发他们的气性,遇事多取激进甚至偏执的姿态,使他们的圈子内部更紧紧地扣合一起,对外又更趋向于取排斥的态度,故作激烈是他们这个时期的共性所在。
其次,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随之而来的对功成者的艳羡和对已身际遇的不满而来的挑战者的姿态。
如果说,前面所言的出身经历与个性气质还只是个人面对社会成为社会人的可能的姿态与选择,那么后来之时势变迁和环境变异带来的个人遭际的群团化的蹇滞蜷缩,停留在创造社个人个性的可能性就会立即转化为具有共同思想指向性和运动指向性的现实性存在。说到创造社的成立的因由,郭沫若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致田汉的信中的一段文字常被引用:“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创造社同人作为新进者对于先进者的功成名就心存怨望,内心的自信、自负遭遇外界环境的打压便造成心理不平衡。后来郭沫若等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虽是由郁达夫执笔起草,却是代表他们共同的心声,内中有文:“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其中“偶像”当有所指,而以“无名作家”自任时心里不无些酸意。
也许是这种酸楚长久郁积所致,郁达夫郭沫若等创造社诸人后来不忌惮于树敌众多,在“创造”的大旗下与胡适、与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笔墨官司,集中体现了青春型社团好斗的心性和企求通过与成名人物的打斗来引来社会的关注,成为新的社会势力的心态。这正是青年人和青春型文化的个性所在。究其实,这种后进对先进的打杀以求名,无名对有名的指斥以自高的做法也不自创造社小伙计始,先进者、有名者当年默无声名时也或多或少持有同样的心态,操持同样的战法,只是创造社小伙计因其特殊的际遇而更为彰显些,也更为自觉些罢了。
在此,我们不妨以互文见义之法来解读一下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个较为有代表性的挑战者的姿态后面的别样意味。
为了落实创造社的宏伟蓝图,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郭沫若和郁达夫先后中断学业回国,在上海与泰东书局合作编辑出版《创造》,生活的困顿和编纂的不顺让这两位既穷且困,可谓身心俱疲,这种疲累感达到极处便是为整个世界所抛弃的彻底的孤独感。据郭沫若回忆录《创造十年》所描绘的,他们感到诺大的上海只有他们两人的“幽灵”还在回荡徘徊,他们一同冲出作为编辑部的门店,直奔街上的酒店,一连在两家酒馆里痛饮,却依然没有满足,到第三家时“直将喝完的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时”方才罢休。此时他们顾影自怜,自诩为“孤竹君之二子”,承受的命运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愤激之余“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像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像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面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
——如此为作,岂非极端对抗既有秩序既有格局者乎?只是此时他们还只是笼而统之的对于现实表达其不满与反抗,姿态固然倔强,攻击的火力却因为失焦而显得骄狂。等到在国内文坛交接既旧,他们才日益分明的感觉到文坛上的功成名就者即为他们事实上的压迫者,反抗于是就有的放矢,这就是郁达夫郭沫若与胡适之间的“夕阳楼”之争的历史的真实。
前面说到貌似同根而生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美好愿景,事实上两者间后来上演的竟然是相煎何急的苦情戏,因为文学研究会是代表占据文化要津掌握文化话语权的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师生群与南方商业大都会上海的集文化出版教育和舆论于一身的商务印书馆的强强联合,相形之下创造社的生存发展空间则相当的逼仄,而作为这种对抗的对象则落到了胡适的头上。胡适本非文学研究会的创始成员,但因为与《新青年》的北大同人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正负二位舵主交情至厚来往至密,便被历史选为接盘侠,至于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是否真正如胡适所批评的《浅薄无聊的创造》,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郁达夫攻击新闻杂志界的人物“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蟲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都没有”,甚至于“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就算新思想家了”,这架势的确有单挑的嫌疑,后来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上阵,则是群殴。
当然,这种挑战到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时攻击的对象已经转变为鲁迅和茅盾等“文学革命”的元老因为他们要的是取而代之的“革命文学”,再至于“左联”时期攻击同为左翼的鲁迅、胡风等,因为他们连文学也不要了,只需要革命,自然主动出击的则永远是始终带有青春期气质的他们。
总之,是极具青春期躁动性格的成员们共同造就了创造社的青春型社团文化形态,并且影响到后来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关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方向与道路选择。
(作者介绍:饶向阳,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