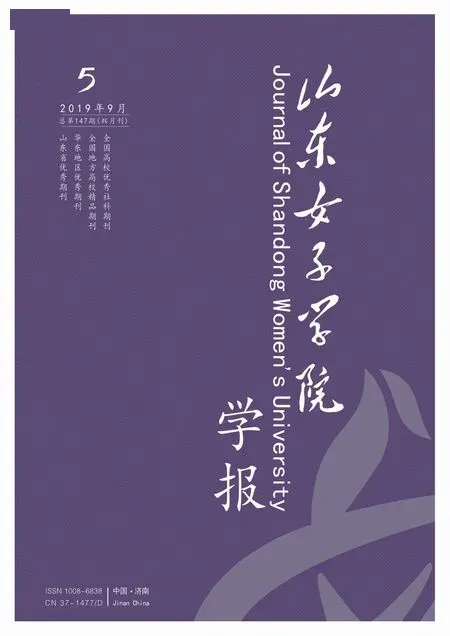吉本芭娜娜小说的空间叙事与女性意识
郭燕梅
(山东政法学院, 山东 济南250014;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引言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学,其故事情节的展开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时空背景。所谓时空,即时间与空间。有学者认为,时间与空间的相融之处在于“时间特征在空间中伸展开来,空间由时间维度来衡量,时间和空间共同决定艺术样式的布局、体裁、艺术主旨和审美价值”[1]。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这二者密不可分,在小说创作中同等重要。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巴赫金写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2]。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在《风土》中将人的存在阐释为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和作为人的集合或共同体的社会性存在。他认为要把握人的存在,就必须“空间和时间同时被捕捉在其根本形态中,两者相即不离。仅拿时间来把握人之存在,会导致片面地只从个人意识的深层去寻找人之存在。如果认为人之存在的两面性是人的本质的话,就必须同时找出与时间相对的空间才行”[3]。基于现代学界对“时空体”这一概念的认识以及对空间这一维度的重视,作家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重视空间维度,在特定的空间背景下展开叙事,利用空间表征人物性格,表达文学诉求,以实现文学的现实意义。
日本当代女作家吉本芭娜娜自1987年登上文坛,至今已逾30年。在这30余年间,芭娜娜发表小说50多部,随笔40余部,合著20余部,可谓多产。以《甘露》(1994年)为界,自《厨房》(1988年)以来的“第一期吉本芭娜娜”结束,芭娜娜坦言“从今往后会判若两人,写出迥异于以往的作品”[4]。近十年之后,芭娜娜在小说集《尽头的回忆》(2003年)的后记中写道:“或许,我是想在待产期间,尽快把过去痛苦的事情全部清算掉吧?”[5]缘此,笔者将芭娜娜至今的小说创作梳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与第二期以《甘露》为界,第二期与第三期以《尽头的回忆》为界。芭娜娜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运用“空间”这一维度,通过空间表征人物性格并推进叙事,关注不同空间中的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父亲吉本隆明在与芭娜娜的对谈中指出,芭娜娜小说的特征之一不是写人物,而是写一个“场”。芭娜娜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在“喜欢”的“场”中出现,如果是十分喜欢的“场”,其中的人物关系会发生改变,甚至会发展为诸如恋爱、同居等亲密关系[6]。这里的“场”,即空间。在芭娜娜的创作观念中,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在特定空间中可以形成或改变。正如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5—1991年)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所指出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空间无疑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
本文聚焦其《厨房》(1988年)、《蜜月旅行》(1997年)、《橡果姐妹》(2010年)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中的空间书写,运用空间叙事等相关理论,分析其中的空间叙事以及不同空间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并尝试探讨芭娜娜小说的空间叙事特点。同时,将小说中涉及的厨房、院子、网络等空间与女性结合,分析置身于不同空间中的女性对成长、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的思考,揭示芭娜娜小说中的女性视角与女性意识,并进一步管窥其文学的现实意义。
二、隐秘与开放的空间——美影的厨房
关于日本人生活空间的“内”与“外”,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指出,“内”即家,家以外的空间就是“外”。他从建筑空间领域上重新认识“家”的内涵,这里的“家”不仅指住宅本身,还指那些即便不属于私人住宅,但依旧能够脱了鞋进去,穿着便衣自由阔步的舒畅空间,例如日本的温泉观光旅馆[8]。厨房作为内部空间,为家庭成员提供一日三餐,是住宅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属于“内”的部分。在传统建筑中,厨房往往被置于住宅的角落,是一个隐秘的空间。关于物理性空间的住宅与住宅所承载的“家”的抽象意义,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为了突出住宅与“家”的密切关系,将住宅称作“家宅”,“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我们常说,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9]。“家宅”是“最初的宇宙”,“宇宙”一词本身就具有包罗万象的开放意义。而在芭娜娜笔下,厨房成了这个“最初的宇宙”的核心,因此芭娜娜小说中的“厨房”兼具隐秘与开放之特性。此外,制作一日三餐的工作主要由妻子、母亲等女性成员承担,厨房里流动着女性气息,是女性主要的活动空间。
小说《厨房》是芭娜娜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主人公樱井美影失去所有至亲后倍感孤寂,只有在厨房的冰箱旁方可安睡。幸运的是,曾受她祖母关照的田边雄一与他的变性人母亲惠理子将她收留,并给予她重振旗鼓的勇气。
小说开门见山地叙述了主人公对厨房的依恋。“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即便是一间邋遢得不行的厨房,我也难抑喜爱之情。”[10]“厨房”成了小说叙事的“舞台”。由于祖母的离去,倍受重创的美影仿佛进入了“宇宙黑洞”,被悲伤、不安、虚幻等不良情绪笼罩着。“这所房子,我生于此长于此,而时间是这样无情地流走,如今竟只有我一个人了。”[10]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撩拨着主人公的孤独。她躺在厨房的冰箱旁边感受着“家庭”所剩无几的温暖。厨房“闪着寂静的微光”,仿佛与主人公一起体味着孤独煎熬。这里的厨房除了是烹饪场所之外,还兼具了卧室的功能。在寄宿田边家之前,美影每天都睡在厨房。厨房原本是日常性的存在,提供一日三餐,是家庭中最具生活气息的场所。随着至亲接踵离去,尤其是祖母,作为主宰厨房的女性撒手人寰,厨房的传统空间意义面临消亡,家庭内部的秩序也因此被打破。“日本的传统是在家的内部建立起井然的秩序,以家族为中心,在一幢建筑里保持着内部秩序”[8]。随着维护家族内部秩序的中心人物祖母的离去,家族解体,传统也将随之崩塌,由此足见女性对于家族与传统的重要意义。秩序混乱时期的厨房开始演化为主人公承受孤独、舔舐心灵伤口的港湾。孤独疲惫的美影甚至想到了死亡,“什么时候死亡降临时,能死在厨房里就好了。无论是孤身一人死在严寒中,还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温暖地死去,我都会无所畏惧地注视着死神。只要是在厨房里就好”[10]。此时的厨房是她孤单一人时唯一的陪伴,甚至给予了她面对死亡的勇气。
厨房对美影来说几乎代表了“家”的全部含义,是她理想的容身之地。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9]。如今,美影传统的“家”不复存在,她不得不寻找新的“家”,于是她接受了田边的邀请。到了田边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大、明亮的厨房以及与厨房相连的客厅中的沙发。田边家的厨房,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日常所需最小限度”的厨具,“银石涂层的平底煎锅和德国产的削皮器”,还有“硕大的盘子”“带盖的啤酒杯”等等。目睹这些与厨房相关的器物,“我不住点头,四下看看。这个厨房,我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在陌生人的家里,“我却没有孤独之感。这也许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吧”[10]。与美影家阴郁昏暗的氛围相对照,田边家给人的感觉始终是阳光灿烂的。小说中反复使用“晨光炫目”“洒满阳光”“灿烂耀眼”“暖阳高照”等词渲染田边家的明媚与美好,正是这些美好的感受让美影决心在这个家寄宿下去,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女性成长之路。
美影家的厨房由于传统女性祖母的存在,传统的厨房是隐秘的空间。而田边家的厨房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开放空间,给了初来乍到的美影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在这里,美影的听觉、视觉、触觉和嗅觉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在田边家的厨房里,美影遇到的另一位厨房的女主人——变性人母亲惠理子。田边家的这种明快灿烂的气氛无疑来自于这位“太阳”般存在的女性。清晨,惠理子在厨房中活动的声音唤醒“我”,她明快地与“我”打招呼。这种安心感日渐延伸,与雄一和惠理子共同生活、一起吃饭谈笑的日子成了美影人生中“无比幸福”的“夏日”回忆。惠理子的歌声、脚步声、开门声、浴室的水声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如交响乐一般,使美影倍感舒适与安心。惠理子,原本是田边雄一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说是,反正今后再也不会喜欢别的人了”[10],就变性为女人成了他的母亲,靠开变性人酒吧抚养雄一成人。变性人惠理子是这个家的“太阳”,是既非父亲亦非母亲的精神领袖般的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由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关联的人们之间的小规模集团”[11]。田边家则将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解构,并经过艰难的探索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此外,还接纳了美影寄宿其中。看似不凡的家庭并未让人感到不适,生活在其中的美影反倒觉得舒适自在。反观以血缘维系的传统家庭,美影在回忆起与祖母的共同生活时感慨道:“无论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快乐地生活着,还是会有无法填满的空间”[10]。以前与祖母的生活虽有血缘维系,精神上却还是会感到莫名的缺失。芭娜娜在解构了传统家庭模式的同时,又探索出一种不拘泥于血缘与法律的新型家庭模式。维系这种新型模式的纽带既非血缘也非婚姻,而是各自独立的精神。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梦中的厨房……我会拥有许多许多厨房,在心中,或是在现实中,又或是在旅途中。有一个人单独的,有大家共有的,有两个人的,在我人生路途的所有站点,一定到处都会存在的”[10]。传统厨房的隐秘为突遭变故的美影提供了短暂疗伤之所,但现代厨房的包容与开放则给予了美影重塑人生的勇气以及今后的人生梦想。芭娜娜笔下的“厨房”,既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又是一个存在于意识中的想象空间,“既是温饱的保障,又是家庭温暖的象征,属于女性空间”[12]。传统女性在厨房劳作、抚育后代,现代女性则赋予厨房这一空间更多的抽象意味,使其成为女性独立成长、追求自我的原点。
三、缓冲与容纳的空间——真加的院子
如果说厨房是哺育生命、慰籍灵魂的人文空间的话,那么庭院则是人为创造的自然空间,既是连接内部住宅与外部街道的缓冲地带,又是容纳与化解的空间。不仅如此,院子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女性之女性意识向外界的进一步延伸。女性不再被禁锢在某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置身于这方寸自然之间,看花开花落、四季轮回,去思考生死、体悟爱情、实现成长。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庭院空间因其历史、地理以及风俗文化之不同而各具特色。日本传统的庭院空间,其造园艺术别具一格。例如,江户末期的汉诗大家广濑旭庄表现夏日庭院的诗作《初夏偶成》中的诗句“街居犹觉远尘嚣,三面高墙护小园”[13],“街居”却不受尘嚣之扰,究其原因乃是“三面高墙”之内的“小园”,也就是院子,由此可见庭院隔离内外、缓冲干涉的作用。由于生活方式欧化、人们居住观念的变化等,现代都市中的个人住宅已较少见到传统庭院。即便如此,不论多小的面积,日本人都会种植花草以营造自然景象,打造出属于私人的一方庭院空间。小说《厨房》中,田边家居住的是高层建筑,没有属于自己的院落。即便如此,主人仍在阳台的大玻璃窗前摆放花草,营造出一个热带丛林般的自然景观。跟随着美影的目光,我们看到“阳台的大玻璃窗前,摆满了一盆盆一罐罐的花草,简直像是热带丛林。细看,家里到处是花,每个角落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瓶,里面装饰着时令鲜花”[10]。不仅窗前,甚至可以说整个住宅空间都兼具着院子凝缩自然的功能。
在芭娜娜的诸多小说中,《蜜月旅行》这部小说对“院子”这一空间着墨最多。该小说讲述了少女真加和少年裕志的情感故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日久生情,高中毕业后马上结婚了。不料爷爷突然离世,使裕志本就晦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为了逃离这样苦闷的日常生活,两人决定踏上旅途探寻生命真谛。小说共分九部分,第一部分“真加的院子”反复描述了“院子”这一空间,表达了真加对“院子”的挚爱,“我从小就喜欢自家的院子。它并不是那么大,但和房子一比,面积就算很大的了”[14]3。真加家的院子是一个真正的庭院空间。因其母亲酷爱园艺,在院子里种植着各种植物,里面既有可供食用的植物,也有供观赏的山茶花等开花树木,“点景石交错成趣”。真加贪恋院子带来的“辽阔而悠远”的感觉,置身院落之中,女性的幻想被唤醒,仿佛将自己融入这自然缩影当中,几乎成了院子的一部分。
院子除却是一方自然的缩影,还是一个阻隔外界干涉的缓冲地带。置身于这“没有墙壁也没有天花板”的院落,时间被静止,空间成为永恒。“无论身处何处,当不安蓦然袭来,我有时便会在心中让自己不知不觉间返回院子里。院子是我感觉的出发点,是我永远不变的基准空间。”[14]4院子对于真加的意义就好像厨房对于美影的意义,置身其中,人物的情感可得到尽情宣泄,又能不为外人所知。正是由于院子的缓冲与隔离,仅由“一道矮矮的篱笆墙”隔开的两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裕志家是一座日式老宅,没有庭院。裕志的父母因热衷某种神秘信仰在他年幼时移居海外,将他丢给爷爷抚养。后来,裕志的父亲死于邪教组织的集体自杀。裕志的家本就“弥漫着一股好像混合了霉味和线香味的怪味”,在裕志的爷爷去世后,这种阴郁怪异之感愈加强烈。作者用“冷寂得恐怖”“寂寥”等词形容裕志家的氛围。裕志在整理爷爷的遗物时,这种阴郁寂寥之感更甚,仿佛要将他和这个家一并吞噬。篱笆墙另一边的真加家是新式的商品房,有一个大院子。真加的母亲虽不是亲生母亲,但“由衷地疼我爱我”,一家三口以及小狗奥利弗一起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
作者一再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宇宙”等词来表明一墙之隔的两个家庭的氛围之差。早春时节,院子里已经能够感到“微微暖意”,但是院子另一端的裕志家仍是“寒冷的世界”。在明亮与晦暗、温暖与寒冷、生机与死寂的对照中,我们更能够体味院子这一空间所具有的意义。
此外,院子作为一个空间还具有容纳功能。与农家院里收纳用具等不同,真加家的院子容纳并化解着种种情绪。首先就是面对死亡时的心痛之感。裕志的爷爷在初春时去世。尽管裕志一直十分担心爷爷死去,但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法则无人能例外。裕志选择独自面对爷爷的离去,希望一个人整理爷爷的遗物。在整理的过程中,尤其是清理那个“阴森可怕到极点”的巨大祭坛时,裕志发现了更多可怕的秘密[14]27。正是祭坛上这些邪恶之物所代表的力量,夺走了裕志的父母、童年与家庭。掩埋了从祭坛清理出的可怕物什,焚烧掉各种恐怖纸头之后,所有悲哀、不幸、神秘的诅咒消失在院子里燃着的火堆里。不久之后,一直陪伴两位主人公的小狗奥利弗也死了。奥利弗死于樱花时节,真加和裕志守着奥利弗的遗骨,深感“在我们中间,一个时代结束了”[14]18。主人公们不仅一次又一次地与死亡相遇,还初次体味到了青春的丧失感,结束的这个时代就是主人公们的青春。面对死亡与丧失,真加不禁思考与叩问生命之意义,“既然迟早要回归泥土,为什么还要出生、生活?”[14]29主人公最终在院子里觅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自然的缩影,院子里的四季变迁就像严谨的日本茶道一般,程序流转毫无多余,“花开花落,枯叶落地,所有一切将在下一时段不知不觉间形成渊源”[14]54。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缘此,面对目前的处境,真加决定不再纠结沉溺于裕志消沉的情绪中,而是尽可能活在当下,做好眼前事,不去做无可挽回之事。
真加借由院子这一空间展开女性思索,她从女性视角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点滴思索爱情、家庭等女性话题。在两个人的爱情里,裕志是“沉默不语”的存在,他依赖真加,却毫无言语表达。尽管如此,真加依然能够体会到裕志的爱,“他的爱,宛若开放在空壳里的一株小小的雏菊”[14]19。在真加看来,裕志的爱静谧恬淡,自然不造作。真加珍视这样的爱情,愿意陪伴裕志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遭遇,静静地等待裕志重新振作。陪裕志清理完爷爷的遗物和可怕的祭坛之后,真加的继母建议他们去真加生母所在的城市——布里斯班旅行。回想起与父母相处的点滴,经过一大段心理独白之后,真加又联想到院子,“我是非常现实的。若非如此,院子不会带给我冥想空间,院子里的风景将变成容纳我娇纵的心的延伸,即被随意排放的美梦的空间”,紧接着又说,“父母则恐怕在疼爱我这个拥有不太可谓一般的经历的女儿的同时,内心某处却早已想要赶我出门”。尽管如此,真加却坚信自己对院子的深厚情谊,“即便成了老太太也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在院子里度过余生”[14]66。这一段描述中的“院子”,是家庭的象征,真加对于自己与院子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事实上是对自己与家庭的关系的反思,不管身处何种境遇,家总是人们避风的港湾。
陪伴裕志重新振作的过程中,真加还悟得许多人生真谛。例如,小说中将事物复原的过程与四季变迁相类比,“事物复原的过程是赏心悦目的,和季节的变迁相似。季节决不会变得更好,叶落叶茂、天青天高,只不过像一种发展趋势而已。和这一过程很相似,当我们的心情恶劣到以为世界末日来临,那种状况却一点点地发生变化,尽管并非有什么好事发生,我们却从中感觉到某种伟大的力量”[14]77。本部分结尾处,作者也写道:“即便被迫闭居高楼大厦的一室,山川河海皆不得见,但只要体内鲜血奔流,人就能沿着类似于大自然流转的生命之河活下去”[14]77。在院子里,关于爱情、家庭、生命等的思考,使得少女变得更加坚定、独立、善解人意,最终在布里斯班壮丽的海边,两位主人公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开始谋划未来的日常生活。
四、禁锢与自由的空间——橡果姐妹的网络空间
厨房、院子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中的生活空间,被人们赋予了种种内涵。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网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芭娜娜的小说中亦有所体现。小说《橡果姐妹》依托网络空间展开叙事,主人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姐妹,姐姐叫橡子,妹妹叫果子。两人的父母原本是一对充满童心的恩爱夫妻,因一次交通事故双双离世。失去父母之后,姐妹俩辗转寄宿在亲戚们家中。她俩先是在静冈县的叔叔家度过了平静的童年时代,后来叔叔猝死,婶婶改嫁,万般无奈之下,她们被姨妈收养。正是这段寄宿姨妈家的日子,导致了妹妹果子的自闭与抑郁。后来,在律师的斡旋之下,她们开始与性格怪异但品行高洁的爷爷一起生活并照顾他直至其离世。姐妹俩在与爷爷相处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在爷爷离世后开设了名为“橡果姐妹”的交流网站,通过网络与人交流,安慰别人的同时也解开了自己的心结[15]1。
所谓的网络空间,是“一个概念空间、符号空间、思维空间,也即一个自为的人造空间,而非一个自在的实存空间或物理空间”[16]。网络空间延伸和拓展了日常空间的领域,尤其是人们的话语空间。女性开设网络空间,是女性主导自我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女性向公共空间迈进的途径之一。《橡果姐妹》中,姐妹俩开设网站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与人聊天来排遣心中的烦闷”的空间,网站的指导理念是“想给人写信,却不想写给熟识的人。就是这种时候的绝佳选择”[15]2。姐姐负责写信,妹妹负责提建议以及其他事务性工作。“在网络社会中,情感和文化认同会促成一种集体的默契行动。”芭娜娜笔下的网络空间叙事也是如此,橡果姐妹通过网站与深陷困苦中的陌生女性交流,实现了女性之间的互助。
父母离世后,俩人在静冈县的叔叔家寄宿的童年时光是平静而美好的,“到处是一派自然景象,晚霞那么灿烂,星星月亮也都闪闪发光,随处是温泉,冬天比较温暖,春天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14]15。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叔叔心肌梗塞猝死,婶婶改嫁他人,姐妹俩只好由本就与母亲关系不和的姨妈暂时收养。在姨妈家的日子,她们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压抑。由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再加上姐姐因不愿接受姨妈安排的相亲而离家出走,妹妹果子频繁出现幻觉、幻听等精神异常现象,孤独的少女干脆将内心封锁了起来。虽然最后果子被姐姐从姨妈家解救出来,但是这样的少年经历,造成了果子日后的幽闭性格。不管是在姨妈家,还是后来被姐姐接到爷爷家,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空间的改变并未使果子的内心症结得到改善。果子可以几天闭门不出,姐姐外出后,“家里的空气仿佛全然凝固不动”,“这半年来,我去过的地方就只有这家超市、DVD出租屋、书店,再就是星巴克了。”果子幽闭自我,认为“世道奇怪,反而是人更令人感到害怕”,对现实世界的人与事物十分抗拒,甚至觉得“现实世界全部是我内心反映并创作出来的,也未必是谎言”[15]3-9。
姐姐橡子似乎比妹妹看起来坚强独立、勇敢固执,更具有反抗意识与叛逆精神,是妹妹的“城堡”。姐姐拒绝了姨妈安排的相亲并离家出走这件事,足以证明其反抗与叛逆的性格。此后,虽然姐姐仍常常会陷入爱情,但她只顾享受爱情初始的甜蜜,拒绝长久稳固的婚姻。对于恋爱的态度,姐姐认为比起构筑一个家庭,更应关注爱情中自己的样子,这又是姐姐强烈的女性主体性的一种体现。下面一段引文可为佐证。
我喜欢谈恋爱,喜欢它带给我的无限遐想,喜欢在他和我面前膨胀得慢慢的空间。……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想我并没有把对方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去想象和他在一起自己会怎样?只是想沐浴在由那个人所引发的想象的洪流之中[15]85。
橡果姐妹通过网络与外界交流,生活空间似乎得到了无限延伸,但事实上她们依旧沉浸在自我意识构筑的狭小空间里。与她们邮件往来的也都是些寂寞孤独的人,因在现实中没有可诉说的对象或者个人烦恼难以与身边人分享,因而通过网络途径来实现宣泄。这些烦恼可能来自因照顾生病的家人而无法外出旅行而苦恼的“咪咪”,还可能是与丈夫死别,满脑子都是与丈夫有关的回忆的“安美”。总之,都是内心苦恼但无法与人诉说,或者找不到倾诉对象的女性。姐妹俩开设的网站,为这些孤独苦恼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安放之所。“在回旋于宇宙空间的意识夹缝里,我们编织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夹缝的空间里,我们橡果姐妹结成像蜘蛛一样的巢,构建出一个小小的空间。”[15]7但是,网络的存在也并非全都是益处。网络一方面为人们彼此间的交流提供了快捷的方式,另一方面却阻隔了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这种现象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如文中所言:“谁都会认为问题是私人的,而实际上在这无限的空间之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着的,这才令人不安。”[15]7正是这种不安,让人们更加禁锢自我,以此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
风暴再大亦有风平浪静之时。爷爷的去世让她们不得不面对生死以及财产等复杂问题。再加上姐妹俩开设橡果姐妹网站,收到各种各样的来信,闻得诸多故事,看过百态人生,从中悟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那便是遵循自然与常规,顺应潮流,随着潮流变化去改变自己。从爷爷的离世、姐姐的恋爱到网友的来信,再到梦中出现的初恋男友阿麦,橡果姐妹似乎重生了。循着回忆与梦境以及安美女士的来信,妹妹果子预感到了初恋男友的离世,这个消息同时也得到了中学同学的证实。世界处在联系之中,如同网络一般充满暗示。果子终于意识到自己“消沉”“蛰伏”的原因正是阿麦的离去。当果子手捧鲜花来到阿麦的家乡,并在游艇码头偶遇阿麦的母亲时,内心深深的歉意、青春的回忆、压抑许久的悲伤一并涌上心头,随之即“飘散于风中”。果子决定去迎接新的人生,从“头”开始,去做了时尚的发型,购置了喜爱的新衣,谋划着一场旅行。对于姐姐的感情生活,果子也希望姐姐“不再偏执于性爱,而能踏出找寻男女关系中的真爱与关怀的第一步”[15]88。
小说在姐妹俩的冲绳之旅中落下帷幕。芭娜娜通过《橡果姐妹》的字里行间营造了一个幽闭的生活空间,这种幽闭特性体现在现实、梦境以及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即便如此,灵魂却跃跃欲试,意欲冲破这牢笼,重获自由与安宁。网络空间的出现,为女性的内心隐秘提供了言说的平台,并有了得到回应的可能性,女性的话语权不再受到束缚,女性可以自由发声去表达自己,由此,女性才能走出伤痛的阴霾,去勇敢地面对人生。
五、结语
芭娜娜的小说总是在某个空间中展开,这个空间可能是厨房、院子,抑或是虚拟的网络,既是物理性空间,又是精神性空间。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芭娜娜描写的空间在现实中大多是私人的、隐秘的、微观的空间,对公共的、开放的、宏观的空间不甚涉及。芭娜娜注重空间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抚慰,对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等命题不够关注。这是芭娜娜小说中空间叙事的特点,也是芭娜娜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即希望人们读毕小说能获得某种慰籍。芭娜娜所描写的这些空间,都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置身其中的女性思考生命、家庭、婚姻以及爱情等女性问题,勇敢地追求自我、自立与自由,体现了芭娜娜对女性生存与成长的关注。
如上论及的空间中,厨房为人们提供一日三餐,在倡导“贤妻良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被禁锢于家中,往往因反叛父权夫权而厌恶厨房,渴望逃离厨房的桎梏,而芭娜娜笔下的女性美影却强烈地热爱着厨房,并且从厨房中获得慰籍与希望。院子是内部住宅与外部社会的中间地带,能够阻隔外界干涉,消解人的情绪,是女性思考与成长的原点。网络空间则进一步延伸与拓展了女性的话语空间。总之,不同的空间场域在芭娜娜的小说中登场,并生产出了更加开放的家庭关系、更加和谐的两性关系以及更加多元的人际关系等新型的社会关系。这些正是现实社会的需求在文学中获得的回应。伴随着日本社会经济水平的发达,信息化社会的日渐跃进,人们的精神家园越来越贫瘠,“低欲望社会”“下流社会”“女性贫困”“平成废物”等一个个标签警示着日本社会中涌动的重重危机。芭娜娜小说中描写的年轻男女在面对死亡、失恋等人生困顿时,总是想方设法地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以寻求自我的生命价值。从这一点上看,芭娜娜的小说对当今日本社会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