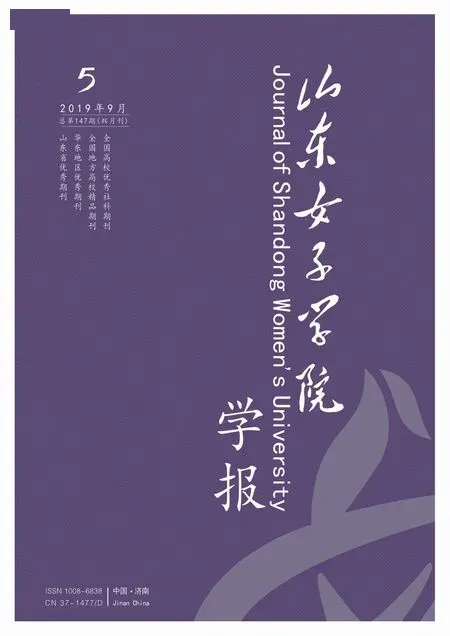娜拉与五四文学中的现代女性范式建构
栾荷莎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娜拉与五四妇女解放思潮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从最初的学生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融合在一起,成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一次文化领域的革命,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端。五四运动并非简单的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观念冲突,而是已经成气候的“子”的文化试图废黜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父”的文化[1]4,是青年中国与老旧中国激烈的对抗,它虽然没能彻底撼动旧制度与旧思想,但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也揭露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压迫。现代女权思想在这一时期空前高涨,妇女解放成为贯穿整个五四时期的重要主题。青年领袖们发起了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并开始系统地宣扬女权思想。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开设了一个“易卜生专号”,并且跟罗家伦一起翻译了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娜拉》(其后来一般被译作《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在中国大热并开启了一个“娜拉”时代。《娜拉》的女主人公娜拉是一位年轻女性,婚后育有三个子女。她深爱着丈夫海尔茂,并未意识到丈夫仅仅是把自己当作玩偶。海尔茂得过一场重病,娜拉为了治好丈夫的病,背着他冒用垂死的父亲的名字借了一大笔钱。海尔茂的身体彻底痊愈后,娜拉要继续背着他慢慢还这笔欠款。一天,海尔茂得知了此事,对娜拉大发雷霆,辱骂她和她已经过世的父亲,责备娜拉毁了他的名声,并且要剥夺她对孩子的教育权。而当问题很快被解决后,海尔茂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声称原谅了娜拉,并且愿意以后好好教育她。娜拉原本天真地以为,如果借款事件败露,他的丈夫会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而她不愿意连累丈夫,早就打算好了由自己来承担一切后果。事情发生后,丈夫的态度令她震惊和失望。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自私伪善的丈夫的玩偶而已,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家庭。
娜拉最后摔门出走的一幕大快人心,因此也深入人心,它恰好满足了五四一代叛逆青年对于挣脱传统家庭禁锢的期待。娜拉的宣言“我首先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2],与娜拉的出走一道,为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潮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范式和行为范式。娜拉在中国迅速成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象征。一时间涌现出众多的“娜拉剧”。为了逃脱包办婚姻,众多五四青年男女叛离父亲的家庭,“出走”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胡适作为《娜拉》的译者和易卜生研究专家,亲自操刀写了一个剧本,名为《终身大事》(1919年)。该剧本的情节较为简单,女主人公田亚梅是一名留过洋的现代女性,她爱上了陈先生。但她的母亲出于封建迷信思想,首先反对这门亲事。她的父亲虽然不迷信,但却固执于祖宗祠规,认为“田”与“陈”本是同姓,因此也反对二人结合。最后,田亚梅跟陈先生离开家,留下了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3]。《终身大事》明显受到《玩偶之家》的影响,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尤其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在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另外,这部作品的细节之处用意颇深,比较典型的是两个家庭的姓氏,“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意味着封闭,代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老旧中国的象征。当时的个体若想获得解放,似乎只有像娜拉一样出走才能突围。
二、死者“娜拉”
五四时代的作家们一方面鞭笞老旧中国,揭露旧社会对当时的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建构了为自由、尊严而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中把五四文学概括成“两个死者,一个镜像”:其中一个“死者”是鲁迅笔下的旧女性祥林嫂;另一个“死者”是鲁迅笔下的新女性子君;镜像是娜拉[1]8-13。祥林嫂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受害者形象,她生平遭遇诸多不幸,只知道一味顺从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最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而子君则是五四一代新女性的典型,虽然也曾反叛过,追求过自由爱情,还发出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但与爱人涓生同居后陷入经济与生活的窘境,仍不免英年早逝。可见当时社会留给女性的生存空间仍然十分狭窄,无论是顺从还是叛离,女性的生存都充满艰辛。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其中有庐隐、冯沅君、陈衡哲、凌叔华、冰心、石评梅等。这些女作家直接受益于20世纪初女子教育的制度化,她们接受了现代教育,拥有中国或西方大学文凭。“娜拉出走”是贯穿整个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女性作家们关切当时女性的解放路径与困境,建构出多种本土化的“娜拉”范式。
冯沅君的三部曲《旅行》(1923)、《隔绝》(1923)和《隔绝之后》(1923)是作者根据表姐的婚恋经历以及自己的某些经历而进行的创作,讲述了一个女青年为反抗包办婚姻和追求自由恋爱而进行的生死抗争。这三部作品虽然各自独立,但放在一起则成为“同一对男女主人公的一部情节连贯的有头有尾的五四青年爱情三部曲”[5]30。在《旅行》中,一对叛逆的青年男女私自去旅行;在《隔绝》中,出走多年的女儿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母亲却把她囚禁在房间中,逼她嫁给刘家财主的儿子;在《隔绝之后》,刘家迎亲的日子到来,一对恋人被迫自杀殉情。事实上,冯沅君的表姐进行过绝食反抗,最后家人答应了她的婚姻自主要求。但在《隔绝之后》,作者给一对恋人安排了惨烈的结局,是对传统礼教更有力的控诉,表达出捍卫婚恋自由的决心。这几个文本充斥着五四时代典型的宣言式话语,如“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6]2“我们要立志实现Ibsen,Toltoy所不敢实现的……”[6]7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父亲是缺席的,母亲代替父亲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母亲向来何等慈爱,但是在女儿的婚恋问题上却变得异常残酷。女儿在新思想和旧风俗之间被撕裂,在男女之爱和母女之爱间被撕裂,在逃离计划未果的情况下只好以自杀来成全爱情与孝道。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年轻女性自杀潮成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突出的社会现象。在此期间,女性自杀人数明显超过男性。自杀女性中既包括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也包括传统妇女;既有城市女性,也有农村女性。其自杀的原因主要是婚恋不自由、家庭问题以及生计问题[7]。在五四文化激烈变革时期,年轻女性们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而家庭观念和社会结构却严重滞后,导致了其无法化解困境,从而选择自杀[8],这是“五四”女性自杀潮产生的深层社会根源。
女性离家出走在当时的西方也是一个重要议题,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这一议题发表过看法。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提到16世纪西方女性的绝境。她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跟莎士比亚有一样的天赋和热情。桀骜不驯的哥哥去伦敦寻求出路,最终因为才华而出人头地。妹妹从小没有像哥哥那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十六七岁时家人就给她指定了婚姻,她拒绝了。父亲为此打了她,逼她结婚。于是她离家出走来到伦敦,渴望成为一名戏剧演员。但女性在当时不能成为演员,演员经理对她动了怜悯之心而接纳了她。但随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最后,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伍尔夫悲叹道:“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的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孤独的茅舍里了结一生。”[9]在伍尔夫时代,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女性仍然无法拥有自己的一间房间。社会对女性仍然持排斥态度,这从伍尔夫提到的大学图书馆不允许女性进入这一事实中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的出路问题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
三、独身者“娜拉”
中国的“娜拉”们叛离了父亲的家庭,这只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中国传统“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惯性力量在五四时期仍是阻碍妇女解放的桎梏。在逃离了父门之后,中国的“娜拉”们或在父权社会中迷失,或在婚姻中迷失。事实上,父权仍然强大且绝不仅仅体现在父权制家庭当中。“娜拉”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就需要突出重围,而多数新女性在追求解放道路上都止步于婚姻。
然而,女作家们笔下的“娜拉”仍在跌跌撞撞地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果说冯沅君的《旅行》和《隔绝》均是第一人称叙事,经常使用复数“我们”,体现出五四青年男女在婚姻自由的抗争中结成“叛逆之爱的精神同盟”的话[5]31,那么庐隐和陈衡哲笔下的女性已经不再毫无保留地信任这种脆弱的精神同盟,而是个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并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独。其中女性人物露沙和洛绮丝是两个选择独身的“娜拉”。
在1925年发表的《海滨故人》中,庐隐揭示了具有现代精神的女青年和依然无处不在的传统力量的不相容,勾勒出受新旧思想撕扯的苦闷彷徨的时代女性形象。庐隐在小说中把几个青年女学生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封闭的女儿国,但这个小世界最终受到男性入侵并解体。故事一开始,同一个学校的五个女学生正在一起度过无忧无虑的暑假。但很快,她们接二连三地被婚恋问题卷入到愁云当中,她们要获得婚姻自主权并非易事。故事的第一女主人公露沙得了“哲学病”,露沙性情孤僻,人生观很消极。她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因此陷入到忧郁与悲观当中;她不信任他人,甚至在唯一的亲人病逝后,仍然拒绝了所爱之人的求婚,宁愿孤身一人。跟露沙一样,故事中的其他几位女孩也被“哲学病”所折磨。她们是受到过良好现代教育的新女性,但她们的人生观跟父母一辈的人生观相冲突,在生活中仍然没多少选择的自由和权利。她们把这些愁烦归咎于现代教育,发现自己受教育越多,精神越痛苦,越与世界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庐隐笔下的年轻女性们不再天真地、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托付给男性,哪怕是自己挚爱的男性。
陈衡哲——五四以来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在《洛绮丝的问题》(1924年)中,虚构了一个西方世界中的女性人物。哲学博士洛绮丝与著名教授瓦德相恋并订婚。但洛绮丝担忧婚后家务劳动和子女教育等会妨碍自己的事业发展,最后与瓦德协商取消了婚约。瓦德理解洛绮丝,很快跟别人结了婚。洛绮丝则独身一人,潜心于学术研究。人到中年的时候,洛绮丝已经是一名享誉世界的哲学教授。但她为牺牲了爱情和婚姻而感到痛苦:“她此时才明白了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么了,名誉吗?成功吗?学术和事业吗?不错,这些都是可爱的,都是伟大的,但它们在生命之中,另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或者能把灵魂上升至青天,但它们终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10]65最后,她不得不接受生命中的这种残缺。这种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撕裂只有在像洛绮丝这样的女性身上才有,而男性无需受此折磨。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五四女作家认同核心家庭,但即便是核心家庭,仍然把女性封闭在家庭琐事中,妨碍着女性的个人发展。中西方的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撕裂,选择自身发展的女性最终也难免落入孤独。
四、欲望者“娜拉”
五四期间,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从女性视角被探讨。然而,女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女性的身体和性欲问题。在冯沅君作品中,叙述者反复强调自己与爱人之间的纯洁。文中省略号的多次出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叙述者虽然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却在男女问题上遮遮掩掩,连诸如“结婚”“夫妻”这样的字眼都需要用省略号来代替,而“接吻”一词则用英文“kiss”来代替。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女作家凌叔华在短篇小说《酒后》中也是自始至终用“kiss”代替“接吻”。如此看来,无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有多叛逆,她们仍要保持肉身的纯洁,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外界的攻讦,保持叛逆爱情的神圣性[5]34。根据孟悦和戴锦华的观点,五四的女儿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和文化积淀,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跟童年说再见,因此,她们的反抗是典型的女儿的反抗,她们的文学创作“充满了青春、骚乱、幻想、脆弱、幼稚和肤浅,不具备成人那种老辣坚定的目光。”[1]16
到了五四后期,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了显著提升。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变得更加立体丰满,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女作家们开始冲破禁忌来展示女性经验,甚至女性性欲。她们笔下的女性在不停地跟自己的欲望和男性的欲望周旋,往往在逃离了一种欲望的陷阱后又陷入另一种欲望的陷阱。
这一时期,丁玲在文坛崭露头角,其作品比陈衡哲一代更为复杂、细腻和成熟。丁玲笔下的女孩们已经不再受到父权家庭的禁锢,而是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她们的痛苦和绝望却并未因此而减轻。《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一部中篇小说,其体裁是私人日记,通过向私人日记倾诉的方式展现了一名女性强烈的欲望。女主人公莎菲远离家庭,独自一人,身体孱弱,精神萎靡,却充满了激情与矛盾。一方面,她残忍地折磨爱她的苇弟——一个同样软弱而敏感的男孩;另一方面,她受到花花公子凌吉士外表的诱惑,被强烈的欲望折磨着。她明知道自己爱的只是凌吉士的迷人外表,而不是他卑鄙庸俗的灵魂,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对他充满了炽热的情欲。她的日记里充满了她无法对他直接言说的欲望:“假使他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11]66此外,莎菲多次使用精神分析术语“下意识”,莎菲的理性和被压抑的欲望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对抗,最后,理性占了上风,莎菲决定离开去另一个城市。
中国现代文学在使用精神分析术语、概念和方法的同时,也从中汲取灵感,把女性性欲内在化和主体化。莎菲的痛苦不仅仅来自被压抑的欲念,更来自她复杂的内心,就如丁玲本人一样。丁玲曾经是理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创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期间经历了政治与人生理想的幻灭,过着贫困、堕落而绝望的生活。莎菲跟丁玲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痛苦和绝望并非完全因为爱情,她所寻求的是生命的意义[5]160。
现代女性文学在日占时期的上海达到一个新高度。由于政治审查,作家们被限制,欲望与婚姻是其书写的重要主题。苏青和张爱玲是佼佼者,她们笔下的女性没有了五四“女儿”式的激烈反抗,而是冷眼洞察一切,以女人的姿态在家庭和社会中求得生存。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1943年)讲述了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从结婚到离婚的十年历程,展示了一代新女性在婚姻中和社会上的挣扎与无助。女主人公怀青跟丁玲笔下的莎菲一样都是充满炽热欲望的女性。《莎菲女士的日记》采用的是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常见的私人日记体裁,莎菲只能把全部情欲诉诸日记,而《结婚十年》采用的是自传体小说形式,女主人公怀青多次肯定女性性欲的存在。怀青在有未婚夫的情况下跟另一个同学相恋,充满少女怀春的幻想:“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12]23然而,生活在一个半新不旧的社会里,无论女主人公在思想上有多大胆前卫,在行动上仍处处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12]241940年代的女性在思想上显得更为奔放,对旧思想有一种不屑的嘲讽,但行为范式跟1930年代相比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怀青与莎菲在行为上处处体现着传统女性的矜持与被动,而男主人公们则表现出主动性和进攻性。
除了表露女性性心理之外,《结婚十年》也详尽而直白地描写了女性的诸多生理体验,如女主人公怀孕、分娩和哺乳。张爱玲赞扬苏青小说是“伟大的单纯”,而同时代的一些人则抨击苏青的小说是色情小说,还有人辱骂苏青为“文妓”,并对她的私生活有诸多揣测。的确,女性以第一人称书写几乎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读者会把小说内容与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的私生活等同起来,甚至直接把自传体小说等同于自传。直到20世纪末也是如此,林白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在发表之初就被某些人视作准色情小说,有人对其私生活进行揣测。但危险之处也是其价值所在。过去,女性一直是被男性书写的客体,虽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写作在近些年被发掘得愈发充分,但毕竟整个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绝大多数是男性的创作。因此,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几乎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通过写作,尤其是用第一人称写作,能够以女性的名义让女性成为观察主体、思考主体和话语主体[5]157,夺回被放逐的身体与被压制的主体性。
五、战斗者“娜拉”
早在晚清,《玩偶之家》未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女性文人已经表达了挣脱家庭束缚的渴望及投身革命的雄心。秋瑾女士曾经创作过大量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和革命色彩的著述。她使用的是传统文体,其中弹词《精卫石》创作于1905—1907年之间,表达出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中华民族女性处境的羞愤之情,认为只有推翻旧制度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和女性解放。在书写现实的部分,黄菊瑞和梁小玉等受传统礼教压迫的女性在西方女权的感召下走出家庭,远赴东洋求学并投身于革命。秋瑾揭示了女性命运与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只有女性强才能国强;反过来,只有建立一个文明的新世界,女性才有可能真正翻身。《精卫石》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秋瑾本人也是一个“娜拉”:她对包办婚姻不满而离家去日本留学,并投身于民族革命,直到英勇牺牲。在很长时间里,秋瑾的榜样仍不失为中国的“娜拉”们的重要出路。受到过易卜生影响的郭沫若在悼念秋瑾的文章《娜拉的答案》(1942年)中写道:
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我们的秋瑾先烈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13]。
秋瑾是中国女性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她奠定了现代女性文学的精神气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经动荡,女性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1924~1927年发生了国民革命;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这些革命与战争都在号召中国男女参加战斗。面对民族危机,一些女性自愿放弃五四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而参与到战争中。
一些投身革命的女作家记录了战斗中的“娜拉”的形象。谢冰莹在其军旅生涯中写了许多战地随笔和散文,并在报上发表,同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引起了国际反响。谢冰莹一生激荡曲折,她在国民革命爆发后考取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次年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回乡,她为反抗包办婚姻再次离家出走,曾经在上海和北平读大学,并两渡去日本求学[14]383。在日期间,由于拒绝拜见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而被逮捕,身心受到摧残;被遣返回中国后,她再次赴日留学。抗日战争一爆发,她立即回国参军。她的作品从一个女兵的视角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战争生活和民众的革命热情”[14]383,同时也对女性解放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一个女兵的自传》讲述了一个逃避包办婚姻的女孩参与国民革命的经历。文中提到,女孩子们参军本是为了摆脱封建家庭的压迫,但军装一穿在身上,她们立即有了民族解放的使命感。过去饱受过旧礼教压迫的女兵们并没有急切地想谈恋爱,而是急于投身革命。战士们抛弃了狭隘的爱的观念,“代表着的是国家的爱,民族的爱”[14]120,“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面”[14]120。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代的丁玲在其政治立场和文学创作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此时的她已经摆脱了梦珂和莎菲时期的忧郁、迷乱与消沉。她投身革命并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战争中的女性的作品,比较典型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这些作品中,丁玲塑造的革命区女性的形象,揭露了女性问题在主张两性平等的革命区的切实存在,同时也揭露了群众对妇女存在偏见的落后思想。在《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中,农村女孩贞贞被日军俘虏,成了日军的性奴。后来她有机会逃脱,但她选择留下来为中国部队提供情报。她因此染上了性病,最严重的时候肚子里面都烂了。有一次她接到紧急任务,夜里来回走了三十里路,她走一步痛一步,提心吊胆,怕被日本人发现,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当贞贞最终回到霞村后,却受到村民们流言蜚语的困扰。人们因为她性奴的经历和她的性病而把她看作耻辱。有人说她被一百个男人睡过,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还有人说她的鼻子都烂没了;而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尊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11]364而贞贞却有着小村“娜拉”的特质。她天性活泼开朗,有着很强的个性。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同情,最后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决意离开家乡去延安。她憧憬到延安后有一番新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是自己的。”[11]370
六、结语
在五四反封建的大背景下,宣扬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玩偶之家》为中国青年一代提供了反叛传统的话语和行为范式。“娜拉出走”既成为新女性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然而,娜拉出走后怎样?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文学领域,现代作家们通过构建不同的“娜拉”范式来揭示妇女解放的路径与困境。其中“死者‘娜拉’”既是对封建礼教之恶的揭露和反抗,也体现出女儿“娜拉”的天真与脆弱;女作家们创作的“独身者‘娜拉’”,是对娜拉出走后“堕落”或“回来”这两个出路的拒绝;“欲望者‘娜拉’”进一步突破禁忌,让女性作为主体来展现女性经验并肯定女性性欲的存在;“战斗者‘娜拉’”则放弃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像男人一样投身于革命,以期在民族的解放与制度的重建中获得自身的解放。这四种“娜拉”范式不但是整个五四时代的写照,而且对中国当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文学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