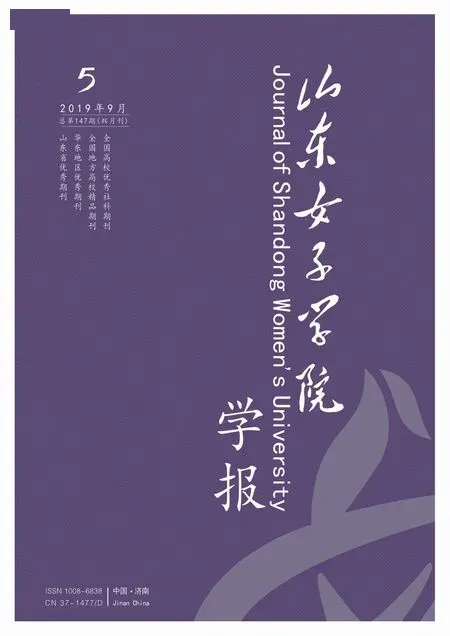唐代女医群体研究
徐艳芹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医患关系及疾病治疗中,儒家男女有别的两性观念逐渐划定了男女各自的生活空间,使男医与女患之间产生了隔阂。医人群体以男性为主这一情形导致女性患者疾病治疗的延误,最终对女患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这也就为女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和必要。太医署作为封建王朝正规的医人教育与培训机构,其始设于隋代。之后唐承隋制,亦设置太医署,又命医学博士教授宫廷女医医疗之法。另从唐传奇小说及相关医书记载中可知,唐时民间也存在部分掌握医治技术的女医和女巫:女医多以正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为病患治疗疾病;而女巫多以符箓、咒术等手段为患者解除病痛。从两者的职责来看,女医、女巫均为当时妇女的健康照顾者,都在本文所要论述的女性“医”的范畴之内。又考诸正史及相关文献,其间较多使用“医人”“医者”两词,均可指称古代社会中的“医”。本文所讲女医,即为医人或医者中的女性群体,她们掌握部分医学知识和技术,并为古代妇女提供医疗帮助。
学界关于古代医者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文中所要探究的女医的学术著作也不在少数。关于唐代医者的考察,以台湾学者李贞德的著述为多,如其创作完成的《女人的中国医疗史》[1]及其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2]79-158两部著作。另有《唐代的性别与医疗》则从《外台秘要》中的一则妇女生产故事探究唐代的生育文化和女性医疗照顾者的作用[3]。具体的唐代医者研究,包括了医学教育、人员选取、医人仕进及其社会地位等问题[4-8]。再有从唐代士人等知识阶层的文学作品中分析医者的文本书写、叙事和形象塑造[9-10]。笔者开始关注唐代女医这一群体则是从李志生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一书开始,“中国古代的妇女医护”一讲中讲述了四类女性医护者,并分析了男女有别观念下男医与女患身体接触中的矛盾[11]259-283。
《天圣令》是近二十年间学界探究唐宋政治、经济、医学等问题不可忽略的史料。上世纪末,戴建国教授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发现了残十卷本的《官品令》,目录上标明为“明抄本”。而后众多学者开始将此册古籍记载与唐宋正史、会要等文献作对比探究,其中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着力最甚,进而推动了唐宋研究的进程。与本文所要论及的唐代女医有关的记载为《天圣令·医疾令》唐令第9条“女医”条。近些年关于《天圣令·医疾令》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程锦从“女医”条考察唐代女医制度和女医教育[12-13]。于赓哲从《医疾令》中发现官方医学对民间医学的尊重与采纳以及当时医学体制的开放与包容[14]。楼劲在程锦论述唐代女医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探究,他分析了太医署女医的来源及其特殊身份,女医学习内容和唐代“女医”制度的缘起等问题[15]。
针对中国古代巫医的讨论,宋镇豪认为在商代鬼神崇拜的社会风气下就有巫师作医的历史现象,巫术与医术结合,巫医掌握一定的疾病治疗术[16]。赵容俊从甲骨卜辞记载探究了先秦时期“巫医不分”观念下巫医的医疗活动,即为医疗巫术和逐疫除凶两种[17]。秦卿根据文献记载分析认为,魏晋时期巫与医出现职能分工,巫主要从事占卜及治病救人,而医趋向科学化的救治,进而导致其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变化[18]。王晓玲探讨了唐代女巫的交往圈,其通过女巫通鬼神的手段及社会职能和女巫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等问题,窥探了唐代民众的鬼神观念[19]。李小红则主要对宋代巫觋群体生存方式、社会地位及职事等进行了深度考察,又通过对巫觋群体与宋代社会相互影响的关系分析,评估了宋代在古代巫觋发展史上的地位[20]。
本文在以上唐代医者、《天圣令·医疾令》和古代巫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唐代女医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考察唐代宫廷女医的受教育情况,探析此时期女巫的文本书写和形象塑造,进而实现对包含宫廷女医和民间女巫在内的唐代女医群体的全面了解。
一、唐代女医的产生及其社会地位
(一)女医的概念界定
正史记载最早的女医为汉武帝时的义姁,据《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载:“(义)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21](卷90)3652此处的义纵之姊即为义姁,她凭借自身医术得到武帝之母王太后的赏识。汉宣帝时,又有“女医”淳于衍,《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霍)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哀后。”[21](卷8)251卷六十八《霍光传》记载:“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21](卷68)2952颜师古注曰:“乳医,视产乳之疾者。”[21](卷68)2953卷九十七上《外戚传》记载:“明年,许皇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21](卷97)3966《古列女传》卷八《霍夫人显》又载:
会宣帝许后当产疾,显乃谓女监淳于衍曰:“夫人孑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孑免身,可因投药去之,使我女得为后,富贵共之。”[22]
由上述关于淳于衍的史料可知,其身份为“女侍医”“乳医”“女医”“女监”,尽管称谓有所不同,但其职责应当都是为宫中女眷提供生产、疾病医疗等帮助。因此,义姁、淳于衍均为当时的女医。“十死一生”也表明当时妇女在生产时将会遭遇极大生命危险,可见女医们担负着重要的助产职责。
王慧芳、楼绍来在《中国古代女医初探》一文中提及:“宫廷女医的设置,直到汉代的‘少府’机构中才有。”[23]但据《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记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东园匠十〔六〕官令丞。”[21](卷19上)731又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21](卷19上)726两处均无女医的明确记载,故汉代或许并未明确设置女医这一宫官,女医也有可能包含在太医群体中。宫中妇女需要女医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当时如义姁、淳于衍等女医大抵有责而无职。故可推测,古代女医多为男医治疗女患疾病的辅助者,也是直接为女患提供医疗帮助的医者。
(二)唐代女医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地位
唐代女医缘何产生?是当时的男医不能治疗女性患者的疾病吗?是男医的技术性问题,还是男医与女患之间的观念隔阂?佟新教授认为,与西方宗教从身体结构的角度论述男女关系不同的是,中国则是基于防范所谓的“男女之患”而强调“男女有别”[24]。
《礼记·郊特牲》中有言:“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孙希旦认为,执挚相见是宾客与主人之间的礼节,夫妇之间讲究执挚之礼是为实现互相恭敬的相处之道,也是一种彰显男女有别的方式,以避免男女之间苟且之事。在社会秩序中,父子之亲由男女有别衍生而来,君臣之义又是从父子之情发展而来,君臣高下便造成“义生而后礼作”。这样“由男女有别,而递推其所致如此,所以深明男女之别之重也。”[25](卷26)708《礼记·内则》篇也有类似的男女规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孙希旦解释为,男女之间有内外的职责差别,家事留于家内,家外之事亦不会影响家内的秩序,以使内与外间有严格的限制[25](卷27)735-736。“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25](卷28)768由上可知,男女之间的差别体现在生活中的各处细节,如教养方式、饮食、寝居、沐浴及内外职责分工等。并且男女之别也是父子、君臣关系稳定和“义”与“礼”兴起的重要基础。
由男女之别生出男尊女卑,这是男性在古代王朝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拥有话语权的结果。“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孙希旦解析为,夫妇出行时须由丈夫带领,妇居于其后,表明夫妇尊卑、夫唱妇随之义[25](卷26)709。其中提及“大门”,古有女子不出中门,可见古代妇女多被限制在家之内,操持家庭事务,自由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又有:“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25](卷27)736孙希旦分析为,此处所说“道路”为宫中道路,宫中之路以右为尊,男子行于右,女子行于左,一方面是为规定男女之间的相处距离,另一方面也是区别男女尊卑的途径。
因此,男尊女卑观念使古代女性多为男性的私有物、附属品,这也导致女医附于男医之后。男女有别观念则是两性之间距离产生的原因,“男女有别的另一层含义,即男女身体或空间上的隔离”[11]259,这便是当时男医在处理女患问题中难以跨越的障碍,而女医正好可以弥补男医的这一缺憾。但“中国医学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26]6,“强调读医书以习医的风气,使医学变为士大夫之业”[26]15。当读医书成为医人必备技能后,女医便难以自立;当经验性的医学变成一门需要系统学习的知识后,女医的医疗技术发展便很难进行。
李志生在《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中提出“女性医护者的被边缘化”[11]259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女性医护者自产生之初便是为男医服务的,是男医在治疗女性患者不便时的辅助者。因此,在医疗技术、医典理论大多掌握在男医手中的情况下,因为原初文化水平和后天受教育条件的限制,女医不可能从辅助角色成为核心,也就不存在边缘化的情况。她们只是在男医与女患的观念隔阂中发挥医人的作用。
二、由《天圣令·医疾令》看唐代的宫廷女医教育
据《天圣令》卷二十七《医疾令》唐令第9条“女医”条记载:
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27](卷26唐令第9)319,[28]。
可见当时宫中已有专门培训女医的程序和方法,宫廷女医主要学习安胎分娩和治疗疮肿、伤折、针灸的方法,大多是在男性医生不方便治疗的妇科疾病方面有所学习。
关于“官户婢”一词,李志生将此处女医身份解读为“官户和官婢”[11]263,属于贱民。李贞德认为是指官奴婢,“女医一如乳母,选取自官奴婢,惟年纪较轻”[2]430。程锦则理解为“官户和官奴婢中的女性”[29]。楼劲在《释唐令〈女医〉条及其所蕴之社会性别观》一文中通过辨析“官户”“户婢”等的身份,论证“官户婢”并非官户之女,而是官户和官婢,故应句读为“官户、婢”[15]96。故而可知所选女医的文化素质大多不高,对于医书典籍及医学理论不甚精通,宫中医学博士便采取“按文口授”的方式。这样一方面女医只懂行医之术不通医典理论,保证了男医在医疗和医学文化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女医习得部分行医之术后,可辅助男医治疗女性患者的疾病。
关于“按文口授”中的“文”指何种医典,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载,太常寺下有太医署,太医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禁咒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凡医师、医工、医正疗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30](卷44)1876此处的“医术”,意为学习《本草》《甲乙》《脉经》。《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中所载与之相同[31]。又参考《天圣令·医疾令》,“诸教习《素问》《黄帝针经》《甲乙》,博士皆案文讲说”,“医生试《甲乙》四条,《本草》《脉经》各三条。针生试《素问》四条,《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各二条”[27](卷26唐令第5、7)318。由以上两条令文可知,医生、针生所学内容有所差异,这与其医疗职责不尽相同有关。医生侧重学习唐《本草》等理论性医典,针生则倾向具体针灸操作技术的获取。推及唐代女医的学习内容,医博士多是传授自身所学知识,因此可推测当时女医学习内容大多为《本草》《甲乙》等医学典籍,又因宫中妇女对针灸术的需要,女医也兼习部分《素问》《脉诀》等技术。
三、唐正史及传奇小说对女巫的形象塑造
唐代正史及传奇小说中记载了一些民间女巫。她们或可受召出入宫廷,参与宫廷妇女的医疗照顾,服务于宫中贵族;或可进入官宦之家,为朝廷官员和家属提供医疗帮助。但其大多数游走于平民家庭之间,以所学巫术和医疗经验帮助妇女解决一些疾病痛苦。因此,女巫是介于巫与医之间的复杂群体。在史料记载中,她们不像宫廷女医那样跟随医博士学习正统的官方医学理论和技术,而是学习些经验性的医治技巧。这样的知识获取途径使女巫在唐代正史及传奇小说中多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被贬低的意味。从以下几则相关材料可以窥见知识阶层对女巫的书写和形象塑造。
《旧唐书》卷五十六《罗艺传》中记载一李氏女子:
曹州女子李氏为五戒,自言通于鬼物,有病癞者,就疗多愈,流闻四方,病人自远而至,门多车骑。高祖闻之,诏赴京师。因往来艺家,谓艺妻孟氏曰:“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笃信之,命密观艺,又曰:“妃之贵者,由于王;王贵色发矣,十日间当升大位。”[30](卷56)2279
可知李氏女子掌握治癞医术,且有一定的名气,以至被唐高祖召入京中。“五戒”为大乘佛教中的五条行为准则,可知李氏或是信奉佛教并以佛教戒律规范自身行为。“通于鬼物”则表明李氏或为当时的巫。唐朝儒、释、道三教融合,李氏在以佛教为信仰的同时,也掌握了一些沟通鬼神的巫术。在治疗病患的同时,李氏女子也具有相面的经验和能力。在观察了罗艺之妻孟氏的面相后,告知孟氏有“母仪天下”的贵相。后又为罗艺相面,并告知孟氏罗艺“十日间当升大位”。这似乎是与正史记载中的罗艺反叛相吻合,但占卜、相面之说不可尽信。然从此则材料可看出,李氏女子兼懂医疗技术和相面巫术。
又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吴湊传》载:“氵奏既疾,不召巫医,药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30](卷183)4749此处“巫医”两字或作“巫、医”两类人,或作“巫医”群体。若是巫和医,外戚吴湊患疾病,当有宫中太医亲为治疗,也会有巫以其术参与其中。若作为巫医群体来理解,则表明当时仍存在巫医不分的现象,巫医便是那些既懂得符咒等巫术又掌握部分医疗知识和技术的特殊医者。
《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皋中》中记载唐宪宗时李固言与老姥及其女儿女巫董氏之间的故事:
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明年,果然状头及第,诗赋题有人镜芙蓉之目。……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如其言,诘旦,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恃势用事,莫敢言者[32]。
由上可知,李固言在蜀地遇到老姥为其预言之后的仕宦之路。二十年后,老姥拜见李固言,又告知其有“出将入相”之命。在李固言坐镇蜀地时,外孙九岁不能言语,后寻访老姥之女女巫董氏为其外孙医治。故可推知董氏之术兼及医学治疗之术和巫术祈福鬼神之技。
考察此则故事,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李固言的仕宦经历、段成式对李固言的描述态度、蜀地这一地域在唐朝末期的特殊性、女巫在文中的作用。其一,李固言入仕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数朝,身处牛李党争之间却不参与矛盾与纷争。其二,李固言于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30](卷173)4506-4507。而段成式之父为蜀中名吏段文昌,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朝廷因为段文昌年少时长于西蜀之地,授予其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在蜀地为官之时,“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宽政为治,严静有断,蛮夷畏服”[30](卷167)4368-4369。可见段文昌对蜀中之人的情意和在蜀地的卓然政绩。段成式作为文昌之子,对蜀地之民和政事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之后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固言也当是一种认可和赞扬的态度。其三,蜀地这一地理区域在秦汉文人笔下多被当作蛮荒偏远之地,但历经东晋、南朝及唐朝安史之乱后人员的大举南迁,蜀地不再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它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等情况逐渐为时人所关注,仅从唐朝中晚期来看便有玄宗、僖宗入蜀躲避战乱,可见蜀地独特的防守优势。又知此时期文人之间掀起一股入蜀热潮,因此唐代文学作品中便有诸多蜀地风光、人物的描绘和呈现。其四,老姥及其女儿女巫董氏的出现似乎是为引出李固言的仕宦经历,将神秘的占卜、巫术运用在朝廷官员身上,又为其政治生涯平添一丝传奇色彩。
四、结语
在唐代社会中,女医既是男医治疗女患疾病的辅助者,又是直接为女患提供医疗帮助的医者。她们的产生和存在是为解决儒家男女有别观念所造成的男医接触女患时的不便。当唐代女医有了活动空间后,医学技术的获取便很重要。《天圣令·医疾令》中唐令第9“女医”条记载了当时宫中女医的选取、教育及考试方式。民间女巫在巫术遗留的基础上,也掌握某些疾病医治之法。然而唐代正史和传奇小说中所记载的“女巫”多为撰写者虚构之形象,我们必须从书写者、被书写者、受众、写作背景等多角度分析“女巫”的形象塑造,进而理解其中的文本书写。另外,从职责和技术上来看,不论是宫中女医,还是民间女医,抑或是女巫,她们都在唐代妇女生产、患病时提供医疗帮助和健康照顾,都可以包含在本文所要叙述的女医群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