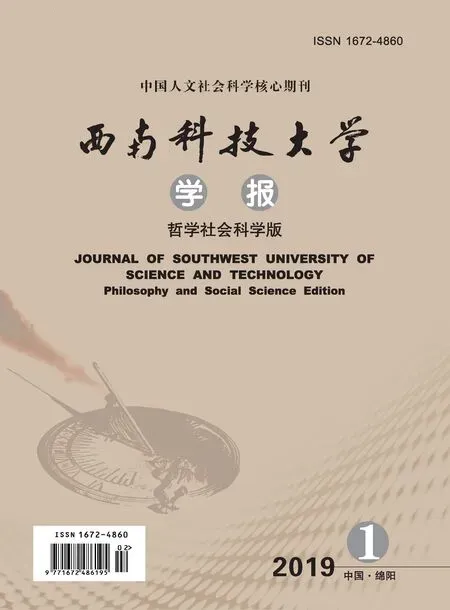论袁宏道的山水自然观
崔 萍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1]567即是称赞袁氏一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之风,追求独抒性灵和率性而行的文学创作情怀。历来研究袁氏作品多注重从其反理学、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以及“性灵”说来探究晚明文士心态,也有从庄禅思想来分析其山水小品文的创作。但袁宏道山水游记中展现出袁氏独特的审美心态和视角所赋予的山水文化品格却没有更加充足的研究。本文以袁氏山水游记为对象,探讨袁氏山水中的文化书写和思想倾向,以求教于通家。
一、山水中见谐趣
所谓山水中的谐趣,是指文学创作者以幽默诙谐的个性化审美赋予客观自然山水以人的思想趣味,这种主观情感不是个人负面情绪发泄,而是着重表现个人内心积极向上的思想态度。赵伯陶先生云:“趣是主、客观两者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是能动而非被动。”[2]123袁宏道作为晚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文学创作中始终奉行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其追求个性解放的特征恰当地体现在他的山水游记创作中。因此,很多游记均表现出“谐趣”的特征。袁宏道山水游记的“谐趣美”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诙谐幽默的语言构造山水内在情趣;二是用拟人来赋予山水自然活泼的个性魅力;三是将个人文学创作主张的抒发与山水融为一体。
(一)以诙谐幽默语言构造山水内在情趣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对于自然山水的文学书写的源流已久,从早期《诗经》中《国风·邶风·谷风》中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3]145借风雨意象渲染气氛,到魏晋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借山水诗歌表现个人潇洒自然的文人情怀,再到唐宋时期以山水田园风光为主题的诗词创作。山水田园作品无论从内在题材,还是外在表现形式,都渐趋完备。而晚明时期,受阳明心学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当时文学创作表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派别与理论主张。
以袁宏道等人为代表的公安派高举反对文风复古的大旗,在个人文学创作中自成一格,尤其在以自然山水风貌为题材的游记散文中,将诙谐幽默的人格魅力与不拘一格的思想主张完美地融汇到山水书写的语言构造中。如袁宏道《西施山》:“余戏谓石篑:‘此诗当注明,不然累尔他时谥文恪公不得也。’石篑大笑,因曰:‘尔昔为馆娃主人,鞭箠叱喝,唐突西子,何颜复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东施娘子矣。’”[4]446袁氏借游览西施山,通过“文恪公”与“浣溪道上皆东施娘子矣”戏谑语,讽刺当时文学界的复古,不知变通的东施效颦的刻板风气,以短小、诙谐的话语将自己追求创作自由与真率的情感价值观融入到自然山水的认知构造中,表面写山,却以戏谑语赋予了西施山社会文化内涵。
袁宏道自身诙谐幽默的品格,通过自我的主观表达,赋予客观山水之中。山水景物不仅具有了人的品格,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袁宏道追求自由、真率的洒脱性格和内在情趣。这种游迹与心迹的结合,使得情与景、意与趣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
(二)拟人化修辞手段赋予山水自然魅力
周振甫先生认为:“自然是对做作说的,指的是不做作,不涂饰,不堆砌。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求精炼,反对陈词滥调,也要写的自然。”[5]342周振甫的观点意在表达文学创作中除要注意语言风格的自然,还要注重客观景物描写的“不做作,不涂饰,不堆砌”。袁宏道在追求谐趣的同时,运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段对山水进行简洁凝练的概括描摹,山水因此而具有自然亲切的特点。《西湖一》:“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4]422以美人比拟湖光山色,可见西湖的无限风情,亲切可人。又如:“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再如《上方》:“虎丘如冶女艳妆,掩映帘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4]160不但以拟人化的审美眼光来模拟山水,同时还以此作为评判山水特色的依据。为了突出上方景色不与流俗,以掩映帘箔的艳妆女子来反衬上方的丰神特秀、与众不同。这种拟人化的修辞与对比的艺术手法的运用,把上方山水的自然魅力凸显的淋漓尽致。
袁宏道对山水的品赏并不是历代文人对自然山水的一种理性评判,更不是站在山水对立面去品评眼前所看到的景物,而是把自我融入到自然之中。看山水如看美人,以人的角度观赏山水,用拟人的手法构造山水自然魅力。袁氏把自己内在的浩然之气与山水精神相往来,与山水进行平等的情感交流,从而达到物我合一,情景相契的高度。
(三)个人内在主观情思与山水融为一体
高明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总会将个人情趣与外在客观景物描摹融为一体,这与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追求的意境渲染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意是作者的主观情思,境是外在客观景物描摹,而如何将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情思转化成读者可以感知的外在客观景物,是在创作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小品文的创作亦是如此。
袁宏道有许多小品文借山水景观描摹来表现个人内在主观情思。其在《叙小修诗》中写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4]187认为文学创作就应该从个人的真实情感出发,遵循自然,随物赋形,而不是模拟古人。袁宏道在山水游记的书写中注重把个人内在主观情思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以心看景、以笔写心。“少焉云缕缕出石下,缭松而过,若茶烟之在枝,已乃为人物鸟兽状,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抚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云,是亦幽奇变换之极也。”[4]1138这里的云,若袅袅茶烟,悠游自在,与晋朝傅玄“浮云含愁气,悲风坐自叹。”[6]576中借云表达前路茫然缥缈和人生飘摇不定之主旨是完全不同的。袁宏道之所以写出无心出岫的云,表现了云的独特风韵,正是作者我心我性的渲染和写照。
袁宏道笔下,有冶女艳妆般鲜妍的虎丘、也有如披褐道士般丰神特秀的上方……山不同,其状千变。而这些孤标特立、不染尘俗的山水,正是作者思想与人格的表露。这种个人主观情感的宣泄在自然山水小品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拓展和发挥。
二、山水中寓性格
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影响文章的行文表达,反之,文章内容亦是创作者个人性格的反应。袁宏道作为晚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以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创作主张,在晚明文坛上独树一帜。在以山水描摹为主要题材的散文作品中,作者对个人内外形象以及性格特点进行了深刻的文学化抒写,“中郎记山水,既不是刻板的摹山范水,也不是简单的融情于景,或淡化景物描写、强化议论色彩以显露作者的生活感受,而是把写山水美与人情美结合起来,充分地无所顾忌地写出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身处山水之中的审美感受。”[7]24表现在作品中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山水意境塑造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借助对自然山水内涵阐释反映个人孤标独世的文化人格特点。总的来看,山水散文中所蕴含的袁宏道个人性格特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从童心童趣到独抒性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进,是在前人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的不断进化与改善,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袁宏道为后世所称道的独抒性灵的文学创作主张,并非是其个人独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一直深受拘束,发展到明代,李贽“童心说”的提出以倡导表达个人真实感受为主要特征,为当时沉闷的文坛注入新的力量。袁宏道在“童心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此种创作观点,认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4]786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不仅是“童心说”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其山水散文创作提供提纲挈领式的理论依据。在其以山水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中,随处可见作者童心童趣的表达与个人真实感受的抒发。如《雨后游六桥记》中写道:“寒食雨后,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4]426雨后,落红满地,作者急于与桃红作别,可见其惜春爱花之情。接着云:“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4]426作者对春天并不是感伤无奈,而是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心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乐趣。
袁氏并不仅仅只是举起反对文以载道的大旗,还积极地进行创作实践,在投身于自然山水中时,自然而然地把独抒性灵的文学创作主张融入到抒写之中,任意挥洒自由、轻松、任性、悠然的人生社会情调,力求文章能够接近真实生活和个人情感世界。
(二)从打破常规到率性所行
受封建体制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创作表达向来是不自由的。知识分子要么成为统治阶级发声的工具,要么在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斗争中退隐山林,以寄情山水和娱宾遣兴为主要乐趣。在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群体,他们以个人思想矛盾游走二者之间,既有治国抱负,又在与现时的激烈冲突中,借山水描写抒一己之块垒。与中国古代前期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不同,散文无论结构还是语式都更为灵活,更擅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作者内心真实情感,故而散文上承诗词整饬的句式,具有语言的诗意美,下启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思想表达的先河。在袁宏道山水散文的抒写中,具有文风上的打破常规以及思想表达上的率性所行的特点。在《游惠山记》中作者直言:“余性疏脱,不耐羁锁,不幸犯东坡、半山之癖,每杜门一日,举身如坐热炉。以故虽霜天黑月,纷庞冗杂,意未尝 一刻不在宾客山水。”[4]419因此,袁氏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山水自然中。这些山水,并不仅仅是一种物象,同时也嵌入了不拘于法度的思想情怀以及不拘于字模句拟的格套。如《灵岩》一文,作者登琴台,看松声如涛时的一段描写,“余笑谓僧曰:‘此美人环佩钗钏声,若受具戒乎?’宜避去”[4]165把山水比作足以令僧人破戒的美人,新颖别致。这种打破常规式的以色饰山水的独特审美心态,正是他率性所行的表现。
小品文的题裁很多,有书信、游记、序跋、杂文、随笔等,因此,其内容可叙事、可抒情、可状物、可画人,相对于要求句式工整、格律和谐的诗歌以及讲究庄重典雅风格的古文来说,小品文要自由灵活,既不需要作文法度的规范,也无需苦心经营,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不必受礼法的桎梏,随意发挥。而袁宏道笔下的山水游记小品打破了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规矩作文禁锢,追求平易、自然、情趣的率性所行风格。
(三)从一吐心胸到一心摄境
中国古代文人即使情绪再乐观放达,也不免吐露内心独有的细腻情怀。但创作者并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往往把自己的内在情思辐射到外在客观景物上面。袁宏道创作的很多散文颇像个人情绪的自述,将内心独有的丰富情感以“移情”的表现手段融入到山水的描写创作中,即从自我内在的一吐心胸到外在的一心摄境。所谓“一心摄境”的性格特征,是指作者将个人心绪与环境描写相结合,从而达到景中见人艺术魅力的创作特点。
袁宏道的山水散文中不乏体现他迫切地一吐心中情绪,同时以自然山水影射个人心性的创作追求。“山水不仅是袁宏道人生乐趣的源泉,也是他自由展现独立自我的舞台。”[8]80“荒草绵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觉凄凉。醉中谓石篑:‘尔狂不如季真,饮酒不如季真,独两眼差同而。’石篑问故。余曰:‘季真识谪仙人,尔认识袁中郎,眼讵不高與?’四坐嘿然,心诽其颠。”[4]445以李白自比,并不是妄自菲薄或是高傲自大,而是在世事沧桑的凄凉景境中,慨叹人生以及知己难求的孤独。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也不例外,其笔下的山水不仅美妙绝伦,多姿多彩,同时也彰显了作者强烈的个性与情致。如上文所举《雨后六桥记》,正是作者任其自然,顺适性情的自我小象的刻画。
三、山水中现理性
在构思想象,下笔作文时,除了文章中语言的巧妙运用与个人独特性格的抒写外,还经常会在文中或结尾客观地表述自己对此文叙述内容或故事的看法与观点,这些议论总是时不时地带些思辩的色彩。此类艺术写作手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谓是一大典型特征,从先秦时期《左传》在叙事结尾后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等话语直接引发议论,对故事或人物进行道德伦理评价,到汉司马迁《史记》中表达的个人思想感情倾向的论赞结构,再到魏晋玄学之辨风气,创作者的文学自觉与理性思辨逐渐成熟。文至唐宋,继承这一传统的是诗与小说,如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与《新乐府》五十首是运用卒章显志的手法,先铺后点,以讽语作结,发人深省;再如唐传奇中的某些创作者在故事结尾也连带着自己的评判思想。发展至晚明,小品文大放异彩,其中也夹杂着作者的客观判断。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散文体现了这种理性思辨的色彩。他的游记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条序的清楚明晰,二是关于人生哲思的发论,三是引用古文诗来与袁氏眼前所看的实景相参照,进行一番古今变化的考辨。
(一)清楚明晰的游记条序
在古今中外的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总能够在形式或内容上看到某种前后的顺序和关联。在运笔行文时也总是会对文章的内在结构和上下文关系进行苦苦思索。这种写作手法的运用,古今作者皆是如此,袁宏道也不例外,在他的山水游记中,这种特征随处可见。“吼山石壁,悉由斧凿成……山下石骨为匠者搜去,积水为潭……每相去数丈,留石柱一以支之。上宇下渊,门闼洞穴……呼小舟游其中,潭深无所用蒿,每一转折,则震荡数四,舟人皆股慄。”[4]447袁氏写吼山,先写鬼斧神工的峭壁,再到深不可测的黑潭,再到沿途的石柱、门庭,再到一行人游瀑帘后的深潭。随着行进路线,眼前的空间都在逐渐地变化,随景赋形,愈走愈幽。最后以吼山幽奇和荒芜作结,表现为一种空间次序的变化。再如《华山记》中的凿壁登山,袁氏用总序和分序相结合的手法,先总写华山以石为山体的特征,再把沿途的石阶天栈分为“壁有罅”和“悬道巨峦”两类,再对其“壁有罅”和“悬道巨峦”之景分为“横亘者”和“长亘者”,然后又分为“目受成焉”和“目乃为崇”,因此,华山山体的各种形态被剥离出来,把华山之险模写殆尽,全文叙述另辟蹊径,条序清晰而不呆滞,在名篇甚多的华山游记中,令人眼前一亮。陆云龙:“折折出奇,具水穷云起之致。”评价是相当确切的。
古代散文向来就有条清缕析的传统,如古文大家韩愈所写的《嵩山天封宫题名》,全文简洁明了,时间、地点、人物、游历都仅在寥寥数语中。袁宏道的散文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如上文《吼山》,即是采用抽丝剥茧的艺术手法组织文章内在结构,言简而有序、景多而不乱,随步赋形、随境摹情。山水、游历、感受,一一道来,毫不板滞。
(二)人生哲思的游记议论
散文的哲思化、议论化,在宋时文章中就已凸现,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以及前后《赤壁赋》,都是这种渗透的印证。袁宏道兼通儒、释、道三家宗教,其游记小品文也明显地呈现出这种哲思化的倾向。其《兰亭记》就明显地呈现出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人生生存问题的意义。“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高者或托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究心仙佛与夫飞升坐化之术。”[4]443-444整篇文章围绕“死生”二字,表述人执着于“生”的各种形态。文士登山临水感叹生之易逝;卑者纵情声色以享生;高者托文章或仙术以求生,最终得出圣人贵生的道理。这不仅是对人生的一种哲思,还有些甚至上升到老庄之境,蕴含一种生活的禅意。如《华山别记》,游华山时重点却并不在山水之间,而是充满了浓浓的回忆,在临山满月之时,想到已过世的亲友,心思流转之间,顿悟人生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整篇文章都充满着人生如梦的感慨。
兼通儒、释、道三家的文学家袁宏道,其山水游记散文议论中很多都表现出一种哲思化的风格。如《游骊山记》,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透过骊山之山水抒发山水之名与文人、山水之灵与朝代兴亡之关系。再如《灵岩》一文,在记叙游历的基础上,由山河绵邈之境,凭吊感慨,抒发古今之幽情,并为千古“红颜祸水”论断翻案。这种随心摄境,以笔运心的高明艺术创作手法,正是其以游记表达人生社会哲思化倾向的重要手段。
(三)古今参照的游记考辨
文士多爱游历,正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许多游士也因此留下了许多游记类的著作,记下某时某地某处的山水人情,由于都是亲眼目睹之景,具有亲力亲为的性质,创作者往往会对前人的相关记述与现时之景作一参照,对某些偏差进行考辨。南北朝的《水经注》中就有许多此类的文字。唐宋散文继承这一传统,如上文所说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再如明清之际的张岱,通常会以史家的眼光对所游之处做出考辨性的观点,在沧海桑田的变化中,抒发黍离之悲,兴亡之感。
同样,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中也有许多考辨之处。如《灵岩》开篇即以《越绝书》中“吴人于砚石山作馆娃宫。”[4]164点出灵岩处即是春秋时吴国遗迹。又对吴王囚范蠡以及吴王与西施泛舟之所进行考辨,引米氏《砚史》即“村石理粗,发墨不糁。”[4]164印证深紫的砚石。再如《灵隐》一文中的“冷泉亭”以及宋之问《灵隐寺》一诗中对登韬光寺描写的真实程度与眼前之景作对比,进行了切身的考辨。
描摹山水固然是袁宏道所长,但其游记小品不仅写出情景俱佳的山水形态,还通过诗文记载与眼前实景作对比,古与今的空间交错,既表现出沧海桑田的时空之变,同时也可穿越历史窥见古人的思想与情致。即使是他自己的游迹,大多也是实录,可看出作者行文的严谨之处。
综上所述,袁宏道山水游记散文中“谐趣美”“性格美”“理性美”的自然山水观,辐射出袁中郎文学创作理论和个人思想情怀。同时,这种创作方式也对后来以“义理”“考辨”“辞章”以及“言之有物,言之有序”为作文原则的桐城派所继承,从这也可看出袁宏道散文的成就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