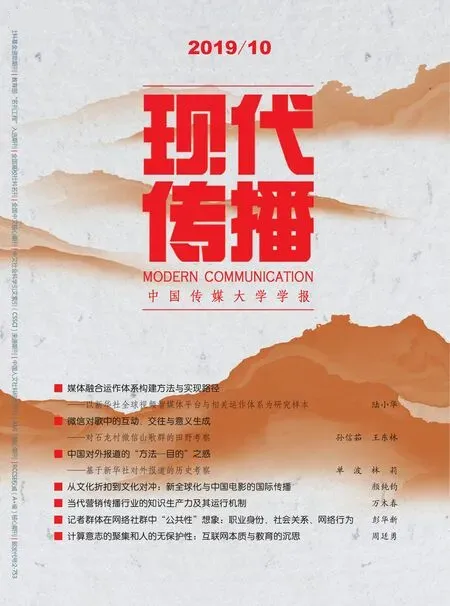生态政治哲学视阈下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创新
■ 李玉洁
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于政治决策和社会政策的现实问题,在学理上还是一个有着巨大政治哲学深度的理论问题①,引发了人类自然观念和自我意识的一次新启蒙、新革命。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政治的道德层面,意指一种特定取向或样态的政治实践或认知的哲学世界观及其价值基础,或者说是关于为何以某种方式践行或阐释某种形式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据。②生态环境危机就其根源和本质来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现代性批判对自然、对科学技术本质、对人本质的需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概念的重新理解。传统工业文明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环境灾难。当前环境危机的解决,亟待批判、发展和创新其政治哲学基础,即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征服自然、经济理性、资本逻辑等价值观念,转向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的生态哲学观。而与此同时,基于原有政治哲学基础的环境传播话语实践也面临反思、重释乃至新构。
一、视为“危机学科”的环境传播及其话语限制
环境传播是传播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环境传播是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以及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和建构的手段。③在国外,环境传播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而在国内“环境传播”正式进入传播学界虽然已超过20年,但其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环境问题的急剧蔓延期待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能仅仅局限在建言献策的“形而下”层面,而是需要提升到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层面来彰显其实践智慧。
环境传播于20世纪 80 年代兴起之时,正值污染、生态灾难、技术风险等环境危机开始涌现。危机既包括人类造成的对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威胁,也包括社会机构未能成功地应对与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压力,环境传播因此被视为“危机学科”④。罗伯特·考克斯也指出“环境传播是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⑤。 这一学科定位决定了其主要致力于环境危机和问题的理论建构和解读,也包含致力于改善环境危机和加强环保意识的伦理责任。在传统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既有环境传播大多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人类二元对立”“经济思维主导”的价值导向,其话语多以风险、危机与冲突的范式呈现。但环境传播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带着人与环境成为和谐共同体的理念,用传播手段帮助人类社会认知、建构进而改变对环境的理解和形成价值判断的框架。⑥
整体来看,西方学界环境传播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话语范式,分别是环境新闻研究范式、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社会建构意义框架。⑦约翰·德莱泽克将环境传播话语概括为九种类型,分别是生存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可持续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话语。⑧
而国内学者有关环境传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保护、环境新闻、环境运动、环境风险、环保实践、绿色媒体、环境抗争等相关领域,出现了一些极具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刘景芳指出中国环境传播的话语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介绍西方理论,尤其是话语修辞理论。二是对环境新闻与报道的研究,近年来围绕有关气候变化、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热点环境议题的报道所展开的话语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三是围绕公共参与展开的话语实践分析,以环境运动、ENGO(环境非政府组织)或民众抗争为重点。⑨可见,国内环境传播的话语也主要关注危机、冲突和抗争。这是因为中国卷入全球经济是以便宜劳动力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且由于缺乏严格的环境监管体系,在卷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自然的禀赋被破坏了,出现了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城市垃圾、能源衰竭等各类问题。而这些生态危机与其他社会危机交织,产生了近年来越来越频发的环境抗争。⑩在这些频发的环境抗争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抗争性话语。
总体来看,中西方环境传播的话语范式整体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自然大多被看作是人类利用和开发的工具,而这一视阈下媒介话语主要被限制在危机和冲突上,带有环境社会学中被称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的印迹,这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二、环境传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价值转向
要改变环境传播的“危机学科”范式及其话语限制,需要突破环境传播领域中“就环境谈环境”的窠臼,转而在更深层上来反思环境危机的实质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不然容易拘泥于环境危机的“表层描述”。这正如赵月枝所说的,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环境传播,能够使环境传播超越具体情境下的应用层面考量,转向反思环境传播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关系这一基本层面,思考重新定义人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形态。而刘涛通过对1938—2007年西方1041篇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也发现贯穿始终的三个解读元素是话语、权力与政治。简而言之,环境传播如果没有政治哲学的思想高度就不可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无法真正地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
1.环境传播的政治哲学基础转向
大卫·哈维认为,西方传统话语在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和胜利主义,另一种则是悲观主义。前者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支配自然、统治自然的观点,这一观点可追溯到17世纪培根、笛卡尔等所确立的“人是自然的主人”思想,后发展成为极端的工具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以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整个自然界,认为自然界唯一的价值就是提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否认大自然自身的价值,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作为对启蒙乐观主义的矫正和批判,悲观主义出现了,其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自然观点的批判和马尔萨斯提出的资源匮乏、自然极限论为代表,但这些观点的实质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
除了这两种观点之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国家还出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批评、生态政治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正义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等各类生态思潮。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对推动西方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它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传统模式,促使西方国家对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政治制度做出调整。但我们应认识到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局限性,一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不彻底,二是没有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的可行方案。
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这一重要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有本·阿格尔、赫伯特·马尔库塞、詹姆斯·奥康纳、戴维·佩珀等,他们从源头指认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认为只有变革社会制度,建构一条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环境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马克思也曾指出,把自然的概念变成一种有用性概念,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价值观,所谓征服自然其实就是资本的一种内在属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某些核心要素如资本逻辑、经济理性、消费主义等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的不可兼容性。几十年来,环境哲学家强调,“唯物主义”的、“还原论”的、“二元论”的西方世界观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办法,就需要使世界观发生一次深刻的变革。
而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一种执政理念,它既具有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也具有实践层面的方法论意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维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结合自身现代化实践所做出的理论推进和深化,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特质。我国当代的生态哲学思想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构建起来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最核心的理念或价值,就是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与诠释。
2.环境传播的价值哲学及其转向
面对环境危机时人类应该如何重新审视环境的价值与自身定位,这也包含在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范畴之内,因此探讨环境传播的价值哲学也是十分必要的。西方环境哲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至70年代末以《环境伦理学》的创刊为标志,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在环境哲学研究中,伦理对象逐步从社会向自然范围扩展。罗德里克·纳什指出把道德考虑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物,这是一场伦理学的革命。环境伦理学从简单的二分法,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开始发生转向。现代西方世界的环境伦理学中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和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这三个主要方向。生态中心主义伦理把价值推到极限,从动物、生物扩展到生态系统,从而赋予整个自然界以道德、价值的意义。虽然这些理论为解决环境危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野,但也存在偏颇,因为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都各执一端,回避了真正的价值平衡与对话问题。
因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更加开放的生态伦理学是趋势所在。在理论层次上,当前环境哲学中最重要且最具创造性之处是自然价值理论,确立自然界除对人有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其内在价值是建立非人类中心论的重要环节。在这个问题上集中了不少环境伦理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包括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保罗·泰勒、巴耶·诺顿等,他们从价值论的不同路径(生态价值、固有价值、审美价值等)出发,试图建立起一个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核心的新型环境伦理思想体系,为环境保护提供一种新的道德依据。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在法律上探寻推动人与自然的平衡价值体系的形成。在美国,价值通常被列入环境法的前言,例如《濒临物种法》中的“审美、生态、教育、历史、娱乐和科学上的价值”,《荒野保护法》中的“科学、教育、景观或历史的价值”,以及《国家环境政策法》中的“我们国家遗产中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方面”。而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也规定:“人民拥有对于清洁空气、水以及保存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的权利。”在加拿大的生态实践中,经济价值通常被列入价值清单,但仅仅是众多价值之一,比如《育空环境法》致力于促进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精神上的关系”。如果人们能找到一种平衡促进上述四种价值的方法,那么经济价值会受到限制;如果不能,该法案将仅仅被当作一项经济法规来实施。可以说,在上述这些情况中,都刻意忽略自然的经济价值,以便通过提倡其他价值来对无节制的经济价值加以禁止或抑制,从而实现多种价值的平衡与对话。
三、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创新
基于环境传播的学科认知和哲学基础的两大转型,本文认为环境传播急需在新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实现话语实践的创新,即突破“危机学科”思维定式和话语范式,拓展至一个超越环境问题本身的更大的认知维度和外在语境,以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精神价值共存的“多元价值平衡与对话体系”。其中,新的生态政治哲学是指导思想,指代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符合生态规律的哲学世界观及价值基础。而话语实践的创新是突破方向,强调由话语所驱动并构建的象征活动与实践过程,以期在话语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探寻环境问题的治理方案。
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是话语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概念,涉及到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发生逻辑与作用关系。话语实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话语实践主要指话语的社会功能及其实践影响;广义的话语实践将话语视为“社会行为的再现系统”和“社会实践的语境重构体系”,强调话语实践研究不仅包括话语的实践功能与过程研究,还包括对话语本身的研究,即话语思想与体系研究。概括来说,话语实践研究涵盖三个维度:一是话语本身的思想与内涵研究,二是话语的符号体系研究,三是话语的社会实践研究。
结合费尔克拉夫、布尔迪厄、福柯、莱考夫、汪民安等学者关于话语实践的分类与操作方法,本文将话语实践视为一个由思想、价值、文本、修辞、传播五部分构成的符号实践系统,相应地也就形成了话语思想、话语价值、话语形态、话语修辞、话语传播五个认识维度。具体来讲,话语思想主要指话语构成的思想内涵及其哲学基础,话语价值主要指环境传播实践的伦理立场,话语形态主要指承载话语传播的文本形态,话语修辞主要指话语体系构成的认知框架和策略,话语传播主要指现实场域中的传播实践。依据这五个认识维度,当前我国环境传播话语的实践创新,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1.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开展环境传播
从政治哲学视阈来看,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有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包括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二元论”、工具主义自然观、机械主义自然观等,而为了应对环境危机其也经历了各类生态思潮的流变过程。我们需要以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和扬弃这些资本主义的生态哲学,肯定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并在反思、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吸收这些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有益之处。而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西方环境与发展问题相关理论的超越,有着理论自洽性和价值观特质,体现了对自然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蕴含着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智慧,代表着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新方向。因此,环境传播需在这一新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开展。
2.批判与发展中国传统生态思想遗产并展示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系统丰富的生态智慧,特别是儒、释、道三家中包含着诸多生态文明思想,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兼爱万物的生命伦理观、中庸之道的生态实践观,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观、道生万物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佛教倡导的佛性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慈悲为怀的生态实践观等,这些都应是当前我们处理环境危机潜在的智慧来源。但结合当前的生态话语建构需要,我们还需反思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对其批判性发展和创新,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3.追求环境传播的多元价值平衡与对话体系
传统环境传播习惯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出发,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将其他社会价值简约化为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层面,这一狭隘的价值取向会限制公众在道德层面的思考行为,也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除了经济价值以外,自然界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也必须得到同样重视,有效的环境传播必须回归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平衡价值体系。回归这一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或者经济思维的终结,而是要保障经济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发挥引领作用并实现对话。在建立环境传播的多元价值平衡与对话体系中,应关照生物文化伦理、自然主义伦理、审美保护主义、生态整体论等新流派和理论。
4.实现环境传播的话语体系创新
当前环境传播主要是按照西方“危机学科”的范式在进行,主流的环境意识形态是由“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导,而有关环境的社会范式、法律和规制也以此为基础。因此,超越环境传播传统的“危机学科”话语和经济价值主导的理性主义话语、“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话语等,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反映更多均衡价值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话语体系至关重要。话语体系创新包括四个突破方向:一是话语内涵的哲学思想创新,二是话语建构的认知框架创新,三是话语表达的修辞体系创新,四是话语传播的文本形态创新。
5.改进环境传播的传播策略
环境问题涉及政府、企业、专家、媒体、公众、环境非政府组织等多个利益相关方,而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对他们各自的话语体系进行分析,从而提出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大众媒体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信息提供者和议题设置者,媒体要广泛、持续地进行高效环境传播,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应对能力。长期以来,媒体在进行环境报道时很少从人与自然的价值互益性关系来报道环境,从而营造了单向度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环境。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体要精选框架和设置议题,要跳出“自然工具价值”“人与自然对立”的冲突报道框架,更多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提升人们对自然的全方位认识。而环境非政府组织也是现代社会公众知晓和理解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传播源。有学者对在网络空间比较活跃的ENGO进行历时分析,发现以下几大特点:一是ENGO利用新媒体进行广泛的话语传播,但话语互动率低;二是以浓重文化色彩和哲学导向的生态话语为主,常将环境问题归因于个人、道德层面;三是倡导以环境教育为主的低政治性环境实践。可见,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传播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通过创新传播手段,引发公众更加活跃地关注和参与讨论环境议题,从而更加理性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伦理道德,这是环境非政府组织需努力的方向。
总之,对自然的态度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话语思想的“危机”,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政治哲学“危机”,而环境传播要跳出西方“危机学科”的模式,就需要在新的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从生态政治哲学视阈来研究环境传播,不仅拓展了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同时推动了哲学本身向自然的回归,促使环境传播能从哲学角度来思考人性、人的需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关涉环境危机解决的最基本问题。
注释:
①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② 郇庆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③ Cox R.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andthePublicSphere(2ndedition),London:Sage,2010.
④ 戴佳、曾繁旭、黄硕:《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⑤ Cox R.Nature'sCrisisDisciplines:Does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HaveanEthicalDuty?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2007,1(1):5-20.
⑥ 纪莉:《纪莉教授谈环境传播与我们》,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KMQ0EVM052182I6.html。
⑦ 刘涛:《“传播环境”还是“环境传播”——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⑧ Dryzek,J.S.ThePoliticsoftheEarth:EnvironmentalDiscour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