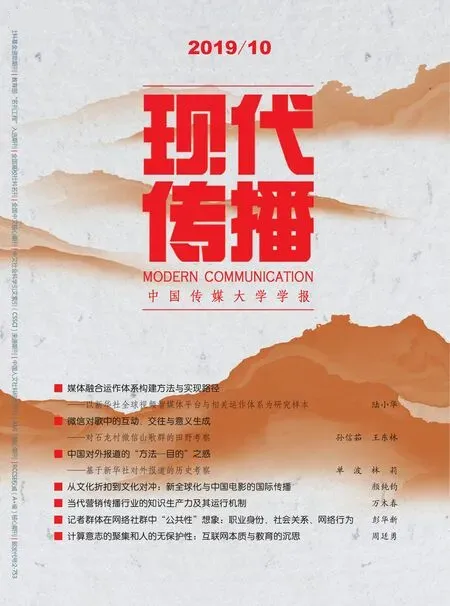网络直播的共鸣效应:群体孤独·虚拟情感·消费认同
■ 王艳玲 刘 可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人们在某些事务上无需“亲身”体验和感知外部世界。网络直播的拟真性使媒介互动主体模糊了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其特有的情感互动体验让网络直播的热度持续居高不下。网民通过直播表达自我并参与当下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视觉呈现局面。
一、网络直播中的外显表达特征
网络媒介的出现对视觉和文化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既为传播主体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交流平台,也由于网络媒介本身碎片化、分裂性、去中心化等媒介特性,使得以往有关某些群体和阶级建构另一种群体与阶级的生活、价值的阐述已不合时宜,青年群体通过新兴的网络媒介获得部分话语权,并开始在网络直播平台以各种方式展现自我。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②
1.弹幕引导下的情感层次双向互动
网络直播的主播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流量和人气的爆炸式增长,主要原因是主播在进行直播的过程中营造了符合受众的个人形象,通过弹幕同受众进行了情感层次的双向交互,无形之间在受众和主播之间形成了情感纽带,“弹幕”和“评论”成为屏幕双方交互思想的媒介,播主和观众在网络世界中共同进行了一场“虚拟约会”,且是一场多人参与和主导的情感体验。
以当下热门的网络“吃播”为例,多个网络用户在同一时间内聚集在直播间内,没有注册或关注播主的用户将无法进入直播间,所有人对主播吃饭过程中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在“吃播”过程中,用户可以随时通过弹幕和打赏与播主进行互动,分享自己对于“美食”的体验或者延伸出的人生琐事,“食物”承载了个人的情感体验或生活经历,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物质要素。这也就意味着“吃播”恰好契合了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的四个要素:两个或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对局外人设置界限、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分享共同的情绪体验,情感能量成为互动仪式的驱动力。③用户在这个时候不再是被迫接受信息的受众,他们充分拥有了选择性体验、参与乃至影响“直播内容”的权利。即网络直播打破了时空限制的壁垒,实现了一场情感层次的跨屏互动,无论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是否有过主动分享或者互动的行为,都在这场直播中获得了特殊的情感体验。
2.家庭参照下的后台场景环境再现
戈夫曼认为,人们总倾向于在前台这个表演场景中呈现符合观众标准和要求的形象,在后台场景中呈现最轻松真实的自我。为了能够让观众完全沉浸在“聊天”的氛围中,实现在后台场景的最大程度放松,网络直播的场景布置以家庭尤其是卧室为主要参照物,因为卧室的物理空间显示了文化边界在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流动性,这意味着在传统行为与媒介促进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合。④
由于网络直播所呈现的画面有限,直播播主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利用屏幕空间打造一个放松的拟态环境。通过小摆件、玩偶等增添场景中的温馨感,观众所看到的不是一个一尘不染或者毫无生活气息的摄影棚,而是一个拥有真实细腻感、令人放松的环境。例如“吃播”播主大胃王密子君,其早期的视频录制主要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卧室中,观众可以完整地看到播主住所的全貌,随处可见的抱枕和玩具、暖色调的窗帘甚至主播的穿着打扮和行动语言等,这些真实性元素建构了一个相对朴素和真实的环境,对后台场景的呈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身体资本下的非公开化猎奇窥视
尽管各个网络直播平台支持UGC的输出,但很明显的是,PGC更容易受到平台或者观众的喜爱,当才能或者技艺缺失、无法进行专业内容输出的时候,以物质身体为依托的身体符号通过直播平台成为一种身体景观,成为绝大多数网络主播的重要“专业资本”,这对于当下的网络女主播尤为重要。在网络秀场的直播中,身体不只体现出社会交往的功能,也承担着“后台表演”的重要任务。即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并不简单意味着传统角色在新的舞台闪亮登场,而是意味着传统角色在上演的过程中被改变。
为了迎合大部分受众对女性身体的想象,网络女主播包括男主播们以受众审美为导向,精心管理和呈现自己的身体图像,大部分网络直播的女播主都以一张精心修饰、毫无瑕疵的个人肖像作为直播封面,以独具特色的第一印象吸引受众进入直播间。当主播认为自己不满足大众对女性的审美趋势时,就会采用整容、美颜等各个手段迎合受众的需求。受众通过虚拟打赏金钱或礼物,就可以让镜头对面的主播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表演,比如吃饭、化妆或者跳舞,甚至是一些更为私密的活动,而勾手指、亲吻等特定的非语言符号也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网络主播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最短时间内引起观众有关欲望的联想,从而使受众获取短暂的精神情感抚慰包括窥私欲望的满足。
二、后现代社会下网络直播的主要成因
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推进使得旧的社群单元不断被打破,当城市化场域中的人生存的空间受到挤压时,在安全感的缺乏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之间无法找到平衡,便转而将视野放在虚拟空间。科技时代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媒介则为此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路径,既可以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也能够进行充分的自我保护。
1.娱乐解压:逃离现实与消极抵抗的方式
在资本利益驱动下的当代社会,民众的私人生活空间被严重挤压,高效率、严要求成为成功职场人士的标签,极度忙碌的反面就是极度无聊的状态。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使得当下群众对于自身的定位和社会认知愈加模糊,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或方式,成为年轻人用来自我娱乐和满足的最佳选择。因受到“娱乐至上”甚至“金钱至上”的扭曲价值观念影响,年轻人的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往往被集体忽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无法排解的负面情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往往渴望通过一种新的途径抒发自我,“人们的快感一定是被压迫者的快感,在此种快感中涵盖了很多消极因素,如抵抗、躲避以及鄙俗等”⑤。在早期的直播中,网络主播倾向于用充满个性的拼贴、剪辑等方式对经典文化进行再次编码,以此表达出对现实和对权威的不满。随着媒介化空间的不断发展,这种编码已经丧失了明确的所指,大量主播不再为了争夺话语权而发声,取而代之的是对商业利益和粉丝流量的争夺,这种恶搞和拼贴不再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抵抗被弱化,夸张和搞笑的动作使得直播内容最终走向了虚拟狂欢。例如网络主播王某在2017年11月14日的直播期间,以搞怪的方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逮捕。王某在被警方拘留后供述,作案动机完全是想以此增加粉丝量,本身对国歌并没有任何抵抗心理。
这样看来,“无聊”看似毫无意义地无处不在,反而成了当前娱乐文化产业的热门现象,一切不需要或者少量耗费精力与资源就能达到娱乐效果的话题乃至“无厘头”的讯息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进而达到在特定的镜像之下的消遣、休闲与各种压力暂时性的排解、发泄和释放。2017年,播主Miss在某平台直播过程中睡着,但就在其睡觉的过程中,仍然有将近20万人观看直播且进行弹幕互动。而网络吃播以直播吃饭为主要视频内容,也在各大视频平台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当下网络直播中的重要分支,其原因之一就是在直播过程中,博主传递出的任何与食物有关的信息都能够被观众轻易消化且产生共鸣,以最小的精力消耗代价换来感官上短暂的娱乐和放松感,这也就成了人们在无聊状态下一种屡试不爽的自我解压手段。
2.虚拟陪伴:群体孤独现象下的解决路径
移动设备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同网络世界紧密相连,在虚拟世界中获得全新的状态。当虚拟网络成为人们社交的主要场地时,它所刻意营造的社交快感会逐渐取代真实社会中复杂的交往,从而导致另一种网络群体孤独的产生。即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某种授权:它可以从现实环境中脱离——包括其中的人,然而网络社交能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碎片化的弱连接。⑥换言之,置身于网络世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实生活中的郁闷孤独都可以在互联网中得到宣泄与补偿。可他们却忽略了传播过程的一个重要现实——身体传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假设传播的前提是身体在场。⑦归根结底,海量的网络直播视频的出现,就是因为在大众传媒的过程中,身体的缺席造成了参与者产生大量焦虑心理。人类不断推进图像、声音、甚至全息影像等各种高科技传播方式,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弥补“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缺位。
基于此,以互动、共联为主题的Web 3.0时代所催生的第三代网红播主与粉丝的互动更主动、多样,且贴近生活。⑧网络直播模拟了现实社会中的约会或沟通流程,播主试图询问用户的生活偏爱和习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以亲密朋友的方式沟通工作是否顺利,对近期发生的各种热门事件做出点评,观众通过播主所制造的话题内容进行弹幕或者评论回复,从而达到一种活跃的、双向的“体验式”互动。即网络直播满足了独居的单身青年的归属感诉求,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心灵慰藉的孤独个体在网络世界中找到了虚拟社交的快乐感,各类社交平台和直播软件的出现为他们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舞台。主播对于观众来说,不再是屏幕另一边的网友,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扮演了“密友”的角色,观看直播的过程就是营造了一种虚拟陪伴感、认同感和获得感。
3.消费认同:商业资本推动下的新口号
不能否认的是,网络直播从诞生直到今天,商业资本都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助力。网络直播的播主通过消费各种物品或者时尚,确认自己的存在或者地位。在今天,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创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⑨正是基于对网络播主的情感依赖,受众往往在网络播主的驱使下进行认同和追随,这种消费主要体现为购买播主所使用的物品、所介绍的商品等。受众在进行消费的时候,不再是为了商品表面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更在于通过购买或者使用这件商品,达到对自己身份的建构和时尚的审美,这就为商业资本的快速进驻建立了一个基本前提,也是网络播主能够快速将人脉和粉丝资本进行变现的主要途径。
换言之,观看直播的用户更倾向于用消费方式去创造小规模社会群体的形式,当自己的消费方式和倾向同主播以及其他用户格格不入时,就会产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恐慌,这正是商业资本推动下利用消费心理达到消费目的的一种手段:金钱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于是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平台和主播的诱导下,陷入娱乐、情感、炫耀等非理性的消费漩涡难以自拔。网络直播依靠社交网络的爆炸式传播,逐渐成为互联网时代下不可小觑的媒体力量,低门槛、变现快、投小产大的诱惑促使各种利益代表方进驻,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直播内容和价值观念冲突的日益扩大化,甚至一些靠着怪诞、猎奇性乃至低级庸俗的内容吸引人眼球的网络直播层出不穷,其背后折射出的群体孤独现象愈加明显,大量盲目跟风的受众群体便在过度娱乐化的网络大环境当中逐渐沉迷。
三、网络直播优化的发展路径
2017年网络直播行业进入洗牌阶段,网络秀场的直播开始进入政策收紧和资本退潮时期,那么要想促使网络直播在发展过程中走出迷途,就需要对其予以客观、理性的思考。
1.发挥网络主播差异化优势、增强优质直播内容输出
网络直播进入冷却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娱乐或同质化内容的占比已经失衡,而用户对娱乐性内容的关注度终究会在某个阶段形成理性认识。即直播平台和播主对于直播节目的内容和受众定位不够准确,就无法完成内容细分和完善运营能力。即便那些自带明星光环和流量属性的直播播主也不是内容生产的主体部分,为了保持与受众之间的神秘感,拉开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他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往往并不会轻易尝试新颖的内容直播,只能作为内容生产的参与者和助力者。加之不是所有的网络主播都具备生产和运营优质内容的能力,特别那些非流量级的直播播主为了能够快速聚拢粉丝,往往会走一条快速通道:加大对身体资本的投入和展示,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走到今天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受众心理,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
更确切地说,仅靠已有主播进行内容输出不能作为长久之计。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如果都是以围观平台内容为主要目的,那么就无法提升用户在平台的参与度,反过来也会使平台关注度下降,已有主播和优质内容流失,良性内容生态体系就被破坏。对于流量级别高的主播来说,可以在明确自身受众定位的基础上不断打磨已有的优质内容,以主流文化为内容导向,通过团队协作、商家合作等方式实现个人形象和品牌的不断升级,在保持流量和关注度的同时带动产出优质内容的直播博主,实现用户精准分流。对于长尾中的大部分尾部主播而言,短期内想实现优质内容产出较为困难,可以尝试新技术,增加差异化内容展示,给用户带来全新的视觉效果,在市场的摸索过程中实现粉丝的原始积累,利用流量变现再转而推进优质内容的生产。于是,在今后的网络直播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全民内容生产输出,增加平台的社交属性和用户黏性,丰富整个平台内部的生态体系,将成为今后网络直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2.提高网络直播准入门槛、全面把关与多方监督并重
“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主播”,这句话毫不夸张。我国直播行业目前的准入门槛仍旧较低,甚至只需要一部支持移动网络的手机,用户在直播平台注册成功后,就能够以个人为中心开始一场直播。直播平台的注册是成为播主的第一道门槛,但大量直播平台为能够快速占领直播市场,达到更高的注册用户数据量,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手机号码验证,对于用户的身份审核力度不够,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使用造假的身份信息等也都能够快速注册,甚至一度出现真假信息难辨的混乱状态。
这就要求网络直播平台采用多重身份识别,利用面部识别信息系统匹配用户真实身份,三个以上亲友进行用户实名认证,对违规进行操作的用户实行短期或永久封禁制度;直播平台也要实行考核制度,对直播的播主进行定期培训,在直播内容的选择和题材上达到共识;同时鼓励观众主动监督,设立直播内容的奖惩制度,依靠大数据筛选技术实现敏感词汇的筛选和辨识,过滤相关有害信息。即可以从对视频评论和弹幕的大数据分析入手,当发现播主多次进行粗俗或同质化直播时,可以对该播主的房间准入人数进行控制,不对播主的直播消息进行大范围推送,以降低播主的曝光量,并禁止首页或榜单展示,甚或通过提高直播过程中打赏金额的抽成比例用于奖励产出高质量作品的网络直播播主。
3.企业与民间网络直播合作、全方位整合平台资源
网络直播打破了以往互动类节目的禁锢,以不可替代的互动性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下的商业推广新模式。网络主播与潜在消费者的受众进行情感互动,与商户端直接合作,成为市场调研和拓展的助力者,由此催生出大量消费行为。因网络直播经济与情感消费紧密相关,当情感系统被强行推入商业背景中时,隐藏在情感规则、情感整饰以及情感交换背后的就是利润。正如霍克希尔德所言:“私人的情感系统己经服从于商业的逻辑,而且己经被它所改变了。”⑩
网络直播的影响力扩大导致大量资本入驻,为了凭借网络播主的个人媒体平台达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一些播主甚至为吸引人眼球、获得流量制作出猎奇、粗俗的视频内容,一些三无产品经过网络播主的包装,也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产品。这样一来就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平台泛滥下的市场资源配置不均也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对此,韩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韩国直播平台AfreecaTV的美食直播节目呈现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韩国政府联合私营公司创立MCN平台,为网络直播中的“吃播”类播主从节目创意到节目制作以及节目后期的社交网络传播提供完整的计划扶持,韩国政府还创立了非营利组织SBA,每年为“吃播”视频的原创者提供1.2亿韩元的资金支持,并免费提供视频制作、粉丝和内容运营等培训课程。我国的网络直播节目则主要集中在直播平台,直播结束后转化为录播视频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放。网络直播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来源主要在粉丝经济、平台入住费用以及商业推广活动,对于优质视频内容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劣质内容的监管力度也不到位。
综上所述,早期的网络直播在流量红利的催使下掀起了一场群体狂欢活动,既推动了文化的自主创新,也对当下传统媒体提出了挑战。可处于互联网娱乐化大环境下,网络直播以庸俗娱乐为内容核心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网络直播平台的社交属性不能产生强大的用户黏性,也意味着大量用户群的流失,导致了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断裂。只有当网络直播真正被作为网络文化传播的渠道,得到官方与民营企业的重视和扶持,全方位整合媒体平台资源,从源头把控内容质量,拓宽优质内容的传播渠道,才意味着有能够充分挖掘网络直播背后的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可能,并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注释:
① 中国网信网: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2/t20190228_70645.htm,2019年2月28日。
② 段德宁:《符号与图像——试论语图关系研究的两种视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③ [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1页。
④ [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⑤ 石开斌:《费斯克的微观政治思想解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⑥ [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⑦ 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⑧ 王月:《消费社会的转型:从消费明星到消费网红》,《现代传播》,2017年第2期。
⑨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⑩ Arlie Russell Hoehschild.HieManagedtheArt:CommercializationofHumanFeel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