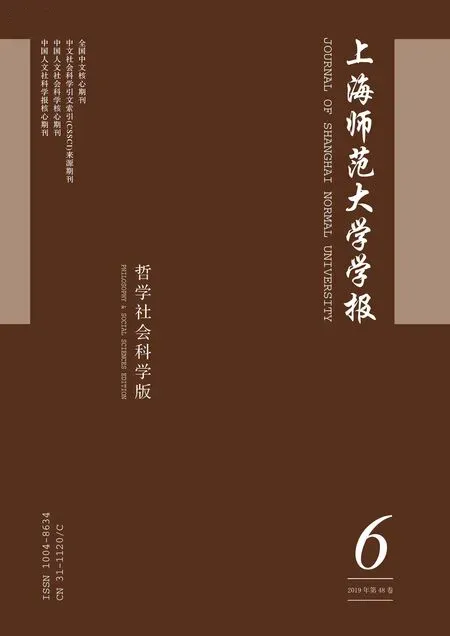20世纪前半叶长江三角洲的湖泊生态与民众生计
吴俊范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我国东部地区的淡水湖泊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主要表现为面积萎缩、水质污染、富营养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对湖泊的治理和生态恢复已成为当务之急。(1)2018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行湖长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了湖泊的管理保护工作,把“改善湖泊生态环境、维护湖泊健康生命、实现湖泊功能永续利用”作为目标。该文指出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湖泊环境问题主要是“围垦湖泊、侵占水域、超标排污、违法养殖、非法采砂,造成湖泊面积萎缩、水域空间减少、水质恶化、生物栖息地破坏等”。为进一步厘清最近半个世纪湖泊生态快速变化的驱动机制,有必要以史为鉴,对这一重大变化前夕的湖泊环境状况和利用方式进行复原。本文以我国淡水湖泊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为考察对象,从湖泊地区的物产与民众生计的关系入手,对20世纪前半期的湖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耦合机制进行历史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初期湖泊利用方式的转型问题进行反思。
本文所论之湖泊水面,不仅包括长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太湖、阳澄湖、淀山湖、固城湖等著名大中型湖泊,也包括数量众多、与民众生计关系密切的湖荡,二者在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价值及利用方式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共同特征。(2)根据现代新编湖泊志有关东部地区湖泊等级的大致标准,可将面积20000亩以上的水面定义为大中型湖泊。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在长三角地区广泛分布的大量数千亩至万亩不等的湖荡,亦应归入“湖泊”之范畴。其依据是1956年浙江省政府颁布的《浙江省淡水区水产事业暂行管理规则》。其中规定,“国有的江河、湖泊、荡漾等,其面积在一千亩以上的大水区由国家经营”(参见《嘉兴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对有关养鱼问题的批复》,嘉兴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6-001-164-093,1956年10月13日)。这说明国家从经济和生态重要性角度对千亩以上湖荡进行统一管理。根据1929年太湖流域水利局的统计,江浙两省太湖流域片内面积在1200亩至20000亩之间的湖荡共有150余个,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的杭嘉湖平原和江苏省的锡、常、太、昆一带,与大中型湖泊和稠密的河港一起构成典型的亚热带水网平原地貌。(3)参见《太湖流域湖泊面积表(民国十八年九月核算)》,《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9年第4期,第8页。虽然民国这次统计所采用的标准是以1200亩为下限,但与1956年浙江省政府所认同的1000亩以上为大水面的标准相差并不大。本文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期刊论文及相关政府档案,但也使用一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地方政府档案,其中对早期湖泊生态和利用的回忆性资料有助于弥补史料的不足。
一、物产丰饶的“湖区”
长江三角洲北起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其中心部分是以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为中心的冲积平原,境内地势低平,河湖密布,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明清以来的经济发达区。在各种历史文献记载中,虽然常用“鱼米之乡”来形容江南地区的富足和繁荣,但真正具备“鱼”和“米”双重丰产条件的,主要还是长江以南以各个大中型湖泊或湖荡群为中心的低洼平原地带。本文采用“湖区”这一概念来概括长江三角洲平原特有的湖体与周围陆地相结合、以物产丰饶为特征的地理亚单元。
在各个湖区,一方面湖泊水体本身盛产鱼虾、贝类、菱草等动植物,为民众生计提供富源;另一方面,湖泊周围陆地水网密布,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水稻,便于育桑养蚕。此外,湖泊水量丰富,可引到岸上利用低洼地形发展人工鱼塘,以养鱼促进农副业经济。总之,由于水陆优势互补,气候和水热条件适宜,长江三角洲湖泊地带往往形成粮、桑、渔并行发展的经济模式,正如民国学者李协在考察太湖后所总结的:“盖水自山间来,不即流入海而得停蓄浸润之力者,湖之功也。种桑而外,鱼藕菱茭之利,亦不可胜算。彼直隶沿海之地,卑下亦如苏浙,何以鱼米之乡,独推江南?是非太湖之为功乎?”(4)李协:《太湖东洞庭山调查记》,《湖州月刊》1926年第2期,第21—28页。由此可见太湖在流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综合性的。太湖之利,首先表现为强大的排蓄水功能,对旱涝时的水环境调节尤为重要;其次是湖区自然条件带来的水土环境和丰厚物产。
湖泊水利与岸上经济形态之密不可分,还可以用1929年国民政府对浙西湖泊地区桑蚕业的调查报告来分析说明:“浙西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最适于桑树之生育,叶大肥嫩,尤适于蚕之营养。益以湖水质佳,所缫之丝色白质韧,为他处所不及。更兼水陆交通均称便利,丝茧之运输销售极易,故人民多乐于栽桑育蚕。”(5)邓宗岱:《调查报告:视察浙江蚕桑业报告》,《河北农矿公报》1929年第3期,第189—203页。湖州所产“湖丝”闻名于世,得益于优良的太湖水质和受湖水滋养的肥美桑叶,丝茧产品的流通又得益于平原上水陆联运之便利。总之,浙西杭嘉湖地区的经济显然具有“湖区”特征,渔农工商各业所赖之资源无不与湖泊相联系。
湖区水陆资源之一体化,还可从湖泊周围人工养鱼业的发展与湖水、湖产、湖滩的关系来证明。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大中型湖泊不仅本身出产大量的淡水鱼,滨湖农民、渔民还利用环湖滩地建造鱼塘,以湖中所产的螺蛳、水草、浮游生物等为天然饵料,发展规模化的人工养鱼业。太湖北岸的无锡居江苏省养鱼之冠,当地人主要是利用湖滨滩地,鱼塘集中分布在太湖两大出水口仙蠡墩和大渲口附近,直接“用太湖之水,由梁溪导入,水量甚丰,水色亦清,水中含有丰富之酸素有机物及微量之盐化物”。(6)《实业消息:无锡养鱼业状况》,《实业杂志》1923年第69期,第114—116页。20世纪40年代,无锡的淡水鱼养殖量每年至少数万担,相当于一个大型湖泊的野生鱼产量。(7)《最近无锡养鱼业概况》,《水产月刊》1948年复刊3第4期,第13—20页。另如丹阳县的练湖,面积约500余亩,浮游生物极多,颇适于淡水鱼类生活,由此湖周围里许范围内养鱼业也颇为发达,1932年统计有6800亩。(8)《江苏省各县养鱼事业调查》,《中行月刊》1932年第6期,第117—120页;另见《苏省各县可利用荒地辟池养鱼面积之统计》,《渔况》1932年第49期,第7页。昆山县阳澄湖周围也是主要的人工养鱼基地,养鱼用的水源全部来自阳澄湖,“由后浦塘引入,色微浊,含有天然饵料颇丰富”。(9)《昆山大盛垦牧公司养鱼概况》,《渔况》1930年第12期,第3—4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府部门曾开展过关于长江三角洲湖泊环境和物产的调查。如1935年京沪、沪杭甬铁路局对沿线大型湖泊与周围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列入调查范围的有太湖、阳湖、阳澄湖、淀山湖、滆湖、固城湖、昆承湖、石臼湖、长荡湖、丹阳湖、赤山湖、玄武湖、莫愁湖、南湖等近20个大型湖泊,均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的腹心位置。该调查将湖泊周围陆地所产的稻米、桑蚕、茶叶、水果、竹木等,与湖水中所产的鱼虾、荸荠、菱角等罗列在一起,同时又紧扣周围民众的生计状况,这正是“湖区”经济体意识的具体表现。从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时人对“湖区”经济体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例如在描写太湖时,作者着意将湖畔洞庭山的物产与湖水中的出产融会贯通,甚至把湖周围的湿地水荡也涵盖在内:“洞庭是产水果闻名,四季出品极多,如东山枇杷、西山杨梅,桃、李、橘子等,产量均丰。他如碧螺峰之茶,西山之青石(质料优良,可制水泥),亦均其驰誉当世。湖中出产,亦甚丰富,有虾、蟹、鲫鱼、鲤鱼、鳗鱼、黄鳝、彩花鱼等,均负盛名。而湖荡中所产荸荠、塘藕、菱,亦殊鲜美可口。”(10)许英:《本路沿线之著名湖泊(二)》,《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5年第1451期,第31—32页。
再如对介于昆山、常熟、吴县、青浦四县之间的淀山湖,该报告称:“湖水澄清,烟波浩渺,湖中产鱼虾等水产动物极富,尤以秋蟹最著声誉。滨湖渔民,恃此湖为生者,不可胜数。湖底水草淤泥,可为农田肥料,湖畔农户,咸取给于是。每当春夏之交,四乡农民放船来湖夹取草泥者,络绎不绝,诚天然一富源也。”(11)许英:《本路沿线之著名湖泊(一)》,《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5年第1450期,第23—24页。
对于武进县境内的滆湖,该报告仍将湖体与陆地一体进行叙述:“湖面纵可五十里,横约三十余里,南抵宜兴,西通长荡,湖中碧波荡漾,湖舟出没,滨湖各地,农村错落,蒲苇深密,风景如画。湖中盛产鱼虾,尤以白鱼秋蟹为最肥美,下酒佳肴也。沿湖田亩,赖此湖灌溉,故农事向称富饶。”(12)许英:《本路沿线之著名湖泊(二)》,第31—32页。
昆山县的阳澄湖在调查者笔下也极为富饶。此湖水质清澈,十分适于大闸蟹的生长:“洋澄湖里的水,青绿可爱,平静的时候,可以洞见水底的游鱼和水草。”(13)张叶舟:《阳澄大蟹》,《杂志》1942年第1期,第61—66页。在收获季节,渔人一夜间可捕获数百只大蟹,每年产蟹三千担之多。(14)《渔业消息:阳澄湖蟹丰年》,《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1936年第9期,第13页。
总之,以上所列举民国文献中对长江三角洲湖泊地带的描述,多溢美之词,极言其物产丰饶、景色优美、民众富庶。在言辞间又自然而然地将湖体与周围陆地联为一体,将沿湖民众的生计与水陆物产放在一起来考量,这说明当时湖区水陆间的物质循环畅通,民众对湖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没有超过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湖区的物产和农副、手工业产品等也能够便利流通。
二、湖泊盛产之淡水鱼及其消费市场
鱼虾蟹贝,尤其是淡水鱼,为湖泊水域最重要的自然物产,也是民食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和江南市场流转的大宗商品。以下着重从淡水鱼的出产和消费来考察20世纪前半期长江三角洲的湖泊生态状况。
太湖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无疑是江南产鱼量最大的湖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曾详述太湖渔船的装载量:“(太湖)渔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装二千担,或五道,可装一千四五百担,或四道,可装千担。无间寒暑,昼夜在湖,每二只合为一舍。……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可装五百担,二道,可装百担以下。”(1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州备录上”,见《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六桅渔船可装两千担,合今20万市斤。而根据20世纪中期官方档案对太湖流域内河小船载重量的统计,一般均在2吨以下。照此估计,一艘太湖大船的装载量就相当于内河小船的500倍。(16)例如,根据1948年丹阳县的淡水渔业调查,全县有捕鱼船980只,载重均在0.5—2吨之间,没有大型捕鱼船(参见《三十七年度渔业统计报告表江苏省丹阳县渔业经营组合报告表》,1948年,江苏省档案馆藏胶卷,档案号:1004-乙-7312);又根据建国初期江苏省水产工作的远期规划,提出要逐步淘汰内河2吨以下的小船,增加5吨以上的大船,便于在湖泊生产(《江苏省水产工作长远规划资料(之一)》,1956年11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72-003-0011)。可见太湖产鱼量为其他湖泊和内河所根本不能匹敌。
长江三角洲多平原浅水湖泊,岸线曲折绵长,水流平稳,这为捕鱼船和渔民的生产作息提供了安全的港湾,因此以湖中捕鱼为生的渔民数量众多。据民国中期的调查报告,太湖南岸“北起长兴夹浦,南迄吴兴南浔,曲折二百余里,皆为渔船出没之所”,(17)《实业须知:太湖一带之渔业状况》,《兴华》1930年第27卷,第26—29页。沿湖分布着大钱、小梅、夹浦、义皋等近百个港口,既为水上交通要道,亦为渔船停泊的港湾。东岸则集中在苏属吴江、吴县两邑,仅两县境内在太湖中捕鱼之渔船就有八千艘(据1926年统计)。总计当时滨太湖各县渔民,“不下十余万人,均恃捕太湖鱼类为活。”(18)《苏州消息》,《申报》1926年7月23日,第10版。高淳县湖泊面积较大,渔民人口比重也相对较高,“除山地外,余统称水乡,水乡河流纵横,北有石臼湖,西有丹阳湖,南有固城湖、离湖较远地方之居民,以农为主,养鱼为副,沿湖居民,则以捕鱼为主,农业为副业。全县十三乡镇,除西溪、安奥、下坝、东坝四乡镇外,余于渔业非属正业即为副业,约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七,其中从事捕鱼者占十分之七,从事养殖者占十分之三,鱼类出产列为该县唯一之外销物品”。(19)《江苏省渔业改进管理委员会:三十六、三十七年度渔贷》,1948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胶卷,档案号:1004-乙-7383。
除大中型湖泊外,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在皆有、数量众多的连片湖荡,也是淡水鱼的重要出产地。湖荡所出鲤、鲫、鳜、鲶、鲢、青等野生鱼类,向来为大批专业渔民和兼渔农民的生计之资。嘉善县地势低洼,湖荡密布,其光绪县志记“近湖荡者,习渔业”,以水荡捕鱼为生是低洼地区的主要经济门类。(20)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物产》,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5》,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绍兴县境内平原地区约有十余万亩水荡,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就有五六千人,据1921年之统计,年产鱼量在两百万斤以上,合两万担。(21)《萧绍行脚》,《申报》1946年8月25日,第8版。这些渔民中一部分为专业捕鱼,多数则为沿水荡居住的农民,他们农忙务农,农闲则以捕鱼捞草为业。(22)一鸣:《绍兴一带养鱼及捕鱼》,《自然界》1931年第7期,第580—585页。又如湖泖地带的吴县,也并不仅仅依赖太湖、阳澄湖等大型湖泊的渔产,其境内的金鸡湖、独墅湖等小型湖泊以及长白荡、太史田、箫田河等连片水荡,累积起来的产鱼量也相当多,在这些湖荡捕鱼的渔民总计达一千多户。(23)《吴县渔业概况》,《渔况》1932年第46期,第4—5页。
1947年,江苏省渔业改进委员会对太湖流域北片(相当于江苏省辖长江以南地区)进行渔产调查。报告显示,凡境内有大中型湖泊的县,其淡水鱼的年产量均偏高:溧水县境内因有石臼湖,年产鱼量达到70000担;昆山县南部毗邻淀山湖,年产鱼量达50000担,北部毗邻阳澄湖,年产鱼量为24000担;吴县除南部享有太湖渔利外,北部毗邻阳澄湖的地方另年产鱼量25920担;金坛县境内的长荡湖面积稍小,但年产鱼量亦有18700担。(24)江苏省渔业改进委员会:《渔业状况调查表》,1947年,江苏省档案馆藏胶卷,档案号:1004-乙-7375。再将这些县与同时段统计的缺少湖泊的县做一对比,位于东部高乡的嘉定县,因境内没有湖荡,仅靠窄小的内河出产零星淡水鱼,其年产鱼量只有3600担。由此显然可见,20世纪前半期长江三角洲的湖泊与湖荡是淡水鱼生产的富源地,而平原上遍布的河流泾浜则因水流不稳,“渔船全系小型”,渔民散漫流动,致使产鱼量无法与前者相比。(25)江苏省渔业改进管理委员会:《江苏省之渔业》,1947年8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0415-0013。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城市愈加成为农副产品消费中心,以初级农副产品为原料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发展。中国日益融入国际贸易圈。在此背景下,农副产品需求市场比传统时期扩大,那么,传统以湖泊为主的淡水鱼生产格局是否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以下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鱼市场消化淡水鱼产品的能力来简要说明。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淡水鱼消费的最大中心,并通过其城市鱼市场转口运销到国内外其他市场。(26)上海为近代中国最大城市和进出口贸易中心,淡水鱼的消费量大于长江三角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市场。1935年一位农学家的文章如此定性上海鱼产品消费的能力:“上海不但是海产鱼消费的市场,就是淡水鱼类的消费量,也着实庞大。内地渔民及运鱼客商,亦莫不视上海为唯一的泄货尾闾。我们随便跑到哪一个小菜场上转一转,就晓得淡水鱼类、虾类、蟹类的数量,并不较少于海产。据《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上的统计,每年淡水鱼的消费量,约计有五百万元之谱。”参见徐季抟:《上海鱼市场应注意淡水鱼的商榷》,《水产月刊》1935年第1期,第4—6页。根据上海鱼市场的鱼货交易数据,1933年上海野生河鱼消费量为159748担,1934年为169509担,1935年为178479担,1936年为236051担。(27)祝年:《抗战期间上海市鱼类之消费量及鱼价》,《水产月刊》1946年复刊号,第19—21页。若取这几年交易量的最大值23万担与前文述及的1947年江苏省太湖流域片鱼产量近40万担做一比对,大致可得出结论:因战后生产处于恢复时期,战前20世纪30年代的产鱼量应高于40万担,那么,仅太湖流域北片湖泊所产鱼类总量的60%已基本可满足上海中心市场的供应,更何况浙西片的湖泊也盛产淡水鱼,其中也有部分可供应上海市场,只不过本统计未将其包含在内;而供应中心口岸市场之外的余量,也完全可供应县级市场和本地基层市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地方上的鱼产品销往上海、县城、本地的比例一般是4∶4∶2。(28)谢潜渊:《湖州、杭州、苏州之养鱼业》,《水产月刊》1946年复刊第1卷第3期,第47—54页。按照这一比例,在湖泊产鱼的基础上,再加上河流产鱼与池塘养鱼,应当可以满足各级市场的需求。即使湖泊出产淡水鱼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时有浮动,湖泊地带素有发展的人工养鱼业也可作为补充。当时上海市场的淡水鱼产品也是包含一部分养殖鱼在内的。
总之,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长江三角洲各类湖泊和湖荡仍然是中国东南地区最主要的淡水鱼生产地,其实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淡水鱼基地,大量渔民和兼渔农民以捕捞野生鱼为生计,淡水鱼品种繁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特色名产。虽然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和工业化的发展,淡水鱼增产的动力也相应增强,但可通过进一步扩大池塘养鱼面积和增加饵料投入来应对。人工养鱼依赖湖泊之水和湖中营养物,充分利用湖泊周围的洼地,再适当添加人工饵料,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人工养鱼可与湖泊出产野生鱼并行发展,而没有必要打破湖泊原有的物产生态链条,像后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把湖泊变为专门养鱼场。
三、民众生计及其对湖泊的情感
湖泊水资源和各种物产最终服务于民众生计和社会消费,因此以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观点看来,民众对湖泊资源的利用方式,以及他们对湖泊的价值认知、情感和维护行为等,应当是研究湖泊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内容。(29)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将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观念、心态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生态系统变化的研究。可参考卞显红、王国聘、黄震方等:《评生态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2002年第2期,第37—45页。实际上,历史时期某一地域的生态环境是否良好,很难套用现代科学所谓精确、繁复的数据指标来运算。回到历史现场,去发现利用某种环境资源的人对自然的赐予有着怎样的态度、情感和回报,对本文所研究案例来说可能更为贴切。由于民国文献中多泛泛而论湖泊物产丰饶的溢美之词,民众对湖泊物产的内在情感和具体行为反而少有细节性记述,本文将利用新中国初期档案中湖区群众对过去生产情况的回忆资料进行若干追溯。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湖荡被一窝蜂地开辟为国营农场和养殖场的时期(大型湖泊的农场化改造稍晚,且推进过程比较曲折),原有生态平衡被打破,湖荡野生鱼的产量骤然下降,同时,由于养殖鱼属于国营渔场所有,原以湖产为生的渔民、农民、商人等不得不改变旧有的生计方式。例如,60年代中期的渔改规定,渔民集中在陆上定居,政府按照对农民的管理方式对他们进行管理,渔民逐渐转变为池塘养鱼者或改事其他农副业。这时,当湖区民众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他们对旧日湖荡物产的丰足充满怀念。
例如,嘉兴南汇地区是浙西湖荡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大跃进”结束后,嘉兴县政府针对当时日益尖锐的湖荡水面利用矛盾,对南汇地区的问题做了重点调查,从百姓口中了解到1952年国营养鱼场大量占用外荡水面进行人工养鱼以前的湖荡物产以及民众的态度:“南汇地区溇浜河港,纵横交错,水荡资源极为丰富,历年来,人们从水荡中取得肥沃的肥料,取得品种繁多的野生鱼虾和菱、芦、蒿、草等多种水生植物。人们赞颂水荡说‘岸上的黄金铺地面,水里的黄金没脚背’,意思是水里的资金比岸上的黄金厚得多。这种情况说明,外荡的合理利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经济意义。”(30)《嘉兴县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嘉兴县南汇地区外荡养鱼问题的调查材料》,1961年4月21日,嘉兴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2-031-161。群众认为外荡养鱼不仅同野生鱼的捕捞有矛盾,而且同粮食生产、副业生产也有矛盾。农民更看重的是湖荡里取之不尽的肥源。湖荡出产的肥料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成本低、肥效高:“农民历来从外荡中取得的肥料有三大类:一是大量的水草、菱秧;二是肥沃的河泥;三是资源无限的螺蛳。农民说,每亩水草、菱秧的肥效,超过一亩草籽,一船河泥抵得上五斤化肥,一担螺蛳抵得上二斤化肥。由于水草、菱秧、河泥、螺蛳等资源丰富,农民取得这些东西,成本低,时间省,收效快,所以1956年以前,这里的农民根本不用化肥,也不种草籽。”(31)《嘉兴县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嘉兴县南汇地区外荡养鱼问题的调查材料》,1961年4月21日。
并且,过去渔民(包括专业渔民和农闲捕鱼的农民)以捕捞湖中天然所产鱼虾为生,“这个地区的天然鱼品种极多,产量很大,常见的有鲤鱼、鲫鱼、白水鱼、鳑鲏鱼、菜花鱼、鸡晓鱼、鲈鱼、小鳊鱼、鳗鱼、黄鳝、鳖、蟹、虾、蚬子、螺蛳等大小二、三十个品种,还有不少名产如鱼窝虾,肉肥味美,运销上海,名次仅在对虾之下。丰富的鱼鲜,不仅充分地满足了当地人的自给需要,而且成为这里重要的商品经济”。(32)《嘉兴县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嘉兴县南汇地区外荡养鱼问题的调查材料》,1961年4月21日。由于渔产丰富,南汇镇的鱼货贸易也很发达。据档案载,1953年以前,南汇镇上有三家鱼行、七个鱼摊,从业人员达40人,每天有四五百条船集岸卖鱼,常年平均每天收购五六十担,全年收购量约在两万担左右。
但是,1956年之后,国营渔场占用来养鱼的水面越来越多。首先是国营场圈占的湖面禁止捕捞,原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和部分农民生活困难,野生鱼成长环境被养殖鱼挤占,产量越来越少了。其次,芦、蒿、草、螺蛳等水生动植物被过量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吃光,菱也无法种植,刚抽芽就被鱼咬断,芦草少了,手工编织、养牛养猪甚至是烧柴燃料都受到影响。而农民由于得不到肥料,不但买起化肥来,而且大量种植草籽,1960年南汇地区草籽播种面积达耕地面积的50%,等同于春粮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减少了50%。湖荡农场化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原有生态系统和周边民众的生计来源,原先民众对湖荡资源的感恩之情变成了抱怨和对抗,继之发生对国营渔场的抗争和社会群体矛盾,甚至不断发生国营渔场职工与本地人为争夺捕鱼权而打架斗殴和流血的事件。这时,不仅群众对湖泊不再爱惜,国营渔场为完成交售指标而养鱼,吃大锅饭,也没有劳动积极性。
又如,昆山县昆承湖地区群众对湖泊的情感和态度,也经历了由依赖、爱惜到漠不关心,甚至故意破坏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以前昆承湖盛产鱼虾,渔民俗称其“来一朝水,来一朝鱼”,说“昆承湖是活宝湖,一天一只活元宝”。沿昆承湖周围有专业渔民340多户,共1486人,历来就在湖内进行常年性的捕捞。当地农民也素有农忙为农、农闲为渔的生产习惯,他们一年有180天到240天时间到湖里捕鱼、捉蟹、摸虾,在1957年前平均每家农户的捕鱼年收入还能达到400元至500元。这种半渔半农的人家有175户,原来每户一天捕鱼5斤,一年捕鱼9担,总产量就有1575担。有社员反映,“一串金丝钓(麦钓)一夜捕鱼,三天吃用”。但是五六十年代的跃进式生产打破了原来的生计方式,国营渔场禁止群众捕鱼,造成渔农群众不满,因此经常与场里发生矛盾。1960年冬天,“港口看守棚被群众拆掉五处,拔掉竹帘子300多丈,损失毛竹500多支,闹事殴打20多起,严重的一个工人被打伤而逃跑回家”。昆承湖养鱼的产量也年年下降。未放养前,每年捕捞天然鱼产量为4486担,平均亩产16.6斤;放养后,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产1668担,亩产为6.18斤,比放养前下降62.3%。(33)《苏州专署副业局:关于昆承湖养殖生产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8月10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H37-002-0010-046。
湖泊作为一种公共水利资源,其社会经济价值体现在蓄水排水、自然捕鱼、农田灌溉、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渔、农、工、商各个群体共同受益。正因湖泊水利和物产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才得到社会各群体的爱惜和维护。在这种机制下,那种为牟利而据湖泊为专有的行为受到群众抵制。民国时期群众反对利用公共湖荡养鱼的例子屡见不鲜,官方也对此严加管制。例如,1919年高淳县有人仗势圈占公共湖荡的一部分进行养鱼,民众推举士绅代表向江苏省实业厅举报,政府以“创办渔业与农田水利均有妨碍”为由,命令禁止两县湖荡用之于养鱼。(34)《江苏省长公署批第一千五百九十四号(1919年1月20日):原具呈人王贻善等呈为呈请饬查湖荡试办渔业》,《江苏省公报》1919年第1832期,第7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公司的风气也影响到农业经营领域,但政府仍然认为湖泊不应用来进行专门的经济牟利,大规模的公司式养鱼仍被禁止。1931年,嘉兴县双桥区的信记和裕泰两公司未经政府批准,私自与地方乡绅达成协议,投资在公共湖荡中养鱼,并筑造了坚固的鱼簖,但不久便被县政府以影响水灾后的排水为由,勒令拆除全部鱼簖,取缔该公司的经营。(35)《嘉兴消息》,《申报》1931年8月31日,第12版。归根结底,民众对湖泊的情感和维护态度,是由其享受湖泊物产的权利及其潜在共享的水利价值决定的,而官方并不参与湖泊的经济经营,使其能够站在公共立场上维护湖泊水利的公共性。
四、结论和思考
通过对20世纪前半期长江三角洲湖泊区域的物产、民众生计、民众对湖泊情感、官方管理机制等要素的考察,可初步得出结论:该时期湖区物产丰饶,生物多样,湖泊之利惠及渔、农、工、商各个社会群体,民众对湖泊有爱惜和维护的意愿,专占湖泊的行为受到抵制,因此,这是一种社会各群体共同参与的权与利相统一的湖泊利用机制。这种机制具有历史传统,查阅古代江南地区的方志和水利文献便可得知,政府一贯的宗旨是着力于湖泊公共水利价值的维持。在这一宗旨下,那些企图独占湖泊资源进行经济开发的行为,例如圈围水面进行养鱼、种菱而不许他人进入,围垦湖荡进行农业种植等,皆因影响湖泊的排蓄水功能和基本的农田水利而受到制止。政府更不直接参与利用湖泊进行牟利的行为。虽然这一公共水利原则并不能完全制止占湖行为,湖泊毕竟是一种“公地”式的资源,各种侵占和过度开发屡有发生,但长期来看还是保障了湖泊的正常水循环和物产多样性。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认为,官方对共享机制的维护,加上民众出于共享湖泊之利的自觉维护,才是维持湖泊生态可持续性的最佳方案。在民众方面,出于湖泊物产对于生计的支持性,面对专占湖泊的垄断性行为,将自发地进行抵制或诉诸官府进行处理,这也是使得湖泊利益共同体得以维持的一种力量。
虽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江南地区已较多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浸润,人们也试图将湖泊环境转化为更大的生产力,例如圈围湖荡进行养鱼和围垦的事件不断发生,渔民“酷鱼滥捕”、不注意保护幼鱼资源的趋势也已显现,(36)例如,可参阅江苏省渔业改进管理委员会文件:《江苏省之渔业》,1947年8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0415-0013。其中对当时湖泊渔业的状况称:“本省湖沼水面广阔,渔船较大,有二、三、四平帆等之称,每一平帆计篷二道,风愈大所经区域愈广,而渔获亦愈多。惟近来渔获数量远逊于前,因渔民酷鱼滥捕,在产卵及稚鱼时期,不加保护,致生产日减。”但是,整体上政府并未允许湖泊资源为某一群体所垄断和专有的现象,湖泊物产的共享机制并未改变。因此,湖泊水质良好,湖区经济体对湖泊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尚得以保持。
本文特别对湖泊鱼产量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做了考证,发现直至20世纪40年代,湖泊鱼产量基本可满足上海中心市场和基层市镇的消费需求,再辅之以湖泊资源支持下的池塘养鱼,可以说长江三角洲淡水鱼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还是平衡的,还看不到“竭泽而渔”或者将湖泊水面改为国家养鱼场的必要性。50年代以后,湖荡农场化运动及其国有化经营机制却使得湖泊自然出产野生鱼和其他物产的环境短时间内被大幅度改变,湖区民众的生计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政府面临着重新为他们寻求生计门路的压力。以渔转农为旨归的渔改的施行,其中便有湖泊生态变化给大批渔民带来生存压力的因素考量。
今天长江三角洲湖泊普遍面临富营养化问题,而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湖泊农场化就已经开始滋生了。再加上后来工业发展和农药、化肥对湖泊水的污染,使得长江三角洲湖泊生态的退化日益严重。目前,政府对长江三角洲湖泊环境的治理已全面展开,但其中水面使用权和湖泊利益的分配仍然是关键问题。希望本文对近代一段历史中的湖泊物产权利和生态关系的分析,能够为之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