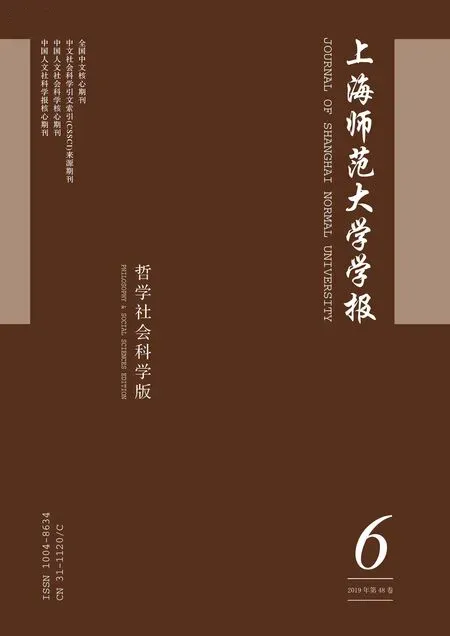从苦恼到朝向他者:列维纳斯关于恶的现象学
刘文瑾
身为犹太人,20世纪的社会历史灾难是激发列维纳斯思考的现实背景和思想酵素,恶的问题是贯穿他一生哲学追问的思想线索,也是其关键词“纯存在”(il y a)、“他者”和“上帝”等意义敞现的思想视域。虽然对恶的直接论述不多,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对存在和存在论差异的思考就是对恶的反思。
除了对恶的一些现象学描述,诸如将恶描述为“过度”(l’excès )、内含意向性,以及对恶的厌恶,(1)“Trancendence et Mal”, 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aris, Vrin, 1982.列维纳斯没有给恶下过定义。恶在哲学史上,实际上也是很难被定义的。帕斯卡说:“恶很容易,有无限繁多,善却近乎唯一。”(2)le Mal, textes 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Claire Crignon, Paris: Flammarion, 2000, p.11.利科则指出,恶是个谜样的词。至少在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这个词包括了一些既相近又相异的现象,诸如:罪、苦难和死亡。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包含着对苦难的参照,恶有别于罪和罪责。(3)Paul Ricoeur, Le Mal: Un défi à la philosophie et à la théologie, Genève: Labort et Fides, 2004, pp.21-22.实际上,法语中的“恶”(mal)这个词便有别于英语中的evil:mal既有邪恶(evil)的含义,也有痛苦(suffering, pain)的含义,既是作恶,也是受难。这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为何能用一个词表达?利科称,在作恶和受难的差别中有种“相同的谜样的深度”。(4)Ricoeur, Le Mal: Un défi à la philosophie et à la théologie, p.22.列维纳斯在其一篇关于恶的重要文章《超越与恶/痛苦》(“Trancendence et Mal”)中,便同时涉及了mal一词作为作恶与受难的两种含义。其中的合理性,既是由于邪恶会导致苦难,也是因为邪恶与苦难不只有自然与物理方面,也有精神性层面:遭受不幸的人感受到同存在之链的脱节,一种被抛弃和排斥的状态;而作恶之人,亦处于同上帝、他人以及世界之关系的出离。
利科总结说:“对于遭遇的恶、受苦或作恶,没有直接的非象征的语言。当人们声称对某种恶负责或受到了某种恶的伤害时,他们首先是在一种象征意义上谈论恶。”(5)Paul Ricoeur,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 Paris: Seuil, 1969, p.285.他指出,恶既不是某种事物,也不是某个概念,而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词。当我们试图以逻辑思辨的语言来谈论恶时,恶就会具有谜一般的性质,因此,恶对于哲学和神学构成了一个挑战。
列维纳斯很少正面讨论恶。即便当他讨论恶时,他的焦点也不是追问恶的本质或本体是什么,而是试图借着对恶的诘问通往对善的领悟。他深知,对于心灵,恶构成了一种诘问,但不属于那些人们以某个观点或某种解决方案就能应付的问题。因为,对恶的超越之道,不是通过解答,而是通过善:“超越存在之诘问,所得到的并非一个真理,而是善。”(6)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Levinas,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1947), Paris, Vrin, 1998, p.28.同样,对善的追求也不在于获得善的知识,而在于善的践行。在列维纳斯那里,善就是对他人的“渴望”(désir d’autri)和朝向上帝。这渴望不同于需求(besoin)或享乐(jouissance):这二者最终回复到自身,而渴望他人则是将他人作为绝对他者,是一种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伦理学”,让人超越存在。在此意义上,恶同善一样,超越知识和理性,而指向与他者的关系和行动。
一、苦恼:恶作为“过度”的精神现象
列维纳斯指出,恶的首要特点是“过度” ,其精神上最尖锐的表现是苦恼。这“过度”并非指数量上超标,而是描述一种断裂性的实质(quiddité)。(7)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aris, Vrin, 1982, p.197.它描述这种状态:被孤独而牢固地系于自身(soi)的物质性生存而无法摆脱,以致既无开端,也无终结,既没有他人,亦无自我(moi)。这状态与正常秩序或标准脱节,出离世界之外,不可能被综合统一,也不可能被归置于任何一种逻辑、形式、类别或整体,仿佛是某种存在的“超越”性。“痛苦(la souffrance)作为痛苦,只是对不可统合、不可证成性事物的具体和半感性展示,恶的‘质量(qualité)’就是不可统合性(non-intégrabilité)本身。……恶不仅是不可统合之物,也是不可统合之物的不可统合性。”(8)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p.197-198. 着重号来自列维纳斯原文。
列维纳斯通过“过度”来描述恶的不可见的精神现象。在此,恶的过度性并非指痛苦或暴力程度方面,不是物理事实上的描绘,而是精神现象上的描述,是描述“恶的恶意性(la malignité de mal)”。(9)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197.恶的恶意性在于,恶指向世界的终结,让人自绝于世界和他人,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孤独中。这种对恶的描述同他对il y a的描述是一致的。
回顾列维纳斯的早期著述,他正是在il y a中描述恶,而且这些关于il y a的描述也正包含某种“过度”的性质:“从本质上说,存在是奇特的,它撞击着我们,如黑夜一般,将我们紧紧地裹挟,令我们窒息,痛苦万分,却不给我们一个答案。这就是存在之恶。”(10)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第11页;Levinas,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28. 少量字词参照原文有改动。“那无法免除亦无可逃离的存在观念构成了存在根本的荒谬性。存在是恶,不是因为存在的有限,而是因为存在没有限度。”(11)Levinas, Le Temps et l’autre, Montpellier,1947; Fata Morgana, 1979, p.29.通过il y a,列维纳斯揭示了存在的可怕处境:孤独地固着于自身当下的物质性生存,既无他人,也没有来自他人的召唤帮助我浮出一种渊面混沌黑暗的空虚处境。这是一种没有起源和创世,没有未来,也没有主体“我”的荒凉。荒凉不是因为没有存在,而就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存在的过度。
列维纳斯经常借助文艺作品来帮助反思il y a,为此既涉及现代艺术对异域感的审美趣味、布朗肖作品中的“中性”、策兰诗歌中的他者性,也涉及经典悲剧名著,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部列维纳斯眼中“悲剧的悲剧”。《约伯记》则是列维纳斯在思考恶时常用来帮助深入理解问题的文本。约伯在苦难中发出叹息:“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10∶20)“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13∶21)夏利埃指出,约伯这种被上帝追击到无处可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觉,与深陷存在之罗网的感觉相连,(12)Catherine Chalier, La Persévérance du mal, Paris, Cerf, 1987, p.42.以致他呼求:“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6∶9)“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骨头。”(7∶15)
在列维纳斯看来,约伯遭遇的苦难,固然首先是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家破人亡之痛、身体发肤之苦,但在这些痛苦之外,约伯感受到了恶(痛苦)最尖锐的内核——“苦恼”(angoisse)。
“苦恼”是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angst(通常中译为‘畏’)”对应的法译词。列维纳斯指出,约伯苦难的核心,苦难中的苦难,正是那与其肉体之痛具有同样深度的精神上的苦难——一种人际关系中的被弃:羞辱、孤独与迫害。(13)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196.这种在其肉体之痛中感受到的“苦恼”,与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苦恼”相通。(14)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p.195-196.“苦恼”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畏”,有别于对具体事物的“怕”,是对死亡背后之虚无的预感和揭示。这种情绪“能够把持续而又完全的、从此在之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存在中涌现出来的此在本身的威胁保持在敞开状态中”。(1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67页。海德格尔强调,“畏”让人在面对“必须独自去死”的事实,从此在的根部获得自我领会,由此而从世界中抽离,学习孤独地向死存在。列维纳斯对“苦恼”的理解,却全然不具有海德格尔式的英雄气。海德格尔的“畏”所开启的,是一种立足于绝望和虚无的勇气,这种勇气让人在向死而在中走向孤独和绝对的唯我主义。而在列维纳斯看来,“苦恼”所对应的,是生命和存在的绝境、无意义与荒谬:“疼痛之恶,其要害所在,是一种绽出(l’éclatement),作为荒谬最深刻的表达。”(16)Levinas, “La Souffrance inutile”, Entre nous, Essais sur le penser-à-l’autre, Paris, Grasset, 1991, EN, p.102.这种荒谬完全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一种亟待救赎的状态。
按照列维纳斯的理解,恶作为与荒谬对应的“苦恼”,以及作为“被弃”和“出离”对应的non-intégrabilité(不可统合性)、inassumabilité(不能承受性),(17)Levinas, “La Souffrance inutile”, p.100.显然带有深刻的圣经痕迹。在圣经中,恶与痛苦的根源在于人对同上帝之约的背叛,从而背叛了与世界的和谐关系,陷入以自我存在为绝对的虚无主义深渊。我们不难在基督教文学经典中看到对这种作为存在之过度的恶之经验的表现。奥尔巴赫谈论但丁《神曲》第十歌对地狱第六圈中的人物、燃棺居士法利那太和加发尔甘底的描述时,反复赞叹其形象的鲜明与传神。但丁让他们在相同处境下始终各自保持着尘世生活时的鲜活个性与特征。这些地狱中人,无论是像法利那太那样,始终坚持自己在尘世时那种超然的道德力量、蔑视当下的地狱处境,还是像加发尔甘底那样,表现出从未如此强烈的对尘世生活的向往和对儿子的爱,都同样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永恒境地”和“上帝的判决”,此即:他们的尘世本性“一如原样在无望的徒劳中延续”。(18)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26页。
奥尔巴赫指出,在但丁这个宇宙建筑师的笔下,地狱之为地狱,除了种种阴森可怖的场景之外,更在于这种被困在尘世生活中的“永恒境地”,这种欲罢不能的永罚处境。“他的死者虽然已经脱离了尘世的现时和变化,然而回忆和对其热切的关心依然驱使着他们,以致彼世的景色完全为其所充溢。在炼狱山和天堂这种氛围就没有如此强烈,因为那些地方的目光不像地狱里的只是往后看尘世生活,而是朝向前方和上方,因此我们越往上走,就越加清晰地将尘世的存在与其神的目的看作一体。”(19)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第227页。但丁以神来之笔揭示:地狱与炼狱和天堂的差别,不在于一种外在于尘世生活的处境,而是在尘世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过度”固着于尘世的存在样态。就像罗得的妻子,由于其恋恋风尘,不舍地回头张望应当离弃的故居,而变成了一根盐柱(《创世记》19∶26)。
但丁的宇宙建筑深谙地狱与天堂的奥秘:如果说地狱之为地狱,在于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无望、热切而固执的徒劳,那么天堂之为天堂,不在于对尘世的取消,而在于其中每个尘世的瞬间都有上帝之爱“随时”与“直接”的光照,在于这些瞬间经由彼岸和上帝这一绝对他者而获得“完成”。(20)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第228—230页。也就是说,“从每个尘世事件和每个尘世的显现随时都与上帝的计划紧密相连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且这种联系丝毫也不依赖发展。也就是说,尘世间的每个现象通过大量的垂直联系直接关系到上天的拯救计划”。(21)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第228页。由此,天堂之于尘世,永恒之于当下,他者之于自我,才构成了一种“完成”或者说救赎。这也正是列维纳斯对终末的思考:“重要的不是那最后的审判,而是对生者于其中受到审判的时间中的每一时刻的审判”;(22)Le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p.8.末世不是未来某个作为终结的时间或“超”时间,而是与圣言同在的当下时刻。而恶,则是这种“同在”的不可能,是不可统合性与不可承受性伴随着被困于自我存在之孤独的苦恼。
二、恶触动灵魂与大写之“你(Toi)”的关系
列维纳斯描述恶的现象学的第二个方面,是恶对灵魂“意向”(intention)的触动,对灵魂与大写之“你”——上帝——之间关系的激发。(23)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200.列维纳斯晚年在《超越与恶/痛苦》一文中,借助对菲利普·内莫(Philip Nemo)《约伯记》解读的评论,深刻表述了他关于恶的现象学。在此,他视恶为感知超越性的契机。这既是他关于恶之问题的独到见解,亦是他对以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某种“存在论神学”类型中的“超越性幻觉”(l’illusion transendantale)(24)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190.之批判。在他看来,无论恶还是超越性,都不是一个智识问题,而是伦理和精神质地的判断。在此意义上,他视伦理而非存在论为形而上学的开端和“第一哲学”,因为形而上学的旨趣是超越。
遭遇巨创不幸之人常会本能地寻找不幸的根源,认为自己被某人或某个诸如“老天爷”之类的神灵刻意“对付”了。即便遭遇的是极其偶然的无妄之灾,人们在求告无门之剧痛中,也难免像约伯那样指责“老天(上帝)怎么没长眼睛”,难免质问为何不幸偏偏发生在“我”而非其他人身上。人们是在一种极其个体化和切身性的处境中与恶迎面相遇。对此列维纳斯描述说,恶是一种对我的“瞄准”。(25)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200.然而这“瞄准”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只是发生于外部的客观事件,更是一种内在心灵的创伤,即我们前面说到的angoisse。
但列维纳斯指出,这只是恶的“瞄准”所意味的一个面向,还有另一面向:被恶“瞄准”、遭遇迫害也是灵魂苏醒的机缘,因为恶唤醒了人们对意义的感知。灵魂在受迫害之痛中开始敏感于善恶有别,并质询大写之“你”,由此产生了列维纳斯描述恶之现象的第三个方面——恶是对恶的厌恶(la haine du mal)。(26)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203.往往正是借由对恶的厌恶,人们才能领悟上帝之善的纯全、宝贵。人对上帝的认识和爱,常是从对恶的切身感受开始的。这是灵魂真正认识自我、世界和上帝的契机。对善恶差别的领会既是人的第一堂成人课,也是对上帝的启蒙课。这对于生活在无神论时代的现代人而言,更是如此。在此意义上,恶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让灵魂麻木冻结,也可能促使灵魂迫切寻找精神转向的契机。在此意义上,拒绝让记忆向恶妥协,保持对恶的见证与记忆,便具有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意味。这种重要性显然不仅在于让我们对恶保持警惕,不让历史重演,更在于让我们对善保持敏感与热爱。因此,但丁笔下的朝圣之旅似乎注定了只能以行至人生中途、深昧人世险恶的幽暗森林开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被当作了某种道德功能,而是说,人们有可能在对善恶差别的感受中开始领会“无限”的意义,并发现他者处身于“无限”的“踪迹”之中。
列维纳斯指出,首要的形而上学问题是对善恶的追问,而非对事物存在与否的好奇,(27)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203.此即缘何伦理学先于存在论。这也是彼岸与此岸的差异和彼岸对此岸的超越性之所在。 超越性不是否定性,而是善恶有别。且善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对他人的责任,意识到他人在我之先。只有作为经由与作为绝对他者的大写之“你”的关系,人才能超越善恶无分的世界。
三、恶是朝向他者的契机:面容与超越
然而,若仅将彼岸和大写的“你”视为对此岸的抽象超越与对立面,这在列维纳斯看来,难免又会重新沦为某种神义论。(28)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203.他指出,神义论的特点,就是将彼岸与此岸纳入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或一种综合中,以致彼岸成了对此岸的证成,此岸成为对彼岸的成全。这种神义论倾向始于圣经传统,而非仅从莱布尼兹的命名开始。其最大问题,是对恶的合理化解释。里斯本大地震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曾对神义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然而,启蒙哲学家虽动摇了传统神义论,却无法阻止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以进步史观为圭臬的现代神义论兴起。列维纳斯正是想要通过他者、面容和无限,通过奥斯维辛之后的上帝——体现为为他人的苦难受苦的主体性——来撼动这个现代神义论传统。
因此列维纳斯对恶之思考的独特,在于他试图超越否定辩证法。恶作为“过度”,已然是对一切统合性和辩证法的拒绝,而善在他那里,同样有种“过度”的性质。善的“过度”,虽然他在《恶与超越性》一文中谦逊地称之为内莫的创见,但其实早已在他自己之前的著作《总体与无限》中得到过深刻缜密地阐发:善,就是渴望那不可见、不可被满足的,是渴望无限。这大写的渴望(Désir)作为一种爱的满溢(Surplus),既不同于因匮乏而产生的需要,也不同于享乐的欲望,而始终超出人们的所想所求。在此意义上,作为超越的善,就是永不停息地向善,是期待那永远在期待之中的无限。(29)参见Emmanuel, “Métaphysique et transcendance ; 1. Désir de l’invisible”, Totalité et Infini, pp.21-24.
那么,善的“过度”与恶的“过度”之间,是否构成一种二元对立或否定辩证法?至少它们在表述上有种对称性。在列维纳斯那里意味着不可统合性的“过度”,显然是对总体性的突破。而善的“过度”对恶的“过度”,则构成了回应和超越。只是这种回应与超越并非经由抽象的逻辑与观念,而是经由物质性的具体内容——来自他人面容的启示。
面容的启示意味着:在瞄准和追逐着我的恶中,他人遭受的恶能触及我;我在自身的痛苦中察觉他人的痛苦;仿佛在我悲叹自己遭受的恶和痛苦,深陷恶的“过度”及其“苦恼”以先,我有责任先回应他人的痛苦。由此,恶的孤独与被弃便有可能被一种为他人的善穿透;由此,我所遭受的迫害得以升华,成为牺牲——向神的献祭;由此,痛苦不再显得纯然荒谬而难以忍耐。因为与他人隔绝是痛苦最尖锐的内核,而当意志放下其自我中心,将重心移出自身之外,能够“为了……人”而忍耐、受苦和牺牲时,暴力、痛苦和死亡的无意义与荒谬才变得可以承受,受难被转换为激情(Passion)。对此艰难的超越,列维纳斯称之为“忍耐”(la patience),(30)Le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pp.266-267.夏利埃则称之为“善的战栗”(le tremblement du bien)。(31)Catherine Chalier, La Persévérance du mal, p.16.
事实上,Passion(激情)这个法文词的拉丁词根Patti就是“受难、忍受”。Patti也是Patience(忍耐)的词根。其过去分词Pass的名词形式Passio在后古典主义时期也被用来指称希腊词Pathos(耶稣受难)的含义。由Pass衍生出来的Passive,由于意味着“能忍受痛苦”而演化为“被动”的意思。
列维纳斯虽然批判神义论和与神义论相连的上帝,但并未放弃超越性和一个没有神义论的上帝。只是这是一个隐藏于他人面容背后的缺席的上帝,有着他人面容的苦弱与卑微。因此在他的哲学中,超越性不是概念的否定辩证法和二元对立,并非对恶的简单倒转,而是通过与他人的苦难面对面,来体现出善对恶的优先。由此,超越性成为对恶的艰难担当,和对人类灵魂尊严的提升;由此,同恶相遇的不幸成为唤醒心灵、感知他者的契机。事实上,在现代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或许唯有经由对痛苦/恶的体验,才有可能让人穿透理性的厚墙,通达对他人的同情与倾听。
与其说这是一种对恶的知识,不如说是对恶的超越之途,是在经历过一个灾难的世纪后,对主体责任意识之觉醒与对启示之意义的反思。在后世俗时代,或许唯有通过对恶的感受,人们才能走向乐土,如同但丁在《神曲》中设计的那样,通往天堂的道路经过了地狱的最深处。这不同于将上帝功能化的神义论,而是世俗时代中人们感知神圣和超越的方式。因为启示并不能与人的感知方式完全脱节,而上帝说着人的语言。只不过,那不是经济学的语言,而是爱的隐喻的语言。亦如但丁在《神曲》中揭示的,爱最终应当成为喜剧——救赎的喜剧,不是因为付出与回收、占有与满足,而是因为人生与历史的轨迹可以被另一种天体运动的方向所改变。在这种运动中,人们的时空与位置不知不觉被挪移被改变,不再只有此生此世,也不以死亡为终点。人们并非在世界的囚笼中,仅有地球引力的必然性运动,而同时也在与另一个不可见的天体发生关系、产生爱之救赎的牵引。
四、约伯的醒悟
最后让我们通过列维纳斯对《约伯记》临近结尾之片段的解读来尝试理解,一种从苦恼到朝向他者的恶的精神现象何以可能。这并非要以圣经的权威性或文学的修辞性来代替哲学的理性思考,而是因为在列维纳斯看来,圣经和文学中可能包含着一种极其重要的思想,可以动摇哲学概念的单一自守。在列维纳斯这样的现象学哲学家看来,他人的面容、文学与哲学,三者应当彼此照亮。
《约伯记》中,在经过了约伯同三位朋友以及年轻的以利户之间的几番大段辩论之后,上帝并未置约伯的申诉于不顾。他从旋风中向约伯显现,批评约伯在申诉中以口犯罪,“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约伯记》38∶2)。他质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约伯记》38∶4)还责备了约伯对上帝的否定:“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 (《约伯记》40∶8)上帝完全没有正面解答约伯对神义论的困惑——义人为何无辜受苦,恶人为何不受惩戒——只是两番讲论自己创造的奇妙可畏,而约伯却在上帝的质问和讲论中幡然醒悟,“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约伯记》42∶6)。
约伯有何可责备或自责的呢?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约伯记》1∶1)。从此世的正义角度,他对上帝和他人不仅没有任何亏欠,还付出很多。如果说他坚持自己是无辜受苦,那也是事实。然而这似乎却是上帝要责备他的地方。列维纳斯说,当上帝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约伯记》38:4)时,这不是责备受造物没有尊敬自己的造物主,也不是想用某种经济学原则的神义论说服约伯跳出自己有限的局部,以超我的智慧心胸来认识全局的和谐,而是在提醒约伯:他的自我在宇宙秩序中,不是第一位的。(32)Le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p.205.如果说从上帝的公义看来约伯还有什么可责备之处,那就是他在前面的申诉中一直自发性地活在世界的规则中:将我当作一切的中心,仿佛我参与了创世并拥有掌控世界的自由,仿佛我就是衡量公义与否的基点。列维纳斯说,这是一种“哲学的自大,唯心主义者的自大”。(33)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1974 ; rééd. Biblio Essais, 1990, p.194.正是这种自大使得此世的公义、哲学和唯心主义者的公义始终缺乏一个面向他者的维度,始终存在一种“失职(carence)”。(34)Le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p.205.也就是说,始终无法从创世的角度理解我与他人的关系:作为主体,我不是在先的,我是受造的,因此我的自由是有限和被赋予的;而且这种“在后”与“延迟”、这种受限与被赋予还带着要求,要求我先于他人分担上帝的重担。(35)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194.
上帝甚至还要求约伯在三个朋友为自己的恶行献上赎罪祭后,去为他们祷告,请求饶恕。而这三个朋友曾在他最艰难痛苦时不惜中伤他来博取自己的安宁。但约伯照着上帝的话做了。虽然约伯对神义论的质疑最后也没得到任何解答,但正如学者沙利耶(Chalier)所指出的,约伯最终的满足不在于这一神圣秩序——“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约伯记》42∶8)——是否经过他深思熟虑后的认同,而在于经文最后呈现的那种对至高者和无限者的遵从,在于那种说“我在此”的谦卑和那种甚至能为自己的迫害者祷告的责任心。(36)Catherine Chalier, La Persévérance du mal, p.149.
在列维纳斯看来,《约伯记》很早就向人们启示这一犹太传统对神义论的批评与对何为义人、何为被拣选的理解。义人不是指没有过错和弱点的人,也不是指那些貌似敬虔、信心无敌的人,而是指那些责任感远超过其潜在过错、将责任置于个人自由之上的人。义人并不自我感觉良好,相反,他们是那些总自觉有罪责、歉疚,没能对世界的苦难负起足够责任的人。这种责任有如一种越偿付越多的“债务”。这种“正义”有种奇怪的模态:越是正义者就越觉不够正义,越是正义者便越觉有罪,以致成为世界的“人质”。这便是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中的著名传说TsadikNistar的内涵。TsadikNistar是指,世界奠基于36个隐匿的义人,而这36个义人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就是义人和世界的支柱。
列维纳斯在我们这个世俗主义时代倡导没有神义论的超越性、责任先于自由的主体性,以及以“踪迹”——他人的面容——这一“无声的书写”(37)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284.作为其存在于世界之方式的上帝观。在他那里,超越性问题、主体性问题和上帝这三者是一体的。(38)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33.它们不提供有关恶是什么的解答,却从根本上回应和承负恶的存在。它们是现代人责任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