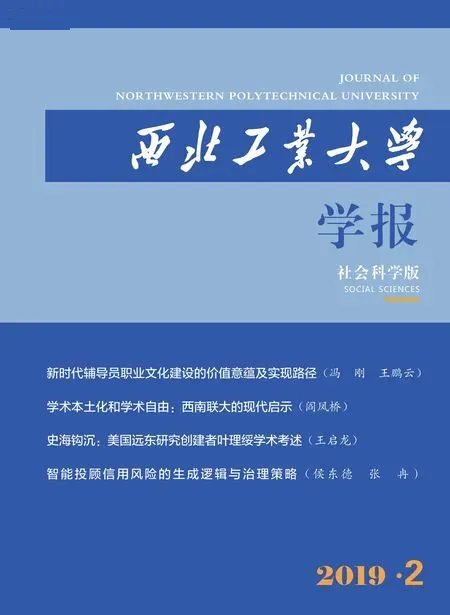史海钩沉:美国远东研究创建者叶理绥学术考述
所谓“东方学”或“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以来欧美国家学者(以及外交官)对作为“他者”的非西方国家,亦即东方国家的人民、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的称谓。在世界东方学版图中,俄罗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历史地缘的特殊性,俄罗斯与传统欧洲在学术文化上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俄罗斯人文学术传统与欧洲一脉相承,其东方学秉承的实际上就是欧洲传统。从18世纪初开始,直到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俄罗斯东方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紧密相连,①曾经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东方学家。
但是,毋庸讳言,1917年苏维埃革命之后,时代裂变的社会阵痛,加上新政权某些政策的偏颇,使得那个特殊时期一批重要的东方学家离开祖国,远赴异国他乡。这段本来很是不幸的历史,客观上却为东方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中不乏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学者,其中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有两位:一位是长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对中国近现代人文学术颇具影响的钢和泰;另一位是被誉为“美国远东研究之父”②的叶理绥。前者我们已经有所研究③;后者是哈佛燕京学社首任主任,也是任期最长的主任,其名号在人文学术界广为人知,但对其生平学术依然缺乏较为系统的了解。本文旨在借鉴学术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叶理绥的生平与学术做一初步的介绍,以抛砖引玉。
一、叶理绥生平述略
(一)青少年时期(1889—1907)
1889年1月13日,圣彼得堡一位富商家庭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他就是本文的主角叶理绥。叶理绥是其中文名字,其本名俄文为谢尔盖·叶里西耶夫,带有法文特色的英文名即Serge Elisséeff。叶理绥后来留学日本,最终成为著名日本学家,也有个日语名字英利世夫。本文均用其中文名字表述。叶理绥的祖父是这个家族产业的创建者,在食品行业这个家族颇负盛名。这个家族信仰东正教。他后来撰写与东正教相关的文章或许与此有一定关系。④
叶理绥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语言培训。除母语俄语外,他幼小时也接受过法语的熏陶,因为“他的父母在餐桌上讲法语,以防止男管家和仆人收集有关主人及其家庭的流言蜚语”。⑤从6岁(1895)起,他跟母亲的秘书,一位出生于德国的一位年轻女子学习德语。
翌年(1896),家里请来一位老先生(Monsieur Doyen)给孩子们当家庭教师(讲法语)。同年秋天,叶理绥开始上小学,那是穆勒(Fräulein Müller)家三姐妹开办的学校,有些课程用德语讲授。
叶理绥很小的时候,德语启蒙老师就爱带他去参观圣彼得堡的博物馆和艺术展览,因此他从小就对艺术颇有兴趣。8岁(1897)时,他主动要求开始学习水彩画和铅笔画。从少年时期开始的艺术教育,为他后来的东方艺术研究打下了最本源的基础。
1899年,叶理绥10岁,开始在凯瑟琳大帝时期建立的拉林斯基学堂上学,这是以拉丁语和希腊语训练为主的完全中学(gymnasium)。
1900年,叶理绥开始学习油画。这年夏天,他居住在巴黎附近的纳伊(Neuilly)家宅,开始接受英语正字法和发音训练。虽然他很早就已经掌握了包括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在内的欧洲主要语言,但对少年叶理绥而言,英语却是最困难的。在他十几岁之前,他就已经掌握了欧洲的主要语言,包括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
1904年,叶理绥15岁。这一年对少年叶理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至巨。首先,俄日战争的爆发吸引了他对远东和左翼政治理论的关注。他订了英国的《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并阅读其中的反俄文章。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对旧俄帝国政府深感不满。与此同时,他开始阅读俄译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并意识到他的老师们大多同情左派,甚至他自己的父母也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视为潜在的弑君者,这让他甚感欣慰。
同年夏天,一位业余爱好绘画的年轻化学教师来到他家的乡间庄园做客,此人使叶理绥放弃了对艺术的“学术”态度,而对法国印象派画家产生了兴趣。在随后的数月里,在一位新艺术老师——马奈(Manet)崇拜者的指导下,他非常认真地对自己的绘画技巧进行了彻底的修正。
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是日、俄帝国列强之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控制权,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的战败导致1905年革命爆发,动摇了沙皇统治,继而推动了一定的政治改革。这些事件强化了叶理绥对左派的同情。他越来越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美学和宗教基础。他对绘画越发着迷,开始希望自己可以摆脱资产阶级背景,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然而,这个梦想被他的俄罗斯文学老师打破了,后者得知他想去巴黎大学学习油画时告诫他说,以他的资产阶级背景和经济保障,他永远不会知道任何创造性艺术所需要的痛苦。老师建议他成为一名人文学者,因为他的艺术敏感性和广泛的语言知识特别适合这样发展。还说由于他对中国和日本的艺术感兴趣,他最好专攻远东研究,为此,他应该请教俄罗斯东方学元老谢尔盖·奥登堡(Serge Oldenburg)教授。两周后,叶理绥应约拜见了奥登堡,当他表示要去牛津大学学习中文时,奥登堡建议他最好是从事日本研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汉学家已然不少,而日本研究者却很少。这些建议得到了叶理绥及其父母的认可,使日后叶理绥的学术生涯和前途命运受益良多。
1907年5月,18岁的叶理绥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从拉林斯基学堂毕业,并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优秀学生金奖。根据奥登堡的建议,他将先赴柏林大学学习汉语和日语,熟悉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方法和著作;然后再赴日留学。奥登堡建议他去柏林而不是巴黎学习,是因为德国对日本教育的影响强大,在柏林读书的西方学生比其他任何大学的学生更有机会被日本大学录取。于是,在从拉林斯基学堂毕业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奥登堡写的介绍信,动身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
(二)海外求学:从德国到日本(1907—1914)
1907年,叶理绥进入柏林大学后,在萨肖(E.Sachau)⑥指导的东方语言研讨会(the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n Sprachen)上开始了他毕生的东方学求索之路。他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汉语和日语,为留日做准备。既然要去日本,直接学习日语即可,为什么还学习汉语呢?因为中日文化之间特殊的源流关系,任何一位域外日本学专家都必须同时学会汉语,才能真正了解日本文化。
他对柏林大学的日语入门教育并不太满意,因为日语教授赫尔曼·普劳特(H. Plaut)博士从未去过日本,日语外教市川代治(Ichikawa Daiji)说的却是日本西北海岸一带的方言,比如日语的ichigo(草莓)在他的家乡话里却念成Echigo。由此可见奥登堡的判断正确:当时日本研究专家稀缺。汉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叶理绥的汉学老师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叶理绥先在格鲁伯⑦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汉语,后者去世后他继续在弗兰克⑧的指导下阅读《孟子》。当然,他的主攻方向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即日本研究。
他还在鲁道夫·兰格(R. Lange)指导下学习德川(幕府时期)历史。参加当地中亚和远东学者两周一次(周五)的非正式会议。虽然听不太懂,但他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还有机会认识一些日本研究学者。
在柏林,他开始交日本朋友。著名语文学家新村出(Shimamura Izuru)碰巧跟他一起听印欧语方面的课程。有一天他注意到叶理绥随身携带的日文书就跟他聊了起来。另外,叶理绥还认识了其他几位日本教授,其中有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桑木严翼(Kuwaki Gen’yoku)、数学家桑木彧雄(Kuwaki Ayao),以及历史学家原胜郎(Hara Katsurō)。他们都对其赴日留学计划充满热情,同时告诫说作为第一个试图成为日本帝国大学正式学生的西方人,前路无疑困难重重。
在这期间,叶理绥的学习兴趣仍然很广泛。他还修了心理学、哲学、美学和劳工问题的通识课程。通过劳工问题的实地考察,他遇到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A. Bebel,1840—1913)和仅仅十多年后就成为德国总统的艾伯特(F. Ebert,1871—1925)。他还结识了一群来自莫斯科的青年学者,他们激发了他对俄罗斯现代诗歌、韵律问题和文学批评的兴趣,并向他介绍法国学者柏格森(H. Bergson,1859—1941)和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的著作。
1908年夏天,完成了柏林一年的进修之后叶理绥回到圣彼得堡。短暂休整后于8月乘火车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日本。随身带着一封岛村写给东京帝国大学日语教授上田万年的信函,以及奥登堡写给其他日本学者的信函。到了日本,他开始了漫长、艰难而重要的留日生涯。
一到东京,他就去拜见大学的俄文教授八杉贞利(Yasugi Sadatoshi)。八杉给他解释大学的课程结构和考试制度,提醒说因为他是第一个试图申请正式录取帝国大学的外国人,又没完成日本大学入学必备的高等中学(Tōtō gakkō)课程,恐有诸多困难。建议他立刻咨询文学院(时称文科大学Bunka daidaku)坪井马九三(Tsuboi Kumazō)院长。第二天与坪井的见面并不令人鼓舞。坪井本人留学德国,主攻历史,德语很好,对这位外国青年彬彬有礼,同时强调接受一个非高中毕业生、日语和古汉语远不如其他学生的外国人入学非常困难。不过他表示,叶理绥可以用日语提交一份书面申请,在下周的教师会议上讨论。
初生牛犊不怕虎!早有准备的叶理绥要求院长能迅速答复:接受或拒绝,以便他必要时能返回柏林就读秋季学期。他还指出,那些不是完全中学(gymnasium)或公立中学(lycée)毕业生,根本不懂拉丁文或希腊语,对现代欧洲语言也所知甚少的日本学生却被欧洲的顶尖大学录取;但是,如果一个已经在柏林大学修完三学期课程的学生被日本大学拒之门外的话,将会令德国学者吃惊。尽管充满自信,但在离开院长办公室时,叶理绥还是怀疑自己的话是否得体。
随后,他带着岛村的信拜访上田万年⑨教授。上田要热忱一些,叫他别担心坪井的态度,因为做决定的是上田及其日本语言文学的同事们。上田又给叶理绥写了几封推荐信,把他介绍给芳贺矢一⑩教授、藤冈作太郎⑪教授和当时还是年轻教员的保科孝一⑫。还建议他请八杉帮他起草申请。八杉欣然答应,但指出叶理绥需要在申请上盖私章。印章雕刻师帮他把名字译成了“英利世夫”,后来他一直沿用。
在收到申请后,坪井院长通知叶理绥必须找两名担保人,并建议请八杉和俄罗斯大使馆某人担保。八杉没问题,但大使馆的某秘书却因无先例而断然拒绝。叶理绥决定从此尽量避免与俄大使馆打交道。于是上田教授做他的第二担保人。他还请求上田推荐的几位学者和奥登堡介绍认识的高楠顺次郎⑬帮忙。竭尽全力之后他才安顿下来静候佳音。当上田私下告诉他已顺利录取的喜讯时,叶理绥立刻给自己买了一套日本学生装。
同年9月,他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学习有条不紊、刻苦认真。他在这里一呆就是六年,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一年四门课算完整的课程设置。
第一学年(1908—1909)对他而言相对艰难些。他选修了四门课程:上田万年讲授的“《古事记》(Kojiki)的语言及其语法”(巴希尔·张伯伦的英译本发挥了决定性帮助);芳贺矢一讲授的“8世纪到1600年的日本文学史”;藤冈胜二⑭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以及俄籍德国人科贝尔⑮用英文讲的“西方语文学导论”。尽管他在日语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但在自身努力和老师的理解和帮助下,他都顺利通过了这个非常严格的课程计划。此外,他还夜以继日地参加各种课外辅导,以弥补他在日本语言和历史文化上的薄弱基础。“这不仅为他的大学学习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而且使他对当时日本人开始发展的通过教育进行民族主义教化的做法有了深邃的了解。”⑯同年,在八杉贞利教授指导下,他撰写了一篇关于现代俄罗斯诗歌的文章,译成日语发表在1909年1月号的《帝国文学》(Teikoku Bungaku)上⑰。
到了第二学年(1909—1910),这位外国青年的艰苦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能够听懂讲课中的全部内容,课程作业他也毫无困难。选修四门正式课程:保科孝一的“日语史研究”;藤冈作太郎的另一门“德川文学”;芳贺矢一的“室町时代文学”选修三分之一;德国著名日本学家卡尔·弗洛伦茨(K. Florenz)的“比较文学”选修四分之一。课外阅读方面,他从初级中学课本转到高中课本,阅读《能》(Nō)、《狂言》(Kyōgen)和《御伽草纸》(Otogi-zōshi)等。他还去听话家(hanashika,即专业的故事讲述者)幽默的寄席(yose)表演,学习模仿他们粗俗的演讲。他还通过参加长呗(nagauta)音乐会,开始艰难地熟悉日本音乐(他的日本老师们也未必能懂)。同时,他开始频繁地光顾歌舞伎(Kabuki)剧院,深入了解舞伎艺术。此后几年,始终如一。于是,他成了许多演员的好朋友,并能成功地模仿了歌舞伎的措辞和舞蹈风格。大学里的日本同学开始更平等地接受他。时为研究生的小宫丰隆⑱把他介绍给了著名作家夏目漱石⑲,后者邀请他们正式出席自己例行的周四会议。
这年叶理绥曾与日本古代历史文献的重要翻译家、《日本文学史》的作者弗洛伦茨畅谈过一次。后者对未来的日本学家叶理绥很感兴趣,但不看好他能精通日语,无论他学了多长时间。劝他在一些狭窄的领域成为专家,比如《万叶集》(Man'yōshü)研究专家,并特别建议可以在某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青年学者帮助下将《万叶集》译成一部厚重的俄文译著。年轻人婉拒建议,继续他的学习计划,他要像日本人一样懂日本。这说明他试图打破传统的东方研究。
大学三年级(1910—1911),叶理绥已经完全被同学们所接受,他们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并经常来他的家里看望他。他的大学同学中有1948年当选日本首相的芦田均⑳。本学年的四门课程是:上田万年的“《万叶集》的语法和句法”,芳贺矢一的“日本平安时代文学”(Heian literature),黑木安雄㉑的“汉文(Kambun)文献阅读”,以及一门“阿伊努语”(原住民语言)。他不时会在周日上午去拜访黑木安雄,通过后者的聚会活动,他逐渐认识了后于1931年担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㉒黑木还使叶理绥对日语草书(sōsho) 产生了兴趣。按照惯例,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在三年级要完成学业,写一篇论文,并参加最后的口试。然而,在上田(万年)教授允许下,叶理绥决定将口试和论文推迟到第四年。
第四学年(1911—1912),他完整选修了下列课程:藤村作(Fujimura Saku)讲授的“德川时代小说”;芳贺矢一的“镰仓时期文学”;上田万年的“室町时代的日本语言”,以及金泽庄三郎(Kanazawa Shōsaburō)的“朝鲜语”等课程。此外,他还圆满完成了从三年级推迟到四年级的研究论文《芭蕉研究之一方面》,研究的是17世纪著名诗人芭蕉(Baishō)的俳句(Haiku)。
1912年6月,叶理绥参加了最后的口试,非常严格,内容繁多,日本语言、文学、文献目录,还有日语方言、语音问题、比较文学和历史等内容,分为四个单元,各一个小时,两位教授主考。据说这一“考试程序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㉓。教授们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给了82分(相当于A-),他以接近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彩排中,他和系里的其他三个A等学生站在第一排。这碰巧是明治天皇最后一次出席官方活动,几周后他去世了。然而,作为外国人,叶理绥还是受到歧视的。在正式的毕业生名单里他的名字被印在最底部,与其他人相隔很远。似有低人一等的意味。后来他要求加入文学士校友会活动,虽无法拒绝他,但每次都是活动结束后次日他才收到邀请。当他问个究竟时,被坦率告知,外国人出席会妨碍讨论。因此,当他拿到文凭时,他仔细辨认其形制是否和其他人一致。由此可见,当时崇洋的日本其实保守而不自信。
但重要的是,1912年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历史上首位取得大学学位的外国学生,也是首位外国研究生。㉔
这年夏天,叶理绥在福井县一海滨小镇度过,并在其朋友兼导师东新(Higashi Arata)先生指导下研究日本文学和《史记》(Shih-chi)。到了秋天,他以优异的成绩轻松获得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资格。进入了为期两年(1912—1914)的研究生学业阶段:他选修了瀧精一(Taki Seiichi)主讲的四门有关中国和日本绘画的课程和研讨会,三上参次(Mikami Sanji)主讲的两门日本历史历史课程,以及藤村(Fujimura)主持的两个有关日本诗人井原西鹤(Ihara Saikaku,1642—1693)和德川戏剧的研讨会。同时,他继续扩大社交和学术圈,广泛深入日本生活,尽情浸润于日本文化之中。㉕开始撰写和发表日本学论著㉖。
(三)回到俄罗斯:成家易而立业难(1914—1920)
1914年,已经在日本学成的叶理绥该回俄罗斯了。一年多前在东京帝国大学任客座教授的德国经济学家海因里希·瓦蒂格(H. E. Waentig,1870—1943)告诫他别在日本呆得太久。原因有二:一是趁俄罗斯日本研究人才缺乏之际赶紧回国谋职;二是当时西方学者对欧洲之外的学术研究(至少在技术层面)是嗤之以鼻的。当瓦蒂格阅读了他1913年在《德国自然与大众杂志》发表的关于芭蕉的论文后,就指出文章条理不清,缺乏问题意识。他觉得叶理绥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远远超过了他组织材料以满足西方学术要求的能力,因此建议他继续在西方而不是日本学习。可见,当时日本大学教育依然属于东方传统模式,受中国文化影响更深,而受西方学理浸润不够,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形颇为相似。
1914年夏,叶理绥回到俄罗斯,在友人帮助下跟教育部副部长见了一面。后者建议他参加圣彼得堡大学博士学位考试,以便有资格担任大学的讲师教职,并提出帮助解决政府接受叶理绥在东京获得的相当于欧洲公认大学学位的学位的主要技术困难——因为当时的俄罗斯遵循的欧洲教育传统,对东方国家——哪怕是早就竭力拥抱西方文明的日本的大学文凭一般是不承认的。沙皇也同意破例处理他的这种例外情况。加上东方语言学院院长尼古拉·马尔(N. Marr)早就从奥登堡和伊万诺夫那里听说过叶理绥,因此,全体教员投票一致同意他为博士候选人,决定他可参加第二年的相关考试。
1914年对叶理绥而言还有一件大事要记载:他与维拉·艾琪(Vera Eiche)在11月22日结婚,开启了他们一生美满而成功的婚姻和家庭生活。㉗
为了准备考试,叶理绥广泛阅读,并得到俄罗斯学者伊万诺夫(Ivanov)、阿列克谢耶夫(B.Alexeev)等教授的大力支持。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圣彼得堡的学者们提出了大量新的、和日本老师从未讨论过的尖锐问题。他还跟伊万诺夫和一名中国教师学汉语。
1915年春,叶理绥参加了日本语言、文学和历史的口试;同年秋天参加相应的汉学口试。然后是一次三小时的笔试,由于笔试的房间是关着的,因此称为“clausura”,笔试之前二十四小时要就一个既定题目讲一堂公开课。根据伊万诺夫的建议,他在3月选择以《传统的日本历史学家新井白石》为题做了演讲。1915年4月的日语口语考试以及汉语考试他都顺利过关。㉘两天后,他轻松通过笔试,并于12月初向约60位听众发表了《清少纳言和她的枕头书》的公开演讲,成功通过了测试。
1916年1月初,叶理绥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大学日语讲师,开始教学时有10位学生听课。因为日语人才奇缺,他可谓炙手可热:被要求担任外交部的正式口译,于是有资格获得外交签证;被选为商会远东分会副主席;加入了考古学会和东方研究学会,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日本考古学会会长。同时,他出任一家私立艺术史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开设中国绘画史课,这可能是西方第一次以汉文和日文材料为主要基础开设的中国艺术课程。
当然,这段时间叶理绥最关心的还是撰写关于芭蕉研究的博士论文,为此他在1916年和1917年的夏天都到日本度过㉙,目的就是为了查找需要的研究资料,正如钢和泰当年到北京为了查找阿育王研究资料一样。事实上,1916年初夏的5月,叶理绥和钢和泰都作为中亚及远东科学考察委员会成员,奉命随同科学考察团到远东考察。考察团最先到达日本东京,后来才到中国北京。㉚可以肯定,1916年夏到日本后,叶理绥没有继续前往中国,而是当年回到了俄罗斯。1917年夏,他再度回到日本。而他的大学同事钢和泰(1909年受聘为梵文助理教授)则在日本停留了一段时间(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随后于1917年来到中国,此后再也没回去。㉛
对他俩而言,1917都是刻骨铭心的年份。滞留北京的钢和泰男爵因为十月革命而失去爱沙尼亚领地的财产,再也没能回去而流落异乡,但这也成就了北京大学的首位梵文教授和哈佛大学的中亚语文学教授。对于叶理绥来说,看似荣归故里,实则厄运连连。
1917年他从日本回国时,考虑到局势混乱(当时正值十月革命前夕),他将快完成的博士论文手稿托付给了俄罗斯外交使团邮差。不幸的是,布尔什维克在邮袋到达前就已经接管了政权,他们烧毁了论文手稿以及邮袋里的所有非官方文件。他的私人财产被剥夺,他在旧政府外交部的兼职被罢免。由于讲师的工资难以养家,他只好在亚洲博物馆(今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可以挣个小钱以补家用,另一方面在那危险的岁月,这里是东方学者的避难所。他尽其所能地继续他的学业,继续听课,偶尔也去讲课。
革命后的新政府也需要人才。他被选为新改组的考古委员会远东部秘书,当该委员会成为物质文化史研究院(the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时,他成为最年轻的正式院士。高尔基组织了一个项目,旨在为年轻作家和学者提供经济援助。这个项目资助叶理绥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文学的短文。
1920年春,东方语言学院和文献学与历史学学院合并,叶理绥被选为新机构秘书,被迫投身于大学的自身保护中。当然,革命确实给他带来一点好处:由于讲师职级的废除,他被转为助理教授职位。然而,叶理绥这样的学者在彼得格勒的生活越发困难:与他有同样社会背景者经常遭到突然搜查和逮捕,他也难以承受教学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压力。这段历史,我们今天可以平和而冷静地谈及和面对,但对叶理绥而言,其艰难和苦痛是难以言表的。
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1918—1920)正值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大饥荒前夜,局势混乱、民不聊生是不争的事实。㉜在1918和1919年的冬天,叶理绥全家从未远离饥饿,一些近亲竟因饥寒而死。为了熬过严冬,他们只好把公寓里不太重要的家具和书房里的一些书籍献给了火炉——结果证明一部过时的大型百科全书这时却非常“有价值”……
迫于无奈,他们决定非法逃离——没有护照或任何合法许可。1920年夏末,在与芬兰湾一带活动的走私犯取得联系后,举家逃到芬兰。虽然获得了自由,但生计依然困难。一个月后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叶理绥在大学里用德语发表有关远东艺术的演讲。在瑞典的三个月里,他还忙于写一本日本童话书,但不幸的是,书还没有写成出版商就破产了。否极泰来,这是自然与人生规律。叶理绥的灰暗人生很快就会画上句号。
(四)游走于法兰西与美利坚的完美人生(1921—1975)
1. 于法兰西获得重生
1921年1月,叶理绥举家搬到巴黎,加入了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行列。从此,叶理绥总算慢慢拉开了未来的人生序幕。
即便在法国,当时像他这样的日本通也是寥寥无几。他往日的艰辛付出终于开始得到回馈:他很快就在著名的吉美博物馆找到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并被日本驻法大使馆聘为翻译。
由于他在给德国—比利时和德国—丹麦边界划界委员会日本首席代表前田侯爵担任秘书时能在法、英、德、日等多种语言间来回翻译,显示出卓越的语言才华,日本大使馆也经常请他协助组织各种活动,推进日法文化交流等。而他所接到的最刺激的任务,是在朋友克劳德·麦特尔(Claude Maitre)帮助下,于1923年12月创办了《日本与远东》(Japon et Extrême-Orient)文化月刊。他每期都要在上面发文章,或是现代日本短篇小说法语译文,或是关于日本文化的小论文,或是某部日文著作的书评,深受法国认人士欢迎。可惜由于麦特尔在1924年秋过早去世,这本杂志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停刊。㉝
但是,这并未对叶理绥产生影响。他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如井喷之势相继发表。随后的几年依然是其学术的高产期。他继续用法文撰述或翻译了大量文章,发表在《亚洲艺术评论》(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上。据统计,从1925年到1934年间,仅在此刊他就发表了30篇文章㉞。主要介绍日本文化、研究日本学术,同时也旁及汉学、藏学、蒙古学以及韩国研究等,领域涵盖艺术、考古、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毫无疑问,他应该是法国(或者说是西方)第一位全面、系统推介日本文化、研究日本学术以及其他东方文化,推动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学者。
在学术上的卓越表现,不但使叶理绥终于可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同时也为他赢得了荣誉。1931年,瑞典国王曾因他出色完成歌舞伎(Kabuki)表演的编目而授予他北极星十字勋章。重要的是,他开始重建原本支离破碎的学术生涯。他充分利用当时西方汉学之都巴黎的有利条件,去听了伯希和、马伯乐、梅耶等人的课并与伯希和成为相知相惜的师友。这为他后来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主任埋下伏笔。
同时,他在巴黎也开始有机会重新从事教学工作:1922年,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在巴黎大学讲授德川文学史课程,在东方语言学院讲日本文法课程,一直到1930年。1928—1929年间,他在卢浮宫讲授日本艺术史。1930年,他被任命为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宗教史分部的会议主任(Maitre de Conférences),讲授日本神道教(Shintoism),并带着他的学生一起读汉文的《妙法莲华经》。两年后(1932),他成为该学院的主任,获得了完全的专业地位。
1931年,他和妻子维拉成为法国公民。他们一生怀着感恩珍视这个身份,因为,是法国这个国度使他们一家获得重生、获得尊重、获得人生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从1934年叶理绥任职哈佛到他1957年退休,他们在美居住了23年也未放弃法国公民身份,他们认为自己对法国的感情比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还要深厚。
2. 转战美利坚
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宣告成立。该学社是为资助亚洲的高等教育而成立的,获得查尔斯霍尔遗产的资助。坊间流传甚广的是,成立之初邀请伯希和出任首任主任。其实未成立之前中美多方机构、众多人士的反复磋商和数年筹备中,大家最先属意的人选并非伯希和,而是同样大名鼎鼎的胡适。㉟学社成立后正式受邀应该是伯希和,但他婉拒邀请,转而推荐他的学生叶理绥接替他任职。当然,哈佛不会贸然听从伯希和的建议。因此,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初大约四五年时间(1928—1933)是由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乔治·蔡斯(George Chase)代行主任职责。蔡斯在学社成立之初,在全球网罗人才,参与学社的教学科研工作。钢和泰就是在这个时候应邀去的哈佛大学,在那里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之后,于1929年正式受聘为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㊱随着哈佛燕京学社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比如在燕京大学旨在提升研究生文言文水平和研究能力、协助中国本科生教学工作等项目的启动——为了帮助在中国的这些活动建立高的学术标准,学社的理事会希望哈佛大学建立一个小型的远东语言系。这时他们需要一位杰出的西方学者在哈佛领导这项工作,并就理事会与中国高等院校之间的关系给予专业性指导。伯希和当初推荐的叶理绥哈佛大学虽然没有立即认可,但哈佛也并没有完全将他忘记,既然需要人才,哈佛决定试试看。于是叶理绥受邀于1932—1933学年到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
所谓访问教授,实际上相当于试用和考察。长期留学日本且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的叶理绥当然不负众望。在访问期间,除了讲授本科生课程外,他还在哈佛洛厄尔学院(the Lowell Institute)就日本艺术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8次系列讲座。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专业才华和管理能力。哈佛燕京学社应该很满意,否则不会在一年结束后的1933年,派他到中国参访与学社有关的几所大学。在返回巴黎之前,他再度访问了日本。此时距他离开日本已有17年之久。
1934年,叶理绥教授受聘为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和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教授,开始了他“日本学之父”㊲的铸就历史,直到他1957年正式退休。随后他回到法国安度晚年,直到1975年去世。
二、叶理绥的学术贡献
坦率地说,自从叶理绥任职哈佛以后,虽然也发表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㊳,但这不是他的最重要“作品”。他一生中“撰写”的最重要“作品”应该是通过日常大量的教学工作和繁重的行政工作,在美国按照欧洲汉学传统建立了哈佛的远东研究中心,并通过这样的中心去影响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汉学研究。他不但高标准地奠定了美国远东研究基础和学科体系,而且还凭借其执掌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东西方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20世纪上半叶,纵然美国的政治经济强国地位已然确立,但其文化教育、学术科技还远没有达到世界之巅。正如上文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叶理绥与钢和泰的往来书信中,当他们谈到教育问题时,就曾流露过对美国教育的不屑,对欧洲教育的赞美,称他们自己的子女都选择在欧洲接受教育,而不是美国。㊴事实上,就东方研究而言,当时美国大学在欧洲学者眼里尚未入流,而在美国大学执教的那些来自欧洲或者与欧洲有渊源关系的学者对此也有冷静而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从未因为美国的国家地位而产生学术自恋,而是积极进取,虚心学习,努力借助叶理绥这种通晓西方学术体制且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学者参与工作,结果很快迎头赶上。尤其在二战以后,美国后来居上,超越传统欧洲独领风骚至今。
叶理绥之所以能成为“美国远东研究之父”,成就非凡的学术事业,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点:
首先,他接受过严格的西方传统人文学术训练,并在长期的东方文化熏陶中深谙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和异同。从上述叶理绥生平中可知,叶理绥从小聪慧过人,且有抱负。他接受过人文学术诸方面的训练,比如语言、文学、历史、宗教、艺术、音乐、心理学、哲学、美学和劳工问题等,尤其是语言。他不但从小就学习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主要欧洲语言,长大后还学习了汉语、日语等东方语言,阅读过《孟子》、《史记》等经典。而更重要的是,他跟随过众多名师,且能择善入流,听从老师的建议,做出明智的选择。当时的潮流是东方学者大多选择中国研究,他反其道而行之,下定决心投身日本研究,成为西方到日本大学留学并获得学位的西方人。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上文已述,他以非凡的毅力、艰苦的学习使自己以与日本同学同样优秀的成绩毕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满足于课堂学习或满足于拿学分,他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学习、体验和熏陶之中,竭尽全力把自己变成地道的日本人。
因为没有先例,他到日本后的入学过程波折颇多。但当上田教授私下告诉他已经录取时,他立刻给自己买了一套日本学生校服。刚到日本,他就坚持租住日本人的房屋,与日本人交朋友。后来独自租用房子时,他甚至自觉地按照德川家族的封建制度来安排他的佣人。他也很快就从学生制服换成和服(kimono)和长袍(hakama),也就是正式的双裙,俨然一副日本传统文人雅士的装扮。
为了深刻了解并融入日本社会,他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为了与青年作家们保持密切联系,年轻的叶理绥还每月在家里举办茶话会,讨论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文学。在参与者中,值得注意的人物有永井荷风、森田草平、久保万田太郎、后藤末雄和小宫丰隆。据说警方曾指控他组织了一次“左翼”会议,会上日本政府甚至天皇都受到了批评云云。
为了亲自领略东方的人文地理风光,他常常利用假期在日本帝国各地旅行。每年春天,他都会去京都地区,在那里他受到了岛村和他在柏林认识的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热烈欢迎。有一个寒假,他前往当时日本占领的台湾,与一位英国领事一起攀登阿里山。他的第一个暑假是在(日本)北方度过的,旅游了北海道和南库页岛;第二个暑假,他去了日本占领的韩国,并在返回东京途中旅游了九州。㊵
可见,叶理绥试图从外到内、从表到里,全方位把自己训练成日本人。
其次,时事造英雄。特定的历史时空,为叶理绥提供了在变故或变化中不断提升自己,在机遇与挑战中投身于东方学研究和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契机。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动荡局势和饥寒交迫,使得他举家破釜沉舟,逃离俄罗斯,几经辗转,来到当时的东方学之都巴黎,自此他才慢慢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世界格局的变迁,美国世界地位的崛起需要相应强大的学术文化和科技实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东方语言研究兴起,美国东方学领域也急需有根本性提升和实质性进步。于是,1934年,叶理绥受聘来到美国东方研究的最高学术殿堂,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专职主任和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教授。
从1934年他上任起到他1957年正式退休,长达23年的时间里,叶理绥全身心投入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哈佛大学远东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或者说美国东方学的创立和发展上,全身心致力于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叶理绥学术行政繁重,社会活动频繁,他在美国这二十多年所撰写的学术论著并不算多,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国际东方学领域的崇高地位。他伟大的学术成就难以详述,这里仅是略举数端,述其大要:
第一,他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作为教师,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学术演讲和语言教学中,不仅以其学识启迪学生,治学热情鼓舞他们,而且还用其智慧使学生们欢欣鼓舞。他既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专业的日本研究专家,又是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兼远东语言系主任,因此,他不但身体力行地承担了远东系大量的教学任务,还要负责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开设初、中、高级日语课程的教授,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大学编订了最为完备、科学的初、中、高级各类日语教材,建立了日语专业的培养体系。他不但亲自上语言课程,还主持初级到高级的研讨会,并毫不吝惜时间地开设个别阅读课程;他隔年讲授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学;有一段时间,他开设了一门阅读《史记》的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担任华盛顿战略服务办公室的顾问,并组织和参加了哈佛大学为军队官兵组织的日语特殊项目,同样,也为民政事务培训学校举办了大规模的军官特殊训项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叶理绥可谓桃李满天下,在美国各界,以至于在世界各地,都有他培养的学生。
第二,他以自己娴熟的欧洲标准,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学术标准建构了美国远东研究的学科体系。为了在美国建立远东研究,叶理绥教授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来培养潜在的学者。根据自身经验,他希望看到学生在西方和亚洲的远东研究中都获得彻底的基础知识。他在1933年就开始将相关奖学金计划付诸实施,研究生被送到巴黎继续学习了两年,接着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习了三年。叶理绥在二十多年里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人通过东西方的生活、学习和文化熏陶,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及研究,通过具体研究项目的培训,再加上叶理绥的启发教学,不仅占据了哈佛新设置的远东研究职位,还占据了其他主要研究中心的大多数职位。
第三,他努力推动美国东方研究的蓬勃发展。为了促进美国的东方学研究,他凭借掌握的学术平台和资源,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和出版计划,目的是发展哈佛远东研究中心,并帮助与学社有联系的中国大学建立学术标准。多年来,在古汉语词典编纂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活动,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他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丛书》(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在他的领导下,学社出版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学术著作。他最雄心勃勃的出版事业是1936年创办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如今已经蜚声中外。迄今(2019)已经出版到了第83卷。此外,他推动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的发展。1932年他第一次来到哈佛时,藏书只有7.5万册,到他退休前的1956年底已达30.6万册。今天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之一。
第四,他推动了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他不但通过派遣学生到欧洲和亚洲留学的方式加强东西方的交流,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他必须身体力行,奔走于中美之间,协调学社和与之有关系的数所大学的关系,解决出现的问题,组织相关的活动,以促进彼此的交流和发展。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古老中国局势动荡,工作开展难度之大、问题之多、事情之繁,在此就难以言尽了。
尽管叶理绥要履行和完成上述种种职责和任务,他依然忙里偷闲,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一些重要著述。㊶由于卓越的学术贡献和广泛的学术影响,他先后荣获了法国远东学院的荣誉院士(1940)、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院士(1955)、荣誉军团骑士(1946)等头衔。鉴于他在美国远东研究方面的杰出地位,他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1954—1955年主席。在他1957年正式退休,准备回法国之际,当时哈佛大学校长内森·普西(Nathan M. Pusey)在其贺信中对他赞誉有加,称“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在所有的学术领域获得并保持卓越的地位。哈佛在本世纪很幸运地在一些方面做得很好。在你自己足智多谋的领导下,在你自己高标准的学术激励下,在远东研究领域中取得的光荣历史和丰硕成果,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超越它。”㊷
总之,无论作为西方第一位专业的“日本学家”(Japanologist)还是 “美国远东研究之父”,叶理绥都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学术贡献不在于有多少论著,而在于他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创了美国远东研究之先河,并推动了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他不但开创了西方的日本学研究,而且改写了20世纪东方学研究的世界版图。在他之后,东方研究不再只是欧洲的学术制高点,美国也逐渐成为东方研究的重要国度。
注释
① SteffiMarung,Katja Naumann (2014): “The Making of Oriental Studies: Its Transational and Transatlantic Past”,in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ume III: The Modern Humanities,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4.
② Edwin O. Reischauer (1957): “Serge Elisseeff”,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No.1/2.
③ 参阅Wang Qilong &Deng Xiaoyong(2014)The Academic Knight between East and West,Cengage Learning Asia,2014;王启龙、邓小咏:《钢和泰学术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④ Serge Elisseeff (1956):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Russian Merchant Class: Some Personal Recollections”,in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49,No.4 (Oct.,1956): 185-205.
⑤ Edwin O. Reischauer (1957): “Serge Elisseeff”,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No.1/2.
⑥ 关于爱德华·萨肖(Eduard Sachau,1845—1930),请参阅A. F. (1931) Eduard Sachau.Journal of the Royal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 1(Jan.,1931): 242-243.
⑦ 德国早期著名汉学家威廉·格鲁伯(Wilhelm Grube,1855—1908)的汉语名字,又译顾路柏、顾威廉。甲柏连孜(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教授在莱比锡大学的高足。1892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讲授汉语和满语。他是德国女真文字研究开创者。关于此人,参阅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⑧ 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O. Franke,1863—1946)汉文名字,又译傅兰克、福兰阁。在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并于188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柏林大学学习两年法律,兼修汉语。1888年起多次来华任德使馆翻译。1901—1907年转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1907年起先后任汉堡大学、柏林大学汉文教授。著术甚丰,达300多篇/部。主要有《中国历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5 vols.,1930-1952)等。
⑨ 上田万年(Ueda Mannen,1876—1937),著名汉学家,著有《汉语大字典》哈佛大学出版社,1945年。
⑩ 芳贺矢一(Haga Yaichi,1867—1927),著名语文学家,著有《国文学史十讲》《日本文献学》等。
⑪ 藤冈作太郎(Fujioka Sakutarō,1870—1910),日本国文学者。他确立了以实证和训诂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方法。
⑫ 保科孝一(Hoshina Kōichi ,1872—1955),著名语言学家。1902年任东京大学助教。1927年晋为教授退职。1930年任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
⑬ 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ō,1866—1945),著名佛学家。先后留学于牛津、柏林、基尔、莱比锡等大学。1897年任东京大学讲师。1899年升任教授。其间,受到上田万年的提拔。1901年,任东京大学首任梵文讲座教授。参与编辑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经》(Taisho Tripitaka)。著有8卷本《南传大藏经解题》(伦敦:1975)等。
⑭ 藤冈胜二(Fujioka Katsuji,1872—1935),著名语言学家。著有《英日大词典》(Tokyo: 1900/1932)等,最早将《满文老档》译为日文。还译介过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等。
⑮ 科贝尔(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俄籍德国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
⑯ 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2页。
⑰ 即《现代俄罗斯诗歌》,载《帝国文学》(Teikoku Bungaku),1909年1月。
⑱ 小宫丰隆(Komiya Toyotaka,1884—1966),夏目漱石门下“四天王”之一,岩波书店版《夏目漱石全集》主编。著有《夏目漱石传》《漱石的文学世界》等,被评论家誉为“漱石研究第一人”。
⑲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6),日本著名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1984年,他的头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纸币上。代表作有《我是猫》《心》等。
⑳ 芦田均(Ashida Hitoshi,1887—1959),日本外交家,政治家。1948年出任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日本首相。
㉑ 黑木安雄(Kuroki Yasuo,1866—1923),日本明治时代书法家、汉学家。
㉒ 犬养毅(Inukai Ki,1855—1932),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人物,第29任首相(1931.12—1932.5)。
㉓ 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5页。
㉔ G. W. B.(1975) Serge Elisséeff: 1889-1975.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5(1975),p.13.
㉕ 研究生期间除了三位日本导师之外,还有一位满族绅士给他讲授中国古典文献、普通话发音和声调结构。与歌舞伎(Kabuki)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学习舞蹈课程,并开始书法和陶瓷作品的收藏。另外,在他还采访了德川家族的最后一位将军(Shōgun)庆喜(Keiki)老人,并用一个春假研究佛教艺术珍品。参阅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6页。
㉖ 比如1913年在《德国自然与大众杂志通报》发表了“1913的日本剧院”一文,后来应夏目漱石之约,在《朝日新闻》文艺栏目发表了几篇有关最近俄罗斯小说的文章。
㉗ 叶理绥夫妇婚后有两个儿子,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学者。长子尼基塔(Nikita)专攻阿拉伯史;幼子瓦迪姆(Vadime)专攻中国考古学。
㉘ 据说伊万诺夫建议叶理绥专注于东方主题的西方目录学,因为考官们不熟悉这些他一直在用日文阅读的材料(言下之意容易通过)。东方语言学院的大多数教授都参加他的口试,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8-19页)也有栩栩如生的描述,这里不赘。
㉙ 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9页。
㉚ 参阅王启龙、邓小咏(2009):第20页;Wang Qilong &Deng Xiaoyong(2014):18,23.
㉛ 关于钢和泰生平学术,参阅王启龙、邓小咏(2009);Wang Qilong &Deng Xiaoyong(2014)。
㉜ 关于大饥荒,可参阅Charles M. Edmondson (1977) The Politics of Hunger: The Soviet Response to Famine,1921.Soviet Studies,Vol.29,No.2: 506-518.
㉝ 叶理绥在上面共发表17篇文章,其中译文有10篇,基本上是日本短篇小说(其中9篇后来结集为《日本小说9篇》(Neuf nouvelles japonaises)由巴黎G. Van Oest出版社于1924年出版);书评有4篇;其他文章有3篇。
㉞ 参阅Edwin O. Reischauer (1957)著述目录部分。
㉟ 关于哈佛燕京学社成立过程的具体细节,请参阅Shuhua Fan(2009) To Educate China in the Humanities and Produce China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unding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24.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16,No.4:251-283.
㊱ 关于蔡斯兼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以及钢和泰先受邀后受聘哈佛的故事,请参阅王启龙、邓小咏(2009);Wang Qilong &Deng Xiaoyong(2014)。
㊲ 他的学生赖世和认为,作为“西方的第一位日本学家”,叶理绥日本学之父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在他看来,叶理绥更应该是“美国远东研究之父”。因为他开创了美国远东研究之先河。参阅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3页。
㊳ 比如《Bommōkyō与东大寺大佛》(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1卷第1期)、《东正教和俄国商人阶级:一些个人的回忆》(载《哈佛神学评论》,第49卷第4期)等,都是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对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㊴ 参阅王启龙、邓小咏(2009):第19页;Wang Qilong &Deng Xiaoyong(2014),pp.17,21.
㊵ 参阅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14-15页。
㊶ 比如除上述系列日语教材的编写外,还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撰述了一系列的论文、书评和讣告,出版了非常有用、多次再版的《关于日本的书籍和文章的精选清单》(1940,1954)、《大学生文献选读》(3 vols. 1942,1947)等。
㊷ 参阅Edwin O. Reischauer (1957):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