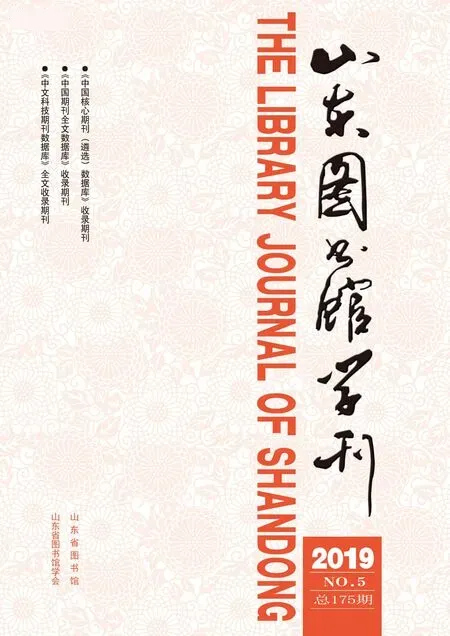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阅读活动浅析
何贤英 白雪梅
(聊城大学图书馆,山东聊城 252059)
随着“她阅读”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女性阅读。而女性阅读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自古以来,女性从未被排除在阅读活动之外。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又是中国历史长河里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关于这个时代的女性阅读,确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阅读的社会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写的这段话如实的描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状况。政权更迭、民族矛盾加剧、经济衰退等,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痛苦。然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性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某种程度的受益者。在这种动乱时代,女性们更容易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通过阅读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1.1 女性阅读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政局的动荡、民族与文化的大整合,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讲究男尊女卑等级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女诫》《列女传》等所阐述的儒家女子言行规则,对女子的束缚作用开始减弱,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晋书·列女传》云:“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2]由此可见,女性只要有才能,是可以得到世人与社会认可的。才华和美重于妇德是这一时期对女子价值的重新定位。[3]东晋“咏絮才”谢道韫,自幼对诗书情有独钟。尝内集,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矣。”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4]这一咏雪诗句不胫而走,在民间广为流传。“咏絮才”也由此而来。对女子才学的记述及赞赏,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对女性阅读行为的肯定与推崇。另外,《世说新语》主要内容记录名士言行与轶事,书中却专辟《贤媛》一门来描述女性,且不再是记述孝顺与贞德的内容,大多是有思想、有个性、有才学有胆略的女子。由此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女性不同与以往朝代的态度及对有学识女子的认可。
1.2 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使得官学发展极不稳定,而私学却逐渐发展壮大。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家庭的女子大多接受的是传统的家庭教育,而一时期兴起的世族门阀的高层教育则是私学发展的重大成就。那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其自身势力和社会地位,对子女的教育都非常重视。正因魏晋南北朝时女子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致使此阶段的才女迭出不穷,光彩照人。如左思之妹左芬自幼酷爱诗歌,其父非但不阻拦,且勉励有嘉。她勤学不倦,才华超群。后被晋武帝纳为嫔妃,作《离思赋》,情辞哀婉,感人肺腑。中国诗歌史上叹为观止的回文诗《璇玑图》的作者苏惠。图中有840字,正、反、横、竖、斜读皆可成诗,显示出超人的才情。武则天对《璇玑图》极为赞赏,说此锦帕“纵横反复,皆成章句”;说她才情之妙,超古过今。[5]
1.3 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儒家奉行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遭到冲击后,魏晋南北朝的女性的家庭地位甚至社会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她们不再像前朝的女性一样,恪守着“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礼教,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曹魏时期,许允娶丑妻阮氏,不满。问:“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6]《世说新语》中第13则,贾充之妻,李丰之女,拒绝回到已娶郭氏的贾充身边。此事中,女子表现出了刚直不阿自尊自立,绝不苟且委曲求全,追求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女性意识。[7]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的觉醒时代,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7]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阅读的内容
2.1 女教典籍类
魏晋南北朝时的女性虽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列女传》《女诫》等儒家女子言行规范,渐渐失去了对女子原来的束缚作用。但也只是相对于前代而言。女性阅读的主流书籍还主要以女教典籍类为主。晋代著名学者曾作《女史箴》一文,主张女子应修行养性,核心内容是柔顺,与班昭《女诫》宣传的宗旨是一样的。张华的观点代表当时士大夫要求女子贞顺的态度。而女子接受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所以类似的女教典籍是必看之书。
2.2 儒家经学类
儒学自不必说,仍是魏晋南北朝时儒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如“贞幼聪敏,有至性。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8]经学也是女子学习的重要内容。给女子传授儒家经书在以前诸代并不多见,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不乏其人。如“和(皇甫和)年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亲授以经书。”[9]西晋宋夫人自幼熟诵儒家经典,具有较扎实的经学功底。婚后生活含辛茹苦,劳累忙碌,也不忘诵习《周官》,增进学业。南朝时吴郡女子韩兰英,十多岁时,便聪敏好学,能文善赋。因经书讲授精当,宋武帝令她担任六宫各员的文化老师。
2.3 诗歌文学类
诗歌文学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阅读的重要内容。有关人士统计,现存的魏晋南北朝女性诗歌约140多首,但实际数量应当多得多。[10]有些诗文有文献著录,尚可查阅,如《隋书·经籍志》藉录该时期有诗传世女诗人11个。还有些只有诗文留世却无文献著录的,或许也有既无文献记载又无诗文留世的已亡佚的一些诗作。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诗歌艺术形式成绩斐然,如苏伯玉之妻所作的杂言诗《盘中诗》,东晋前秦人苏蕙的回文诗《璇玑图》,晋代的民间女子子夜创作的《子夜歌》等。据《隋书·经籍志四》载:两晋妇女有文集者12人,共40卷。这些文集至隋时皆亡佚,但其中不少名篇佳作仍得以保存至今。南朝妇女有文集者计7人共39卷,隋时犹存。[11]当然,这些诗词文的女作者,必然是在大量阅读他人诗词文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
2.4 书法绘画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书家是这一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者陶宗仪通过对相关文献史籍的统计,得出这一时期见诸史料记载的书家总数为660人,而女性书家占了38人之多,仅《玉台书史》一书就收录了26人,占这一时期书家总数的6%。[12]三国吴孙权之妻赵夫人“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以指尖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13]东晋太尉庾亮之妻旬氏“善正、行、隶、篆等书体”[13]。
2.5 老庄之学类
魏晋之际,玄学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玄学清谈主要是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老庄之学产生于魏晋时期的,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之人大都为男性,但也不乏一些具有渊博知识的女性。她们凭借自身广博的阅读和不卓的见识也积极参与到玄学清谈中来。如,“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仪,词理将曲,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4]毫无疑问,谢道韫出色的清谈之功得益于日常对老庄、周易等类书籍的阅读及思考。
另外,魏晋女性在佛教、史学及医学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很深的造诣。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分裂与纷争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女性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阅读的范围也更宽泛和自由。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阅读特点
3.1 多以家庭为阅读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发展壮大,女性在教育中的地位也相应的提高。她们首先接受的是家族内的文化教育。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的阅读基本是多以家庭为阅读背景。一般师从父亲、母亲、叔伯等亲人。北周,“公义早孤,为母氏所养,亲授《书》《传》。”[14]家族教育也蕴育了西晋兄妹文学双璧——左思、左芬。“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为《离思赋》,文辞清丽。”[15]在门阀士族的家庭里,甚至有奴婢也能读书识字的例子,如郑玄家婢女皆能读书。
3.2 阅读内容更加多元化
女性阅读不像男子读书有科举的压力,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各类阅读内容,阅读内容呈现多元化。如“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时名士。”[16]梁武皇后郗徽,“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17]又如,谢安与子女们齐聚一堂问:“《毛诗》何句最佳?”谢道韫应声而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由此可见,谢道韫对《诗经》熟悉程度及热爱程度。
3.3 成为终身阅读的实践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拥有了比前代更高的家庭地位,也有了更平稳的心态与闲暇时间来阅读,且能持续终身。如西晋宋夫人终身不缀地诵习《周官》,以增进学业。“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15]魏晋名士钟会其母好读书,涉书众多,尤好《易》《老子》。南朝吴郡韩英兰,十多岁便能文善赋。后博学多识,尤善经书,且讲授精当,宋武帝令她担任六宫各员的文化老师,教授诗书等各科知识。一旦为师,且自身具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更需持续不断的学习,成为终身阅读的女性实践者。
4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阅读的意义
4.1 对女性自身价值及社会地位的提升
女性通过阅读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并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里,逐渐认识到自身独立的价值。前面说过,“妇之四德所乏唯容尔”的许允之妻阮氏另一个例子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18]最后,许允听从了妻子“以理夺”的劝诫向皇上陈辞,终得以释放。又如,“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帏中察之,……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4]这些事例凸显女性言论在男性心中的份量,及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世说新语》是专门记述魏晋士人言行的,却专门开辟“贤媛”篇,记述了24位女性的事迹。且多为学识渊博、见识通达之女子。如谢道韫、班婕妤、王昭君等。《世说新语》记述才女事迹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对阅读女性的赏识与肯定。无论男女只要有才有德,皆能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女性家庭地位及社会地位的提升,对整个社会及后世社会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4.2 对文化传承的重要贡献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子女。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作用下,相夫教子是女子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承担了蒙学甚至专门学问的传授任务。贤能博学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如太学博士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19]
二是教育学生。魏晋南北朝时,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女性导师的出现。如宣文君宋夫人,讲授《周官》音义,“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授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15]这大概是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最早有史料佐证的由女性教师主持的班级教学的案例。[20]“周官学复行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15]她为保存文化典籍,传承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有魏晋时期的卫铄讲授书法,李彪之女给皇帝妹传授书法及经史等。魏晋时期女性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培养出了许多出色的人才,使得很多文化得以以另种方式传承下来,同时也为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是著书立说。今人逯钦立校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王延梯《中国古代女作家集》收集作品务求其备,二书所收该时期女诗人最为齐全,约四十多位。[21]《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著录女子26位。毫无疑问,女性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书法、儒学、经学等许多方面的传承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5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女性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尤其阅读使女性更优雅、更自信、更独立,使女性以新的姿态屹立于家庭、家族和社会舞台上。虽然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女性阅读内容、文学作品等方面还不能与唐、明清等相比,但它也自其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