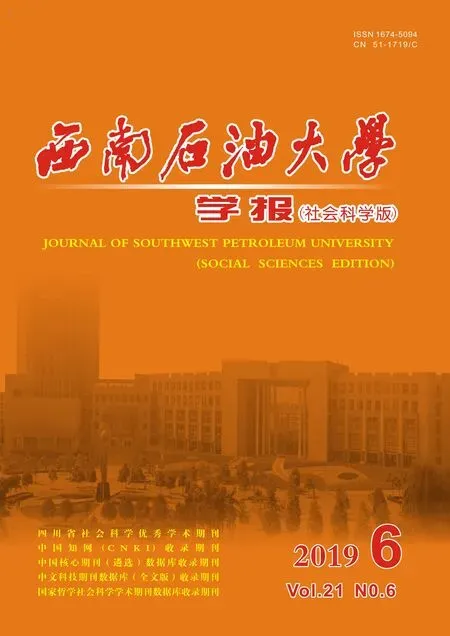巴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析
——从巴人精神到巴中人民革命精神
李学林,毛嘉琪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10500
引言
2017 年1 月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进展,巴人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的关注与人民群众的喜爱。巴中作为巴人精神的衍生与传承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正是研究者们探究巴人精神沿袭与发展的恰当实例之地。探求巴人精神与巴中红色精神的传承脉络,为进一步打造巴人精神与巴中红色文化相结合的“红+古”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奠定理论基石,既是新时代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强烈要求,又有利于传播先进红色文化,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实例。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巴人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考,笔者希望推进巴文化研究在两方面有所突破:一方面,更加准确地评估巴文化的文明传承价值。巴人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中红色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它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对于搞好文明传承,特别是建设具有巴中地域特色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更加明确巴中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内涵,为实现巴文化成为助推巴中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目标奠定理论基石。深入挖掘巴人历史悠久的淳朴古风民俗与革命老根据地巴中的红色精神之间的有效传承性,为以现代社会的眼光审视、以“红+古”为特色来整合开发此类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奠定理论基础。
1 古代巴人精神的内涵
古代巴人长期生存在悬岩峡谷、河流纵横的高山大川中,他们一代代绵延不绝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坚强地生活发展、繁衍生息。在时代的更迭、朝局的变动和民族群体的不断迁徙融合过程中,古代巴人们以无畏的勇气、忠肝义胆的气节、自强不息的风气、开放包容的心态、崇尚统一的情怀,日渐锤炼出巴中人民富有特质又内涵丰富的民族群体精神,在巴中文化的价值理念核心层面熠熠生辉。
1.1 刚勇尚武
巴中人民世代居住在川东一带险恶的崇山峻岭之中。大巴山山脉地势险要、连亘数百里,其间更有河流交错、河谷遍布,古代巴人在如此的自然环境结构中艰辛生存,自然铸就了他们强壮的体质、顽强的意志和崇力尚勇的精神品质。加之社会环境的变迁,他们不得不以武勇的方式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在一次又一次战争的洗礼中,古代巴人刚勇尚武的精神品格得到了更深的磨练和锻造,升华为巴族人民根本的民族性格和基本的人文精神。
史籍上的古代巴人以“崇力尚勇”著称于世。据古文献《舆地纪胜》记载,他们的最大特质就是“勇健,好歌舞”①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162.;《华阳国志》引《尚书》亦记载“賨人天性劲勇”②(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10.;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再次提及:“板楯蛮七姓......其人勇猛,善于兵战。”[1]“巴”字的起源也与早期巴人们尚武的习惯息息相关。中原地区的各民族在夏、商朝之时,便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即甲骨文文体。在此期间,中原民族与巴人先民们的交往,多以战争方面的事务为主。由此,他们根据古代巴人在交战之中表现出来的身手敏捷、攀援技娴的特性,以战争中人的形状创造了“巴”字的形体,这从甲骨文“巴”字的几种形体皆能观察出来。
对白虎的原始崇拜深刻地体现出古代巴人们崇尚武勇的民族精神。巴人先民们长期敬信、崇奉白虎,甚至视其为祖先,因为虎是万兽之王,他们期望自己的部落民众能够像白虎一般勇猛、武力强悍。这在《博物志》《搜神记》《五杂姐》《虎荟》等史料典籍之中均有记载。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便有文字道:“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人祠焉。”其中的巴氏廪君因在投剑中石穴的比武大赛中胜出,而被推举为武落钟离山五姓的部落领导人。他带领巴人沿江而上,扩展地域,经多次战争打败盐水女神族,夺取盐源,最终建国安邦。在巴人心中,战功彪炳的廪君与山林之王的白虎相符,因此有了廪君化虎的说法,究其实质仍是对武勇的崇拜。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系列与早期巴人生产、生活、军事相关活动的遗物,其中带有虎纹饰的器物和戈剑比比皆是。例如,在宣汉罗家坝遗址墓葬出土的剑、戈、矛等青铜兵器上,皆铸有虎纹,印证着巴人崇虎的习俗与尚武的精神。
巴人先民们的强悍武勇精神在生死攸关的征战、平乱和反暴斗争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公元前1046 年的商朝末期,周武王伐纣,英勇善战的巴人将士被周武王派任为先锋部队,一路勇猛杀敌,大破殷人士卒。正如《华阳国志· 巴志》中所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2]巴人也因其赫赫军功获赐姬姓封国,名垂历史。汉代巴人的后裔们,也曾在刘邦平定三秦之时,以其传统军舞,再次立下显赫战功。此外,还有“浮江伐楚”“南征平乱”“黄巾军起义”等等征战事迹,无一不是以巴人士兵为先锋部队或主力部队,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巴人气势磅礴的战舞在征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不论是周武王还是刘邦,都曾特意命人将其编导为宫廷表演或祭祀祖先的舞蹈,而威武雄壮、狂野豪迈的军舞也将古代巴人勇往直前、刚强果敢、崇尚武功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2 忠义至上
古代巴人的武勇,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天性劲勇,更是因为他们尚义崇德的古老价值观和秉持信义的精神理念。早在巴人先祖们的精魂中,便禀赋一种要替天行道的忠义之感,为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荣誉而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舍身取义的优秀精神和宝贵品格,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千载之下纵横史籍,我们不难看到巴人忠肝义胆的生动形象呼之欲出,颇获先贤尤其史学家的赞誉。
据《华阳国志》中《巴志》记载,巴人“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3]39,其中还明确赞扬巴人“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3]2从中可以看出,忠勇正义之人、义薄云天之事实为古代巴人之常态。
坚守信义、舍身爱国,把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保护国家的安泰置于个人性命之前,古代巴人忠烈的精神与崇高气节在巴地世世代代相传的巴蔓子将军的感人事迹中得到具体体现。根据《华阳国志· 巴志》中的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难以平复,身为卿相和将军的巴蔓子,为了获得楚国军队的援助,便向楚国许诺说:评定内乱后用三座城池作为酬谢。巴国的内乱平息之后,巴蔓子自刎并令人把自己的头送去楚国,说:“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32.楚王被深深动容,感叹道:“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3]32,并以上卿之礼将其埋葬。巴蔓子将军这种忠于父母之邦,不惜舍身取义的坚贞气节,正是古代巴族人民忠义精神、崇高气节的缩影。
1.3 勤劳智慧
古代巴人不仅忠勇信义,而且勤劳智慧、自强不息。西南地区遍布高山大川、河流沟壑纵横的艰险自然面貌,使他们在适应环境、改造自然、繁衍生息的生活劳作历程中,不断开动自己的智慧,自力更生,勤劳耕作,锻造出山一样坚韧不拨的禀性和强健彪悍的身体素质,培植出巴族人民勤劳智慧、勇于进取和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了在连绵起伏的山川丘陵中获得耕种谋生的土地,古代巴人开动智慧,在陡峭的山坡上垒石造田,制作绳索工具滑到山腰耕作。为了阻止山林野兽在播种和收获时节前来糟踢庄稼,古代巴人就在田地旁侧生烟起火,轮流值守。为了与外界交换产品,巴人先民们便伐木造船,无论是枯水还是洪水季节,他们都会勤勤恳恳地驾船外运。如此种种,无一不诉说着巴人们在辛酸艰难中的自强精神。
在荒莽的大巴山,古代巴人直面现实、不畏艰辛,用其勤劳与智慧,拼搏进取、奋发图强,不仅发展农业、畜牧业,制作业和交通建筑技术也是声闻遐迩、史籍有载。例如,古代巴人历史上蔚为大观的交通网络线路——米仓道巴人遗址,纵贯秦巴山脉的崇山峻岭,绵延米仓山中的沟壑急流之上,在悬崖边搭建栈道,设众多关隘要塞,建造形式各异的桥梁津渡,无论是其设计技术还是施工难度,均令人叹为观止。今天遗存下来的还有各色古寨、古镇、古桥,以及精致绝伦、美不胜收的大量青铜器、玉器、兵器、陶器、石器等。这些从遗址出土的众多巴人物质文明成果,反映出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勤劳和自强不息精神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1.4 开放包容
古代巴人文明能够繁衍、发展至今,离不开巴人们开放包容的精神。因为一个区域只有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充满活力,才能像河流一般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巴人文明是以其区域性地理环境为自然基础,在与外界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兼收并蓄,一步一步形成合力,最终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在陆续的部落战争、移民、族群迁徙的历史进程中,巴人以开放包容的精神理念,在不同时期吸收和借鉴了中原、吴越、蜀、楚、秦、汉等他地文明,从而使巴人文明获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古代巴人居住的区域和当时的整个四川一样,在其他族群的移民不断迁徙出入的进程中,以包容开放的精神,动态融合着其他族群的民众与文化。在历史上,巴地流域经历过六七次的大规模移民,最早能追溯到东周时期的楚地移民。《战国策·秦策》中记载的“楚苞九夷,又方千里”①刘向集录.战国策(第一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7.,明确指出楚国人当时也占据了賨人亦即巴人之地,并称“其人半楚”云云。当地考古发掘的战国时期古迹,如罗家坝遗址中的日用陶器、丧葬风俗,皆映衬出楚国移民之众这一史实。还有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也给巴中等渠江流域带来了大量的移民。而巴人秉持着历来兼容并包的精神,与外来移民和睦相处,杂居局面甚为融洽。
古代巴人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对外来文明兼收并蓄、吸收借鉴,从而促进了自身文明的发展。楚文明的传入,促使巴人创新了其青铜铸造工艺、丰富了青铜器的样式。中原文明的传入,促使巴人的青铜兵器更加先进。还有陶器的制作、铁器的传入等等,都促进了巴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
2 巴人去向与巴人精神传承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古代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尔后,活动之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即今川东、陕南、鄂西、湘西、黔东一带),并先后建国定都于夷城、江州、垫江、平都、阆中、忠州、枳等处(今湖北、川东之地)。由此可见,古代巴人的活动范围与活动中心为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等地。明末清初,四川省由于连年战乱、天灾频发以及严重虎患,总人口数锐减至不足50万②李世平.四川人口史[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55-156.。由清政府行政引导、政策鼓励的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这一大型移民运动拉开了历时百年的序幕。自此以后,四川省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九为迁移而来的湖南、湖北之人③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M].中国移民史 卷五明时期[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61.,而湖北省麻城县和黄州府作为主要集散地,其民众为主要入川人口。今天四川省的巴中市,古代便属于川东地区,是古代巴人的生活区域。广大的巴中人民,不管是当地土著人口的子孙,还是当年湖广填四川时迁移而来的湖广人,其基因里都流淌着巴人的血脉,骨子里传承着巴人的精神。
2.1 古代巴人的去向之谜
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与楚人关系密切,又相互攻伐。《楚辞》所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④屈原.楚辞[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8.,此时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里已有许多巴人。据今天的考古资料显示,在此时期,巴人开始不断地向鄂西、湘西、黔东北等地迁徙。在巴国彻底被秦灭国以后,他们更是大举向湘鄂川黔继续迁移,此后,巴人的行动便鲜少在史书中出现,至唐宋元明清之后,其踪迹更是烟消云散于史料。直至1955 年,民族学家潘光旦发表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这篇追根溯源土家族历史的文章之后,巴人后裔的神秘面纱才逐渐揭露于大众的视野当中。该文揭示出:即使历经上千年的历史间隔与朝代更迭,当今土家族人与古代巴人之间生活的地理区域联系、宗教习俗渊源、文化艺术相似性特征以及血脉的一脉相承,无不昭示着彼此之间的种族历史传承性。
就历史发展脉络的连续性和生活的地理区域而言,巴人生活的地域范围和土家族人聚居的实际位置基本吻合。古代巴人自鄂西起源,春秋战国时期在强秦和强楚的迫使下大规模向湘、鄂、渝、黔等地的交界处迁徙,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依然不断地向四处迁移,但大多数都未曾离开湘鄂川黔边境,隋唐五代后改称为“土人”“土司”和“土家”等名①杨铭.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历史文化渊源[J].中华文化论坛,2004(2):20-23.。不论是在古代巴国时期,还是在灭国后的迁徙时段,巴人活动的总体地域都未曾离开川东南、湘西、鄂西、黔东北一带,而土家族人居住的区域恰恰也是山峦连绵、河流密布的重庆、湖南、湖北、贵州四省交界处,生活地域不谋而合。基于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社会调查,在《土家族简史》这类介绍土家族的文献中也称“土家来源于楚、秦灭巴后定居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的巴人”[4]。《鄂西土家族简史》也持此观点,认为“古代居住在鄂西地区的巴人......其后代即现在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土家族”[5]。
在宗教习俗方面,两者也具有诸多共通的特点。巴人与土家族人皆崇尚信仰白虎。在有关古代巴人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便有不少关于廪君死后化身为白虎,巴人“血祭白虎”以祈求图腾保护、神灵庇佑的记载。而在有关土家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材料和其民间传说中,同样发现颇多土家族崇拜老虎的遗迹,比如将老虎视为祖先,其织锦中的祖宗花图案便为虎形,以及小孩从小便头戴虎头式样的帽子等。另外,巴人宗教中后期的杀死图腾神的模式在土家族这里则延续成了赶虎的宗教习俗。
从文化、艺术视域来说,古代巴人的巴渝舞、竹枝歌等舞蹈音乐形式与土家族人的大摆手舞、跳廪舞、土家族民歌在元素和内容上有颇多的相似性。巴人崇尚歌舞,其著名的征战舞蹈巴渝舞和土家族人的祭祀舞蹈摆手舞在内容和形式上皆具有一致性:在表现形式上,都通过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和金鼓齐鸣的音乐节奏来表现战争场面的气势磅礴和战士舞者们的威武雄壮;在元素内容上,都采用舞蹈道具刀剑、弓弩、长矛、木棍等武器作格斗姿态、摹仿战斗动作,同时都主要采用鼓为伴奏的乐器,击鼓为节,顺其势踏地而歌。古代巴人的大量音乐艺术元素,也蕴含在土家族人的民歌、摆手歌、婚嫁歌、祭祀歌和丧歌中[6]。比如,唐宋之时盛行的巴人所创的竹枝歌,流传至今,仍可用土家族民歌的曲调配唱。
从人类体征学和基因学的内在生物层面来讲,古代巴人和当代土家族人不论是在人骨体征类型方面,还是在血液基因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强烈的内在一致性。20 世纪90 年代初,鄂西地区长阳县深潭湾的一崖穴里,挖掘出100 多具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巴人人骨标本。研究者通过将其与如今聚居在湖北省的土家族人体征类型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鉴定结果使人们有理由推测:长阳地区青铜时期的深潭湾巴人是现居土家族人的祖先,且其人体的总特征始终变化不大[7]。许多学者认为,土家族是在以巴人为主体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逐渐形成的。其中,董珞认为,土家先民为古代巴人,但北部方言区的土家人与南部方言区之间在族缘上存在着差别:北部方言区土家族的主体先民应是廪君蛮,南部方言区的土家人的主体先民则应是板楯蛮[8]。
2.2 “湖广填四川”后巴人精神的传承
在明末清初时期,四川由于历经张献忠农民起义、清军入川铁骑践踏、吴三桂叛乱之战等持续兵灾战乱的摧残,以及随后旱灾频发、瘟疫不断、虎患甚烈的席卷,全省总人口骤然衰减至不足50 万人。清政府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便颁布了一系列优惠鼓励政策,引导湖南、湖北等地区的广大百姓移民四川,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活动,即耗时达105 年之久的“湖广填四川”运动,把四川重建成一个人口达1 000 多万的大省②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J].社会科学研究,1998(6):111-118.。《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把四川人口结构概括为“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有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9]。如上所述,古代巴人的后裔土家族人,在此次迁徙的浪潮中便大规模地迁入四川定居,构成四川总人口的主体,也即是巴中总人口的主体成分。加之,巴中市自古以来的地理位置就处在川东北,而川东北地区在数千年以前就一直属于古代巴人长期生活聚居的区域范围。由此,居于四川东北一隅的巴中人民,不管是湖广填四川运动迁徙而来的移民后代,还是长期居住于此地的土著人口的后裔,相当一部分都仍属于古代巴人的子孙,在血脉上为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引导湖广地区人民大规模迁移到四川有其客观必然性。其一,明末清初四川境内长期战乱不息。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 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 年)的60 年之间,四川地区先后出现了当地土司之战导致的“三藩之乱”、张献忠农民义军同明朝军队之间的平叛之战、南明政权武装与清朝军队之间的夺权之战、吴三桂反叛之乱等持续不断的兵灾战乱。其二,从顺治初年开始四川大地上便灾荒频发。根据四川苍溪、崇庆等多地的县志所载,由于当时旱灾的大面积爆发,甚至出现了“赤地千里”的极度荒凉景象①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M].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49.。连年的饥荒再次导致当地的人口锐减,加之战乱和灾害之后瘟疫肆虐,大头瘟、马蹄瘟等疾病无药可治②李懋君.论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行政引导[J].湖北社会科学,2012(8):111-113.,甚至出现全村皆死的凄惨场面。其三,长期战乱后各地城池设施遭到严重毁坏且四处人烟稀少,为当地华南虎的繁殖、肆虐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四川通志》关于“明末圮”的记载中,清初年间多地“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③(清)张晋生.四川通志:卷四[M].四川:巴蜀书社,1984:190.,许多地方城中草木繁茂,豺虎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就连蜀王府内也成野兽聚集之地,官员孤守城楼、官兵城中狩猎。综上种种原因,四川由“天府之国”衰败为“蜀民至是殆尽矣”“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萧索、凋零境况,呈现出灾伤遍地、生灵涂炭、社会经济空前破坏的一片惨淡景象,亟待恢复。而鄂湘赣闽等省在休养生息后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清政府在康熙33 年颁发《招民填川诏》,以任占荒地、长期免税、给予户籍、发放耕牛种子等优惠政策鼓励湖广居民移民填蜀,取得了巨大成效。
在政府主导、政策推动下,百姓自愿自发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让归属于四川省东北区域的巴中市人口也得到了迅速填充和增长,人口结构发生相应改变,居民生存空间分布更加合理,社会风貌得以重塑。尤其在巴中的人口结构层面,原本位于大巴山脚下长期自成一隅的巴中地区土著、古代巴人后裔仅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二,而随移民潮从湖广省迁移而来的客居在巴中的古代巴人血脉土家族人则占约二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三四则为安徽、河南、江西等东南各地的零散移民。此次移民运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巴中当地巴人后裔与湖南、湖北之地巴人后代的继续血脉融合。相应地,在巴中的社会面貌视域,湖南、湖北等地的移民与当地人民共同携手,在经济生产上,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买卖商品作物、开矿经商;在文化艺术上,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在人种繁衍优化上,客民与土著逐渐相互融合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繁衍绵长。
从精神层面来说,“湖广填四川”以后,生活于巴中地域的人民,不仅与古代巴人在血缘关系上具有更高程度的联系,而且由于生活在相同地域,所面临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同一性带给了他们与古代巴人同样的生存压力,加之对古老习俗和精神的传承,巴中人民愈发表现出与古代巴人相似的文化特色和精神面貌。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们,也带来了更加多样的文化、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为巴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兴素材,为巴中精神的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到了1932 年,红军进入巴中境内后,巴中人民又逐步接受了先进的共产主义理论,在革命实践中,巴人精神进一步与红色文化相融合,创造性地转换为巴中人民革命精神。
3 革命战争年代的巴中人民革命精神
古代巴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为革命战争时期大巴山红四方面军形成“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10]的十六字川陕苏区红军精神奠定了思想渊源。1932 年12 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州地区,创建了以巴中为政治、经济、军事首府的川陕地区革命根据地,由此开始了时达两年的与反动势力展开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巴人先民们在战胜自然、改造社会中凝炼而出的民族人文精神,在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再次升华为大巴山广大军民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坚定革命的忠义精神、智慧斗争的创新精神、勤劳建设的自强精神、军民交融的包容精神,并逐渐演化为巴山儿女不朽的精魂。
3.1 骁勇善战的大无畏精神
巴山儿女自古以来便刚勇尚武。1932 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巴山人民更是秉持着一贯勇往直前、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踊跃参加革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仅仅两年的时间,川陕苏区的红军人数就从初期的10 000 多人发展壮大到加上地方武装共12 余万人,而当时通南巴地区人民的总人口数不过120 万人。他们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将满腔热血洒在战场之上,其中4 万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战地。巴中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伟大的牺牲与不朽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诗篇,同时,巴地也为新中国的缔造和建设锻炼了大批骨干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巴中籍的吴瑞林、傅崇碧、何正文、陈其通、胥光义等27 名勇士被授衔为将军,刘海清、李培基、孙洪道等80 多名战士成长为省部(军)级以上干部,巴山人民的英勇得到了最好的表彰①秦勇,李单晶,罗大明.巴中红军对长征胜利的重大贡献[J].中华文化论坛,2012,4(4):145-149.。
1932 年,红四方面军入川,传承着先人勇敢精神的巴地人民络绎不绝地报名参军,许多乡亲父老甚至主动将自己的儿女送入红军。1932 年12 月,红军部队刚到达巴中县的清江渡、得胜山、江口场等地方,当地便有五六百人民子弟踊跃报名参军,8个独立团在1 个月之内就得以组建。花溪乡的王杨氏,不仅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红军,还动员了同乡20 多名青年到清江参军。1933 年10 月,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人数已达到70 000 多人,再加上地方武装人员,累计有90 000 多巴中英雄儿女投入革命洪流[11]64。
巴中的英雄儿女们除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外,更有不计其数的人民群众投身地方武装工作。他们以独立团营连、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共青团、儿童团、妇女会等多种形式自觉组织起来,主要负责维护治安、清剿反动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等工作。如: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平息平岗寨“盖天党”叛乱;得胜、兰草等地方武装配合红33 团成功夜袭寿南寨;南江工人师参加反“六路围攻”战役;江口独立团参加营渠战役。在无数次的战斗考验中,这些地方武装组织的成员骁勇善战、英明果敢,仅南江、长赤两县就有8 000 多独立团或游击队优秀成员陆陆续续加入了红军大部队[11]86。
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况最激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中,广大巴山儿女充分发扬了古代巴人刚勇尚武的精神,与红军一起,齐心协力、奋勇杀敌,全面击溃了敌人主力的猛烈进攻,沉重打击了刘湘及其四川军阀的反动势力,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部署。敌人的“六路围攻”投入了200 万元军费、20 余万兵力、1 万余支枪、500 万发子弹、18 架飞机,人员、装备远胜红军,来势汹汹。面对敌人的进攻,巴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与红军站在同一阵线,纷纷放下生产,勇敢参军,拿起刀矛,英勇作战。他们一次次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最终在黄猫垭取得了大捷,毙敌4 000 余人[11]205,俘敌1 万余人,缴获枪支炮弹数万,彻底粉碎了“六路围攻”的阴谋。
在革命战争中,传承着刚勇精神的巴山儿女们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大批劳动妇女剪掉辫子,拿起大刀长矛,参军参战,浴血奋战在革命的最前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上万名妇女脱产参加部队、机关、学校的工作,创造了中国妇运史上的奇迹”[12]。她们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组织严谨、战斗力强悍,为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英勇战斗,堪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独树一帜的妇女武装旗帜。她们吃苦耐劳,不分昼夜地进行军事训练,像男子一样剃光头、绑裹腿、背子弹带子[13],训练投弹、射击、刺杀等科目,每每杀声震天。妇女独立营经常冒着枪林弹雨运送枪支弹药,保卫交通要道和攻击线,有时还要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或是参与正面交锋。如在反“三路围攻”后,妇女独立营驻扎在毛浴镇,一天晚上遭突袭,全体妇女战士奋起反击,不仅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而且在邻近兄弟部队的支援下,全歼敌人一个营。1935 年4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地区开始长征,2 000 名女红军成立了妇女独立师,随着主力部队踏上了艰险的西征之路[14]16。英勇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大巴山红军妇女独立营、团、师,不仅是其他苏区没有的,而且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15]。
3.2 宁死不屈的忠义精神
忠肝义胆的民族气节是古代巴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川陕苏区长达两年的战火洗礼中,传承着忠义精神的巴中儿女们,始终保持着忠于革命的气节、坚守着心中革命的信念。
巴中游击队在与红军大部队隔绝联络的情况下,“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了5 年多游击战争,在人迹罕至的巴山老林生存两千个日日夜夜”[14]13。直到1940 年,在南江这支“最后的红军”队伍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血液里流淌着的巴人精神,早已升华为了坚定革命的忠义精神,谱写了党的武装斗争史上一曲不朽凯歌。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刘子才入狱后,动员赵大德、万明富等人趁夜越狱,说“你们啥都不要管,全算我的。要死,我一人去死,你们出去又好革命”[11]232。最后,他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
1935 年4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通南巴区域的人民群众遭到了卷土重来的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但即使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巴山人民仍旧以崇高的革命气节,坚守对革命的忠心,至死不屈,用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持巴山游击队的斗争。南江县沙河区老屋基乡党支部书记岳家伍,被敌人逮捕,酷刑之下不吐一字,燃烧的锅炭烧伤了他的喉咙,他却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1939 年冬,国民党残酷“清剿”巴山游击队,断绝了游击队的粮食来源。当地巴山群众得知后,为支援游击队,不顾生命危险,上山送粮食,不少乡亲惨遭杀害。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大巴山的忠义壮歌。
3.3 机智灵活的创新精神
在革命斗争中,巴中人民充分承袭了古代巴人善于开拓智慧的创新精神。无论是在剿灭土匪,还是在革命作战中,巴中人民都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各方优势,以智取敌。在反动势力对川陕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期间,巴中群众和川陕苏区政府一起共同开拓创新,用智慧打开新局面。在大革命时期,巴山人民利用当地山高石头多的资源优势,创造了石刻标语的文字宣传方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历史文化奇观。
在川陕苏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巴地人民充分发扬了其历史传承而下的智慧创新精神。在巴中县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不久,隐藏在深山洞穴的“盖天党”土匪和地主反动武装,背地里残酷屠杀革命人民,抢劫苏维埃政权的物资。巴中人民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采取利诱与进剿相结合的策略,彻底消除了匪患。在反“三路围攻”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地红军创新战略战法的典型打法,即“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利用川东山高林密、河流纵布、谷深路险地势环境,通过收紧阵地将敌人包围的战略,全歼敌部,其智谋足可见。
当然,反动武装势力长时期,对苏区进行封锁,但巴山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用自身的智慧开拓创新,不仅突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线,还形成了川陕苏区系统的红色金融货币体系、财政税收制度。面对刘湘划定的封锁区,智慧的巴中人民通过陆运和水运,将本地过剩的银耳、黑白木耳、木材、毛猪、桐油等物品运到赤白交界处交换所需的西药、油印机、电话机、手枪等物资,川陕苏区的金融货币体系和税收制度也应运而生。为了满足当地的民用军需,创造发行了5 种质地、20 多种版式或面额不同的货币,设置了累进税和关税等税法,在有序的财政政策之下发展赤区贸易、突破白区贸易①四川省社科院、陕西省社科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1.。
在开展宣传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巴山人民结合通南巴区域的独特喀斯特地貌,利用当地石头资源丰富、刻字能工巧匠多的优势,在缺少宣传纸张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发明了运用石刻文献、标语、对联进行宣传的特色宣传形式。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街道周围、祠堂庙宇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石板壁上,皆可见到这些鼓舞人民、震慑敌人、配合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的石刻宣传文字。在苏维埃干部群众涂抹、遮盖、深埋、暂时移作他用等千方百计的保护下,目前巴中市尚存的红军石刻仍近1 000 幅。这不仅是红军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巴中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
3.4 勤奋建设的自强精神
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之下,巴山人民的勤劳自强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他们艰苦奋斗、辛勤劳作、自强不息,使根据地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蓬勃发展,整体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在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政策的引导下,巴中县的每个农民都分得了至少一亩田地,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自强精神得以发挥。在巴中人民日夜勤劳耕耘下,加之风调雨顺的自然气候,在两年多的苏区建设中,巴中农业生产都取得了连续丰收的硕果,不管是水稻、土豆等粮食作物,还是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普遍比1932 年增产一倍以上[11]121。长赤县李子娅乡明确提出了要发挥勤劳自强精神,“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建设苏区”。1933 年冬,江口县得胜乡的村民冒着凛冽的寒冬开荒30 余亩,该县在短短小半年的时间内,便筹集了糙米70 万担、土布5 000 丈,并昼夜兼程运送给大后方红军[11]107。正如1933 年在整个通南巴地区传颁着的“谷出双穗,麦见二吊(穗)”的丰收佳话那样,在巴山人民勤劳自强的艰苦奋斗之下,赤区出现了家家杀年猪、人人添新衣的景象,还大量支援红军粮食与猪肉。
在两年的时间内,当地人民凭着勤劳自强、踏实肯干的精神,让巴中地区的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基本满足了民用军需。自1933 年起,巴中地区累计开办工厂100 多个,工人数量达到2 000 余人①张秉直.川陕苏区模范县--巴中[J].四川党史,1994(5):33-35.。在巴中县的综合厂里,每个生产战线的20 多名工人能每日生产出马刀400 多把、矛子1 000 多把,每月做出军装800 多套,每月造好油纸斗笠900多顶,每月织土布1 200 丈。在通江钢溪河铁厂,工人们勤劳工作,在两年时间内生产铁近200 万斤。
在巴中农业与工业得到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巴山人民并没有停下自强不息的脚步。闲余之时,他们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之下,修建乡村道路、疏通河道,发展陆运与水运等交通运输业。1933 年春,上万名巴中群众修建乡村道路1 700 多华里;1933 年夏秋,2 000 多名巴中石工铺成石板大道120 多华里;1933 年8 月到11 月,数万名巴中人民疏通了巴中至江口、江口至通江的300 里河道,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当地军民的水陆交通运输。
此外,巴中人民充分利用当时一切学习的机会,不断自强与提升自我,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全面普及,群众性识字读书活动在当地蔚然成风。除了常规的学校教育活动外,每个村和每个厂,都开办了夜间识字学习班,让当地人民充分利用晚上的闲余时间学习知识;较大的乡镇都设有阅览室,为苏区群众提供阅读之地;还有业余工读学校面向人民开放。
3.5 军民交融的包容精神
巴山人民自古以来便有开放包容的精神传统。1932 年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本着包容共生、共同发展的精神,本地人同外地人之间的隔阂很快便被打破,老百姓与红军战士之间亲如一家。古代巴人的包容精神,在川陕苏区的各种建设活动中,逐渐凝练和升华为军民交融的拥护爱戴之情。
在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巴中人民开放包容的精神奠定的思想基础,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立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地方武装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红四方面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顺利实施,根据地各项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战役全面胜利之后,苏区党、政、军、民各项系统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趋于完善,建立了苏维埃区84个、乡(市)568 个、村4 300 余个,可见巴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接纳包容程度之高。仅在1933 年6 月,南江、长赤两县就发展了共产党员2 000 多名②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印.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他们思想政治觉悟高,听党指挥,作战、搜山、抬伤兵、背粮食都不在话下,与入川的红军共同成为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同时,巴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通过参加各类革命团体组织,协助入川红军开展各项工作,密切了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1933 年6 月,恩阳县工会动员近800 人参加红军,并建立一支2 000 多人的运输大队,为营渠战役运送食盐、粮食、水等军需物资;1934 年秋,巴中当地被共青团(少共)组织起来的青年人数达10 万之众,成为党和红军的有力助手;1933 年,巴中少年先锋队约30 000 余人,承担了不少看守哨棚、捉拿豪绅地主、协助“清反”、维护赤区治安的任务;还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川陕苏区至少有30 万妇女参与其中,她们替红军做鞋、做袜、打草鞋,协助运输伤员与各类军需用品,军民鱼水相依、血肉相连。
在两年多的苏区建设时间里,巴山的劳苦大众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很快就认识到了红四方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自觉地将自身利益与革命利益相融,主动拥护、竭诚支援苏维埃政权,箪食壶浆援红军,充分发挥其后勤保障作用,不断密切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巴中县的人民群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红军运粮运物运伤员、传递消息、屯粮食,投入运输100 万人次、提供军粮15 万吨、打军鞋20 000 余双,涌现了不少鱼水情深的事例。1933 年春,巴中县正值冬春粮荒之季,百姓们自己都粮食紧张,但是很多人将下锅的粮食倒入米柜,筹集了57 万斤粮食献给红军。为了及时运输粮食、食盐和其他军需物资给作战红军,巴中人民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妇女孩童都会在战时冒着枪林弹雨,抢运枪支弹药到前线,抢回伤员、战利品到后方。邮政人员更是随身佩戴步枪、马刀,战线打到哪里,就冒着枪林弹雨将文件送到哪里、标语帖到哪里,而且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或者销毁文件。
4 结语
巴人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中红色文化是中国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二者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文化资源。笔者以巴人精神衍生与承袭之地的巴中作为研究对象,对巴人精神与巴中红色精神的传承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深刻探究,全面详细地梳理出了战争年代巴中人民革命精神对古代巴人精神的5 个维度的承袭内容,将为更加准确地评估巴人文化的文明传承价值提供史料支撑,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一定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