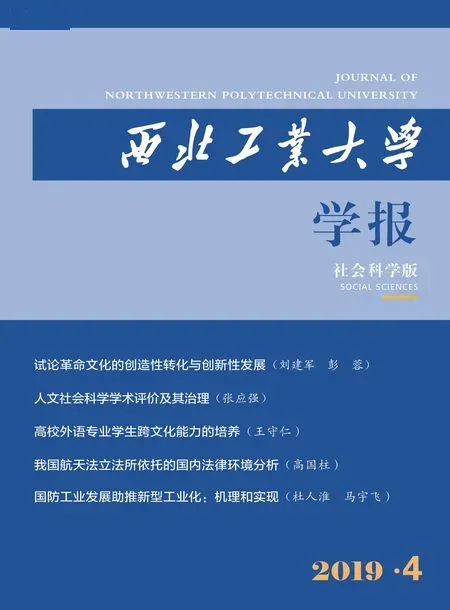文化十字路口的香港电影《王宝川》
1957年11月14日,熊式一编导制作的电影《王宝川》在香港乐声戏院举行世界首映。该活动由太平洋影业公司推出,旨在为当地最大的慈善组织东华三院筹募资金。该医院准备扩大其医疗设施以及义校校舍,以帮助本地的民众和穷困人士,但苦于资金短缺,急需社会各方的支持。这次义映活动,获得香港各界赞助,收入全部捐赠给东华三院,一时轰轰烈烈,传为佳话。
熊式一是20世纪上半期最有成就的华人英语作家之一,他在世界上的盛名和影响不下于林语堂和蒋彝。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旅居英国期间,用英语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小说、传记、散文,还把《西厢记》翻译成英语。但他最出名的作品要数《王宝川》。那是一出英语戏剧,于1934年出版并上演,此后二十多年来,它传遍了世界许多大城市。熊式一因戏剧《王宝川》闻名遐迩,成为第一个在戏剧界享有国际声誉的华人剧作家。他的名字因此与《王宝川》形影相连,《王宝川》似乎成了他的代名词。但熊式一始终怀有一个愿望,他要把《王宝川》搬上银幕,借助现代媒体工具,让世界上更多的观众得以分享这美丽的中国传统故事。他在1953年曾公开宣布:
我只剩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我坚信这部戏本身就能拍成一部最具艺术性和最成功的电影,它无须像一般好莱坞电影所要求的那样大刀阔斧进行改写。至今为止,所有的制片人都宣称这不可能办到,可是我有信心,总有一天会碰到一个人,能证明他们全都判断错误。①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各种意识形态、语言、情趣、品味交融杂汇之地,熊式一的梦想,在那里终于得以实现了。他制作了电影《王宝川》,把它搬上电影银幕。当然,文化十字路口既提供了机遇和创新的可能,也有风险和挑战。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熊式一亲自担任制片人、编剧、导演等多重角色。他的努力,是否最终获得成功?是否证明了其他制片人确实都判断错误了呢?
本文先考察20世纪30年代英语剧《王宝川》的创作特色和上演背景;然后介绍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文化政治背景,以及电影《王宝川》的摄制;最后,探讨该电影制作之后的情况,并分析导致这一部文化作品令人失望的结局的一些主要因素。
熊式一出生于江西南昌,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毕业,英语专业。1932年底,他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攻读英语博士学位。到英国之后不久,他根据古典京剧《红鬃烈马》改编成了英语戏剧《王宝川》。1934年,《王宝川》由麦勋书局出版,11月间,在伦敦西区的小剧院首演,此后三年,连续上演近900场,成为当时伦敦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出戏。1935年,经由莫里斯 · 韦斯特联系,熊式一去百老汇,在布思剧院导演《王宝川》,剧组在下一个演出季又去美国东西海岸几个主要大城市演出。除此以外,英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都先后上演过《王宝川》。
二十多年来,《王宝川》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嬗变。除了大量的舞台演出和十多种文字的版本之外,还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和电视节目中播出,1950年,熊式一本人又将这部英语戏剧改编成同名小说。1955年底,他移居香港,不久又将它翻译成中文出版,1956年春季,香港第二届艺术节期间,他亲自执导《王宝川》粤语剧,在舞台上演。
《王宝川》的原型《红鬃烈马》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爱情故事。宰相王允的小女儿王宝钏,放弃富贵和权势,下嫁给沦落街头的乞丐薛平贵。不久,薛平贵应征入伍,被派去远征西域。他后来遭魏虎陷害,被敌人俘虏。幸运的是,西凉国王非但没有杀害他,反而让他与代战公主结婚。18年后,薛平贵思乡心切,逃回故乡,与妻子王宝钏团聚。
熊式一在改编时做了几处重大的修改,将这传统的京剧变成了一出现代的英语戏剧。他的改编使那些不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西方观众觉得很容易接受。原剧本由八折戏组成,通常戏院每次仅仅选取其中的一两折上演。熊式一对所有的八折戏进行浓缩,去除其中的唱段,把它们融合成为一出两个多小时的英语戏剧。经过这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王宝川》与西方的戏剧传统惯例趋于一致。熊式一又把女主角的名字“王宝钏”意译改成了“Lady Precious Stream”,即“王宝川”,用它作为剧名。他对这大胆的意译得意不已,多次自豪地宣称,这一名字更优雅,更具诗意,远远胜过直译“Precious Bracelet ”或者音译“Baochuan”。
《王宝川》除了形式上的更改外,内容上也作了一些重大修改。《王宝川》首场开始的内容完全是熊式一创作添加的:农历新年,宰相王允在相府花园内摆设酒席,贺岁赏雪,商量小女儿王宝川的婚事。《红鬃烈马》中所有迷信和奇幻的内容全都被删削去了。例如,在原剧中,薛平贵是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王宝钏发现他的时候,他在相府门外的地上躺着睡觉。在《王宝川》中,薛平贵成了相府的园丁,稳重老成,有胆有识,而且体魄强壮,能文能武。对现代的西方观众来说,他与王宝川之间产生爱情,合乎逻辑,也在情理之中。此外,《红鬃烈马》中王宝钏抛绣球招婿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戏。原剧中,王孙公子和商贾官仕群集在彩楼前,争着抢绣球,结果,媒神月老拦截住绣球,把它递送给了薛平贵。《王宝川》保留了抛绣球的细节,却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折:王宝川先把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开去,然后把绣球抛给预先约定在角落等候的薛平贵。这一修改,看似简单,却突出了王宝川反传统规范、追寻自由幸福的努力,而不是依赖天神相助或运气巧合。《王宝川》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关于薛平贵与西凉国代战公主的关系:薛平贵一直没有与公主成亲,多年来他一直借故拖延,最后在登基大典前夕灌醉公主,策马飞驰回到故国。这一改编不仅体现了薛平贵的智慧和他对王宝川的忠诚,而且剔除了重婚细节,避开了这部戏剧在西方可能面临的棘手的道德问题,因为重婚内容很可能会引起激烈的批评。
20世纪初,好莱坞电影被引入中国后,中国开始成立电影公司并摄制国产电影。熊式一对电影素有兴趣。他自幼爱看电影,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曾在真光戏院担任副经理,之后又在上海经管百星大戏院。这两家戏院都属于现代化的娱乐场所,既上演舞台戏剧,又放映好莱坞电影。 1936年,有消息称他正在伦敦郊外的梅德韦片场写电影剧本,他被誉为“中国电影制作和发行的先驱人物”。1941年,他在根据萧伯纳同名剧本拍摄的电影《芭芭拉少校》中扮演一个唐人街华人的角色。
事实上,熊式一一直在四处寻找机会,想把《王宝川》搬上银幕。1937年,普赖米尔 · 斯塔福德电影公司同意拍摄《王宝川》彩色电影。1938年末,熊式一与维吉 · 纽文洽谈 《王宝川》电影的合同事项。根据合同,熊式一得提供电影导演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影片的长度限于5000英尺,即片长大约55分钟。合同还规定在签约后14天内就得开始电影的拍摄工作。但是,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该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此后20年中,熊式一与许多电影制片人和公司有过联系,讨论拍制电影的事,但一直没能成功。
1954年,熊式一去新加坡,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年之后,他搬迁到香港,迎接一个难得的机会:筹建太平洋影业公司,制作《王宝川》电影。他到香港后才两周,就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他的计划。戏剧《王宝川》已经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被译为十多种主要的欧洲语言,并且在世界上的许多城市进行了演出,他充满信心,认为可以根据戏剧版本制作一部电影,无须进行任何改动。《王宝川》这部香港影片,将使用时新的伊士曼七彩胶片拍摄,并且配有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当时香港影片尚未打入欧洲或美国电影市场,熊式一雄心勃勃,希望这部电影成为票房大热门,并且长驱直入,进军国际电影市场。
1955年12月13日,太平洋影业公司注册成立,资金为50万港元。熊式一得到一股资金,价值10000港元,换取《王宝川》的版权。熊式一和周昌盛担任该公司的经理,熊式一的月薪为2000港元。1956年1月28日,太平洋影业公司开始制作其第一部国产彩色影片《王宝川》。
20世纪50年代,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香港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至1950年4月底,香港人口增长到260万,比1949年5月增加了100万,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0%。那些新近从内地来香港的人中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以前在内地的各种文化领域工作,如作家、编剧、编辑、出版商、艺术家、电影制片人。他们去香港以后的文化实践,为当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多元变化,促使香港进一步成为中西文化、风格、影响相互交错邂逅的枢纽。
与此同时,电影业呈现爆炸性增长。数十家电影公司应运而生,它们大量制作电影,满足民众的需要。这些公司中有一部分非常成功,例如长城、中联、新联、华侨、电懋、邵氏等电影公司,后者甚至建立了邵氏影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制片厂。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制作的电影中,有些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有些则是非政治性的,例如武术电影、喜剧、传统故事等。新来香港的作家与本地作家一起,除了创作以外,以文学作品和传统题材改写电影剧本。这些文学电影极为流行,刺激了香港的电影业。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制作的文学电影分别为78部和149部。到了20世纪50年代,猛增至550余部,随后的10年间,又有500部问世。像《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说,都有十几部不同的电影。所有这些电影,除少数例外,大多是国语或粤语。②
作为电影题材,《王宝川》是不错的选择。《红鬃烈马》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而熊式一的《王宝川》又获得国际声誉,因此,这部电影的成功可谓十拿九稳。事实上,香港许多人相当熟悉《王宝川》。早在1935年,香港大学就上演过这部戏,此后的20年里,新闻媒体时常有关于它和熊式一的报道。熊式一在香港广为人知,深受尊敬,有众多的“粉丝”,其中包括不少欧美国家的外交人员和外国公司的职员。熊式一曾经自豪地宣称:“他们都是《王宝川》的仰慕者。”
6月间,电影《王宝川》在九龙机场附近的钻石片场正式开拍。熊式一招募了十多位年轻的华人演员,李香君演王宝川,鲁怡演薛平贵,缪海涛演王允,夏德华演代战公主。熊式一对所谓的老牌影星不感兴趣,他聘用的演员都必须会说国语,而且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他满怀信心,经过他的训练指导,一旦电影成功,那些演员都会一夜成名,就像他当年在西区和百老汇执导的舞台剧中的外国演员一样。李香君新近从内地迁居香港,被遴选担纲主演。她虽然才21岁,却已经具有精湛的京剧表演技能和丰富的舞台经验。这部电影的经历,开始了她的影业人生的关键一步,后来她果然成为邵氏电影公司当家花旦之一,成为香港最耀眼的女明星。
熊式一用两台摄影机拍片,一台使用黑白胶卷,另一台用伊士曼七彩胶卷。使用黑白胶卷是为了保险,因为当时彩色胶卷必须送到英国的兰克片场冲洗处理,一般得等2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知道结果,万一彩色胶卷出了差错,再要重新拍摄就非常困难了。当然,这么一来,制作成本随之增高了很多。11月中旬拍摄工作完成,影片长度大约一个小时三刻钟。熊式一随即动身去英国,与伦敦电影学院和电影界接洽。他对此行寄予厚望,认为一定能获得放映商的认可。
但是,熊式一的伦敦之行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顺利。他与电影学院、英国联合影业公司等一些主要电影放映商和发行商的谈判都没有能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原定的短期旅行转眼延长到了8个月,熊式一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就好像他当年《王宝川》剧本完成后在伦敦四下找戏院上演的那一阵子。然而,相比较而言,眼下的境遇更为糟糕:太平洋影业公司资金短缺,陷入了财务危机;电影的制作大大超出预算;聘用的演员在等着薪水;伦敦的兰克片场也在索取欠款;更有甚者,谣诼纷纭,说电影《王宝川》已经以失败告终,电影公司将宣布破产。为了摆脱这棘手的局面,如果有谁愿意出个好价钱,熊式一会义无反顾,马上同意出售电影的版权。
那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众对太平洋影业公司和《王宝川》的态度褒贬不一,熊式一去英国期间,甚至有人预测说他不会再回香港。但是熊式一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猜测和判断都是无中生有,他回到了香港。不过他急需资金,需要支付账单,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还得解决其他杂项开支。安排放映一场《王宝川》,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马上消除众人的顾虑、增添信心,对于那些骑墙观望、迟疑不决的投资人,更是如此。
1957年9月30日,熊式一写信给葛量洪港督,告诉他说彩色电影《王宝川》已经制作完成,配有英语对话,将于明年初在伦敦的电影学院举行正式公映,现拟在香港先举办一场慈善义映。他强调,那将是唯一的一场。葛量洪在年底将卸职离港,熊式一表示这场活动可以安排在适合他的时间举办。葛量洪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回复信写道:“您在本地拍摄制作了面向世界市场的彩色影片,这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非常高兴能在香港一睹为快。”
熊式一急切地期盼着义映活动,他希望能看到公众对这部影片的反应。如果它受到欢迎、获得好评,那些香港的投资人就可能会马上慷慨解囊,而且还会为影片进军国际市场鸣锣开道。10月30日,他在寓所招待葛量洪港督和夫人以及其他几位客人,包括英国驻菲律宾大使乔治 · 克勒顿以及民航局局长M.J.马斯普拉特 · 威廉姆斯夫妇。在有关的新闻报道中,含有以下幽默的细节:
马斯普拉特·威廉姆斯的兄弟托尼在不列颠战役期间驾驶一架喷火战斗机,那架战斗机的名字叫“王宝川”。他用油漆把这名字写在机身上,写了中文和英文两种。熊博士笑着介绍说:“那中文名字写得倒是挺漂亮的,但那是托尼自己拼造出来的字,要不是有下面那英文名字,谁都没法破译解读。”
电影义映晚会可谓盛况空前,各界名流咸集,热闹非凡。乐声戏院是二战后香港建造的第一座现代豪华剧院,坐落在新近发展的娱乐商业区铜锣湾。熊式一身穿一袭长衫,神采奕奕,迎接嘉宾。葛量洪夫妇光临时,他上前恭迎,陪同入座。
义映晚会的节目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大约27厘米长,20厘米宽,包括封面和封底,共56页。封面是一幅典雅的中国画,几杆疏密有致的绿色竹子,左上方是熊式一毛笔题写的中文标题“王宝川”,垂直向下,行书字体,飘逸潇洒,下方是他的署名,还有朱印私章。节目单用双语印制,大约一半是中文,另一半是英文。不过,其中的内容、信息并非绝对均等。比较有意思的是,中文部分附有电影《王宝川》的概要,而英文部分却没有。这电影概要中述及一些重要的修改细节,包括相府赏雪、薛平贵借故推迟与代战公主的婚姻、赦免魏虎死刑等,附在中文部分中,可能是为了让熟悉《红鬃烈马》的华人观众有所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节目单的中文部分约三分之一,计18页,全都是关于东华三院的历史和扩建项目、业务概括、筹款报告,而英文部分却一点都没有相关的内容。节目单的中间部分附有4页舞台剧照,下面有双语说明。
这一本节目单类如广告集成,洋洋大观。成发建筑公司、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美国工程公司、时装编织公司、海外信托银行等单位的中英文商业广告,计10页之多。其中最独特的是14页宣传戏剧《王宝川》的文字,那都是报纸杂志上有关《王宝川》的新闻报道和批评,以及庄士敦、阿乐迪斯 · 尼科尔、约瑟夫 · 麦克劳德、里昂 · M.莱昂、林语堂等著名作家和各界人士的盛赞佳评。其中还有一页题为《有关〈王宝川〉的事实点滴》的介绍,其开始部分如下:
1934年由熊式一编导,在伦敦首演,连续上演三年,其间承蒙伊丽莎白王太后、玛丽王后、而后现任的女王观摩,英国诸首相也先后光临,包括:
鲍德温、张伯伦、丘吉尔、艾德礼、艾登
1935年,熊式一又在纽约上演《王宝川》,从东岸到西岸演了三年,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和夫人的观看和赞赏。罗斯福夫人在1936年的每日一篇《我的一天》中对这部戏和演员给予高度赞扬。③
电影《王宝川》配有英语字幕,有伴奏音乐,整体而言,犹如舞台戏剧《王宝川》的电影复制品。它一共由七个场景组成,最开始的两个场景是相府庭院;第三、第四、第六个场景在寒窑外;第五个场景在西域;最后一个场景是西凉国王的行宫内部。舞台的周边按中国的传统风格设计,精心彩绘的宫殿式建筑显得富丽堂皇,舞台前沿设有栏杆,两侧是立柱。舞台的布景则采用大型中国山水画,例如,王允相府庭院的场景,画的是一座亭阁,四周有假山石、花草、树木点缀。身穿彩缎服饰的演员们运用抽象的戏剧表演手法,比如,在轿子中趋步向前代表马车行驶;手持鞭子急步向前表示飞马疾驰。简而言之,这是一部舞台剧电影,观众在银幕上欣赏舞台表演。
对于《王宝川》的义映晚会,熊式一颇为满意。他告诉夫人蔡岱梅:“义映相当好,各方面的评价也挺不错的”,“最令人满意的是现场观众的反应,因为他们在快乐和悲伤的时刻都作出了正确的反应”。④义映活动结束之后,他的朋友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令人难忘”;“表演精彩,难得一见,令人耳目一新”;“风格独特,丰富多彩,给人无限启迪”。香港新成立的电视台《丽的呼声》节目主管罗伊 · 邓洛普对这部影片赞不绝口。他表示,制作这样一部电影,难免要经历许许多多的 “头痛和心痛”,但他预言,这是一部“美妙绝伦、扣人心弦的影片”,“一定能在世界各地遍受欢迎”。⑤
可惜的是,媒体各界的反应相当冷淡。义映之后,这部电影几乎就销声匿迹了。此后的十多年里,戏剧《王宝川》依然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有演出,但它的电影版本却犹如流星,稍纵即逝,仅仅留下瞬间的炫目光彩。
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电影《王宝川》如此令人失望的结局呢?细细分析,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之一无疑与激烈的竞争有关。在放映《王宝川》的那个星期,除了附近的剧院在上演各种舞台戏剧外,周边的电影院有几十部好莱坞电影在上映,包括《金玉盟》《绝代艳姬》《血溅虎头门》《寻金热》。此外还有很多国产电影,包括《谁是凶手》《春归何处》《梁山伯与祝英台》《关公千里送嫂》《洛神》。《红鬃烈马》这出戏家喻户晓,普受欢迎,因此有几部据此摄制的影片。就在《王宝川》义映前两个月,9月12日那天,粤语电影《薛平贵与王宝钏》在香港发行,1959年6月10日,又出了另一部彩色粤剧戏曲片《王宝钏》。⑥
《王宝川》没有成功,也可以归咎于二战后亚洲与西方观众的新品味。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剧院一直受到电影业和日渐普及的电视机的威胁。光顾剧院的人数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电影院,或者在家里舒适地坐在电视机前欣赏节目。由于电视和电影的发展,大众的审美口味和要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电影和电视可以变换节奏,可以运用特技,可以对感官造成强烈的刺激,更容易吸引观众,远胜于戏剧院的轻步慢移的优雅。在剧院看舞台上的表演,得认真聆听对话,细细地琢磨体会,而观看电影电视则相对轻松得多。还有,电影《王宝川》去除了武打和唱段,银幕上的一些近镜头对话和动作就显得单调呆板。武打和唱腔属于京剧的基本要素,当年在英文剧中去除了这些内容,是为了让《王宝川》更符合西方的戏剧惯例,让那些没有京剧表演训练基础的西方演员不至于望而却步。熊式一在准备拍摄电影时,他的夫人蔡岱梅曾经建议增补武打和唱段,但她的建议没有被重视和采纳。熊式一完全忠实于戏剧版本拍摄电影,完全依赖对话和舞台剧的表演形式。在电影制作方面,熊式一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员。结果,这部电影显得节奏缓慢,乏味无聊,难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戏剧和电影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戏剧《王宝川》本身就不适合在银幕上表现。其实,《王宝川》在戏剧舞台上取得戏剧性成功的原因,恰恰就是它在电影院失败的关键。这部戏使用极端虚拟的表演手法,需要观众的参与,需要观众运用想象来建构场景,等等。譬如,一根竹竿被用来代表树,一条鞭子表示坐骑,两面旗帜作为马车。它要求观众想象一座大雪覆盖的花园,一块巨大的岩石,或者一个山洞。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这种象征和极简的舞台表现给西方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使他们大开眼界,简约的舞台风格和设计成为其成功的秘诀。南希 · 普莱斯是最初把《王宝川》搬上舞台的伦敦小剧院经理,她曾经一语道破天机:“布景的缺乏,使观众有了个任务。看戏的时候,他得在脑中绘制布景,他得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他会发现自己在看戏的时候思想变得活跃,就像在电影院里思想会变得不活跃一样。”⑦
电影与戏剧截然不同,它可以运用特写镜头、变速跳跃、改换角度、快速移动等各种技术手法。要想把戏剧改编成电影,如果不作重大改变,其魅力肯定会大打折扣。兰克公司当年拒绝参与拍《王宝川》电影,其理由与此有关: “电影的功能是将剧院扩大展现,并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仅仅拍摄舞台表演而已。”安东尼 · 阿斯奎斯和西德尼 · 科尔也持有相似的观点:由于《王宝川》的舞台表演很大程度上依赖舞台幻觉,拍成了电影,就不会有实际舞台表演的那种效果。确实,不少电影制片人对这部迷人的戏剧表示出极大兴趣,但因为意识到改编工作的困难,先后拒绝合作拍摄。当然也有几位制片人表示愿意按原样拍摄《王宝川》,但最终没有一个人答应接手摄制任务。
1935年8月,威廉 · 威廉姆斯在讨论戏剧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时,曾谈到戏剧受限于慢节奏和道具场景的限制,也提到电影的优势,像快节奏、蒙太奇、人群效应等。威廉姆斯认为,剧院靠“精明的资源”生存下来,他特别以《王宝川》为例,强调了它在克服舞台戏剧表演的局限性方面的“精明独创性”。不过,威廉姆斯认为,不能把《王宝川》看作是“当代剧院的典范”,因为它无法真正对抗电影现实主义的冲击。他的结论:《王宝川》属于“令人愉悦的博物馆藏品”⑧。“博物馆藏品”这词语在肯定这部戏剧的高度文化价值的同时,似乎也在含蓄地暗示它未来的归属,多多少少预示了电影版注定失败的厄运。
总之,电影《王宝川》在义映之后,从未公开发行,也从未在世界任何地方再放映过。摄制组和演员很快被解散,李香君接受邀请去邵氏公司拍片。太平洋影业公司始终没有能彻底摆脱财务困境。熊式一作为公司经理,自1957年1月以后的几年里,除了享受免费住房外,一直没有领薪水。为了拍摄电影,他把自己的积蓄几乎都投了进去。好几个朋友在他的鼓动下,也投入不少钱。大家都对这部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深信不疑。不幸的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一些朋友知道熊式一无法归还欠款,也就不再向他索还。他的多年至交威廉 · 阿尔贝特 · 罗宾森曾经借给他1300元美金,帮助解决经费。他后来写信告诉熊式一,既然这笔借款无望收还,他已经在联邦税单中申明作为坏账处理。
电影《王宝川》是熊式一继同名戏剧的成功之后,借助现代的电影媒介,将它再度推向世界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实践。他完成了电影《王宝川》的制作,可惜,由于影界竞争、审美趣味、戏剧和电影的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这一部文化作品最终未能公映和进入世界电影市场。它的失败令人惋惜,因为熊式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这部电影也确实有它独到的艺术之美。
熊式一的电影实践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他勇于探索,不甘现状,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他不畏艰难,而且不计个人的得失。他的奋斗精神,可钦可佩,值得赞赏,值得后人推崇。虽然电影《王宝川》没有预想的成功,但他丝毫不见气馁。在年近六旬时,重整旗鼓,振作精神,在香港继续他在文学、戏剧、教育等领域的开拓,且作出了极为可观的新成就。
注释
① Shih-I Hsiung.All the Managers Were Wrong about Lady Precious Stream.Radio Times,July 31,1953,pp.19.
② 梁秉钧、黄淑娴主编《香港文学电影篇目》,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2005。
③ 《王宝川》,电影节目单,香港太平洋影业公司,1959。
④ 熊式一,《致蔡岱梅》,1957。
⑤ Helen Dunlop and Roy Dunlop to Shih-I Hsiung,November 15,1957.
⑥ 与此同时,台湾的电影业也迅猛发展。1956年发行的闽南方言电影《薛平贵与王宝钏》,被誉为引发了台湾电影艺术并促成当地的电影市场。四年后,另一部题为《王宝钏》的电影问世。
⑦ Rejected All Round.Evening Standard,February 20,1936.
⑧ William E.Williams,Can Literature Survive?The Listener,August 28,193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