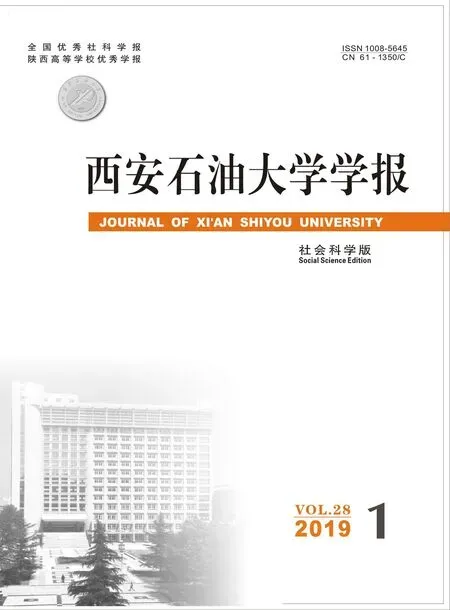论贾平凹《极花》的现实批判与精神困境
徐小雪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0 引 言
贾平凹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改革的探索者。他的创作始终密切地关注着社会的变化,揭露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但是其创作又不仅仅只再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而是在努力探索一条文化救赎之路,为转型中的社会发展提供自己的思路。小说《极花》表现出贾平凹对惨然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它以拐卖事件入手,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男性婚姻问题以及人的生存问题,同时又进行乡土叙写,反映了文明进程中所掩盖的城乡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折射出贾平凹对乡土的深沉忧思。但是,与《浮躁》《古炉》等贾平凹的一贯创作中的救赎道路相比,《极花》中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治愈时代病痛的疗药,面对惨然的社会现实虽有批判却无从救赎。因此,《极花》的书写,既彰显了贾平凹强烈的文人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贾平凹在寻找时代疗药上的精神困顿。
1 《极花》中的现实批判
一直以来,贾平凹都自觉地做着时代的记录者,见证着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世态人情,特别是秦岭大山深处的地域风貌、人的生活百态与精神裂变,其写作传达出对乡土的喜爱、留恋,对失落的乡土中国的无奈、惋惜,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思考,他是一位敢于批判现实、用心去书写的良知作家。
《极花》中,胡蝶为什么会被拐卖至西北一个名叫圪梁村的极其凋敝的村庄?这就不得不梳理一下故事的发展脉络了。弟弟上县中学后在学校吃住,胡蝶无事可干,于是进城帮助收破烂的母亲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经济的窘困使胡蝶暗下决心:“我也要去挣钱,能挣多少是多少,即便不能让娘过上好日子,也要减轻娘的负担。”[1]50但就是这种想找工作挣钱的念头,使胡蝶被人贩子成功利用并拐卖至偏远的圪梁村。圪梁村男多女少,有许多男性光棍,这里还盛产男性壮阳的血葱,使得男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了圪梁村延续后代的障碍,所以胡蝶才会被拐卖至这里。通过对《极花》故事的梳理,可以发现涉及到了三桩社会现实问题:收破烂群体的生活问题,拐卖妇女的问题,男性婚姻的问题。贾平凹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社会问题,并以文学的形式对其进行再创造,以此来揭露并批判惨然的社会现实。
1.1 拐卖问题
《极花》里,最直接、显性的惨然现实是拐卖问题。“拐卖”,一个听着就让人痛心与难以接受的字眼。电影《盲山》和《亲爱的》都是以拐卖为主题的影片。贾平凹的《极花》并没有止于《盲山》中惊心惨然的情节,而是把解救胡蝶以及回归圪梁村以梦境的形式表现,使其趋于理性与文学化,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体现出贾平凹对文明进程中社会阴暗现实的独特批判与思考。同时,《极花》也没有像《亲爱的》那样曲折地叙写寻找的艰辛,而是通过胡蝶的猜测简简单单几笔带过,更多的笔触是专注于对胡蝶在圪梁村的见闻进行乡土叙事。《极花》的写作是贾平凹在采风调查后,内心深处迫切感的使然。在《极花》后记中,贾平凹这样说道:“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有数千人。”[1]205同样在后记中,贾平凹说他采风去过甘肃定西、榆林的横山和绥德等地,他看到脸色黝黑、背着沉重的篓子、O型腿的妇女,他就想起了被拐卖的老乡的女儿。在某个村庄,看到农家的一边给小孩擦鼻涕一边朝隔壁骂的妇女,他也想起了被拐卖的老乡的女儿。在往另一个村庄去的路口,看到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奶奶,他仍然想起了被拐卖的老乡的女儿。在现实社会中,拐卖竟是如此平常,而且在他身边就有发生,这深深触动着贾平凹的内心。贾平凹借《极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控诉着这一野蛮的不文明的社会现象。
1.2 男性婚姻问题
贾平凹通过《极花》对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进行了揭露。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男女比例是失调的,且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我国男女性别比是102.71∶100;到2015年总人口13亿多,男性70 414万人,女性67 048万人,男女比例是105.02∶100,男性多出女性3 366万人,适婚(20~24岁)男女性别比是108.51∶100。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如此突出,对农村地区男性来说结婚成了一项生活必需而又极其困难的生存问题。在《极花》后记中,贾平凹透露:“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1]206可以想象进行采风时贾平凹的内心是极其复杂而又无奈的。在其作品中,贾平凹从不避讳这惨然的现实,而是敢于直面时代辉煌所掩盖下的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现实。“城市化进程中,文学作品中城市对乡村掠夺的主题并不新鲜,而且我国也已经从国家层面上提出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极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掠夺、资源的掠夺方面着眼,它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男性生育的权利、性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了。”[2]90《极花》中,胡蝶最终还是被黑亮强暴,同样被拐卖至此的訾米则成为立春和腊八兄弟俩共同的女人;黑亮爹用石头打刻“女人”摆放至村子里各处。在圪梁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可又偏偏盛产血葱,男性婚姻问题尤为迫切显著,女人成为满足男人性欲的工具。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农村男性成为无辜受害者,同样,被拐卖的妇女也是不幸的遭遇者。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但却要承受莫名的痛楚。
1.3 拾破烂群体
《极花》对城市化进程中所造成的农民工进城后的生存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城市的发展需要工业,更需要劳动力,因此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中去打拼。由于他们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下,收破烂就成为一部分农民工进城后的生存手段。贾平凹对农民工拾破烂群体也是非常关注的,《高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以刘高兴为主的农民进城者,他们带着理想、热情来到城市,希望脱离农村,但现实是残酷的,由于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也没有“关系”,最终只能选择城市里最脏最累而又最没有地位的工作——拾破烂。《极花》是贾平凹对这一群体的再次关注,胡蝶娘就是在城里收破烂以维持一家的生计,没人喊她的名字,都是直接喊“破烂”,只有房东老伯和房东的儿子青文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在城市里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过着最底层的生活,不仅得不到尊重,还被歧视嘲笑。也许因为自己之前的作品《高兴》已经对拾荒者进行了专门的叙述,所以在《极花》中贾平凹没有过多地再次进行叙写,而是在后记中进行了一定的阐述,“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1]204拾荒者的生活是艰辛的,其命运更是无情与悲哀的,《极花》中的胡蝶娘、后记中的老乡,他们不仅生活窘困,而且宝贝女儿又被拐卖,其身体和精神都遭受着生活无情的打击。
《极花》后记中谈到“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1]210贾平凹《极花》的创作不是寄情美景的豪情书写,也不是闭门造车的凭空瞎想,更不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而是深涵对城市化进程中所造成的拐卖、男性婚姻、拾破烂等农村生存现状问题的深刻批判。
2 精神困境
2.1 艰难写作
新闻报道力求真实性,还原事件的本初面貌,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眼前现实既是参照,也可能是束缚。贾平凹密切地注视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用文学的方式力图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小说《极花》的写作,以老乡女儿被拐卖的事件为原型,但又要冲破真实事件的束缚,避免故事新闻化、历史化,从而进行深刻的现实批判,所以《极花》的创作是一场艰难的跋涉。老乡的女儿被拐卖的事,如刀子一样在贾平凹内心深处划割,但十年间贾平凹一个字都没有写过。开始写作后,却又因“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1]208虽然拐卖事件就发生在贾平凹老乡的女儿身上,且贾平凹对乡村也是非常了解与热爱的,理应说《极花》的创作对贾平凹来说应该是轻松的,但是他不想把小说写成纯粹的历史故事。《极花》里有着深刻的现实批判,也有贾平凹对乡土的深沉忧思。这种艰难的写作,在贾平凹其他小说的创作中也是存在的,“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3]291《老生》后记中还写到:“能记忆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且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3]295这部宏大记忆的书写,是记忆的释然,也是痛苦的触摸。《秦腔》后记中,“书稿整整写了一年零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4]479贾平凹的写作从来就不是轻松的,其过程漫长而又身心煎熬,他的作品既不能用来娱乐消遣,也不仅是资讯的简单获取,而是精神的撕裂与心灵的震颤。
2.2 矛盾充斥
作为文坛鬼才,贾平凹笔耕不辍,创作力惊人,却为何在创作中断断续续、甚至停滞?其创作艰难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创作始终充满着矛盾。首先,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城市化进程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由于有了城乡两方面的生活体验与观察,接触了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对于这两种文化,他们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之中。”[5]56贾平凹深受城乡两种生活与文化的熏陶,一方面他知道现代化是发展的必然方向,渴望没有矛盾的社会文明,一方面他又对乡土有着复杂的留恋。《极花》中黑亮骂城市,说城市是血盆大口,吸走了农村的钱、物,还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事实就是这样,圪梁村被吸得一无所有,这里盛产极花,常常有商人来收购,于是村民疯狂采挖,最终极花几乎被挖得灭绝。农村生活贫困,于是有人进城去谋求生存,有人残废,有人损命。农村姑娘纯洁美丽,又常常被城里人骗走,使得圪梁村成了光棍村……城市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耗费农村的资源、人力,从而导致了城市愈发展愈广大、繁华,甚至浮躁;传统乡村反而越凋敝、落寞,甚至是消逝,两者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巨大反差。
其次,还在于文明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谢有顺评论贾平凹的创作:他“总是写当下、当代看到的和体验到的东西,即便有历史,也是曾经经历过的,这很难,写时间久远的容易写好,但刚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东西,写好很难,但他写出了当代人生活的味道和精神,当代人的精神不完全是以传统的眼光看,传统的角度无非是家国情怀,但他的小说中是家国中这种个体的衰败、时代精神的溃败,在溃败中召唤精神的重建和有力量的人的出现,写的是现代人的彷徨和痛苦和悲哀。”[6]118中国是深受儒家传统伦理影响的国度,文明礼仪、伦理秩序深入人心,但现代文明对传统有着明显的冲击,贾平凹作为一位文人,其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村人又特别注重生男孩,从而完成代代相传的使命——延续香火。《极花》中的黑亮也不例外,当胡蝶生下男孩后,黑亮极其高兴,梦想着再多生几个。可是在圪梁村这样的贫困地区,男性婚姻是极大的问题,这里几乎都要成为光棍村了,却还在梦想着生男孩,那以后孩子也当光棍吗?还是也像黑亮等愚昧的人一样继续纵容助长拐卖妇女现象的发生?圪梁村中,老老爷可谓是村里的传统权威代表,村民有什么事都会请教他,他就像是村民心中的神,在他的传统权威之下,圪梁村表面上还能维续下去。但以老老爷为代表的传统正在逐渐逝去,村里的现代新生力量正在崛起,逐渐挑战以老老爷为代表的传统权威。城市化的文明进程中,传统伦理权威已在淡去,现代新生力量刚刚崛起,因而充斥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
3 无从救赎
贾平凹的创作在揭示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解决方式,探索着文化救赎道路。《浮躁》中,“贾平凹通过州河对改革做出了合理的期盼,改革虽然现在问题很多,道路很艰难,但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会愈加向好的方向发展。”[7]37小说中,金狗从州河出发,经历一系列困难与变故之后,又重新回到州河且前途光明,这也暗示着贾平凹找到了浮躁社会的救赎道路:改革还处于起始阶段,虽有各种问题存在,但不必过多指责,中国正摸索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困难终会克服,改革终究会回归正轨并持续向前发展。“《古炉》中,贾平凹不仅表现了国民精神上的痼疾和病态的生存状况,而且开出了疗救的药方。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善人这个人物形象上。”[8]69,《土门》中贾平凹着力建构的理想家园——仁厚村,其实质也是对社会现实所表现出的救赎期盼。“对自己精神上的困惑和颓唐,敏感而有灵气的贾平凹不可能没有认知和警觉。因此,为了走出精神的颓唐和困惑,找到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出路,他特别注意对西方文化境界和资源的学习和借鉴。”[9]107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虽然充满矛盾,有着各式的社会问题,但基本上都是在努力探索救赎之路,且不论这些救赎是否有效,他总是有自己期待的解决路径,对发展有一定的预见性与指示性。
《极花》虽然是贾平凹矛盾纠结的隐痛书写,但“《极花》只呈现了这个时代的痛楚,却无力找到消除痛楚的利剑,更为无奈的是,连造成痛楚的原因都模糊了。”[10]《极花》中,贾平凹一面批判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掠夺所造成的拐卖、男性婚姻、拾破烂等生存现实问题,一方面也对圪梁村表现出充分的同情。胡蝶被解救回到城市后又重回圪梁村,黑亮为主的乡下人善良、勤劳且对待胡蝶也很好,圪梁村的村民还处在温饱线挣扎,基本主食就是土豆,圪梁村买女人是为了基本生存延续……这些叙述都充分展现了贾平凹对城乡矛盾中处于弱势一方的乡土、乡人的极大同情。贾平凹对乡土的浓浓深情,并不是他在为拐卖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也不是在否定城市化本身的文明进步,更不是他没有法律意识的法盲表现,究其原因根本上还在于《极花》中贾平凹面对惨然的社会现实问题,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解决道路。梦中,胡蝶回到城市后,迫于舆论媒体的压力、街坊邻里的嘲讽以及城市文明的冷漠,她又自己回到了圪梁村。胡蝶面临着城市回不去、圪梁村想逃离的两难处境,她的希望之路在哪里?黑亮是幸运的,他有了老婆胡蝶,有了儿子兔子,但日后渐长的兔子以及圪梁村的其他光棍,他们又如何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抢夺了农村的资源、劳动力……给圪梁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圪梁村日渐凋敝,甚至成为历史,与圪梁村同样命运的传统村落又该如何救赎?看似文明的社会却又是如此的不和谐,各种矛盾与现实问题交织,该怎么去解决。《极花》中贾平凹不仅没有给出明晰的救赎道路,甚至连思路方向也没有。
4 结 语
初心未移,笔耕不辍,贾平凹始终密切注视着中国的社会变化,饱含深情地书写乡土。《极花》虽然表面上讲的是一个被拐卖妇女的生活故事,实则展现了贾平凹对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这是他作家敏感天性与责任意识的使然。但《极花》中解救时代痛楚的疗药是什么,作为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面对这些问题,贾平凹似乎也陷入了矛盾与无措中。因而,《极花》这部小说既显示出深刻的现实批判,也存在着一定的无从救赎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