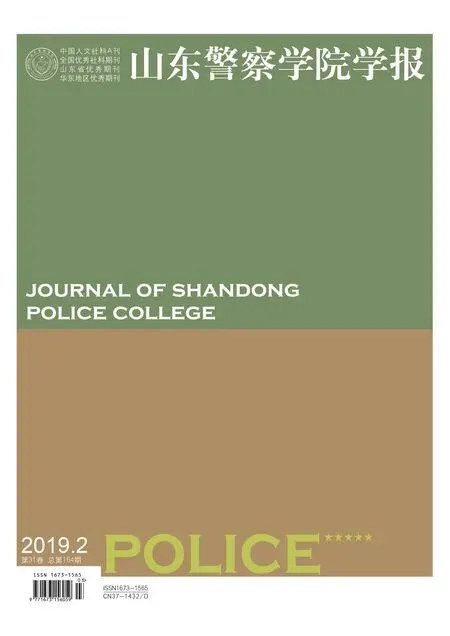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的分流及其启示
李长城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德语中的“分流”(Diversion,意思也为“偏离”、“改变”)来自英语中的“divert”;[1]在拉丁语中,divertere的意思是“驶向旁边、驶向一侧”。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的“分流”指中止正式的惩罚。德国青少年程序分流的刑事策略学自美国的分流项目,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如加入了(司法官的)职权指示等。因此,“分流”这一概念容纳了多种可能性条件下青少年刑事程序因为裁量的原因而中止。[2]
德国司法实务中支撑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法律以《青少年法院法》为主。早在1923年的《青少年法院法》中,德国的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就已经在检察院和法院中开始了中止程序的可能性规定,从1990年《青少年法院法》第一次修订以来,青少年程序中止的可能性得到了扩展。根据这些法律赋予的权限,最近十年来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有了大量的运用。德国的青少年刑法在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一种自己奉行的策略,即在一个刑事指控提起以及刑事判决作出前,程序暂时中止的可能性。德国的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充分展示出一种刑事政策的潮流,即追求青少年犯罪人员一种完全的程序的改变,尤其是法庭审理的避免。[3]在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得到广泛运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于轻微的犯罪,禁止权威的过度使用。法庭审理被视为国家权威的集中体现,如果轻微的犯罪行为也要在法庭审理的话,就会产生国家权威的过度使用。
第二,人们希望通过青少年事件的多元化处理来实现更少的耻辱 。如果一名实施了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而是被使用不固定的措施进行教育,他(她)会产生较少的耻辱感。就此方面而言,程序分流与所谓的标签方式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从根本上期待,如果一个青少年的刑事行为没有经过完整的刑事程序,或者尽早以无固定场所的措施被施以感化,能够避免受到耻辱或者减少耻辱。
第三,减轻刑事司法的负担。首先,青少年通过程序分流减少了刑事照看的费用。其次,它使更快的反应成为可能。通过快速处理冲突以及缩短程序,实现了程序的经济性。最后,青少年程序分流提高了特殊预防的效率。[4]
不可避免地,在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运动遭到了批评。例如,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确定下来的法定原则原则性地存在于青少年刑法中(如《青少年法院法》第2条),但是,有人批评青少年程序分流消除了法治国的保证,因为很多分流都不是正式的程序,而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结束,法律规定的义务被中断,发生的是没有结果的中止(中止成为不了了之)。人们的印象是,国家没有对青少年犯罪作出反应,因此一般预防的作用似乎成了问题。此外,在不同地区的程序中止实践中还存在未同样对待的问题。还有人指出,青少年程序分流存在实际的社会控制扩大的问题(所谓的“网之伸展”)。
一、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原则
德国的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遵循以下四大原则:
1.个别化原则。德国的青少年刑法贯彻的原则之一是个别化原则,即通过逐一找出违法青少年的特殊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矫治,以便成功地避免其再次犯罪。基于青少年刑法的目标和作为个体预防的结果,青少年法院的应对必须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包括其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个人情况,以及适当的惩罚措施(参见《青少年法院法》第18条第2款对刑罚期限的规定)。在分流的框架下,感化措施的指令导向一种合作性惩戒,以共同的行为来推动。合作性惩戒与“刑事程序中的协商”不同,后者主要是缩短程序、着眼于程序经济性。合作性惩戒可以看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合法律性和惩戒的可接受性之间进行调停,促进尤其是考察性的惩戒措施,诸如照顾指示,社会训练课程以及“犯罪人—被害人”平衡。在缓刑的指示和任务中,立法者已经明确地首先提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积极参与(参见《青少年法院法》第23条第2款、第29条第2款以及第88条第6款第1项)。
对青少年的“治疗”以一种弱化国家权威的方式进行。首先,在广泛的相互联系中,常态化的司法实践是,年轻的被告人被用“你”称呼,而他的案件被则作为疑难问题加以讨论。案件处理中用“你”称呼,能够展示出“一种权威的消解”,[注]在德国,“您”(Sie)是较常用的客套的称呼,“你”(du)通常只用于朋友之间的互相称呼。展示出不可能性中的责备。在所有14岁和15岁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你”称呼被广泛地使用,如在被告人和证人被问及是否理解案件时使用。但是对于少女,由于通常在以后的发展中对过往所受到的对待是敏感的,应当被毫无例外地用这种信任的语气谈话。其次,青少年特殊的交流目的也可能反对法官穿戴法袍。在简化的青少年程序中(《青少年法院法》第76条至第78条),法官不着法袍,在总体上是被接受的;但是,必须首先在《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3款的框架内正确适用告诫谈话。除此之外,在调查儿童证人时,法官穿着法袍,这是适当的。很显然,国家权威的弱化有助于被告人作为程序的主体参与和运作。
2.灵活性原则。德国《青少年法院法》中灵活性原则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惩戒的灵活性。《青少年法院法》第18条提供了广泛的惩戒种类以及灵活的刑罚持续期间,与分流的规则一起,使得青少年刑事司法能够对青少年的刑事行为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二,程序的灵活性。程序的灵活性既体现在运用感化措施代替调查监禁,也表现在《青少年法院法》第76条至第78条规定的简易程序上。第三,执行的灵活性。《青少年法院法》第87条对刑罚的执行作出了包括“放弃执行”在内的形式灵活的规定。
3.辅助性原则。根据法律的规定,起诉仅能在一种基于感化原因的形式的行为被认为没有达到效果时才可以提出。因此,起诉只能作为一项辅助性的原则。由于存在非正式的程序的可能性,分流就出现了。[5]
对于辅助性原则的适用必须嵌入从法治国原则(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导出的比例原则。[6]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13款第1条规定了对青少年惩戒的种类和适用,第17条第2款规定了青少年刑罚的形式和条件,因此在对青少年制裁的选择上存在一种等级关系:首先是感化措施,其次是惩戒手段(Zuchtmittel),最后是青少年刑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时适用一种感化措施带来的侵犯程度可能比一种惩戒手段更大。例如,某种感化措施的“照料指示”相比警告以及罚金等惩戒手段,可能带来更严重的侵犯。
具体而言,青少年惩戒的等级关系如下:首先,是从正式程序中分流。在分流里面,首先是自由登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3条),适用于无严重犯罪后果(《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1款)和因感化的中止(《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2款)。其次,在固定的惩罚之前首先是流动的惩罚。在流动的惩罚里面,在压制性质的惩罚前首先是帮助性质的惩罚。最后,在固定的惩罚里面,在无条件的青少年刑罚之前首先是有条件的刑罚中止(缓刑)。
4.不恶化状况原则。《联邦德国基本法》第3条规定了平等对待的原则,但是考虑到青少年经常面临较差的辩护,以及年轻人对于惩戒的敏感性、与成年人相比有更大的悔改性,在德国的法理和判决上已经发展出“禁止在可比较的程序状况下歧视青少年”的原则。[7]在惩戒实践和刑事程序中存在的部分歧视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如调查监禁的命令。针对此,立法者用登记和感化登记中的中止登记(《联邦中央登记法》第60条第1款第7项)以及根据《青少年法院法》第55条权利上诉的限制,确保青少年的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
二、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种类
司法实务中,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包括适用《青少年法院法》在侦查程序中止和提起公诉后由法官中止以及《青少年法院法》以外的其他中止,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1.轻罪的中止。根据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I,作为国家一种完全的宽恕反应,允许程序无结果的中止;但是根据《联邦中央登记法》(BZRG)第60条I,必须进行感化登记。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已经存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条件:程序已经失去了对象,行为人的罪责是微小的,并且程序进行的结果不存在公共利益。决定中止的唯一决定主体是青少年检察官。在2007年,德国适用上述条款处理的青少年人数是90297名。
2.因为实施感化措施而中止。根据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II,在执行社会的或者青少年考察的法定措施等之后包含一种中止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成功地达到“犯罪人—被害人”平衡后,存在一个最终的外部刑法的反应可能性。这些措施的采取可能涉及父母、学校、培训或者雇佣人、警察(这里主要看是否经过授权)或者青少年管理局。在考虑“犯罪人—被害人”平衡时,犯罪人的真诚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II的中止尤其应当指多次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结果,如果之前的程序根据《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I已经被中止了,距离严重的轻微犯罪尚远,并不需要一份青少年的明确的认罪,对此决定作出的唯一主体也是青少年检察官。检察官的这一决定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刑事追诉程序能够随时重新开始。在2007年,德国适用上述条款处理的青少年人数是101338名。
3.由于法官的介入放弃追诉。根据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III,对犯罪青少年可以实施不经法庭审判的、形式灵活的青少年法官的感化程序;此处可能有告诫、指示以及口头宣布的任务。就此而言,这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刑法反应。如果根据《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III,法官最终作出了决定,那么青少年检察官的追诉行为也随之中止。不过,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认罪,检察官在此有必要发布一种类似法官的指示或者命令措施,而不必提起指控。在此情况下,法官会提出建议,而检察官遵循其建议并发布相应的指示或者任务。这种中止具有有限的法律效力。在2007年,德国适用该条款处理的青少年人数是9171名。
4.提起公诉后由法官中止。在检察官已经提起指控之后,即在中间程序和审判程序中也能发生程序的中止。根据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47条,在青少年检察官的同意下,允许青少年法官在如同《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调查程序中实质的同一联系下中止程序。在2007年,德国适用上述条款处理的青少年是48397名。
5.《青少年法院法》以外的程序中止。德国《青少年法院法》以外的程序中止主要是依据《刑事诉讼法》、《麻醉品管理法》的中止以及地方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程序分流实践。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 款中止。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基于事实的或法律的原因,无条件地优先适用中止。《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规定,检察官要让犯罪嫌疑人知道,如果他正在被进行这样的调查或者针对他的羁押令已经宣布;以及检察官已经就一项告知提出了请求,或者有关事项的公布存在明显的特殊利益,此时检察官可以中止程序。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款的中止也是因为《青少年法院法》第3条中规定的刑事责任尚未确定。
(2)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中止。《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如果犯罪人的罪责被预见是轻微的,而且公诉不具有公共利益,在中间程序管辖法院法官的同意下,检察官可以中止程序。如果一项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没有遭受最低限度的刑罚的危险,法官不能同意进行审理。只有当青少年检察官出于预防的原因,在感化登记册登记是必须被考虑时,则按照《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1款来处理。《联邦登记法》第60条第1款第7项在恰当和必要时直接适用。[8]除此之外,《刑事诉讼法》第153条通常首先作为更少负担的措施优先使用。当然,此处法官的同意是必需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也与《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1款不一致。
(3)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 中止。如果《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3款列出的措施并不“适合”,则在《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3款相近的情况下,能够适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与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1款和第2款的中止程序不同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第2款的规定只具有辅助意义。《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第2款规定,在公诉已经提起之后,直到审判结束,即在案件事实被最终确定之前,法院可以在检察官和被告人的同意下,暂时中止程序,与此同时分配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第1款第1项(赔偿因犯罪行为的结果造成的损失)和第2项(赔偿因犯罪行为的结果造成的损失)规定的任务和指示,《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第1款第3至6项也相应适用。其中,法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作出的决定以裁定的形式发布,该裁定是不可争辩或反驳的。
《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第1款规定,在中间程序中,在管辖法院和犯罪嫌疑人的同意下,检察官如果能够适当地分配犯罪嫌疑人一定的任务或指示,刑事追诉的公共利益因此得以消除,并且与该罪行的严重程度不相抵触的情况下,那么检察院能够暂时中止公诉的提起。在此情况下,检察官通过分配任务和发布指示来中止程序,在解决思路上尤其值得考虑。
但是,在《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 与《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3款之间的适用关系上,也有人表达了疑虑。原因在于,根据《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3款,可能存在一个不合法的认罪,而据此来绕开《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的适用。因此,以作出供述作为程序中止的条件值得怀疑,并且在《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变成了一个好的理由展示出来。由此看来,立法者在《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3款中的中止程序要求预定的措施与供述是同时的,明显是一种违背了法律协调性的设计。[9]
(4) 因为《麻醉品管理法》第31 条a 的中止和因为《麻醉品管理法》第38条第2款和第37条第1款的放弃追诉。随着1992年9月生效的德国《麻醉品管理法》的修改,《麻醉品管理法》第31条a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第1款第2项的任务分配,以检察官中止而结束刑事程序。根据立法的原因,进一步扩展的中止可能性应当通过检察官在麻醉品消费者程序中完成。[10]这些中止的可能性首先考虑了优先于《青少年法院法》第45条和第47条适用的特性。
(5)警察的分流。在警察侦查的实践中,经常运用警告、告诫,这种“威胁”足够作为国家的反应。但是,有人对警察通过告诫以及建议判以感化措施明确结束刑事程序的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违反法治国原则的。理由在于,警察分流模式意味着权力从检察机构以及法院向警察的完全转移。不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罪责或者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而是由警察来施加惩罚,这不仅违反了法治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而且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尽管犯罪嫌疑人不需要遵从警察的“建议”,实际上青少年却会被施加一种他们很难经受得住的压力。在此,人们必须看到一种危险,即在可能中止程序的指示以及特别是以正式的青少年司法程序相威胁的情况下,警察掏出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在一些地区实施的分流方针中,司法终结权转移给警察成为潮流,并且也种下了混同调查与最终惩罚的危险。在1999年巴登州召开的德国各州司法部长会议上,与此相关的一致决议是,“司法部长们分享了这一观点:在警察的第一次调查谈话中,常规解释已经能够对青少年产生影响,这在很多案件中是有意义的。就通过分流的决定能够产生预先判决而言,应当要求案件的负责人负有向检察官报告的义务。”[11]
(6)青少年学生法庭的中止。在德国阿沙芬堡的犯罪学生矫正项目中,学生因其青少年犯罪行为受到的惩罚在检察官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矫正,在一个关于该行为的对话框架下,与犯罪嫌疑人就一项矫正措施的确定达成合意。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模仿项目。通过其他青少年解决冲突的思想以青少年学生法庭的形式诞生在美国,并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自主处理冲突的萌芽在青少年中是如此的积极,如通过学生冲突规则的指引。
与常规青少年法相比,这种不严肃的法官角色显然偏爱不严肃的刑罚需求。在青少年学生法庭中按照规则的惩罚下降得很厉害。青少年学生法庭作为补充,能够缩小刑事程序的象征意义和严肃性。但是,也有人指出,刑事程序应当由专业人士掌握。[12]
三、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启示
德国的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制度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当然相关的改革还远未结束。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实践揭示出了青少年刑事司法的一些基本规律,其中一些成熟的司法理念以及实务经验值得我国充分借鉴。笔者认为,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给予我国的有益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青少年刑法的首要目标应当是防止青少年再次犯罪。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2条明确提出, 青少年刑法适用的目标首先是防止青少年或尚未完全成年人再次实施触犯刑法的行为。因此,青少年刑法的适用不以惩罚犯罪作为首要目的,而要对青少年进行保护,避免其再犯,防止其更深地跌向犯罪深渊,毁掉人生。毕竟对青少年的保护也是对社会的保护。
我国青少年刑事立法也应当把防止青少年再次犯罪明确列为首要目标。一个特别的原因在于,我国青少年服刑人员再次犯罪的比例较高,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修复因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刑事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对青少年采用什么方式处理,以及这种处理方式所产生的后续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人们必须注意到,青少年犯人如果改造不好,将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原因很简单,普通成年犯人刑满释放年龄很可能已经在40岁之后,而年轻的青少年犯人刑满释放、进入社会很可能只有20多岁,比成年犯人多出20多年的时间。
第二,我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扩展。首先,应当把14岁以下、12岁以上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纳入矫治范围,规定必须进入工读学校或者感化机构接受矫治。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14岁以下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时期;另一方面,14岁以下的罪错少年如果要进入工读学校矫正,必须取得家长的同意,但是这些家长并不愿自己的孩子进入工读学校,因此实际上这类少年并未接受任何矫治措施。在家庭、学校、公安机关“三不管”的情况下,这类少年通常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次,应当把18-21岁的人也纳入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的适用范围。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年虽然已经成年,但是由于刚过18岁不久,在大脑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事物的辨别能力上还未充分发育成熟,有的只因一时冲动酿成大错,实际上具有较好的可矫正性。[注]德国《青少年法院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是实施了可能受到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的不满18岁的青少年以及实施行为时18岁以上21岁以下尚未完全成年人。青少年罪犯短期刑的负面效应中最突出的无疑是标签效应,青少年容易“破罐破摔”,发展成为常习惯犯。因此,应当把18-21岁的青年纳入刑事程序分流的范围,在实现有效矫治的前提下,以不产生法庭判决的方式结束案件。对我国大量18-21岁的青年人适用程序分流,显然既能提高特殊预防的效率,又能减轻刑事司法的负担。
第三,对青少年进行惩戒的同时给予其切实帮助,贯彻“解决问题式司法”。在德国,为了实现“防止青少年再次犯罪“的目标,以及考虑到父母亲的教化权,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时首先要考虑感化。青少年能够从司法处理的可接受性中获得一定希望,即刑事分流程序能够变为一个“治疗的请求”。国家惩罚的威胁并不被掩盖,而青少年对国家的信任也没有辜负。在国家对青少年的惩戒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国家相关机构对青少年的帮助、关怀和照料。青少年也能够通过多种司法处理可能性中感受到国家的防卫。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落实对青少年的矫治和帮助。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有心理疾病、价值观畸形、家庭管教以及情感缺失、缺乏社会谋生技能等。在对犯罪青少年进行惩戒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探寻其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必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式”司法要求司法官员不是只简单地套用法律条文,而是聚焦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和社区的问题,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 “解决问题式司法”关注公共安全,[13]将司法工作延伸到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提高了罪犯和服务提供者的责任。[14]
第四,我国应当通过制定统一的立法,建立灵活、顺畅的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机制。德国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是多法律、多机构体系化运作的结果。例如,德国相关的法律除《青少年法院法》和《刑事诉讼法》之外,还包括《青少年保护法》(JugendschutzG)、《青少年考察法》(SGB III: Kinder u. Jugendhilfe)、《青少年媒体保护法》(Jugendmedienschutz—Staatvertrag)、《联邦教育促进法》(BAföG)、《青少年工作保护法》(Jugendarbeitsschutz)以及《职业培训法》(BerufsbildungsG);青少年司法相关的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则包括青少年感化机构、青少年管理局、青少年检察官、青少年法官等。我国目前关于青少年司法的立法数量少,缺乏体系性,各有关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也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于各地自行摸索试行的状态,缺乏可持续性,这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青少年刑事司法工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我国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来建立多机构之间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势在必行,并且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建立以下青少年刑事程序分流机制:首先,在案件由警察处理阶段,可以通过警察附条件告诫和强制进入工读学校或者感化机构的方式分流。其中,警察实施告诫时,可以同时命令罪错青少年实施一定的行为(如进行道歉、赔偿、参加社会劳动等),同时少年及其家长(或监护人)需要写出书面保证,警察同时将处理结果向同级检察机构报告,以便接受监督。其次,在案件由检察机关处理的阶段,青少年的程序分流主要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主,所附条件主要是在感化机构得到成功矫治。再次,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之后,在案件的审理阶段也可进行分流。法官可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附条件地中止案件的审理,同时要求被告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如进行道歉、赔偿、参加社会劳动等)。最后,对进入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的青少年实行不定期刑,根据其矫正的状况相应适用缩短刑期、中止执行等。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程序分流机制是可逆的,如果青少年的感化和矫治未达到实际效果的,应当恢复刑事追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