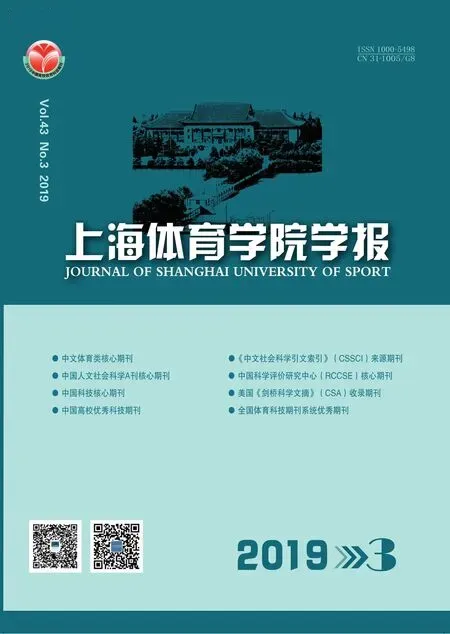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问题的理论展开和中国语境
王理万
(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北京 100088)
体育运动在建构、维系和强化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学术命题,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晚近才获得重视。1945年12月,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1]在评论苏联和英国足球赛时,首次指出竞争性体育赛事的政治含义:“国际体育比赛是对战争的直白模仿,其中最重要的并非参赛者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代表的整个国家。”这是关于体育和政治关系的最早论述,隐含了体育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意识,但尚未明确使用国家认同的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才开始重视体育运动在建构国家认同、巩固民族主义、去殖民化等议题中的特殊地位,把体育运动放置在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语境下,赋予其新的政治意义[2]。
在中国学术界,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现实中,体育运动在争取国家荣誉、维护国家利益、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等方面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作为学术命题还非常新颖。孙睿诒等[3]认识到,“优秀竞赛成绩能够集中展示综合国力和民族优越性,最有利于唤起民族情绪,提振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体育民族主义的发展、媒介体育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体育与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关于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理论研究尚未完全展开,以下问题有待系统解答:① 作为体育政治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为何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直到晚近才被重视起来,如何厘清二者的理论连接和内在逻辑?② 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在实践中如何互动,二者存在哪些契合之处和互动形态,体育民族主义是否存在负面作用?③ 如何在中国语境中定位体育运动对于国家认同的作用?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全面梳理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理论脉络,并结合中国国情,讨论体育运动对强化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
1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理论框架
中西方在研究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时,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理论被反复引述——这2种理论都揭示了国家认同的主观性和可塑性,国家和民众共同参与和塑造了国家意识和政治认同。Smith等[4]提出,多数体育运动的竞争性、超语言性(supra-linguistic)和平民性特征,使其成为表达群体性身份(group identities)的最好媒介。体育运动能够使人们秉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念,构成本尼迪克·安德森语境中的“想象的共同体”。艾瑞克·霍布斯鲍姆[5]进一步提出,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那些看似古老的传统,其实都是当代的人为制造。在现实中,多数国家也在有意或无意地确立了能够体现自身传统和特质的体育运动,并使之成为国家认同和公众参与的载体。
需要指出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和“传统的发明”等理论,仅能为理解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提供背景知识,但并非完整的理论框架。系统解释二者的关系,需要把它们放置在时间、空间、政治和对象的4维视角下:① 在时间维度上,需要区分现代体育和古典体育;② 在空间维度上,全球化构成了当下论证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关系的空间背景;③ 在政治维度上,体育运动具有多层面的政治功能,存在不同体育运动的政治话语;④ 在对象维度上,体育能够为现代社会日趋“原子化”的个体塑造出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
1.1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时间框架在体育运动史和政治思想史中,“体育古代起源说”和“体育近代起源说”长期对峙,据此可以粗略区分为“古典体育”和“现代体育”2种基本类型[6]。它们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对身体的“政治启蒙”。在古典时期,基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形成了身体与精神的“二分法”,身体仅仅被视作精神的载体,“身体遭到贬抑,有关身体的论说更多地是为了证明精神的存在”[3]。甚至在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中,还认为无节制的体育运动违背了清教的“禁欲原则”[7]。在现代语境下,身体与精神不再处于对立和屈从的状态,身体的独立价值得以凸显,身体的偏好也得到了认可和尊重。现代体育获得了独立的价值空间,并被作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发挥其特殊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体育还意味着国家对于身体的规划和控制。体育成为国家实现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的手段。国家对于体育的管理,一方面表现为对身体暴力的控制,确认或建立起一套体育规则,积极介入民众的身体规训,并抑制其中的暴力因素。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8]所指出的,古典体育虽然也认可人的价值,但是放任身体暴力,“在比赛活动中对身体暴力的容忍程度也高于我们,为了取悦观众,他们反感人们互相伤害甚至残杀的程度相应地比我们要低”。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任务,体育被广泛运用于塑造国家认同。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新型社会制度国家、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急需一种常态化、竞争性、仪式性和团体性的活动,来激发和维持国家认同。现代体育运动恰恰满足了上述标准,因而被纳入国家议程,用来改造民众的身体、强化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1.2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空间框架全球化成为当下讨论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空间背景。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强势展开,并经现代媒体技术和全球性体育产业链条,形成了西方主导的体育全球化。这种趋势在正反两方面对国家认同形成了影响。
一方面,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为近代以来国际法所倡导的“主权平等”理念提供了现实印证,这有利于形成国家认同。“足球世界杯赛和奥运会为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平等竞技的平台,这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其他政治或者文化组织无法比拟的价值”[9]2。事实上,国际体育比赛体现的主权平等、永久和平、公平竞争、规则透明的“国际政治乌托邦”,满足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期待和想象。也正是由于现实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平等,国际体育赛事的公开性和平等性才显得弥足珍贵,“人们更愿意承认一个想象空间的存在,在这个空间中,中小国家对大国的体育胜利唤起人们对乌托邦式的世界新秩序的想象”[10]。在这层意义上,体育全球化支撑起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育竞争,从而强化了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体育全球化也带来了“识别障碍”,国家认同建立在对其所属国家清晰且明确识别的基础上,但是体育全球化可能会造成在国家认同上的困境。具体表现在:① 体育移民(归化运动员)成为当代国际体育界的普遍现象。“从短期看,有助于快速提高成绩、鼓舞人心、凝聚支持;从长远看,归化运动员对国内同行的教、传、帮、带作用亦不能忽视”[11]。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若多数民众无法接受不同渊源的运动员代表国家出战,则无法达成国家认同的效果。② 在足球、篮球、冰球等项目中的“无国界运动员”,对传统的“体育无国界,运动员有祖国”的认识形成冲击。③ 一些新兴的体育赛事,脱离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机制。如一级方程式赛车(F1)就主要是由汽车厂商参与,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队”有明显差别;有着悠久历史的美洲杯帆船赛越来越呈现国际化的趋势[12]。④ 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建立,民族国家向地区性国际组织让渡部分权力。民众(特别是精英分子)也开始形成对某些地区性国际组织的认同,这与传统的国家认同构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欧盟组织的泛欧洲运动会、欧洲奥运代表队,欧盟赞助的欧洲游泳俱乐部赛等,都是欧洲性质的比赛[13]。
体育的全球化趋势,已经从心理和制度上对国家认同形成了挑战。尽管如此,体育全球化趋势还远远未达到消解主权观念、突破国家壁垒的程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体育运动仍将持续强化国家认同。
1.3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政治框架在研究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时,难以回避“体育政治化”问题。现代体育区别于古典体育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对体育运动的介入和控制。在现实中,体育运动的政治目标是多元的,包括提升公民健康水平、维持良好社会秩序、巩固国家认同、实现社会动员等。Houlihan[14]指出,国家介入体育的时间非常晚,早期体育运动对于国家是非常边缘化的利益(marginal interest),但是随着体育运动价值的凸显,国家开始介入体育运动。
具体而言,体育政治化的话语体系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① 体育的阶级话语,即把体育和阶层身份、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有些运动被视为贵族或精英阶层的运动,有些运动得到了中产阶级的青睐,还有些运动则主要流行于劳工阶层。Pereira[15]指出,足球之所以在巴西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如此流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足球运动不需要特殊的装备和服装。② 体育的国族话语,这与建构国家认同有直接关系。在相关研究中,体育民族主义(sportive nationalism)已经成为专用词汇,显示了国族话语的强势地位。③ 体育的国际话语,就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体育运动的整体发展。现有的国际体育赛事、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体育标准为这种话语提供了现实基础。上述3种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阶级话语就一定程度对冲了国族话语,彰显了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殊;国际话语也会对国族话语形成稀释,即用人类利益、永久和平、责任连带等充满“政治正确”的词汇冲击体育民族主义。尽管如此,国族话语的主流地位难以撼动,主权国家之间的体育竞争仍将是常态。
1.4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对象框架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最终需要落实到参与对象(受众)的问题上,即追问“谁的体育运动,何种国家认同”。该问题的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国家应动员尽量多的公民参与体育运动,为公民行使体育权利提供制度保障,才能形成以公民为主体的国家认同。不过,公民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已经成为常态,在公民和国家之间横亘着选举制度、官僚体制、利益集团等参与屏障,使公民感觉与国家愈发疏离,缺乏政治上的存在感、参与感和支配感,削弱了国家赖以存在的认同基础。体育运动恰恰在政治冷漠的总体背景下,架起了连接公共与私人的纽带。Jaksa[16]对此指出:“国家性体育运动扮演了共同体(common thread)的角色,把社会中的公民个体编织起来——这样的体育项目在各国都有,如加拿大的冰球、新西兰的英式橄榄球、印度的板球、中国的乒乓球、美国的美式足球等,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运动项目。”
体育在联结公共和私人领域、克服政治冷漠、维系国家认同方面,有其固有的界限。在现代国家中,国家不能强迫公民参与或者支持某项体育运动,只能通过舆论引导、政治动员和软性激励的方式,推广某项体育运动,特别是舆论引导对于公民树立国家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体育运动固然可以激发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但若缺少媒体作为中介,其效果也肯定大打折扣。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媒体的舆论动员和报道技巧,能够成功建构起关于特定体育人物的“英雄形象”,这类报道兼顾私人(娱乐性)和公共(政治性)的需求,契合了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媒体深入介入体育运动,也可能产生过度商业化的后果。“媒体已经把体育变成了全球性的超大生意,报道时间、纸媒版面、体育明星、运动队及其观众都被纳入其中,呈现出严重的金钱化(cash dimension)”[17]。因而,从建构国家认同的角度而言,在发挥媒体舆论动员效果的同时,应防止体育报道的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平衡受众偏好和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
2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互动机制
2.1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契合国家认同存在多元建构方式,民族宗教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国家标志符号等被广泛用于强化国家认同。在“祛魅”的当代世界,国家认同并未完全蜕去其神圣外衣,兼具非理性色彩(情感因素)和实用主义的面向。Tomlinson[9]100-101指出,国家认同往往呈现出“双重面孔”(Janus-like form):一方面是在文化上“往后看”,从历史中寻求舒适性、稳定性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在现实上“向前看”,追求现代性的物质利益。与之同理,经由体育运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也同时存在理性和情感的因素。
从理性的角度而言,通过体育运动建构国家认同意味着国家需要着力进行体育建设。这就要求国家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满足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多元需求。用权利话语表述,“体育权利包括了防御权、受益权和客观价值秩序的内容,其中防御权对应国家的消极义务,受益权对应国家的积极义务,客观价值秩序对应国家在体育领域的制度性保障”[18]。质言之,国家对于体育运动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公民对待国家的权利诉求是匹配的。以权利话语为纽带,联结起宏观层面的国家目标和微观层面的公民个体利益。
从情感的角度而言,公民和国家之间不再是“需求—供给”的利益关系,而是价值共同体。公民通过参与、体验和观摩体育活动,在有意和无意间形成了对于国家的认可和效忠。
一方面,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存在形式上的契合,使得体育运动能够有效激发国家认同。① 仪式性:体育运动往往利用仪式感极强的开幕式、颁奖典礼、运动规则等形式,不断强化参与者的国家意识。参加体育赛事,能够在仪式和情感层面上维护“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19]。② 竞争性:体育运动重在竞争和对抗,特别是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各自代表不同国家,把体育赛事转化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竞赛扮演了“模拟战争”的角色。赛场成为国力竞争的战场,直接指向了参与者和观众的国家认同感。③ 团体性:多数体育运动具有团体性的特点,需要成员协作才能取得理想成绩。国家认同也具有很强的团体性色彩,公民个体差异被最小化,突出内在的共同性和利益一致性。④ 英雄塑造:一些成绩卓著的体育明星被塑造成为“体育英雄”,进而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符号和资源。塑造和演绎体育英雄的本质在于构建“同一性”,即创造受众和英雄之间的超血缘联系,使双方以国家为纽带,共享荣誉感和忠诚感。
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也存在实质性的契合。① 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在构成要件上高度类似。Houlihan[20]认为,国家认同的特征包括领土主义、政治参与、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在这4个方面,体育均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比如国家间的体育竞赛就是“领土主义”的体现,将日常生活中逐渐淡漠的政治参与转化为对体育的激情,强化了关于公民身份的自我体认。② 体育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和吸纳公民政治认同发挥基础性功能。
在营造体育文化方面,现代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打造自身代表性体育运动,悄然完成了政治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建构。董进霞等[21]指出:“当我们看NBA时,我们记住了美国;我们看曼联时,我们记住了英国;我们看环法自行车赛时,我们又记住了法国——这种由体育赛事无形中渗透出的国家文化不正是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和力量吗?”
2.2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3种形态国家认同的概念在政治学领域有复杂的定义和类型划分。政治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22]根据国家认同的起源和形式,把其分为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拒斥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计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3种类型:① 合法性认同是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② 拒斥性认同是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③ 计划性认同是指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任何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需要说明的是,曼纽尔·卡斯特并没有将这3种类型截然分开,而是认为3者处于转化的动态过程,比如拒斥性认同可能会引发一些计划,成长为支配性地位,甚至最后成为合法性认同。此种分类有助于理解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发展阶段,体育运动对建构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在拒斥性认同方面,体育运动主要发挥了去殖民化的功能,促使殖民地从宗主国的母体中剥离出独立的国家认同。以澳大利亚的板球运动为例,澳大利亚与英国开展板球比赛,使板球一度成为澳大利亚的国家象征[23]。在澳大利亚摆脱殖民地身份并确立自身独立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以板球运动为载体,将宗主国(英国)确立为竞争者,赋予板球运动以政治内涵[24]。由此可见,体育运动对前殖民地挣脱与宗主国的精神和文化“脐带”,创立自身独立的国家符号体系,建立稳定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国家认同把宗主国的体育运动作为参照系,具有明显的拒斥性,达到了去殖民化的政治效果。
在合法性认同方面,体育运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制度优越性的重要途径。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竞赛,“体育成为冷战时期国家政治立场风向标,体育的选择已经成为政治盟友的选择”[13]。在这种背景下,冰球在凝聚国家意志、体现制度优越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红军(Red Army)冰球队的持续取胜就被视为“苏维埃制度最好的证明”[25]。因此,苏联把冰球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举全国之力培养冰球运动员。在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上,苏联冰球队爆冷负于新成立的美国队,对苏联的国家自信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一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冰上神话”,此后被西方各国传颂,成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明”[26]。类似的例证也包括了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之间的体育竞赛,“在冷战时期,东德和西德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奥运会金牌”[27]。
在计划性认同方面,国家有意识地以体育作为媒介,引导建立和强化国家认同。这种模式曾经作为殖民者对殖民地进行文化同化的工具,目前多见于多民族国家、多种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殖民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就曾把体育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平等友善的假象[28]。在新兴国家中,体育运动也被频繁用于塑造国家认同,比如韩国积极把跆拳道塑造成民族认同的工具[29],印度把曲棍球树立为寻求民族尊严和身份、确立体育民族主义的重要资源[30]。在多民族国家和多种族国家中,政府更是有意识地通过体育运动达到民族融合、种族和谐的目标,使不同的民族、种族、地域和阶层的公民迅速凝聚起来,消弭国内矛盾,强化国家认同。由此,计划性认同较之于拒斥性认同、合法性认同所适用的范围更广,也最能体现国家对于体育运动政治效果的清晰定位和有效使用。
2.3 体育民族主义的潜在负面作用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存在契合,并在实践中展开有效互动,但这并不能否定在特定条件下体育运动也会给国家认同带来负面影响。并非体育运动本身对国家认同产生负面作用,而是体育运动所附带的意识形态因素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对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产生消极作用,甚至走向国家认同的反面。
一方面,体育运动既可以作为建构政治认同的资源,也可能被分离主义所利用,成为稀释、消解甚至对抗主流国家认同的工具。上文所论及的殖民地对抗宗主国的体育策略,与之具有共通的逻辑,不同的是后者在“去殖民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政治正当性。不可忽视的是,体育民族主义有可能削弱和对冲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甚至成为分离运动的基础。在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过程中,或者统一国家内的异质地区(heterogeneous region),往往通过发展本地性的体育项目、追求在体育竞赛中战胜宗主国等方式,把特定体育项目塑造成为本土主义的运动形式。如爱尔兰在1884年成立了“盖尔运动协会”,旨在抵御英式体育的冲击,发展爱尔兰传统的盖尔运动[31]。在统一国家中的政治异质地区,分离主义势力也往往会通过推广本地化的体育运动,与国家主流运动形成区隔,从而推动狭隘的体育民族主义,对国家统一和稳定形成了现实威胁。
另一方面,体育民族主义容易走向极端化,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上述中的“盖尔运动协会”在历史上就被作为典型的极端爱尔兰主义组织。韩国也是体育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这既有长期殖民历史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客观原因,也有政府有意推动和扶持的主观原因。这种体育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攻击性和封闭性,容易导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32]。因而,体育民族主义如果超越必要的限度,很容易走向狭隘偏私的极端,对国家利益、荣誉和形象带来消极影响。
各国应善用体育运动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特殊作用,避免体育民族主义带来的消极后果,警惕分离主义对体育运动的操纵,彰显体育精神和国家认同的正面互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体育运动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了政府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现实动力,但也容易走向“金牌战争”(gold war),把国际体育赛事异化为奖牌甚或金牌之争。这种把体育异化为“金牌战争”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建构“计划性认同”,急需体育竞赛的优异成绩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由于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限制,“在奥运会赛场上,发达国家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难以负担这场‘金牌战争’,越来越成为奥运会的看客”[33]。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体育和国家实力的直接联系,同时提醒发展中国家不应陷入“全球体育军备竞赛”(global sporting arms race)的怪圈,而应致力于发展体现本国特色、凝聚本国认同的体育运动,平衡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之间的关系,建立适合本国的体育发展模式。
3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中国语境
3.1 体育运动建构国家认同的中国背景相对于一般国家而言,中国面临着繁重的国家认同建构使命。中国历史上曾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有着深重的“国耻记忆”,也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民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希望经由体育促成国家认同、证成国家力量、推动国家融合和发展的强烈愿望。①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把塑造健康强劲的国民体格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特别是“东亚病夫”的标签激发了中国人民探索强国强种之路,改变政治和身体上贫弱地位的决心[34]。② 中国作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体育运动可以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加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各民族团结友好的总体趋势下,中国也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威胁,“在一些国际大赛中常常掺杂着民族分裂主义的噪音,不但影响赛事的正常进行,还通过混淆视听危害国家形象”[35]。③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体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体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用体育运动证明自身巨大的发展成就和潜力,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由此,中国的多重历史背景和政治特点决定了体育在国家议程中的重要位置,也决定了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深度关联。
中国领导人对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贺龙元帅曾指出:“体育工作者今天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这光荣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的健康,增强人民的体质,以便全国人民更好地、有保障地进行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体育工作必须结合并服务于国家的建设”[36]。这意味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运动就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契合起来,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体育运动发挥了增进人民体质、提振爱国热情、凝聚民族意志的作用,体现了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爱国敬业、拼搏超越的精神,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内在契合。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从体育大国逐步走向体育强国的历程,“女排精神”“乒乓精神”“体操精神”等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竞技体育有着凝心聚力的强大感召力,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敢于争先的拼搏精神、扬我国威的民族自信,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37]。因而,中国体育在促成国家认同方面,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具有一致性,符合上文梳理的体育运动和国家认同的理论框架和互动机制,并且是成功实践体育精神的典范国家。
3.2 体育运动建构国家认同的中国目标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关于体育的政治功能,特别是体育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特殊作用,形成了一系列新判断、新论述。主要包括:① 体育运动是实现人民健康和全面小康的必要途径,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国家体育总局在2016年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体育在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方面的独特作用,继续推动内地与港澳体育界的交流互动,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② 体育运动是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关键步骤,这是建构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听取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在北京举办一场全球瞩目的冬奥盛会,必将极大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于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③ 体育运动是发展国家外交、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方式,也直接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青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勉励青年运动员“放松心态,甩掉包袱,赛出水平,展示风采,让外国朋友看到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力”。在其后一系列的重要外交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体育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体育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在文化上彼此欣赏、心灵上相亲相近。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复合性、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综合体,承载了更加丰厚的理论内涵。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38]。虽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针对的是民族和宗教问题,却对理解中国国家认同的结构和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新时代,中国体育运动强化、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也要在“5个认同”的框架内展开,通过体育运动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政党观和制度观。
(1) 通过体育运动加强对于伟大祖国的认同,正确认识个体和国家的关系,把个体价值蕴于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体育运动在国家认同方面的功能,不仅包括优异的体育成绩可以增强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可和信赖,也包括促进政治的社会化,使公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39]。
(2) 通过体育运动巩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确立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认识。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构成、有高度政治认同、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体育运动能够增强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体认,分享共同的民族荣耀感和归属感,从而避免了民族隔阂和矛盾。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这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价值,解构全球趋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主动消解西方强势体育文化造成的体育认同危机[40]。
(3) 通过体育运动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把体育作为传承、复兴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必要步骤[41]。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下,传统体育文化面临创造性转化的机遇和挑战,由此需要把体育运动与文化传承创新结合起来,通过体育加深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4) 通过体育运动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即通过新中国体育的巨大成就增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认同。新中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追求的强国强民目标,这是形成政党认同(party identity)的事实基础和历史逻辑。体育运动能够充分凝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证明党的领导地位符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待。
(5) 通过体育运动夯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体育事业增进了人民体质,实现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上述5个方面的认同体系,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所强调的,“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42]。
3.3 体育运动建构国家认同的中国路径中国在通过体育运动强化多维度的国家认同时,需要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维护体育精神。2018年3月27日,孙春兰副总理在视察国家体育总局时强调,新时代体育工作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充分挖掘和有效释放体育综合价值,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增强群众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3]。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应作为“体育综合价值”的重要方面,发挥体育在强国和强身方面的功能,提升公民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具体而言,体育运动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可以分为观念、制度和行动3个方面。观念塑造制度,制度决定行动。
(1) 在观念方面,需要对体育运动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特殊作用有清晰的定位。特别是意识到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下,体育运动对于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重要价值,即达到“体育强国”和“体育强民”的双重目标[4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经由体育运动强化国家认同并不必然导向体育民族主义,而是旨在培养积极自律的现代公民。对内应尽快把体育比赛的定位由“为国争光”转到“国家认同”,“不再单纯地追求金牌,而是努力地去构建一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提升公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为目的,以爱国主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体育文化”[45]。对外应把体育运动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超越民族主义的狭窄叙事框架和心理结构,着重阐释体育运动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意义,为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铺垫,也为建构更加开放包容的国家认同提供出路。
(2) 在制度方面,应建立起促进国家认同的现代体育制度。① 在宏观层面上,应平衡政府规划、商业运作和全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举国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其长远之路是以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以制度保障社会投资的利益预期,人才培养体系逐步社会化、市场化,体育竞赛项目职业化,最终形成以社会投资为主、政府制度扶持、市场配置资源、个人积极参与的全民发展体育的体制”[46]。② 在中观层面上,应设立国家级体育荣誉制度,通过体育荣誉吸纳政治参与、凝聚国家认同。“荣誉制度可以强化公民与国家的政治联系,将市民生活的热情转换成为国奉献的勇气”[47]。2015年颁布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中,明确了“国家设立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③ 在微观层面上,通过体育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要求国家建立、健全体育权利保障制度,落实公民参加体育运动、享受基本体育公共设施的权利,为现役和退役运动员提供合理保障。唯有通过落实各种制度保障,才能不断强化公民个体和国家的联系,使运动员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3) 在行动方面,政府、集体和个人均作为重要的行动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家认同。①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应善用体育运动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功能,发挥其正面效果,着力控制体育民族主义中的消极影响,把弘扬体育民族主义和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结合起来,避免体育民族主义的泛化和极端化,警惕体育运动被分离主义势力所利用。在容易滋生分离主义的地区,更应有意识地加强体育建设,促进各地间的体育文化交流,以此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② 从体育职业行为的角度,健全体育团体的内部自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体育运动固有的价值,严厉制裁使用兴奋剂、收买裁判员等违法行为,为体育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致力形成更加稳定和理性的国家认同。③ 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无论作为普通公民还是运动员,均需要意识到自身健康、职业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积极融入参与国家的健康推广和体育规划,通过体育培养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使自身价值与国家持续发展深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