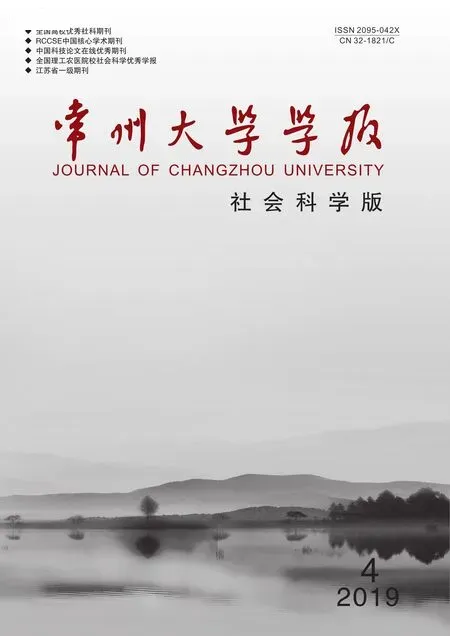文化视野下的托尼·莫里森与莫言比较研究
吴海芳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小说家,年近不惑,才发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但从此之后,她文思泉涌,又先后发表了《所罗门之歌》《秀拉》《柏油娃》《宠儿》《爵士乐》《天堂》《爱》《恩惠》《家》等九部长篇小说。1993年,因“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1],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黑人作家,被阿特伍特视为“无论在自己时代还是任何其他的时代都堪称杰出的美国小说家”[2]。莫言,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获奖的理由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莫言因此被视为“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3]。
将托尼·莫里森与莫言的作品并置,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两者之间寻找共同点。因为从创作的内容看,莫里森作品关注的是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种族和文化问题,而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则聚焦作为中国农村缩影的高密东北乡。空间、文化抑或心理的距离使得两位作家笔下的世界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文学就具有这样的魅力:它能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疆界呈现出某些普遍的共性。因此,笔者将以莫里森与莫言的作品为考察对象,尝试在文化视野下分析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化态度、文化表达及其文化建构的价值。
一、文化自信的张扬:溯源民间文化
基于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作家在整个文学表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褒或贬,自信或自卑。考察莫里森和莫言的作品,读者可以发现他们对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及其内容的挖掘、利用、改写和创新不仅使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陌生化艺术效果,也鲜明地体现出他们对各自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有研究者指出,文化自信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后的状态,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结果[4]。莫里森和莫言弘扬文化自信的起点就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提到民间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会讲故事的老祖母”。无论对于莫里森还是莫言来说,不管其童年时期物质有多么匮乏,他们都有幸以倾听的方式从长辈处接触到无数的民间故事,这为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插上了神奇的翅膀,并为其日后的创作储备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在莫里森的作品中,有黑人会飞的传说、隐藏着家族历史秘密的歌谣、生死越界的对话、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神秘的丧葬仪式,等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形式反映了黑人族裔的集体梦想、生存智慧和生存意志,是黑人族裔独特风貌的典型再现。以《宠儿》为例,小说讲述了黑奴赛丝与被她杀死的亲生女儿的鬼魂纠缠的故事。小说的叙述完全打破生死界限、人鬼界限,使婴儿的鬼魂附身于一个年轻女子,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超自然的鬼怪故事为莫里森的小说平添了几分神秘恐怖的色彩。我们眼里的某些“迷信”现象和活动,在非洲人的文化里却是理解其世界的重要方式和内容。莫里森曾说:“活人与死者的鸿沟不存在,现在与过去的鸿沟不存在。”[5]而神话是人类经历的隐喻。《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的家族是飞人的家族:他的曾祖父只身飞回非洲老家;他的姑姑派拉特是一位“不用离开地面就能飞翔的人”;奶娃继承了祖先的飞行能力,也成为一位“驾驭大气的高手”。飞人神话表达了黑人对自由的渴望与梦想。莫里森把非洲祖先文化、黑人民间文化和西方经典文化绝妙结合,从而赋予作品非凡的绚丽色彩。这对恢复黑人庄严的民族原貌、激发黑人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6]18。
莫言的创作同样受到民间故事的深刻影响。他曾在演讲中提及,长辈及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里,死人与活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动物、植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许多物品,譬如一把扫地的笤帚,一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借助某种机会成为精灵”[7]315。莫言的家乡距离撰就《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蒲松龄的故乡,大概“两三百里”。莫言曾说:“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因此,莫言在写作过程中,熟练地将他听到的故事加以利用、改写、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魔幻风格。《红蝗》中,四老爷及乡亲们看到蝗虫从爆裂的泥土中轰然出世,然后排成条条巨龙,迸射着幽蓝的火花,在河堤上缓缓流动。《马驹穿过沼泽》《生蹼的祖先们》中,高密东北乡有一个手脚生蹼的食草家族,其家族的女祖先原是一匹漂亮的红马驹。这个家族曾经有过兴旺发达的辉煌岁月,但后来日趋败落。《生死疲劳》中,被枪毙的地主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通过此类描写,莫言将古典与现代、魔幻与现实、人文与自然完美地融为一体。中国读者惊喜地发现,深藏于潜意识中的文化因素在阅读的过程中被一一唤醒,他们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奇特之美,从而获得久违的阅读享受。
黑人文化作为美国边缘文化,在黑人族群被殖民的历史过程中处于被剥夺的状态。另外,由于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很多黑人出于生存的策略和考虑,主动接受、内化白人文化。这样的结果是身份的迷失与焦虑,从而成为文化的孤儿。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治、经济的落后导致国人对民族文化不自信。虽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但这种舍近求远的文化重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国人的文化自信。因此,两位作家的文化策略有以边缘对抗中心(莫里森)、以东方抗衡西方影响(莫言)的焦虑的意味。他们的创作通过重返民间、寻找民族文化的源头来激发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建构集体人格奠定心理基础。
尽管如此,两位作家在民族文化建构方面还是有不同之处。莫里森注重从文化角度来思考民族文化对黑人族裔身份认同、价值确立、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如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孩佩科拉渴望拥有白人女孩的蓝眼睛,但她“以白为美”的极端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了其自我身份的迷失与人生的悲剧。《柏油娃》中的雅丹,原有很好的前途,却因为接受白人的教育并认可白人的成功标准而成为文化孤儿。《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通过南方之行找到家族的历史,实现了文化的回归,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从而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在这几部作品中,莫里森塑造的主要角色对民族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显而易见的是,莫里森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基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意识。她依托小说人物的经历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黑人只有回归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才能更好地融入现实社会。
在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上,莫言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他赞同汪曾祺先生在一篇关于京剧的文章中的几句话:文学史上有一条规律,凡是一种文学形式衰退了的时候,挽救它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一是外来的东西[8]。出于某种文化焦虑,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之初也如饥似渴地从西方的文学经典中吸取新鲜的血液。莫言坦言:“80年代的我们跪在外国同行面前仰视他们。”[7]324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及日本的川端康成对他有巨大的影响。值得赞赏的是,影响的焦虑也促使莫言努力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高炉”,思考如何实现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莫言通过广泛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之后,获得一种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参照体系。文化自信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和欣赏、借鉴和创新、吸收和传播。有研究者指出,“莫言的多部长篇巨著(《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显示出来的宏大叙事气度、恣肆的语言洪流、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就是一种自信。特别是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采用古典章回体架构形式,吸收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佛教元素,传承古典神怪小说魔幻手法,可谓是向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致敬的作品。这部成功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传播,是中国文化自信力的体现”[9]。在创作《檀香刑》和《生死疲劳》时,莫言开始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从民间寻找创作的资源,这可以说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转向。所以,在后期的作品中,莫言已经能够将民间文化的元素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娴熟地结合在一起。
二、历史的文化表达:可能的存在
文学中的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是构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在论述司马迁《史记》中故事的真实性时,余秋雨指出,司马迁的史学是一种“文学化的史学”,而不是“科学化的史学”[10]。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尚且不能达到完全的真实,具有虚构特征的文学作品则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作者写历史,其意往往不在历史,而是现实。如昆德拉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指出,小说中的历史不过是为人物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一个“抽象的舞台”,因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11]。换言之,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文学家关心的是历史可能发生过什么,即“可能的存在”。
莫里森和莫言的系列作品往往选择民族历史的某个阶段,以明晰或隐晦的表征让读者看到清晰的时代脉络,在强烈的历史感中,呈现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困境及整体情绪。莫里森的作品主要聚焦于黑人女性,时间跨度从奴隶制时期直至当代。莫里森的创作,虽有现实原型带来的灵感,但更多的是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围绕事件和人物创作出系列故事,重构历史中黑人可能的存在状况。她所讲述的是无法掌控的身心、残缺破碎的家庭、伤痕累累的心灵,以及萦绕不去的噩梦;整体的情绪是痛苦、挣扎和绝望。以《爵士乐》为例,包括乔、多卡斯和维奥莉特在内的小说主要人物都被剥夺了正常的母爱。维奥莉特九岁的时候,母亲因不堪贫困跳井自杀,这在维奥莉特的心理上投下阴影。因此,她从母亲的悲剧中得出的最大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孩子。不管发生什么,决不要有一双小黑脚叠在一起,一张饥饿的小嘴叫着:妈妈?”[12]。母爱的缺失使他们生活在某种“空虚”当中,无法正常地爱和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莫里森笔下的黑人社区似乎有一种自救的力量,那就是在这些令人绝望的处境中依旧存在的爱、温暖和希望。比如派拉特、贝比·萨格斯、曼弗雷德太太及《天堂》中的修道院院长,她们就像“老祖母”,以自己博大的胸怀给那些绝境中的女性带来爱,给予她们莫大的精神安慰。《天堂》中,到女修道院避难的五位女性都饱受社会和家庭给她们带来的痛苦。她们初到修道院时,处于一种失语和沉默的状态。修道院院长康索拉塔用爱心帮助这些社会和家庭的弃儿找回了声音和自我,她的宽容和大度使她们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女修道院成了她们逃避孤独、暴力、冷漠和背叛的远离尘嚣的乐园[6]137。莫里森透过历史的外衣,呈现黑人女性总体的生存状态,这是在书写、弥合、建构黑人历史。莫里森以文学为媒介,储存、传播黑人的历史经验,从而把黑人的经历上升到文化记忆的高度,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塑造和生成。
莫言书写的历史,是一种民间视野下的“传奇化”历史,而非真实的历史。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相似,莫言也虚构了一个自己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他自称自己如同这个王国的国王,颐指气使,把全国各地的山脉、河流、沼泽和沙漠腾挪到此,并调派各色人马,在此上演轰轰烈烈的故事。莫言曾说:“我就要达到这个目的,反映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哪怕是地球上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人那样生存过,那更好,那才是创造,才是贡献。”[13]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莫言在《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中采用了家族叙事方式进行叙述。《丰乳肥臀》中,以上官鲁氏为核心的三代人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苦难的承受者。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1900年德国侵占胶东、日寇侵华、国共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都通过母亲上官鲁氏及其后代所组成的家庭的命运的描写而汇聚在一起。余秋雨认为,“人类的整体史与个体生命史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个体生命史是可以体察的,因此,一旦把历史作人生化处理,它也就变得生气勃勃,易于为人们所体察了”[14]62。在此,人成为呈现历史的最佳载体。其次,莫言笔下的传奇,以人性为根本的出发点,“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技艺高超的盗贼、胆大包天的土匪、容貌绝伦的娼妓”[7]316,均有可能成为其故事中的传奇人物。在认同民间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莫言在忠实地践行其写作的原则:把好人与坏人都当人来写。他认为,好人不管多么完美,都有人性的弱点;坏人即便再坏,也必定有善良的一面。由此可见,莫言的历史眼光,超越阶级、党派、民族,“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并为这种生命状态寻找直觉形式的视角”[14]47。所以,尽管莫言在写中国的故事,但他的故事可以突破时空的界限、文化的隔阂,以其人性的力量为全世界的读者所理解。
三、文化表达的意义:集体人格的建构
那么,莫里森和莫言不约而同地关注民间文化的意图和价值何在?答案或许可以从文化的经典定义中找到。何谓文化?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余秋雨则从功能角度对文化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造集体人格”[15]6。在这一定义中,核心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较好地阐释了文化的核心内容及文化的最终旨归。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16]。“浮士德”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所以,“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15]7。
莫里森和莫言都较为倚重的民间文学形式何以具有建构集体人格的功能?汤玛斯·佛斯特认为:首先,典故具有深度和厚度,能够引起共鸣,读者会因了解典故而使得领悟更为深刻;其次,神话、传说故事“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我们的集体记忆,构筑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建构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17]。换言之,因为神话、传说与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深层记忆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所以作者在文化溯源的过程中,复制和传达了一个族群感知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和原则,在不经意中唤起了人们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正像荣格所指出的,“人类的所有文化沉淀为人格,个人的文化沉淀为个人人格,民族的文化沉淀为民族集体人格”[18]。总之,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利用、创新,以及对历史的文化表达,反映了两位作家对民族性即集体人格的一种期望和建构。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民间文化的溯源为集体人格的塑造奠定了共同的心理基础,并且营造了精神家园;二是对历史“可能性存在”的讲述寄托了作者所希望塑造的集体人格。
莫里森和莫言对集体人格的建构不仅体现于对民间文学形式的挖掘、利用和创新,还体现于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莫里森小说中有几组鲜明的男性形象:一是以白人价值观为生活准则的麦肯·戴德,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变成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二是吉他及 “七日”集团的成员,因仇恨白人,以暴制暴,失去理性,成为复仇的机器;三是《天堂》中小镇上的男人们,为了小镇的纯洁性,排斥外来者,不惜对修道院的几位女性大开杀戒。莫里森在塑造这些形象的过程中,既忠实呈现了黑人男性生存的困境,也批判了其所代表的某些人格特征:金钱至上、心胸狭隘、责任心缺乏。所以,奶娃的出现,寄托了莫里森对黑人男性的期望:只有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获得归属感、找到生命的意义、承担起家庭乃至整个民族的使命。与此同时,莫里森对于理想集体人格的希望还更多地放在女性身上。比如,派拉特、贝比·萨格斯、修道院院长等,她们是黑人族裔文化的传承者和传递者,她们身上体现的博爱、宽容、互助成为社区团结的黏合剂,也是莫里森所强调的黑人理想集体人格的重要组成。
不谋而合的是,莫里森和莫言在各自的一部重要作品中均塑造了一个长不大的老婴儿形象,即《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和《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奶娃吃奶吃到六岁,所以得了“奶娃”这一绰号。而上官金童是小说中的母亲和一个传教士孕育的孩子。这个混血儿长大后身材高大,非常帅气,却是一个离开了母亲的乳房就没法生存的人。他们不能断奶的原因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奶娃的母亲露丝自幼丧母,生活在感情的饥渴中。结婚后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使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露丝不愿让儿子长大。露丝的做法不仅使奶娃沦为他人的笑柄,更妨碍他独立健全人格的形成。而上官金童的经历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的母亲在经受种种虐待后,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即“女人,不出嫁不行,出了嫁不生孩子不行,光生女孩也不行。要想在家庭中取得地位,必须生儿子”[19]。所以,为了生存,上官鲁氏几乎沦为生殖的机器,在生育七个女儿之后,才迎来家中唯一的男孩。金童自然享受着母亲的偏爱和姐姐们的照顾,从而成为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头上的窝囊废”。奶娃和上官金童作为身体上或精神上断不了奶的“老婴儿”,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家庭原因,但也共同反映了父权制“男人至上”观念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在家庭中,男孩被过分宠溺会妨碍他们成为独立、有担当的个体。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但是,国民性未必都是正面的,鲁迅曾深刻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同样,莫言在传承民间文学优良传统的同时,还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向前探索,对中国传统人格心理中的一些阴暗、落后成分——如《檀香刑》中的看客心理、《酒国》《四十一炮》中的吃喝纵欲、《丰乳肥臀》《蛙》中的生育观念等——进行了无情抨击。莫言关于中国人集体人格的认识充分体现于其英雄观。他曾说:“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20]他不惜笔墨地塑造了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英雄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凝聚了他对英雄性格的阐释:行为坦荡、爱憎分明、气概豪迈。虽然他们身上也有自私的、恶的品性,但是,“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21]。祖先的英勇豪迈和子孙的懦弱胆怯形成鲜明对比。莫言同莫里森一样,他亦以女性群像承载了他所崇尚的集体人格理想,如戴凤莲、上官鲁氏、孙大姑、孙媚娘等。这些女性散发出自主、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光辉:热爱生活,爱惜生命,张扬个性。面对苦难,她们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表现出坚韧的正视和径直穿越的态度,不是站立在苦难的对立面,而是正视和置身于苦难中,从而超越苦难”[22]。
四、结语
从文化溯源到文化构建[23-37],从文化认同到文明互鉴[38-44],从文化角度探讨莫里森和莫言创作的意义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热点之一。莫里森和莫言两位作家以文学为媒介,重溯文化的源头,其作品所构建的民族精神家园成为族群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他们对历史可能性存在的建构是对历史的一种积极见证。诚如他们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只有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才能获得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获得文化自信。而他们也只有在了解、铭记民族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文学文本天然地具有“媒介功能、见证功能及艺术感染功能”[45]。经由作家建构的历史文化内容进入艺术领域,必然凝聚成审美的语言,呼唤读者进入文学的世界,产生心灵的共鸣,认同文中人物的精神价值与人格特征,从而潜移默化地促进民族理想人格的形成。至此,作家便完成了文化记忆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