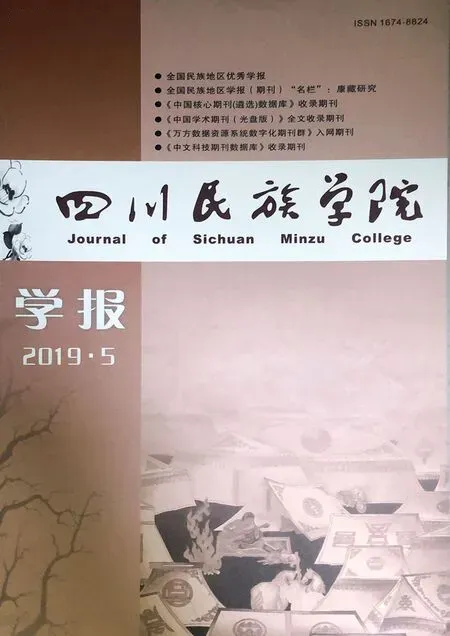清代边疆政策研究
——以拉卜楞地区为例
张利军
一、拉卜楞寺的创建
清康熙年间,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察罕丹津在藏区寻求高僧,欲请回安多建寺弘法。经过考察衡量,物色到在拉萨修习深造,出生于安多藏区甘加境内,在藏区有着崇高声誉和满腹学识的嘉木样雅巴(1)又译为嘉木样协巴,意为喜笑文殊。据传说,嘉木样一世在拉萨学法期间,向文殊菩萨敬献哈达时,文殊菩萨面容含笑,可这毕竟是传说。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当时的摄政第巴·桑吉嘉措向大师提出了四个疑难问题,大师回答的一清二楚,于是被第巴敬称为“嘉木样雅巴”。至此,嘉木样雅巴之称逐渐传开。。后经多次派人进藏诚意邀请,嘉木样大师接受邀请,于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率领主要亲信弟子百余人等启程,返回安多家乡建寺弘法。
同年,嘉木样大师一行人等,到达安多地区的大夏河流域。随即展开了建寺选址事宜,经过多方奔走寻找,发现在一个叫扎西奇的地方,建寺吉兆显现,便选定寺址,开始修建。起初,由河南亲王出资修建了规模有八十根明柱的大经堂,“这时的拉卜楞寺已初步具备了既管教又管民的职能”[1]。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拉卜楞寺规模不断扩大,政教势力遍及青海、四川、甘肃、内蒙等地,拥有属寺百余座,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重大寺院之一,是安多地区佛学的最高学府,声誉遍及蒙藏地区及国内外。况且拉卜楞寺还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中历史最短,创建最晚的一个。
拉卜楞一词,原是藏语拉章之音译,意为寺主嘉木样大师的居住之地,后演变为寺院所在地的代称。新中国成立前,拉卜楞寺所管辖的甘青川广大政教区域,文中统称为拉卜楞地区。
目前,关于清代涉藏政策的研究成果较多。清政府对拉卜楞地区的管理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尚无专门著作论述,公开发表的论文成果主要有:丹曲的《嘉木样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2],林跃勇的《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联系渠道》[3],扎扎的《论述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4],杨红伟的《拉卜楞寺与清政府关系综论》[5]等。其中,丹文按时间顺序叙述了历代寺主与清政府的相关史实,进而述及拉卜楞寺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林文着重从清政府设立的理藩院、西宁办事大臣、陕甘总督三个官方机构,阐述了拉卜楞寺与官方的联系,注重管理机构与寺院的史实。扎文以拉卜楞寺历代寺主嘉木样为主线,探讨了拉卜楞寺与清朝的关系,并指出拉卜楞寺的发展是中央政府扶持的结果。杨文着重讨论了拉卜楞寺的发展是宗教抑制的产物,并指出尽管拉卜楞寺的发展壮大与中央扶植分不开,但其发展也始终伴随着抑制政策。上述成果,大多都侧重于从寺主嘉木样和拉卜楞寺,或地方机构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本文认为,要探讨这一问题,除以上因素外,还离不开拉卜楞寺处于整个蒙藏地区这个大的环境,更应结合清政府对青藏地区的施政态度。
二、清政府对甘青藏区的施政
明代,北方蒙古军事力量强大,对明朝统治造成一定压力。清朝统治者吸取教训,更加重视蒙藏问题,主要对蒙古族采取优抚,对藏族则进行扶植。清朝建立不久,为竭力稳定局势,平定三藩和准噶尔部边患,尽量避免藏区再生事端的不利局面,进而对蒙藏地区采取优抚扶植政策。统治者们看到蒙古势力在青藏地区的强势存在,一时无力改变这一局面,便开启了“以蒙治藏”模式。同时,他们看到蒙古各部和广大藏区民众崇信藏传佛教,遂利用这个共同点,实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后来,在西藏修习的嘉木样大师卷入到蒙藏各部争权的复杂斗争中,在诸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大师始终冷静处理,受到清政府的赏识。这时,青海地区的蒙古势力强大,受河南亲王察罕丹津之邀,大师遂离藏返乡建寺。由此可以看出,拉卜楞寺的创建,既符合优抚青海蒙古和扶植格鲁派势力的一贯政策,又达到了抓住察罕丹津和嘉木样等蒙藏关键人物的效果,是“以蒙治藏”模式和“兴黄教,安蒙古”政策的结果,因而始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扶植。
明代后期,俺答汗部首先入驻青海,开始建立起蒙古民族长期的占据统治。清初,蒙古喀尔喀部、察哈尔部、和硕特部都羡慕青海地区丰美的草场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彼此间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以和硕特部固始汗获胜占据青海而告终。为了长期统治,他将青海地区划分给子孙们进行管理,本来意欲作为进驻西藏的大后方,不料成为引发青海蒙古各部之间内讧的重要原因。经过多年的发展,以罗卜藏丹津(2)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之曾孙,长期驻牧于青海。为首的一部逐渐强大,极力想恢复先祖固始汗对青藏地区的统治权,这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警觉。为了政治上分势制衡,经济上制裁限制,遂晋升青海蒙古另外一支重要力量的察罕丹津(3)青海和硕特部另一支重要力量,济农(藏名达尔吉)郡王之子,拉卜楞寺根本施主。为亲王,并断绝其收取康区赋税的权力。此后,罗卜藏丹津对清政府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以护送达赖进藏有功而未予合理奖封为由,联络青海众多格鲁派寺院发动武装叛乱。察罕丹津势力也遭到攻击,兵败逃回河州。事态进一步扩大,清政府急忙调派陕甘总督年羹尧赴青海平叛,清军对参与反叛的蒙古各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一些有联系的格鲁派寺院也牵连其中,寺院被拆除烧毁,僧人被抓捕遣散,叛乱遂被平息。为防止青海蒙古各部再次闹事,清政府对青藏地区的管理态度也开始向“抑蒙扶藏”转变。作为安多藏区具有影响力的拉卜楞寺因未参与此次事件,而受到清政府的认可和嘉奖。“而今甘南藏区的夏河一带却十分安宁,这对于拉卜楞寺是的发展却是一个大好时机。”[6]众多的蒙藏部落和寺院归附于拉卜楞寺,促进了拉卜楞寺的快速发展。18世纪中叶,“由于蒙古王公已不能统辖藏族部落,拉卜楞寺就通过众多属寺,由控制所在部落的教权,进而控制了政权”,其“势力很快地从大夏河流域扩展到整个藏区”。[7]经过这次事件,青海蒙古各部元气大伤,实力渐衰,藏族实力逐渐增强。
清代中后期,达赖、班禅在西藏的地位更加趋于稳固,格鲁派成为藏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教派,而安多藏区的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经过近百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面对拉卜楞寺的快速发展,清朝统治者们看到,不能让其无限增强,成为一支难以驾驭的力量,进而开始采取“抑藏扶蒙”策略。由此可见,清代对拉卜楞地区的管理始终发生着变化,拉卜楞寺的创建发展也与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不无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清政府对拉卜楞地区的管理
(一)设立机构,加强管控
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其中,理藩院之柔远司“掌治外札萨克众部,凡喇嘛番僧禄凛朝贡并司其仪制”,理刑司“掌蒙古番回刑狱争讼”[8]。理藩院中柔远司、理刑司的设置,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事务的高度重视。此后,蒙古和西藏地方之间争夺实际控制权的斗争、准噶尔部袭扰西藏、青海罗卜藏丹津反叛、拉卜楞寺与其它地区的纠纷等诸多事件中,理藩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乾隆年间,拉卜楞寺与黑错寺因在选立法台问题上产生纠纷,理藩院曾立案批准,经过调查后,责令其“各管各寺”[3]。
地方上,为了加强对甘肃藏区的管控,防止形成较大的地方势力,清政府采用分化手段,把甘肃境内藏区划分为几个地区,隶属不同的府州管理。其中,“设巩昌府,管辖岷州、洮州厅,其辖地包括今甘南临潭、卓尼、碌曲、迭部及岷县、宕昌等县藏区。河州,属兰州府,管辖今甘南夏河县大部及临夏、和政等县藏族部落。循化厅,属西宁府,但该厅下辖今甘南、临夏部分藏区。”[6]从管理范围和机构设置来看,为了防止形成较强的地方集团,清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把一部分划归西宁府循化厅管理,另一部分隶属河州,还有部分则归巩昌府洮州进行管理。
清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地方上设立府、州、道、厅等机构,通过细化行政机构和调整隶属关系,削弱各少数民族地方集团的权力,达到对甘青藏区统治管理的最佳效果。清政府还对藏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强制性地实行迁移,使其形成若干个小的居住区域,进而达到分散其势的目的。
(二)茶马互市,以茶驭蕃的延续
藏族喜欢饮茶,但藏区大都不产茶叶,所需茶叶均通过滇藏线、川藏线、陕甘线三条途径从内地输入。统治者深知 “番人以茶为命,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道理,在严禁民间私自交易茶叶的同时,设置官府机构——茶马司,控制茶叶向藏区的输入。
明代,仅在甘肃境内就设置了六个茶马司,在征调到大量上等马匹的同时,提高了军队战斗力,间接控制着甘青藏区。清初,基于一定的军事和政权需要,延续了这一政策,直到雍正时期才渐衰落。“对现今甘肃境内的藏族……,对这些地方实行以茶易马政策,直接进行统治”。[9]其中,临近拉卜楞地区的河州茶马司的交易量较大。同时,为防止类似于金川事件的再次发生,清政府令“经济上每年输自四川取道松潘,经甘肃夏河而入青海、西藏地区的数百万斤雅安边茶的生产,也由四川总督直接掌管”。[9]正是由于拉卜楞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输入青海、西藏等广大藏区的物品大多都在这里交易,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私茶的贩运,又促进了拉卜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拉卜楞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洮州、河州、青海等地相邻,有其交易输送的便利性。作为安多藏区的政教中心,自然对茶叶的需求量也较大。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政府制定多项严格措施,加强对甘青藏区的统治。同时,随着对马匹需求量的减少,加之商茶和私茶的贩运,茶马交易逐渐衰落,基于茶马交易而控制拉卜楞地区的政策逐渐废止。
(三)清政府的赏封与驻京留任
拉卜楞寺发展成为安多地区重要的政教势力,清政府予以重视优待,敕封了多位高僧活佛。其中对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的册封就有:康熙帝敕封嘉木样一世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乾隆帝敕封嘉木样二世为“扶法禅师额尔德尼诺门罕”(4)对于嘉木样二世的封号有不同的译法。如洲塔、乔高才让著:《甘肃藏族通史》第631页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唐景福.拉卜楞僧人学经制度与经济来源述略[J],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00期,第264页也采用此种说法。,道光帝敕封嘉木样三世为“扶法禅师”,光绪帝敕封嘉木样四世为“广济禅师扎木养呼图克图”。对拉卜楞寺其它活佛高僧的分封有:册封贡唐二世俄昂丹贝坚赞为“贡唐呼图克图”,萨木察二世晋美南喀为“辅印喇嘛”及“驻京呼图克图”,萨木察四世晋美桑珠嘉措为“掌印喇嘛”,喇嘛噶绕仓为“将军”和“根噶坚赞呼图克图”。从上述清代中央政府所册封活佛的数量、规格、时间上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拉卜楞寺的重视程度,也反映出拉卜楞寺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地位。有清一代,对于拉卜楞寺的认可扶持也是自始至终的,这为拉卜楞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其快速发展。
清政府不仅敕封拉卜楞寺的高僧活佛,为拉卜楞寺赏赐亲笔匾牌,还不断选派有重要影响力的拉卜楞寺高僧入京,他们或受到礼遇、或专门供职。其中,对拉卜楞寺及各大扎仓赏赐的亲笔匾牌有:“慧觉寺”“寿禧寺”“三宝慈光普照世界”“寿安寺” “普祥寺”“般若洲”“喜金刚学院”等[5]。先后选派进京的拉卜楞寺高僧有:1759年,贡唐二世丹贝坚赞应召进京,曾任乾隆帝师,清廷册封其为驻京呼图克图[10];1798年,萨木察二世晋美南喀应召入京,得到嘉庆皇帝的赏识,清廷册封为驻京呼图克图[10];1852年,萨木察四世晋美桑珠嘉措奉命赴京任职。
对清政府而言,敕封高僧活佛,赏赐御制匾额,应召入京供职等方式,一方面起到扶植笼络拉卜楞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达到了监督管理的政治效果。而对于拉卜楞寺来说,这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重视,又获得了册封赏赐的政治荣誉,疏通调解了上下关系,对拉卜楞寺的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拉卜楞寺修习制度完备,佛学人才济济,涌现出了一批享誉全藏区高僧活佛的历史事实。
(四)多封众建、军事震慑与严格限制
1.多封众建
明代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 和“多封众建”政策,对甘肃藏区各教派宗教上层给予优待册封。清代,只要是有实力的地方集团,清政府都予以分封。“清政府对甘肃、青海各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给予分封。在甘肃分封大小土司二十七家,青海大小土司三百零四家”。[11]尤其是“对现今甘肃境内的藏区……,这些地方藏族为土司所辖,清朝仍然授予藏族僧侣首领一定的权力”。[9]比如实力雄厚的禅定寺,德尔隆寺等。
杨土司及其禅定寺的历史悠久,是甘南藏区的另一支重要政教势力。明代时,就被册封为“世袭指挥使佥事兼武德将军”。到清代时,又多次受封,免于改土归流,成为甘青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实力集团之一。赛仓活佛是拉卜楞地区的著名活佛世系,在拉卜楞地区有重要影响。赛仓一世对拉卜楞寺的创建发展有一定的功绩,是拉卜楞寺的第二任大法台。后因在寺主嘉木样活佛转世问题上发生分歧,离开拉卜楞寺,创建了德尔隆寺。1872年,德尔隆寺寺主活佛赛仓三世被同治帝册封为“护国扶法大师”,委任管理大夏河流域的土门关到长石头之间,这是清政府在甘南藏区境内分封的另一重要实力集团。
分封是对地方势力重视的表现,但也是相互制衡的重要措施。乾隆十六年(1751年)密谕驻藏大臣班弟“应多立头人,分杀其势”。[12]这样,甘南藏区实际上形成了以拉卜楞寺、禅定寺、德尔隆寺为主的三大政教集团,成为鼎足争雄甘南藏区的重要政治力量。清政府在甘南藏区境内的分封措施,既达到了“多立头人,分杀其势”而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又防止了某一地方实力过于强大而难于驾驭,也使得各地方势力互相掣肘,无力与清政府抗衡,可谓一举三得。
2.军事震慑
统治者认为有必要对甘青藏区各实力集团进行一定的军事震慑,以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威和统治。“1839年,因甘加军马被盗事件,嘉木样三世被河州镇总兵截留于河州城。”[13]“1845年,因合作、扎油两部落的匪徒劫掠了巡游途中的陕甘总督,循化同知、河州镇台、陕甘总督的代表等军政官员带领大队清兵到拉卜楞寺搜捕。”[13]“金龙年1880庚辰6月,公华觉率官兵到拉寺巡察。”[14]这些事例都说明,清朝统治者对拉卜楞寺进行优待的同时,也奉行一定的军事震慑政策。
3.严格限制
《拉卜楞寺志》载:“拉卜楞寺的喇嘛,在极盛时期,其总数超过四千。”[10]“1801年,贡唐三世贡曲乎丹贝仲美在祈愿大法会上,向3000僧众施以茶饭 。”[15]这些数据表明,仅在建寺后的短短90年当中,拉卜楞寺的僧众数量快速增长到三四千人,属寺教区不断拓展,由此可见拉卜楞寺的发展迅速程度。早在罗卜藏丹津事件中,就出现过一些寺院僧众集体反叛的事件。“惟西宁周围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16]在平息叛乱后,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清政府很快便吸取经验教训,开始严格限制拉卜楞寺的僧团规模和僧人数量,到“1890年,朝廷降谕拉寺上报呼图克图名册和僧侣数额。”[21]进而从控制寺院僧人数量方面入手,对拉卜楞寺进行严格限制。
四、拉卜楞寺的积极发展
诚然,拉卜楞寺的发展离不开清政府的扶持,但也离不开拉卜楞寺僧众自身积极的争取。“黄教在整个藏区寻求发展,它还与卫藏、阿里、康区、安多各地区的封建势力广泛联系。同时,还和蒙古族、汉族、满族封建统治者联系。”[17]清代中后期,拉卜楞寺在清政府的扶持下,政教区域迅速扩大,开始逐步向邻近的川康地区、青海地区、甘南境内其它地区发展。同时,加强与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地区的政教联系,积极争取甘青川藏滇以外各地区的支持。
甘南地区的禅定寺、德尔隆寺、黑错寺,青海同仁地区的隆务寺,四川的格尔迪寺均有较强实力。拉卜楞寺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引起邻近各地寺院集团的不满,甚至是引发彼此间的武装冲突。其中,拉卜楞寺与隆务寺之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德尔隆寺、黑错寺也结束了与拉卜楞寺的政教隶属关系,加入了隆务寺集团,这使得拉卜楞寺在大夏河流域的发展受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拉卜楞寺在甘南藏区的政教实力。
为了向新疆、内外蒙古拓展教区,拉卜楞寺曾多次派高僧前往各地进行宣化,或是拉卜楞寺一些活佛的转世之地就在这些地区。内外蒙古地区一直是藏传佛教各寺院积极争取的区域,拉卜楞寺的许多高僧活佛就出生于内外蒙古地区。除嘉木样四世外,到蒙古宣化的拉卜楞寺其它高僧还有:贡唐五世嘉央丹贝尼玛、霍尔藏四世晋美丹贝尼玛、萨木察四世晋美桑珠嘉措、德哇三世嘉央图丹尼玛等。
拉卜楞寺创建之初,就与新疆准噶尔部关系密切。“1709年,嘉木样一世提名准噶尔籍学僧然卷巴·智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选派的代表陪送嘉木样到安多。这位学僧没有再返回西藏,而是担当起了拉寺与准噶尔部之间联络使者的角色。”[18]此后,经班禅大师卜算,建立起准噶尔活佛转世系统,成为拉卜楞寺著名的活佛世系。
拉卜楞寺高僧对于上述各地的游历宣化,所到之处或是传法授戒、或是举行法事、或是募集资金,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也扩大了拉卜楞寺的影响和政教区域,争取到了更多的外部支持和财力,为拉卜楞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统治者的需要和蒙藏地区形势的发展,清政府对拉卜楞地区的管理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前期,对于拉卜楞地区延续了明朝的一些政策措施。拉卜楞寺的建立,既顺应“以蒙治藏”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优待扶植政策,也符合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实际利益。中期,清政府对藏区的管理,转向“抑蒙扶藏”政策,进而通过笼络扶植藏传佛教寺院对甘青藏区进行统治。尤其是罗卜藏丹津反叛事件,使清政府加强了对甘青藏区的管控,亦而趁机削弱蒙古势力,这给未参与事件的拉卜楞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后期,青海蒙古势力日渐衰落,藏族势力渐盛,清政府继而实行抑制震慑政策。拉卜楞寺在积极争取清中央政府支持的同时,建立起与西藏、川康、青海、内外蒙古等广大地区的政教联系,趁机拓展教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