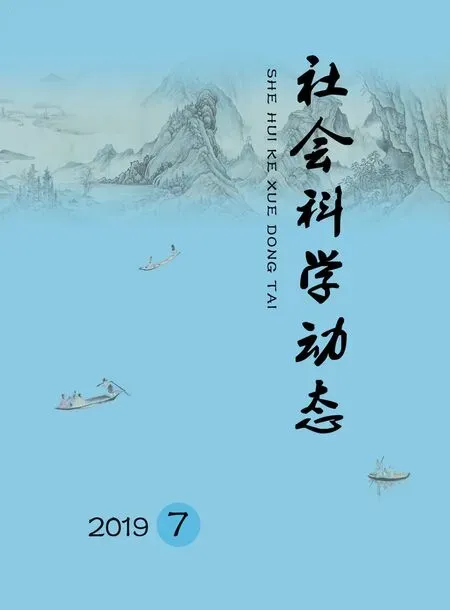曹军庆的文学辩证法
———以《贵人》《猪喜剧》为例
王海军
文学叙事的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总会以与确立自我血缘关系之地为“奇点”,以独特的人生经验为半径不断地向周边旋转辐射,其所辐射过的面积便形成了作家独特的“文化场域”。如莫言的高密乡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棣花村、苏童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村、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毕飞宇的苏北平原等。曹军庆似乎深谙此道,他以“烟灯村”故乡为文化叙事场域,关注烟灯村人在改革大潮中的生存状态,以悲天悯人的哲思凝视着那些被生活所伤害和正在接受着伤害的父老乡亲。在主人公悲喜交加的命运流转中表达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当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严肃思考和敏锐判断。对作家而言,“文化场域”是他们的叙事空间,作为其“文化场域”中的香草美人——文学作品,不但是作为炼金术师的作家苦心孤诣炼就的金丹,而且也代表了作家的冶炼技艺。在炼金过程中,作家逐步确立其叙事法则、叙事策略、叙事技巧、叙事风格乃是叙事理想或理念。高明的作家往往不会执着一端,乃至固执己见,他们往往以“佛智”诸如“灭尽执著”方能“明心见性”等作为自己的文学辩证法,从而形成一套自己对世界的解释逻辑和认知方法,并藉此展示自己的远大抱负,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就此而言,我认为作家曹军庆便是这样一位炼金术师。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①从自身角度出发,鲁迅将“人生价值”毁灭与否作为判断悲剧和喜剧的标准。同样,曹军庆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经验引入到文学叙事中,将底层人物置于改革的大潮中,令其在贫病交困中呈现出生存的伦理困境,在得失、祸福之间展现出命运的流转和迁延。同时,在向人性深处不断开掘的过程中,文学叙事中氤氲着悲喜交加的戏剧性漫溢而出。他创作的《贵人》和《猪喜剧》对“福祸相依”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经验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也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文学辩证法。这种立足于“奇点”处(烟灯村)的创作不但有效地接通了传统叙事经验,而且成就了其独特的叙事风格。
《贵人》以对“贵人”的探寻和溯源不断将读者带入作家精心设计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中。全文贯穿着“谁为贵人”式的哲学追问。命题中蕴含着“谁是谁的贵人”,这使得“贵人”一词不但成为了一个无效的无限循环,而且“贵人”同时处于一种序列化的存在中,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链条。在这个进化的链条中,每一个看似“贵人”之人在作者精心设计的命定逻辑中都无疑令“贵人”一次雪上加霜,恰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命定逻辑。每一个人在生命进化的逻辑链条中,都可能成为他人的“贵人”亦或相反,每一个该链条中的“贵人”都无疑在生存的贫困线上“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看似时来运转,亦或得意洋洋,但“潘多拉的盒子”并没有释放出“希望”的曙光。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作者笔下“烟灯村”蝼蚁般的存在,作者将同情的目光给予他们,并注入人文主义的温馨气息,以脉脉的温情余晖暗示着“贵人”的主题,同时也构成了对“贵人”一次次的重新拆解和赋意。
首先,《贵人》在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尽显其“悲喜剧”式的“福祸”辩证法,并体现出农村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曹军庆在《贵人》中通过潘富贵一家人命运的三次悲喜转换来完成其文学辩证法。第一次,乐极生悲。潘冬明“金榜题名”实乃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但潘家无法筹足学费,其父潘富贵上山采药坠崖被摔成了植物人,令潘家陷入生存困境,其母李翠花大举外债为救潘富贵令一家陷入更深的绝境。第二次,悲喜交加。卓记者连续报道潘冬明家的情况后,潘家收到捐款和商人郭德兴的资助,这不但使得潘冬明能顺利上学,而且李翠花开始慢慢还债,但此后捐款的突然中断,又令李翠花一家陷入到还债的危机中。第三次,一地鸡毛。为再次筹措捐款,李翠花为潘富贵筹备四十岁生日。当天潘冬明找到了恩人郭德兴,却发现郭德兴是个专门诈骗农民的诈骗犯。三次悲喜之间的自如转化,恰好完成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同时也对应“贵人”的逻辑链条。对潘冬明、潘富贵、李翠花、卓记者、郭德兴而言,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叙事链条中的“贵人”,亦或相反。
其次,在小说主题的开掘上,作者围绕对“贵人”的寻找呈现出伦理困境,体现出曹军庆独特的“名利”辩证法。表面上看,通讯员、卓记者和郭德兴为潘富贵一家的“贵人”。正是通讯员的报道受到了卓记者的关注,而卓记者的报道为潘家带来捐款乃至商人郭德兴的慷慨资助,这使得潘家部分程度上摆脱了生存困境。实际上,植物人潘富贵不但是潘家的“贵人”,更是卓记者的“贵人”。或者说是潘富贵的不幸为潘家带了经济利益,同时也为卓记者带来了可资写作的素材和出名的资本。卓记者早已按自己预设的题目诸如“妻子的善良感动了上苍”、“真情创造医学奇迹”③等拟写好了采提纲,只期待潘富贵的苏醒。但作者的深刻发现在于:所有的善良亦或是正义之举的背后都可能陷入伦理的困境。通讯员的出手相助是为了获得关注度,卓记者的连篇报道是为获取更大的影响力,郭德兴用诈骗农民的黑钱慷慨解囊是为了实现自己未曾完成的读书梦。更为甚者,李翠花大举外债,为夫治病则是为了希望潘富贵早日苏醒,能支撑家庭重担,她期待获得捐助以缓解外债的焦虑将其慢慢推入了伦理困境,直至在为丈夫大办四十岁生日以获取更大的捐助时,现实将她直接推向了伦理的审判台。期间李翠花对外界表现出的善良和美德,也被她对潘富贵的变态式殴打而陷入伦理困境。小说中每个人都像饿狼一样有意无意地寻找着自己的猎物,同时也无形中将自己绑上了伦理的审判台。
在《猪喜剧》中,作者有意向轻喜剧转向,但仍然坚持其“福祸相依”的文学辩证法。烟灯村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了城市化之旅。他们投身这种大潮,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也是接受生活的挑战。他们很自然地顺应着这种安排,这使得原本的家庭结构被强行分割,男女关系被“重新洗牌”,“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是一张牌,放在一起重新搓洗”。④人物的命运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得到不同形式的转换,使得“福祸相依”的悲喜剧辩证法得以呈现。外出与留守成为摆在烟灯村人面前的难题,更为困难的抉择是谁留守、谁外出?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为传统型。按照逻辑,外出的女性从事理上推想起来,“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⑤烟灯村外出东莞打工的女性李玉兰和陶秀芝都做了妓女,一个抽烟,一个吃摇头丸,这在事实上证明了女性外出的危险性。明知“外面的世界和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但人们依然向往外界。就这样,刘发松的妻子王桂芬以保护两个女儿的名义一起去了东莞。此后,“猪”的喜剧便在男性的性焦虑中以“福祸相依”的悲喜剧辩证法逐次展开,人物的命运也在这样的变换中呈现出特有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
在《猪喜剧》中,生存困境的直接承受者,一为刘发松,一为陈文广和陈白义叔侄俩。他们身上分别体现出作者“祸福相依”为基础的“悲喜剧”辩证法。对刘发松而言,妻子去东莞打工无疑是一场悲剧,也是他为缓解性焦虑嫖妓被抓的直接原因。他偷窥刘玉英的“成功”以及向陈文广直接举报陈白义与刘玉英通奸又带给他人生的“喜悦”。但陈氏叔侄俩的和平交易对刘发松来说则直接造成了强烈的精神打击。此后他嫖妓被抓,在被村长孙得贵解救过程中被坑,这又构成了他人生的“悲剧”。因而,刘发松的命运基本上是围绕着得—失—得的“福祸相依”的辩证法,从而形成了悲—喜—悲的文学辩证法。而陈文广和陈白义建立于“祸福相依”基础上的悲喜剧则几乎是互补的,陈文广的悲剧就是陈白义的喜剧,反之亦然。陈白义与刘玉英侄婶通奸对陈白义来说是“福”,是喜剧,但对陈文广来说是“祸”,是悲剧。陈白义的两头母猪被陈文广赶走后,陈白义的“祸”成了陈文广的“福”,陈白义的悲剧成了陈文广的喜剧。此后,被村长所黑的陈白义要回了自己的母猪,对陈白义而言是失而复得,对陈文广而言是双重失去,这直接造成了陈文广的离家出走。 因而,陈白义的命运经历了喜(通奸得逞)—悲(以猪抵偿、被村长黑)—喜(要回母猪、母猪生崽);而陈文广则经历了悲(被戴绿帽子)—喜(索取母猪)—悲(还回母猪、离家出走)—喜(妻子生下孩子)。
显然,曹军庆在《猪喜剧》中仍然在积极探索着烟灯村人的伦理困境,并将批判的笔触指向了基层权利阶层。在整个叙事中,作为农民的刘发松、陈文广、陈白义均为受害者。对刘发松而言,两次嫖妓未遂,但却受到高额罚款。然而,其萌发嫖妓的想法却是来自派出所的职业线人“老油条”的劝诱,而游走于各个村子的“老油条”则通过向派出所举报以获取奖金利益。这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钓鱼执法”,因为体制应该导人向善,而不是为获取利益制造请君入瓮。村长孙得贵在保释刘发松的过程中暗自黑钱是以权谋私,此外他为了获取政绩还曾诱导陈白义盲目扩大养猪规模。这样的基层干部理应受到法律规约制裁,然而他却是烟灯村的基层管理者和执法者。此外,侄子与婶娘通奸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批判,但作为丈夫的陈文广不是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相反却在妻子刘玉英的怂恿下提出以两头母猪作为赔偿。在陈文广赶走母猪后,陈白义则是直接去找村长送礼以要回自己的两头母猪。无论是刘发松,还是陈文广叔侄,他们都是村长治下的“顺民”,都深深地陷入伦理困境中无法自拔。由此可见作家对现行体制社会治理漏洞的深层思考。
改革大潮令几千年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开始慢慢嬗变,人们建立在对土地依存关系之上的“品性”和“特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变。显而易见,“三农”之间以及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断协调中造成的扭伤,最直接的作用是反映在“农民”身上,他们是苦难的最终承担者,也是苦难的最后化解者。这不但源于数量之众,更源于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伦理道德传统。同情并关注他们是作家唯一和最软弱的表达方式,这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所秉持的写作伦理。如莫言所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而非代表老百姓写作,这既是当代作家理应秉持的写作伦理,也是当代作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之重。从这个角度而言,曹军庆的“烟灯村”叙事恰好暗合了这一历史逻辑。
综上所述,在结合传统哲学诸如“名利双收”和“祸福相依”的基础上,曹军庆逐渐将其转化为自己独特的文学叙事经验,这不但使其作品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学叙事中悲天悯人的感伤主义美学特征,更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风格。作者将烟灯村故乡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农村生活的缩影,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潮下,理性思考农村和农民问题,为他们的人生命运寻找可资依托的栖息地,这既是作家的无奈,也是中国当代农村社会所面临的改革之殇。曹军庆此后的作品更是将关注的视野投入到农村的城镇化运作中来考察,如《玻璃发卡》 (2010年)、 《工厂村》 (2012年) 以及 《家谱学》(2013年),这使得他的小说叙事显得更加立体和多面。但无论如何,其创作的“奇点”——烟灯村——一如既往,始终给予他创作力量和深思。这对作家而言,幸亦或不幸?
注释:
①④ 鲁迅:《鲁迅全集·坟》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166页。
② 曹军庆:《贵人》,《中国作家》2008年第24期。
③ 曹军庆:《猪喜剧》,《长江文艺》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