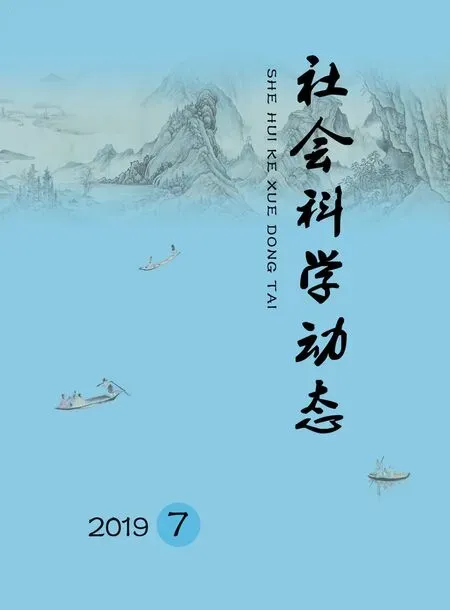乡村女性与乡村的生存困境
——以曹军庆的小说为例
钟 毅
从1986年进入文坛到2005年引起文坛的关注,湖北作家曹军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近年来,他的长中短篇小说频频被转载、获奖,引起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他和吕志青、晓苏被文学评论界并称为“荆楚三杰”。
曹军庆的小说视野是乡土的,“其作品的主要底色,是农村、乡镇的生活底色。他追求的不仅仅是通过比较实在或者是更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去写农村的生活变化、人际关系变化,而是以这种生活底色去反映、去体现一种精神性的思考”。①因此,他的小说不是着力于总体性的社会剖析,而是从切片式的生活细节出发,并以此反映人性的正面和背面,从这个意义讲,他的小说又具有先锋性。
作家的工作包括了创造具体的写作套路和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曹军庆喜欢讲故事,却并未掉入早期先锋派的“叙事陷阱”,其作品的故事性始终是为人物服务的。文学作为“人的文学”,人物形象直接承载着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曹军庆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是鲜活的,这得益于他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在他所创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乡村女性形象尤其值得注意。
一、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与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相比,乡村由于其封闭的结构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呈现出变化速率很慢甚至静止的特点。即使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传播百年,但乡村社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的绝对权威为主导的父系社会,女性由于其边缘地位深受男性的压迫。作家曹军庆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传统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传统乡村中,男性对女性的爱往往带有性占有的成分,甚至女性被异化为男性的所属物。小说《魔气》中,管素珍就面临着不同男性的侵占。作为单身汉的支部书记王光忠,从雪地里捡回了管素珍,在他的心中管素珍就成了自己的所有物。他在后者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当他发现管素珍竟然是一个处女,于是便将沾着管素珍“处女血”的被子晾在屋外,向全村人炫耀。另一个男性是烟灯村的会计刘胜利,他暗恋着管素珍,但由于无法占有她而因爱生恨。他要挟了兽医驴子,指使其加重管素珍的病情,最好让她成为残疾。在刘胜利的心中,管素珍就是一个物品,自己得不到也不想让别人占有,那他就要毁掉它。然而最让人悲哀的是,面对着男性的侵犯,管素珍们却几乎全然秉持着一种不抵抗的态度。
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早已经内化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制约着女性的一举一动。曹军庆看到了在长期父权制压迫和奴化过程中,女性逐渐产生了一种自我压迫意识,而这种自我贬低才是导致乡村女性悲剧命运的最大因素。正如作家铁凝指出的:“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②自我意识与外部环境交织,使得女性更加无法摆脱其悲剧命运。在作家方方的笔下,乡村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现实也体现得相当明显。在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中,英芝经常遭受丈夫贵清的毒打,然而当她跑回娘家时,母亲却告诉她:“要认命。你是个女人,要记得,做女人的命就是伺候好男人,莫要跟他斗,你斗不赢的。”③当男权文化演化成乡村社会的伦理道德时,女性即使遭到男性的蹂躏和粗暴,却又因为自我压迫意识而选择了逆来顺受。
随着现代文明渗透的金钱至上的观念不仅影响着城市,更诱惑着物质匮乏的乡村。落后、贫困的乡村越来越留不住人。小说《风水宝地》中的吴大姐就说道:“住在乡下没面子。死人才会安心住在乡下,活人不会。人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往外头奔,奔死奔活就奔一口气。”④于是,乡下的女性跟随着打工浪潮纷纷进城。这是乡村女性为改变自身命运所作出的尝试,然而在进城之后,她们依旧摆脱不了被物化和被奴役的命运。
男性中心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即使是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现代的思想想要彻底改变固有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作为商业化大潮的首当其冲者——女人,她们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推进者,而且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商品社会不仅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而且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必然再次以女人作为其必要的代价与牺牲”。⑤消费社会异化了人的本质,乡村女性则面临着被进一步物化的危险境遇。在曹军庆笔下,女性被物化多是源于男性的欲望。小说《猪喜剧》中,陈白义趁着自己的叔叔陈文广不在家而与婶娘私通,等到陈文广回家之后,事情败露的陈白义选择将两头怀崽儿的母猪送给陈文广,以此作为道德补偿,似乎女性身体的价值就值这两头母猪。《李玉兰还乡》中,村长孙得贵为了得到李玉兰的身子,便把一块宅基地批给了李玉兰家。在男性文化中,女性的身体不是她们能自由支配的,而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而存在,当金钱和权力同样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时,女性的身体逐渐与这些利益划上等号,被当作了男性之间交易的替代物。
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事物都有可能被异化为商品用作消费,包括人的身体。乡村女性在进城之后,由于缺少满足城市需求的劳动技能,很多女性只能从事单一而繁重的流水线生产,而有的人为了“轻松便捷”,便从事起最古老的妓女行业。两种现象都导致了乡村女性被商品化,而后者则更加彻底。小说《猪喜剧》中写道:“从烟灯村出去的女孩子,至少已经有李玉兰和陶秀芝做了妓女,还有没有别的人现在还很难说……她们依靠自己的肚子挣钱。过渡使用化妆品,不规则的饮食和睡眠,接客。像贼一样不停地更换租住地和淫乱场所。”⑥李玉兰似乎为烟灯村的女性打开了一条进城的通道,从此,她们陆陆续续地从乡下走出来做了妓女。这也暗示着乡村女性彻底地被商品化,她们的身体被明码标价用于男性的消费。曹军庆的眼光是尖锐的,他看到了这些乡村女性进城之后的处境,即使她们更换了生存空间,但依旧没有摆脱被物化的悲剧命运。
乡村女性进城找寻出路,却无力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在“进城梦”破碎之后,其中的一部分试图还乡以安放身心,但另一部分则成为城市的漂泊者。然而,前者在“还乡”之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依旧只是乡村男性的附庸,后者由于既回不到乡村又被城市所排挤而最终滞留在城市的边缘位置。这是曹军庆独特的发现,他不仅看到了女性从乡村到城市的行走历程,更看到了她们在心态上从“进城”到“还乡”或“留城”的转变,最终揭示出她们无处安放的精神状态。
女性在乡村感受到的是恶劣的性别语境和生存环境,因而城市对于她们而言意味着此处摆脱这种穷困的“天堂”。但是,当她们真正到了“天堂”,才发现这个天堂仍然是压抑的。在《李玉兰还乡》中,“李玉兰过了几年的风尘生涯,她亲眼目睹了许多姐妹的悲剧。做妓女这一行,能有善终者确实不多,这既要看你个人的意志,还要看你的运气”。如果女性选择进入工厂打工,生活也是压抑而艰辛的,“她感到自己就像一株植物一样,如果硬性移植到这样的车间里她一定会枯死的”⑦。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对于女性甚至是男性的身体都是一种摧残。无独有偶,作家严歌苓在《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也曾如此描述乡村女性的打工生活:“慧慧在深圳流水线上做了一年出头,回来脸白得像张纸,一天吐好几口血。从县医院拍回的片子上,个个人都看得见慧慧烂出洞眼的肺。”⑧在城市里的艰难处境迫使乡村女性逃离城市,同时李玉兰们又希望回家,“她始终放不下的就是家里人”,于是踏上了“还乡”之路。李玉兰一回家,就为家里人盖了楼房,他们家也第一次在村子里有了脸面。家里人感激李玉兰出钱,李玉兰也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但是她的哥哥李明义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知道妹子这钱是怎么来的么?”“你弄回来的钱就干净么?”此时,李兰玉才发现最瞧不起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哥哥。而村里“瞧得起”她的男人们也不过是看上了她的身体和金钱,唯一对她真心以待的男人吴小栓还是犯过罪蹲过监狱的。于是,作家最后以一种同情的悲悯让这两个边缘人走到一起抱团取暖。
反观李明义从以前的勤劳简朴到后来的唯利是图,这种变化既有时代原因,也有其原本的劣根性。在商品化的洪流之中,个体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李明义们感受到了金钱的力量,金钱能带给他们楼房,能带给他们面子和地位,然而他们内心对于女性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与其说现代城市文明给乡村带来了金钱至上的观念,不如说它激活了乡村人与生俱来的贪婪。现代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乡村这潭死水中激起的水花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妇女的地位并未因为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潮改变多少。正如李玉兰们改变了家里人的物质生活,却改变不了自身在家庭中的弱势话语地位。
费孝通曾说:“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衍生出巨大的城乡差异,贫困依旧是乡村的主题,而城市五颜六色的繁华诱使着千百万乡村人闯进城市来冒险。当他们再次面对曾经的故土时,又会因为已经膨胀了的欲望而无法再次适应乡村,最终使其甘心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的漂泊者。
在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慧慧虽然因为城市的工作而累垮了身体,但是“她却跟巧巧说深圳的好,一天在流水线上坐十六个小时,吃饭只有五分钟而买饭的队要排一小时,就那样也不耽误深圳天堂般的好。因此巧巧是怎样也要离开黄桷坪的”。城市的灯红酒绿占据了慧慧们的内心,即使她们遭受了排挤和折磨,也要执着地留在城市。曹军庆的新作《向影子射击》更是将乡村女性渴望“留城”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小说讲述了一个有钱有权的城市人家招募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做奶娘,而吃奶的则是一个地位崇高的中年先生,奶娘们居住的地点在一个豪华的庭院,“工作”期限是一年。一年期限已到,主人公云嫂却迷恋上大城市,迷恋上那个住所,迷恋上那个位高权重的男人。她试图强行留在庭院,结果却被保安当作“精神病”赶了出来,这样三番五次之后,她被迫回到乡村,却无法再次融入乡村。她嫌弃老公,拒绝和他同房,甚至嫌弃自己的孩子,拒绝让孩子吃自己的奶。云嫂们希望留在城市,但被城市所抛弃。即使她们留在了城市,最终也只是这个城市的附庸,凭借自身的身体乞求男性社会的需要。
曹军庆为“进城”的乡村女性设计了两种未来,直指现实生活中乡村女性无处安放的生存处境。《李玉兰还乡》中,李玉兰在结束自己的妓女生涯前,曾给自己设计过两条出路。第一条是“留城”,“随便哪座城市就像一座森林一样,一个人就像一片树叶,烂在里面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第二条是“还乡”,“回到烟灯村,李玉兰可以用自己的钱给家里做点事,比如起一幢楼房什么的”。如果选择了前者,也就意味着李玉兰们像一片孤零零的树叶一样沦落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体系中。然而,李玉兰们知道“回去的风险更大,因为未知的因素比城市更多”。对于“还乡”的女性而言,乡村和家人就是她们的“乌托邦”,在外时无比思念家人,但最后“乌托邦”成为了“敌托邦”;对于“留城”的女性而言,城市就是她们的“乌托邦”,但城市最终却用冷漠和残酷拒绝了她们,这个“乌托邦”也成为了“敌托邦”。因此,曹军庆通过一系列作品深刻地展示出了当代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从“进城”到“还乡”或“留城”,她们都无法逃脱一种无处安放的境遇。
二、乡村的生存困境
同乡村男性相比,乡村女性在城市中面临的是双重弱势语境,即性别弱势和乡土弱势。乡村女性在城市文明中是最边缘的存在。在“消失了一切坚固东西”的城市消费文化中,她们的身体逐渐沦为一个筹码,实则成为了男性政治的附庸并迷失了主体价值。乡村女性身体被编码和被消费的过程背后,蕴含了一种城市的性政治逻辑。在曹军庆的笔下,乡村女性和乡村经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们都是被城市消费和控制的对象。如果将城市与乡村进行对比,那么乡村无疑是和感性的“地母”形象挂钩的,而城市作为一种理性的产物则更像是代表着男性的符号。城市的主流话语定义着乡村的历史,而乡村是游离在历史之外的陪衬,正如男性“中心”观看女性“他者”时的情景一样。因此,比起曹军庆笔下的其他人物形象,乡村女性无疑更能映射出乡村在城乡碰撞中所处的位置。学者戴锦华曾说:“承造了救赎的女人始终在历史之外;如果说此间的男性形象更多是文明的造物,那么个中的女人便更像是‘自然的女儿’。”⑩城市诞生于乡村,乡村滋养着城市的发展,正如“母亲”是生命的哺育者。但随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越来越和落后、陈旧划上等号。在城市中心话语体系下,乡村无疑是边缘的,因此它试图通过城市化改变这种边缘处境,而乡村向城市过渡往往是以工业化作为现实路径。在曹军庆《工厂村》里,飞龙化工厂落户了白龙村,化工厂为村民带了迁地补偿款和平整的道路,却也带来了怪病。白龙村的人工建筑越修越好,但自然环境却越来越差。最终,白龙村并没有成为白龙市,只是成为一个工厂村,生产出来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城市。白龙村在“进城”之后并没有改变其自身性质,依旧是作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并逐渐失去其主体性。
然而现代性作为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乡村被拖拽着前行,倒退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白龙村前村长孙德福为了把化工厂赶出去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生涯,“多年来,把孙德福上访的次数加起来,总有成百次。他拄着拐杖,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像乞丐。家里的钱财早被他耗光了……有时,他会在纸板牌上写上黑体字:化工厂毁了我们村子。他就挂着这牌子,挂在胸前,或是背在背上。他这样子,就是‘文革’期间游街的走资派。走在街上,没人理睬他,很多人会把他当成疯子”⑪。对于一个时代而言,那些试图重归旧有的社会秩序的人由于与这个时代脱节,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话语下的“疯子”。因此,乡村和乡村女性被裹挟着参与了“进城”的浪潮,最终的命运要么是像云嫂那样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要么是像李兰玉那样重新回到落后的价值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军庆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刻的现实问题,即乡村在城乡文化碰撞中所面临的困境。
三、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曹军庆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核心意象——恐惧。所谓恐惧,是指人在面临某种危险情境,企图摆脱而又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担惊受怕的一种强烈压抑情绪体验。在他的小说中,恐惧不仅是一种心理体验,更是一种文化体验。那么,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从根本而言,乃是因为人意识到了在现代性结构之下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更深的物化和奴役。”⑫对于乡村女性而言,“进城”、“还乡”和“留城”都是为了摆脱生存困境所做的努力,当她们发现自己面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时便产生了恐惧感。同一些女性作家相比,曹军庆对于乡村女性生存状况的反映是不够的,仅以目前的作品而言,他笔下的乡村女性书写无法成为他的独具特色,这一点从乡村女性所占其作品的篇幅便可以看出来。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使得其作品没有成为一种“女性苦难式”的呼喊,也没有局限在性别身份认同的条条框框之中,而能够由点及面地触及到广泛的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从乡村和乡村女性出发,曹军庆的作品延展出的是一整幅现代社会的图景。而在乡村女性与男性的交际之中,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则凸显得格外明显,因而其作品是具有普世性的。他的笔下充满了人性负面的东西,集中反映着现代社会的危机和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小说《额头上的暗物质》塑造了一个“天眼”意象,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秘密都会被这个“天眼”察觉,比如小强的妻子隐瞒了自己的婚前堕胎行为。“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要解剖的是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⑬曹军庆拥有丰富的基层生活经验,因而在运用“真实生活+平时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上显得得心应手。他用自己的手术刀解剖出一个身心俱残的现代社会,这种解剖发人深省,却往往“暗无天日”。不过,曹军庆的作品是不断发展的,正如其近作 《有没有一直着了火的鸟儿》中塑造了一只寄予了改变现实的火鸟,而这只火鸟最后成为了补偿灰暗现实的替代品,让人在身处无家可归的困境时能感到一点慰藉与希望。在 《李玉兰还乡》的结尾,曹军庆也为李玉兰安排了一个 “善意的”归宿,至少有一个吴小栓这样的男人供她们依靠。虽然年轻人们大多离开了烟灯村,不过乡村并没有死去,而是凭借它坚韧的生命力存活着并且逐渐恢复生机。作家迟子建曾说: “当我的手苍老的时候,我相信文学的手依然会新鲜明媚。这双手会带给我们对青春永恒的遐想,对朴素生活的热爱,对磨难的超然态度,对荣誉的自省,对未来的憧憬。”⑭未来不只是一个 “着了火的鸟儿”,而是明日的太阳。温情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是带给人安宁和幸福的力量。就目前的文学创作现实而言,一些底层文学作家在刻画灰色现实时显得得心应手,却容易陷入 “为苦难而苦难”的窠臼,而忽略了历史的整体前进性。值得高兴的是,从曹军庆的近作中,我们看到了转变的可能,这也是他对于底层文学如何发展的一种启示。
在曹军庆笔下,乡村和乡村女性的善良或许是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一种可能。如小说 《魔气》中,同行尸走肉的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呈现出人性的温情。管素珍永远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贾文翠因为当过 “破鞋”被村人耻笑,后来又不计前嫌地用草药医治村人。曹军庆曾称 《魔气》是自己对以前的乡土写作的总结以及对童年生活的回望,“而这种总结和回望更像是一种告别和凭吊,乡村的两性世界构筑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底层人的生存图景与精神困境”⑮。曹军庆通过叙述乡村女性的境遇反映了乡村整体的状态,更揭示出现代人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曹军庆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需要曹军庆这样的作家们不断地探索和思考。
凭借叙述乡村女性和乡村的生存困境,曹军庆深刻探究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其成因,这种批判现代性的策略是对于现代主流文学主旨的一种呼应。因此,这颗 “沧海遗珠”尚需要仔细鉴赏。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以 “批判现代性”为主旨逐渐成为了文学的一种传统。曹军庆的作品无疑是对这个母题的有力呼应。曹军庆看到并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原因的复杂性,即一方是无处可归的废墟,另一方是前途渺茫的尘霾,最终导致了现代人的惴惴不安感。曹军庆试图给出他的回答,而这些答案不啻为一种承上启下的 “齿轮”。从这个意义上讲,曹军庆作品的内涵还需要读者们深入挖掘。另外,曹军庆笔下的当代乡村女性书写是人道主义式的,充满了同情与悲悯,他的作品对于女性主义文学、底层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注释:
① 晓苏、曹军庆:《普玄作品研讨会现场》,《长江丛刊》2017年第1期。
② 铁凝:《铁凝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③ 方方:《奔跑的火光》,《收获》2001年第5期。
④ 曹军庆:《风水宝地》,《天涯》2015年第6期。
⑤⑩ 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4页。
⑥ 曹军庆:《猪喜剧》,《长江文艺》2010年第3期。
⑦ 曹军庆:《李玉兰还乡》,《清明》2001年第3期。
⑧ 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北京文学》2001年第5期。
⑨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⑪ 曹军庆:《工厂村》,《北京文学》2012年第3期。
⑫蔡家园:《装置、恐惧以及现代性批判——略谈曹军庆的三部近作》,《长江丛刊》2017年第1期。
⑬ 刘川鄂:《曹军庆的手术刀》,《长江文艺》2003年第9期。
⑭ 迟子建:《在温暖中流逝的美》,《北京文学》2003年第7期。
⑮吴佳燕:《存在之困与精神之殇——读曹军庆长篇小说〈魔气〉》,《牡丹》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