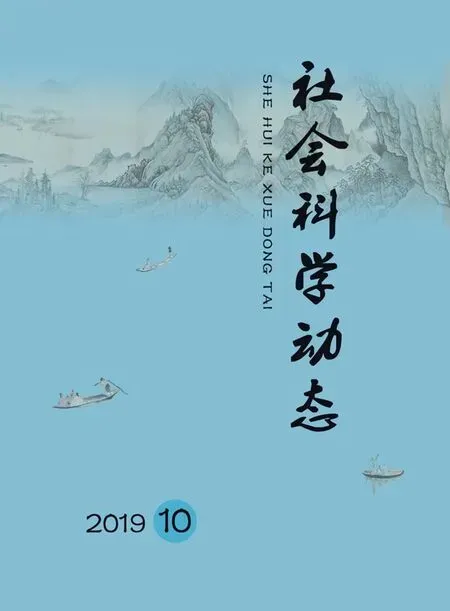吴兵入郢之战的进退军路线考辨
叶 植
一
定公四年(前506),蔡国联合吴国和唐国(下称联军)发动了一场“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①的灭楚之战,一路势如破竹攻占楚郢都及其国土中心地区。惯于远程外线征战、远较联军强大的楚国几近亡国。翌年,在秦救兵援助下才打败联军复国。对此役发生的路线与战地,学术界一直纷纭莫辨,笔者试就这一问题发表浅见,以就教于诸方家。
此役战前,面对已沿淮大举西进的入侵联军,楚国方面与吴军作战经验丰富的左司马沈尹戌胸有成竹地制定了纵敌深入、关门打狗、一举歼敌的作战计划:
由令尹子常率楚军主力沿汉江西岸巡防警戒,自己北出集结方城外楚军绕至淮汭毁掉吴军舟船,旋军抢占大隧、直辕、冥隘三关,切断吴军退路。其时,令尹子常率楚军主力跨过汉水,与沈尹戌部前后夹击,聚歼入侵联军。只要依此锦囊行事,楚军胜算很大。
然而,自知此战是由自己无耻贪婪所致的令尹子常心不自安,妄图通过自己统领的主力楚军单独打败联军,扭转其恶名昭彰的贪腐形象,遂置事先制定的作战方案于不顾,以所率楚军主力抢在沈尹戌前率先渡过汉水与联军仓促接战,不料首战受挫,退却中又先后落败于小别和大别,眼看单凭自己孤军不仅取胜无望,且有随时覆军之虞,遂退至柏举固守,期待沈尹戌回军再按原定作战计划与联军决战并战而胜之。或是识破子常计谋,吴王阖闾拒绝夫槩王向驻守柏举主力楚军发起强攻的请求,夫槩王却不顾军令,于十一月庚午,仅率所属5000先锋军强行突袭楚军。憎恨子常、失去斗志的楚军当即被冲垮溃散,无力回天的子常弃军逃往郑国。联军没有给楚军任何喘息机会,乘胜向郢都方向追击进军,接连在清发、雍澨打败本已土崩的楚军余部,抢渡汉水,仅用10天时间就一举攻占郢都。期间,匆忙从息县回援的沈尹戌偏军,虽在雍澨追上联军,但楚军大势已去,沈尹戌力战三阵殉国。
对这次吴军进军路线和几场大战战场所在地,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发轫于《水经注》,经《元和郡县志》 《太平寰宇记》 《舆地纪胜》 《方舆胜览》等唐宋地理名著轮番解读与补充的传统观点认为,此战发生在从鄂东举水流域至鄂中江陵的长江北岸。加上陈陈相因的明清学者递相祖述,使这一观点日趋丰满完整。尽管该说仍存在着柏举、大别、小别在麻城还是在黄州、汉口、汉川的区别,要皆都在长江北岸沿线,推定的战争经过大致是:
吴军自安徽寿县之淮汭上岸,会合蔡、唐军,从义阳三关进至今安陆城东章山(豫章)与楚军形成夹汉对峙之势,然后西进,途中遭遇提前渡汉东进的楚军主力,将其打败。受挫楚军南撤至汉水以南长江北岸之汉阳甑山(小别)时再败于联军,东退百余里又三败于汉阳龟山(大别),遂再涉汉水东奔两百余里,与联军决战于长江北岸举水之滨、地点不能指实的柏举。持柏举在麻城东北柏子山与举水间、大别为麻城东南六十余里龟山论者认为,楚军受挫于安陆章山、汉阳甑山和麻城龟山后,于柏子山与举水上游一带同联军决战,溃败后子常弃军逃往郑国,失去主帅的溃军一路西奔六、七百里至安陆西石门山下的清水(涢水的一段),半渡时被尾追而至的联军再次击败。接着,联军于追击途中将西逃楚军余部在京山西南(一说在汉川南)的雍澨彻底击溃,同时大败从淮河新息回援的沈尹戌偏军,抢渡汉水,进占位于江陵北十里的郢都。对于翌年六月秦、楚军反击与联军退军路线等,相关学者并未作过多涉及,似乎是从淮河上游的稷(河南桐柏)、沂(河南正阳)沿淮撤回。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于当时的地理环境、战线长度、后勤保障,楚军事先制定的作战方案等皆相扞格,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违于常识。
其一,该路线和主战场几乎都在长江北岸河湖纵横、水网密布、碍难进行大规模连续作战之蛮荒地,单凭700多年后曹操从赤壁撤军,途经秦汉时业已干涸的云梦泽时之窘况即可得出否定结论。
其二,长江北岸沿线明显与楚军制定的两军夹击联军的预设战场地理环境不符。而且,一再失利的楚军只会向郢都方向边打边退,决不会反向逃至人烟稀少、离郢都千里之遥的鄂东北地区②。对阵双方皆不可能战不旋踵以急行军状态三跨汉江,两渡涢水、滠水(武口水)、倒水(西归水)、举水及众多的湖陂沼泽等重重险阻,从鄂中战至鄂东北,然后回头一气攻入郢都。
其三,唐军从哪里与吴、蔡军会合?迎着敌军兵锋,令尹子常如何于激战中逃往千里之遥的郑国?楚昭王一行如何于联军入郢前一天,冲着从郧公邑、竟陵至郢都大道西进的联军从容逸入云中的郧公邑,再由云中安然逃往随国?
其四,次年,秦、楚军反击联军时,不仅没有穿越郢都等楚国腹心地区,连汉水都没有沾上边。双方首战之稷、沂地如在所谓的河南桐柏、正阳,战前联军岂不已惊猿脱兔,先行逃遁至桐柏山北的淮河上游地区?事实却是,吴军仍在楚境内的沂、军祥、唐、雍澨、麇、公壻之谿等地与秦楚军有过约三个月的持久鏖战,若非越国乘机入吴,夫槩王又率军归国自立为吴王,阖庐被迫匆匆归国御敌和平叛,尚不知秦、楚军与联军将在楚境战至何时,甚至胜败难测。全由车兵组成的秦楚军如何快速通过河流纵横、湖沼密布的淮河与唐河上游分水岭山地。
其五,联军既然已远遁至鄂东柏举等地,楚国复国任务已算基本完成,秦、楚军根本没有可能和必要对穷寇长途追击作战,也无暇于进军途中顺手灭掉远离作战路线的唐国。
此说可商榷之处尚多,兹不一一列举。而且,清华简《楚居》篇已经坐实此时的楚郢都在宜城西南的鄢郢③,传统说法的根基被进一步动摇。
当代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力证联军系经潢川、固始间陆路,“西南取桐柏大别间山势低薄地带,达举水上游,循举水西南行,与渡汉之楚军相角逐,最后柏举一役,而胜负大定”。并以此役作为先秦时该道已开通之证。④实则《名胜志》早作是解⑤,其说虽较陈说理正,然仍不能冰释上述诸疑,也没有解释从息县回救之沈尹戌军是如何赶至雍澨追上吴军,史籍亦无先秦此道已开通之其他实例。鄂东北地域广大,汉武帝设置江夏郡⑥时其人口尚较四围之郡少得多⑦,举水流域迄今并未发现春秋时遗存,战国遗迹尚属稀见,始创于南朝的阴山、穆陵诸关,明系分裂时期南北对峙产物,持久的抗金、抗元战争又使这些关隘的影响更为扩大,凡此,其说不立甚明。当然,陈说向不乏异议者,如《湖广通志》载:
黄冈县柳子港即古举水,《春秋》所谓柏举是也。《元和志》又谓麻城东南六十里有龟头山,春秋时楚战于柏举即此……今豫章即德安治东之章山,大隧、冥阨者,孝感之黄岘、南阳之平靖二关也。吴既因唐、蔡而来,则其入必由此关,故司马戌欲断其归路而击之耳。详其兵势,皆在西北,不当绕出东南,且自豫章与楚夹汉,则柏举战地虽不可考,大约在德
安、平靖之间,与黄麻无涉。⑧
质疑理据皎然,陈述却无足采,解惑更无凿证可凭,自不能达致主流认可,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纳此说当属无奈之举。
首先打破陈说的是钱穆先生。钱先生据《水经注》淯水旁有“豫章大陂”推定,吴自豫章与楚夹汉以及此前吴楚7次争战的古豫章皆在河南新野附近、淯水旁的豫章,惜未加申说。⑨钱先生将春秋所见吴楚争战之豫章悉断于斯实有待商榷,但毕竟提出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新见。杨守敬、童书业诸先贤对陈说也多有质疑⑩,而真正凿破鸿蒙提出系统新说的是石泉先生,其著名论文《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力证吴蔡联军的进军路线是“先自本国乘船溯淮水西上,在蔡国境内登陆,会合蔡师,共同西进,越过楚方城南段的隘口(所谓“城口”)到达唐国,会合唐师,继续沿今唐河岸西进,自豫章大陂进到汉水北岸,与楚军夹汉对峙。然后楚令尹子常率大军渡过汉水,在汉东(偏北)的小别、大别向吴反攻,双方随即于大别西北的柏举展开决战,楚师大败,向清发(今清河)溃退;被吴师追及,又败;南退至汉水北岸的雍澨(今樊城),又败。于是吴师渡汉水南下,迅速攻陷楚郢都。”为此,他将春秋时期的唐国考订在“今唐县南境,自县城南至湖阳镇之间的唐河以东地”,否定《水经注》等地理名著所载之随枣走廊中部说。将刘秀的故乡考订到今南阳“南阳县瓦店南,近新野县界”,而不是枣阳东南的吴店镇,将冥阨定在“今确山县西与泌阳县东的长城山丘陵地的一个隘口”,大隧、直辕在其附近,对沿途涉及地名大多予以新解⑪,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观点,将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学术界所重视。但详加考察,其矛盾冲突处亦多,如绕道方城前往淮汭的沈尹戌偏军,如何完全避开沿淮西进的联军并不走漏风声?柏举溃败,令尹子常怎么能迎着联军的长蛇阵逃往郑国?南阳盆地南部四通八达,明显与楚军制定的两头夹击吴军的预设战场地理环境不符;吴军主力、包括受到重创的夫槩王先锋军如何安全有序地从敌军的进攻方向撤退归国等,致其考难成定说。
二
受几位前辈大家研究和近些年成批涌现的考古新材料及研究成果启发,笔者认为,此役吴楚军的进退军路线与主战场都发生在从襄阳通往淮泗地区的楚东津道上,已有详文专述。为此,我们仍不妨将《左传》所载该战役的相关内容摘录如次:
(定公四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 既谋而行……
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槩王晨请于阖庐……弗许……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
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槩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三战皆伤……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奔郧……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吴人乃退……。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
(定公五年夏),越入吴,吴在楚也。
(六月),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槩王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夫槩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壻之谿,吴师大败,吴子乃归。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洩。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
(十月) 楚子入于郢。⑫上述记载有如下关键点:
(1) 是役,吴、蔡、唐、楚皆动用了倾国之师,加上救援的秦军,对阵双方总兵力至少在20万以上。⑬
(2)沈尹戌如此有把握快速完成对联军的迂回包抄,表明其时的郢都离方城、淮域不远,联军所走路线不会是南阳盆地,而且楚军对联军的进军路线、可能渡汉的河段与渡口了然于胸,需要重兵防控的地域并不多。
(3) 尽管一时附属国众叛亲离,内部矛盾重重,主帅恶名昭彰,但楚国的综合实力、声威与影响仍远胜联军。虽然吴王⑭和蔡侯皆有灭楚之志,验之此前吴楚之间的经年屡战,不过是彼此蚕食寸进,不难想象,吴伐楚的初始目标未必是攻入郢都,若非楚军一再溃败,吴军断不敢轻入关内。纵使攻占郢郊,吴军中仍不乏因恐惧而以自杀方式谏阖闾撤军的将军便是明证。⑮
(4)吴、蔡大军从淮汭舍舟登岸,沿淮河南岸大摇大摆朝楚境杀奔而来,征之楚军之纵敌深入战略,势力单薄之沿途楚邑只能婴城固守。吴军舍舟之地必在蔡境,否则淮域诸邑楚军虽不足以阻挡吴、蔡大军进兵,毁其屯舟的能力应绰绰有余。
(5)战争的进退非常迅速,秦、楚以车兵对敌⑯,其行军道路必定宽畅,战场势必阔大。
(6)溃逃楚军与尾追之联军只有通过一个大型军事渡口,方有足够的舟楫如此迅速渡过已颇具寒意的汉江。
(7)联军进退军时在雍澨与楚军各交战一次,柏举决战时楚军大量将士阵亡麇中,当翌年吴军退避麇中时,楚军不顾麇中相藉的楚军骸骨火烧麇中,凿证联军的进退军路线、主战场几乎相同。
(8)翌年六月,秦救兵自西北与楚军会师南阳北部,由重集的楚军充任先锋向联军发起反击。联军则在稷、沂地迎战并遭败绩,且战且退中唐国被顺带轻松收拾,却未发生过收复汉水西南楚国腹地与郢都的战斗,吴、蔡军在战事不利时沿来路有序撤退归国,秦、楚军并未穷追,双方损失不大。
(9)吴军入郢前一天,仓惶出逃的楚昭王一行先后渡过雎水、江水和成臼水,躲入云梦泽中逃难并等待救援,因郧公斗辛之弟斗怀谋杀昭王,眼看着追兵又至,走投无路的昭王才不得不就近冒险逃往随国避难,尾追而至的吴军向随国索要未果。
(10)郢都失陷、昭王避难随国,子西冒充昭王在离柏举不远的脾洩组建临时政府,收聚流散,伺机复国。秦军抵达后,子西充当先锋向吴军发起反击,首战在军祥打败吴军。
凡此种种,当我们将这次战役的行军路线和主战场放到楚东津道上⑰加以考察时皆可豁然获解。
唐 唐位于枣阳南、涢水中游以北之两汉上唐乡,后魏曾于上唐乡东南溠水与水间置西县,南朝梁废西县为下溠戍,隋于戍治置唐城县,后世遂误认唐城县(今随县唐县镇)为唐国都邑所在。参诸《水经注·涢水》篇有关唐国地理位置的详细描述,枣阳南部的滚河及其支流清水应是春秋时期唐国的中心区域甚或是其都邑所在。⑱民国二年(1913)湖北讲授地图上标示的唐家店、唐家城⑲,俗称唐店、唐城,仍为当地知名聚落,东北距唐县镇及其相邻的唐王店直线距离仅约80里,其北面约40里的毛狗洞、段家湾、吴庄遗址和段营春秋初期墓地应是其核心地区,是唐封于斯地的重要依据。⑳吴店资山出土过2件“孟姬冶”簋,2件“阳飤生”簋盖和1件匜。㉑李零先生将楚地所出战国秦汉简牍中的阳字解读为唐㉒,清华简《系年》第十九章“秦异公命子蒲、子虎率师救楚,与楚师会,伐阳,县之”。㉓将唐写作阳是其凿证。“阳飤生”器当是一组唐国青铜器,乃唐宗室公子与公主“追孝于其辟君武公”的祭器,铭文中尊称之武公或许是《中觯》所载昭王南巡时的那位在位之君。昭王于唐(阳)举行盛大庆典无疑是唐国历史上最值得炫耀的大事。唐地位尊崇,《逸周书·王会解》载成周大会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尧舜后也。”于此不难概见,周王朝用曾、唐两国从南北二面将强大的鄂国压制在涢水中上游山地一角,或是西周后期逼反鄂侯御方并导致鄂国覆亡的重要原因。㉔
豫章 失解,《春秋》凡八见,杜预注“汉东江北地名”,于昭公十三年再注“在江北淮水南”,虽不得其详,但二者并非矛盾。后人解说纷纭,言其阔者,将汉东、皖西、淮南至赣北之地皆囊括其中;道其狭者,以安徽寿县、合肥间湖沼地属之;江南说者乃以后世之豫章凿凿言之。㉕形成淮南、汉东、江南三说。而以汉东安陆章山说占优。《舆地纪胜》称章山“在府东四十里,古人以为内方山,《左传》吴自豫章与楚夹汉,《图经》云:‘即今之章山也。’”并将李白写给时居豫章(今南昌)宗氏的《南流夜郞寄内》诗误解为写给时已故去的安陆许氏㉖,进而将《图经》所载之安陆章山解释为李白诗中的豫章相佐证㉗,成为其说之重要支撑。安陆章山北距黄岘、平靖二关不远,貌似有其合理之处,或许是其说得以流行的原由。
今按,此章山系《舆地纪胜》误将《汉书·地理志》所载竟陵之章山移花接木至安陆城东之槎山。竟陵章山因诸经史学家皆依班固将其释为《禹贡》之内方山而声名显赫。㉘王象之在同书卷29《荆门军》尚言:“章山,在长林县,《九域志》云即《禹贡》所谓内方也。”唐武德四年(621) 于其地置章山县,七年改属郢州,贞观年间改属荆州。㉙在隋统一前,南北两郢州并存数十年,西魏所置之郢州以钟祥为治所,元至元十五年(1278)升钟祥为安陆府,当是造成二者混淆的重要原因。殊不知此郢州非彼郢州,此安陆非彼安陆,此章山亦非彼章山,此章山在今湖北沙洋县汉水西岸之马良镇,安陆章山凿空昭然。㉚较《地理志》后刊之《元和郡县志》 《太平寰宇记》等将内方改注于汉川县南90里,目的是与《禹贡》“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相对应,系视汉阳龟山为大别以与之契合。至于解豫章为大木本属无稽,况枣阳东南山地亦不乏修竹巨木㉛,淯水流经之邓林更是珍稀林木之渊薮,其说无足论。从当时战争的态势看,豫章显然不是一座小山,而是一个与汉水大致平行、相距不远且较平缓的阔大地理空间。循此论证法,笔者以为,豫章不是始见于六朝《图经》之安陆章山,而是后汉帝乡之章陵。初元四年(前45),析封于零陵郡的第三代舂陵考侯仁请旨改封至蔡阳县白水、上唐二乡获元帝恩准,本应以故国为荣并生长于斯的光武帝却于建武六年(30)将携来之舂陵更名为章陵㉜,建武十八年(42) 令中郎将耿遵筑章陵城㉝,其得名时间远较妄定之安陆章山为早,地域更是大得多。建安二年(197),“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㉞随之荆州刺史、宗室刘表升章陵为郡,先后拜蒯越、黄射为章陵太守。㉟魏武平荆州,继以赵俨为章陵太守,《隶释》 《宝刻丛编》收录有《魏章陵太守吕君碑》。㊱
章陵位于平靖关通往东津的主干道上,与东津相距不过150里左右,吴、蔡联军于此会合位于上唐乡的唐军与楚夹汉而阵,较安陆之章山说理正得多。
耿遵所筑章陵城遗址及其北面刘秀先考南顿君墓至今完好保存在枣阳市吴店镇北六里的舂陵村东岗丘上,东南距郭家庙曾国墓地仅20余里,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东西北三面均可见城垣及护城河残迹,地表遗物丰富,城名依旧,为襄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水经注》载淯水流域先秦至六朝时大陂颇多,松子陂、六门堰、樊陂等皆是,豫章大陂大致位于襄州区东、枣阳西北一带㊲,该地地势低洼开阔,为唐河支流黄河、黑清河径流区,陂东之唐子山、唐子亭是该地汉以前隶上唐乡之标志㊳,故豫章大陂或可称之为章陵大陂。又《周礼·职方》以溠水为豫州之巨浸,郑玄、许慎俱正之为荆州浸㊴,或据《禹贡》以随枣走廊北半部先秦时原本为豫州地,证溠为豫州浸无错㊵,要皆以先秦时章陵南境之溠水径流区具豫章地貌特征,殆可称之为豫章欤?又,东魏于此一度置南豫州,后周曾于枣阳县南置过漳川县,与豫章皆或有某种渊源关系。㊶
小别、大别 不知属何种地理实体,其地望均不明确,论者皆认为别和龟有关之山,别乃龟,龟乃别,以别释龟未知何据却是其解读关键,当有其理据。㊷以此推之,小别或为浉河与界河交界处,始见于康熙元年(1662) “州东南五里,上有土垄,纵横有纹,首足昂伏,俨如巨龟”㊸的龟山,海拔仅160余米,俨然别之小者。乾隆十二年(1747),信阳知州张钺一首《龟山晴雪》使其跻身信阳八景之一。大别乃《荆州记》 《隋书》所载平靖关内之大龟山㊹,即前述《水经注》所言之大溃山(后雅化为大贵山,《大明一统志》雅化为高贵山,现讹为高桂山)㊺。定小别、大别于斯虽乏凿证,但以情理推之,胜旧说甚多。
城口 唐宋以来学者无不以六朝义阳三关之三个隘口之统称释之,自无足凭信,应是自信阳东北罗山石城山至随州广水之冥阨关之相邻一路三关隘口。㊻
柏举 《公羊传》作伯侣,《榖梁传》 《战国策》作伯举。柏举当在前汉蔡阳后汉章陵之白水乡、春秋早期曾国都邑所在的白水(《水经注·沔水》支流之洞水,今滚河)之滨。《吴太伯世家》称双方“夹水阵”㊼,其水只能是一条不十分宽阔的浅溪,柏举或为白渚之音讹。东赵湖东仅里余的九连墩墓群及其周围的众多大型遗址和墓地足证入楚后,白水上游地区因其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而递变为楚国的重要封邑与军事重镇。武丁时三条卜辞揭示举可能是商武丁南征的舆。《合集》6667:“贞,令望乘众与途虎方?十一月。”《合集》5504:“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合集》5512:“乙未卜……宰立事……右比我,比舆,左比(曾) ……十二月。”这个位于商王朝虎方、与“曾”“我”两地相邻的“舆”,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柏举的“举”,二字形近易讹易误。
乡一直是县下最高一级基层行政区,乡里为秦汉基层政权的基本架构,故白水乡的建制当不晚于汉初。鉴于随枣走廊一直是楚的重点经营地区,楚又是较早实行县乡制度的诸侯国,白水乡于春秋时或已设立并非不可能,其存在远较鄂东当时与楚国几乎没有多少联系的举水、柏子山为早,与楚都的里程近得多则是毋庸质疑的。柏子山得名于“唐虚应禅师立寺于上,种柏百株”㊽的传说,源自曹学佺仅以“柏举之名盖合柏山、举水而得”言而将柏举之战地定于麻城柏子山与举水之间未免太过轻率。
清发 吴店西南十余里有一条自南向北流入白水的溪流——清水,清水两岸夷敞开阔,是唐国的中心区域,隋唐时设立过以清水命名的清潭县㊾,县治清潭店位于清水上游,一直为当地名镇,北距舂陵城约60里。
脾氵曳 文献无征,泌、卑、比、折相通,折通新。㊿古籍中泄、洩常互相替代,世、曳、泄、洩相通[51],世又通筮、通射[52],是脾通比,洩通泄、谢、澨、新,脾洩可写作比泄、比澨、比谢、比新。笔者认为其地或在泌阳县南泄水入沘水至唐河县西谢水入沘水(汉棘阳城在此)至新都的百余里间,其地南距本文所考柏举战地不远,是柏举溃兵当时可去唯一相对安全地区,是子常逃往郑国必经之途,或是子常率败军溃逃至此后,子西等部分楚军将卒没有跟随其继续北奔,而是于此停驻下来,打出临时政府旗号,其地有多个楚国北方城邑或乡聚,也是重要的军事前线。《吕氏春秋》载:“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篾将而拒之……与荆人夹泚水而军……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篾。”泚水,《后汉书·光武本纪》作沘水,谓:“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李贤注:“沘水在今唐州沘阳县南。”[53]是指其发源之上游言之。《水经注》“泚水出泚阳东北太胡山,东南流迳其县南,泄水从南来注。(注)……昔汉光武破甄阜、梁丘赐于比水西,斩之于斯水也。比水又南,赵、醴二渠出焉。比水又西南流,谢水注之,水出谢城北,其源微小,至城渐大,城周回侧水,申伯之都邑,诗所谓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为谢阳侯,即其国也……城之西,旧棘阳县治,故亦谓之棘阳城也。谢水又东南迳新都县,左注比水。比水又西南流迳新都县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国志》以为新野之东乡,故新都者也。”[54]先秦两汉之谢邑、棘阳、新都皆位于比水侧,其地正位于随枣走廊进入南阳盆地的要道上,商周时就已是随枣走廊通往中原的要津,其地可随时与方城内外尚未沦陷的楚国郡县取得联系,相互支持,既有利于聚蓄力量组织反攻,断吴归路,又可震慑南边的随国,保护甚至随时营救身陷小邦的昭王。
麇 已见前述,乃脾洩至柏举区域内的一个重要地名,是柏举之战的主战场。昭王会合子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让子西在脾洩修筑麇城[55],显示的资讯似乎是,导致柏举决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系此前楚国在麇地的防卫设施不足。
雍氵筮 为雍水边的台地。澨乃“水陆相半,又无山源出处之所津途关路”。[56]雍水或为《左传·庄公十八年》之涌水[57],两汉蔡阳县的瀴水,《水经注》之洞水,宋以后之淳河。[58]古嘤、噰通用。《尔雅·释诂》:“噰噰,声音和也。”“噰噰”,李善注《文选·南都赋》引作“嘤嘤”。嘤从婴声,噰从雍声。婴是耕母影纽,雍(邕)是东母影纽,二字影纽双声,东、耕旁转,涌为东部用纽[59],三字古音相近,并可通假。瀴水发源于枣阳东南的瀴源山(亦称石鼓山、石虎山),西魏曾于此置瀴源县,大业初废,县治在枣阳县西南70里的瀴源店。[60]吴从政《襄沔记》:“瀴水源出石鼓山西,迳襄阳县界一百五十里入汉,不通船运”。[61]《方舆胜览》称:“瀴水出枣阳县,经襄阳县界”[62],当地仍保留着瀴水、瀴源店的旧称。两周时的楚王城遗址正位于瀴水西岸台地上,与雍澨的地理位置相合,其地东离白水乡约三舍路程,西向直通东津,直线距离不足百里,无疑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秦军于此击败吴军后顺手灭掉唐国乃理所当然事,《吴越春秋》谓“楚司马子乘、秦公子子蒲与吴王相守,私以间兵伐唐,灭之”[63],当更近情实并可与上述清华简《系年》文字印证。
稷 秦楚军反击联军首战地。《伍子胥传》“(秦)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兵于稷”。《集解》 《索引》谓楚郊外地名稷丘者[64],不得其详。顾栋高谓稷在“河南南阳府桐柏县境”[65]并为诸名宿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纳。桐柏偏离秦楚交通干道甚远,其时吴师并未逃遁而是在稷地迎战秦楚大军,其说不足据甚明。故稷只能于南阳盆地秦楚交通干道上求之。秦楚会师之地当在宛城或其附近之申地,乃申包胥籍居地,与脾洩相距不远,星散之楚诸路军齐集于此迎接秦军,充当先锋反攻联军,方合情理。故稷当宛城南的淯水旁,吴军必水陆两路沿淯水北上据险迎战。建武二年(26),刘秀遣征南大将军岑彭、吴汉率三万余人大军从南阳南征割据黎丘的秦丰,先夺取新野之黄邮聚南下[66],《郡国志》新野“有黄邮聚”,刘昭注“吴汉破秦丰地”。[67]哀帝曾“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68]此地或为稷地所在。
前汉末,下江兵曾盘踞劫掠于平靖关内石龙山至三钟山间的蒌谿[69]山地,后北上唐子乡大败新莽军,被刘纟寅招入麾下合兵刘秀进击棘阳、小长安、黄淳聚与宛城。[70]晋刘弘从南阳南下安陆平定张昌之乱,西魏进军安州,唐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出击经平靖进占随州的淮西李希烈叛军等大型军事行动的行军路线与吴楚之战的进退军路线几无二致,即其佐证。
沂 清华简作析,整理者认为此析并非豫西丹淅地区之楚析邑,而是宣公十一年“令尹蒍艾猎城沂”之沂,甚是。但他们采纳高士奇说将沂定于河南正阳则失之甚远[71],此盖与上述顾氏误定稷地于桐柏相匹配的缘故。近见魏栋先生将沂考定为今随州之淅河,力证稷在随州北部的小林、淮河、草店镇一带,秦楚军系从南阳顺淮源进军至此大败吴军,再从稷地南下至淅河之沂。[72]稷若果在小林一带,则吴蔡军只会顺淮河南岸东撤,焉有南下淅河之理?此凿空之论实于研究无补。
今按,沂,《战国策》 《淮南子》作浊[73],或是形近致讹,而沂、析本为一字,水名,是析、沂、浊乃同一地。《襄阳耆旧记》“楚王之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熊会贞断此浊水为斯役之沂水[74],良是。浊水即流经今樊城北、邓城南,东南向经邓塞南注入小清河之溪流,系邓城之母亲河。[75]邓是涿鹿之战中打败蚩尤所率东夷部落联盟的功勋部落,早期活动于因涿鹿山和源于该山之涿水而得名的河北省涿鹿及其不远的“邓之墟”一带。[76]《太平寰宇记》载:“涿水,源出(范阳) 县西土山下,东北流经县北五里,又东流注圣水。应劭注《汉书》:‘涿水出上谷涿鹿县。’水西入海。《土地十三州志》云:‘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为涿鹿河,其支入匈奴中者,谓之涿耶水’”。又称“(涿鹿)山下有涿鹿故城,涿水出焉。”[77]史籍中“涿”常写作“浊”。
涿鹿之战是邓国史诗中之辉煌篇章,邓城南侧离襄阳20里的七里河自先秦至两晋称浊水[78],其后亦称弱水、挠沟水、闹沟水,其名或由邓人从涿鹿带来。
沂城应位于沂水旁而得名,筑于春秋楚北侵陈、郑,东伐宋,灭舒蓼,盟吴、越,正当庄王开启霸业、邲之战之前夜,乃邓故都、楚邓县县治所在地,为楚国的战略大后方与前进基地,工程由楚令尹蒍艾猎亲自主持,大员分工负责,事先周密科学规划,足见沂城的建筑是一件对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79],其城应即是淯水以西沂水北岸唐宋以来率以邓城相称的邓城。联军以沂城为中心驻防,表明其时南阳盆地北部、丹淅和方城以外地区仍掌控在楚人手中,占领楚中心区域的联军则于沂、鄾(白河口西岸[80])、西陵、东津一线布防,依托沂城为中心抵御来自北方的反击,确保其侧翼尤其是东津的安全,为随时可能面临的撤退提供保障。《淮南子》称浊水之战是“以存楚国”[81]的关键之战,可见沂邑在楚国所具有的军事地位。
邓城沿浊水至邓塞一线最迟于春秋时起就一直是荆襄门户襄樊二城的外围防线。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79),大良造白起攻楚拔郢之前一年,先夺取汉江北岸的邓和西陵。[82]建武二年(26),刘秀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3万余大军南击略有12县割据于黎丘的秦丰,在夺取黄邮聚后被秦丰阻击于邓城一线数月不得进。[83]孙坚从南阳南下于这一带击败刘表将黄祖,然后抢渡汉水进击襄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水军于邓塞浮舟顺汉水入长江,企图乘战胜之威,逼降东吴。西晋末期,镇南将军、荆州刺史(治襄阳)刘弘离世,其子衰绖将准备拥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帝的府司马郭劢斩于浊水之滨。[84]东晋庾翼、南齐崔景慧都曾于此狙击北军。元军于这一线设置了围困襄樊二城达五年之久之12连城之安阳、邓城、鄾城、古城。[85]一直是襄阳汉水北岸的攻防要地。
《左传·哀公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86]此析应该就是鄾邑西北数里的沂而非丹淅地区之析,故将浊(沂)水定于邓城南侧之七里河于史有征,理据皎然。
襄阳樊城有不少伍子胥的故事,樊城西北隅两军屯传为伍子胥屯兵处[87],汉水最大的洲鱼梁洲亦称伍娘洲。[88]在邓城北侧发现一批战国楚墓打破一批春秋楚中型空墓的怪异现象[89],1976年在其东北蔡坡战国M12出土一把吴王夫差剑,M4出土蔡公子姬安缶、徐王义楚剑等吴、蔡、徐国青铜器[90],或与吴、楚之战有所关联。
公壻可作多种解读。晋灵公有位女婿称公壻池,公壻乃指国君之婿,与地名无关。这次大战中有伍子胥和申包胥两位楚国著名人物,《晋书·刘琨传》:“昔申胥不徇伯举,而成公壻之勋;伍员不从城父,而济入郢之庸。”[91]将公壻之战的胜利归功于申包胥。而胥亦可作伍子胥的省称,扬雄《羽猎赋》“饷屈原与彭、胥”,颜师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92]公通谷、雍、滚、甬、洞、宛。[93]淯水后世称宛水,白水,雍、甬、洞已见前述。谿, 《说文解字》:“山无所通者,从谷,奚声。”段注:“,各本作渎,今正。阜部曰:、通沟也。读若洞。古文作豄。”[94]《尔雅·释山》曰:“山豄无所通、谿。”《释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会曰渎。”[95]谿、谷字义并无太大的不同,系指小的河沟或山谷。是“公壻之谿”实亦“公壻谿(峪)”,亦可写作“洞(涌、澭、滚、宛)壻谿(峪)”,胡可为公壻之注?虽如此,笔者认为,东津道中的一段小河谷(道)特别值得关注。乾隆《襄阳府志》:“公羊峪距(襄阳)七十里”。[96]同治《襄阳县志》:“峪山即公羊峪地方,距城四十里。”“黄龙荡,亦公羊峪地方,距城六十里,随枣赴襄便道。”[97]黄龙垱和峪山分别为今襄阳城东40里和60里、襄州区的黄龙和峪山镇,是随枣走廊至襄阳的捷径,是楚东津至随枣走廊的关键路段,即今之淳河河谷,前述雍澨位于其东端,当是其要邑。峪山亦写作玉山,方志中最早见于天顺《襄阳郡志·山川》、万历《襄阳府志》[98],同治《襄阳县志·山川》谓“峪山,县东四十里,土石皆白,故又名玉山,山首临淳河”,其名古老无疑。“公羊峪”或亦“公壻谿”,诚如此,则吴军系在沂、雍澨、至麇、柏举百余里的东津道上与秦楚军对峙鏖战三月余,全力守卫着楚东津道,多次受挫后方于东津道从容撤退归国,秦楚军亦未发起穷追。
三
最后,让我们辨析一下昭王的逃亡路线。
杨守敬、童书业、石泉诸前辈已证昭王系从宜城平原的楚都济汉,渡过钟祥东南的臼水逸往云梦泽中的郧公邑[99],又随郧公莘辗转逃至随国,甚是。需稍加辨析的是,其时的郧公邑与随国地望所在。
郧是最早与楚发生关系并被楚灭国设县的诸侯小国。[100]楚封斗莘的郧公邑是昭王出奔的直接目的地。郧,《春秋·桓公十一年(前701)》杜注于江夏云杜县东南之郧城。《春秋分记》谓:“郧,复州沔阳县西北有汉云杜城,云杜东南有郧国城。”[101]是楚郧公邑在今云梦县东南天门县北或东北。《史记》三家注并主古郧国、楚郧(县) 邑在安陆。[102]《水经注》谓郧在巾水入汉水处对岸之竟陵大城,白起拔郢,“东至竟陵”之竟陵[103],地在今潜江西北多宝镇一带。通为安陆、天门北、潜江西北三说。《战国策》载白起“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104]《史记正义》谓“(竟陵)故城在郢州长寿县南百五十里,今复州亦是其地也。”[105]北大《里程简》载“竟陵到郧乡百廿里,郧乡到安陆百卅里”。“安陆到涢漰亭六十里”。如此,我们于江陵至江夏之竟陵与安陆段间的交通干线上,大致可以给郧公邑圈出一个较为可靠的地理区域。昭王系沿大洪山南、绿林山北的东西廊道奔往郧邑,天门皂市笑城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被人为分割为高家山、夏熊岭、凤凰嘴、钟家台、钟刘村、刘家河等十多个遗址,实际是一个以凤凰嘴为中心的大型聚落址,分布在一条南北长约5里、东西宽约3里的平岗上,下层有新石器晚期遗迹,其上为春秋至六朝地层,局部可采集到战国至两汉时的大量筒板瓦,其地正位于江陵至江夏的上古交通干线之上,当地文物工作者断此为春秋时郧国、楚郧公邑所在,然与《里程简》所载里距尚有不小差距,当循《里程简》所载里距进一步于笑城西北二三十里东西交通线上实地寻找,从此经出土过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大墓的漳河中下游至随国远较笑城近便,昭王逃亡路线的重重迷雾由此可立获通解。
上考若从大的方面庶几成立,吴兵入郢之战的路线、主战场所在地、昭王逃亡路线的来踪去迹都得以基本还原,揆情度理,所有的疑团皆获冰释且能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撑,与经过梳理后的较早文献亦能相互印证发明,姑备一说以待新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注释:
① 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卷4《阖闾内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② 鄂东北英山、罗田、麻城、红安、大悟、孝昌地区考古发现的楚文化遗迹极少,上限无早至春秋者,亦乏当地春秋时文献资料,据此可判定春秋时举水流域人口不多,开发水平不高。
③ 参见赵平安:《〈楚居〉“为郢”考》,《中国史研究》2012年4期;赵庆淼:《〈楚居〉“为郢”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3期;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1、190页。
④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6《河南淮南区·桐柏山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2—1967页。
⑤ 参见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9《楚下》“柏举”条,《四库全书》本;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6《湖广》“黄州府”,中华书局1993年本,第679、686页。
⑥ 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苏卫国:《西汉江夏郡沿革略考——从纪南松柏汉墓简牍说起》,《学术交流》2010年第5期。
⑦ 参见《汉书》卷28《地理志》。
⑧ 参见《湖广通志》卷118《杂纪志》“古举水”条。
⑨ 参见钱穆:《古豫章考》,载《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05—306页。
⑩ 参见童书业:《春秋楚郢都辨疑》,载《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7—219页。
⑪ 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416页。
⑫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42—1548页。
⑬ 《春秋》诸注家皆据《司马法》以75人为一乘,秦兵500乘为37500人。加楚、吴、蔡、唐四国之师,总兵力必不少于20万人。
⑭ 参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⑮ 参见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15《指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9页。
⑯ 从安州六器、《竹书纪年》等载昭王曾率倾国之师南巡,南阳盆地与随枣走廊间的交通必已十分发达。
⑰ 本文楚东津道系指从襄阳东南侧之楚东津过汉水,经滚河、淳河间的廊道进入随枣走廊,经平靖关进入至淮泗地区,见《楚东津道及相关问题考辨》,《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9期。
⑱ 参见《水经注疏》卷31《涢水》:经“涢水出蔡阳县”。注:“涢水东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东,北流注于涢,谓之小涢水,而乱流,东北迳上唐县故城南,本蔡阳之上唐乡,旧唐侯国。”《汉书·地理志》:“舂陵,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
⑲ 《湖北讲授地图》,民国二年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
⑳ 叶植:《毛狗洞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
㉑ 参见叶植:《襄樊市、谷城县馆藏青铜器》,《文物》1986年4期。
㉒㉓ 李零:《包山楚简研究》,载《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73页。
㉔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㉕ 《史记》卷40《楚世家》。
㉖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25《古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3-1194页。
㉗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77《德安府》安陆景物上“章山”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31-2532页。
㉘ 《史记》卷2《夏本纪》“内方至于大別”注;《水经注疏》卷28《沔水》。
㉙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江陵“长林”条。
㉚ 参见潘锡恩、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65《安陆府》“章山”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05页。
㉛ 参见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33《枣阳军》山川“资山”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87页。
㉜ 参见刘珍等著、吴树平注:《东观汉纪》卷1《世祖光武皇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下》。
㉝ 参见《后汉书》卷112《郡国志四》荆州南阳郡“章陵”条注引《古今注》。
㉞ 参见《三国志》卷1《武帝纪》。
㉟ 参见《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傅子》;《后汉书》卷80《祢衡传》;《三国志》卷1《武帝纪》;《三国志》卷23《赵俨传》。
㊱ 参见陈思:《宝刻丛编》卷3《京西南路·邓州》,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页。
㊲[74][78] 参见 《水经注疏》 卷31《淯水》。
㊳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10《南阳府》山川“唐子山”条。
㊴ 参见杨天宇:《周礼译注·夏官司马第四》“职方”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
㊵ 参见丁晏:《禹贡集释》卷2《荆州》,《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㊶ 参见《隋书》卷31《地理下》汉东郡“隋”条、“唐城”条。
㊷ 按,冥亦作鄳、黽,黽为其本字,蛙的一种,昂首方甲长尾,形似龟,易讹,或是释家皆以别为龟之故。又鱉、别为同目动物,声部韵部同,可通假,形体相近亦或是其解的原因。
㊸ 参见康熙《汝宁府志》卷2《舆地山川》信阳州“龟山”条。
㊹ 参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安陆郡“应山”条。《太平寰宇记》卷132《淮南道》安州应山县“大龟山”条并引《荆州记》。
㊺ 参见《大明一统志》卷61《德安府》山川“高贵山”条。
㊻ 参见叶植:《楚东津道及相关问题考辨》,《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9期。
㊼ 参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㊽ 参见《湖广通志》卷8《山川志》黄州府麻城县“柏子山”条。
㊾ 参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舂陵郡“清潭”条;《旧唐书》卷39《地理志·山南道五》隋州郡“枣阳县”条。
㊿[51][52][59][93] 张儒、刘毓庆: 《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07,492、623,614、623、567、320 页。
[53]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54] 《水经注疏》卷29《比水》。
[55] 参见白居易、孔传:《白孔六帖》卷9《城》“城麏”条,《四库全书》本。
[56] 参见傅寅:《禹贡说断》卷3“过三澨”条,《四库全书》本。
[57] 《春秋左传注·庄公十八年》。
[58]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2-2386页。笔者按:郦氏所载与后世的水道不合。其所言洞水上游(章陵、蔡阳县南)之白水、浕水、蔡水,后世称滚河,于襄州双沟之梁集流入淯水(唐白河)并未直接西流入汉。今峪山东的淳河(上游为瀴河)的地理位置、流向与郦氏洞水入汉地理位置相合。今滚河与淳河间有明显的分水岗垄,滚河后世改道入淯水的可能性似不大,或郦氏小误。然,东津至随枣走廊间,地势低平,《宋史·河渠志》记熙宁间襄阳知州史炤上疏谓“开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余顷,修治陂堰”,因滚河水量大,不能壅其水溉田,是否此次修渠时将滚河导入淯水,以便利用淳河水堰水溉田亦未可知。
[60] 参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舂陵郡;《大明一统志》卷60《襄阳府》山川“瀴源山”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0《襄阳府》山川“瀴源山”条。
[61]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0《襄阳府》山川“瀴水”条。
[62] 《方舆胜览》卷33《枣阳军》“瀴水”条。
[63] 《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
[64] 参见《史记》卷66《伍子胥传》。
[65] 参见《春秋大事表》卷6《附列国地名考异》,“晋、齐、楚、宋俱有稷地”条。
[66] 《后汉书》卷17《岑彭传》。
[67] 《后汉书》卷32《郡国志四·南阳郡》。
[68] 《汉书》卷99《王莽传》。
[69] 《后汉书》卷15《王常传》注引盛弘之《荆州记》:“石龙山,在应山东北二十五里。三钟山,在随县东北五十里。”《太平寰宇记》卷144《山南东道三》随县“三钟山”条:“三钟山在县东五十里,山有石,状如覆钟。”《舆地广记》亦有载。
[70] 参见《后汉书》卷14《齐王纟寅传》;《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上》;《后汉书》卷15《王常传》。
[71] 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十五章《系年》:“昭王归随,与吴人战于析。”整理者注25:“析,今河南西峡,在随州以北,楚与吴大战于此,似与当时形势不合,《左传》定公五年载,‘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槩王于沂。’简文‘析’应为‘沂’,在河南正阳。”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8《楚上》 (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73页)“沂”条:“臣谨按,定五年大败夫槩王于沂,即江国,在今汝宁真阳县境。”并见允礼、张廷玉等:《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卷29《宣公十一年》,《四库全书》本。
[72] 参见魏栋:《秦楚联军破吴之沂(析) 地考》,《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73] 参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14《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章》,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514页;刘文典著、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19《修务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3页。
[75] 唐白河(淯水) 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 改道于其东五里的龙坑入汉,邓塞位于樊城东团山南至小清河入汉处的唐白河故道西侧。参见《水经注疏》卷31《淯水》;《元和郡县志》卷21《山南道二》,襄州临汉县“邓塞故城”条。
[76] 参见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77] 参见《太平寰宇记》卷70《河北道十九》涿州范阳县“涿水”条;卷71《河北道二十》妫州怀戎县“涿鹿山”条。
[79] 参见《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一年》。
[80] 参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的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220、244页,西陵笔者另文专考。
[81] 参见《淮南鸿烈集解》卷19《修务训》。
[82] 《史记》卷5《秦本纪》谓“取鄢邓”、《史记》卷73《白起传》作“拔鄢、邓五城”;《资治通鉴》卷4《周纪四》,作“取鄢、邓、西陵”,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35页;西陵,据北大藏《里程简》在淯口上游12里,参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的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220、244页,
[83] 《后汉书》卷17《岑彭传》。
[84] 参见《晋书》卷66《刘弘传》。
[85] 乾隆《襄阳府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并见李贤等著《大明一统志》卷60《襄阳府》古迹“邓城条”,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0页。
[86] 《春秋左传注·哀公十八年》。
[87] 参见《大明一统志》卷60《襄阳府》古迹“邓城”条。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樊城”条。
[88] 见乾隆《襄阳府志》襄阳县图。
[89] 笔者就本文写作拜访了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刚、刘江声两位先生,他们告诉笔者,在邓城北里余的南岗、汴营一带发现一批战国楚墓打破同为楚人的一批春秋中型空墓(大多未作清理),春秋墓应为当时外人所破坏,认为或与吴兵入楚之战有关。
[90]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汉汉考古》1985年第1期。
[91]《晋书》卷62《刘琨传》。
[92] 《汉书》卷87《扬雄传上》。
[94]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0页。
[9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96] 乾隆《襄阳府志》卷11《乡镇》“公羊峪”条。
[97] 同治《襄阳县志》卷1《乡镇》。
[98] 见天顺《襄阳郡志》卷1《山川》“襄阳县”“玉山”条。万历《襄阳府志》卷6《山川》“襄阳县”“玉山”条,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98页。
[99] 参见杨守敬:《沮漳水考》,载《晦明轩稿》,光绪辛丑(1901)邻苏园自刊本,第72页。
[100] 参见《春秋左传注·桓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注·宣公四年》。
[101] 程公说:《春秋分记》卷31《疆理书》,《四库全书》本。
[102] 《史记》卷66《伍子胥传》“王走郧”注;《史记》卷40《楚世家》“王走郧”注;《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奔郧”注。
[103] 《史记》卷73《白起传》。
[104] 《战国策新校注》卷33《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章》。